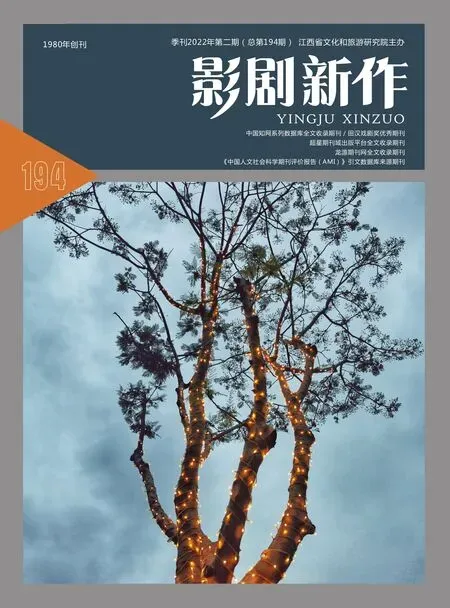论《战马》的剧场艺术
刘 丽
2007年,尼克·斯塔福德(Nick Stafford)将迈克尔·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创作的儿童小说《战马》(1982)改编成舞台剧,英国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以下简称“NT”)将其搬上舞台。该剧融合话剧、木偶剧、音乐剧等元素,目前在全球演出超过4000场,英语版之外,还有德语、荷兰语版的演出。2014年4月23日,中国国家话剧院(以下简称“国话”)与“NT”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战马》成为中英戏剧战略合作的第一部作品,2015年9月4日中文版《战马》于“国话”大剧场首演后,连续4年在“国话”驻场演出,并巡演至上海、广州、天津、西安、哈尔滨、石家庄、重庆等城市,累计达300余场,所到之处引起轰动,形成一种特有的“《战马》现象”。作为创意文化产业的一种,继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同名电影之后,中文版再度挖掘了《战马》的商业价值。“创意(创造性)产业是个大生意。……作为一种创意(创造性)产业的艺术的观念突破了原先艺术家的创造性或独创性的藩篱,它既包括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独特的灵感、妙悟、神思、意念,也包括将独特的创意与人分享——出售、营销、供人消费,实现其价值的流通方式。”《战马》演出的成功,得益于商业与技术、商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但不容否认的是,核心仍在于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如果说戏偶制作、舞美设计以及表演艺术是该剧的形式、外壳,而支撑这外壳并使之岿然站立的,乃是人与马、马与马、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内在精神,以及鲜明的反战主题。本文在论及上述问题时,兼对中文版与NT版之异同做一比较分析。
一、戏偶:精密设计与艺术呈现
《战马》除了使用马偶之外,还有鸽子、秃鹫、坦克、大白鹅、士兵等,演员用手或者身体撑起戏偶的骨架,灯光打在镂空的骨架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质感美。当然,剧中的主要角色是红马乔伊。当乔伊从一匹活泼、灵动的小马,一跃冲出幕布,灯光暗下,成年偶奋蹄出场,前蹄高高扬起,那一种威风凛凛的气势,带来不期然出现的惊喜感。乔伊幼年偶由三人操控,因体形较小,操控马头的演员尚能直立身躯,操控前腿的演员,则全程弯着腰在行走,还要注意不遮挡观众的视线,控制后腿的演员在走动的同时,不时要撩动马尾;成年偶则由一位木偶演员站在马头旁操控马偶,控制方向、耳朵转动以及模拟马的情感发出各种嘶鸣声音,两位木偶演员站在马偶的“肚腹”(骨架)里,操纵马偶的四肢,一人操控前腿,一人操控后腿,共同承担马身的重量。马偶由无数零件手工制作而成,几乎每个关节都可以活动,其灵巧程度并不逊色于真马:喝水、吃草料、昂首嘶鸣、奔跑,抿耳、高昂或低垂脖子、摆动尾巴,呼吸的节奏、变化的鼻息、行走的步调、站立时的弯腿、身体的起伏,以至于活灵活现的眼神,情感表现丰富。细节上,马偶的表现几近于完美,甚至在某些场景比人的表演都更为细腻、传神,与马偶演员精湛的口技、训练有素的表演相融合,共同创造出一匹饱含生命力的“活马”。
乔伊初露面时,操控的木偶演员多少令观众会有一些不适感,但随着演出的进行,戏剧假定性会让观众接受这样一匹鲜活的“马”,逐渐忽略马偶演员的存在,而专注于乔伊的“表演”本身。阿尔伯特骑在成年乔伊的背上纵横驰骋时,乔伊年轻、健壮、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乔伊和战马界“大佬”汤普森角力的戏码,也生动无比。角力伊始,两匹马彼此观察,等待时机,关键时节甚至使用了慢镜头动作,最终,汤普森后腿奋力一踢,乔伊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愿赌服输。不打不相识,战场上的乔伊与汤普森建立了友谊,为保护汤普森,乔伊主动去拉大炮,并在行动上影响了汤普森;当汤普森筋疲力竭,与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乔伊在其用力摆首、蹬足的微妙动作中,让观众看到了它的善良、忠诚与勇敢,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无言控诉着战争的残酷,那鲜明的同理心并不弱于人类的情感。
马偶中有“完整”的马,也有“残缺”的马。在乔伊和汤普森冲锋陷阵时,后面4匹只有头、身却没有腿的马,每一匹由一个演员撑起马身,半隐藏于背景中,就像速写时虚化的那些轮廓线;马背上坐着的“兵”,也是机械偶,多是左手持刀指向天空,但舞台前部的真人都是右手持刀,为增加表演的逼真度,操控人偶的演员利用机关,令人偶互相击剑。“士兵们”前仰后合的动作,颇似“醉酒”,渲染紧张气氛的同时,也缓解了场上紧张气氛。
戏偶在舞台上的生动呈现,源自于NT的精密设计与科学研发。《战马》中仅马偶的研发便耗费了5年时间,NT有专门用来做舞台技术研发的工作室,每一年剧院会拨给每个项目去做表演工作坊或技术研究,再由艺术委员会论证、评选出较为成熟的项目,继续研发并促其走向成熟。《战马》是从这些研发项目里遴选出来的,从两人扛一条条凳开始实验木偶的表演。中方导演之一刘丹说:“我相信5年当中一定不是每隔一年便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肯定不是这样的。剧院给艺术家时间做实验,实验的结果一定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因为这是艺术,……艺术是每天都会觉得这件事有可能做不成,但是我们可以再努一把力。我们一定是把所有的弯路都走过了,才有可能去说:‘也许……大概我们是对的’。”正是源于这样严谨、细致的设计与打磨,奠定了《战马》成功的基础。
二、舞美:力量与诗意并存
《战马》的舞美设计,分寸之间拿捏得很到位,地板做了人性化设计,有弹性,目的是保护演员的膝盖,舞台融化在戏剧演出形象之中,舞美设计在整场戏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散发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大幕拉开,随着灯光暗去,画布上出现静谧的旷野,群鸟飞过,小马乔伊若隐若现,民谣歌者从后方走出,质朴的歌声令观众屏息。现场并没有拟真布景,只需三两小道具,灯光投下,时空即刻扭转。仅有的一次换幕(中场休息),除了剧终战马被升起,为构建两层舞台的高低差使用了电动升台,全剧没有使用音乐剧常见的电动布景更换装置。整场戏中,布景(撕下来的那一角素描)起到重要的作用:一块不规则投影幕布吊挂在舞台中央上空,与阿尔伯特从素描本上撕下的乔伊画像那张小纸条相呼应,透过灯光的作用,边缘的撕口清晰可见,似乎象征着被战争撕裂的伤口,烘托、渲染着剧情。绘景师受未来主义、涡旋主义和表现主义画派的影响,画出那些凌乱破碎的环境,更多地表现了士兵个人对战争的体验与感受,从速写本上撕下画稿的想法便是从这里产生,小阿尔伯特带着它上的战场。演出时,屏幕上根据剧情表现出不同的场景,比如显示每一幕发生的时间,有“1914”“1918”等不同的年代,也有“德文郡”等剧情发生地的字样。光从屏幕后面打下来,整个舞台就像一幅油画,既有欧洲乡间的质朴,又有战场上的惨烈。在这个“伤口”上,既有千军万马或炮弹横飞的投影,也有血染苍穹、田园摧毁的画面,屏幕主要负责大远景,屏幕下方的舞台负责近景,反战的主旨相当清晰。
场上布景极其简约,一道小门、一扇小窗,构成阿尔伯特家的小农场;一辆推车便成掩体;两条木棍,便是小桥;四根木条一拦,就成了拍卖场地;木条两长两短搭起来,成了阿尔伯特家的马厩;阿尔伯特骑着去战场的自行车,与歌唱春天的小鸟、啃噬尸体的秃鹫、蹒跚傲娇的大白鹅、凌乱残缺的战马、你一言我一语的邻里一起,非但没有弱化戏剧性,反而灵活机动,既节省了换幕时间,也衬托出台上人物与鸟兽的生命力。
灯光是舞台上的灵魂之一。当战争来临,屏幕上出现的白云、土地等田园牧歌叙事渐行渐远,舞台上取而代之的是战争、死亡的惨烈与揪心,冷光取代了和平时期的暖光:或者衬托阵亡士兵高大剪影的背光,或者在炮弹轰炸声、枪声里裹挟着刺眼的道道白光,以及滚动的人影表现危机四伏的陷阱,与灰蒙蒙的烟雾一起,合成一场明暗变幻、层次分明的“灯光秀”,当舞台上出现不断死去的士兵、倒下的战马,无需对白,对于生命、死亡、信仰,令人有了新的认知,观众席上甚至有孩子哭得很大声。如第一幕,拍卖乔伊的群戏那一场,小马乔伊被围住,舞台光打开的时候,集中在小马身上,都是高角的灯光,温暖明亮,为的是能够使观众感受到德文郡的漫漫炎夏和那里独特的景色、空间,之后舞台渐亮,人声慢慢嘈杂起来,拍卖师站在中间,两边构图对称,德文郡小镇上的男女老幼交头接耳,泰德和阿瑟站在两边竞价,异常热闹。随后,随着情节的推进,从德文郡乡下的美景,转入地狱般的一战现场。当场景转到战场时,灯光会突然以一种非常非常低而且不停变换的角度,利用幕布后的空间打过来,射向观众,令其感同身受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征兵那场,每次胶片照相机闪光灯一亮,冒出一股白烟,全场所有人都静止了,既像是内心独白,又给观众造成错觉,似乎被拍摄者真的定格成了一张黑白照片,只有追光下的人物继续表演,这样的设计相当巧妙。
此外,《战马》的每一个道具都非常考究。阿尔伯特手中拿的画册,几乎每一页都有风景画,那是Nicholls最初的作品。1914年的德文郡乡下,小幅的乡村景物和写生小品,他画出了乔伊和阿尔伯特在山丘上飞驰的场景,而夜幕笼罩下的原野,似乎在预示着战争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绘景师创作时,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是不是应该这样画?”他们撕下画稿,放在剧院的模型箱里,就有了一朵美丽的云彩,或者一处风景,或者一条裂缝,试图为观众呈现截然不同的观剧体验。其他如酒壶精细到经得起蒙太奇般的特写镜头,甚至可以看到上面清晰的磕痕,包括触摸到酒壶旋盖的质感。犁具、套轭、枪支、匕首、军服、望远镜、挎包、皮带、伤兵偶等,道具的细节不是做给观众看的,而是为演员的表演做支撑。
《战马》在最为空旷简陋的舞台上拉开帷幕,没有布景板,没有借助高科技手段频繁换景,但在这“贫困”的舞台上,却蕴含着无限的力量与诗意,“《战马》的舞台设计通过对投影景的综合运用,布景元素中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也有象征主义的成分,甚至还有表现主义的成分。传统的与现代的、手绘的与电脑合成的,各种成分互相渗透、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这个综合而完整的史诗般的舞台空间。”清新质朴的民谣,令观众在残酷的战争情境里,想到开场时平和、安详的田园牧歌场景,增加了剧场的空灵美感,从头顶打下的晕黄色灯光,使歌者看起来如同天使,声音宛如天籁。这样的场景令人倍加怀念和平时期的温馨时光。
三、表演:人偶合一的戏剧假定性
戏剧性主要来源于戏剧的假定性,这种假定性与情境预设、人物装扮等关系密切。《战马》的人偶合一,使得生活的真实在戏剧的假定性中得到了体现。中方导演之一王婷婷说:“木偶演员十分珍贵,他们不仅要有运动员的身体、演员的头脑,还需要长期在一起磨合协作。一匹马三个人要靠一个思想、一个呼吸来完成复杂的木偶动作,创造逼真的战马形象。”思考和感受一匹马的动作、情感,共同操作木偶的人真正沟通的唯一方式,便是通过呼吸,以团队的形式工作。据刘晓邑导演说,中文版木偶演员的遴选相当严格,自2014年演员招募工作启动,中方导演组从1500份简历中挑选出80余人,英方导演甄选后,以一周的体能训练、配合训练和偶的训练,筛选出18名,再经过一年半的系统训练才能走上舞台。而这些演员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演出一年结束后,多半都会有伤病,然后再重新遴选演员,训练之后再走上舞台。刘晓邑本人也曾是操纵乔伊和汤普森马头的木偶演员,肩膀、膝盖、腰部有不同程度的伤病。乔伊重达108斤,汤普森130斤,在演出过程中,骑“马”的演员也有一定的重量,“这些重量几乎都压在马的前腿位置上。在正式演出中每一次战马的出场都是经过精细的时间考量的,剧组聘请心理辅导师测算出演员在幽闭的马偶空间里不宜超过十五分钟,极限是半个小时。演出中途木偶演员必须出来透透气、补充水分、缓和情绪。”
马应该是“马”、是“动物”,不应该像人一样“守规矩”,应该充分展现出动物性,它们的动作又是随意性的,难以控制。但在舞台上,乔伊是有思维、有情感的动物,它与黑马汤普森曾有争夺权威地位的决战,但在套轭拉大炮时,它给汤普森做了良好的示范,得以在战争中残存生命;当汤普森在战场上倒下的时候,“兔死狐悲”的悲悯情怀,在乔伊的眼神、动作里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汤普森筋疲力尽倒在了战场,坦克出现在舞台上,德军溃败,胜利在即,铁丝网却困住了乔伊。在隆隆的炮弹声中,它一次次尝试自救,7个人操控一匹马,发出悲戚的呜鸣,就在命悬一线之际,英法军队同时发现了它,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了乔伊归属英军,一起回到医院,眼睛被催泪瓦斯喷伤住院的阿尔伯特,以熟悉的口哨声唤醒了它的记忆,他们终于团聚了,重归故里。乔伊是一匹被赋予人类生命情感的战马,让观众在观看中共情,并带着理性思考走出剧场:谁发动并受益于战争?每一个生命个体是否都应该被尊重,比如一个人、一匹马、一只鹅?
全场比较出众的还有大白鹅,木偶师全身并无遮挡,但观众的视线也都在鹅的身上。大白鹅总在剧情紧张的时候出来缓解气氛,因不受理智、道德的社会约束,恰可以把内心情感如傲慢、愤怒等随心所欲地释放出来,它在自家的悠闲、傲娇,对比利、泰德的飞身痛啄,既抢镜又带来笑点,而操控者的不动声色与沉稳,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敬业心。不同的是,其他偶的操控者戴着整体划一的呢帽,大白鹅操控者戴一顶有圆球的棉帽,与大白鹅带来的喜剧效果很搭配。再如,艾米莉教德国骑兵队长说法语时,意即保证乔伊和汤普森不再受到战争的伤害,前接阿尔伯特在战场上请战友大卫给妈妈写信,阿尔伯特、大卫站在舞台右侧,妈妈站在舞台左侧,艾米莉和德国骑兵队长在舞台中后区,三个区域呈三角形,各亮起一束黄色的光,三个空间交错,靠灯光转换场景,即便演员处在不是自己表演的空间里,也表现得相当投入。艾米莉这条线铺垫得很成功,相关演员的表演都很真实,自然而然地把感情推向了高潮。
此外,“在每场演出前,剧组的全体演员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因为这部戏的演出相当于一场运动赛事。……在演出前还有一个必须完成的工作是‘安全测试’,就是将这部戏里十几个的较为关键的技术点,比如说马踢人、阿尔伯特上马、拿鞭子抽马、两匹马角力等环节预先演练一遍,四年来从未遗漏过一次,因为这跟演员的安全紧密相关。”正是演员这种敬业和彼此的默契配合,才成就一台好戏,给观众留下美好的观剧体验。
四、异同:中文版与NT版之比较
中文版《战马》质量与英文版齐平,甚至略高于原版,但由于是移植演出,中文版《战马》在文本翻译和情节设计上,多少会有些南橘北枳般的“水土不服”,在台词翻译及情节处理上,与NT版显然有一些差异。
在“文本翻译”上,把英方舞台文学本转换成适合中方演员表演的演出本,最终找到适合在中国演出的表达,并不容易。很多翻译(包括歌词)非常到位,如Rose说,If ya hear strange noises from the house, don't worry, it's me killing your father,此处意译为“收拾你爸”很自然,现场一片笑声。但中文版也有一些处理比较生硬,比如乔伊的取名,阿尔伯特一开始使用了“大侠”和“神驹”,后来直接转变成“乔伊”,这个转折明显牵强。还有,战场上的阿尔伯特给妈妈写信时,想称赞她“你是一个好妈妈”,他想用法语表达“好”字,中文版变成了“你是一个棒妈妈”,虽然“棒”与法语里的“Bon” 接近,但妈妈说自己看不懂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也有部分台词在英文里听着顺耳,译成中文就有了隔膜。比如“Good boy, Joey.”翻译成“好小子,乔伊。”固然没错,但如果说“太棒了!”或者“棒呆了!”似乎更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尤其当这类台词重复多遍后,听起来会觉得别扭。再如,战场上涉及英军、法军、德军,多种语言交织,在NT舞台上以英语、法语、德语进行对话,节奏是顺畅的,没有滞涩之感,“翻译成中文后,导演组考虑过要不要用方言来区别,但是我们很快又把这个方案否掉了,因为方言的使用会让演出变得搞笑,与战争的规定情境不符,所以我们决定全部采用普通话,靠演员的表演来展现人物语言的不通,这是我们在‘文本翻译’阶段为全剧定下的基调。”在中文版舞台上,语言之间并没有达到自由转换的境界,笔者在现场看到的是,战场上的英、德两军同时发现乔伊,他们友好地“协商”以解决乔伊的归属问题,两军都在说中文,彼此却无法听懂,这样的场景设计,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即使是上乘的表演,仍然显得与情境格格不入,也因此引发了观众思考:在戏剧本土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的改编、移植问题?有人提议把故事背景放到中国,让交战双方说彼此听不懂的方言,才能更生动传神,直击观众内心,这样的提议虽具有建设性,但一旦沿着这个思路修改,结果可能就是另一台戏了。
在一些情节设计上,中文版尽量按照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做了一些调整。原文本中有许多英国乡村俚语,中文版尽可能遵守它的原汁原味,有些翻译工作是一度、二度创作在同时进行,包括一些带有人物特质的台词,比如演员模仿马的腔调说“不”,原文是“Nay(颤音)”,中文版演出时改用嘴唇打嘟噜,做出马的喷口的声音。中文版里,阿尔伯特的好友大卫战死,更加凸显出战争的无情;比利被枪杀,NT版则是德军用比利父亲留给比利的匕首残忍地刺死比利。
除了上述一些差异之外,中文版与NT版在其他方面基本一致,也因此受到英方的赞赏:“每年英方都会有巡演经理来看中文版的演出质量,他们说中文版的演出质量超越了北美巡演版、澳大利亚版和德国版,是除英国伦敦驻场之外世界上最好的《战马》演出。”
结 语
舞台剧《战马》是商业与技术、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中文版通过线下活动(如开设《战马》体验课、工作坊、交流会)、出售衍生品、票务营销以及新媒体传播等多种推广方式,演出在国内一再造成轰动;但《战马》首先是“戏剧艺术”,这才是演出之所以升级为“现象”的根本。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当阿尔伯特带着乔伊重返故里,战争的残酷,少年的执著,人性的善良,见证过忠诚与死亡的他们,即便伤痕累累,幸运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方,相互依赖成为彼此的生命支柱,而不幸战死在异乡的兵士与马匹,是否在死亡来临前,经历过这样的爱与信任?还是带着倦怠与痛苦咽下最后一口气?综观舞台剧《战马》,从对战争的观察、反思,到反战、回归人性,实现了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的统一,乔伊这匹没有被战火吞噬的战马,令观众跟随它曲折的足迹,完成了一场心灵的洗礼与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