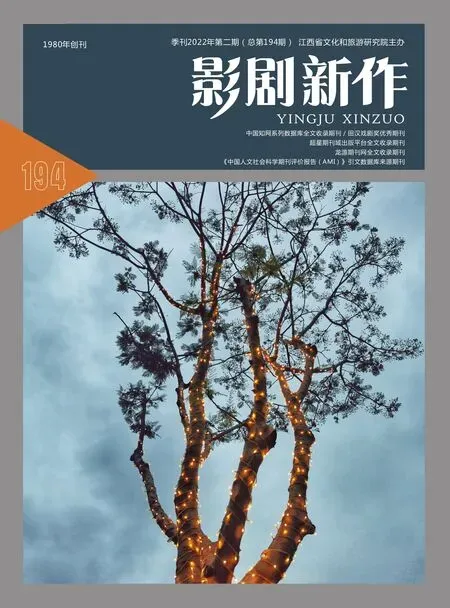现代女性的出逃和抗争
——对电影《人·鬼·情》的拉康式解读
刘 影
当一个小姑娘,不仅立志拜师入梨园,而且想要成为女武生,想要扮演“最好的男人”的时候,她所走的必定是一段布满荆棘的曲折道路。我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所拍摄的电影《人·鬼·情》便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它以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故事为原型,细腻地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不平凡的女性秋芸坚韧的内心世界。戴锦华在《<人·鬼·情>:一个女人的困境》一文中高度评价其为“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
诚然,《人·鬼·情》中所展现的女性意识,不仅仅流于成为“兼备家庭与事业”“看似拥有与男性平等权利”的表层,更是以秋芸之实像与钟馗之虚像的交织铺展叙事,直指女性在普遍意义上可能面临的困境。评论界对于《人·鬼·情》所探讨的议题也看法不一,在其面世的最初阶段,评论家们认为其是“人性的标本”,当时的批评与性别毫无关系;而其后的评论主要为女性主义角度的褒赞,同时也有评论将秋芸的困惑定性为性别认同与身份认同的焦虑。[本文尝试运用拉康的“三界说”“乔装”观点和“凝视”理论,对《人·鬼·情》进行细读和分析,透视女主角秋芸——这一现代独立女性代表,在困境中通过“跨性别扮演”进行的出逃和抗争。
一、钟馗:在“想象界”中的误认
影片开头便是秋芸在一片黑暗中面对镜子的场景,此时镜子中出现了她所扮演的角色钟馗,其后影像增多,形成了黑暗中重重叠叠的钟馗镜像空间,这样的开头似乎直接点明了影片女主角秋芸与钟馗的“镜像关系”,也是拉康“镜像阶段”的具体化表达。尽管拉康的“镜像阶段”在实验心理学的思想源流上指的是婴儿在6到18个月期间,对于镜子初步产生了视觉上的“自我感知”,在完整性的视觉感知与不完整性的神经感知的冲突中,婴儿产生了一种想象性的完整的自我形象,进入了“想象界”。但是这种“镜像阶段”或者说“想象界”并不是一种实在的发展阶段,而是处于我们经验的核心,强调的是主体与自我的这种结构性的关系。
《人·鬼·情》以这样一个拉康式的开头开始了它的故事讲述,而在开头便出场的钟馗这一戏曲形象,也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重要镜像。小秋芸的母亲是一名旦角,穿着红衣服、扎着两个小辫的小秋芸经常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被一个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原初场景”打破,小秋芸在草垛中捉迷藏时撞见自己的母亲与另一个“陌生男人”(实际上是秋芸的生父)的性爱场景,她惊叫着逃离,这样一个对于小秋芸而言无法理解的场景成为了秋芸的“创伤”。相异于处于原始混沌状态的婴儿的本能一般的“需要”,1964年之后拉康,更多地将“实在界”这个概念与“创伤”相联系,“创伤”是无法象征化的,无法被言说的,因而它是实在的,即使我们言说它或者表达它,它总是有剩余物。撞见母亲与他人性爱的“创伤”可以看作秋芸终其一生寻找自己的镜像的起点,第二日,当小秋芸仿佛没有受到“创伤”的伤害(因为年幼无法理解),依旧与平常一样和自己的青梅竹马二娃哥一起看戏的时候,搬弄是非的大人们闲言碎语道秋芸的母亲跟人跑了,小秋芸哭着寻找母亲,却发现自己的母亲确实离开了,此时的小秋芸仿佛再一次跌出了“想象界”,陷入了“实在界”缺失的痛楚中,母亲作为“实在界”的他者离开了秋芸,痛哭流涕的秋芸这时候看见戏台上被喝倒彩的狼狈的钟馗,此时钟馗因为某种“被抛弃”的相似性成为了小秋芸的镜像,小秋芸需要这种即使是虚幻的误认来赋予自己一个完整性的形象,以修复主体的支离破碎。自此,钟馗开始成为小秋芸的镜像,在小秋芸被所谓的“青梅竹马”二娃哥抛弃和殴打时作为一个幻象抚慰和拯救了小秋芸,而在每次秋芸遭受挫折之时,钟馗都会出来担任“拯救者”的角色,在秋芸的手掌被舞台上的钉子扎伤后,周围人仅投以漠然的冷眼,她歇斯底里地面对镜子往自己脸上涂抹油彩,试图成为“钟馗”,从“想象界”的镜像中寻求安慰,此时影片中出现了畏畏缩缩、表情苦闷的钟馗形象,与痛苦呼号的秋芸构成了镜像的呼应,秋芸也通过拉康意义上的“穿越幻想”(traversing the fantasy)抵御了缺失的“实在界”闯入她的生活,将之转化为戏剧性的迷狂体验。
秋芸与其镜像“钟馗”在“想象界”的认同关系,在影片的结尾达到了最高的层次,“衣锦还乡”的秋芸在演出后与喝醉的养父欢声笑语,洋溢着温暖和睦的亲情氛围,这时候接生婆出现,讲述了秋芸出生时的故事,“你爸以为是个儿子,等我一看呐,少那个玩意”,此时的秋芸其表情仿佛面临审判一般突然怔住了。尚且给予她平等之爱的养父其内心“真相”仿佛宣告了秋芸在“象征界”抗争的失败,其后影片中出现了秋芸与钟馗的对话:“你就是我。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只不过你是一个女人”,此时秋芸与其镜像钟馗达成了最高层次的二者的统一与相互认同,秋芸也最终明白,象征系统的父法秩序暴力地挤压着她的生存空间,而这个在她被侮辱和被损害时都会出现的镜像钟馗,才能够修补她内心的伤痕。尽管秋芸与钟馗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镜像误认,但是它也给予了秋芸抵御创伤和阻止崩溃的能力。
二、乔装:试图成为“能指”的秋芸
《人·鬼·情》曾被网友称为女版的《霸王别姬》,然而此种称号不仅时间顺序无法对应,并且也混淆了二者所表现的主题的本质区别。《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对段小楼的感情是同性之爱,并且他经历了性别认同转变的过程;而《人·鬼·情》中的秋芸,对于性别认同并没有困惑,性取向为异性恋,她所执着的是扮演男性角色,而非成为男性。秋芸为何执着于扮演男性角色?影片中秋芸第一次表达扮演男性角色的欲望是在其养父给予她艰苦训练时,养父以母亲为反例想要劝退秋芸,秋芸累倒在地上,依旧抬起头大声说“我不演旦角,我演男的”,颇有意味的是,影片的后两帧,画面的右上方出现了当时在场的小男孩的生理性别指称,秋芸嘲弄地向露出阳具的小男孩吼了一句。戴锦华认为这个情节所表示的并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菲勒斯崇拜”,而是单纯陈述秋芸可以拒绝女性角色,而无法改变女性性别,因而无法逃脱社会意义上的女性“宿命”。然而,秋芸通过拒绝女性角色所拒绝的是像母亲这个个体一样的女性命运,她并没有改变女性性别的意图,相反,笔者认为秋芸想要以女性为主体尝试进入“象征界”,成为“能指”。
拉康所言的“阳具”实际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具有特权地位的“能指”,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如果主体想要进入“菲勒斯”所标记的“象征界”,则应该接受“以父之名”为代表的父法,去认同父法。这在影片中主要体现为秋芸与张老师的关系中。张老师与秋芸互生情愫,秋芸因此第一次尝试打扮成旦角,有了对自己女性魅力的第一次焦虑,有了关乎自我女性魅力的展示欲望,张老师看了她的旦角打扮后,先称赞秋芸的美,接下来便是如师长一样劝告她“把大男子演美,才算是真美”。张老师的目光是来自“象征界”的“凝视”的目光,而他的规劝便是“父法”的“禁止”,他虽有妻子与孩子,但是仍然在情愫萌动下想要与秋芸亲热,他展现着具有特权的“阳具”一般的“能指”在“象征界”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但是秋芸没有接受这种“阉割”,并没有认同这种即使看起来柔和的“父法”,她在月光下逃离了这种暗流涌动的情愫,拒绝以被阉割的方式进入“象征界”。这一场景被影片安排在秋芸创伤情结的发生地——草垛丛中,秋芸用这种逃跑的方式来抵御创伤情境的再次上演。
乔安·里维尔(Joan·Riviere)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女人味之为乔装》(Womanliness as Masquerade)引入了一种更具有当代社会特质的女性概念——知性的女性(intellectual woman),并且提出一个相当新颖也是相对激进的观点:知性的女性为了隐藏自己的男性特征和避免男性对此出于焦虑和恐惧的报复,会戴上一副充满女人味的面具。在里维尔看来,女性气质的存在是伪命题,女性气质只不过是生理女性掩盖男性气质的乔装,假面和女人味是同一的。拉康吸收了里维尔的观点,发展了“乔装”这一概念,认为“女性是为了成为男根,也就是说成为他人欲望中的能指,而抛弃掉她妇女性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假面舞会中她的所有装饰。她希望成为她所不是的那个来被欲求来被爱。”导演黄蜀芹的观点与里维尔和拉康的论述产生了内在的呼应与共鸣,她在访谈中明确表示秋芸是人格非常完整而独立的女性,但恰恰是因为她人格独立,她却过不上她作为一个平常女性所渴望的和美生活,她是孤独的。秋芸执着于扮演男性是她不齿于做一个像母亲那样的女人,她具有刚强、坚毅、帅气的男性特质的一面,她想要成为象征系统中的“能指”,因而她扮演男性,想要通过扮演男性来成为阳具本身,成为“能指”本身,从而在象征秩序中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话语权。但是处于异性恋的关系之中时,秋芸又因为焦虑自己无法吸引张老师,因此戴上了里维尔所说的充满女人味的“假面”。
拉康曾有“女性不存在”(the woman does not exist)这一颇具争议性的论断,但实际上他所表达的是:女性因为不完全在象征系统中,她才相比男性接近某种“更多”(encore),比如女性相比男性,除了阳具的享乐,还可以拥有迷狂的享乐这种享乐类型。但是,在父法领导下的象征系统中,女性并没有享受所谓的“更多”,相反,她们处于象征系统的暴力之下,处于“能指”的绝对压制之下,就如雅克-阿兰·米勒所言“毫无疑问,我们把女人们(women)遮掩起来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女性(Women)。我们只能发明女性”,黄蜀芹的《人·鬼·情》不过是用电影艺术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女性在象征系统中是失声的;女性特质在象征系统中是不存在的。戴锦华的评论也表达的是此意涵,在“阳具”具有主导地位的“象征界”,独立完整如秋芸这样的女性只能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这仿佛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但似乎也是既定的现实,女性进入象征系统,要么成为“能指”,要么出逃到“想象界”的镜像当中,秋芸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抗象征秩序,她在扮演男性、通过“乔装”成为“能指”的同时,在压迫性的“象征界”,在喘息的间隙出逃到她与想象中的“钟馗”相依为命的“想象界”。
三、戏台:“想象的凝视”与“凝视功能的逃避”
与《霸王别姬》不同,《人·鬼·情》中的秋芸不存在性别认同焦虑的问题,在影片中有关日常生活的片段,作为女性秋芸都是非常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与如今后现代语境下的“性别酷儿”的形象相距甚远。尤其是成名后,影片特意描绘了秋芸在家带孩子的场景,以及在不甚幸福的婚姻关系中惯于包容忍耐的“贤妻良母”形象。也就是在这个片段,秋芸对怀中的孩子说“妈妈要扮演最好的男人”,整部影片主要突显的是秋芸想要扮演一个男性,而非成为一个男性。秋芸与钟馗构成的“想象界”的镜像关系,这种“镜像”并非指的是实在的“镜子”,而是可以进一步看作是“观看装置”,而秋芸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执着于在戏台这样一个“观看装置”中进行跨性别的表演,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凝视”的强化。
虽然从童年起,秋芸与想象中的“钟馗”就已经构成了镜像认同的关系,但是秋芸的跨性别扮演之路却是经过了“俊扮武生”到“钟馗”的选角转变的,起初的秋芸所扮演的都是赵云、诸葛亮、关羽这样的在男性世界中的成功者,或者说是完美的象征界的“能指”角色的形象。在戏台这样的“观看装置”上表演,台下有着切实存在的观众,主体的“想象的凝视”得以强化。拉康所说的“想象的凝视”(gaze of the imaginary)中,主体总是“满足于把自己想象为有意识的”,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凝视中形成理想自我形象,并且认同他者的目光来把这一凝视内化为自我的理想;二是“看到自己在观看自己” ( seeing oneself seeing onesel f),这是一种否认他者凝视,自以为是自己在看自己的“意识幻觉”。青少年时期扮演关公的秋芸,在男性观众的评价里是“她比男孩还男孩”,在秋芸俊美的扮相和帅气的动作下张老师听到稚嫩的女孩嗓音,也露出了微笑,观众的反应折射出的信息是很微妙的,装扮为异性的被凝视的女性,似乎更加能够引起男性的凝视欲望。秋芸在受到大家的赞扬和认同后理应将这一凝视的目光内化为自己的理想形象,但是秋芸却似乎走了一条迥异的、仿佛故意抗争的道路——她要饰演不讨喜的“丑陋的”钟馗。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敏锐如秋芸在戏曲道路上她逐步意识到了这种来自他人(尤其是异性)的目光的凝视施加给自己的来自象征秩序的权力压迫,尤其是在与张老师告别之后,张老师否认秋芸那转瞬即逝的“魅力女性”的镜像认同,以“为了你好”之名留给她一个来自充满秩序与规范的“象征界”的告别之礼。于是秋芸选择了扮演钟馗,钟馗不仅仅是从小到大她用以抵御“实在界”的重要镜像,同时也是“获贡士首状元不及,抗辩无果,报国无门,舍生取义,怒撞殿柱亡”这么一个被象征秩序禁止了的边缘男性形象。一个男性都不愿扮演的“丑陋的”“怪诞的”角色,对于台下的观众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性吸引力,秋芸看似巧妙地规避了来自他人的凝视的目光,达成了自以为自己在看自己的“意识幻觉”,也就是拉康所言的“凝视功能的逃避”,殊不知她在本质上与其他扮演武生或者旦角的女性一样,接受了象征秩序,只是她在“想象界”的镜像中获得了更多的满足。有意味的是,拉康认为这种来自父法秩序的凝视就像绘画中的透视线消失的“灭点”一般,是被凝视的主体所不可见的,而在影片中,“钟馗”的每次出场,以及和秋芸的对话,都是在一片黑暗之中,这仿佛暗示着秋芸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想象界”,依靠镜像钟馗获得的安慰和满足,实际上都被着巨大的、无边无垠的、不可见的黑暗深渊所凝视,而这片黑暗的凝视,就如拉康所言的“实在界的凝视”(gaze of the real),一次次地唤起秋芸在欲望之路上的追逐。秋芸在“想象的凝视”中,徘徊逡巡于认同和回避之间的茕茕孑影,是她坚毅不屈的个性的体现,也是她对于现代女性困境抗争的写照。
结 语
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是一首细腻温情而又压抑的独立女性悲歌,更是一首赞歌。秋芸终其一生抵御创伤的苦痛和反抗象征系统的父法压迫,她温婉娴静的外表下包藏着坚毅勇敢的灵魂,她扮演男性,扮演镜像,最终在戏台上成为自己的镜像“钟馗”,无怨无悔地“嫁给舞台”,活出了灿烂夺目的自我。诚如拉康所言,自我主体的完整性似乎只是一种幻想,每个人,无论男性或是女性,都如同秋芸一样是破碎而割裂的主体,“实在界”永恒凝视着我们,我们为追逐欲望疲于奔命。填补永恒的缺失或许是如同精卫填海一般的徒劳,但是在“想象界”的镜像里,我们也能够在追逐理想自我的不懈努力中,终有所获。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