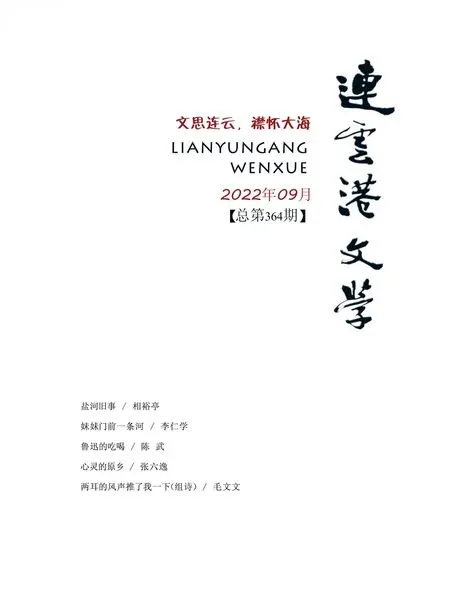盐河旧事
相裕亭
说 合
那个女人是谁?
九奶奶恍惚地看到月牙塘对面独自坐着个女人。
那个时候,天快黑了。九奶奶忙着在塘边剖鱼、洗鱼呐。渔船上刚捕捞来的狗腿子鱼,条条都是亮晶晶的白肚皮——新鲜的鱼。
九奶奶顾不上去看水塘对面的那个女人。但她担心那女人可别掉进塘里。
这塘里的水可深,九奶奶蹲在塘边洗鱼、剖鱼时,极为小心。
“滋,啦——”
九奶奶打鱼鳞时,如同木匠推刨花似的,将刀刃倾斜着,从鱼尾到鱼头,逆着鱼鳞的花瓣,一下一下刮得“滋啦啦”响。
说也怪呢,那种灰背、白肚皮的狗腿子鱼,别管个头大小,鱼鳞一概像是细小的黑芝麻、白芝麻,还紧贴在鱼皮上,每刮一条鱼,都要翻来覆去地打理半天。幸亏九奶奶有耐心,她“滋滋啦啦”地在那一下一下刮得认真。
狗腿子鱼,又名辫子鱼。它头大尾细,乍一看,还真是有点像清朝男人脑后的那根独辫子。但它周身长着扎人的刺。
好在,九奶奶剖鱼有技巧。她先用剪刀把鱼鳃两边的燕尾刺给剪掉,再剪腹部、脊背上两排像小梳子一样尖利的鱼鳍长针。然后,刮鳞、破肚。
九奶奶给鱼破肚子也有技巧,她先用剪刀找准了那鱼的屁股眼,并将剪尖轻巧地伸进那“眼”里,随即用力往前一推,就听“扑——”的一声闷响,那鱼儿煞白、柔软的白肚皮,就像是布店的掌柜扯布匹一样,瞬间被撕扯开来。随后,取腮、拽肠,留其肝脏和它吞食在前半部分胃囊里的小鱼小虾,那也是上好的美味,连同洗干净的鱼肠子,一同放在鱼锅里炖熟以后,软糯而又清香。期间,还要把扇面一样的鱼尾巴留下来。鱼尾巴虽然不能吃,但摆在盘子里,好看!
当天,九奶奶拎来半篮子狗腿子鱼,她一条一条地在水塘边洗呀、剖地收拾干净,耗费了大半天的时光。
回头,等九奶奶拎起篮子里的鱼,准备回家汆汤炖煮时,抬头一望,水塘对面的那个女人,还坐在那棵倒伏在塘边的枯柳段上。
那时间,天已经黑了。
谁家的女人?怎么还坐在那儿呢?莫不是与公婆怄气,或是与自家男人吵架了不成。
九奶奶那样想着,便拎着篮子里洗得亮汪汪的鱼,拧着一双小脚,绕到水塘的那一边。感觉不认识眼前的那个女人,但她还是试探着问人家:“天黑了,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什么?”
那女人低着头,紧拧着衣角不吭声。
九奶奶伏下身,打量了那女人的眉眼儿,似乎不是这村里的人,再看她脸上的泪痕,隐约觉得这妇人心里有事情。于是,九奶奶就问她:“你是哪村的?”
那妇人仍旧拧着衣角不吭声。
九奶奶知道,这小妇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了,她便扯她的衣袖,如同召唤自家的亲闺女一样,跟她说:“走吧,跟我回家熬鱼吃。”
妇人摇摇头,且轻轻地掰开九奶奶的手。好像她就要坐在那水塘边,死活都不需要九奶奶管。
九奶奶呢,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想起这水塘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她告诉那妇人,说这水塘里可淹死过人——
九奶奶絮絮叨叨地说,抗日战争那会儿,有个日本人的“狗腿子”(汉奸),赶在一天晚上喝多了酒,一头栽进这黑咕隆咚的塘里了。当时,那人还骑着一辆新崭崭的洋车子(自行车)。等人们把他从塘里捞上来,发现他正光着腚。
当时,大伙都议论那个坏人是到某户人家偷女人被人打死后,连人带车给扔进塘里的。
后来,上面来人查实,是他骑车路过这塘边时,一条裤脚缠进“牙盘”里,将他连人带车地拽进水塘里了。人们推测他在水下时,可能想脱掉裤子,光着屁股爬上来,可他没有想到裤脚被缠住,裤子都脱到他腿弯那儿了,还是被淹死在这塘里了。
妇人听九奶奶那样一说,果然就不敢在塘边坐了。
接下来,也就是九奶奶领上那妇人,一同回家炖鱼吃的时候,那妇人告诉九奶奶,说她姓梁,娘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小梁庄上。但她不想回去丢了娘家人的脸面——她是被婆家那边驱逐出家门的。
旧时,盐区这边,好多年轻的汉子外出打鱼时,赶上风浪(遇到台风),淹死在海里,撇下家中一个个俊巴巴的小媳妇。守不住妇道的,往往会被婆家那边给逐出门户。
眼前这小梁,是不是也是那样的?她自己不说,九奶奶也就没有细问。
过了一夜,九奶奶得知小梁的生辰八字正攥在她自个的手上(类似于当今的《离婚证》)。想必婆家那边真是断了她的“回头路”。九奶奶便试探着跟小梁说,她娘家那边,有个叔辈侄子,年岁嘛,可能要比小梁大一些(其实大很多),左边的脚踝子那儿,还有一点歪歪着(瘸子)。若是小梁不嫌弃,她想从中搭个嘴儿,说合说合。
小梁低着头,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九奶奶这就两边拉扯(两边说好话)。先是让她那瘸腿的侄子,骑着一头通体灰白的小毛驴来相亲。紧接着,对方送来八尺大花布。一件亲事,就这样定妥了。
赶小梁掏出自己的生辰八字,让对方去找个识字的先生,推算大婚的良辰吉日时,九奶奶这边却像嫁闺女一样,开始给小梁张罗碗筷呀,脸盆子呀,还有夫妻间夜晚要用的小码子(尿盆)等陪嫁物儿。
大婚那天清晨,小梁一大早起来帮九奶奶烧火煮饭时,将额前的刘海儿缠绕在滚烫的挑火棍上,烙烫出一圈一圈俏眼的弯弯儿。随后,她还往脸上涂了一层鸡蛋白(鸡蛋煮熟后的蛋白儿,被她当作雪花膏来用了),紧接着,又找来一片红纸衔在口中,“吧唧吧唧”连抿了几口,将上下两片嘴唇染得红红的,再一照镜子,还真比原来俊了呢。
回头,赶迎亲的队伍,在九奶奶家的小巷口“噼噼啪啪”地燃起一挂小鞭时,端坐在里屋炕沿上的小梁,眼窝一热,“扑簌簌”地滚下泪来。
戏 匣
张康能从县上捧回一台会唱歌、会讲话的戏匣子,也是经过层层举荐和筛选的。先是村子里的坊长(保长)把张康的名单报到乡里。乡里认可以后,又把他推举到县上。县上组织多方面的人士进行评估与论证,感觉张康的条件还可以,这才把那台戏匣子当作奖品奖赏给他。
张康在县上登台领取那台戏匣子时,场面应该是很壮观的。他本人也应该感到很荣耀。但那场面村上人没有看到。村上人只看到张康从县上回来时,前胸后背斜挎着一条巴掌宽的红飘带,胸口那儿还坠挂着一朵碗口大的大红花。坊长组织起敲锣板在村头迎接他,张康走到人群中散烟卷。
那场面,同样也是很光鲜的。
接下来,村上人都很好奇地想听到那台戏匣子里唱歌、说话的声音。可张康家的门台高,并非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迈进的。县上、乡里来的干部可以;村里的治保长、坊长也可以。还有盐区几家大户人家的老爷、太太、姨太、二当家的(管家),他们也都很受张康家欢迎。再者,就是本地教书的贾先生,他同样也是张康家的座上宾。
不过,贾先生那人有些格色,他是前清的秀才,很少与外界交往,整日在家闭门教授几个学童。偶尔,乡邻们有事找到他,他会像个判官一样,把事情这样那样地问明白了。然后,再告诉你这样办,或那样办。但是,贾先生那人懒得求人——他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譬如张康从县上捧回的那台戏匣子,贾先生应该是早就知道的。但他跟不知道那回事一样。直到张康请到他门上,跟他说了那个洋玩意儿如何会唱歌、会讲话,他这才很是惊讶的样子,说:“呀!那是个什么洋货?等我抽空,到贵府去瞧瞧。”
当时,盐区这边的香烟、火柴、煤油,包括布匹,都属于“洋货”,市面上统称为:洋烟、洋火、洋油、洋布等等。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还有人把香烟叫洋烟、火柴叫洋火呢。
那么,张康从县上抱回来的那台戏匣子,用当今的电子器物来推测,它应该是一台收音机。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段(晚间),才可以听到它里面的声响。这就是说,当时的广播电台,并非是全天都在对外广播。
张康呢,他把那台戏匣子当作宝贝一样,摆在自家正厅的条案上。并请来县上的专业人士,在院子里架起一根高过房顶的天线,装上了两个牛蛋样大的干电池,这才把那戏匣子里的声音调当出来。
最初,被张康请到家中来听戏的人,都是盐区的头面人物。他们接到张康的请帖以后,如同到张康家去赴酒宴一样,提上四色礼盒,且礼帽、长衫地穿戴整齐,各家太太、姨太们脸上也都施了胭脂、扑了香粉。等张康请到贾先生时,那应该是大伙儿在听戏时遇到什么难以破解的问题了。
因为,张康来请贾先生时,说:“戏匣子里面有好些话语,大伙儿都听不明白。”言下之意,贾先生读书多,学问深,请贾先生过去给破解一下。
贾先生嘴上说:“好!”
可他心里面并没有拿那个戏匣子当回事儿。在贾先生看来,什么戏匣子?无非就是一台留声机。早年,贾先生在县上做参事时,见过那玩意儿,放上唱片,就可以听戏。贾先生甚至想到,张康家可能把不同戏种的唱片放在上面了,譬如越剧、沪剧、苏州评弹,那种江南人卷起舌尖儿说唱的地方戏,盐区这边的人,确实是听不习惯。
可贾先生没有料到,张康从县上抱来的那台戏匣子,并非是他想象中的留声机。而是一台比留声机更加先进的洋玩意儿,不用唱片,就能听到里面唱戏、讲话的声音。
贾先生头一晚来听那戏匣子时,他几乎是一句话没讲。当时,张康还把贾先生的几位在乡里做事的高徒也一同请来陪着贾先生。同时被张康邀请来的还有村上的坊长和盐区的吴家、沈家、谢家、杨家几位老爷和他们的太太、姨太。
那天晚上,张康把戏匣子一打开,里面确实是“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随后,便是一个女人娇里娇气的讲话声。那或许就是张康听不明白,或是大伙儿犯疑惑的原因——大家猜不透那里面怎么还会有一个女人同大伙儿嚓呱(谈心)呢。
但贾先生听出了门道,那戏匣子里面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应该是一个日本女人讲的。也就是说,张康家的那台戏匣子,是盐区沦陷以后,日军使用的舆论宣传工具。
那个晚上,贾先生如同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张康家的客厅里静静地听,临到散场时,大伙儿想听听他的高见,贾先生却一句外话没有多讲,起身向大伙儿打了个拱手,便告辞了。
第二天晚上,贾先生又来听那戏匣子时,其间到院子里抽了两袋烟。回来后,仍然是一句话没讲地坐了坐就回去了。到了第三天晚上,贾先生听到戏匣子里面又开始讲话时,他立马喊住张康,说:“慢着,慢着!你把那女人说话的声音再给我重放一遍。”贾先生好像要研究一下刚才那女人在戏匣子里面讲了什么,他让张康旋动那个旋扭,把刚才那个女人讲话的声音重播一遍。
张康愣住了!他想不明白,那是人家戏匣子里面传出来的声音,他张康能有什么办法让那女人再讲一遍呢。
贾先生却俨然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他教给张康说:“你这样,把那旋扭往回拧一拧,那女人刚才讲话的声音,自然就会出来啦!”
贾先生还跟张康说,留声机就是那样的,听过的戏曲,要想再听一遍,把唱盘上的支架重新调回原来的位置上就可以了。敢情这戏匣子也是可以那样的。他让张康试着旋动那旋扭试试。
张康呢,他按照贾先生教给他的办法,转动那个旋扭,戏匣子里面随之传出“滋滋啦啦”的一阵乱响,并没有找回刚才那个女人讲话的声音。
贾先生为张康着急,他甚至认为张康转动旋扭时不够得力,随起身走到那戏匣的跟前,捏住那个旋扭,用力一拧,只听“咔叭”一声脆响——旋扭断了,里面“滋滋啦啦”的声响也随之没了。
刹那间,在场的人都为贾先生的举动而尴尬。
贾先生可能也意识到那戏匣子被他拧坏了,一时间,他很是专注的样子伏在那戏匣子上左右摆弄,仍然听不到里面有声响。期间,陆续有人起身到院子里去说话、抽烟、望星星,还有人感觉时候不早了,干脆与张康的家人打了声招呼便提前退场了。
那个夜晚,贾先生是最后一个走出张康家的,他可能留在后面与张康说了些歉意的话。但贾先生的那几个门生,一直都在院门外候着他。
末了,也就是贾先生从张康家出来时,大伙儿也都不好问他有关那戏匣子的事,一个个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响彻寂静的街巷。忽而,贾先生抬高了嗓音,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混账东西!”
贾先生那话,不知是骂张康的,还是骂日本人的。但有一点,大伙儿心里是明白的——当晚贾先生拧坏那台戏匣子,是他故意的。
新 婚
大川结婚了。新媳妇是梁家河子的。
盐区这地方,沟湾河汊子多,水泡子多,堤坝也多。依水而居的人家,多以姓氏和所居住的水源,来给自己的村落起名字。譬如朱家沟,王家坝,梁家河子,都是因为村子里面朱姓人家多,或是王姓人家落居得早,就周边的沟河堤坝而取名朱家沟,王家坝,或是梁家河子。
集市的地摊上,买卖双方,往往会因为三五分钱的零头,在那儿争执不下。临到最后付款成交时,相互间的语气自然会和气许多,甚至还会叙起家常,一方问:“哪个庄上的?”
另一方回答:“梁家河子的。”
“姓梁?”
“姓梁。”
“呀!我们还是亲戚呢!俺家侄子媳妇,就是你们庄上的,姓梁。”
“是吗,谁呀?”
“……”
他们说的是大川的媳妇梁小良。
刚刚还在为那三五分零头钱,一个不买,另一个不卖呢,这会儿都谦让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川的媳妇梁小良做过盐区识字班的队长,周边几个庄上的人都认识她。她嫁到大川家这个村子里以后,这个村子里仍然推选她当妇女队长。
那媳妇做事情利落。新婚第二天,大川领她给爹妈磕头,给伯父、大娘、叔叔、婶子们磕头(认宗亲)。临到给姑、舅、姨磕头时。小良私下里问大川:“怎么没见到咱老姑?”
大川开始不言语。
赶到晚间,小两口熄灯上床以后,小良又想起大川老姑的事情来,她扳过大川的肩膀,问:“咱老姑呢?我怎么一直没见着?”
大川看事情不好再隐瞒,便如实告诉小良说:“咱家与姑家,几十年都没有来往了。”
小良问:“为什么?”
大川略顿了一下,说:“为气穷!”
赶小良再往深处问时,大川就不说了。
小良觉得奇怪。怎么为气穷,与老姑几十年来就不上门了呢?话再说回来,那些年(指新中国成立前),盐区这边的土地、盐田都掌控在地主老财和盐商们手中,做佃农的、打盐工的,哪家不穷哈哈的?可再穷,也不能割断了亲情呀!
大川看小良满脸疑惑,便跟媳妇亮出实底,说:“为了一双鞋。”说完,大川又补充说,就是那种东北人带回关内来的棉焐儿鞋。
大川的姑夫是东北客。
盐区这边所说东北客,是指水乡穷苦人家的男儿们,到了讨媳妇、娶老婆的年龄时,仍然还没有媒婆登门,那就要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去东北闯荡几年了。混两身好看的新衣裳,再带回一些积蓄,或东北的貂皮、人参、黑木耳,就可以招引到盐区这边的大姑娘、小寡妇们的喜爱。
可大川那老姑夫,在东北闯荡了几年以后,只混得一身好皮囊(带回几件好看的新衣裳),外表看,挺光鲜的!可他手头并没有多少积蓄,以至于大川的老姑嫁过去以后,还要娘家来接济些粮草度日月。
那个时候,大川的爷爷、奶奶还在。老姑娘回到婆家来,明着是看望爹娘,暗中却是瞒着哥嫂,带走些食物与用物。一来二往,大川娘便有所察觉。有一回,大川的老姑用一件破旧的外衣,遮盖住半篮子玉米往外走,正好被大川娘给堵上了。
当时,大川娘的怀里正抱着大川。
姑嫂二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
嫂子想知道姑子臂下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而姑子却不想让嫂子看到她将要带走的那半篮子玉米。
那个当口,姑嫂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年代久远,不好再去对证。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姑嫂二人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儿),让两家人相互怨恨了对方几十年。
其一,是嫂子,也就是大川娘,她把怀中的大川递给姑子,谎说她的裤腰带要开了,她让姑子帮她抱一下大川,她要紧一下腰带。可等姑子把她手中的篮子放在地上去接抱大川时,做嫂子的却弯腰掀开了她篮子里那金灿灿的玉米粒儿。
当时,大川姑的脸,就“腾”地一下,羞红到了脖子。
盐区这边,嫁出去的姑娘,回到娘家来倒腾财物,是极为不光彩的事情。可做爹妈的,看到姑娘嫁了户人家吃不上饭,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要给姑娘留一口食物,十指连心呀,做爹妈的,哪个儿女都疼爱。
而大川娘要张罗这一大家子的吃喝,她哪能容得下小姑子倒腾走家中保命的粮食。大川娘不冷不热地说姑子:“俺家里也快断顿啦!”言下之意,那玉米是不能拿走的。随后,她便拎起那半篮子玉米,倒回自家的缸里了。
其二,也就是大川娘把姑子那半篮子玉米给断下来以后,大川的姑恼羞成怒,就手把大川脚上的一双棉焐儿鞋给扒了下来。那是大川的姑夫闯关东时带回来的。当初,大川的老姑是为了讨好娘家的哥嫂,才送给大川的。而今,嫂子连半篮子玉米都不肯给她。那双棉焐儿鞋她也要收回了。
那年月,那种胶皮底的棉焐儿鞋,都是东北客从关外带回内地来的,它的前头有胶皮包住鞋尖,后头还有块半圆的胶皮兜住鞋跟儿,里面是棉毛绒的,穿在脚上,防水又暖和,大人、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大川姑夫当初把那样一双小巧而又暖脚的鞋子送给大川,也算是一件很贵重的礼物了。
而今,姑嫂二人,为了半篮子玉米,将怒气直接转嫁到大川的身上了——大川的老姑,硬生生地从大川的脚上,把那双棉焐儿鞋给扒下来带走了。
这件事情,在大川记事以后,曾多次听娘在他耳边絮叨过。以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川每当在街上看到谁脚上穿着那样的棉焐儿鞋,他心里就像捂上了一把盐一样不舒服。在大川看来,那样的棉焐儿鞋,如同一粒怨恨的种子,在他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儿。也就是说,大川在不知不觉中,也同母亲一样,怨恨上了他的老姑。
当然,这里面最为怨恨的,还是大川的母亲与大川的老姑。那一对姑嫂,为了那半篮子玉米,或者说是为了一双棉焐儿鞋,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了。尤其是大川的爷爷、奶奶相继过世以后,大川的老姑,再也没有回过娘家,更没有登过哥嫂的家门。
大川的新媳妇小良走进这个家以后,想到去叩拜姑、舅、姨,这才知道婆母与姑婆(老姑),还有那么一段难解的恩怨。小良思量再三,跟大川说,当初,咱娘与老姑之间,无论是因为那双棉鞋,还是因为那半篮子玉米,都不是冲着咱们晚辈人来的。要说这里面谁对谁错,那是她们老一辈人的事情。咱们做晚辈的,不应该顺延他们的仇结。
小良跟大川说:“你还是领我去认认咱们的老姑吧!”
大川说:“这事情,就怕俺娘不认可。”
小良说:“那咱们先不跟娘说。”
大川想了想,媳妇的话在理儿。或者说,大川在媳妇的劝导下,以领着新媳妇认姑婆为借口,赶在新婚蜜月里,提上他们新婚的糖果,前去拜见他们的老姑。
老姑一见娘家侄子领上新媳妇登门,一时间喜泪相迎,第一句话便问:“是你妈让你们来的吗?”
大川与媳妇,异口同声地说:“是。”
刹那间,埋在老姑心里几十年的恩怨,如同一堵不堪重负的老墙,在一场酥润的春雨到来时,轰然倒塌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放亮,老姑便嚷嚷着喊起了儿子。她让儿子用独轮车子推上她,回到了她几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娘家。
姑嫂二人,再次相见时,谁都没有说什么,上来就抱在一起,“呜呜咽咽”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