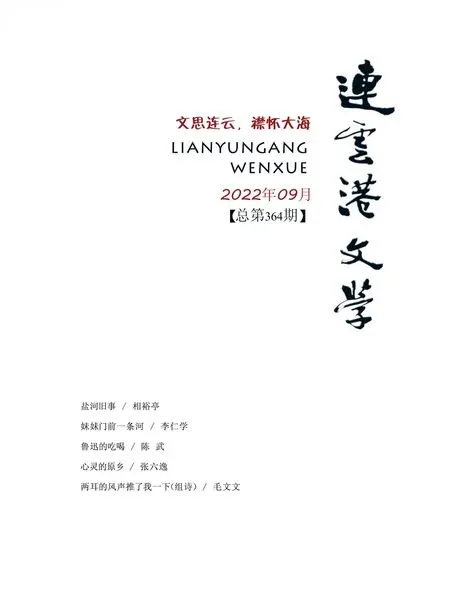妹妹门前一条河
李仁学
一
野渡无人,一条小船孤独地泊在岸边,听细浪絮语,闲闲地晃荡着。他四下里巡睃一遍,喊道,过河啦——
过河,那是一片熟悉的土地,却又是一座陌生的城堡,刘德草已经多年没有踏足那片土地了。此行过河,首先缘于一个神秘电话的诱惑。电话是个陌生女子打来的,那女子几乎没有任何铺垫性的语言,开门见山就说要约他谈一件事情。刘德草问,我跟您认识吗?女子笑道,不认识,不过见面不就认识了?他付之一笑,不待女子说完,便将电话挂了。没过几天,他参加了区里召开的一个扶贫会议,会议中有一项决定,就是选派一名区直机关干部到鹊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一听这消息,旁边几个干部便嘀嘀咕咕地开起了“小会”:扶个牛粑粑哟,鹊村人是烂泥巴糊不上墙!
刘德草可是土生土长的鹊村人,这话就像一记耳光,扇得他两眼冒火,脸都绿了。恰好就在这天,那个陌生女子又来电话了,他没接,她又发来一条短信。而正是这条短信,使他看过之后仰天一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鹊村这个第一书记他是当定了,不仅如此,他还要甩开膀子跨出一步——过河去!
刘德草不过是文化部门的一员小科长,若非毛遂自荐,这个“第一书记”最终也未必能够落到他头上。好在那天他是有备而去,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分管扶贫工作的马副区长对他的桑梓情怀颇为动容,但沉吟片刻却又惆怅了:老刘啊,你也知道,鹊村是个偏远贫困村,又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区里这次要求务必使鹊村两年脱贫、三年“脱棍”,任务艰巨啊!你们文化部门是个清水衙门,一无资金二没项目,两手空空的怎么帮人家脱贫“脱棍”?搞不好最后还会被“乱棍”打回。顿了顿又说,其实,鹊村先天条件很好,眼前娇花照水,即便不能沾光,也可染得几分香气呀,可咱鹊村人偏偏不争气,惹得织女村人白眼相看……
说到织女村,刘德草立马接茬,其实,那个织女集团董事长跟我还是同学呢。
是吗?马副区长认真瞅了他一眼,问道,你是说蒲芳草——那个蒲芳草跟你是同学?
显然,马副区长对他抛出的这句话很感兴趣。此前,马副区长也曾多次拜访过蒲芳草,蒲芳草每次也是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他。可每次马副区长一提鹊村的事,蒲芳草总是绷着脸,说什么逐利是企业的本质,织女集团做公益慈善是有原则的。又说公司正在开展几个本土扶贫项目,哪有闲心把手伸到贵地去啊?说罢一脸是霜。马副区长见状只好打住,弄得好不狼狈。此后马副区长便开始琢磨,这蒲芳草走的是一条草根逆袭之路,一路上跌跌撞撞走来,据说从来不依附于任何关系,对于政商关系也是向来看得很淡。看来,要想走近她,跟织女集团把关系搞热络,最好还是另辟蹊径——走情感路线!
刘德草点头道,是的,我跟她是高中同学。其实呢,不光同学,还楚河汉界地共过一张课桌呢……
马副区长迅即意识到,这倒是一张很好的“情感牌”呢,不禁喜出望外,造句似的一连蹦出三个“好”字:好、很好、非常好!
二
七夕这天,刘德草终于直奔渡口,打算过河去了。
过河——过河喽……没人应,刘德草敞开腔门,一通砸门似的猛喊。
这边呢,过来歇哈(下)脚再走!终于有人应了,是“鹊桥仙”的声音。
鹊桥仙几乎干了一辈子摆渡,不过,他既不是鹊村人,也非织女村土著,而是“一橹摇三代”的最后一个梨香溪艄公。几十年浪里行舟,循环往返于梨香溪两岸,他亲眼见证了两座村庄的兴衰与恩怨。早先,两岸一边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另一边则是结网捕鱼的小渔村,两边差距不大、贫富相当,彼此鱼米互换,往来倒也稠密。那时候,他不单渡人,也渡情,经他牵线搭桥,还成全过不少“鱼米良缘”呢。既然是在梨香溪摆渡,又做过许多鹊桥善举,所以两边的人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称他艄公,而是亲切地送了他一个雅号:鹊桥仙!
鹊桥仙正坐在芦苇林的荫凉下跟人走象棋呢,见刘德草趟着齐腰深的野草“哗哗啦啦”地过来了,不禁诧异道,嗬,原来刘书记呀,你可真是稀客呢!他示意刘德草坐下观棋,说收拾完残局就走。
跟鹊桥仙对局的是刘二贵。刘二贵一手捏棋子,一手拿棵甘蔗,每次落子都要“嘎嘣”咬个脆响,然后老牛反刍似的不住地“吧唧吧唧”。刘德草在他对面席地而坐,他却连眼皮都没撩一下。其实,这也难怪,刘德草除了年根还乡祭祖,平素几乎不怎么回来,况且像刘二贵这一茬年轻人,跟他隔着年代,又互无交集,即使偶尔相遇,难免也是形同路人。
鹊桥仙提醒道,刘书记可是城里派来的扶贫干部呢,见面咋不招呼一声,你就不指望他以后扶你一把?说罢瞄刘二贵一眼,拱卒过河。
刘二贵鼓囊着腮帮子敷衍地“喔喔”了两声,连渣带水地吐了一口,说吃着蔗梢子了,苦!接着哂笑道,卒子过河无退路,你算老几?驱车撵了过去。
鹊桥仙举棋横行一步,说,卒子过河能当车!接着架炮轰帅,说,你没救了,赶紧投降吧,不然我驾马推磨,晕死你!
鹊桥仙除了摆渡,其实闲敲棋子也是他的一宗爱好,往往一局不消几个回合,对方便推棋认怂了,刘二贵哪是他的对手。刘二贵瞪着棋盘挠了半天脑门,没辙,只好怏怏地掏口袋,磨叽半天才抠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团,悻悻地扔在了棋盘上。
鹊桥仙将纸团拾起,展开了捋平,却又还给他了,说,留着吧,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攒点钱娶个媳妇才是,别老是混在光棍堆里跟人赌了。
一听“媳妇”二字,刘二贵表情立马生动,脸也红了、瞳也亮了,扔下甘蔗直搓手丫子,说,仙爷,您这话可挠着我痒窝子了,其实,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呢……
鹊桥仙知道他要说什么,嗤笑道,别再信口雌黄了,那小草可不是一般女子——果子挂那么高,连看一眼都晕,你咋还想爬上去摘呢,就不怕跌下来摔死你?
刘二贵呛道,想一下都犯法啊?
鹊桥仙烦道,走吧走吧,回家做你的白日梦去,我还要送刘书记过河呢。
刘二贵涎着脸死缠不放:那您跟“王母”说说,让我到她企业打工也行哪——您老不是她的救命恩人吗,她总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
鹊桥仙重重地叹了口气,撇开他不再理会,一声不吭地朝渡口走了。
刘二贵狗一样“嗷”地叫了声,使劲朝一棵蒲草踢去,气哼哼地骂道,狗屁“王母”!
“王母”就是蒲芳草,鹊村人恨死蒲芳草了。这几年,织女集团就像热气球膨胀似的,规模越做越大,企业到处招兵买马,可气的是,织女集团招工单单不要鹊村人,凡是打对岸过来的,一概拒之门外……
梨香溪空旷而寂寥,间或有几只水鸟从芦苇林“扑通”一声钻出来,它们蜻蜓点水地吻一下河面,河面上笑出几个小酒窝来,它们却“啾”的一声消失在了远处。
待刘德草上船坐稳,鹊桥仙像个老道的撑竿运动员,先是紧攥竹篙一端,猫着身子猛地一撑,竹篙成了拉满弦的弓,“嗖”的一下便将船射出去了。接着他将竹篙放下,开始摇橹,两只橹就像鸟的翅膀一样扇动起来。鹊桥仙一直固守着人力摇橹的传统摆渡方式,蒲芳草担心他吃不消,曾提出要送给他一台机动船,可这怪老头嫌机动船动静太大,一来怕船屁股的“铁扇子”伤着河里的鱼儿,二来担心机器里的油渍泄出来弄脏了河水,谢绝了。
小船就像一把剪刀,悠悠地剪开绸缎一般平滑的河面;又像一枚针,拽着长长的水线向对岸驶去,仿佛要把两岸缝合起来似的。鹊桥仙一边摇橹,一边摇起了他的故事篓子,篓子里抖出来的依然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故事——牛郎织女。
说完天上,话锋一转又回到地上。说两边弄成这个局面,其实也不能全怪人家芳草。起初,鹊村也有不少人在织女城打工,就因为几个光棍在厂子里头闹事,强扭着要跟那边的女子搞对象,可人家嫌鹊村穷,不干,几个光棍死磨硬缠,居然动起手脚来了——你说这跟牛郎偷衣服有啥区别,明摆就是耍流氓嘛!这事传到芳草耳里,可把她惹火了,结果乌龟背时连着壳,在那边打工的鹊村人一个个卷铺盖走人——全都被开了。接着又感慨,芳草可是个有气性的女子,当年不是一口气吐不出来,怎会跳河寻死?倘若不是跟人斗气,咋又会只身远走他乡。好在这女子有骨气,后来靠打工攒下的一点钱开了个裁缝店。谁承想,一个当初只有七八个土裁缝的小作坊,居然就像母鸡孵鸡苗似的,把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孵化成了那么大个服装城。说到这儿,鹊桥仙一声叹息,只可惜芳草成就了事业却耽误了自己,人生半百依旧还是形单影只……
夏天的梨香溪貌似娴静,其实静水流深。此刻,刘德草看似一脸平静,其实内心深处早已是一壶沸腾的苦药,往事就像船头簇拥的浪花,哗哗地朝他涌来……
那个暑期,他仿佛丢了魂儿似的,过河就像过马路,没几天便要过去跟女孩偷偷地见上一面。那女孩就是蒲芳草——他的初恋。那段初恋就像一枚青涩的野果,静静地生长,悄悄地挂在柔嫩的枝头。那时他俩刚结束高考,闲在家里等着命运的下一步安排。等待是一种煎熬,也是一种挣扎。她在他怀里努力挣扎了一下,借着月亮的微光,她发现他的脸上写满了煎熬与痛苦,忽然心疼了,羞涩地擂他一拳,柔声说,就一次,啊?他手忙脚乱地嗯了一声,她的身子便渐渐地沉了下去,最后竟像一团雪似的在他怀里融化了。
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结果是她幽幽地哭了,他却满面春风地笑了。坐在晚风习习的梨香溪岸边,望着渔火,她随手丢下一颗石子,河里的两个人影凌乱地碎了,她的梦也碎了。她郁郁地问,你还会过河来找我吗?他一口笃定地回道,会的,一定会的——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过河来娶你。他要她把左手伸出来,她不明就里地把手给他了,只见他非常有仪式感地在她面前单膝跪下,然后将一枚戒指套在她的食指上,望着她一本正经地说,嫁给我吧!
那是一枚铭有“喜鹊踏梅”图案的老戒指,是他母亲当年结婚时的信物。那枚戒指是他当着母亲的面,从她奁子里翻出来的,当时他还笑嘻嘻地对母亲说,妈,这枚金戒指挺好看的,反正您平时也没怎么戴,就放在我手里吧,等我将来结婚了,我就把它送给我媳妇。母亲当时满脸笑成菊花,乐呵呵地一连声说好,说她就等着那一天了。
他踌躇满志地走了,不久她惊骇地发现,那一次融化竟然化作了腹中难言的苦水。她方寸大乱,急得要哭。那时候手机还没普及,通信方式仍然靠鸿雁传书。她写信问他咋办?他却回信道,芳,你别吓唬我好吗?末了还是那句话,放心,我一定会回来娶你!她想亲自到学校去一趟,一来向他倾诉相思之苦,二来也好顺便给他亲眼瞧瞧,让他明白,她并非是在无中生有地要挟他,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她担心打扰他的学习,更害怕这事儿一旦让学校知道了,将会给他造成怎样的影响和后果。
她迷惘地伫望着梨香溪,河那边就是鹊村,她未来的婆家也就蛰伏于那片浩如烟波的芦苇林后面,虽然看不见村庄,却能隐约听到一两声鸡鸣犬吠,甚至还能依稀嗅到一丝淡淡的烟火气。她蹙着眉头沉思良久,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过河去!
她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路上躲开许多蜇人的目光,终于惴惴不安地站在了他父母面前。当她羞怯而又语无伦次地道明情由和来意,他父亲惊得手一颤,一支刚吸了几口的纸烟都掉在地上了。他母亲更是吓得要死,赶忙瞅一眼屋外,“哐”的一声便将大门封上了,慌腔走板地说,闺女啊,这话可不能乱讲哟!我家德草可是规矩人家的孩子,一直都在老实巴交地念书求学,没在社会上鬼混过一天,也没听说有什么闲言碎语,几时做过这种缺德事呀——你莫不是认错人了吧?
她强忍着泪水,犹豫再三,终于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来。他母亲一见那戒指上的“喜鹊踏梅”,“扑通”一声便跪下了,痛哭流涕地说,闺女啊,咱家祖坟好容易冒一回青烟,也不知德草他几世修来的福气,今天才总算熬出个头来了,他怎么可能谈个乡下女子呢?再说了,德草他如今还是个学生呢,这话若是传出去让他学校知道了,嗨哟唉,那可怎么得了哦……
三
船到河心,鹊桥仙似乎有些累了,两只船橹就像水鸟疲惫的翅膀,偶尔才蔫蔫地扇动一下。刘德草想他毕竟老了,胳膊上的肌肉已不似从前那一对铁疙瘩,而像吊在老鸡脖子下的嗉囊一样,软趴趴地晃荡着。他想上去帮他一把,于是扶着船舷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不料鹊桥仙板着脸说,你只管好生坐着说话就行,别老是不搭理我,不然我把船摇回去,不渡你过河了。
刘德草赶紧赔笑,您老说,我洗耳恭听呢。
鹊桥仙孩子气地笑了,说,今天可是个喜日子呢。
刘德草嗯道,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
鹊桥仙满脸枯木逢春,笑眯眯地问,那你今天过河去,又是跟谁相会呢?
刘德草窘着脸又沉默了。鹊桥仙放下橹,生气地说,德草呀,你这次过河是不是去找芳草?不说实话,我真的就不走了,让你自己光着身子游过去。
船在河心打了个旋儿,扭头向下游滑去。刘德草心里急,生怕耽误了约定时间,只好无奈地说,我想过去试试,可不知道她还认不认我这个老同学呢?
鹊桥仙乜斜他一眼:还老同学呢,你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过我?当年,你春猫子似的三天两头往那边窜,谁渡你过河的?尽管你嘴巴闸得严,一直滴水不漏,可我早瞧出猫腻来了。这些年,如果不是我替你捂着,如果大伙儿都知道你是个过河拆桥的负心汉,恐怕你脊梁骨早给人戳碎了。照我看啊,其实这事你早该这么做了,咋这时候才想起要过河去找她呢?
刘德草忽然想起老人曾经救过芳草一命,于是奇怪地问,您没劝过她吗,她总该听您一句吧?
鹊桥仙沮丧地说,劝过,没用!我看啊,解铃还须系铃人,也只有你才能解开这个结了。又说,你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为啥每天还守着一条破船,有时候即便是空着仓,还不是照样这么摇来摇去的,你说图个啥?我还不是巴望哪天飞来一群喜鹊,这梨香溪上突然升起一座鹊桥来,让两边重归于好……
说到这儿,老人拿袖子搌了搌眼角,眼眶竟然有些湿了。刘德草心里更是五味杂陈,想当年自己真是糊涂,怎么就轻易信了母亲那句话,以为芳草真的嫁人,跟人远走高飞了呢?不过,后来他确实再也没收到她写的信了,他给她写的信也从此没了回音。他曾经到她家里去过一趟,她家里人说,她外出打工已经好几年没归家了,他们也不知道她究竟去哪儿了。一段初恋就这样戛然而止。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心急火燎地四处找工作,等有了工作,一段新的爱情又悄然走近了。接下来就是结婚生子,疲于应对工作的种种压力和生活的无尽琐碎,那段青涩的初恋就像潮汐一样,在他记忆当中渐渐消退了。后来,当芳草在彼岸长成一棵大树,仰望之际,他骤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卑微,甚至连走近一步的勇气也没有了,于是,梨香溪成了挡在他面前的一道坎,成了他此生再也无法逾越的鸿沟。后来,当他收到那个陌生女子发来的短信,倏然心潮起伏,时光裁剪的碎片纷纷攘攘地向他飞来,他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虽然那条短信寥寥数行,内容也很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却是令人品咂,意味深长。那女子说她是织女集团董事长秘书,她是受董事长委托,才主动跟他联系的,希望他有空到织女集团一趟,董事长将要亲自和他面谈一项重要业务,并当面奉还一样特殊礼物。那一刻,他心里怦怦直跳,不由得浮想联翩。特殊礼物?就是当年他送给她的那枚小小的戒指吗?重要业务?他一直忝居于一群自命清高的文化人当中,从未染指过生意方面的事情,也从没有过弃文从商、一夜暴富的梦想和企图,能有啥重要业务可谈呢?他蒙了,但很快就会心地笑了——那一笑是苦涩的,也是卑微的,或者干脆说就是卑鄙的。他想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很难看,甚至十分恶心,犹如那个月色修饰的夜晚……
昨天,当他接到那个女秘书打来的预约电话,同样是那么苦涩而又卑微地笑了,那一刻他找不到其他释放自己和表达心声的更好方式,那死水微澜似的一笑纵然很丑,却很真实。
四
刘德草刚上岸,一个白衣女子便款步迎上来,眼波流转地打量了他一下,笑吟吟地问,您是……您就是刘书记吗?
刘德草一听声音便知,面前这个女子,便是那个给他打电话的女秘书了。女秘书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手来,他有些局促,一只手正要迎上去,女秘书却莞尔一笑,亲昵地将他挽住了,然后将他请进了一辆乳白色小汽车。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街道,刘德草一直盯着窗外,他有些恍惚,恍惚间是在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那个昔日的渔村已经远去,眼前到处是高楼大厦和繁花绿草,找不到一丝熟悉的痕迹。其实,织女城以前也是一座村庄,一座靠水吃水的小渔村,不过,渔村早就咸鱼翻身,城镇化了,比起繁华的都市已然没啥差别。他不禁轻叹一声,唉,两座村庄同饮一河水,犹如衔着同一个母乳长大的孩子,可一个出落得亭亭玉立,另一个却是生得灰头土脸。
女秘书一边驱车行驶,一边小嘴不停地播广告:织女城是一座现代化的服装服饰工业城,虽然它发端于一个小小渔村,最初的规模也是小得可怜,可随着小宇宙爆炸式的不断裂变,其辐射半径现在已经覆盖所有周边村庄。如果用一个模糊概念来形容,只能是一个字——大;倘若找一个具体参照物来比拟,那就是它比一座普通县城的体量还要大出许多;假如非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呢,那就只能是一个“牛”字。
女秘书说,集团总部以前一直在渔村,前不久搬迁到织女城的东环去了,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说着,她打开车载音乐。
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
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我们的爱虽然已经死去
可我依然期盼你能再次回来
让你看看我的精彩和美丽
只是希望你别再披那件牛皮
因为我已不是从前那个傻傻的织女
……
歌曲声声入耳、句句锥心。刘德草如坐针毡,说这音乐太吵,他有点晕车,想安静一点。
女秘书赶紧关掉音乐,递给他一瓶矿泉水,问他是不是有点中暑了,也许喝一点水就好了。接着歉意地说,这是董事长的坐骑,车上就这么一支曲子。董事长说这歌曲挺励志的,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捯着听。不过我比较赞同您的说法,这歌确实有点吵,活像小女子被人一脚踹了,爬起来了还要跟人矫情似的。
女秘书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没掺一点本地口音。刘德草第一次听她在电话中说话,就被她的声音迷住了。显然,听女秘书说话要比欣赏那个歌曲要享受得多,于是主动跟她搭讪,姑娘,你贵姓芳名?
女秘书轻描淡写地一笑,说,姓不贵,名字也不芳,普通得就像一棵小草——我是蒲董事长秘书,您就简称我“秘书”吧。
刘德草又问,你不是本地人吧?
女秘书说,是吧,也不全是。
刘德草不明其意,转念一想,织女城就像一个巨大的鸟巢,许多外地女子候鸟迁徙似的朝这里涌来,有的是在这里打工就业,有的干脆就在这里栖息落户,想必这女子便是嫁到这里的外乡人了。刘德草不经意地多瞅了女秘书一眼,发现这女子确实漂亮,眉清目秀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就像他手里的矿泉水,清澈得不掺一点渣子;脸上也是白皙干净,没有一丝瑕疵,显然不像一个浸染了红尘俗事的已婚女子。
集团总部到了。刘德草举目张望了一下,只见整个集团大厦由三个部分组成,左边是织女生产研发中心,右边是织女国际宾馆,中间是集团写字楼,“银河集团”四个大字高耸云端,醒目地矗立在写字楼最顶端。刘德草有些好奇,不是织女集团吗,怎么又叫银河集团?
两人乘电梯直抵集团高层办公区。就在女秘书推门进入董事长办公室的一刹那,刘德草突然感觉那只戴着戒指的手,恨恨地攥成拳头,雨点般地朝他砸来了,那拳头不是砸在他身上,而是猛烈地砸在他心里,砸得他心里嗵嗵直响,额头猝然蹦出了许多豆大的汗珠。
女秘书看他一眼,忍不住想笑,却又掩嘴把笑抿回去了,说,别激动,董事长这会儿不在办公室呢,她让我先陪您聊聊。说罢,朝着放有地球仪的董事长办公桌走去,径直坐在了主人位置上。
女秘书示意刘德草在她对面就座,然后伸出手指优雅地点了一下地球仪,地球仪迅疾旋转起来。望着飞速旋转的地球仪,女秘书喃喃自语道,地球真小呀,可它转得那么快,以至于我们都快跟不上节奏了。接着又说,您刚才看到“银河集团”几个字,是不是有些困惑?其实,这是两代织女、两种不同观念所碰撞的结果,结果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即将酝酿成熟,而首当其冲要改变的,就是“织女”这个称谓。织女这个名字固然很美,但却充满了悲情色彩,而且格局太小,缺乏宏观性战略眼光,所以我们不久将正式更名为“银河集团”。
刘德草恍然大悟,心想这名字确实比原来要大气,不由得点头赞道,银河比地球大,包容性也更强——这名字改得好!
女秘书继续说,未来的银河集团将放眼全球市场,集团大本营在继续东进的同时,将重点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固步自封,跨过梨香溪,向西延伸!
刘德草心里咯噔一下,女秘书释放的这一信息直接击中他的兴奋点,他抑制不住兴奋地连连点头,忙不迭声地说,好!向西、向西……
向西就是鹊村,他此行的目的不就是引织女向西,试图让鹊村人搭上织女这趟飞奔的快车?不过,兴奋之余他又有些怀疑,毕竟,这话是从一个小秘书嘴里说出来的,显然缺乏权威性。他望了望地球仪,地球仪仍在旋转,他有些眼花缭乱,又将目光移到女秘书脸上,试图从她的表情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两人的目光正好触碰在一起,此时,女秘书那双水亮的大眼睛就像星光似的忽闪忽闪,闪得他突然有些恍惚,恍惚又回到了那个满天星汉、一弯瘦月的夜晚……
直到女秘书连喊两声“刘书记”,又拿手在他面前晃了晃,刘德草这才回过神来,说,我这不是做梦吧,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女秘书说,好了,不闲聊了,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刘德草疑惑地问,不是说董事长亲自跟我面谈吗?
女秘书说,董事长身体不是太好,现在许多事情都是由我直接替她打理。您放心,我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也是可以向集团和您负责的。
女秘书不容置疑的口吻让刘德草暗暗吃惊,心想这女子不过也就二十来岁,竟有如此大的能量和担当,比照自己,这大半辈子真是个窝囊鼠辈,白活了!
女秘书说,目前我们正在搞一个“一桥一路”计划,今天请您刘书记亲自过河来,就是想跟您谈一谈这桩业务,听一听您的意见。说着,她起身邀请刘德草移步窗前说话。她将窗帷哗地拉开,眺望远处说,梨香溪可真是一条美丽的母亲河啊,可躺在她怀里的两个孩子却是那么的不同。前些天我特地过河看了看,真是看着都是泪,说来都是痛啊。您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好项目,得尽快把乡亲们扶起来呀。
刘德草迟疑了一下说,项目倒不是问题,就是资金是个大问题。比如说,我想利用梨香溪滩涂的天然草场资源,带着大伙搞个万头野猪场、千头养牛场……
不待他说完,女秘书当即打断,那怎么行?那可是两岸唯一可以深呼吸的天然氧吧,千万不能再糟蹋了。董事长至今都还后悔不已呢,东岸的那片绿洲一旦牺牲,从此再也回不来了。西岸的那片绿地得好生保护起来才是,以后可以建一个梨香溪湿地公园。接着问他还有什么项目,刘德草说没想好,暂时没有了。
既然没有了,那就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吧。女秘书说,我们的“一桥一路”计划,就是打算在梨香溪架一座桥梁,给鹊村修一条标准四车道的柏油马路,让两岸相连,使鹊村和外面的世界通畅起来。不过,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求把鹊村纳入我们的辐射和发展半径,以增加集团的外延空间,解决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土地不足的问题。
这哪是什么洽谈业务啊,分明就是往鹊村人头顶上砸金砖嘛!刘德草激动得无以名状,高兴得恨不得跳楼——直接跳下楼去,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鹊村的乡亲们,告诉马副区长。对了,还要告诉正等着他好消息的鹊桥仙。他紧握住女秘书的手说,谢谢,真是太感谢啦!
女秘书突然咧着嘴叫唤了一声,刘德草这才意识到,刚才那浑然不觉的发力一握,竟然把女秘书的小手握疼了。刘德草非常尴尬,连声说对不起,女秘书却甩了甩手说,没事没事,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吧……
此时,刘德草惊讶地发现,女秘书那只甩动的左手食指上,居然戴着一枚传统款式的老戒指,戒指上竟然也有一个“喜鹊踏梅”——他一眼得出结论,这便是当年他戴在芳草手上的那一枚。
刘德草呆望着戒指,半天才愧疚地说,戒指就不用还我了——如果你喜欢,我就送给你吧。
女秘书睨他一眼,嗔道,这是董事长送给我的,干吗要还给您,又干吗要您送给我呀?
刘德草懵懂地问,既然不是这枚戒指,那你说的特殊礼物又是什么呢?
女秘书调皮地一笑,朝自己指了指,一字一顿地说,特殊礼物嘛……特殊礼物就是我呀!
刘德草愣怔地看了女秘书一眼,发现女秘书也是定定地望着他,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就像一条美丽的河。女秘书的嘴唇忽然嚅动了两下,似乎想要说什么,可最终却什么也没说,眼泪哗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