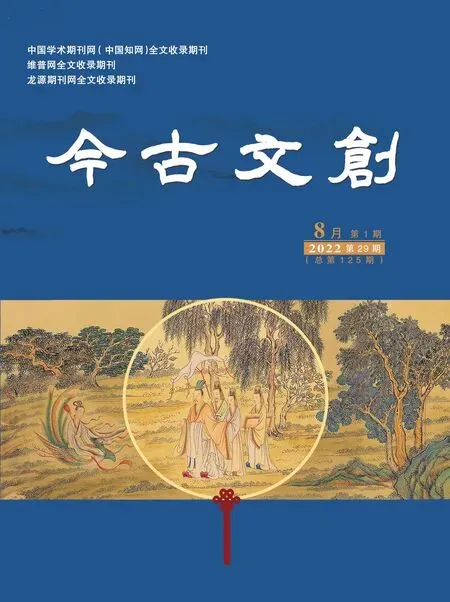《明实录》中方孝孺的政治形象塑造
◎魏圆圆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方孝孺,明初著名儒臣,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卒于明建文四年(1402)。自幼警敏,资质过人,被宋濂称赞为孤凤凰“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宁海县志》称:“诸儒所长,互有得失,孝孺卓然为一世儒宗。”明清士儒皆尊其为正学和读书种子。
朱允炆即位后非常器重方孝孺,“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
方孝孺坚定支持建文帝削藩,但燕王朱棣兵破南京后,方孝孺作为建文帝遗臣而殉难。
朱棣以藩王身份起兵夺位,一直重视塑造自身的合法性。自起兵以来,朱棣以“清君侧”为旗号,着力将靖难之役爆发、发展等理由归结为建文帝身边“奸臣”挑拨宗室矛盾,强调自己是被迫维护祖训。朱棣即位后,先后组织臣下编写了《奉天靖难记》,重新编修《太祖实录》,丑化建文君臣。由于方孝孺始终主张削藩,且坚决不肯投降,明朝前期官方对于方孝孺的历史书写基本奉承“春秋笔法”的主旨,重点强调方孝孺的各种过失,以达到抹黑建文君臣、美化朱棣的目的,从而为靖难之役和朱棣夺权篡位的行为制造合法性依据。下文从《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中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记述加以讨论。
《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中方孝孺被塑造成顽固好战、专横迂腐、贪生怕死的形象。
一、顽固好战、祸国殃民的形象
建文二年七月,李景隆屡败燕军,退至济南之际,建文朝便派李得成与燕军讲和,朱棣借机让李得成带回他愿意罢兵息民的消息。这时候突如其来的一场承天门灾挑动着不少人的神经。“九月壬戌朔,先是承天门灾,朝臣多言宜罢兵息民以答天谴,翰林文学博士方孝孺独言:‘诸侯当灭之应’”。《明太祖实录》记述了方孝孺面对突如其来的承天门灾祸的反应,他不光没有听取朝臣的建议罢兵休战,还力排众议、坚持战争,将此灾解释为是诸侯将灭的应召。
承天门灾事件在《奉天靖难记》中也有记载:
九月壬戌朔。先是承天门灾,占者以为天示警戒,欲劝允炆息兵。方孝孺独言:“承天门灾,应在诸侯灭之象。”闻者切齿。
《明太祖实录》的内容多来源于《奉天靖难记》,但是关于承天门灾事件,《奉天靖难记》指责的色彩更加浓烈一些。《奉天靖难记》中劝说建文帝偃兵息民的对象不再是群臣而是占卜者,方孝孺反抗的不光是群臣议论还有上天的旨意。《明太祖实录》对于承天门灾的记叙态度更加缓和一些,没有直接贬低方孝孺的词汇,而是通过罗列群臣和方孝孺的态度来衬托方孝孺的独断专行。虽然同基于抹黑建文君臣、对其事迹进行丑化的修史基调,但是《明实录》由于本身的修纂范式问题,所以对于对方孝孺的直接抨击更为克制。
此外,《明实录》中多次提到了燕王、建文帝都试图议和,而遭方孝孺阻拦。
朱棣发动靖难之战的旗号是清君侧,建文三年齐泰、黄子澄被黜,朱棣上书商议罢兵:“初闻齐、黄被黜,即以遍告三军将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权奸矣。且夕必下宽贷洗雪之恩,吾与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明太宗实录》称:“建文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诏宣言,欲罢兵”。但方孝孺反对议和并寄希望于缓兵致胜,“我方将怠之此奏之来止,宜令各处兵已多集,独云南兵未至,燕军久驻大名,暑雨为沴,不战将自困”。
《明太宗实录》又载,燕王希望吴杰平、安盛庸撤兵,建文帝想让燕王缴械,于是燕王继续派使者武胜上书:
虽臣将士不能无疑于权奸之欺,臣之父子盖已欣戴陛下之仁矣……此皆奸臣之所为,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闻耶。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亲也。今为奸臣所恶,陛下虽有怜之之心,而不能见疵,则臣所以自救之计,敢一日而忽之哉?……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无任战兢俟命之至。
而《明实录》中建文朝臣对此的反应则是:
书进,建文君览之,益感悟有罢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词甚直,奈何?”孝孺未言。建文君曰:“此孝康皇帝同产弟,朕叔父也,今日无辜罪之,他日不见宗庙神灵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罢兵耶,天下军马一散,即难复聚,彼或长驱犯阙,何以御之,骑虎之势可下哉?且今军马毕集不数日,必有捷报,毋感其言。”孝孺出,矫命锦衣卫执武胜系狱。
《奉天靖难记》也当中收录了燕王信件,还记载了建文君臣的反应:
允炆见书,颇有感动,方孝孺在傍力争曰:“今军马四集,不数日必有捷报,毋听其言。”遂执武胜系狱。
《奉天靖难记》与《明实录》都强调了朱允炆见朱棣上书之后,都有所感动,但是《明实录》更加明确,指出了建文帝也有罢兵之意“益感悟有罢意”。两者都在行文上表明了罢兵的可能性,且都把最后的责任归咎于方孝孺从中作梗,而使得燕王与建文帝君臣之义彻底绝裂,靖难之役必不可免。其实无论方孝孺如何抉择,燕王并不会因此而罢兵,两书的叙述都将拒绝息兵的罪责归到了方孝孺身上为燕王不愿罢兵而继续征战找了借口。《明太宗实录》这样塑造方孝孺顽固好战、祸国殃民的形象,有助于将战争责任推给方孝孺。
二、专断独行、挑拨离间的形象
《明实录》也存在利用方孝孺为建文帝决策失误做替罪羊的现象。在任命薛嵓一事上,《明太宗实录》记载:“建文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诏宣言,欲罢兵。建文君览诏曰:‘既欲怠之,则当婉辞,庶几肯从’。孝孺曰:‘辞婉则示弱矣’。遂令大理少卿薛嵓赍至军中密散之,以懈我将士心,嵓竟匿宣谕不敢出。”《奉天靖难记》调整了叙述任命薛嵓和讨论言辞是否需要委婉的讨论的顺序,“允炆善其策,乃以大理少卿薛嵓等赍诏至军,阳言休兵。”《明实录》中把叙事放在方孝孺说“辞婉则示弱矣”之后,让人联想到是方孝孺任用的薛嵓。而《奉天靖难记》里面明确地说明了在朱允炆同意方孝孺计策之后,朱允炆任命薛嵓办理此事。《明史·方孝孺传》当中亦延续的是《奉天靖难记》中的叙事方式。
虽然在承天门灾事件上面《明实录》对方孝孺的态度更加缓和委婉一些,但是一旦涉及皇帝的是非对错之时,《明实录》会通过一些粉饰和模糊,将责任推卸给方孝孺的刚愎自用和决策失误,以维护建文帝背后的朱明王朝颜面。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在面对连连败绩、德州饷道又绝的情况之下,方孝孺献上了离间计:
“燕世子孝谨仁厚,得国人心,燕王最爱之,而其弟高燧狡谲,素忌其宠,屡谗之于父不信。今但用计离间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则必趣归北平,即吾德州之饷道通矣,饷道通即兵气振,可图进取也。”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悉?”孝孺曰:“臣之徒有林嘉猷者,燕王尝召至府中居久,故得之悉。”建文君曰:“此策固善,但父子钟爱既深,恐未能间之。”孝孺曰:“可行。”遂令孝孺草书贻世子,令背父归朝,许以燕王之位,而令锦衣卫千户张安赍诣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遣人送军前。时中官黄俨奸险,素为世子所恶,而高燧深结之为己地。及安持书至,俨已先遣人驰报上曰:“朝廷与世子已通密谋。”上不信,高煦时侍上,亦替俨言非谬,上亦不信。语竟,世子所遣人以书及张安皆至。上览书叹曰:“甚矣,奸人之险诈。吾父子至亲爱,犹见离间,况君臣哉?”
《明实录》对于离间计的记载非常详细,尤其是方孝孺分析燕王二子关系、性格等处在《奉天靖难记》中无所考。这里存在一些可疑之处,既然方孝孺深知燕世子为燕王最爱,那燕王的藩王之位于朱高炽而言乃是囊中之物,信中劝燕世子背叛朱棣的条件是“许以燕王之位”,其实对于朱高炽而言并没有什么诱惑力,方孝孺为何要明知而行呢?其实燕王最爱的也并非燕世子,而是朱高煦。朱棣曾在靖难途中对朱高煦直言:“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病”,暗含着对朱高煦作为继承人的认可。朱高煦常常随父出征,战功赫赫,“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
《明太宗实录》对于方孝孺分析燕王儿子关系的描述放在这里有许多抵牾之处,但是回到《明太宗实录》的修纂背景来看,便可以有所理解。《明太宗实录》为朱棣的继任者朱高炽遣人修纂,正是因为朱棣对朱高煦的偏爱,使得朱高炽多次处在皇位动摇的边缘。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明仁宗朝在实录修纂时进行了许多美化,直言朱高炽最受先皇宠爱与信任,并在离间计当中能够果断处理,抬高明仁宗的同时还不忘记叙朱高燧、朱高煦对明仁宗的不断诬陷,有利于帮助明仁宗塑造其光辉形象和正统地位。
建文四年,建文朝败绩连连,许多将士率众投降、六部大臣皆图自全朝廷派郡主与朱棣交谈,《明实录》对此的记载是:
上见郡主,恸哭曰:“我父陵土未干,我兄弟频见残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且一入谗臣之言,即如胶漆不可解。至亲之言,纵倾吐肝心,如水洗石。今我之来,岂其得也哉?”
《明太宗实录》控诉了方孝孺的“谗臣”性质,在打压方孝孺的同时为建文帝粉饰,也掩盖朱棣篡位夺权的昭然之心。
三、迂腐无能、贪生怕死的形象
燕军抵近南京时,方孝孺扬言:“长江可当十万兵。江北船已遣人尽烧之矣,北兵能飞度?况天气蒸,易以染疾,不十日,彼自退。若遽度江,祇送死耳。”从《明太宗实录》这段记载看,方孝孺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燕军的强大和局势的危急,《明太宗实录》这样书写意在表达方孝孺在军事方面的无知与无能。《奉天靖难记》还特意记载了人们对于方孝孺这番言论的态度:“其言缪妄,识者笑之”,讽刺了方孝孺的大言不惭、纸上谈兵之举。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率军横渡长江直达南京,朱橞开门投降,燕王军“按兵而入,城中军民皆具香花夹道迎拜,将士入城肃然,秋毫无犯,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在《明实录》的笔下,不光守城将领愿意投降迎接燕王朱棣,城中百姓也欢喜迎接,一派民心所向的景象。朱棣马上见了周王、齐王。周王曰:“天生大兄,戡定祸乱社稷,保全骨肉,不然皆落奸臣之手矣。”《明实录》借周王之口,将靖难之役的谋权篡位粉饰为燕王扫除奸臣、勘定祸乱、保全骨肉的义举。
最后靖难之役以建文帝阖宫自焚宣告结束,方孝孺的命运也随着发生改变。方孝孺从朝廷重臣变为了被拘罪臣:
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执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
《明实录》的叙述下,建文朝辅弼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一起被列为奸臣。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策划靖难之役,仅将齐泰、黄子澄视为奸臣。《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癸酉,燕王誓师,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明史》载:“上书天子指泰、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自署官属,称其师曰‘靖难’”。
为了继续为这场政变找合理性,方孝孺和齐泰、黄子澄一样成了燕军的众矢之的,也被加入了奸臣的行列。在《明实录》的记叙中方孝孺被抓捕之后并没有慷慨赴义、为国殉难而是“扣头祈哀”。方孝孺之死在《奉天靖难记》中的记载与《明实录》相似:“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折哀乞怜,遂命收之”。两者的记叙大部分文字相同,部分更改,都强调孝孺面对燕王叩头乞哀的情形,塑造了方孝孺罪恶滔天而又乞怜求饶的宵小形象。
四、总结
《明实录》中方孝孺形象的构建充斥着永乐君臣的政治利益诉求。《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对于方孝孺的记载大部分皆为奸臣形象。当只谈及方孝孺时,《明太宗实录》比较克制,删减了《奉天靖难记》当中对方孝孺评论、贬低的直接记述,通过委婉、反衬的方式烘托方孝孺顽固好战、祸国殃民的形象。但是,一旦涉及皇帝是非对错之际,《明太宗实录》对方孝孺的态度就会改变。《明太宗实录》通过粉饰、主语模糊化等手段将方孝孺塑造成专断独行、挑拨离间的奸佞,建文帝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只能听之任之。在面对敌军时,方孝孺十分轻敌,决策上迂腐无能。城破失败后,方孝孺折哀乞怜,塑造了方孝孺迂腐无能、贪生怕死的形象。
《明太宗实录》着力将靖难之役爆发、发展等理由归结为建文帝身边的“奸臣”所致,削弱建文帝作用。实际上不仅仅是太宗实录的历史书写,早在燕王起兵之初就编织了这样一种“清君侧”的说法,朱棣即位以后更是把这种逻辑作为他合法性的重要论据。太宗实录的编修者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严守旨意。朱棣需要给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又不能直接攻讦建文帝之过,便通过丑化方孝孺等建文帝身边大臣来推脱罪责。所以明朝前期对于方孝孺的书写基本奉承“春秋笔法”的主旨,以达到否定建文帝的正统地位、歪曲历史、抹黑建文君臣、美化朱棣的目的,从而为靖难之役和朱棣夺权篡位的行为制造合法性依据。
注释:
①(明)宋濂:《送方生还天台诗并序》,收录于宋濂著,徐光大校点:《逊志斋集》,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867页。
②(明)宋奎光:《宁海县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页。
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41,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明太祖实录》,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⑤《奉天靖难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⑥《明太宗实录》,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⑦(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7,中华书局,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