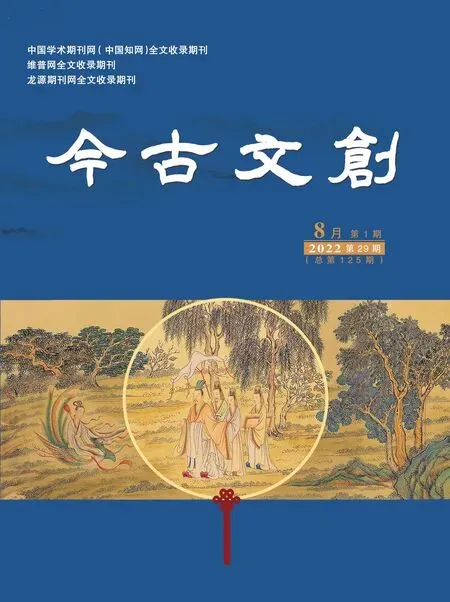《雪国》:日本物哀文化之“悲美”交融
◎陈伊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日本三大主流美学文化: 物哀、幽玄、侘寂,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特色,在《雪国》中“物哀”美学占主导地位。作品中作者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和架构,甚至是模糊人物具体描绘的笔法,最终通过一种朦胧虚无的意境构造,近于风流甚至颓唐的笔法传达若有若无的人物神韵。半虚半实的世界弥漫着淡淡的哀伤,表达日本传统审美下的自然美学,将“物哀”文化以新的尝试立于文坛。其次,“物哀”文化强调的重点是“悲与美是相通的”,这两股势力始终贯穿着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作品的灵魂,同时也是吸引无数读者并为之动容的最主要原因。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呈现作品在物哀文化下的“悲美”交融,体会日本文学的美感世界。
一、“悲美”交融:悲哀与爱情
关于《雪国》谁是叙述中心的问题,学者们的解读存在分歧。而作者的观点是,“我认为与其说以岛村为中心把驹子和叶子放在两边,不如说以驹子为中心把岛村和叶子放在两边好。”近代以来虽存在“作者已死”等的评判视角,以此来忽视作家创作立场,但这部作品至少还不能够完全脱离作者而独立于读者想象世界,并且“以驹子为中心”这种看法无疑是明智的。倘若是持前者观点,那么作品的讲述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与他眼里的艺妓形象,加之对爱情不忠、玩弄女性,其形象并不讨喜。因而笔者认为,以岛村为主要表达人物,作品的可挖掘性不大,也无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但若是持后者观点,以驹子为中心,那么作品可挖掘之处将会丰富得多,读者所处视角看到的将会比岛村自视清高、满眼虚无的视角丰富得多。
《雪国》的第一层悲美是对男女恋情的哀感,集中体现为驹子对岛村的感情真挚、热烈,飞蛾扑火。
驹子第一次遇见岛村,还处在纯情的少女时代,作者着墨最多的就是她的“干净”,连“脚趾弯”也是干净的。或许正是因为岛村不想破坏这份干净,所以请驹子帮他另寻一名艺妓。驹子说:“你这种人倒是少见。”两人的初次见面,岛村把驹子当作良家女子来看待,互相成为聊天的伴儿,而驹子也被岛村的学识和修养所吸引,以致到后来对他的依恋不断增加,朦胧爱意的萌发渐渐产生。
然而,二者的情感关系实际是不平等的,驹子对岛村近乎卑微,甚至是一种单向的畸形爱慕。在第二次岛村来到雪国时,两人见面,“虽然发生过那种事情,但他没有来信,也没有约会,更没有信守诺言送来舞蹈造型的书。”“岛村是应该首先向她赔礼道歉或解释一番的,但岛村没有正眼瞧她,就径直往前走,他察觉到她非但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反而还对自己一片痴情。”驹子在原地的苦苦等待,只等来心爱之人的冷漠和无视,纵使这样自尊被践踏却也毫无责备。而在岛村眼里,她只不过是度假解闷的玩物,对于女子的痴情只是感慨于自己的魅力。之后两人熟络第发生关系,岛村对驹子说:“你是个好姑娘”“你是一个好女人。”驹子一直追问怎么个好法,岛村没有说话。驹子失望地说:“你说嘛。你就是因为这个常来的?你是在笑我,你还在笑我呀?”驹子难受得落泪,走出房间,可是很快又轻手轻脚地回来,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自尊在面对岛村时根本不存在。驹子就是这样在反复被伤害后,自我愈合,又再一次重新扑向没有结果的爱情,呈现出妥协和卑微的姿态。
对于岛村而言,对驹子只是怜悯,她只是一个排遣空虚寂寞的对象。
岛村是已有妻室的人,却因一面之缘爱上了驹子,后来滥情地迷恋上叶子。事实上,他只是把驹子一类人看成了“玩物”,追求的只是一种虚幻短暂的爱情,妄图从女性身上寻求安慰。他完全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文中有一段写到,“岛村了解驹子的一切,但驹子对岛村一无所知。驹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升,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的心田。”驹子的热烈在岛村的心中不过是飘落的雪花罢了,但雪花终会融化,最后不剩一点痕迹。
川端康成说:“在感情上,驹子的悲哀也就是我的悲哀所以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吧。”驹子也渴望像普通女人一样拥有爱情,可惜遇上了悲哀的感情,错误地爱人,让读者为驹子的付出感到惋惜和同情。但尽管这是一份徒劳的爱情,我们同样能为驹子的热烈、真挚而感动。热烈而真挚的爱情是美的,飞蛾扑火的勇敢更是美得不可方物。
二、“悲美”交融:人生“徒劳”走向绝望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驹子的人生是一出壮烈的悲剧,所以在岛村看来驹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毫无意义的。驹子努力读书做笔记是毫无意义的;在寂寥的山村里勤奋地练琴是毫无意义的;给即将去世的行男治病是毫无意义的;爱上根本不可能会爱她的人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只剩叶子一人,也在火海中走到了尽头,仿佛守护仅存的叶子也是没有意义的。看见所有努力原来都成了徒劳,驹子也疯了。
小说中驹子和叶子两人交集甚少,基本看不出二者关系的亲昵,更多是清疏或者带有一些嫉妒的言语。如驹子在看见叶子存在于岛村眼里时,说:“别以为我在这撒酒疯,每当想到她在你身边会受到你的疼爱,我在山沟里过放荡生活才痛快呢。”还有一些零碎的片段出现两个人的相遇,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读者只知道驹子、叶子和行男的微妙关系,但叶子最后死的时候,驹子疯了。文中写到驹子抱着叶子“像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其次,驹子堕入风尘,为了给行男治病,叶子同驹子的身世一样凄惨,但却能保持纯洁的品性,“叶子总在厨房里帮忙,从没赴宴陪过客。”更爱行男的叶子没有和驹子一样堕入风尘,反而还保持着来自世间的绝对纯净,可以推测驹子的帮助必不可少。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加引人深思,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性效果。
作者承认驹子是有原型的,但叶子是虚构出来的,为什么要虚构一个叶子呢?除了男性视角的灵肉分离,还代表着驹子的美好理想,她纯净、不沾染世俗的污秽,是仅剩的家人,而驹子早已堕入风尘,受人凌辱糟蹋也要保持温顺姿态。驹子保护着她,何尝不是保护着自己仅存的精神理想,最后叶子的死代表着亲人的死、精神的死,是徒劳的再次证明,驹子疯了的结局合情合理。小说中有一个看似无情的场景却是驹子的难言之痛,行男死的时候,驹子在火车站送岛村,叶子求她回去见最后一面,“驹子忍受着肩头的疼痛,闭上眼睛脸色刷地变白了。但出乎意料地断然摇头说:‘我在送客人,我现在回不去。’”原因有二,其一确有对岛村的留恋,希望可以跟他相处更久一点,但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回去面对自己所付出的惨烈代价最终是徒劳一场。故事最后,行男已经死了,岛村不爱自己,每日陷入肮脏的无法被救赎的生活,世界无望仅剩驹子作陪,却也命葬火海。最终证明了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就好像自己正如岛村眼中的那样,自己生存本身就是徒劳的。
驹子所做的一切,对她自己来说,只是想有尊严有价值地活下去。她始终在与自己周围的环境抗争着,可最终她的抗争只是成了一种虚无的东西,她的抗争是实实在在的,可最终的结果却是虚无的。在这实与虚的矛盾中,驹子的人生化为了一种真真正正的徒劳的悲哀。
三、“悲美”交融:死亡的美学艺术
“物哀”不仅仅是日本审美文化,还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作者川康端成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口含煤气管的自杀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纸质遗书。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在日本文化中,他们并不把死亡看作过于悲痛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淡然的哀伤审视万物规律,生命衰亡是美的一种表现,可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的静寂”。
《雪国》中叶子的死是故事的结局,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岛村突感心头一震,他仿佛没有马上预感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的幻影。僵直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然而,她的模样宛若没有一丝反抗的玩偶,正因生命不复存在而重获了自由一般,一刹那,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叶子的死,川端康成借岛村的意识流,传达“生命不复存在而重获自由一般”“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的感受,可见“死”对于川端康成来说并不是悲剧。还有值得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叶子坠落时“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川端康成从小就参加各种葬礼,死去的亲人在棺材里平躺着,外面的人们痛哭哀悼,是他最为熟悉的场景。而大量频繁的参加这种仪式,对川端康成的生命观、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叶子坠落的过程中也是保持水平的姿势,实际上川端康成已经借助岛村的意识流对叶子的死亡做出了哀悼,叶子的坠落正如人们到生命尽头所呈现的那样,肃穆沉寂。
这个结局川端康成坦言纠结了很久,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可以说,叶子的死是作者的偏爱。叶子向岛村请求带她去东京,岛村问叶子想要在东京做什么,叶子回答“一个女人总会有办法的”。那个时代日本底层女性的生存手段大多走向驹子那条幽暗的道路,川端康成不愿意她成为第二个驹子。为了保持她超凡脱俗的纯洁形象,让这种理想之美免遭命运的扼杀,但又无法为叶子找寻真正的出路,最终川端康成选择用一场熊熊烈火净化世间的纷扰。“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都停歇了。”死而永生,不灭为美。叶子的死亡并非真正的死亡,而是一种升华。川端康成将这种超脱现实的虚无之美永远封存在雪国。美好与悲剧在同一时刻产生强烈的撞击,深刻体现了悲美结合的物哀文化。
四、悲美交融:强大的意境塑造力
1968年诺贝尔颁奖辞称赞川端康成的作品“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这种敏锐的感受力不仅表现在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深入,更在意象的选取、组合、体悟上,并运用高超的叙述技巧创作属于日本美学的意境审美。
“万物有灵”是日本文化对大自然的看法,川端康成作品的环境描写绝非无关紧要的白描或是为了环境本身而大洒笔墨,我们细究其每一个细节,可发现处处留有余情,与人物情绪、情感流动互相补充融合,形成巨大的审美张力。在绝美的意境中融入悲凉的基调,是川端康成作品又一个较大的特点,以颓唐的笔法哀万物,表现了日本民族的精神特质。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作为小说的开头,一向为人所称道。作者通过穿梭在隧道里的火车将读者拉进一个半虚半实的世界。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有意思的分析,“长长的隧道”是象征着女性的产道,雪国是孕育生命的母体,“一片白茫茫”是母体的世界,岛村来到雪国,更像是一种逃离,与代表着物质文明,充满着世俗诱惑和现代罪恶的东京完全隔离开来。岛村来到雪国象征着人摆脱异化的现实回归原始淳朴的尝试。而善良纯洁的驹子无异象征着“热和光”,是暂时驱散人内心“虚无”的力量。笔者认为这与当时日本所处的战败境况有关,1947年川端康成在《哀愁》一文中说“战败后的我,只有回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中去”。国民情绪低落,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对战争的无奈和对军国主义政治的逃避,雪国是岛村度假的地方,何尝不是日本人民心理逃避和栖息之所,川端康成为此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让人们得以摆脱异化的现实,回归到最淳朴原始的世界。
岛村在这趟火车上遇到了叶子。“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动,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现代派作家擅长运用镜子来表现虚实世界,镜子里的世界兼具扭曲和写实,可以成为自我凝视的工具。“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细看,却又扑朔迷离。”在火车上的片段,岛村和叶子没有对话,只有岛村的内心独白,出于对虚无美的欣赏,岛村对叶子的朦胧爱意倾泻而出。而叶子的首次出现就是以这种扑朔迷离的方式存在,越不真实的事物越容易幻灭,一切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虚无缥缈,无法触及。叶子留给读者的,只剩“近乎悲戚的声音”和“如镜般澄澈的眼睛”。字里行间流露着感伤的基调,预示着人物的命运以及结局的走向。
在故事的最后,蚕房失火,叶子从蚕房的二楼坠落。众人陷入一片混乱,驹子踉踉跄跄地走进人群,仿佛带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故事并以这样一句话收尾,“待岛村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
冰冷的现实世界,大雪纷纷落下,毁灭了一切暖色和温情,所有的希望和喜悦都沉落在雪国。岛村妄图欣赏徒劳本身,却陷入徒劳无法自拔。岛村从一开始以上帝视角审视驹子、叶子,认为她们的人生是徒劳,到了最后,自己也成为徒劳的一部分,川端康成最后将所有人都纳入徒劳、虚无之境,悲凉又无可奈何。
作品无论从人物、情节还是环境描写中,都实现了悲美的融合,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温度,川端康成作品的温度是较冰凉的,个体遭受的苦难和命运的挫折,时代的动荡,国民情绪的低落以及原本就具有的日本物哀传统,使意境充满着悲凉的气息。但是纵使作者秉持虚无的思想,但对世间万物仍怀有敬畏之心,对自然美发自内心地欣赏,透过作者的视觉滤镜流动至笔尖,落在纸上。
五、结语
川端康成提倡虚无思想,主张虚无之美。行男悲惨的人生让叶子、驹子的努力变成了徒劳,滥情的岛村让驹子对爱情的追求成了徒劳,作者通过人物的境遇向读者传达的是人生虚无、命运无常之感。但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处事态度,而是带有日本文化特有的物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日本小岛国国民自始以来的多灾多难,本身就带有命运无常之感,再加上川端康成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当时所处的日本战败境况,无常和虚无之感愈加强烈。命运无常,世事虚无,对无法掌控的命运不必去纠结和深陷其中。人们也不必惧怕死亡,死亡只是另一种存在的方式,“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并且在行文过程中保持冰冷的温度以渗透物哀和虚无的思想,运用敏锐的感受和高超的技艺,营造悲凉凄美的气氛,将“悲美”融入行文中的每一次细微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