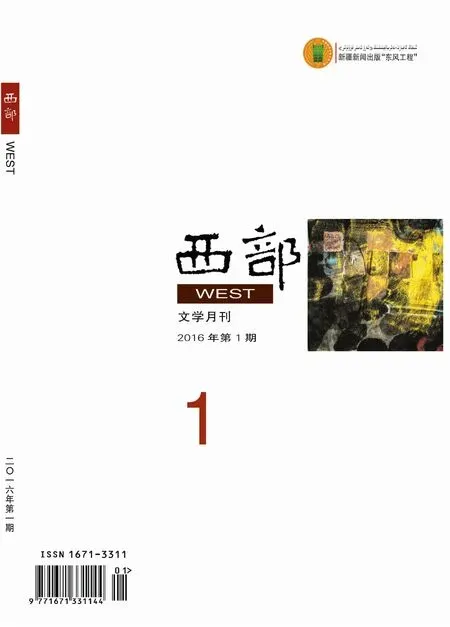燃烧的冰棍
川 宇
燃烧的冰棍
川宇
冰棍一直在燃烧,就像我燃烧的青春一样,让我疼痛并快乐着。
在我憋足劲,鼓起勇气按下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电话号码时,冰棍又开始燃烧了。确切地说,我又想起了一些陈年旧事,想起了羊驹子花白的头发和她倔强的眼神。
“还好吗?”我怯怯地问羊驹子。话筒中没有传来她的声音,而是出现了一个男人磁性的声音:“快,快来接海里麦的电话!”那男人叫优素福,退伍军人,是羊驹子的第六任丈夫。我不情愿地叫了他一声巴巴(长者),然后不再吭声。紧接着,我听到话筒中传出了一阵吧嗒吧嗒的声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脚步声,又好像是谁在敲击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在我胡乱猜测的时候,话筒里传出了羊驹子苍白无力的声音:“好,还好!”听到她声音的一刹那,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酸酸的,一股咸咸的味道开始通过话筒在空气中飘散开来。
哦,她还活着。真好,她还活着。我悠悠地想。握着话筒,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说什么呢?又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只是听她说,偶尔嗯啊一下,随声附和着她的声音。
“之前,我还在想你。”羊驹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地在电话那头说。我想她肯定是孤独太久了,才会在听到我声音的时候那样开心。而电话这头的我却默不作声,只是任那声音在话筒里嗡嗡不停。
想,想顶个啥用?想,就不会从小离开我!我有些怨她。说实话,我甚至还有些恨她。恨她
为什么要撇下我和义思麻不回头地离去?恨她为什么在离去后还要一嫁再嫁?当然,我还是爱她的。天底下有哪一个儿女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爱,爱得撕心裂肺;恨,恨得撕心裂肺。我不知道我脆弱的心到底能容纳多少爱和多少恨。我只知道,羊驹子像一根刺一样长在了我心头,深深地刺疼着我。
说到底,羊驹子其实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她生在饥荒年代,没读过一天书,脑瓜子却很聪慧。因为挨过饿,所以她常常不安分,也不守己,总是想方设法东挣一分钱西挣一分钱。她挣钱的原因也很简单,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为了填饱我和义思麻的肚子。羊驹子的第一个男人鲁格麻,也就是我大(爸),是个铁匠,老实得像个榆木疙瘩。每天他总是不停地打铁,铁锤总是叮叮当当地响个没完。因为打铁,他总把羊驹子缝补的衣服弄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他打铁也挣不了几个钱,为此,他没少挨羊驹子的骂。羊驹子骂他窝囊废,骂他蔫木郎,他也不吭声,只是低着头摆弄着他手里的铁器。他这人就是这样,把什么话都埋在心里。后来,羊驹子渐渐不满足于一日三餐的生活,跑到村子外面挣大钱去了。再后来,她离开了我大,离开了我和义思麻。
羊驹子离开我的时候,我十二岁,义思麻十岁。她走的时候,我和义思麻像两只折断翅膀的小鸟一样,站在涧沟边的小路上,一个劲地淌眼泪。她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都没有看。她只带了一小口袋钱,走了。我恨羊驹子,更恨那口袋里的钱。要是没有那钱,或许羊驹子就不会离开我和义思麻,是吗?我一遍遍地问涧沟里那棵歪脖子树,一遍遍地失望。她走后,义思麻不好好念书,整天跟着一帮死狗烂娃胡混,不是游手好闲,就是打架斗殴,我大也管不住他,只能由着他去了。再后来,义思麻到新疆当兵去了,而我也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沉默不语,只是拼命地念书。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我趋于内向和孤僻的性格。这让我越发恨羊驹子,要是没有羊驹子与我大离婚这茬子事,我或许会是个乐观开朗的人。
三年后,羊驹子再嫁。她嫁给了一个开皮毛货栈的回族老头,听说他特别有钱。要不是因为我想羊驹子,我才不会从涧沟村跑到三十里外的马家沟去,也不会见到那老头。我第一次见到那老头时却傻眼了。那老头根本不老啊,只是留着很长很长的胡子而已。他的长相,我根本就没有记下。为啥要记住他呢?谁也比不上我大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羊驹子问了我好多生活上的细节,那老头也没话找话与我说,我机械地点头,摇头,抑或说上几句他们希望听到的话。不知为什么,那时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是个陌生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庭院,听着两个陌生人有一言没一言的说话声。对我来说,马家沟是陌生的,那老头是陌生的,羊驹子也是陌生的。是的,陌生,一切都是陌生的。最终,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马家沟。
离开的途中,我摇摇晃晃地走着,白帽子和白胡子也在我脑袋中一直摇晃着,晃着晃着我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还好,小轿车没有当场送了我的命,只是让我陷入了短暂的昏迷,随即失去了意识。在没有意识的那些日子,我整天无缘无故地笑,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甚至我的大小便都失禁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整整三个月,奶奶陪着我在箭场里的那座医院里,她不是在我身边念《古兰经》,就是一勺子一勺子喂我喝阿訇念过都阿义(祷文)的糖水。中途,为了替换奶奶,羊驹子来过一次。那次她将我的双手及双脚用绷带绑在了病床的四角,美其名曰在看护我。她那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我的自
由,不让我在医院里到处乱窜。因为我一乱窜,就会跑到其他病人的房间,或是唱歌,或是跳舞,或是与那些病人一起疯癫,闹腾个没完没了。羊驹子绑住了我的四肢,但没有缝住我的嘴巴,我就躺在床上拼命地尖叫,或是大声地唱当时的一些流行歌曲。我的行为让羊驹子特别恼火,她嫌我不安生,吵得她耳膜发疼。不仅如此,她还脱下她的红条绒布鞋使劲地打我。她越打我,我就越发难以控制自己,尖叫声也越来越大。她打累了,便挤在我身旁呼呼大睡。不知为什么,那时羊驹子无论怎样打我,我都感觉不到疼痛,她的红条绒布鞋落在我身上,仿佛一团棉花,轻盈而美妙。那时,我会看着红条绒布鞋咯咯笑个不停,一直笑到所有人的耳朵发疼,笑到穿白大褂的护士给我打一支镇静剂,我才沉沉睡去。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我在箭场里的医院度过了大半年时光。离开医院的时候,院子里的树叶全落了,我认识的几个疯婆子走了,我的好多同学也都考上大学走了。走就走吧,羊驹子也走了,去了新疆。她怎么说走就走呢?纵然我心中万般恨她,她走时也应该看看我呀。她的行为让我越发恨她。那以后,我与她失去了联系。
失去联系的一年后,听人说,她走时与马家沟的那个老头离婚了。又一年后,我再次从别人嘴里得知,羊驹子在新疆塔城又嫁了个男人。塔城的那个男人,是羊驹子的第三任丈夫,听说家境不错,那男人对羊驹子也不错,从不让她上锅抹灶,也不让她干重活。当然,这些都是我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我结婚的时候,羊驹子与那男人还给我邮寄了一套粉红色的床罩。我本以为羊驹子会老老实实地在塔城过日子,但我错了。我结婚后没多久,也就是我二十四岁那年,羊驹子又从塔城回到了这座西北的边陲小镇。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心中除了恨,还多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那些情感里,有爱,有忧,还有好多惆怅,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羊驹子从塔城回来后,奶奶不让我与她有过多的接触,认识她的人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而她却满不在乎,照样打扮得光鲜亮丽,在大街上转悠。我从来没有与羊驹子一起到大街上转悠过,我害怕背后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我刻意躲着她,不去见她。我不去见她,但阻挡不了她来看我。有一天,她带着一个小个子男人来看我,并悄悄问我那男人怎样。我无言。说什么呢?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谁也左右不了。她见我长时间不吭声,便又悄悄带着那男人走了。其实那男人我以前见过,他是西关村的一个手艺人,靠修理汽车维持生计。没多久,她就与那小个子男人结婚了。那小个子男人是她的第四任丈夫。她与他结婚后,送了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总认为羊驹子亏欠了我好多,譬如母亲的疼爱、关怀等等,所以只要羊驹子给我什么东西我都坦然接受。至于羊驹子的那些事,我才懒得管,她要怎样就怎样,随她去吧,只要她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了。
美好的东西总是稍纵即逝。两年后,羊驹子与她的第四任丈夫又离异了。离异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大多数人都把过错归在了羊驹子身上。那时,我真想当着羊驹子的面,将她臭骂一通。可儿不嫌母丑,我又有什么资格去骂她呀?我只能咬牙切齿地恨她,咬牙切齿地怨她。我恨她,是恨她的不负责;我怨她,是怨她的游戏人生。对于她,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只能选择沉默。羊驹子再次离开了小镇,我不知道她离开时是怎么想的,但我猜她一定很落寞。是的,落寞。谁又能体会到她离开时心里的滋味呢?再后来,听人说她去了邻县,在汽车站
旁经营着一家小旅馆。有个男人经常到那家小旅馆去,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轻轻一笑,她结不结婚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左右不了她的生活,她亦左右不了我的生活。我们各自的生活如同两条平行线,无限延伸,无限拓展,没有交汇的那一天。
对于羊驹子的那些事,我听着听着好像已经麻木了。她每结一次婚,我都要在心底恨她一次;她每结一次婚,人们都断定维持时间不长。在人们不断的议论声中,她在邻县的第五次婚姻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一次次失败的婚姻,让她坐实了坏女人的名号。之后,听人说她去了临夏三家集。再之后,听人说她又去了新疆。好几年时间里,我都没有她的音讯。好像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急啊。顿亚(现世)上那个生下我的人不见了踪影,我怎能不急?我不知道她的音讯,就好像饭里面少了盐,没有一丝味道。我害怕啊,害怕她从此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喊她的名字,羊驹子,羊驹子,不,我应该喊她的经名,赛力麦。我之所以喊羊驹子的经名赛力麦,是为了让她在无常(过世)后记得自己的经名。当然,我不希望她有事,我只希望她活着。我在心里喊了声娘,回来吧,我不再恨你了!说实话,自从羊驹子与我大离婚后,因为恨,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喊过她娘。
羊驹子到底是生还是死?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头疼,就无所适从。在我对她的生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大约在我三十岁那年的秋天,羊驹子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我记得那天刮着大风,院子里的梨树沙沙作响,穆萨告诉我大门外有人找我。我跑出院子,看到她站在门外踌躇不前。那一瞬,我喜极而泣,泪水不由地流了下来。活着,羊驹子还活着,我的娘还活着!这比什么都好。我将她迎进了门,同时也迎进了她身后跟着的那个男人,也就是她的第六任丈夫优素福。她怯怯地进了院子,怯怯地看着我和我的孩子。她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正在不安地等待着别人的审问。其实,她大可不必愧疚,更不必怯怯地看我,我早已经原谅了她。无论她曾经有过多少故事,犯过多少错,我都原谅了她,因为她是生我的娘啊!她与优素福在我家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说了一些她的过往。她说,她贩过药材,摆过地摊,做过保姆,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活……等等,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我能够想象一个单身女人在外独自生活的不容易。如果换作我,我肯定会寸步难行。
羊驹子在小镇呆了两天后,就与优素福返回新疆了。他们走的那天,我破天荒地跑到小镇的汽车站去送他们。她以前走我都没有送她。不是我不送,是我害怕小镇上有人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这就是那个婊子养的女儿!”那样的话,像一把刀子,会将我戳得体无完肤。我不想听到那样的话。但是那天,我去送羊驹子了,我给她买了两个锅盖一般大的锅盔。隔着车窗,我看到她眼里溢满了泪水,像锅里面沸腾的清水一样,让我的心也跟着碎了。我没有哭。多年前,羊驹子离开的时候,我就明白泪水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那些年,为了不让人说我,我拼命地学习,拼命地考取大学,拼命地证明着自己。我要证明,卖葱人的孩子不一定还去卖葱,卖蒜人的孩子也不一定还去卖蒜。若干年后,我证明了自己,终于有人说,那女人的女儿与那女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可是,娘还是娘,娘始终是生下我的那个人啊。我看着羊驹子,心疼连连,不知道她此去新疆是否安稳。也许,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吧。
说真话,羊驹子与优素福结婚后,我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就像一根燃烧的冰棍一样备受煎熬。我担心他们最后也会不欢而散。那
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我隔三差五托人打听他们的消息。我所掌握的消息是:第一年,他们养鸡,日子过得很滋润;第二年,他们成了昌吉的养鸡大户,电视台还采访了他们;第三年,禽流感,他们埋了所有的鸡,得到了政府一笔补偿金;第四年,他们很清闲,到全国各地旅游。第五年我却没有他们的消息。于是,我与义思麻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去看羊驹子。很好找,羊驹子与优素福的家就在呼图壁县西关清真寺旁边。我们到的时候,清真寺里的邦克(宣礼)声一声声传进了我的耳朵。
第二天,天色还没大亮,我听到大门响动的声音。羊驹子与优素福推着小推车,拿着扫把出了门。小推车咯吱咯吱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到的那天,看见院子里成堆成堆的垃圾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起。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清扫某一条街道,顺便拾些垃圾回来,光是卖垃圾的钱,都足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小推车走了大约十分钟后,我忽然有种想去帮他们扫大街的冲动,就像小时候我帮羊驹子卖冰棍的心情一样,既迫切又兴奋。我不知道那条大街的名字,只是毫无目的地跑过一条大街又一条大街,在一条条大街上搜寻着羊驹子和优素福的身影。大街上每一个穿橘红色马甲的人,都不是羊驹子,也不是优素福。我有点气馁,蹲在巷道的大树旁长长地喘气。一会儿后,我站起身,跑过一个十字路口,再跑过一个十字跑口,拐过一条路,再拐过一条路,一条大街道就那样出现在了我眼前,羊驹子也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她头上包着棉布头巾,穿着旧军装,正低头将一些垃圾扫到簸箕里,再将其倒入三轮车上。优素福戴着白帽子,穿着橘红色马甲,拿着大扫帚一下一下地清扫着地上被风吹下来的树叶。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羊驹子身旁,夺过她手中的扫帚,一下下扫了起来。那一瞬,我的眼里噙着泪水,但没有流下来。
回去的时候,天刚刚亮,太阳缓缓地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优素福骑着三轮车,三轮车上的垃圾早已被他倒进垃圾集中箱里了,车上换成了我和羊驹子。我坐在车上,忽然有种怪异荒诞的感觉,就好像我与羊驹子成了某个物件似的,被扫在了三轮车上。是的,扫,我像一片落叶一样被轻轻地扫在了三轮车上。我想哭,但却哭不出来。我对羊驹子说:“给我唱首花儿吧。”那是我第一次要求羊驹子给我唱花儿。优素福也一边骑着小推车,一边回头用他那带有浓重新疆味的普通话说:“唱吧,我也没有听过。”羊驹子拗不过我们,说:“都是年轻时的玩耍,不要笑。”她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一道河水挡住了我。公鹅在前面不回头,母鹅在后面叫咯咯……”哈哈,羊驹子把她比作了母鹅,把优素福比作了公鹅。太阳在路的前方缓缓升起,细碎的光照耀着我们,照耀着那条被我们清扫过的马路。我们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
一切都是那样美好,美好得让我无法相信。我宁愿这样的美好常在。
电话中,羊驹子兴奋地说着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清。十多年前的事情一幕幕在我脑中回放,我怎么能听得清?无奈,无助,痛苦,忧伤,所有的情感都涌进了我的脑袋,让我思绪绵绵。
“海里麦,你在听吗?”羊驹子不确定地问我。
“在,我在听啊!”我善意地骗她,其实我在想一些往事。
“我想起了你小时候帮我卖冰棍的事!”羊驹子忽然对我说。
听到这话的那一瞬,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酸酸的,遥远的回忆漫上了心头。
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六七岁的时候,我
帮羊驹子卖过冰棍,一根冰棍卖五分钱。那时候,小镇上好多孩子都吃不上冰棍,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冰棍箱,再一下下吸吮着自己的手指头。那个年代没有冰箱,冰棍只能放在厚木头做的箱子里。我记得很清楚,我卖冰棍的箱子,包括放箱子的手推车架子,都是我大鲁格麻亲手做的。羊驹子在城东卖的时候,我就在城西卖,羊驹子在城西卖的时候,我就在城东卖,总之,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卖。但无论怎样卖,我都比羊驹子卖得多。一天下来,我能卖四五箱,她只卖了一两箱。我卖得最多的一天,是八箱。我大鲁格麻瞅着我说:“娃就是心疼,还会吆喝,卖得不多才怪呢。”还别说,那时我头扎两个羊角辫,胸前挂一个布书包,站在冰棍箱子后,要多神气就有多神气。一大群孩子围着我,他们有的也会拽着大人来,闹着给他们买冰棍吃。有时,我也会把即将消融了的冰棍从箱子里拿出来自己吃。我一点一点地吮着,每吮一口,嘴巴就嘬一下,好像在吮着这世上最甜的东西。这样的结果,往往惹得更多的孩子来买冰棍。晚上回家,我与羊驹子坐在土炕上,头对头地清点那些亮澄澄的硬币和一些残损的角币。我大和义思麻也会坐在一旁协助。昏暗的灯光照着我们,也照着炕桌上那些散落的硬币和我们的笑容。我们的影子交叠着映在墙上,一个叠一个,像我在小镇看过的皮影戏,美丽而动人。
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且一去不复返。
“我还帮你卖过铁犁铧呢!”我在电话里强调着说。
“是,是有这回事。”羊驹子回想着说。
那时候,我不仅帮羊驹子卖过冰棍,还帮她卖过铁犁铧。当我与羊驹子把锃亮锃亮的铁犁铧摆放在集市上,看着来自不同村落的人挑选铁犁铧时,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一种溺爱,他们看着铁犁铧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脸上的笑容要多甜就有多甜。也是,当铁犁铧被套在固有的架子上,一点一点将僵硬的土地犁出一道道深沟,松软的泥土露了出来,再将种子撒下,说不定来年是个大丰收呢。戴白帽子的老大爷小心翼翼地将选中的铁犁铧装进尼龙袋子,唾了口唾沫,数了一块二角钱给我,我又转交给羊驹子。有些庄稼人还会在羊驹子面前笑着夸我:“你这碎女子,真心疼!”每逢他们这样夸我,我都会朝着他们咧嘴一笑,然后羞涩地扭过头去,将一个个零乱的铁犁铧摆放整齐,因为那些铁犁铧里面,有我大鲁格麻用模具做的,也有羊驹子做的,那些铁犁铧旁边还摆放着我大用铁打制出来的斧头、锄头、铲子等等。每每摆放起我大做的那些农具来,我心中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自豪感。
锃亮锃亮的铁犁铧,它不仅承载了一个人的快乐,也承载了一个人的悲伤,如同当年的冰棍一样,让人在回味中体会了生活的温馨和甜蜜。我喜欢那样的温馨和甜蜜。但是那样的日子又有多久?如果羊驹子还在这小镇上该多好?说不定我还可以再帮她扫扫地,或者卖卖什么东西,或许还与她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情。
电话中,我叫了声娘。她没有吭声,我听到她哆嗦着挂了电话。
赛尔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我身后说:“娘,吃一口冰淇淋!”我扭过身子,看到他拿着一个塑料勺子,并一个劲地将勺子里的冰淇淋往我嘴里送。我含着冰淇淋,像含着一口炽热的火焰,那火焰燃烧着、跳跃着,一直通到我的嗓子眼里,通到了我的心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