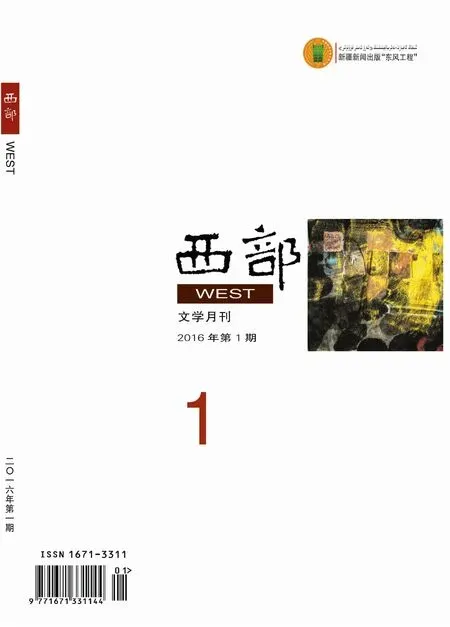楼
学 群
楼
学群
1
曾大木当上局长,正式从803坐到801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吕子木从临江宾馆调过来。没有人知道曾局长干吗要从外边弄一个人进来给他开车,也不知搞营销的吕子木干吗要跑过来当司机。不知道就不知道,那时大家都觉得这事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吕子木调过来不久,他老婆小金就在机关大院旁边开了一家餐馆,只要丈夫用汽车把曾局长载过来,她就用野鸡王八喂他。不久,吕子木便成了车队长。坐车的是一把手,开车的做车队长,这事儿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当车队长将近一年时,曾局长提出让吕子木担任行政科副科长。有人担心他不是干部编制。拿出档案一看,给局长开车的确实也是干部。既然是干部编制,从车队长到副科长,也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吕子木当上副科长不久,人们突然发现:摆在他前头的吴副科长已经到了五十三岁了。按规定,女同志五十三岁退线,五十五岁退休。于是吴副科长就成了主任科员,吕副科长前面就只剩唐科长了。
那天重阳节,老同志会餐。曾局长过来敬酒的时候,老唐正跟保卫科两个老家伙喝得火热。他没看到曾局长,但他看到了那双软底鞋。鳄鱼牌,张牙舞爪的鳄鱼,要咬人的样子。打省局开会回来,他穿的就是这双鞋,老虎巡视领地似的。老虎巡边,一下下往边界上撒尿。曾局
长交替抡起两条鳄鱼,一下一下踩到地上,那架式分明在宣示:这地方现在不是杨记,是曾记!可老唐不喜欢。顺着鞋子往上看,曾局长的眼睛观照全场,举着酒杯,一言九鼎的样子。吕子木则跟在曾局长身后,亦步亦趋的样子也让他窝火。喝下去的酒,正好把他点燃,他用接近酒精的浓度朝曾局长喊话:
“老曾,老曾!你是从803坐到801去了,什么时候把我的档案也拿出来瞧瞧,看长霉了没!”
曾局长将酒杯一收,捏在手上:
“你一张野猪嘴,乱吃乱喝还乱说!”
老唐把筷子一丢,转身走人。第二天,一份辞职报告就摆在了曾局长桌上。
老唐辞职,不少人认为是事先设计好的一场戏,尤其是在他成了副调研员之后。
曾局长知道自己没法找老唐谈。他首先想到陈组长。可老陈提出一个问题:“我是纪检组长,让纪检组长找他,他会不会发火?”曾局长点点头。他知道老唐,火一来就什么都不顾,说不定就会冲到801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他转而找隋副局长。凭老隋的嘴边子功夫,老唐至少不会跳起脚骂人。老隋说:“局长发了话,我当然要执行。只怕到最后不是我找他谈话,而是他找我谈话。局长要是不便亲自出马,干吗不让老陈找他谈谈呢?”
曾局长当然明白是因为座位牌的缘故。除了老隋就只剩省局刚下派的张副局长了。他咽了一下口水,淡淡说了句:“那就算了。”老唐辞职的事就这样搁在那里。没有人来找老唐,老唐也懒得去问。他不再理行政科的事,他知道,行政科的事,自然会有人去管。
整个局机关,除去人员经费,一年下来,少说也有五六百万的费用要从行政科花出去。用水用电用车用餐用钱,谁不找行政科?很多人跟我一样,到行政科报条子时才发现,行政科实际上到了一双握方向盘的手上。
人们开始回过头来看这事:从调进来开车到老婆过来开店,从车队长到副科长,从吴副科长退线到唐科长辞职,人家吕子木就是奔这个来的。传言由此而起。有人说他们是亲戚,一个叫曾大木,一个叫吕子木,连名字都有同一个字。有人说,吕子木给曾局长送了一套房子。也有人说,曾局长在小金餐馆吃王八吃多了。还有人开玩笑:三种说法其实可以合到一起,吃王八吃出亲戚来。至于送房子,那不是一般的房子,是一座宫殿。
那时候,我也认为吕子木是奔行政科来的,后来才知道不是。
2
好久以后,跟我谈及当年的辞职,老唐还是不能理解:成了一把手后,曾大木怎么就像换了一个人呢?
曾大木和他是同乡,两人一同长大,一起参加工作,不但在同一个单位,而且还在同一间宿舍住过好长时间。后来他们结婚生子,又差不多同时当上副科长、科长。再往后,曾大木当上了副局长,而老唐仍旧在原地踏步。位置虽变了,但两人的关系好像没变,老唐依旧咋咋呼呼,曾副局长总是一笑置之。杨局长调走,排在曾大木前头的刘副局长即将到点。曾大木正逢其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拿了一张研究生文凭在手上,省局指定,局里的工作暂时由他牵头。不久,又明确由他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没想到这一“主持”就是一年多,局长前面那个“副”字原封未动,曾副局长依旧坐在803干着801的活。曾大木心里着急,老唐也跟着
急。老唐在行政科,一些事少不了要他打理。除了往省局跑,他们还悄悄请来一位八卦先生。八卦先生说:曾局长的档案还在睡大觉,得往801去坐一坐,把它激活。第二天,去803找曾局长的人发现,曾局长坐进了801。档案激活没激活不知道,一些人写举报信的想法倒是激活了。省局一连收到几封信。听到消息,曾局长又连夜搬回803,找曾局长的人又得从801往回找。
曾大木跟老唐一商量,从老家那边的大山里请来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白髯飘飘,在院里院外一转,说问题在门口那两只狮子。石狮子底座下面的两枚铜钱不姓曾。于是两只石狮子连同底座被撬开,几只地虱婆一阵惊惶失措。周围全是水泥地,只有这两块地方是沙土。对于一些地底生命来说,这两块地方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条缝隙一点儿湿意就足够它们过上一辈子。人们不会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那两枚连红布一起压进沙土里的铜钱。红布上写的是杨局长的名字。他们换上了曾大木的红布。
“红布一换,省里翟局长就来了,翟局长一来,曾大木就上去了!”后来,老唐这样强调他的作用。曾大木最恼火的就是他把这些尿片翻出来,挂在嘴巴上。
老唐记得很清楚,翟局长是星期五来的。周五之后是周六周日。曾大木跟他计议:翟局长能留下来过周末,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他们先跟同来的肖秘书沟通。座谈会之后,曾大木小心翼翼试探,翟局长没说什么。老唐大大咧咧在一旁帮腔,翟局长终于笑着骂了一句“你小子”。曾大木信心大增。
第二天,开始一切都顺利。车子往郊外开,翟局长没说什么。车子在鱼塘边停下,他也没说什么。看见老唐拿钓竿过来,他问:“要钓鱼吗?”老唐说:“我表哥没见过厅级干部,他和他们家的鱼都想看看大干部是什么样!”局长笑起来。他一笑,曾大木他们赶紧跟着笑。
没想到问题出在鱼身上。这塘里的鱼似乎并不想见翟局长。它们一点儿也不识抬举,约好了似的,不来咬翟局长的钓饵。不来这边也就罢了,还要一个劲地去咬曾大木的钓饵——也太目无组织纪律了!老唐嘻嘻哈哈向我描述曾大木如何急得心里像猫爪子抓:那边翟局长坐在太阳伞底下,又是抽烟,又是喝水,到后来甚至站起来伸懒腰,就是不见收杆取鱼。这边曾大木钓过几条之后,钓也不是,不钓也不是。只见你在起钓,好像你比人家翟局长还厉害似的。可老不起钓似乎也不行,好像这塘里没鱼似的。没鱼你把堂堂的翟局长唬弄到这儿做什么?可怜这位主持工作的曾副局长,只恨翟局长要钓饵的不是人!如果是人,他就会第一个跳下去把钓饵咬住。他可以开大会作动员,可以评先进发奖金,也可以扣工资处分人。他还可以到临江宾馆的娱乐城拉一车美人鱼,让她们一个接一个往塘里跳。可惜鱼不是人,它们不要评职称,不要当科长,它们不管你是局长还是屠夫。
临近中午,翟局长总算钓到一条黄牯鱼。虽不大,但破了零。这时候,曾大木还不敢走过去。接着翟局长又是两条。于是曾大木就拉上肖秘书,半猫着腰赶过去打趣:“这几条鱼胆子也太大了,厅局长的饵料都敢吃!”翟局长朝他笑笑,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回到原位。往回走时,他特意抓住肖秘书的手握了握。昨天一只红包,肖秘书一直在捧场。
吃过午饭,翟局长手下的情况好多了。最后的结果,翟局长第一,肖秘书第二,曾大木第三,其他不在话下。翟局长高兴,曾大木比他老人家还高兴。
那次去省局开会,曾大木副局长去了,老
唐没去,应该是听来的——
晚上会餐,省局管人事的副局长当着众人对曾大木说:“你的事省局党组已经研究过了,快敬翟局长酒!”一拨过来敬酒的人闻言,赶紧让到一旁。众目之下,曾大木举起酒杯:“感谢首长错爱!”翟局长不接受:“你的意思,省局党组的决定错了?”曾大木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感谢抬爱!”翟局长还是揪住不放:“这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给你抬轿的喽!”曾大木诚惶诚恐,红着一张脸。肖秘书赶紧过来圆场:“是垂爱,关心!”曾大木赶紧接上:“对对对,感谢首长垂爱,感谢关心!”翟局长总算端起了酒杯。他端酒杯的样子,让曾大木折服。他也暗暗学了一手。
从省局回来,曾大木就不是原来的曾大木了。我们这座院子从此姓曾。那双鳄鱼牌软底鞋载着的,是曾记的曾。他堂堂正正坐进了801。坐进801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吕子木。老唐看不出,这位曾局长是否还记得有一个老唐。
老唐弄不懂,一个人成了一把手之后,怎么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呢?他大概认为,老唐既然还是老唐,曾大木自然也应该是曾大木。他跟我一边喝酒一边说着这些。酒喝多了,我也变得跟老唐一样。我说:“一把手是什么?一把手就是,他把手一伸,这块地方,他的手就是天。一个人的手掌成了天,怎么能指望他还是原来那个人呢!就像一块牛皮,一旦制成一双名牌鞋,你怎么能还说它是一块牛皮呢?”
老唐说:“我不管,曾大木就是曾大木!手掌是手掌,天是天。曾大木烧成灰,化成烟,也还是曾大木!”我说:“你不是说你喜欢读历史么,朱元璋杀功臣,不就因为他们都像你老唐一样?曾局长还算好,不但没砍你的头,还给你弄了一只蚌壳——带括号的副处级也是副处级呀……”老唐打断我:“算了吧,我那蚌壳可不是他给的!他想人家小金的蚌壳还来不及,还有时间想我的事?我的蚌壳是翟局长给的,是我打麻将打来的。”
老唐打麻将,嘴巴呱啦个不停。摸到“将”,他说:“曾大局长来啦,穿着名牌鞋来的。”要不就是“陈组长、隋副局长来了”。摸到手的牌要调整位置,他说:“老隋,你怎么坐这里呢?你坐那边去,让老陈坐过来!”那天晚上老唐手气臭,老输。快到十二点时,他门清只差一只将。将老不来,他说:“曾大木呀曾大木,你老躲在那里吃王八吃野鸡,只管自己好过,也不来帮兄弟一把!”“将”一直不来,他就一直在骂曾大木。其他三个人只是笑。他说:“你们笑什么,当了官就这副德性!”他们说你不也当科长吗?他正要说什么,摸到手的那只牌把注意力一下拉过去——右手,食指在牌背部,拇指在它的腹部徐徐扫过,从一个圆滑向另一个圆,不用看就知道是两坨——曾大木!他连手带牌拍到桌子上。桌子一跳,两坨不见了。桌上没有。抬开桌子,地上也没有。他长呼短叫:
“曾大木啊曾大木,你真不是好东西!”
三个人哈哈大笑。不见两坨,他的门清自摸没法算。他除了骂曾大木骂那只两坨,没有别的办法。退休的老刘在一旁打趣:“老唐呀,算你胆子大,敢把人家局长说成两坨。”
脱衣睡觉的时候,两坨从衣兜里掉了出来。他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摔了出去——去你妈的,曾鸡巴!
3
老唐在这边打麻将的时候,曾大木也在小金餐馆的楼上打麻将。老唐打麻将时念念不忘曾大木,曾大木却连自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
了。老唐从牌桌上摸到两坨时,那边的牌桌底下,有一只脚正在抵达曾局长那两坨。
我们在楼下吃饭,不知道楼上还有一处打麻将的地方。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八十几平米。打开盼盼防盗门,客厅正中摆着麻将机,四张大椅围着。厨房当然不用做饭,只做沏茶烧水用。卫生间里装着大功率热水器,可供两个人同时淋浴。两间卧室不大,里头各有一张一米四宽的床。睡一个人算宽,睡两个人得紧挨着。房子临街一面的窗户挂着很厚的窗帘。一棵羽叶栾不知长了多久,才把灯笼一样的花朵举到窗口。可它们什么也照不见,顶多隔着玻璃把影子投在窗帘上。另一边的窗户上挂着窗纱,阳光可以斜进来,风可以荡进来。从对面房子伸过来的目光,只能在窗纱上捕捉到灯光与人影,没有人知道人影是谁。
曾局长就在这里打麻将。同他打牌的人是固定的:王总,一个胖胖的男人,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总;阚总,王总下面的副总,一个丰满而不显臃肿的女人。喝酒的时候,曾局长问:“一个王总,一个阚总,你们到底谁领导谁?”阚总很干脆:“王总在上我在下。”王总喜欢喝两盅。喝到一定时候,阚总就会出来干涉。曾局长说:“副的怎么管起正的来了!”小金跟阚总是好朋友,她嘻嘻一笑,接过话头:“曾哥不知道,王总喝下去的酒,最后都跑到阚总那儿去了!”曾局长望着小金一笑,又转向阚总:“听说王总尿出来的尿都有三十五度,是真的吗?”那边笑眉笑眼答道:“是啊,弄得我长期处于酒精中毒状态!”曾局长哈哈大笑,边笑边拍王总的肩,边拍边拿眼睛往小金身上看。小金是那种瘦不露骨的女人,他觉得,在这具瘦长的身子里流动的,是一种酒精一样的东西,一下就可以把你点燃。和王总一样,小金只是笑,她眼睛里闪动的笑,在曾大木看来,是酒精那蓝色的火苗在闪动。
刘主任和我到餐馆来加餐的时候,当然不知道曾局长在楼上打牌。我们只知道写在纸上的东西,比方说经管局如何内抓管理外树形象;局领导班子如何团结战斗洁身自好;曾局长如何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心和身子都扑在工作上。年初在纸上部署工作,说的是:围绕一个中心,坚持两手抓,把住三个重点,上下四方一齐动员。年底作工作总结,把年初的东西换一种姿式,就成了:四轮驱动,三路出击,坚持两手硬,全年工作跨上一个新台阶。
刘主任是单位上的老笔杆子,杨局长当局长,他写材料,曾局长当局长,他还是写材料。从一般科员到副科级,从副科级到办公室副主任,从副主任到主任,他是用笔在纸上写出来的。我研究生毕业上班第一天,他就带我去看他的资料室。几大柜文字资料,全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他的体会是:一个人只要埋头做事,领导自然会考虑的。他一心伏在桌子上,头顶那块慢慢秃了出来。那天吕子木对他说:“曾局长有指示,写材料的时候,可以到外面吃点饭加加餐。”刘主任高兴地望着我,那意思我知道:怎么样,领导在“考虑”着呢!
说是到外面吃饭,我们很识趣,没有走太远。出大门不远就是小金餐馆,在这里吃完在单子上签个字就可以走人。其实一份辣椒炒肉,顶多再加个把小菜就够了。小金一张笑脸,还把身子往刘主任身上靠,叫我们吃野鸡吃乌龟。每次去那里,不是乌龟,就是野鸡。吃多了就发现,野鸡有头有翅,偶尔有一两块身子骨,两条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乌龟好像尽是头。有一次,我们从一堆辣椒中整整吃出五只龟头来。小金嘻嘻哈哈的,说是吃什么补什么。在这里吃饭,我们不止一次打量过小金那张线条分明的脸,确实吸引目光。瘦长的身子,该起来的
地方并不含糊。唯一的问题是她不能笑,浅笑还可以,一放开来笑,就有一种粗俗相从眉眼间冒出,就像一锅清汤,突然浮起一层肉末。
吃了回去我们没有办法双管齐下,顾了上头顾不了下头,只能伏到桌子上接着写。方块字排着队一路往前走,走向报纸,走向刊物和电视,走向上级的信息简报,走进各种各样的会场。所有这些,构成一个字面上的帝国,坐在帝国上头的,是曾大木曾局长。
隋副局长一句话才让我们想起,写这些的时候,吃龟头吃得多了一点儿。隋副局长当着刘主任和我的面好像很随意:加班写材料,加点餐是应该的,何必老是吃那些野鸡王八呢?算下来也上十万了哟!
吕子木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楼上有一套房,也知道曾局长在那里打牌,但他从来不去,连下面的餐馆都很少去,曾局长离开那里时,他才跟上他。曾局长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办公室,在机关院里忙这忙那。他把机关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吕子木正式接任的时候,连老唐自己都承认,吕子木比他管得好。想放松一下,他会去临江宾馆。喝酒、K歌、玩女人,在那里他可以过得很开心。
他去餐馆楼上,是在后来。去那里以后,他填上了张副局长回省局出现的空缺,成了副局长。
4
吕子木一当上副局长,隋副局长就对自己的仕途失望了。
刘副局长退下来的时候,他曾经满怀希望,尤其是在省局派了刚提拔的张副局长过来的时候。他比曾局长小五岁,这就是他的希望所在。在那五年时间里,让经管局姓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好些现在不能做的事,可以留到那时候去做,他可以排兵布阵,可以在这块满是水泥的地面上扎下根来。即使退下来,他的话还会像冬天的风一样拍打办公楼的窗户,把院里的几棵大樟树摇得哗哗响。人生的很多东西,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实现,为此,哪怕下一个轮回变成畜牲。在变成畜牲之前,他可以先扎一根尾巴在屁股后面摇。
曾大木主持工作的时候,刘副局长还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坐过一段时间。除了曾大木,他是老二。局里开会,他一直坐在曾大木左手边。曾大木成了局长时,老刘也成了调研员。隋副局长盯上了老刘坐过的那个位置。他知道,曾大木不会提出来要配副书记。副书记就是铁定的二把手。一个一把手干吗要弄一个二把手呢?二和一之间就差一个“一”,那感觉就像在自己屁股后头写上接班人。后面那个“二”什么都不想,单等前面的“一”出事走人似的。老隋不要做副书记,他只要坐得离“一”近一点儿。这次省局下派的副局长人选,给了他想象的空间。
老隋坐那里,纪检组陈组长似乎是一个障碍。论进班子的时间,他和老陈是同时提拔的。问题在省局党组的那个文件上。或许是陈字笔画少,也或许是老陈的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都在同一个文件上任命,而他的党组成员在这边,副局长则在行政那边发文,总之,在这边的文件上,老陈的名字放在前头。就因为这,老隋往常不是排第三,而是排第四。这样的第三第四,当然跟第二没什么关联。经管局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它的老二理应是一位副局长,而不是政工干部。其实,老陈也该有点自知之明,他比曾局长还大一岁,要个第二做什么?改调研员吗?谁说老三就只能改副调研员!再说,副调研员跟调研员又有什么区别?加不了工资,多一个字少一
个字都是一个名头,一退休就没了。
老刘退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党组会,老隋第一个进会场。老陈进来时,老刘坐过的那把椅子倒是空在那里,椅子前面,一只茶杯正在桌子上冒热气。笔记本已经摊开,一支笔大模大样躺在本子上。老隋站在座位旁抽烟。从鼻孔里冒出的烟缕与茶杯上的热气两相呼应,仿佛在宣告:这个位置是他的。老陈及时收住脚,没往原来的座位上去。他知道,往老三的位置上一坐,就等于承认人家是老二。他回转身,将粗笨的屁股压在党组秘书做记录的座位上。曾局长进来,看了看,没说什么。直到散会,才说了句:老刘退了,座位会有些变化,下次大家按座位牌入座。
老隋屈辱地接受了那块写着他名字的座位牌。一屁股坐到老陈坐过的椅子上,老陈那只蠢笨肥大的屁股能把什么好东西留在上面呢!他整个儿都在排斥这张座椅。而那个人用几年时间留在海绵座垫上的一切,也像针一样在扎他的屁股。老陈坐在对面他上次坐过的座位上。他只坐过一回,没能在上面留下太多,老陈那只屁股足以把它压平。整个开会的时间,老陈都没朝这边望过,他也没朝那边望。座位牌那儿有一只杯子,他的目光到此为止。他连笔记本都没有打开,无所事事的笔歪斜着身子躺在一边。轮到表态发言时,他就三个字:没意见。
“你以为老陈是你的对手?你的对手在后头!”
一开始,老隋对老唐的咋咋呼呼颇为不屑。一个人打麻将还能打出什么来?可老唐硬是打出一个副处级来。
那次翟局长来参加省政府在这边召开的防汛工作会,晚上老隋也去了他住的房间。翟局长把手一摆:“你们都回去,把老唐那家伙给我找来!”曾大木面有难色:“老唐动不动胡言乱语的……”翟局长脸一沉:“你们这些家伙,就知道拿蜜糖往我耳朵里灌,腻了!”
老唐一来,翟局长换上笑脸:“听说你打麻将时说你们曾局长是两坨。你倒是说说看,我是什么?”
老唐根本不理会曾大木使过来的眼色,嘿嘿一笑:“市里局长是两坨,总不能说您一坨吧——那不成了半居屌子?您就八坨吧!”
翟局长做出不高兴的样子,可听声音听得出,他并没有不高兴:“说说看,我怎么是八坨?”
老唐大大咧咧全无顾忌:“二五八将,八最大。都说领导是播种机,大领导功率也大,光两坨怎么行呢!”
老唐一顿胡说,把曾大木吓个半死,却把翟局长说得哈哈大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老唐打麻将的事:
“那天晚上,你把那两坨弄到哪儿去了?”听说在兜里,翟局长伸出一根指头点着他:“好啊,你居然把曾局长那两坨装进自己兜里!”
一屋子的人全笑起来。
笑过,翟局长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了老唐、曾大木和肖秘书,四人凑成一桌打麻将。翟局长回去之后,肖秘书还不止一次打来电话叫老唐过去,后来,老唐就成了副调研员。老隋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跟老唐一起打麻将的。
“你呀,骨子里还是个业务干部!”
打麻将的时候,老唐不止一次念叨。老隋不得不承认老唐的汤汤水水中,不乏先见之明,吕子木这个潜在对手就是他最先点破的。眼见着吕子木当上副局长,老隋感觉到,即便他来生想做畜牲,看来也好像没有指标。曾大木正把吕子木往未来一把手的位置上推。
再好的鞋子也有穿旧穿丢的时候,曾大木这样一个男人,有模有样有权有势,吕子木或
者说小金究竟凭什么把他吃定?
5
省局来考察之前,连着收到几封信,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曾大木在单位上任人唯亲;二是吕子木在门里边当行政科长,老婆则在门外边开店,借机敛财。消息一传过来,曾大木就和吕子木坐到一起商量。在餐馆楼上相遇之后,这是他们第二次坐到一起说事。上一次有些像谈判,这次是联合御敌。上次吕子木显得轻松,这次他可没这么轻松了。他倒是隐隐觉得,轻松的是曾大木。显然,两个方面的问题中,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开店的事。店已经开了,没法倒回去,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吕子木跟小金离婚。不管怎样,有一个离婚证就行,而且时间得往前移。
曾大木起身要走时,吕子木变得怯生生的,甚至有一抹红云罕见地从他那张马脸上一掠而过:“小金那边,你能不能跟她说一句?”
“什么意思?她是你的老婆!”
转身准备往外走时,曾大木觉得背后什么东西一动。回过身去,依旧是那张不动声色的马脸。防盗门哐的一声关上。隔着门,他依然感到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他后背发冷。想到自己在现在的位置上时间将不是很长了,他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被一根裤带捆绑在门里的这个人身上。人生就像木偶戏,只看到一些人穿着衣服戴着帽子舞来弄去,谁知道后面有多少绳子牵着,一开始甚至是心甘情愿让人家牵着,到后来不情愿也没了办法。没有别的,到时也得拿点什么捏在自己手上。
一看到吕子木脸上讨好的表情,小金就明白又跟前两次一样,没什么好事。她只是拿眼睛望,望得那张鲜有表情的脸不自在起来。他偏了偏脸,稍稍避开她眼睛里的锋芒,开始说人家往省局写信的事,从餐馆说到他和曾局长商量如何应对。他发现越往下说越艰难,比那次他让她去钓曾局长更难。那次他们至少还有共同点,两个人都希望从姓曾的身上捞取他们想要的:他想在经管局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她想要钱。她其实愿意让自己作钓饵,只是希望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好像她只是为了他,这样他就没有二话可说。两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对方,在临江宾馆经营着这里的娱乐城,看过许多的男女苟合,身上那点东西,无论他的还是她的,早已不再放在心上。重要的是手里头握着实实在在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离婚?”
她叼住一支烟,点燃,和着烟把他没能说出的话吐了出来。有一阵,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只是抽烟,抽了一根,又从烟盒里叼出一根。她的面前,大理石茶几像一座纪念堂,玻璃烟缸就像水晶棺,躺在里面的烟头,白色过滤嘴带着口红,看起来有些像血。
“你手上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离婚呀!”
他当然知道她的潜台词:她手上握着他的把柄,她只要往下一拽,不但是他,还有另一个会一齐翻身落马。
他说:“不就做做样子,弄张纸出来应付吗!一切还不是跟原来一样?我上来了,不是对大家都好吗?”
他们去了民政局。吕子木早就把门径打点好了。离婚证上的时间是去年。
吕子木当上副局长后不久,刘主任就病倒了。没有人知道他病倒与吕子木提升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前他老对我说:“只要认真干,领导自然会知道的。”可领导不知道。他除了成天伏在桌上写材料,还会有别的想法。一个人,就那
么几个话把子,颠来倒去地说,写了工作计划,转过身去写总结,加点班还可以到外面去加餐,自己已经坐到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了,儿子也有了工作,安安然然一辈子,还要怎样呢?知道的只有我。
刘主任哈着腰,一瘸一拐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起他留在墙上的那幅字:实实在在做人。六个字全都让人想起他弯身伏案的样子,尤其最后那个人字,几乎是趴在地上。无休无止地伏案工作,从脊椎开始,一步一步把他摧垮。在这之前,他还能忍受。我知道,他一直在暗暗期待。论工作,论资历,他完全有理由期待。而且,从办事员到办公室主任,每一步期待不都成了现实?副调研究员落到老唐身上,并没有让他绝望。还有一处地方可供他继续想象。等到吕子木踩着他的想象爬上去,知道自己这一生只能定格在一个正科级上头后,他感到身上的骨架再也没法把他撑起。
离开办公室前,他老泪纵横。三十年如一日,他的心血,他的生命就在这一捆一捆、一柜一柜的材料上。杨局长时他为杨局长写,杨局长前是柳局长,杨局长之后是曾局长,再往后呢?说不定是吕局长。
这些都有什么用?烧成灰连四两都没有,风一吹就散了……
办公桌上还有一沓——他一生中最后的几个材料。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加班用餐吃野味的说明。这是曾局长找他谈过话之后写的。
后来,说到刘主任这个人,老隋说:“这个人,长了一辈子也长不大。”
6
餐馆楼上的房门,对于曾大木就像一扇自动门,他一来,门就会开。他有一把钥匙,但从来没用过。这一天,他的脚步声、咳嗽声、敲门声统统不灵了。他在公文包的一角找到钥匙,打开门。门里只有黑暗和空寂。在餐馆里,他也没有找到小金。打电话她不接,后来干脆关机。姓阚的女人打来电话,问他打不打牌。他说在开会。
突然就觉得这个夜没了着落。
曾大木并不缺少女人。唯独小金,看到她第一眼,他就怦然心动。一开始,她只是远远地朝他笑,不让他靠近。有一次,借着酒性,他从后面突然抱住她。她挣脱的方式居然是揪住他的两坨。挣脱以后,她依旧面带微笑。好长时间,他一直不知道对这只让人动心的刺猬该从哪里下口。可后来,她却把自己送到了他的办公室——吕子木调动的事,她来找他签字。在那张表格签上字之前,他先把她签了。
她身上有一种让人着迷的东西。他屡屡想弄清楚那是什么。可是他始终没能弄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女人让他像抽大烟一样上瘾。餐馆楼上的房子有些像银行保管箱。他把她存在这里,随时可以提取。直到有一天,吕子木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当时还以为只要把吕子木弄上去就行了,没想到吕子木上去了,小金却不见了。
7
因为那两千万贷款,曾大木不再去801上班。餐馆楼上那套房子也不去了,改去麻将房,跟老唐他们打麻将。当初贷下两千万,是为了不让小金到这里打牌。贷下之后,他自己却到这儿打牌来了。他来以后,老隋就不来了。
在小金去打麻将的路上,两个局长,一个正的,一个副的,居然像劫匪一样把她截住。对于她来说,他们只是两个准备作废的男人。一
个带着餐馆楼上那些日子站在她面前;还有一个,似乎可以带上很多,但最终发现一样也不能带到她面前,于是他站得稍远一些。他们叫她回屋里说话。她问凭什么:凭过去的日子吗?凭你们是局长、副局长吗?她告诉他们,不要希望凭暴力,所有的录音还有字条都已经存放好,上面还有一段留言:一旦身家性命出了问题,就只有两个人。他们说:有事好商量,干吗这样!她同意商量。
现在是他们跟着她。出电梯以后,她在前面掏钥匙,插钥匙,转动钥匙。两个男人一边一个站在后面望着她:从头顶径直梳下的头发,到肩头之后波浪似地往上一回转。曾大木心里一动。那件紧身羊毛衫像是在配合牛仔裤的隆起。牛仔裤准确地把臀面分成两半,面对两个男人。吕子木注意到那把挂回屁股一侧的钥匙。钥匙晃了晃。不用它提醒,他来过,发现他的旧钥匙打不开新换的锁。现在,他重又回到这个被自己一脚踹出去的地方。曾大木是第一次来这里。隔了这么久,牛仔裤里的内容让他的眼睛恨不得伸出两只手来。那地方,他曾经拥有绝对的股份。
他们很快弄清楚,她已经在海南注册了一家公司,王总阚总已经去了那边。有一块地在等着,她需要两千万。
曾大木不是不知道,在贷款的问题上,吕子木总是躲在他身后。他当然知道,一旦小金把攥在手里的那些东西抛出去,最先摔下来且摔得最惨的,是吕子木。可他禁不住牛仔裤的诱惑,像着了魔。当然,还有一点,他的话银行肯听。吕子木曾说:“你的话闹得鱼死。”他也知道,贷款炒房产,上头已经踩刹车。但他相信,若把控得好,上头不会知道。
曾大木便跟小金去了一趟海南。这是他一生中快乐的巅峰,两个女人把他往后的日子都赊了过来。他没有看到王总那个憨憨一笑的男人。小金和小阚陪着他。城市合作银行同来的信贷科长,一落地就不知道被她们塞到哪儿去了。那是一幢临海别墅,拉开窗帘可以看到海。海无边无际,包容万象。海吐出又吞下眼前的沙滩。拉上窗帘,海把涌动的节奏传进屋来。他突然觉得把两个人摆到一起,世界一下变得非常奇妙。一个念头从他脑子里一晃而过:一辈子能有这么一趟也就够了。
临走那天,明显瘦了一圈的信贷科长,像一面镜子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在这里脱胎换骨。他还记得问海边那块地看过没有。信贷科长回答:“看过,临海,很平的一块地。”
信是从北京批下来的。写信的人显然想一锅端。所谓空前绝后,前是指曾大木,后是吕子木。北京的批示很明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动用信贷资金炒房地产,必须追回资金,追究责任。几个人追到海南,那幢临海别墅还在,顶多也就一百多万。抵押的那块地原来是一片沙滩,有关文书是伪造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也没想找到。曾大木知道在劫难逃,他一个人揽下,没有把吕子木捎上。省局没有手软,曾大木被撤职,行政降两级。至于那个信贷科长,城市合作银行干脆让他下岗收贷。省里新派来一个肖局长,就是原来的肖秘书。
8
仿佛要证明某种东西,一年多以后,肖局长回省局,吕子木副局长主持工作。这时候,他的办公室恰好是803。老陈已经退休,坐在802的老隋,上头给他一个正处级,让他退了线。
主持工作的吕副局长找我谈话,叫我在办
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好好干。他告诉我:“纪检组长省局会派一个下来,可副局长的位置还空在那里。”不知道当年曾大木是否跟刘主任说过这些。吕子木应该知道,现在像刘主任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从801出来,曾大木在办公楼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他现在的身份是正科级科员,局里没法像局领导一样给他安一间办公室,又不能像其他科员一样,把他塞到某个科室去。他说他不用办公室,他现在在老唐那里上班。他很快融入老唐的麻将组合。他知道,老唐还是原来的老唐,他却不是原来的曾大木了。老唐喜欢喝两杯,喜欢咋呼几句,老唐说什么,他就听着。老唐说:“这人不当局长了,又变回来像个人了!”
曾大木的儿子找了媳妇,媳妇要工作,儿子跑到打麻将的地方找他吵。老唐抬起抓麻将的手指着曾大木:“去找吕子木!你一手把他抱大,他还能不办?他不办,我回老家扛一把耙头挖他的屁股!”
曾大木找吕子木说过一次,是在路上。吕子木笑了笑,没说什么。曾大木知道,光说不行,手里头得有东西。他想起那盘录音。吕子木闯进餐馆楼上那套房子时,曾大木不知道他事先放了窃听器。小金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大大方方进了卫生间,在淋浴。他问吕子木要怎么样?穿上衣服之后,他不怕怎么样。吕子木说得轻巧:“把我的副局长报上去。”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吕子木依旧不急不躁:“得马上报!”他一笑:“不然呢?”吕子木还给他一个笑:“不然,我就把录音送到省局去。”后来,他问过吕子木:“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老辣?”吕子木还是那种胜券在握不达目的不罢休式的笑:“你不知道,如今吃的都是速成饲料,一头猪,昨天还是猪娃子,今天就成了大肥猪。我们就是吃这些猪肉鸡肉长大的。”
老唐哪里知道这些!他呱呱啦啦打了几场麻将,人家顺手给了他一块骨头,他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显然,他曾大木不会像老唐想的那样去找吕子木。
两年来,这是曾大木第一次进办公楼。一楼大厅的保安显然没见过他,问他找谁?他说找吕子木。那伙计似乎还想让他往登记簿上登记。他没有理会,转身往电梯那里走。大概是从他嘴里吐出的“吕子木”三个字起了作用,保安“喂”了一下,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电梯在三楼停下,上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女的叫出一个“曾”字,又尴尬地在“局长”两个字前面停下。他淡定地接受这一切,还朝她笑了笑。他不知道她叫什么。那时他坐在台上,台下的自然认得台上的。他的鞋子又一次踩在八楼的地板上。有好些年,从他脚底发出的声音在楼道传响,一直响到天花板上头,那时候,这儿的一切都姓曾。现在,他的脚步声在这里显得既陌生又别扭,墙和天花板早已适应了另外的鞋另外的声音。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娘的,老子就这样!
看到他,我朝他一笑:“曾老板!”这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称呼。他会心一笑,同我握了握手。我径直将他往吕子木的办公室引。我心想:有事还要跑到办公室来找,看来曾吕之间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我替他敲了敲803的门。看到曾大木站在门口,吕子木并没有显出惊讶。历经千锤百炼,两个人的脸早已滴水不漏。
我把门关上,让两个人独自面对对方。
803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曾大木在这里的时候,桌子朝门摆着,窗户从背后照过来。现在,桌子朝着西墙,窗户到了吕子木的左边,门
在右边。桌子变成了老板桌,稍稍向内弯起,朝里面的大转椅形成拱卫之势。靠窗那边的桌面搁着一尊铜像。离铜像不远,有一只玻璃盘子,用水养着几块鹅卵石。气乘风而散,得水则止。积水聚气,当年曾大木在大门口所用的功夫,吕子木把它做在室内。
曾大木没有选择老板桌前面那把椅子入座,那是吕子木坐在大转椅上听汇报时,给汇报的人坐的。他在一旁的沙发上落座。吕子木跟了过来,坐在另一张沙发上。两个人都注意把身子坐直,两脚平放在地上。吕子木先把话挑明:
“你儿媳妇调进来的事,现在还不是时候。”
曾大木徐徐一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笑过来。笑过之后,问吕子木还记不记得那盘录音。吕子木没有说话,只是望着对方。他记得,在他提了副局长之后,曾大木把录音从他手上要了过去。当时他以为,堂堂的曾局长只是不愿让把柄继续留在他手上。他暗自好笑:假如我想留着,就不能复制一盘吗?
“这盘东西我还留着!”听得出来,这个曾经被这盘东西烦着的人正为留下它派上用场而自豪,“你可能没在意,那东西放在那里,一直都在往下录。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全都在里面。”
“那又怎样呢?”
“没别的,它只是说明,你当副局长是一桩交易的结果。”他记得,那时候吕子木用的也是这样的口气。
“你把它捅出去,不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呵呵,我关心的是你的前途。我无所谓。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失去的是一无所有。”
“其实,我只是想等时机成熟一点儿,再来弄你儿媳妇的事。”
“那时候,我也是想等时机好一点儿,再来弄副局长的事。现在我知道,你当时急是对的,这样的事办了就办了。”
“那好吧。到时候,那盘录音谁都不要留了!”这时他忘了,录音是可以复制的。
9
相比曾大木,吕子木的事情在省局那边要顺利得多。肖局长回省局之后,成了人事处长,有他从中运作,吕子木很快就从803坐到了801。
和曾局长不一样,吕局长走在院子里的时候,穿的是一双厚底鞋。骆驼牌。厚厚的鞋底,一下一下踩踏在地上,稳扎。可是不久后,他感到的却是沉重。
801比803要大很多,摆下桌子椅子和沙发茶几之后,还有很多富余,足够他坐在转椅上向四周展望。就在他在新办公室展望一个局长的前景时,一个电话把他拉回过去。
电话是小金从海南打来的。一开始,他还能显得轻松,甚至在电话里跟她开玩笑:“收贷的时候怎么找也找不着,怎么一下又冒出来了!”
“我就在海南,真要找还会找不到?怕只怕把我找到了,你们谁都不好过!让我说完——你们不找我,我来找你们——不,那一个没什么找头了,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