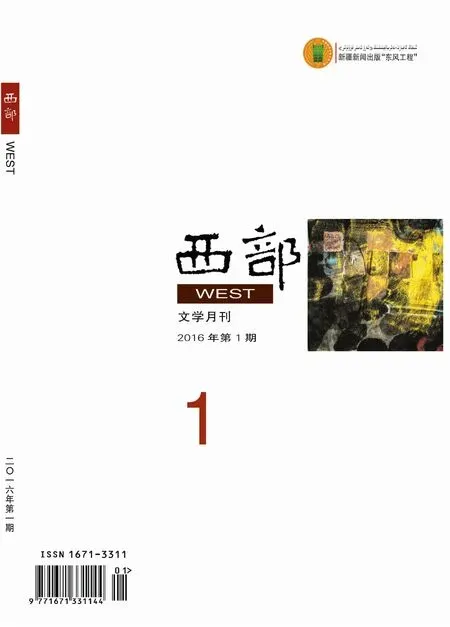姐
高 君
姐
高君
大海宛若一面广阔而蔚蓝的镜子,瘦长的海岸线如同镶在镜子上的裙边。而蔓荆、肾叶打碗花、紫花补血草、匍匐苦荬菜则是裙边上点缀的小纹饰。
村落闪烁在高大的麻栎和松心木间,屋瓦和窗棂的反光就像海面上跳动的点点金色。
徐庶闻到的竟是老家初春新鲜的泥土味儿和淡淡的霉腐、腥膻混合的江风气息。
姐和小孙子站在二层小楼门前。
你猫儿子呢?咋没抱来?大宝贝就等着和他玩呢。
火车不让带,徐庶抱起姐的小孙子,嘴巴在他小脸上蹭了蹭:下次舅爷做大客给你抱来,这回你奶可拔不动根喽。
卵子大坠住了,这三年哪儿也走不了了。
老寿星呢?徐庶问。
烧锅炉呢,上次把你冻跑,你十六年没登门。
就等给他过大寿呢。
这是徐庶第二次来大姐家。
十六年前的腊月二十八,徐庶来时,姐刚搬来两个多月。当天,辽东半岛一带普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几度。打小就听姐夫说自己老家那边暖和,穿双单千层底布鞋就能过冬。临走,徐庶特地褪去棉衣,着了一身秋装。第二天清晨一下火车他就傻眼了。雪虽停了,凛冽的海风却像一把把小李飞刀。更让他傻眼的是,所有的汽车都停运了——司机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雪,不敢开,给
钱、叫爹都没用。徐庶瞬间就产生了一个很坏的印象:这地方的司机咋这么怕死啊,真是少见多怪!若在东北,这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小菜一碟,即便是鹅毛大雪,山路十八弯光可鉴人,顶多在车轱辘上加条防滑链,司机照样气定神闲,还会跟你聊天呢。捱到傍晚,终于碰上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但只到沙屯——原来是困住的沙屯司机。
还好,姐夫的四哥就住沙屯。
大饥荒那年,有这边的女人逃荒嫁到徐庶老家的,后来,姐夫一家被定为“大富农”,他父亲一夜间被斗死,哥几个领着老妈就投奔了过来。老四当时正准备高考,老五——也就是未来的姐夫——在读高中。
四十多年前,北方以北,松花江畔那个闭塞的山村,以其富庶的水土和淳朴的民风,接纳了一拨又一拨从“南边”来落脚和讨活路的逃荒者,他们统统被称作“盲流”。
姐夫一家只是其中之一。
姐自作主张退掉奶奶给定下的亲事,嫁给大自己六岁的“地富反坏右”,在当时绝不仅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或狗屎上这么简单,而是关乎阶级、命运的大事情。其时,就连屯里身体有残疾的姑娘都坚决不嫁呢。首先是小叔阻挠得厉害:他怕给八辈贫农的祖上抹黑,殃及子孙后代的前程。父母则担心:南边人见过世面,心路子野,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在山旮旯里待不住,指不定哪天光景一好就拍屁股走人了,不是撇下闺女就是给领走。但女大不由娘,见女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也就默许了。父母默许,小叔自然也就奈何不了。后来,老四的媳妇也是徐庶父母给张罗的。
又过了许多年,走亲戚的回来说,沿海一带日子好过得不行了,家家都发了。于是,这些看上去早已落地生根的“盲流”,心一下子就活了。那年,徐庶老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返乡热潮,拉老婆带孩子,几乎是连窝端连根拔。姐家是最后一个搬走的,起初姐坚决不走,且俩女儿都已经成家,都不想跟着走;再则姐家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当然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带上两个儿子和大女儿一家走了。
再说姐夫的四哥,因回去得早,在大理石厂谋了份差事,干了几年后,开始往北边倒腾苹果。这年春天江面比往年开化得早,他着急过江清账,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过江,结果刚离江岸就一头扎了进去。一个月后尸首才被打捞上来,就地埋在了岸边山坡上——横死是不能进祖坟的。这是规矩。徐庶想,这冥冥之中倒是应了一句老话:生有处,死有地。
四哥的儿子开着农用三轮车送徐庶,车开得飞快。孩子是在北边出生长大的,面对风雪有着一种天然的好感。他一路按捺不住兴奋,眉飞色舞,进村时,险些翻进路边的阴沟。
村子凌乱得很。多半是平顶的泥巴房,好似一只只倒扣的纸板箱子。少数是石墙黑瓦房——形状不一的石材纵横交错彼此勾连,仿佛龟裂的土地,或玻璃上炸开的裂纹。瓦盖被积雪弄成了大花脸,枯瘦的杂草随风摇曳。
姐家石墙一角堆放着玉米根、干杂草和树叶子,看上去冷涩又萧索。
徐庶浑身都冻透了。
姐拎着烧火棍儿跑出来,劈头就问:小活鬼呢?徐庶愣了一下,立即就反应过来:去我三姐家了。姐眼泪就下来了:你咋不领她来呢?爹妈没了,我就惦记你俩。这个死四朵,一个顶仨,你说咋就瞪眼嫁不出去了呢?南挑北选,圆了不行扁了也不行,到底要找个啥样的呀?我算看透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末了非挑杨木钉子上不可。姐甩了一把鼻涕,带上门,说:她
现在干啥呢?
在宾馆做面食。
这辈子就离不开面食了,累死的货,给钱都不要,白长一副漂亮壳子。你瞅瞅这边的小姑娘,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都快赶上猪八戒他老姨了,出去两年就都发了。这可倒好,再有十年也是白费,就知道啃娘家人,往后你可有心操了。
徐庶不吱声了,心里暗暗有些不舒服。话怎能这么说呢,什么叫出去两年就发了?还有出去一年就发的呢!能这么比吗?什么叫往后你可有心操了?那你当姐的呢?
徐庶放下东西,径直进了里屋。
炕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儿地方是热的。徐庶屁股一挨炕沿,立即跳下地,炕沿凉得跟冰似的。
姐蹲在灶前,一手拿火棍挑着玉米根,一手拿盖帘扇风,哈气和烟立刻如翻滚的云团涌满整个外屋。所有阻隔都消失了,所有器物都不见了,人像在天上,在云里雾里。徐庶像失重了似的,突然一晕,蹲下来,点着烟,却只看见一个豆子似的红色烟头,夹烟的手也不见了。
我在这呢。他求救似地说了一句,然后就像一个瞎眼的猩猩,朝想象的灶膛方向挪去。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姐的声音突然冒出来。灶膛像一个漆黑的洞口似地显现出来,姐如同一个飘忽的影子。
放点纸吧。徐庶下意识地说道。恍惚中好似看到了老家红彤彤的大子火。
要是听爹妈的话,死都不会来这边,该——正说着,一缕浓烟携着暗黄的火苗突地蹿出灶膛,就像青蛙捕食的舌头一样,直奔姐的脑门——完了,又燎猪头了。姐扔了火棍和盖帘,起身冲里屋喊:出来!稀罕草根你来烧!姐夫立即低眉顺眼地出来了。海耗子托生的,在江里给肉不吃,非进海里吃屎。姐还在生气:过完年我自己逃活命,让这帮海耗子在这儿过。
过段时间就好了。徐庶安慰道。
等着,江里的王八扔海里能好吗?我腰疼病脑神经病都犯了,一上炕就想热炕头,一闭眼睛就看见门前的大江。海物我一口不动,明明腥得直打鼻子,愣说是鲜,搬屁股坐嘴,不知香臭。多亏你拎了两条江鱼,要不我这个年就没法过了。现在我连老家的猫狗都想,见谁都想亲一口,能长翅膀我早飞回去了。
闲时看看老乡。徐庶岔开话题。
我可不去,去了倒添堵,哭天抹泪的,没几家好的。
去四嫂家也不远。徐庶说。
不愿看四哥,刚扔下要饭棍儿就打花子,净说那边不是,忘了三根肠子闲两根半时是在哪儿活过来的了。说过了年,回去好好走一圈,什么走一圈?是显摆去。
你姐看问题就是偏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姐夫直起腰道。
你少给我甩文词儿!我可没沾你一滴墨水的光,年轻时跟你受罪,老了还跟你受罪。
没事儿多跟邻居走动走动。徐庶又把话题岔开。
得了,满嘴的海蛎子味儿,开口就是你们北边如何如何——姐突然停住,说对了,我问过别人,原来这也不是南边。
晚上,徐庶缩在被窝里,尽量装作不冷的样子——少说话,因为一张嘴,牙齿就跟通电似地敲起来。姐占着那块巴掌大的热炕头。姐夫鼾声响起之后,姐才说话。
要不是为了老儿子,我才不来。他气管不好,不能种地,过了年去纺织厂。
等大儿子毕业后就好了。
毕业了得自己攒钱娶媳妇。开春我俩去赶海,一天能挣一百。你别为我犯愁,得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这回妈死了,傻子也没了——姐突然停住话头,半天才说,人肯定没了,青岛跟这差不多,冬天死冷,冻也冻死了。他天生就胆小,见生人躲老远,哪敢要饭啊,饿也饿死了。你说要扔就扔远点儿啊,扔海南岛去,我听说那边才是真正的南边,冬天光腚都不冷,随便拣点儿瓜果梨桃就能度命。你二嫂肯定是没舍得路费。
四朵去找了半年,连工地的水泥管子都翻遍了。
不是去找小木匠吗?
徐庶不吱声了。
两个搅灾鬼,愣是把爹妈的寿数给搅没了。四朵打小就是个闹人精,红口白牙没病没灾,一天到晚咧咧个没完,贴符、烧替身、认梨树干妈都不好使。我扔下俺家孩子,天天回来奶她,奶完抱着里外屋晃,啥时晃睡啥时拉倒。傻子天天喝汤药,十来岁都不会自己吃饭,炕上拉炕上尿。等他自己会吃了,反倒麻烦了,自家饭一口不动,我顿顿端碗去别人家给他换饭。就你一点儿不闹,自己跟自己玩。我结婚时你三岁,刚会说话,天天扶着窗台指着岭岗俺家方向呀呀地叫,我都快揪心死了,三更半夜往回跑。姐唉了一声,这样也好,死肠子好舍,要不早晚还是你的事儿。
徐庶拽过衣服,从兜里掏出一卷钱,刚要张嘴,姐突然说:别动,我去迎保家仙。
它们怕生人。姐立即披衣下地,拎起一包蛋糕又说。
回来了!姐又惊又喜地进屋,傍晚放的那包没啦!
猫吃的。姐夫在北炕突然冒了一句。
放屁!姐愣了一下,骂道。
爆竹声从年三十下午开始,就一直排山倒海似地响着。徐庶感觉两只耳朵就要聋掉了。
尽是些破规矩!姐说,过年不比吃喝,就比放炮,吃大葱蘸酱反倒说你会过日子。炮仗买少了却能让人笑掉大牙,家家往死里买往死里放,来人不看饭桌,专看院里堆的炮仗末儿,越厚脸上越有光。还有,小的给老的拜完年,老的还得回拜,弄得跟走马灯似的,一天到晚都不消停。
姐夫说,这些年家家开始搞人工养殖,每年上秋鱼虾出圈,赚上钱的当场就放鞭炮,没赚上钱的也放,图来年吉利。渐渐就兴了这风俗,不光年节,平常遇个大事小事也攒着劲儿放。
你家老宅在哪儿?徐庶问。
当年就卖了。二十多间砖瓦房,一间一百块钱。八个绸布庄直接充公。房子充公一段时间又退回来,后来定了成分,老爹被斗死,又闹了饥荒,就赶紧卖了跑到东北去。如今,老宅都推了盖了大楼,老爹的坟深卧在地下,上面种了庄稼,找不到了。
徐庶把目光从姐夫的脸上移开。前面是乳白色的天空和浓雾一样不知名的岛屿。落潮了,浅海上的冰层开始慢慢在动,有水从礁石上静静地往下流。
临走,徐庶对外甥女婿大毛说,要回就赶紧回,晚了地就没了。
点着一根烟,徐庶又说,你们的根又不在这边,干吗来凑热闹?满山的木头不捡来搂树叶?大子不烧来烧草棍儿?听景不如见景,听蛄叫就不种豆子啦?人得有主意,男的没主意受穷!
女的没主意养汉!外甥女生气地说了
一句。
房子还没卖。大毛道。
要不是我拦着早卖了,听风就是雨,比谁张罗得都欢,以为这块儿天上能掉馅饼呢。
不是怕你想爹妈,爹妈想你吗!
那就赶紧回去!
搬一回家穷三年啊!外甥女婿狠吸了一口烟:来回折腾,让人笑话。
怕人笑话,将来有咧大嘴哭的时候。徐庶也狠吸了一口烟:别等到时哭都找不着调儿!
给姐夫祝完寿当晚,徐庶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给四朵采块坟地。
姐愣了一下,说这事儿哪有娘家管的?她生的是儿子,就是生丫头也得婆家管。
活着时她婆家都没管过呢,死了就更不可能管了。
那也用不着娘家管,等陈一博长大了让他管。
人都走了,可能是回河南老家了。
姐又愣了一下,说一博几岁了?四朵死那年他是九毛岁。
现在毛岁十五了。
小遭罪的一晃就死这么多年了。姐叹了一声,当时连个信儿都不知道。
怕你难受,没告诉你。
妈死时我和你二姐顶着瓢泼大雨去干谷挨家医院找你,谁知你又调下边去啦,回头就看见你捧的骨灰盒……
不是骨灰盒,妈不要,是小红松棺材,木香镇那地方盛产木材。
这回,连骨灰都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她死时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碰到个啥人家呢,有病不要了不说,末了火化费还得娘家掏,真是损透了。
骨灰存放费就交了三年,我还没去补呢。我怕时间长按没主的给扬了。
你没再好好打听打听,那家人真搬走了?
婆家楼都卖了,一博学也退了。
那是诚心要跟咱这支人断啊,姨娘亲不算亲,死了姨娘断了亲。过了一会儿,姐突然说,那——这辈子还能见着陈一博了吗?
指不上了,所以我想给四朵采块坟地,不能老在火化场地下室放着啊,暗无天日的。
不能瞎立坟,对她晚生下辈不好,对侄儿侄女也不好。
所以我得跟你商量,你是咱家老大。
老大有啥用?啥责任都没尽到。
我和我二哥上学那些年,爹妈全靠你们照顾了,现在你都老了,若尽责任,也该是我们。
这时姐就哭了:我是恨铁不成钢,要知她是个短命鬼,那年回去就不说她了。
说也是为她好,当姐的就是打两下,也是应该的。
当时她肚子还没大,可像铁块似的硬邦邦的,我摸过。我是心疼你,她还没完了,人都嫁出去了,儿子也生了,有事儿咋还回来找你呢?
我是她哥,不找我找谁。
工作没了,你自己吃饭都费劲呢,咋还能让你供药喝呢?我当时是真生气了。
她没招儿,她知道心疼人。
心疼有啥用?净干反事儿,说一套,做一套。
是事与愿违。她还想养我老呢,肚子都鼓起来了,还卖八珍熟食呢。
卖什么八珍熟食,纯粹是祸害人!你要不提这茬儿,我都忘了。在你那儿吃药,家里的店让“懒王”给挑了她不知道?没脸,死到脖颈了,
还张罗开店,开店也行,去婆家要底垫呀,回娘家借啥呀?大鼻涕哭多长,不借都不行。说得好听,借?谁还?咋还?不如明要呢,明要还能少搭点儿,这可倒好,都填了大坑!肉包子打狗!娘家又给挨个祸害一圈,钱全让人家给装兜里了。我就纳闷了,满街晃的闲人她不雇,偏叫懒王和他妈看店!你说她这安的是啥心?
她心眼儿实,拿谁都当自己家人。
我看是你们心眼儿实,傻狗不禁逗乐,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人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你们算啥?说白了都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活着是人家的人,死了是人家的鬼,你们愿意跟着瞎操心,心坎儿挂笊篱——多劳(捞)。
话不能这么说,不是一奶同胞吗,婆家不管娘家也不管,那她咋办?
咋办,他们不管,凭什么不管?告他们去!不行了找娘家,能干时咋不找呢?挣钱给你花了还是给我花了?死到临头还没忘了祸害娘家。我看她是成心的。
徐庶不吱声了,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不光是姐的话说得难听,而是其中部分似乎指涉了某些隐秘的、难以启齿、又无法言说的事实真相,并触碰到了他某根脆弱敏感的神经。徐庶感觉自己的心一点点往下沉,甚至提不起精神继续说下去了。
还是你二嫂有心眼儿,一分没借。你二姐那两千块是二分利抬的。你三姐和你咋拿的我就不知道了。
就当帮她完成最后一个心愿吧。
我看还是想想你自个儿吧,这么光杆儿下去,末了自己都得在祖坟边上待着。
我无所谓,哪里死哪里埋,不行把骨灰扬了喂鱼。
那还给她采哪门子坟地?
她在乎。
在乎有啥用?有心栽花花不开,命里注定。
徐庶愣了一会儿,点着一根烟。
她临死前几天,我心烦得不行,她说啥我都不愿听,一张嘴我就给顶回去了,我知道她是在交代后事,可我就是不想听,跟我交代什么后事啊?我把她骂了一顿,还把这些年的糟心事儿一块儿给抖搂了一遍。打那之后,她人就一下子蔫了下来,什么也不说了。当时我比你现在还生气呢,心都伤透了。你想啊,我把她从农村老家领出来,就像屁股后长个小尾巴似的,我走哪儿她跟哪儿,走一步跟一步,想甩都甩不掉。八年啊,变户口找工作,为了进我们工行城市信用社,我和领导都干起来了,弄得人家日后不停地给我穿小鞋。算了,不说这个了,应该的。
还有不该操的心呢,就说搞对象,城里男的有几个是省油的灯啊,人家怕啥呀,完了拍拍屁股照样,可咱不行啊,咱是女的,日后得嫁人呢。不是我封建,是那茬人在乎这事儿呢。所以我和妈隔三差五就扒嘴告诉她一遍。人家呢,可是有主意得很呢,任你千条妙计,嘴上刚答应完,掉过身就不是她了。事实上是我指东她打西,指南她打北,她不听我的我怎么管啊,这种事儿是管的吗?就是管也应该你们当姐的管啊,可你们管了吗?你们不管让我一个没成家的哥怎么管啊?结果就总出事儿。其实早就出事儿了,在老家,徐三凤给介绍的那个,可我哪知道啊,若知道干脆就嫁他好了。这个也不说了。
盼了八年,总算嫁出去了,可心却一直悬着,结果呢,怕啥来啥,偏偏就碰上一个封建脑袋,不是一般的封建,简直都拿这事儿当命了。本来是就低不就高的,下跪作揖追求去的,结果掉过来了,好胳膊好腿一米八大个儿,就不
干活,不干活不算,还整天喝闷酒生闷气,动不动就过堂。我就劝她赶紧离开那懒王逃活命,否则非死他手里不可。命是爹妈给的,除非自己结果了,否则死谁手里都犯不上。她是舍不得儿子。劝了好几年,总算差不多想开了,我就拿钱打发她和儿子去徐二香家散心。临走,我扒嘴告诉她就在徐二香家老实待着,没钱我给邮,千万别去徐三凤家,她家天天无风三尺浪,动不动房盖就能掀起来,接她都别去。可偏偏徐三凤就来接了,接就去了。然后呢,丢下她娘俩儿追自己男人去了——怕在外扯犊子。第二天夜里下大雨,四朵下地关门,门玻璃落下来,割断了手腕上的血管和筋。要不是小星子在家就彻底完蛋了。婚还咋离?一天三遍电话追人家来接人交住院费。婚离不成不说,恶性失血导致骨髓造血功能丧失——骨髓纤维化,脾代偿性肿大……
我就想啊,好不容易刚要听我一回,就把命给丢了,你说我心里是啥滋味?临死前我还臭骂她一顿,连话都不让她说,居然还把她扔给雇来的一个大姐参加同学会去了!你说一想起来我心里是啥滋味?爹死了,她和妈整天窝在炕上一梭子一扣地给人织网挣手工费,供我读完后两年大学,她连买棉鞋的钱都给了我,穿了一冬天单鞋片儿,你说现在我想起来心里是啥滋味?我知道她临死要说的话是啥,她怕将来公公婆婆不在了,陈一博没人管流浪去。不还没到那一天吗?到那一天,他背个小兜儿来找我,我能不管吗?我是他亲娘舅,我没儿没女光杆儿一个,我能不管吗?她知道自己死后婆家不会管,娘家也不会管,两下都不靠,可她怕做孤魂野鬼,想入土为安,你说我要不管,心里是啥滋味?
除非在城里买个墓地。
太贵了,最次的也要三四万呢。
那就没招儿了。
我想把她埋爹妈跟前,听人说,埋一百步开外就行。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你得跟你二哥二嫂商量去。姑姑可管侄子。
我是问你有没有意见?
我一个外姓人,说了也是多嘴,你问你二哥他们去。
我想让你先发话。
我发什么话?这是你们老徐家的事儿,我可不背这黑锅。
什么叫老徐家的事?什么叫让你背黑锅?你难道不姓徐?
我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光我,小死鬼也不姓徐。
得,那我就不废话了,我跟你说,我要非这么做不可呢?
那就别怪我说你了,你凭啥?她有儿子,你一个老跑腿子当哥的,自己老祖坟还没哭过来呢,替人家哭什么乱坟岗子?那可真像咱爹说的,书念得越多越糊涂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姑姑可管侄子,咱家可就那一个后代,你要硬把一个半路死的外姓人埋进祖坟,将来大侄儿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得负全部责任!
……
栏目责编:方娜
一首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