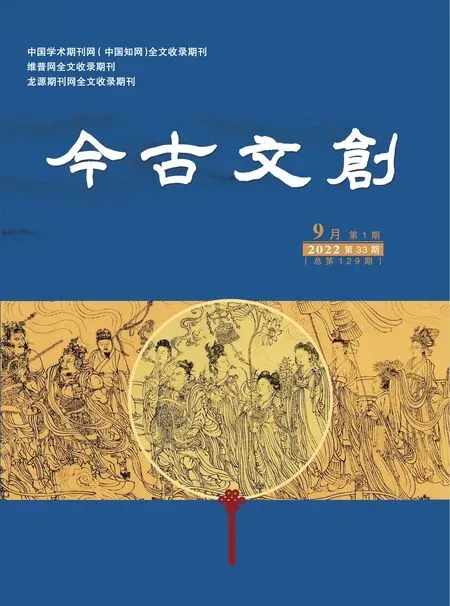宋代女性词乐的审美研究
◎张程鹏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文人词乐的高度发达,兼具男性与女性的词乐创作,使宋代文化呈现出一个开放与进步的状态;同时作为历史的转型期,词乐上承唐诗,下启元曲,为宋代文化增添了一份历史使命感。宋代的女性词人、诗人约有200多位,以李清照为代表,并与朱淑真、张玉娘、吴淑姬四人称为“宋代四大才女”,当然还有魏夫人(魏玩)、孙道绚、王清惠等。她们的词乐创作最大的特征是词乐所表现的内容与风格特征,但在创作技巧与手法上与男性词人一同遵循以词入乐、词乐合一的规范。
一、以词入乐的审美规范
(一)以词之律协乐之律
“宫商角徵羽,是音乐的高低抑扬,平仄四声是字音的高低抑扬”。以词乐之平仄四声协于音调之宫商,如若不然就是“失律”词之格律。词的音高与长短与音的高度与长短相协调,其节奏与音韵协和共融,那么即使排除音乐,词本身也能散发音乐性,这也是为何宋词在词与乐分离单独成词也有其音韵美的原因。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论》:“盖诗文分平测,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即是指词相对于诗而言,不同之处在于求平仄之分,不仅需要协六律,还要有四声五音词均拍轻重清浊的差别。“五音”是指喉牙舌齿唇,主要是说在演唱时将声母发音进行分类;五声即是五类声母类型;六律与六吕构成我国古代十二调。她强调词即是作为乐中之词,是能歌的词,词应入乐才能成为词。其作《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音字节奏短促有力,加之其音节的有规律的出现以及同音相和的声调重复,造成人们音声上的回旋之感并给人以语言音韵的形式美感。
词区别于诗的重要之处有音乐之律的规范即可以拥有歌唱的音乐属性,但是只将两者单纯地合在一起,未能实现词与乐完美协调与融合,重要的是需注意词韵与音均和谐统一。
(二)以词之韵入乐之均
“词腔谓之韵,均即韵也”。古代“韵”与“均”常混用,两者都读“yun”,但细究两者都有各自所要表达的内容。“凡字之尾音相类者为韵”。那么韵主要是指诗词文赋中的押韵关系,由声母与韵母构成的音韵关系。当然宏观上讲,还有声音起伏有致之音乐美的意思。而“均”于音乐中也有不同的释义,乐律学角度出发,是以宫为主的一组音列,意为“均音阶”;从乐句的角度出发,是以乐句为单位的一段旋律,且“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声待拍,方和乐曲之节”。
词发展于宋代时当能“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那么如何以词之韵入乐之均?“韵”与“均”的协调更在于整体上的规范,需要对词的节奏、四声即上、平、去、入的音韵规范。如此则要谈到音乐中的调式主音(宫)的问题,音乐以主音开始并以主音结束即重视首尾音的标准。那词入乐即也需重视首字与尾字的声韵关系,也便是词之开始要有调,即“起调毕曲”也。在首尾音韵相同情况下,加之声势的节奏快慢与音声高低,便能起旋律悠扬婉转之意。
词入乐的规范在诗、词作家等中尽可以找到详细的论述与评论,宋代现存可考的带有词谱的有姜夔的《自度曲》,即是词与曲相协调的词乐形式。而女性词乐可考的只有歌词方面,但也强调入乐歌唱,李清照就曾列举《声声慢》《玉楼春》为例,如词只是词,没有协于音乐,那么词调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虽没有词谱,但词入乐的音乐性并没有丢失,即词之“韵”也包含乐之“均”。而从“韵”字本身的结构上来说,也是由“音”与“匀”组成,也说明“韵”之音乐性内涵。
二、词乐相融的审美体验
(一)婉转悠扬的旋律美感
李清照、朱淑真等女性词人在宋代隶属于“婉约派”,其特点主要词性婉转、情感细腻,而文辞内容上也多是对丈夫的情爱或思念的表达。这与当时“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形成鲜明的对比,苏轼不拘于诗词格律,也不限于四声、五音的关系。“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除苏轼之外,晏殊、欧阳修以及苏轼都不协于音律,而李清照将主要的原因归结于未将诗与词加以严格区分,更未注意到音律的作用。此评价虽未能获得后世的认可,但其对词之音乐的重视是值得探讨与肯定的。
词之内在音韵在四声平仄、五音、节奏的规范下,声调的抑扬顿挫之感也会带来旋律音乐宛转悠扬。“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却道海棠依旧”。中的“试”的领头字与“旧”的结句字都为去声字分别与前或后形成上去、去平的关系,而这种音调变化最能体现旋律的走向。词中的领字也相当于乐曲开始的音调,能起到“发调定音”或“转折跌宕”的作用。而在词作中,凡有“抑扬高下之处”,往往是需要用“上去”或是“去上”等声调连用的。朱淑真的《蝶恋花·送春》:“少住春还去”与“犹自风前飘柳絮”、“绿满山川闻杜宇”与“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中的“去”与“犹”“宇”与“便”即是去声与平声、上声与去声的关系,其声音的跌宕起伏和音乐的高低变化形成和谐统一的形式。“盖上升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厉尽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声势上下转折能使其腔形成高低变化的抑扬顿挫之感,这样才能使词方能体现其情感的迸发与词乐的歌唱性。
词的音势转折拊合于音乐的旋律就形成了曲,音势的曲折长短的不同随之配乐的长短也会增加几个音符或减少几个音符,而词若要入乐也不能呆板的只强调词律或是音律,两者应协和的发展,达到“合之管弦,付之歌喉”。
(二)悲美凄清的情感风尚
宋词声势与旋律的抑扬婉转,加之词的内容,将女性词作人的悲美凄清的思想感情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她们作为区别于男性的词乐创作特征就是在于词乐创作的内容的细腻程度与表达的情感思想等层面,且词的内容多传达出对青春美好时光流逝感叹与思念远方亲人的悲美情感。而她们的词乐形象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与现实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李清照与朱淑真等丈夫都为官,张玉娘与吴淑姬两人身世没有前者好,但四人都有生活或是情感上的烦恼,因此其词乐都表现出悲情色彩。
她们的词作中表达悲伤的情感与词的音乐性相融后,使整个词乐达到了既悲又美的风尚。吴淑姬的《小重山·谢了荼蘼春事休》即是非常普遍的八韵结构,其词“庭槐影碎。莺虽老,声尙带娇羞”、“独自倚妆楼”前一句以自然之景做喻,小莺长成老莺,但其声音还略带少女的娇羞之意,这恰似也在暗喻词人的成长,而后一句则从自己角度出发,表达孤独、凄清的情感状态,不免多了份伤愁之意。朱淑真的《谒金门》中“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中“燕”“卷”的去声字作为韵脚,音声的押韵与“断肠芳草远”的思恋远方亲人的情感共融,更为这一词添上了悲美的色彩。
李调元曾评论夸赞李清照:“不徒俯视巾帼, 直欲压倒须眉”。李清照之词在宋代女性中当属最佳,不仅有女性婉转妩媚词意抒发,更有胜于男性的婉约中有清狂、豪放的情感体现。但也离不开其身世经历所带来的悲情色彩,《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中前有“愁”之“千缕”,后有“花雨”以相协,且后者更富于了审美的内涵,“愁”在这里似乎也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
如果词的内容表达的是词作人的悲伤情感,而词之声势与平仄的起伏变化则形成了美的听觉感受,两者相融变刺激了听众的感官,也产生了受众者心的触动,而达到受众与词作者“共情”的美感体验。
三、词乐合一的审美意象
(一)“春”意象之生命意识
词不同于诗在于采用长短句的句式,而且具体的音韵位置并未有确定,主要是依据调的变化而变化。这增加了词之音韵的丰富性与可变性,且相应地词乐所表达的审美意象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宽阔的想象空间。“立象以尽意”之“象”在宋代女词作中主要有在于自然之物,“春”作为四季之首,经常被用来感怀时间的流走。尤其女性对岁月的珍视,在其词作中尤为能体现出来。
吴淑姬的《小重山》中“谢了茶蘼,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描述的春天要走了,但是还有“花片子”点缀在枝头上,这说明春天还未走,也是对时间消逝的挽留之意。“莺虽老,声尚带娇羞”之“莺”是否指代的就是作者自己,虽老但是还未老,感叹青春时光的飞逝流转,是对自己的尚有“娇羞”声音的真实写照。朱淑真的《蝶恋花·送春》:“把酒送青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举起杯来送别春天,春天却不知我心意而不语,到了黄昏的时候又下起了潇潇雨。“春”是四季之始,也是嫩芽出土的季节,一切都刚刚开始,因此“春”有换发自然之物的作用。当然也寓意着少女的“青春”懵懂的美好时光,“潇潇雨”既是作者对春天的送别之意,又或是对自己青春的惋惜之情。“潇潇”的叠字形式加强了句式的音韵美,渲染了气氛,将“潇潇”的动态融入内心的情感波动之中。
“春”既有期盼之喜又有缅怀之伤,女性作为将其作为时间流逝的象征寓意,来表达对生命意识的重视。词乐合一的状态即是音声互相协调,词之长短句的形式促成了音势高低与节奏快慢的变化多端,乐也会根据词的平仄、韵位、声势的长短来增加或减少音符的时值。而以此词之平仄四声的高低婉转可以将每个词的情感内容都显露出来,并使产生“余音绕梁之意”,词乐也会带来寓情于景的审美感受,并与词人共同体味无形无象的意蕴。
(二)“花”意象之少女情怀
“花”的题材在女性词作中尤为凸显,或是睹物思情,或是对国家的担忧,都不同程度借“花”以抒情。“梅”“荷”“杏”等不同种类的花作为暗喻,都为词作的整体范畴增添了文学上的美感。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花作为歌词入乐歌唱,旋律赋予歌词以悠扬婉转的声调,歌词丰富旋律的情感内涵,即是“音乐的文学性”。
李清照的《如梦令》中“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海棠”之花暗喻自己,“红瘦”在这里是意在“憔悴零落”的含义,或有海棠的凋落也在指青春的不复返,有惋惜之意。“知否,知否?”的叠句形式,恰似疑问的语调,实则包含否定的语气。通常是通过乐句的重叠或延长来表达某种不一样的声情。这种“叠句”的形式或作为和声适应词乐声情的需要,或渲染气氛,强化了词的音乐感染力。她另一首《如梦令》中:“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其中“藕花”即是荷花之意,这首词是她十六岁时所作,也是其处女作。但词如白话一般但却有“百读不厌”的艺术魅力,“争渡,争渡”与“惊”词义上动与静的完美结合,两次“争渡”情感表达上也不完全一致,后者像是和声,给人以一唱三叹的感觉。
朱淑真词作中的“花”暗喻少女形象表达得更是淋漓尽致,其《绛都春·梅》中“粉蕊弄香,芳脸凝酥,琼枝小”与“盈盈笑靥称娇面,爱学宫妆新巧”。看似在写花,实则在写人。“凝酥”与“娇面”即是青春少女娇美的形象描写,也是早梅的典型化特征。词句的长短形式与节奏的快慢相协调,加之声势的变化,“梅”的艺术形象就更加生动立体地展现出来。
宋代女性词人对“少女”时期的感怀,也正是对自己生命流逝的感叹,虽现在未能考察其原有的词谱,其词(歌词)作为协音的部分,仍能感受其中的音乐与情感的魅力。
四、结语
女性词作的兴起在宋代是必然化的趋势,她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宋代词学,而且发展增添了一份女性的力量。虽然宋代流传下来可考的女性词作未带有词谱,但人们也可以从中体味其内在的音乐艺术魅力。词乐的韵律和谐,声词相从的悠然婉转意味结其叠字、叠句的和声效应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之美。而女性词乐的魅力在于其词婉转的歌唱性与形象的意象化表达,更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①刘尧民:《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②(宋)沈义父撰:《四库家藏 乐府指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宋)李清照著、吴惠娟导读:《李清照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④(宋)李清照著、吴惠娟导读:《李清照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⑤(清)万树:《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⑥李调元,清代戏曲理论家、诗人,著有《雨村词话》《童山文集》《蠢翁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