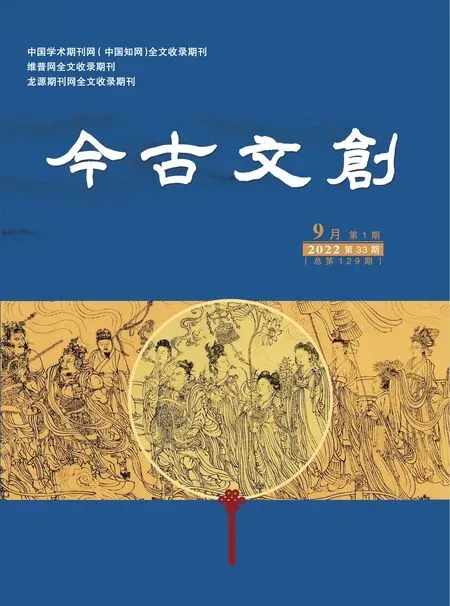永恒的诗意: 启蒙到深层的生命审美哲思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命若琴弦》诗性发展
◎彭 妍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0)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史铁生挖掘自我记忆为基础的前期作品。小说讲述了作者插队时和陕北人民在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放牛的故事,描述了他所体验的独特的“爱”与“美”支撑的世界,是返城知青“我”对插队生活的深情回忆。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潮流中,史铁生开始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以短篇小说《命若琴弦》为标志,史铁生进入对人本困境的深切追问。《命若琴弦》讲述了老瞎子和小瞎子以弹琴说书为生,为了虚设的无字药方而活,并且不断轮回的故事。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命若琴弦》作品中,都展现了作者内在的诗意,但前期作品大多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进而对生命意义初步探索,因而前期诗意更具有史铁生自身独特的个性和初步的启蒙意识;后期的作品诗意性则转向更深层次的群体哲理思考。
一、启蒙生命:个体诗意笔法的“清平调”发现
较之于知青“伤痕文学”主流社会的叙述立场,史铁生、陈村、张承志等人侧重描写乡村净土,表达乡村思恋之情,强调农村生活的价值,进而对民间生活中的人性品格进行审视。史铁生1969年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独特的人生经历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80年代在对插队生活回忆时,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书中用文字谱写清远、真挚的生命之曲。清平湾的一切植入了他的内心深处,展现了作者的理想精神世界。散文化的笔法下,全文抒情诗意的传递在叙事手法、音乐性和文学风格等各方面均有体现。
(一)诗性清平调的总特征
在叙事基调上,以清平调为主,即清贫、平淡。相较于之前的“伤痕”与自哀自怜与稍后理想主义及悲壮悲情的英雄主义高亢,《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叙事基调更加平淡、朴素并带有淡淡的忧伤。题目中,“遥远”是相对于城市中心来说的空间感,表层意为偏僻、荒远;“湾”则是乡村的代名词。但深层内涵上,这是作者对那片土地的情感依恋与感怀。这与当地的人生境遇体验相关,折射了陕北人民古朴的民风:生活清苦,却没人捕食野鸽子、野鸡、燕子等小动物;渗透了当地古老悠远的文化:清明的子推馍,“呐喊”(喊)“芫荽”(香菜)“玄谎”(骗人)等古老的字眼的日常化。
(二)诗意、音乐、语言的歌唱性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展现了史铁生对黄土高原的特殊情感及其对陕北记忆的音乐性书写。陕北民歌在这篇小说中的表达效果是诗意化的。虽然语言不似中国古典诗歌典雅,但这也是本土生活的艺术化体现,歌唱了人们的淳朴的心声。更者,相较于复杂的城市化,乡土气息的回忆在作者心中实际上更具有诗意化、真挚性,这样外在真实的刻画实际上是因为内在的渴望而诗意化了。此外,小说的音乐语言音韵与音乐节奏的独特融合对于现代歌剧音乐的发展、影视剧改编音乐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音乐是现在影视及音乐剧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对于相关作品的表达意义重大。因此,为了防止文本的“失声”,可借助当代舞台和影视技术不断对文本的音乐媒介进行深刻地挖掘,使其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焕发活力,更具魅力。《边走边唱》对《命若琴弦》进行了影视改编,虽两者表达方式不同,但相互融合与发展,为文化传播开辟了新的道路,两种媒介形式的交互传播也是市场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诗意苦淡的乡土叙事手法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注重对于乡土的叙述,创造了一个诗意的乡土世界。在这里,没有控诉或痛斥,虽有苦难,带着淡淡的忧伤,但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意图展现一种诗性的真挚人生与个性美。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乡野山村、风俗人情、民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了较为真实地描绘。这一“另类”叙事既使得80年代初政治语境中知青文学进一步反思新时期“文革题材”文本及思潮的历史局限,也促进了主流知青文学中新的叙述气氛和情绪流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知青“知识分子”,眼光逐渐从自己的“苦难”转移到了那片被忽视的黄土地农民身上,产生了底层关怀。关注、悲悯焦点的转移,从道德到情感上都感受着农民化残酷的生活为豁达的人生的生存耐力,呈现出了知青文学书写的另类平民姿态。陕北农民破老汉连同他那《走西口》《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起融进知青文学的描写主体,成为重要的精神资源。虽仍由知青来书写,但文本已经是知青文本中的“乡土叙事”了,发出了知青文学民族精神的先声。相较于梁晓声早期文本的“一批以苦难为旗的道德自救、救赎者的形象”,这一乡土叙述更具有自省与批判,对知青文学的重构和多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这一乡土叙事意义不只是对于“食”“色”的田园牧歌和简单朴素的耕种生活的刻画,也不限于诗意地展现陕北农民的清平与闲适的心境,更是作者对现实苦痛的希望回忆,进而启蒙生命的思考。
(四)诗意的笔触结论
作者对黄土地上丰富多变的四季景色与农事风物进行了细致描写,展现了清淡的叙事风格和高昂的人格歌唱,如人物合一中“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在物质与精神匮乏而苦涩的小山村,这一描写既凄美,又传达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儒雅温和是丑,横蛮粗野为美),别开新境界。散文诗叙述,闲谈的笔调、故事情节上的弱化、语言的文学之美,高扬着纯朴、善良的人性美和超脱人生苦难的精神美。
此外,整体上呈现自然的特点,清平湾的牧歌情调恰恰是人、动物、自然之间和谐的灵性所营造出的。这是文学艺术的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自然的叙述手法;语言、人物的素朴美;理想清贫的美感、节奏上的跳跃回放;散文诗的气质。虽然如此,但再读则感觉文章中深藏着强烈的人生悲剧意识和忧伤,这就引发了对于生命意义的初步哲思。
(五)初步的启蒙:实现个体价值
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展现了诗性的世界风貌,但这不是纯粹的审美形式,诗意的选择是审美与价值同构的结果。这一前期的回忆作品则是初步对生命进行了启蒙思考。
生命的更迭是必然的,个人的价值在于过程。这一阶段,通过这一作品主要通过“我”对老黑牛的态度转变。老黑牛也曾年轻过,也有自己生命的价值,并且不断诠释自我价值。虽和年轻的红犍牛比赛输了,但真正的意义在于最后也始终坚持了生命意义。这一过程所留下的伤疤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标志,也更为重要。
二、深层哲思:生命姿态的审美与价值建构
(一)诗意的审美建构——神性的“虚真”
1.融合
史铁生是对国外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借鉴吸收与本国现实融合较为圆熟,在《命若琴弦》《礼拜日》《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等作品中蕴藏了神性的意味及扎根当时现实土壤的鲜活人性生命体验。史铁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即是艺术与人灵魂的“内在需要”同构。因此,在史铁生的文学世界里,作为审美主体的史铁生发现了艺术欣赏的诗意和美感,具有抒情性。《命若琴弦》中的无字药方,作为艺术符号的象征物,是连接人生“奇点”或者说“起点”,唤起了人生命的记忆和印象,进而把握个体人的心灵背后的现实和历史。
2.理想人性
史铁生找到了理想人性的合理限度,理想人性即神性。但人不可能成为神,所以理想人性即是“虚真”的。人类整体存在的背景下,相对而言,具体的个体是有限的,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无限的。人作为个体性的存在,要想“永恒轮回”(如老瞎子、小瞎子的传承轮回)地发展下去,必然要人类整体之中。有限是残缺,无限是圆满。《命若琴弦》作品采取寓言的审美经验的表达,以部分象征整体,以具象隐喻抽象,即以人显神或以神喻人,敬畏和现实悲剧。
史铁生在对神性的圆满与人性的残缺对比中(两个极点),得出人与神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架构。因为绝对的神人冲突与相对的神人融合终究会产生距离,所以史铁生的作品中,丑弱的人与残缺的人生是其主要表现对象,如《命若琴弦》中的大、小瞎子,展现了史铁生更具现实性的人性关怀与哲思:心灵救赎与生存力量。
3.残缺美
受难者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是史铁生建构自身文学世界的核心要素,这不仅标志着史铁生创作的重大转变,暗示着新时期文学审美风尚的重大转变。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强调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共生,而史铁生与雨果有着大致相同的观点,但其进一步确立了残缺作为美的存在的基础性地位,认为完美和圆满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之中,实现审美现代形态的转变。
而史铁生的残缺美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感悟和美感经验结合下,具有灵魂深度和广度的结果。人的广义残疾,即人命运的局限。从病理学的残疾中剥离出来,史铁生发现人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残疾作为人的抽象本质与神的圆满形成对照,从而形成审美距离感,产生审美效果。
此外,两者对照下,人的残缺直接表现即是人性恶。对此,史铁生表现了深切同情与人性的虚伪和残酷。神性需要对人性进行监督和引领,但不可矫枉过正。
史铁生由世情描墓到生命感悟,由故事构筑到寓言象征,由自叙传的写实到关注人类的精神性存在的创作历程,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命若琴弦》的过渡可知,这是新时期文学向前发展的大致缩影,也是史铁生自己独特的个体意义及突出的典型意义。
(二)诗意的生命哲学——困境中的荒谬目的与价值过程
1.困境
史铁生在《自言自语》中说到人生的三个困境。《命若琴弦》展现了目标即使是虚设、荒谬的,但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的追求与反抗。《命若琴弦》对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展现了缺憾的人生,引出在对困境的超越中实现价值,进而思考生存的真相。层层深入,不断探索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但始终在虚设目标完成前没有进行检验,形成了反抗的缺失。这一无字的药方实际上是人们虚幻的象征。三种根本困境中《命若琴弦》将生命寓于过程的哲理性思考,有着对精神的彼岸世界的期待。
生之所依和生存意义是这部作品之中渗透作者的深刻感悟。无法预知人生,生活其中,即使有困境就必须面对,并寻找与之相对抗的人生价值理念,以此为人生信念,使人的存在具有价值意义。这样的人生哲理具有诗意化,是现实深层思维的内在诗歌。但目的是虚设的,虚设的目的却能引导着实在的过程。人生是实在的,但是结局却是虚设的,这就是人生的荒诞,也是人生的悲剧。
2.命运
可以说,《命若琴弦》最后老瞎子没有成功的原因和痛苦,主人公更倾向将此归结于命运。之所以能坚守承诺,坚持每一根弦都通过真心弹奏而断裂,都是因为命运的作用。在真正发现这个承诺无意义时,“老瞎子的心弦断了,现在发现那目的原来是空的”,目标的最终落空衬出了作者将人生过程当作一种审美连续体的无谓的苍凉诗性。老瞎子应该是幸福的,毕竟大半辈子都因为这个虚设的目的而实现了人生价值;小瞎子应该是幸福的,在下一个轮回中,他也可以实现重新的轮回。但他们也是可悲的,永久地轮回,永久地在命运的束缚下挣扎,毫无尽头。
(三)诗意的超越——灵性维度“无意识”的抒情塑造
史铁生早期的抒情小说,和京派小说的创作理念“安魂”“移情”等治疗功能上,在文化乌托邦建构灵性维度的确立和诗化语言等方面上,表现出了与“京派小说”之间密切的艺术关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历史真实中的“清平湾”仍有差距,是心灵的反馈。真正现实中那片土地可能应该是自然环境恶劣贫瘠、长期处于饥荒的生存状态、政治生活……可作者只听到了飘荡着的时而高亢、凄婉、忧伤的歌声。史铁生表示:“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真情的陕北民歌,笔下每有与这种旋律不和谐的句子出现,立刻身上就别扭,非删去不能再往下写。”此时,陕北民歌更展现出人类心灵自我疗伤的一种本能性力量,在苦难中激励人类,如简单的语气词,最生动地表达出了苦难中的人们像幼儿那样对天地表达单纯的相信和祈望。
史铁生在“我”的个体生命体验中找到治愈现实生活伤痛的力量源泉而非“创伤”价值。个体生命体验也是京派作家所重视的,他们都共同地以回忆性叙事的方式来突显他们所要强调的主观性生命体验。
“五四”启蒙文学等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探讨苦难中人们的出路问题,而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则又提供了灵性的维度。新时期初,作为京派小说家的汪曾祺更多地强调世俗性的欢乐,缺少了如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灵性层面。史铁生和京派作家有着某种联系,虽作者并未点明。同隐含的宗教因素一样,史铁生与京派作家相比,更深入也更有艺术性。
三、结语
史铁生对于人生及生命的哲思不断深入,塑造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形成了独特的诗意人生。诗意的人生对于史铁生来说,不是对于古典语言意境的追求,而是自我思考与构建的审美哲思境界。在这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回忆支撑的“善美”诗意世界,《命若琴弦》是真实血肉哲思映射下的“虚真”内在群体意识。不同于其他当代作家,虽然人生的经历带来了苦痛,但苦痛引起了作者的深层反思与情感体验,最终升华为艺术化的“诗意人生”。
①庞倩、李曦珍:《浅析影视媒介与小说文本的互动关系—— 〈命若琴弦〉与〈边走边唱〉之比较》,《求实》2013年第1期,第252页。
②(俄)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③史铁生:《写给本刊编辑部的信》,《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