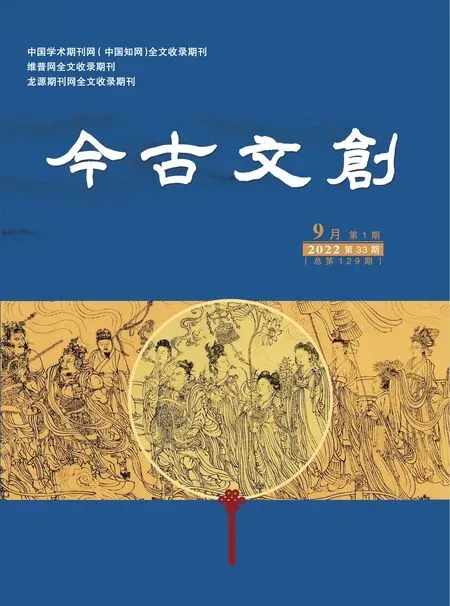浅析《十二楼》中的媒妁形象
◎崔文元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为李渔所撰拟话本小说集,共收小说12篇,每篇以一座楼为中心关目,讲述着有关才子佳人、义夫节妇、昏君奸相、侠士诤友的市井杂谈,以昭示作者“觉世”之旨。其中的才子佳人型故事多有媒妁形象出现,他们虽不是主要角色但在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有些自身性格也较为出彩,有着丰富的文学意蕴。
一、媒妁形象类型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为人作媒是成人之美的好事,而且担任媒妁又无太多其他条件限制,“似人人可为,造成了为媒者的多元角色”。
(一)职业媒
职业媒指专以做媒为生的媒妁,多以女性为主,是《十二楼》中出场频率最高的媒妁类型。《十二楼》所描写的职业媒们没有自己的姓名来历,仅被以“媒人”“媒婆”等代称,在完成说亲任务后便立即消失,不会贯穿情节始终。有关她们的行为描述也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如“媒人照他的话过来回复”“但叫媒婆致意小姐”等,大多数情况下,职业媒只是小说叙事中用来联系男女双方的“功能性人物”,并不是作者重点着墨之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楼》对职业媒的描写较少触及其负面形象,展现更多的是她们的责任感和时常出力不讨好的无奈,《拂云楼》中裴翁在悔婚多年后央求旧时媒妁重去韦家说亲,媒妁被韦翁拒绝后“只得赔罪出门,转到裴家,以前言奉复”,后因裴翁下跪“求他勉力周全”又再度前去韦府传话引得韦家夫人破口咒骂;《十卺楼》中姚家父母借官府声威逼媒人三次传说换亲事宜,“媒人没奈何,只得又去传说”。说媒一方面是媒人们“成人之美”的自尊感与成就感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处于市井底层的媒人们赖以谋生的职业。
(二)官吏媒
官吏媒指官吏为百姓做媒。在以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官吏为媒”往往具有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契合统一的合法性。《夺锦楼》篇中的刑尊便是典型的官吏媒形象。钱小江和边氏夫妻因将二女嫁四男而被告上了官府,暂行太守职责的刑尊见两人所许之人皆非良配,便判夫妻二人所谋的亲事都不做准,自己又亲自在科举考试中替二女谋求亲事,最终慧眼识英雄,为二女觅得佳偶,一时传为美谈。刑尊是明清文学作品常见的清官形象,认真负责、公正无私的性格特点加上身居官职、社交面广的特殊身份,赋予了他成就良缘的客观条件。同时“官为民之父母”的家长观念,也使得此种媒妁对于当事人带有强制性和荣耀性的双重性质。
(三)亲友媒
亲友媒指男女双方亲友为彼此说媒,此种媒妁因熟悉双方家庭背景和彼此意愿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被视为说媒的最佳人选,《十二楼》里的亲友媒说媒结果都较为圆满。《合影楼》中屠珍生和管玉娟隔水相爱,但因两家向来不和而无由说亲,故“与屠管二人都相契厚”的路子由便在小说中承担起这份任务,从中巧妙斡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拂云楼》中的俞阿妈一方面是韦小姐和能红的女工师父,另一方面又是裴七郎学中门斗之妻,双重身份为其了解彼此心意提供便利,最终促使能红愿意嫁入裴府。以亲友为媒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媒人说辞虚妄不实而造成的婚姻悲剧,而且也因熟悉双方情况增加了彼此婚前了解的可能性。
(四)侍女媒
侍女媒是媒妁类型中的一个特别存在,作为封建大家族的下人,婢女原没有为主人说媒的资格,但也正因为身份的低微使得她们可不受礼制的严格约束四处奔走,从而为男女方沟通提供便利,同时又因为谙熟主人心思,做媒往往能够成功。《拂云楼》中的能红为韦小姐婢女,美貌过人且善用智谋,得知裴七郎求亲之意后,巧施计谋使韦家心甘情愿将小姐嫁入裴府,同时自己借之与小姐同嫁,“公事”“私事”一起做成,无怪乎其于一开始说:“这头亲事,只怕能红不许,若还许出了口,莫说平等人家图我们不去,就是皇帝要选妃,地方报了名字,抬到官府堂上,凭着我一张利嘴,也骗得脱身。”一番言论足可见侍女在说合姻缘中的重要作用。
二、媒妁行媒动机
纵观《十二楼》中的媒妁形象,他们虽都以说合男女婚姻为己任,但行媒动机却又各有差异,同与不同之间,媒妁群体的形象得以丰富。
(一)营生工具
媒妁作为一种职业在明清时期多由妇女担任,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部分女性凭借着广泛的人脉和能说会道的本领选择担任媒妁以获得自主谋生的机会,《十二楼》中的“职业媒”多出于此种动机而行媒。由于以说媒为生活收入来源,媒妁在行媒时多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而尽量满足主家要求或极力避免与其产生正面冲突。《拂云楼》和《十卺楼》中的媒婆因受男方所托,在明知所提要求非分的情况下却无奈再三往返于女方之家;《归鹤楼》中的媒婆受官尚宝要求,在成亲时竟私自调换新娘;《夺锦楼》中的众媒人因惧怕得罪边氏拒绝为钱小江说合,只说:“丈夫可欺,妻子难惹,求男不如求女,瞒妻不若瞒夫……”在此条件下的媒妁或无自己的独立性格或显得欺软怕硬,做媒也就不以为男女双方觅得良配为主要考量,而是一切以主家所托为准,呈现出重“谋合”而失“斟酌”的特点。
(二)促成良缘
在“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十二楼》中不少媒妁出于一心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望而前去说媒,他们怀揣着对做媒这件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媒时多尽心尽责,情真意切。《合影楼》中的路公收到替屠公子说亲的请求后立即表示:“既属至亲,原该缔好,当效犬马之力”;《夺锦楼》里的刑尊出于“没有这等两个人都配了村夫俗子之理”的考量,亲自为二女选亲,“既要看他妍媸好歹,又要决他富贵穷通”。此种“媒妁之言”一心一意为成就男女双方良缘考虑,并不完全为“父母之命”所限,呈现出较为积极正面的媒妁形象。
(三)兼求私事
在《十二楼》中,一些媒妁在媒人身份外自身与男女两家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故其往往于说媒的“公事”外兼谋自己的“私事”。如《合影楼》中的路公在得知女儿芳心暗许屠珍生以致成疾后,考虑到已答应为屠管二人说媒不好食言,便巧设圈套将两门亲事合做一头,既完成媒妁之职,又治好了女儿的病;《拂云楼》里侍女能红一开始向小姐说媒的原因就是想借之同嫁裴七郎,“公事若做得就,连私事也会成。岂不是一举两得?”此种复杂动机的产生源于此类角色只是暂行媒妁之事,在媒妁身份之外还有更为日常的主要身份,这便塑造了人物形象的多个侧面,使其不会陷入类型化的窠臼,而显得富有人情味。
三、媒妁形象的文本功能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构思新颖、情节曲折是《十二楼》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李渔既编撰戏曲,又创作小说,在创作小说时极其重视创作技巧的使用,曾言:“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人物安排多有其独到之处,《十二楼》中的媒妁群体除说媒职能外于小说叙事中即有多方面作用。
第一,通过媒妁言语间接塑造男女主人公形象。
在《十二楼》里,语言描写是塑造媒妁形象的主要手法,而这些言语多是直接转述当事人的话,并不夹杂媒妁的个人意志,她们实际上在充当着男女双方的“扮演者”。如《夏宜楼》中詹娴娴于婚前从未见过瞿吉人,瞿吉人频频授意媒婆代自己向詹娴娴传话,或探望病情、或谎称有神眼、或递送诗歌……一件件事情下来,詹娴娴早已认定其为俊俏风流才子,非他不嫁,看似媒婆说合成功,实则是男方运用巧智谋得。又如《拂云楼》中俞阿妈替裴七郎向韦小姐传话,其“照依七郎的话一字不改,只把图谋之意变做撺掇之词”,受小姐严词拒绝后又回去向裴七郎“把小姐的话对他细述一番”,看似小姐驳斥的是说媒的俞阿妈,实际上主要是对男方悔婚又提亲行为的驳斥。媒妁群体的存在为小说里男女双方的情感交流以至于后续情节的发生提供了合理性,而透过其言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从侧面得以塑造。
第二,充当读者耳目,代读者议论、提问。
李渔的短篇小说在整体上多采用作者全知视角叙事,除了“入话”、篇末部分的评论外,在正文中也经常使用说书人口吻来间出己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行文中也会有意识地使用限知视角以设置悬念使情节跌宕起伏。如《十二楼》中的媒妁群体作为剧中角色,所知并不比读者多,从媒人的视角发出的议论、质疑也就道出了读者的所思所想。如《夏宜楼》中的媒婆不知瞿吉人“神眼”的关窍,在传递瞿吉人送给詹娴娴的密札时,责怪他道:“你既有这样神通,为什么不早些显应,成就姻缘,又等他许着别个”,问詹娴娴是什么法子,小姐“只是笑而不答”,一来一往之间双方计策都已谋定,只有读者和媒人还不明就里;《拂云楼》中俞阿妈听见能红知晓自己与裴七郎的往来,吓得毛骨悚然,暗自思量:“为什么我家的事她件件得知,连受人一跪也瞒她不得?难道是有千里眼、顺风耳的不成?”造成悬念,随着后来作者补叙能红于拂云楼上巧遇这一幕的来由,真相才得以大白。这种限知视角的安排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也就增加作品本身的吸引力。
第三,推动情节发展。
媒妁在《十二楼》中还具有聚合人物关系、催生故事情节的功能。古代封建社会受男女大防观念限制,单身男女多无由相见,而媒妁的职业特质使她可以自由往来于有说亲意向的男女双方家庭之间,“通过媒人,作者可以任意选择两个符合其构思的人物,使他们建立联系,从而使某种偶然性成为必然性”。换言之,没有媒人在小说情节中反复游走于男女双方之间,许多情节片段的精彩程度将会大打折扣,甚至还会失去原本的合理性与流畅性。如《十卺楼》中姚子榖连娶九次都不尽如人意,母舅郭从古提议替其去外地选亲,洞房之夜姚子榖发现所娶新人竟是第一回娶亲的“石女”,出乎读者预料又促成了故事的圆满。《合影楼》中管玉娟不知路公谋划,只当自己无法嫁给珍生,终日郁郁,险寻短见,路公便“把女儿权做红娘,过去传消递息”,才化解一场危机。就这样,媒妁形象的安排使得小说中的人物经历重重考验坎坷,最终都走向了大团圆式的结局。
四、媒妁形象的时代价值
从社会意义上看,《十二楼》中对媒妁形象的刻画展现了明清时期的婚俗状况,为后世评价媒妁提供了多方面角度。
首先,媒妁作为时代的产物,有其特定的社会作用。在“男女授受不亲”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缺乏交往机会,到适婚年龄时由于父母多不了解当地各家婚姻嫁娶情况,就需要每天走东串西的媒妁来帮他们介绍。同时,媒妁也担任着婚姻制度的执行者、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自唐朝始对媒妁做媒便有了法律约束,媒妁不仅要提亲、撮合更要斟酌,如说媒有过失,其自身也会受到惩罚。《大明律》就曾规定“凡嫁娶违律……若媒人知情者,各减犯人罪一等,不知者不坐”。《夺锦楼》中刑尊面对二女嫁四男的案件,不仅传唤当事人双方还要审问“状上有名的媒妁”即是一例,《十卺楼》中姚家发现所娶女子不能生育之时,也首先“把媒人唤来,要究他欺骗之罪”。可见说亲以后媒妁的工作还并没有结束,为这门亲事负责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之所在。
其次,通过对《十二楼》中媒妁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婚恋观的转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婚姻嫁娶的必要条件,媒妁作为封建礼法的需要,代表的是对于婚姻的控制,与私订终身似乎矛盾。但事实上,男女由互生爱慕到私订终身往往无法得到父母认可,这时就需要一位媒妁来帮助他们穿针引线。《十二楼》中的婚恋故事多呈现出男女先私下互通情意再用“媒妁之言”去巧妙改变原本持否定态度的“父母之命”的固定模式:《合影楼》中管屠两家本断绝来往,但屠珍生因与管玉娟隔水相恋便执意要父亲遣人说亲,经过一番波折竟借由路公这个媒人瞒过管父谋得佳人。《夏宜楼》中瞿吉人借由千里镜窥得詹娴娴之姿,一心求娶,但无奈詹娴娴之父囿于门第之见总不应允,故瞿吉人托媒人与詹娴娴来回传言谋划,最终二人得以结亲。虽然作者声称这些小说是为“劝惩”而作,“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但通观全篇可发现李渔一面承认现实的权力秩序,一面袒护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在这些故事中给予私订终身的有情人以充分的理解。
最后,《十二楼》中对媒妁形象的描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媒妁的负面观念,丰富了文学世界中媒妁群体的整体形象。客观而言,媒妁群体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作用”,一方面他们是封建礼制的维护者,往往因酿成爱情悲剧而受人责骂;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因促成良缘而受人赞美。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部分媒妁为逐利而丧失职业操守,文学作品在此背景下多丑化媒妁形象以作为民众心理宣泄的出口。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媒妁不但有时为私情通奸铺路搭桥,甚至为了利益不惜作破坏他人情感的帮凶,凌濛初便曾写道:“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之口……正是富贵随口定,美丑趁心生,再无一句实话。”尽管此种媒妁形象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但单一的负面描写易导致媒妁形象的类型化,也不利于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整体认知。《十二楼》中的媒妁群体虽然部分在做媒中怀有私心,但绝非反面角色,他们多忠于所托,替人谋划,于男女双方间费心劝解,使彼此解开嫌隙或加深感情。这些媒妁造就的多为夫妻恩爱的美好结局,也仿佛是作者对于美好婚姻一种新的寄托。
诚然,媒妁在中国婚姻史上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奔走撮合之间也不乏物化女性的嫌疑。但李渔在《十二楼》的文学世界中,为读者刻画了这样一群媒妁形象:他们秉持着“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的信念为男女姻缘牵线搭桥,凭借能说会道的本事化解男女主人公心中的隔阂,其存在本身也在丰富小说的叙事手法和情节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随着封建礼教的崩溃、男女交往日益公开,不再需要媒妁充当彼此联络的中间人,这类古典式的媒妁形象也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留给读者的只是对这一文学形象颇有意味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