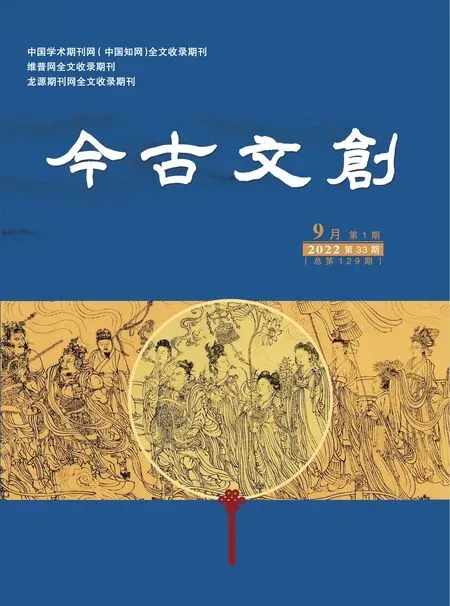“逃避自由” 视角下网络社会交往困境研究
◎于 琦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会交往活动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使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更加平等、范围更加广泛,促进了现代人社会交往的效率。随着网络社交软件的不断普及,也导致网络社会交往困境出现,深切地危害着现代人的网络社会交往。对网络社会交往困境生成机制的探究,不能只停留在表象问题的分析,而要深度挖掘其出现的背后原因。本文通过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心理机制来分析网络社会交往困境的形成,并据此对如何走出网络交往困境做出相关探究。
一、网络社会交往困境的出现
弗洛姆曾指出,当个体从自然中逐渐独立出来时人类的个体化进程便开始了,也只有这种个体化进程的推进才会产生人类的历史,人类才可能从自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由。然而在个体日渐摆脱掉原始的束缚时,同时也逐渐失去来自自然的安全感,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在不断摆脱这种自由带来的孤独,从而发生“逃避自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社会交往是一种满足个体自身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方式。网络社会交往指的是主体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物质、精神交流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介的普及,通过网络进行社会交往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绝大多数的社会交往情况中,主体内心是恐惧交往的。他们会通过逃避与他人交往来摆脱这种社交带给他们的不安感与恐惧感,因此在现代人的社会交往中难免呈现出“逃避社交自由”的倾向。然而网络社交软件的出现似乎解决了现代人逃避交往的难题,互联网仿佛给每个网民披上了安全感的外衣,相比于传统的线下社会交往方式,现代人似乎更倾向于选择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社交,甚至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恐惧症患者”竟可以活跃于各个网络社交平台,网民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更加主动、更加自由。出于对传统交往方式带给人的不安感的逃避和进行社会交往的需要,现代人通常会选择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社会交往,但是随着网络社会交往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它背后的问题也在不断地暴露出来。
互联网在给现代人的社会交往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交往困境。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逃避社交自由”已经发展到“逃避网络社交自由”阶段,例如,包括盲目从众的网络跟风现象和包括有网络暴力、舆论绑架、PUA等行为的网络不文明行为都是网络社会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逃避网络社交自由”的表现。现代人看似利用网络社交摆脱了传统社交带给自己的不安,实则网络社会交往的出现并没有使主体避免走向“逃避自由”,反而将“逃避自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二、网络社会交往困境出现的心理机制分析
弗洛姆指出,在人的个体化进程中,由于对自然束缚的摆脱个体会不断地获得更多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与自然的原始联系所带来的安全感也丢失了,这就是个体化进程带来的两个面相——自由与孤独。一旦个体开始孤独地面对世界时,他们便会通过两种方式来摆脱孤独带给他们的不安感。一是追求积极自由,二是向后退步,放弃自由。在放弃自由的方式中,个体会放弃自己的个体性与完整性,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自由,这显然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路径。社会交往是从动态层面体现社会现象的概念,当前社会交往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能在弗洛姆分析的“逃避自由”的表现形式中找到影子。
网络社交软件的出现使现代人的交往方式更加多样、交往范围更加广阔,个体的社会交往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此同时,网络上的社会交往也不可避免地给现代人带来孤独感,当人们感觉到自己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的渺小与无力时便会开始“逃避网络社交自由”。根据弗洛姆分析的“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三种形式,分析当代网络社会交往中“逃避自由”现象的表现,有利于找到现代人“逃避网络社交自由”的根本原因。
(一)网络社交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指个体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并通过寻求和依靠新的力量来弥补脱离原始枷锁的不安感的倾向。而网络社会交往中的极权主义便是指在网络社交平台上,部分网友放弃自己独立表达和思考的能力,来顺从于某些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的行为,以求在社会交往中处于主流地位的倾向。这类群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不想处于主流群体的对立面而被孤立,因而依赖于网络中有影响力的群体,完全享受被别人支配的感觉,即使主流舆论是错误的他们也视而不见。与此同时,网络上那些有影响力的群体也享受着控制别人的感觉。这是典型的“施虐”和“受虐”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的表现,网络跟风现象就属于此类。在网络社交极权主义中,“施虐”的一方通常控制着舆论的走向,“受虐”的一方则是舆论真正的推波助澜者。“受虐”者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自由,追随于“施虐”者们的脚步,具有明显的依赖他人的特征。而“施虐”者表面是具有话语权的强大的一方,其实他们也是依赖于“受虐”者的,这是因为“施虐”者们只有在控制着他人的时候才是感觉自己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甘愿跟风的网民来帮助网络大V们传播言论和提高热度,这些所谓的网络大V也会变成网络透明人,他们自身也会产生深深的恐惧与不安,从而追随其他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所以可以说,“施虐”与“受虐”双方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在这种网络社会交往中的“施虐”与“受虐”关系中,“受虐”的一方放弃追求自身社交自由的权力,以此来躲避享受社交自由带来的孤独与不安。
(二)网络破坏性社交
破坏性不同于极权主义,它不是“施虐”与“受虐”般的共生关系,而是强调消灭对方,它也源于人们试图从不堪忍受的孤独与不安中解脱出来。网络中的破坏性社交则指网民们感觉到自己在网络中的微不足道,他们认为当消灭掉那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后,自己就可以从这种渺小、无力的感觉中摆脱出来,通常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不需要合理的理由。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网民间的关系到处充满着破坏性,但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破坏行为会被破坏者用爱、责任、道德等字眼来掩盖,网络暴力、舆论绑架、PUA现象都属于此类。在网络社会交往中,施暴者通常都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仇富”“嫉妒”等词可以很贴切的描绘这些网络“键盘侠”的内心,他们借助网络平台来攻击那些看起来比自己更具优越感的网友,试图破坏他们的美好生活,旨在消灭一切让自己感觉到孤独与无助的存在者,当然即使他们摧毁掉整个网络社交世界他们也不会完全地摆脱孤独。
(三)机械式网络社交
机械地自动适应是绝大多数现代人会采用的来逃避孤独的方式,他们顺从于世界的一切变化,不主张自身的个性体现,而完全按照他人的标准要求塑造自己。机械式网络社交指的是在网络中网友社交活动的内容是按照大众的期望去进行的,他们的社交行为就是简单地趋同,与周围人保持一致,绝不做出头鸟。也因为与大家的一致性,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再孤独,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在逃避社交孤独时,丧失了真正的自我和社交自由。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代人接触的网络信息越来越多,众多的“主流思潮”也在主导着网友们的心理变化,大家不自觉地就会追随大众的步伐。例如,追星、追剧、购物等这种看似平常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跟随大众的脚步去关注这一时期的热点就会被看作是落伍的,如果你站在热点的对立面就会被孤立。所以众多网友们在慢慢被网络大环境所同化,会不自觉地去关注热点八卦、追星和大肆购物,变得同网络中的芸芸众生没有任何区别。
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就是网络社交中的“加一”效应,当大多数人都对某一言论或行为持赞同态度时,人们就会不假思索的“加一”,这是典型的放弃主体思考顺从大众的表现。在网络社会交往中,机械式社交是一种最容易被忽视却也是最普遍存在的“逃避社交自由”的形式。
结合弗洛姆所提出的“逃避自由”心理机制来分析网络社会交往中的自由逃避现象生成机制,可以发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逃避社交自由都是出于对自身孤独和无力量的恐惧。这些病态的社交行为方式最终会导致现代人的主体性丧失,人们无法追求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急需走出网络社会交往困境,避免在逃避自由的路上越走越远。
三、弗洛姆自由观与马克思自由观对走出网络社会交往困境的路径启示
在现代社会的网络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逃避自由走向了社交中的极权主义、破坏性以及机械地自动适应。网络社会交往中的困境表明,人们通过逃避社交自由获得的“自由”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而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这种长期的“病态自由”不利于个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健全发展。
针对社会中不健康现象,弗洛姆、马克思各自提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解放的路径。弗洛姆和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自由是必然会实现的,并且他们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以批判异化为出发点关注现实的人的自由问题。同时,他们在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解、人的自由的需要、人的自由实现等方面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我们借以弗洛姆和马克思在对自由实现上理解的不同比较,来进一步分析如何走出现代网络社交困境。
(一)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
弗洛姆虽然承认经济和社会条件对人的社会性格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承认工人阶级在解放人类中的革命性作用,也没有提及要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革。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和解放应该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性,并没有要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设想。因此,弗洛姆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最终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修补。
而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鲜明地指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人的自由问题的解决要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解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对人的异化进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缺陷,这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最终会被更优越的制度——共产主义所替代。因此,马克思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一个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的,可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社会制度。
通过对弗洛姆与马克思在对待资本主义态度上的比较可以得知,弗洛姆的批判是具有空想性的,他的批判中没有看到造成“逃避自由”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我们目前的国际环境仍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与博弈的阶段,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经常会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丑化人民英雄以及贬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错误信息出现,这对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造成恶劣影响,我们要善于辨别这些错误的信息,杜绝盲目跟风,敢于同错误信息和不良言论说不。
(二)实现个人的自由的方式不同
弗洛姆特别强调爱和自发性的活动对人的自由实现的重要作用。这里的爱不仅指简单的情感传达,而且是一种可以克服孤独、实现积极自由的途径。弗洛姆认为,现代人必须要用爱去拯救孤独,这种爱是一种无私的博爱而不是仅限于个人之间的私爱。同时,针对工业化机器大生产造成人的异化的状况,弗洛姆指出人们要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重新唤起人们的创造性和工作热情,从而走出异化,实现人的自由。
马克思则认为实现人类的解放需要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再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每个人的劳动自由,完全消除异化,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两者的实现个人的自由方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弗洛姆对自由实现的解决方式停留在个体的人身上,过于夸大了人自身的力量而没有看到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面对当前的网络社会交往困境,个体的人的思想转变包括舍弃消极社交、进行主动的社交,改变错误的价值观、用爱去与他人进行交往,在社会交往中保持自己的个体性等对构建良好的网络社会交往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仅靠个人层面的改变对网络社会交往大环境的改变是远不够的,因此从制度层面上的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还需要不断加大网络执法的力度,对网络交往中的不文明现象进行整治,将制度建设同个人努力相结合,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三)构建理想社会模式的差异
弗洛姆认为积极自由的实现还需要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来保护人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按照自己内心去从事活动,都能够理性地看待一切事物。整个社会善恶分明,每个人都团结、友爱,并且可以进行自发性的活动。马克思主张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共产主义,即实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社会。虽然两者的社会模式构想都是对资本社会主义的否定,但是“健全的社会”构想并没有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停留在抽象层面。“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具有可实现性的。从这个层面来看,网络社会交往困境解决的根本在于消灭私有制,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会促进个人和群体意识的觉醒,进一步为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做准备。当前我国社会的不断改革就是在为生产力发展服务,只有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有利于网络社会环境的构建,利于网络社会交往困境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