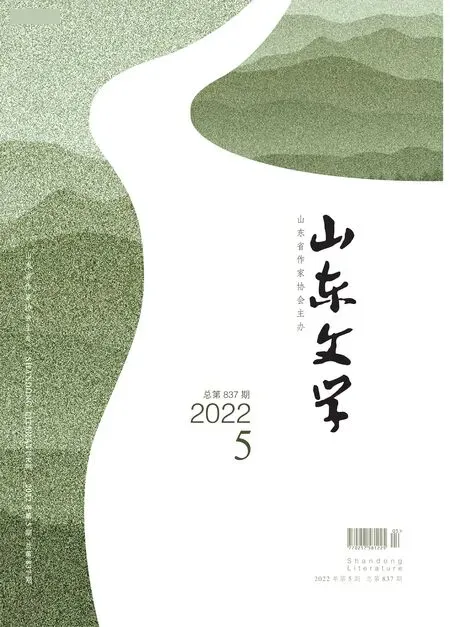画 眉
马碧静
到“南边”去,是他想念两只画眉了。
他在想两只画眉的时候,正将那件白底细黑色条纹的衬衫往旅行背包里装,柔软的质感、若有若无的茉莉花洗衣液清香。这件已经穿了五年的衬衫是“南边”的她买的,是她第一次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喜欢看你穿衬衫的样子,帅帅的……”她眼睛闭上,又瞬间睁开,翘着红唇,娇嗲地给了他一个飞吻。她习惯用力闭一下眼睛再猛地张开,这一闭一张之间,一种特别的神采便在她的眼波间流转,每每忆起,他仍有心动的感觉。
他那两只画眉,一雄一雌,长得很像,上体橄榄黄,头顶至上背呈棕褐色,并具浅黑色纵纹,雄的比雌的更深一个色号。眼圈像京剧脸谱画了一圈纯白,并沿上缘精致地描画出一细长的窄纹,向后延伸至枕侧,形成清晰好看的眉纹,想来“画眉”由此而来。要说真有不同,便是那只雌的虹膜呈落日时的橙黄,雄的却是极为罕见的湛蓝色,像倒映一片蓝天。
他将手窝在衬衫的质感里。这是件“自由鸟”,他最喜欢的品牌。不只设计感强、灵动、优雅、柔软亲肤,还因为喜欢这个名字:自由鸟。一听到这名字,他就能想象一只鸟儿自由地翱翔在天空。
与肌肤相亲了五年,磨损、汗渍油渍、日晒雨淋,使它更加绵软,领条那个位置,颜色要比其他部位的浅一点,那是妻子洗得过勤了。他告诉她这衬衫是自己买的,她信了。
回头想想,妻子似乎一直都相信他?只是,在她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当她倚在床头,一次次定定地看他良久,带着犹疑与凄怨,像要把他的魂魄摄入眼底时,他就会忍不住地回忆、分析、猜测有可能露出的蛛丝马迹:她知道多少?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他还是想念那两只画眉。
那是两只千狮山上的画眉,来历却富戏剧性。是和“南边”的她去满贤林千狮山看狮子,据说那里雕塑了三千多只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狮子,集中展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石雕狮子的艺术风格。上了千台坡她就不肯走了,耍赖地靠着石牌坊,蹬直了腿喊累,说要歇一会儿。
画眉是在千狮壁遇上的,千狮壁雕于临渊山崖,不能近前,日久年深很多狮子已被青苔大面积覆盖,愣神间,两双翅膀“扑棱棱”先后扇过他眼前,强大的气流使他闭上眼睛。鸟儿落在他肩上几乎是无声的,尖细的小爪却深深抠在他隔着T恤的肩肉上,一边一只,他心跳着,缓缓转头看,那精细描画出的纯白眼线表明它们是一对画眉,雄的胸脯纵纹黑一些,雌的浅一些,鸟儿跗跖和趾呈甜蜜的焦糖色。
“北边”的千秋万代公墓园也有画眉,起初他并不知道。送亡妻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过得昏昏沉沉。好在她娘家姊妹多,除了掏腰包,具体的事情她们都呼前喊后操持着办。有时他也自嘲地想,这倒为他省了不少精力。他害怕与人之间的相互应付,这方面他是极不擅长的。当初媒人来说亲,父母也是看中了妻子强悍能干、大包大揽的性情才像捡了个宝似的帮他应承下来。那一年,他读大四,学的是桥梁工程。
上山那一天是阴雨天气,其实离清明节还有一个月,雨水来得早了点。淅淅沥沥,如泣如诉,下起来就没个完。好在有殡葬公司的一条龙服务:接运遗体、预约火化炉和告别厅、遗体告别流程……都有公司在有条不紊地操办,他倒更像个闲人。
殡仪馆偌大的告别厅,抛光砖反着能够照清人脸的釉光。工作人员忙着布置灵堂,几十只黄白相间的大花圈,多半是妻子那边亲朋送过来的,他们更讲究排场,希望风风光光送她一程。他只有一个姐姐,在他刚上大学那年就远嫁沿海了,几年也难得回来一趟。朋友嘛,他少得可怜,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小姨妹们将妻子的遗像摆上灵堂时,他还是感觉到了极大的不舒服。那对内双的眼睛看着他,就像活着时那样,离得近,他看到辐射状的虹膜死死盯紧他,像要将他的魂摄走……她们在角落烧纸,黄黄白白的纸,被火舌舔一下,回光返照“腾”地蹿起老高,压抑的纸灰味附着在他的鼻黏膜,他感到呼吸困难,浑身发冷。
不知怎么出的门,沿着上公墓的小道行走,没打伞,雨丝在风向的怂恿下贴合着他的脸,他的额头,很快集结成小溪,肆意在他脸颊和脖颈横流。镜片上都是雾气,他没抹去蒙蔽眼睛的雨水,只是埋头不断往上攀爬,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或许就在他埋头穿梭于一排排袖珍的墓碑间时停止的。“这才几年,就发展成这么大的规模。”埋头爬山时,他模糊地想,却没勇气看一看那些男女老少的相片。
在他攀到公墓缓坡尽头时,两只画眉自小叶黄杨灌木丛中蹿了出来,翻飞嬉戏于其间,啼叫响亮悦耳。后来他有一闪念的恍惚:“北边”墓地这两只画眉,会不会就是“南边”与他投缘那两只?它们是那么相似,橄榄黄的上体,京剧脸谱般纯白色的眼圈,雌的眼底是落日的橙黄,雄的倒映了天空的一抹湛蓝……可是两地相隔千山万水,画眉也不是擅长远飞的候鸟。最关键的是,那两只画眉,应该正在笼子里。
柔顺的齐耳短发,白皙到毫无血色的肤色,黑眼珠比一般孩子要黑几个色比,身高却比一般孩子要矮一大截。在他从小区超市出来时,这孩子正乐颠颠地朝里跑,差不多是擦着他的身子而过,淡淡的薄荷糖甜香,他瞥见她儿童口罩里的小嘴鼓鼓的,他本能地往边儿上一闪,低头将口罩往上紧了紧。
她没看到他?或是没认出他来。他情愿是这样子,算起来,她该有八岁了吧?他却始终无法自然地面对她,有时是羞赧,有时是愧疚,更多的时候是陌生,他常常会偷偷观察她的侧脸,将她的五官与自己的“合并同类项”,这很像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小游戏,带着点儿企盼,也带着点儿不怀好意与小伤感,有瞬间的窃喜,也有漫长的疑惑。
像之前的每一次,他迅速转进那幢楼,他要赶在小纤从超市出来之前坐到家里的沙发上。她不在家里,这个时候,应该在麻将桌上交战正酣。她的一个闺蜜偷偷告诉过他,她作为母亲的失职:不接送孩子上下学、不给孩子做饭、点外卖给孩子是常态、半夜三更才归家、打起孩子来狠……他默默地听着,不插一句嘴。闺蜜四十岁了,还单着。闺蜜喜欢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他聊天,他曾经问过:他这么闷的人,为什么找他?一向开朗的人,沉默了半晌,敲过来几个字:寂寞呗,知道有个人在听就行。
开门进来他就听见鸟叫声了,一低一高、一长一短,两只鸟笼挂在窗前,他近前观看,画眉像是认识他的,笼内跳跃更欢了。他查看了鸟食、饮水和保健砂,清洁而富有条理。他猜这些都是小纤在打理,小纤像是天生就有饲养画眉的异秉。原本这些他只是了解到点皮毛,毕竟从未养过鸟。后来他才知道,画眉其实是最难驯服的一种笼鸟,与百灵、绣眼、点颏并列为中国四大名鸟。早在宋代就有饲养史,到清代基本已发展到千家万户有鸟的规模。
这让他对拥有两只画眉的经过总抱有一种奇特的向往。仿佛在一个多维的看不见的世界里,有决定他命运的神,做出了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决定,通过一种迹象,给予他启示。北方的冬天奇寒,小时候他是个“鼻涕虫”,有个长他几岁的男孩盯准了他,高兴不高兴了都拿他来耍。一个大雪天,那男孩把他侧摁在雪地上半小时,害他差点冻掉了耳朵;还有一次,把他硬塞进半平米大小的砖石鸡厩里,鸡粪的臭味差不多让他窒息。狭窄闭塞空间造成的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了成年,最初乘坐电梯时,他都适应了好长时间……他不敢把被他人欺负的事告诉父母,自己“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报复方式:臆想大男孩倒霉。他几乎臆想出一百种让大男孩“倒霉”的场景:走路掉进水坑淹死、放羊滚下山坡摔死、吃泡馍噎死、被更大的坏孩子围殴致死……
午饭他给小纤做了羊肉泡馍,北边带过来的。小纤挑两筷头,又仰脸看看他,多数时候他就装作没发现,要与一双纯净的眼睛对视,他还是缺乏勇气。他俩安静地吃饭,除了简短地交流。
“爸爸,喝杯橙汁吧。”
“爸爸,这是我上学期获得的奖状。”
“爸爸,我们让蓝子和橙子洗澡吧……”蓝子和橙子,是小纤给两只画眉取的名字。
小纤打来两盆适中的水,将鸟笼放在水盆上,拽着他的手躲到一边儿,不一会儿,两只画眉便跳进水里自行梳洗了起来,自然而欢快。再听叫声,这一连串叫开花的声音,代表就是养得好。听她说,都是小纤在养在管,两年前她才六岁?他对这孩子充满了好奇。
“开始也挺费劲……”小纤嘟着湿润的粉唇:“我就准备了一只洗澡笼,罩上笼衣,将笼子与洗澡笼门对门,洗澡笼放在光线畅亮的阳台。画眉趋光,驯养一段时间后雄鸟先过去了。”
“喔,过笼,雌鸟呢?”
“雌鸟更清高点,后来我又去‘爱鸟网’请教,那些大佬传授了秘诀……”小纤掩住嘴巴笑,笑声在掌心里左突右冲,带着孩子获胜后特有的小骄傲。她就不会这么笑,她的牙齿洁白整齐,笑起来张扬动静大,迎光两排白牙闪闪发亮。
画眉洗完澡了,小纤轻车熟路地拎起笼子,挂在向阳处,让它们自然晒干。洗完澡的画眉鸣叫欢畅婉转,水头足,鸟性好,这些让他心头大喜,暗暗将功劳都归于小纤。
雨停了,天空低而阴沉。
四周静谧,两只画眉已不知飞向何处。居高临下,大片整齐林立的铅灰,目光放远,殡仪馆默然。他将目光投向西南方向的那个屋子,在他上来之前,入殓师正给妻子美容化妆。他不知道需要多久。记得几年前,他看过一个使他动容的片子:日本导演泷田洋二郎的《入殓师》,该片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低沉浑厚的大提琴响起,鸟群在天空中低飞,父亲手中的鹅卵石,鲜活又归于沉寂的生命……他突然有点烦躁,皱眉抬腕看表,他希望这个事情能早点结束。
手机适时地响了起来,是最小的小姨妹,声音咋咋呼呼:“ 姐夫你在哪儿?快开始了……”
戴白花黑纱、行默哀礼奏哀乐、三鞠躬、介绍生平、遗体告别……仪式尚未开始前,亲朋同事都一一进来给妻子上香、行礼,他站在一边回礼,一次次地弯腰鞠躬,片刻便腰酸背痛,他是有颈椎病的,年久日深了。一边回礼,他暗自想,为妻子做的这一点点事,会不会多少抵消一点他的愧疚?
两个儿子是妻子被推进火化炉时前后脚赶到的。作为桥梁工程师,他在全国各地修筑高架桥的二十多年间,妻子为他培养了两个名牌大学生,如今两个儿子均在比故乡更大的城市安家立业。妻子在确诊前,时好时坏已一年,他曾经平和地跟两个儿子表过态:“你们该上班上班,该生活生活……到时我会给你们电话。能赶上最好,赶不上也没关系……”妻子在时,儿子就是她生命中最大的骄傲,当然,也是与他争吵时讥讽他的长矛。火化炉前,他伫立不动,思绪像风筝不知飘向何处。大儿子将手搭在他的肩头,安抚式地捏了捏。大儿子的手劲轻重适中,与他的为人处世态度一样,永远不温不火。小儿子抱着胳膊站在一边,眉头轻锁,不知在想什么,小儿子的性格更像妻子。
取灰了,并不是他在影视片里看到的细细的白灰,而是夹杂了一些烟灰色块状的骨头。工人师傅告诉他:病人火化后大都是这样子。他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成人骨灰平均重量约为2.4kg,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入葬倒快一点。每当他想到快与慢的问题时,还是忍不住自责,二十几年的夫妻,他陪在妻子身边的时间可能不足十年,送她最后一程时,居然如此没耐心。
然而对自己不满的情绪只是一瞬间的闪现,无论如何,他仍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快一点过去。就像一只无形中将他的头往下强摁的手,只有等这只手松了劲,他才能喘得上一口气。下山时,原本停歇了几个小时的雨水又不屈不挠地洒了起来,天空依旧压得很低很沉。他一门心思往山下走,偶抬眼看看围绕在这片铅灰石林边的各种植物:香樟、水杉、国槐、圆柏、广玉兰、桂花……不必说,风景是美好的,想来长眠于此的人也不寂寞,这让他多少有点欣慰,像是生活亏欠他的,又给他补回来一点。石板铺就的小径两旁长满了牛筋草,这是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禾本科草本植物,幼年时,小伙伴们常扯来喂牛羊,催膘。这种草的花序为穗状,几枝花穗自主茎上放射性生长,此时沾满了剔透的水珠,草棵打湿了他的裤脚和鞋袜,他也不在意。他下山的姿势有点奇怪,身体倾斜,左肩高右肩低,就像一个逆风而行的人,在用左肩膀试探风向,大儿子追上他,将雨伞撑在他头顶时,他并未马上发觉,只以为雨停了,抬头才看到那把墨蓝色的雨伞。
此时他又听到画眉的鸣叫了,这让他想到千狮山那两只奇怪的画眉。
千狮山的画眉一直跟着他下山,有时肆无忌惮地站立他肩头,有时上下翻飞着低空嬉戏,有时就躲进灌木丛,在他听不到画眉的鸣叫,以为它们已经飞远,心下莫名空落时,它们又神奇地出现了。就这样走走停停,抱着点儿模糊的期待,竟一路走到了石牌坊。他听到了对谈声,在旁边的杉树林里,多了一个卖鸟人,那人一顶草帽压得很低,看不清面目。卖鸟人看到他肩头的画眉,“喔”了一声,吹着口哨逗画眉,像囊中取物一样,轻易就将画眉从他肩头取了下来。
“这像是去年‘家去’的两只画眉。”卖鸟人的用词同样令他惊奇,倒像是从古代穿越来的人。只是他暗自琢磨,卖鸟人指的是鸟的家,是他的家?还是天地间这个广阔的家?
下千台坡时,他不住地回头看,卖鸟人重又盘腿坐在了树根底下,居然掏出手机刷了起来,这一刻,他又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人。他有点恍惚。在他旁边的水杉树丫杈上,挂满了鸟笼。只有一笼有鸟,其他都是空笼。说不清他是卖鸟还是卖笼。起初他以为卖鸟人卖的鸟都是从千狮山上捕捉而来,结果却令他惊叹。
“愚从不强迫鸟儿,只带粮食和虫子来……若一日,缘尽,鸟去……”
“比如这一对……”卖鸟人咬定了这一对画眉,就是去年自己放掉的那一对,他将两只画眉分别请进鸟笼,关好笼门。鸟儿很服笼,根本没有一点生鸟的抗拒。他一左一右拎着两个鸟笼下千台坡,她不愿帮忙,说是自身难保,管不了鸟的事。对于他养画眉的行为,她不置可否。
“画眉地盘性很强,一雌一雄也万不可同笼,谨防养废了。”卖鸟人说养废了的意思就是失了“鸟性”,那时他才知道,人讲“人性”,鸟讲“鸟性”。
后来他又去过两次千狮山,却再没见过卖鸟人。
终归是孩子,他和她说话的当口,吃过晚饭的小纤又将他在超市买的零食袋口打开来,找出她最爱吃的华夫饼。每次过来,他都不知道买点什么好,后来觉得还是买零食好,孩子爱吃的他都知道,不会买错了,而且方便。
“这次要待几天?又哄她在云南架桥吗?”她斜躺在贵妃榻上,飞着眼“哧哧哧”地笑,高高的颧骨上两块显眼的高原红,一双媚态十足的大眼睛在高原红的映衬下汪满了水,他有点发怔,回忆起了头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九年前吧,那次是真的在这边架桥,惯常出去“放松”,是的,这对他并不是第一次,二十来年的全国各地风里雨里跑,聚少离多的寂寞与需求……他后来反复确认,自己就是被她那两块颧骨上显眼的高原红打动的,那两块像玫瑰一样盛开的激情燃烧的红,一直烧到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情感世界里。
“我有家庭……”
“我不在乎,也不想结婚……”
“啊?”
“只想和你有个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
她将一双脚揣进他怀里,孩子背对着他们看动画片,很入神。她的脚不安分起来,他没动,她立身突然掏了一把,带着股狠劲,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挑逗。他朝孩子的方向努努嘴,装作给保温杯续水,其实杯子还是满的。
是十一“黄金周”,他待了一个礼拜,走时他告诉孩子:“爸爸等你放寒假了再来,带你去动物园看猴子。”难得的小长假,太早了,孩子还没起床。他站在孩子房间前良久,最后还是轻叩了下房门,贴着门缝说了这句话,小纤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不知道回答了什么。
她倚在门边送他,穿着肉色的睡衣,叉着腿,身体在睡衣里影影绰绰。他推推眼镜,透过镜片望着她,她迷离的大眼睛布满血丝,嘟嘴挑逗地对他飞吻,想到这几晚上的折腾,他有点难为情。
“走了。”他又抬手推了下眼镜,嘴角上扬,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却没有真正微笑。
“好,再来,慢走不送。”她眨着眼也笑着,奚落的语气,显得很潇洒很无所谓,仿佛他只是一个旅客。当飞机不断朝空中攀升,失重感袭来,他闭上眼睛,想起她半开玩笑的话:“说好了啊,要是她走了……我可就要登堂入室了哦……这么多年了,副室也有‘扶正’的一天啊……”
他心下一凛,明白这才是她最真实的想法。
可是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他还是想到了两年前,带画眉下山的那个下午,小姨妹打电话来,他将一只鸟笼递到她手里,她撇着嘴,边无所谓地踢着小石子,边侧耳倾听。小姨妹在电话里低低抽泣,声音有点难以自控。妻子确诊了,宫颈癌晚期。
挂了电话,她审问的眼神适时地探过来,他镇定自若,只说家里老人生病了,让他立马赶回去。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天衣无缝,包括后来她有意无意的玩笑“如果她先走了……”的话,他都当成是因为妻子大他六岁的缘故。只是现在他恍然醒悟:或许并不是。
“这些年,你就是个‘甩手爸’,我一个人带娃……”
“也该补偿补偿我了吧……”
这些话总让他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一种重新将他安排人生的被动感。
当初完全不是这样的。生小纤时他在京都的一个工地上,国家立项的桥梁大工程,他在网络平台上请了月嫂,还托付她的闺蜜多照顾。闺蜜发了条语音:“你要怎么谢我呢?”声音娇嗔得让人头皮发麻,这让他想到,往常趁她不注意时,闺蜜眼睛里热辣辣向他牵过来的那根丝。“给你包个红包吧……”他发了红包,闺蜜毫不客气地收了。这些他都瞒着她,孩子五个月了他才瞅了个空过来,无意中提到她闺蜜,她打着慵懒的哈欠不在意地说,拢共也就过来两三次,天天忙着打麻将嘛。孩子浓密的黑发、白皙的皮肤像他,脸型也像他。只是很瘦小,弱弱的像根小瓜秧。
“叫她什么?”他突然问,压抑着心底一阵阵往上泛的温情。
“小纤啊,李小纤,还是你自己取的名字。”她瞪大眼睛,像芭比娃娃一样使劲闭眼睁眼,有点嗔怪他的意思。想起来了,产后她给孩子拍了照片给他,端详着屏幕上粉嘟嘟的小可人儿,他说“就叫小纤吧”。
“嗯,小纤,李小纤……”他喃喃着,在睡熟的孩子粉颊上啄了啄,将孩子递给她,开始打扫卫生。他嘴上没哼歌,心里却哼唱起一首欣快的歌。他挽袖忙活着,洗衣服、抹家具、扫地拖地,茶几脚边有几个瓜子壳,他弯腰扫出来,发现一张火柴盒大小反扣的照片。是她和一个圆脸阔口男人的结婚证件照,他心头有点泛酸,知道这是和她“办假证”的男人,为了帮小纤落户。当初他揣摩着她电话里的口气:无奈?抱怨?抑或夹带着点隐隐的报复?他品不出来。他从微信上给她转了一万,生活费也从五千提到了八千,钱财上,他对她从未吝啬过。
飞机颠簸了一阵,穿过棉花一样的云层,开始平稳下行,空姐甜美的声音响起,从舷窗俯瞰他的城市,这个号称“六朝古都”的城市灯火阑珊,他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关上门,屋里一片沉寂,他长长舒出一口气,感觉又将一个秘密关在了门内。妻子的遗像他只挂了一个月就收起来了,照片总给他如芒在刺的不适感,那双像在石板上刀凿斧刻出的眼睛、那刚毅的可以主宰一切的神情……
“小李,不是我说你,你这事欠缺考虑……”
“小李,遇事多用脑子,你呀……还是不够成熟……”
“小李,孩子的志愿我让填报了,大儿工商管理,小儿法律,吃香啊……不好意思呀,没和你商量……”她往他碗里夹了块糖醋排骨,脸上露出配合着她语气的“不好意思”,他却从她眼里捕捉到了一缕得意。
他没开腔,只是冷冷地想:你“不好意思”的事还少吗?又何差这一件呢?
当晚小儿子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次日眼睛都是红肿的,小儿子喜欢画画,这个冷门的专业在妻子眼里就是不入流,就是没前途。后来他知道,之前小儿子为这事和妻子闹得天翻地覆,最终这场战役还是妻子大获全胜。大儿子虽然也无奈放弃了自己的所爱专业,却能不动声色地隐忍,这点很像他。然而,后来却悄悄娶了个她反对的外地姑娘,从此一年也难得回来几趟,这点,似乎也像他?这让他每每想起来,总有快感与忐忑同时袭来。
现在,偌大的一个家,空荡荡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每回从工地上回来,关上门,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他也与外面那个世界无关。该出门了,背包一打,带走的就是他的一个家,以及所有的情感与牵挂。他开始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日子、静谧得只剩下钟摆机械地“达达”赶路的日子。他可以冲杯咖啡,安静地窝在沙发里看书,不会有人嫌弃他风里来雨里去捂出来的脚气;可以一日三餐只吃老米家的羊肉泡馍,没人会唠叨他饮食单一不营养;更没人会用一副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吻对他说:小李,你还不够成熟……
有时一闪念,他也曾有过这样的幻想:工地上忙累了几个月,开门就有人递热茶盛热饭,那个皮肤白皙眼珠灵动的小女孩围着他说:“爸爸,我们给橙子和蓝子洗澡吧……”
可是,他真的了解她吗?哪怕是熟悉她吗?连那个喊自己“爸爸”的小女孩,他也总有一种拘束的陌生感……
只是想想,他仍有一阵后怕,怕这些幻想,在他的一不留神之下就变为了现实。
“小时候家里穷,六七岁就跟着大人赶街子卖菜、割牛草、上山背柴……苦怕了。”她说着话,将一口烟子缓缓喷到他脸上,他在迷蒙的烟雾中,捕捉到她那只翘起来夹着女士薄荷香烟的手,那关节明显粗大,她应该没说谎。
“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我在这边生活,你想来了,就来看看我们……”她嘟起嘴,她的嘴唇肥厚,即便不擦口红,也有着暗红色唇纹。
“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平常打打麻将……孩子长大成人了,我也有了依靠……”他信以为真,帮她过上了理想的生活,他没深想的是:理想是会改变的,更何况,他能断定她一开始说的就是真话?
时间过得很慢,比如一天何其漫长。也过得很快,比如一个月、一年、十年。一个人的世界,东西南北飞一圈儿,一年就到头了。
“爸爸,放寒假了,你说过带我去动物园。”电话线那头,孩子的声音怯怯的。他想起,有时过去,想尽下做父亲的责任送送孩子,孩子也不肯把硕大的书包给他。小纤自己背着书包,用棉签摁电梯键,戴着口罩的上方,浓密而黑亮的刘海下,露出一双鸽子一样安静的眼睛。出了电梯,她带头走在前面,却不忘用余光瞟一眼他,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以便他追得上她。
“好的……等爸爸把手头的事忙完了,就马上来……”他浇着花水,若有所思,目光穿过城市空茫茫的上空,望向南方的远山,万重山的背后,一个三线小城市,有他的另一个“家”。其实工地的事提早一个礼拜完成了,接下来要转战西南方向,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家里休整。他迟迟不动身的原因,连自己也不愿深究。
“爸爸,你快来……橙子和蓝子养坏了……它俩撞笼……两天了……”
急火火赶上当晚的航班,一路马不停蹄向着彩云之南,恨不能立马飞到两只画眉面前,看看它俩是怎么回事。然而,他没想到,一场暴风雨正在等着他……
“你到底什么意思?两年,她整整死了两年,你不告诉我……”她叉着腰,一下下点着头,像是和他算总账,全然没有和他撒娇时令他心动的神情,这让他觉得陌生。
“真害怕我们娘俩儿赖上你吗?”她气愤难消,丰满的胸部剧烈起浮着,胸前彩色的圆形图案似要把他漩进深渊……他闭上眼睛。“砰、砰、砰”,两只画眉在撞笼,橙子羽翅耷拉,眼神绝望,笼里散乱着绒毛,蓝子已撞得头破血流,那抹湛蓝的眼底写满焦躁与不安,他实在不知道,这两只乖巧的鸟儿到底怎么了?受到了什么惊吓?有什么东西令它们变成这样?
“说话呀,你哑巴了?”她不依不饶,一副追问到底的架势。
他睁开眼,一片茫然。他模糊地想:她是怎么知道的?是的,远隔千山万水,他们之间也没有共同的熟人,除了她那个四十了仍单着的闺蜜。
“来,咱俩干一杯……”手机视频连线里,他和闺蜜各自摆了一桌子啤酒,开始对饮。一来二去,两人都高了。她说要表演一段“脱衣舞”,他大笑,心想:一个偏肥的女人,跳起舞来会是什么样子?他很快被自己脑补出的画面给逗乐了,臆想中,他给她加上了黑色蕾丝袜和假尾翼,跳起来就好像一只黑天鹅。
他红着眼圈白着脸狂笑,他一喝酒脸色就死白,医学上说身体缺少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会加重肝脏负担。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他多开心啊,他很少这么放肆地狂笑。似乎从童年开始就这样,小心着、抑郁着、沉默着,被打压着、被误解着、被轻视着……她说到做到,居然真在那边跳起了脱衣舞,事实是:他马上发现自己错了,她不仅跳得有模有样,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霸气侧漏。那晚他们边喝边聊,醉了醒,醒了醉,直到凌晨三点,他记得说过好多话,亡妻的事有没说过?记不清了,或许没说,或许说了就忘了。
两只画眉在笼子里扑腾,叫声凄楚、哀婉,给人一种气息奄奄,垂死挣扎的揪心与焦虑,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如果不马上去放飞,两只画眉可能会自己撞死。就如当初画眉主动跟着他,到现在以决绝的提示要求回去,他突然想到,千狮山上装腔作势的卖鸟人所说的“家去”。
“我先去放画眉,回来会给你个说法……”他听到自己说。拎着笼子,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到她说:“我会等你回来,把我们的事好好说清楚。”他转头张了张嘴,像要打个呵欠,也似乎想说什么,然而一个音节也发不出来,最后只是推了推眼镜。
他拉开门,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千狮山上人迹寥寥,爬千台坡的时候,他才明显感觉脚力不逮,回头想想,是啊,已经是四十九岁的人了。这吃人的时间啊。
爬尽千台坡,仰天长望,藏蓝色的天空不染纤尘,如明镜高悬,他突然想起一句佛家偈语:万物于镜中空相,终诸相无相。
他抱着一点隐约的希望,想要再见一见卖鸟人,再听一听他那故意哗众取宠的“古文”,但石牌坊附近并没有卖鸟人,也没有那一排排挂在水杉树杈上的红酸枝鸟笼。鸟儿性灵,橙子和蓝子知道来到了生于此长于此的千狮山,都停止了扑笼,转着灵动的头颅倾听,听到野鸟的鸣叫,便争相积极回应着,满山回荡着一场盛大的鸟鸣交响乐,他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他拎着画眉,爬坡上坎,走过年深日久颤巍巍的迎仙桥,忽见一面巨崖挡住去路,仰面看,上书“一窍通灵”几个大字。细观,巨石如象鼻,静听,内里涧水潺潺。旁有把门金刚,并刻有剑川名士赵藩题联:天工错,人巧极;风云涌,路径绝。他立地定了定神,想此处已无路。此刻,所有鸟儿都停止了啼鸣,风声、水声都离他远去,山林静谧,只听得到他被无限放大的呼吸声。少顷,他转变方向,终寻到一处小径,一直攀爬到山巅。艳阳高照,眯着眼睛,他看到一串串七彩光圈从高悬的太阳处连接到山巅,像搭建了一道天桥。千里苍翠连波、万里林涛起伏,风儿鼓起了他的衬衫,顿有袖管处化羽、双脚腾空的奇妙错觉……他打开鸟笼,两只画眉跳至笼门处,焦糖色的趾犹疑着,前后跳动几次,终于,“哧溜”一声,蹿出笼门,直啸蓝天。
观景台那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正在用望远镜观景,一眨眼的工夫,小姑娘兴奋地对旁边的男人说:“呀,爸爸,我看到了三只画眉鸟……”
“你怎么知道是画眉鸟呢?”
“我在《动物世界》里看过的呀。”
“哦,那你说说。”
“画眉鸟画着白色的眼圈和眼线,很灵敏,也极富个性。”
“嗯,不错。”
“它可以是唱鸟,也可以是斗鸟。”
“对。”
“可以是笼鸟,也可以是野鸟。”
男人摸摸小姑娘的头,表示鼓励。
“哇,爸爸,它们飞得好自由,我也好想有一双像它们一样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