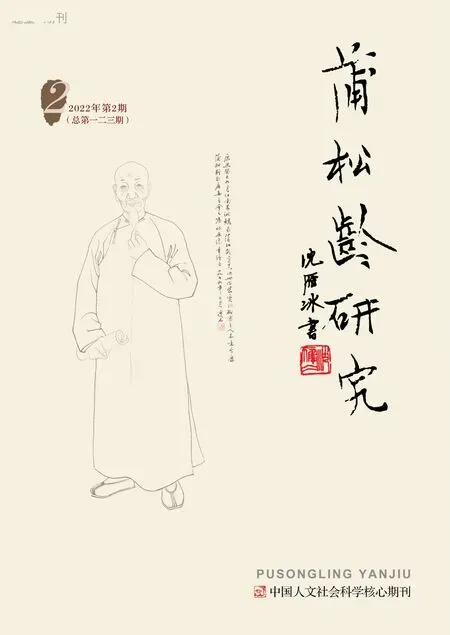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三)
王潇萱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译者按
宋贤德教授在本卷共迻译出82篇聊斋故事,其中大部分与科举题材有关,其在序言中提及《冷生》《画马》《褚生》《司文郎》《沂水秀才》《钟生》等。透过这些作品,宋贤德发现,蒲松龄在聊斋故事中隐秘地回应了自己屡试未第的科考经历,并展现出自己对于科举制的真实态度及深度思考。蒲松龄反对科举考试对儒家思想学习和实践之间的割裂,认为科考进阶并不意味着成为“儒家价值模范”,相反,很多儒生并未完成儒家价值观的内在转化,这也造成种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背离了儒家思想本身。作者指出,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使儒生真正掌握并践行自己的儒家理想,而使其变成了一种谋求向上阶级的工具。因此,蒲松龄猛烈抨击这种现象并倡导思与行的紧密结合。最后,作者借助蒲松龄聊斋故事中深度阐发的“孝”这一核心概念,见微知著,以此诠释蒲松龄眼中儒家思想的推行和实现,从而揭示出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宋贤德教授关注到蒲松龄故事中除狐妖、志怪题材外的另一重要题材,从文本细读出发,研究聊斋故事背后所展现出的社会制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可知,海外汉学家不仅关注《聊斋志异》的故事性问题,还考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层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贤德教授并未局限于《聊斋志异》的讽刺价值,而是深入考察作者身份、儒家思想、社会制度等多方因素,深度探求其背后的隐藏涵义。可以看到西方学者的研究正逐渐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开始关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具体问题。宋贤德教授的译介工作拓宽了西方学界对聊斋故事的认知视域,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异质文化下的研究视角,促进国内外聊斋研究的纵深发展。
宋贤德教授《聊斋志异》全英译本第四卷第一篇序言翻译如下:
奇闻异事中隐含的儒家思想与社会进阶:蒲松龄笔下价值观和科举制的分离
从香港屏山社区的“汤家学堂”(the Tang examination study halls),到孔子齐鲁故里山东曲阜的“仲尼燕居堂”(the study center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今天仍存有大量物质遗产昭示着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科举制建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它通过考察士子的学识来确定个人是否有资格担任官职,而非根据他们先有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进行分配。它构想设立一个学术精英管理体制,但不可避免地像其他任何一个官僚体制一样变得僵化而教条(而且往往是腐败的)。年仅5岁的幼童在开蒙后,经由塾师指导背诵儒家经典及各家注疏。这些核心的经文包括相传由孔子亲自编订的“五经”(《周易》《诗经》《礼记》《尚书》《春秋》),以及“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经过这样的训练,儒生们开始依次准备参加童生试、乡试和会试,每次考试的难度都比之前更上一个层级。在八股取士开始时,考生会拿到一个取自儒家经典的短句,考生必须依此阐发议论,以成文章,试题涉及“经、史、时务、诗赋的问题”。蒲松龄(1640-1715)透过《聊斋志异》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自己屡试未第的科考经历,他赞颂那些蔑视考试规则但仍然能在精神上超脱的儒生。就像在《冷生》一篇中,乡试学使发现绰号为“笑生”的冷生在考场上哗然大笑。虽其文超拔可诵,但考官仍黜其名。事实上,在十项可能会取消考试资格的违规行为中,有两项就是在考试期间说话或者哼唱。但考生在诗赋考试时会不自觉地这样做,同时考虑诗赋的格律。
早慧的男童通常会面临来自家族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在学习中出类拔萃并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因为这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家族可能获得物质成功的少数途径之一。例如,在《画马》一篇中“家屡贫”的崔家,就是寄希望于一个有才华的儿子来摆脱贫困的典型。这给那些在备考期间未得任何宗族资助的士子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比如在《褚生》一篇中,家境清贫的褚生惜寸金之阴,攻苦讲求,未敢暇息,“加以夜半,则我之二日,可当人三日”。尽管如此,褚生还是穷苦潦倒难以为继,他只能通过制造和贩卖用苘麻和硫磺制成的火具赚得薄薪,以遗塾师。后来,曾得褚生帮助的陈生心生疑虑,方悟其为鬼魂,显然是他在刻苦求学的过程中不幸离世。蒲松龄在文末大赞:“褚生者,未以身报师,先以魂报友,其志其行,可贯日月,岂以其鬼故奇之与!”
蒲松龄经常在文中建立联系,将故事中的“奇异”成分与他笔下学者人物身上儒学价值的正面典范相结合,这显然是因为他并不认为儒家经典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应该有所区别。无论是为了保护普通人的利益还是练达地与神鬼交往,皆是如此。例如在《尚书·洪范》中就体现了这种平和的心态和一致的反应,它概述为五个方面的行为:“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从作谋,睿作圣。”在蒲松龄笔下《司文郎》一篇中,宋生和王生向倨傲无礼的余杭生发起挑战,他们根据《论语》命题进行八股比试。这位余杭生必然失败,因为他还没能完成儒家经典中价值涵义的内在转化。之后,一瞽僧焚其文,并从散发的烟雾中神秘嗅闻,以此来评判文章优劣,他发现余杭生写的文章燃烧时所散发的气味简直腐臭难闻。
儒家典籍中的经验教训和蒲松龄故事中的经验教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显然是作者的构思与设计。最终目的或是为了证明自己对经典的研究程度,或是通过特殊的叙述形式来阐释他认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哲学内涵。孔子在《论语》中曾教导他的弟子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八大王》一篇中,冯生只是稍稍改变了这一点,他对耽于饮酒的八大王发问:“既自知之,何勿改之?”儒家认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会不断反思并重塑他(她)的整体生活,并且“凭借这样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准确评估并重新定义他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也许是为了鼓励积极的改变,蒲松龄似乎更喜欢在他的故事中明确而直接地阐明思与行的关系,有时甚至会直接借鉴儒家经典中的人物和义旨。以子路为例,他是孔子的心腹肱股,总是成为孔子批评(因为他行事草率)或赞扬(因为他为人忠义)的对象。《论语》记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蒲松龄在《鬼令》一篇中就着重强调了子路粗暴的行事作风,文中讲到教谕展先生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回来,驰马过文庙殿阶。直到有一次他在醉酒后又做出这样的亵渎行为,不幸把头猛地撞到了树上,他在死前喊道:“子路怒我无礼,击脑破矣。”展先生从儒家经典中曾览子路之事,但他并未从孔子这个充满善意但行事鲁莽的弟子的错误中学到什么。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有志于仕途的儒生中经常发生———甚至在蒲松龄之前的时代也是如此。到16世纪,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而本应成为“儒家价值模范”的士人群体不但偏离了儒家所设立的社会道德体系,而且通过“非法且不道德的手段——敲诈、欺骗和威胁——来获得房产、田产以及其他形式的财产”。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的儒生们被认为是智力超群者而备受尊崇,这种威信却常常助长这样非法的侵占行为。孔子早在《论语》中就曾告诫子路:“好知不好学,其敝也荡。”在《沂水秀才》一篇的结尾,蒲松龄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只会装腔作势的儒生,讽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富贵态状”。而在《颠道人》一篇中,伪装成儒生的仙人殷文屏嘲弄寒贱出身的周生,因为他自科举进阶,则舆盖而往。
在蒲松龄的故事中,无良官员的贪婪通常表现为暴虐无端和铁石心肠,这一点在儒家经典中也有直接的表述。《礼记》中曾记载孔子和一位在坟前哭诉的妇人的对话。这名妇人向孔子解释:“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于是,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如果一个人能兼具大公无私的精神和甘愿先人后己的操守,同时又能抵挡财富和地位的诱惑,那么这个人才配得上为官的权力。这样的人“在发现生命不值得维续,或者说值得维护的价值信念和生命相冲突,且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他甘愿舍生而赴死”。
蒲松龄故事中的反面典型必然会因其德不配位或滥用职权而受到惩罚,或通过公开羞辱的方式实现,比如无论是《局诈》一篇中因为贪图假公主给它提供宫廷靠山而上当受骗的御史,还是《三朝元老》一篇中被迫承认自己一臣侍二主的兵部尚书洪承畴,皆是如此。亦或通过一些不太明显的手段来判决,这些手段通常是由阴曹地府或者世俗中超自然的神鬼所触发的。比如在《梦狼》一篇中,白甲身为县令但贪赃枉法,而后他正直而受人尊敬的父亲在梦中受到了关于他儿子自我毁灭的警告,但其子不可劝止,后遭寇,决其首。诸寇不为盗,“为一邑之民泄怨愤耳”。
这些故事成为蒲松龄表达意见的重要工具,用以否定科举制是考察个人领悟通晓儒家思想的最重要方式,同时也展现出自己对儒家价值观的坚定拥护。孔子在家庭语境中明确提出了“孝”这一核心概念,并主要考虑其对统治者的影响,但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超越了家庭的畛域,蒲松龄总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孝”这一概念作为个人其他品质的强化、补充或对比。对蒲松龄来说,儒家提倡的孝道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包含了一个人对父母及他人的责任,同时也反映出佛教中众生平等的教义和因果报应的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孟子是儒家传统的积极拥护者,他的言行被记录下来并最终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他在书中规定要恪守“三年之丧”(就像孔子早先提倡的那样),并做到“齐疏之服”和“饣亶粥之食”。这种对父母的奉献,为个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设定了一个高的标准。
在国家层面上,《孝经》规定了孝道在实施过程中的等级划分和彼此依存关系。孔子在《孝经》中阐释孝道依次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最后的庶人降序实施,最终形成了一套针对普通人的综合的四项原则:“由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这些原则在每一个上升的等级中都以各自的方式加以复制。因此,如果每个国人都能将孝道视为对家庭、社会资源和国家责任的基础,那么就能实现国家的和谐与繁荣。
蒲松龄经常关注孝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以渲染孝子们自我牺牲所带来的辛酸。在《青娥》一篇中,孝子霍桓年迈抱病的母亲“逆害饮食,但思鱼羹”,他为了寻找食材,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以至两足跛跻起泡,步不能咫。同样,《钟生》一篇的主人公也非常孝顺,有位能预知未来的道士告诉他,如果不参加此次乡试,过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但道士同时也告诉他,一旦参加此次科考,荣归后恐不复见尊堂,钟生遂欲不试而归。在《崔猛》一篇中,崔猛性情刚毅,“抑强扶弱,不避怨嫌”,但他的母亲却谴责备至,反对他打抱不平而惹祸上身,即使当他被恶人的暴虐或贪官的无餍所激怒时,“惟事母孝,母至则解”,他遵从母亲的要求直到她离世。这些孝子们都因为对母亲的至孝和对他人的赤诚而获得了超世俗力量的奖赏。
蒲松龄崇尚儒家,同时也对佛教和道教有着类似的尊重,这并不矛盾。这三个教派在价值观倡导方面是相通的,特别是在群体行为准则方面,因为“仪式的象征领域具有多种解释,可以在施为结构没有过多改变的基础上加以拓展”。由于每个教派都提倡崇尚和平和尊重自我意识的基本原则,因此蒲松龄认为尊重每个教派的思想对沉思的个体都有潜在好处,三者并行不悖。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唐甄(1630-1704)有着相同的立场。唐甄是一个“平庸”的儒者,他从未跃出当时国家体制下儒学思想的桎梏,他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与具体的政治实践相分离:他“对当代的儒家思想和他眼中中国万恶的专制统治极度幻灭”,但这并没有导致他在“儒家理想的现实不满及其最终有效性”之间建立不当关联。在蒲松龄的故事中,道士、和尚和超自然的实体(鬼怪)经常起着催化的作用,促使他笔下的儒生反省或改变。在《郭秀才》一篇中,一群玩乐的鬼怪假扮成儒生,引诱郭秀才放松下来和他们一起饮酒取乐(还嘲弄他“君真酸腐!”),并展示自己的口技。在《仙人岛》一篇中,王勉“有才思,累冠文场”,同时也“心气颇高”,直到他遇见了一个道教的仙人后才改掉自己“善诮骂,颇多凌辱”的习惯。正是由于蒲松龄对儒、道、佛三教思想并重,才使得他在处理这些超自然的、不可解释的事物时能如此耐人寻味:他故事中的人物处于世俗和幻想的交汇点上,因此他塑造出来的人物既有普适性又兼具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与“神仙鬼怪”的交往往往也揭示出我们自己身上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