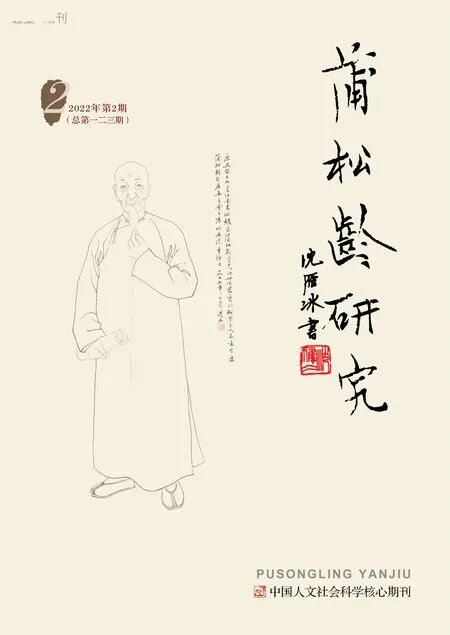《聊斋志异》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的基本走向
赵薇清 陈恒新
(1.山东理工大学 汉籍整理研究中心,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是“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背后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文学造诣,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杰出代表。他“在完全现实的背景下,讲述最神异鬼怪的故事”,志怪小说的表象下暗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以及蒲松龄个人的人生理想与先进思想。精炼的文言语言,略带记史形式的叙事方式,“最虚幻、最讽刺、最现实”的文学内核,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价值。
《聊斋志异》法译以单篇为开端,发展为多篇选译本,通过法国译者一百多年的努力,篇目数量不断扩大,最终在2005年《聊斋志异》全译本问世。译介初期,译者多集中在法国传教士群体,在传教目的下操控《聊斋志异》的译介传播。随着中法交流不断加深,《聊斋志异》的文学与社会价值逐步受到重视,译者主体转移到了汉学家群体。并有不少留法学子对《聊斋志异》展现出浓厚兴趣,成为《聊斋志异》研究的主力军。随着《聊斋志异》的不断译介传播,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过往将《聊斋志异》刻意扭曲为“异教书籍”所造成的“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有印象被打破,对《聊斋志异》的忠实翻译使“中国气质”逐步感染世界。
一、篇章上,由单篇到多篇、全译
《聊斋志异》在海外的译介起始时间较晚,但属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版本最多、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版本多达近百种。相较于晚清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42年便在《中国丛报》首次向英语世界译介《聊斋志异》,法国则是相对较晚。法译《聊斋志异》的起点是1880年由法国领事官、汉学家于雅乐(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译介的单篇译文《种梨》,载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117期,《聊斋志异》法译进程自此开启。
但由于19世纪大部分法国汉学学者都从未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就只能借助不成体系的、由来华传教士译介的、由旅行者或商人来华购买带回法国的中文藏书。而这些传播贡献者的教育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兴趣品味也各不相同,因而呈现在法国社会上的中文图书往往无法代表最先进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成果。这种对中国的无知,也直接导致了法国学界对中国文化及作品的译介传播工作受到阻碍。
1889年,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总兵衔军事参赞陈季同(Tcheng ki-tong)将军编译的《中国故事》在巴黎出版,共收录《聊斋志异》故事26篇。分别为《王桂庵》《白秋练》《陆判》《乔女》《仇大娘》《香玉》《青梅》《侠女》《画皮》《恒娘》《罗刹海市》《黄英》《云萝公主》《婴宁》《张鸿渐》《晚霞》《巩仙》《崔猛》《聂小倩》《莲花公主》《宦娘》《金生色》《珠儿》《续黄粱》《阿宝》《辛十四娘》。陈季同对《聊斋志异》的译介极大推进了《聊斋志异》法译进程,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法国读者与中国文学之间的障碍,拉近了中法两国文学间的距离。
其后,法国耶稣会神父、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编译的《汉语入门》于1895年出版,《汉语入门》第五卷中选译了9篇《聊斋志异》故事,分别为《赵城虎》《考城隍》《劳山道士》《狐嫁女》《长清僧》《陆判》《种梨》《妖术》《任秀》。同时,戴遂良1908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民间传说》中也自《聊斋志异》故事中选译了13篇。这两本书皆为法汉对照课本,编写法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正文均为竖排繁体,版面为左右中法双语对照,篇尾带有脚注,脚注多为解释文化差异词或进行编者评述。
1923年阿尔方(J.Halphen)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选译16篇:《瞳人语》《画壁》《种梨》《劳山道士》《长清僧》《狐嫁女》《娇娜》《妖术》《王成》《画皮》《贾儿》《叶生》《青凤》《董生》《成仙》《考城隍》。1925年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的《魔怪集:蒲松龄(留仙)小说选》选译20篇。1940年皮艾尔·道丹(Pierre Daudin)的《中国故事五十则:聊斋志异选译》选译《考城隍》《陆判》《祝翁》《阿纤》《五通》《甄后》《神女》《马介甫》等50篇故事。
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法国仅坚持了42天时间便举白旗投降,而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局部抗战开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14年的伟大抗战历程。不知是否是过往深入人心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受到了冲击,此后大约三十年间,法国再无译者继续尝试译介《聊斋志异》。
这种困境直到1969年才开始被打破。1969年,由吴德明(Yves Hervouet)领导的一批汉学家合力以《聊斋志异》中文原著为底本,对《聊斋志异》进行精心的翻译。该选本被收录在“东方知识丛书”中,这是第一部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法文译本,其中选译了26篇故事,但只有5、6篇是前人已经译过的,极大地拓展了《聊斋志异》译介内容范围。1986年由李风白(Li/Ly)夫妇译介出版的《聊斋志异选》选译了38篇故事,该译本在中国首次出版,但在法国大量发行、多次再版,在法国产生巨大影响。
1996年法国汉学大家雷威安(André Lévy)先生译介出版的《奇异史话》问世。该译本根据权威中文版本(1962年,张友鹤辑校的“三会本”,共503篇)的一、二卷选译了前82篇故事,这是直至当时选译故事最多的《聊斋志异》法文译本。此时《聊斋志异》全译本已然成书,却因出版社中途反悔迟迟不得出版。正如雷威安先生本人提到的“1991年,出版社口头表示把《聊斋志异》全译本列入出版计划。翻译初稿完成后,出版社却改变了计划……对后几卷的出版,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令人高兴的是,雷威安的两卷本《异史》最终于2005年秋通过毕基耶出版社成功出版,这是《聊斋志异》第一个法文全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二、译者身份上,传教士首创,汉学家发展,高校学子助力
如果说《聊斋志异》在法的译介遵循了中国名著译介的总体趋势,那它在法的传播则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聊斋志异》的译介研究起始于一批来华传教士,这些人的译介带有强烈的宗教与政治目的,即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试图控制中华民族思想信仰,从而达到助力西方殖民主义者完成殖民活动的目的。1842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实腊首先将《聊斋志异》投入西方视野,便试图对《聊斋志异》实施跨文化操纵。他为《聊斋志异》打上了“异教书籍”的烙印,直接影响了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对《聊斋志异》作品形象的塑造,在其之后卫三畏、翟理思的译介研究均受其影响。
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两卷本的《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对之后的西方汉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翟理思以“严肃的文学作品”定位《聊斋志异》,并将其收录于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中国文学史》中。翟理思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被广泛认可为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发展角度系统阐述中国文学流传的著作。全书446页,仅专项介绍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篇幅就达20页,极大程度地扭转了西方汉学界对《聊斋志异》的固有观念,法国汉学界也自此开始以严肃文学作品的观点看待《聊斋志异》。
在《聊斋志异》法译历程中有一人显得尤为特殊,即清末外交官陈季同,一名在法国编译中国名著的中国人。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晚清外交官,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总兵衔军事参赞。1877年,陈季同以翻译的身份,随官派留欧生进入法国政治学堂,学习“公法律例”。后担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在巴黎居住长达16年之久。陈季同客居法国时,适逢中法战争爆发,陈季同一方面饱尝思乡之苦,另一方面深入领略了法国长期对中国文化抱有的无知与偏见。为了扭转法国对中国的看法认识,反抗对中国的无端歪曲诋毁,重塑中国礼仪之邦、政通人和的国际形象,陈季同走上了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
1889年,陈季同编译的《中国故事》由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该节本选译了26篇聊斋故事,是《聊斋志异》的首部法译节本。陈季同坚持以“意译”立场翻译《聊斋志异》,即表述清楚文章意义,对形式是否忠实原文不做强求。在翻译策略上采取外文的“归化”策略,即在语言、文化与美学等层面上的价值取向均有意向译介地法国靠拢,努力迎合法国读者阅读习惯与阅读需求。情感上“忠于原著”,但在译介过程中积极大胆改译:集中表现为对原著情爱情节的省略与改写;同时对原著作者避而不谈,仅以故事本身作为译介对象;并删除篇尾最能代表作者主观写作目的的“异史氏曰”评述部分。陈季同对《聊斋志异》的译介尽可能地顺应了法国读者的文学传统及预期,最大程度地以法国化的表现形式展现《聊斋志异》,但也充分保留了故事本质与民族色彩,“其外在形式已尽可能的法国式,其本质和民族色彩却完全保留了原样”。但同样应明确的是,陈季同笔下所传递出的“中国”仅代表符合西方世界心理预期的、被修改润色的、合乎法国“道德”的“中国”,而非当时真正的中国文明。陈季同明确的文化传播意识,使法国读者大大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精髓的理解。
1895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编纂的《汉语入门》成书出版。与过往传教士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看待《聊斋志异》不同,戴遂良是译介研究《聊斋志异》的汉学家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来到中国、并对中华文化有深入了解的汉学家。他先是以医生的身份传教,后致力于汉学研究。戴遂良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可能是从其个人兴趣出发的,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价值。戴遂良个人偏爱超现实、志怪题材的文学作品,从4世纪的《搜神记》到19世纪的《暗室灯》,戴遂良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翻译解读,《聊斋志异》也不例外。在他1895年出版的《汉语口语基础》、1908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民间传说》中均选译部分《聊斋志异》知名篇目。
戴遂良编纂的《汉语入门》于1895年由河间府天主教会印刷所出版,它的本质是一本帮助法国读者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因而设中法双语对照帮助读者阅读学习,并以通行白话为主要语言形态。在《汉语入门》的五、六卷中,戴遂良选译了《聊斋志异》的篇目,包括《赵城虎》《考城隍》《劳山道士》《狐嫁女》《长清僧》《陆判》《种梨》《妖术》《任秀》等。戴遂良创造性的用通俗口语改编文言小说,体现了其文学观、语言观的超前性。在译介策略上,戴遂良坚持了“忠实于原著”的作风,保留了原著特有的中国式开篇体例,同时对于专有名词及汉民族特有词等采取了“音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使原著的特有风味被最大程度保存了下来,但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国读者的阅读难度。同时,戴遂良凭借自身扎实的汉文化基础为原文加入评注与评述帮助法国读者理解,并首创性地在每篇文章篇尾加述了译者评说。但这一时期其译介成果仍未完全摆脱西方传统的传教士思维带来的局限。客观上看,戴遂良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与其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密不可分,他带领《聊斋志异》初步走出了单纯的“异教读物”的阴霾,使其文学语言价值开始受到汉学界注意。1905年戴遂良获得有“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也无疑证明了法国汉学界对其专业成就的认可。
《聊斋志异》译介研究成就最高的要属法国汉学界巨擘雷威安(André Lévy)先生。雷威安先生兼具译者、教师与研究者的多重身份,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与研究,由他译介的《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等法文全译本译作均在国际汉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果斐然。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并非进行社会学或历史学研究的工具,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文学既不是对社会简单的反映,亦非意识形态卑微的奴隶”。
在《聊斋志异》的译介过程中,雷威安坚持以严苛的态度进行全译,依据原著逐句译出,这是前人译介所不可及的。由他翻译出版的《聊斋志异》法译本《奇异史话(Chroniques de l'étrange)》是公认的迄今为止译介《聊斋志异》最完整、最忠实的版本。在翻译策略上,雷威安真正做到了“忠于原著”,这种“忠实”是“既要克服差异,又要表现差异”,“最理想的是让读者感觉得到在读中文,然而是一种看得懂的中文!他不是在读一部法文小说,而是一部中文小说”。雷威安先生始终力图引导读者不断贴近中国文学,采取更贴近原著作者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向法国民众真实反映了来自中国的异域民族特征与语言风格特色。雷威安除了对《聊斋志异》进行翻译,还首次开启了《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这是也过去译者所从未做到的。
继雷威安之后,法国《聊斋志异》的研究高潮则聚集于法国高校校园,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的博士论文研究中。有关《聊斋志异》研究的博士论文风潮始于80年代中期一篇题为《蒲松龄(1640—1715)聊斋志异中的讽刺现象》的博士论文。90年代之后《蒲松龄幻想小说的结构分析》《中国文学中的狐狸形象:蒲松龄作品中动物伴侣的情欲》《聊斋志异法文翻译史与批评研究:1880—2004》以及《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十七世纪》等博士研究论文也受风潮影响相继写成。这些论文以独特的视角切入《聊斋志异》,不同程度地运用西方文学批评概念与理论解读《聊斋志异》,对其中所涉及的相关民俗文化以及部分性爱题材、同性恋题材进行解读,并创造性的进行了不同学科交叉研究,使《聊斋志异》更丰富的内容视角为法国学界所感知。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博士研究论文的作者均来自中国,而导师均为法国本土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这也致使这些《聊斋志异》相关研究论文既受中华传统文化渗透熏陶,又采用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精神一以贯之。受中法双重文化影响得出研究成果,在研究立场的客观性上有了质的飞跃。《聊斋志异》研究队伍自此由知名汉学家团队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高校学术团体,这在《聊斋志异》的研究进程上,又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陈季同、戴遂良、雷威安等法国一系列汉学家与高校学子的努力,《聊斋志异》的内涵价值被一层层剖析开来。他们或带着浓厚的爱国情结、或出于宗教文化传播等实用目的、或从汉学研究专业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为《聊斋志异》在法流传付出了努力。
三、接受态度上,由西方眼中的“异教书籍”到认识“中国气质”的窗口
早期《聊斋志异》走出国门,并非主要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而是被“污名化”,作为“异教书籍”传入西方。译者大多采用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过分地改写与删除使原著故事变得面目全非。且受传教等政治、宗教目的影响,刻意歪曲中国本地宗教信仰,间接帮助西方殖民者掌握中国民众心理,从而达到殖民掠夺的邪恶目的。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站在了时代浪潮的顶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坚不可摧。受清政府“闭关锁国”影响,世界各国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西方世界始终持有“中国停滞、堕落、不道德”的观点。
但随着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一些汉学家开始注意到《聊斋志异》的实用价值与社会意义,将《聊斋志异》作为了解中国文化民俗的窗口,《聊斋志异》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学界口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同时因其短小精悍、语言平实的特点,一些侨居的汉学家将其作为迅速学习汉语“最好的工具书”,编入教材在殖民地出版,《聊斋志异》得以在汉学研究者、外交官、传教士、旅中商人范围内迅速流传,译介《聊斋志异》使西方固有印象中神秘莫测的中国变得具象化。但此时西方通过《聊斋志异》认识到的中国仍是被译者模糊了本来面貌的中国,仍不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的真实样貌。
随着一代代汉学家大量译介《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作品与典籍,西方对中国“停滞、堕落、不道德”的思想逐步得到转变,对中国的认识了解不断加深,甚至开始着迷于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蒲松龄独特的叙事艺术也被越来越多专家学者所瞻仰。卫三畏称赞《聊斋志异》:“文风纯雅,包蓄万象,语句活灵,如在目前,欲知华文之奥博精深,不可不读之。”翟理思认为蒲松龄“发展并丰富了中国的讽喻文学,在西方只有卡莱尔的风格可以与之相比”。克罗德·卢阿将蒲松龄誉为“满洲王朝的夏尔·贝洛”,认为其作品“反映了一个令人仰慕的民族的深刻思考”。透过西方学者对《聊斋志异》的译介与研究,重塑了“中国气质”,带领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延续了五千年历史文明、底蕴深厚、儒雅魅力的中国。
在中国迅速腾飞的今天,继续《聊斋志异》的译介传播工作,仍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必由之路,仍是引导世界人民认识中国思想文化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华民族自身,《聊斋志异》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幅展现清朝中国面貌的时代画卷,使今日中国能更好地认识历史,继承优良传统民俗,同时对于落后文化做到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也提醒我们要珍视优秀文学作品,善于从浩瀚的中国文学典籍中汲取有益营养,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是展现一个国家文化最为直接的途径之一。在利用中华优良文化修为自身的同时,可通过新兴的网络社交平台,利用数量庞大的国外网友作为中华文化的隐形传播者,使世界人民受到中华文化的感染,将本国优秀作品传递出国门,调动世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以此吸引更多外来译者、研究者前来研究我们的文化,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为世界所接纳、所热爱。通过中国文学、民俗文化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刮起“中国风”,展现我国五千年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各国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