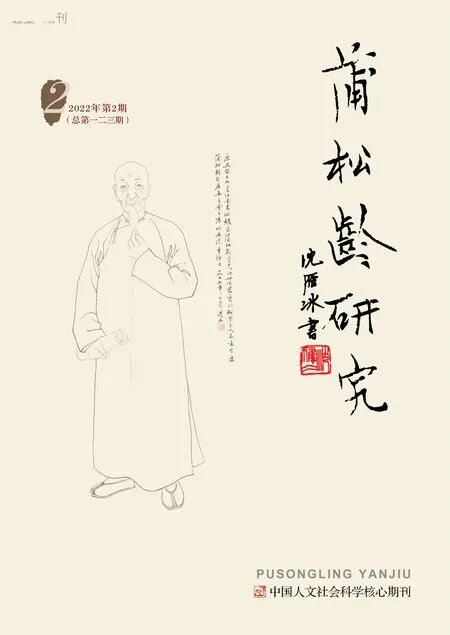对《聊斋志异·席方平》的重读及其创作启示的探讨
陈国学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席方平》作为《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过去往往被当作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标杆,这固然没错,但笔者在反复阅读该文和教学过程中,对这篇杰作有了很多的思考。在此文中,我就想根据这些思考,从人物形象及思想渊源、题材来源、文体渊源等角度对它进行更深入地审视,并探讨由此产生的有关创作启示的问题。
一、《席方平》的人物形象及思想渊源
《席方平》描写的是席方平出生入死、死而复生、生而又死地去为父亲鸣冤昭雪的故事,作者在文后总结席方平是“……死而又死,生而复生……忠孝志定,万劫不移”。这一曲折经历和作者的定论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以及汤显祖给她的定性:“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而席方平显然也可以说是个至情之人,只不过,这种至情不是男女之情,而是儿子对父亲的感情。为此,我们需要明白,至情之情如何从男女之情扩展到了父子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冯梦龙在《情史》序言中所写的《情偈》:“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蒲松龄有没有受到冯梦龙这段话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他所写的《席方平》可以说就是在为《情史》所倡导的的“情教”观中“子有情于父”这一说法在做形象的演绎。
晚明人冯梦龙看到了汤显祖“至情说”的巨大意义,但可能觉得他的至情有点狭隘,于是把这种情扩大到人类的一切感情,主张用这种包容一切的情教来教化百姓。在此,我们不论其局限性,而应该看到它对“至情说”的挽救。应该说,蒲松龄塑造席方平形象时,受到了汤显祖“至情说”与冯梦龙“情教说”两方面的影响,方有那个下地上天为父申冤的铮铮铁汉席方平的形象。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设酒肴,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
蔡支开始来到的地方显然是泰山府君(即文中的“太山神”)之所在,府君让他带一封信给天帝,结果他乘着马就到了天帝之所在,显然是泰山府君的神力所致。这里并没有人间、死后世界及后来所谓上界之间的划分。《席方平》中作为凡人的却能穿越三界的构思与此极为类似,如果是这样,那说明蒲松龄的思路没有被明清时期已定型的人间、地府、天界这三界的划分所限制,而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不拘一格的汲取能力。
二、《席方平》的题材来源
《席方平》的整个结构框架表明其题材来源于传统的“入冥——复活”类型的故事,这一点笔者在《“旧瓶装新酒”:〈聊斋志异〉对传统冥游题材小说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已有解说,在此简单概括一下。席方平冥游地府,不是因为鬼差的勾招,而是出于为父申冤的自由意志,而他也因此经受了地狱的种种酷刑,最后到达天帝处告状,天帝殿下九王子命二郎神审理此案,将地府各级官员及为富不仁的仇家羊某一网打尽,然后席方平苏醒过来。显然,作者借用了传统的“入冥——复活”题材,却不是简单地为佛教的地狱思想做传声筒,因为地狱里原来用以惩罚恶人、坏人的种种酷刑现在却被用来对付良善之辈,所以本文是在影射人间官府的官官相卫、只认钱财、贪酷无比。
《席方平》一文中还杂糅了离魂、投胎转世等传统题材,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它对于封建社会黑暗的揭示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这让我们想到,借用精怪鬼神、宗教题材竟也可以写出如此杰出的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三、《席方平》的中的判案文:公案文体与断案文的杰作
《席方平》又可以看作一篇公案小说,要说它表达了封建社会底层人民对于所谓清官的期盼也是可以的,其中的二郎神显然类似于公案戏中常见的包公形象。不过这里笔者更想赏析其中那篇犀利无比的断案文,如其中讽刺冥王的“繁缨棨戟,徒夸品秩之尊;羊狠狼贪,竟玷人臣之节”,可谓将贪官的面目揭示得无比形象。二郎神判决词中对他的惩罚则是“当掬西江之水,为尔湔肠;即烧东壁之床,请君入瓮”,简直大快人心。接下来谴责城隍、郡司官员收受贿赂后“上下其鹰鸷之手,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狯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对于为虎作伥的下层差役,则批判其“飞扬跋扈,狗脸生六月之霜;隳突叫号,虎威断九衢之路”。最后,对以金钱买通官府的羊某,也不忘指责他“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这里其实更多地还是隐含着对官府黑暗的揭露。通观这篇断案文,可以说表现了蒲松龄高度的文言文修养,其对现实社会犀利尖锐的揭露以及对用典、对偶、比喻等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样的作者却一辈子考不上科举,真正是冤哉枉哉!
由此想到作为“文备众体”的小说的文体渊源。在小说中杂入公文,自然不始自《聊斋志异》。在《金瓶梅词话》第48回即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弹劾山东提刑所正副千户夏寿、西门庆的奏折,文中说正千户夏寿:“葺茸之材,贪鄙之行,久于物议,有玷班行……接物则奴颜婢膝,时人有丫头之称;问事则依违两可,群下有木偶之诮。”又批判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之后总批二人“皆贪鄙不职,久乖清议,一刻不可居任者”,这篇奏折就很类似《席方平》一文中的断案文。《醒世姻缘传》第13回则正式出现了断案文,该回在描写东昌府理刑褚推官对晁源的妾施珍哥诽谤正妻计氏与和尚通奸、致使计氏上吊自尽一案后,发布断案文,文中说施珍哥:“惑主工于九尾,杀人毒于两头。倚新间旧,蛾眉翻妒于入宫;欲贱凌尊,狡计反行以逐室。乘计氏无自防之智,窥晁源有可炫之昏,鹿马得以混陈,强师姑为男道;雌雄可从互指,捏婆塞为优夷。桑濮之秽德以加主母,帷簿之丑行以激夫君。剑锋自敛,片舌利于干将;拘票深藏,柔曼捷于急脚。若不诛心而论,周伯仁之死无由;第惟据迹以观,吴伯之奸有辨。合律文威逼之条,绞无所枉;抵匹妇含冤之缢,死有余辜。”说晁源“升斗之器易盈,辘轴之心辄变。盟山誓海,夷凤鸣于脱屣之轻;折柳攀花,埒乌合于挟山之重。因野鹜而逐家鸡,植繁花而推蒯草。夺宠先为弃置,听谗又欲休离。以致计氏涉淇之枉不可居,覆水之惭何以受?无聊自尽,虽妾之由;为从加功,拟徒匪枉”。后文还批判差役伍圣道、邵强仁“鼠共猫眠,擒纵惟凭指使;狈因狼突,金钱悉任箕攒。二百两自认无虚,五年徒薄从宽拟”。就更加类似于《席方平》一文了。
由上引文可知,明代小说中引入公文甚至更具体的判案文已经是并不罕见的情况,蒲松龄先生应该是对此非常了解,才在《席方平》一文中创作了一篇绝佳的断案文,显示了他高超的文言造诣。该文的杂入虽不无炫才的特点,但简洁地显示了二郎神对冥府各级官吏及行使贿赂以报私仇的羊某的一网打尽,有大快人心的效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四、结语
以上从人物形象及思想渊源、题材来源、文体渊源等角度探讨了《席方平》可能的灵感来源,探讨显示出该篇是有着多处的源头的:其思想渊源是明代中后期从汤显祖到冯梦龙的的主情思潮;题材渊源则是《太平广记》中大量存在的佛教的“入冥——复活”小说;文体渊源还与公案小说中杂入的判案公文有关。而蒲松龄先生对这些源头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融会贯通,表现出杰出的锻造本领。其创作启示至少有二:其一,利用宗教题材却不拘于宗教宣教意识的创作宗旨,这表明,宗教题材是可以用来表现非宗教内容的,而且可以表现得相当成功。其二,突破固有观念的想象力,正是这一点,使作者突破了宗教题材的限制,例如席方平可以自由地摆脱肉体的束缚,魂灵自主地来到阴曹地府为父申冤。而以往的入冥题材中,入冥者一般都是被阴间使者(即所谓黑白无常)带入地府的,席方平投胎为婴儿后,三天不吃奶气绝身亡,死后灵魂再次获得自由,在去寻找灌口二郎神的路上遇到天帝殿下九王子,告状成功。这里没有明确地讲席方平的灵魂是到了天上,但按固有观念应该是来到了天界,而一般而言,凡人的灵魂是难以到达天界的。所以说,文中的席方平是自由出入三界,才得以表现他为父申冤的坚定意志,这是蒲松龄追求法制公正思想的表现,但是呈现为突破三界不可随意穿越的固有观念的自由意志。伟大作家利用宗教又突破宗教观念,简直达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步,令人赞叹不已。而这显然是充沛的创造力的体现,可谓“元气淋漓,真宰上诉”。
当然,《席方平》一文本身还是首重对儒家思想中孝道的表达,结尾处坏人被一网打尽、好人获得好报仍然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可见什么时候需要遵守传统,什么时候需要突破固有观念,在伟大作家那里是有衡量的。也许可以说,在道德观念上遵循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不作随意大胆的逾越,而在想象力上尽可以天马行空,是《席方平》一文给我们的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