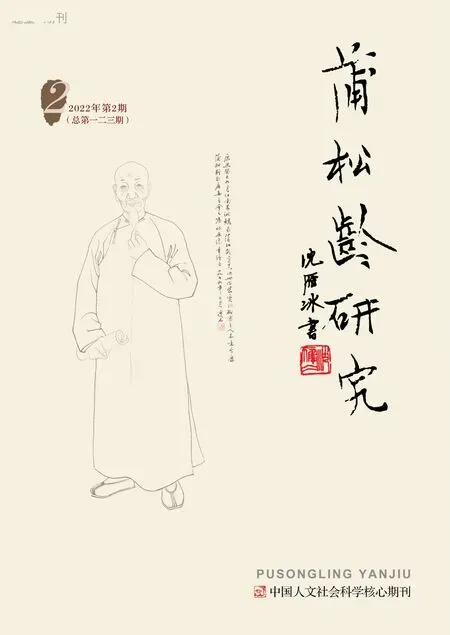莫言《金发婴儿》取材考
——兼论“妻子怀上别人孩子”的道德困境
刘洪强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莫言偏爱《金发婴儿》,他说:“它更像一篇小说,深入到人的隐秘世界里。虽然好多人不喜欢,但我个人最喜欢。”这篇被作者“个人最喜欢”的小说极为精彩动人。那么这个故事是有所本还是莫言自己独创的呢?季羡林先生说:“创造一个真正动人的故事,同在自然科学上发现一条定律一样的困难。”莫言虽然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他似乎很难讲述一个完全独创的故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物,而且对一个作家来说,也不一定非要独创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故事情节。这样一来,我们阅读莫言《金发婴儿》就会发现,在这“更像一篇小说”的背后的确有许多读者熟悉的素材。
一、《金发婴儿》与《聊斋志异》
《金发婴儿》写紫荆的丈夫孙天球当兵长年在外,对紫荆很是冷漠,紫荆在青年男子黄毛强烈追求下,和黄毛走到了一起。后来孙天球撞破两人私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孙天球掐死了紫荆生下的那个金发婴儿。
《金发婴儿》中的紫荆特别爱笑的特点与《聊斋志异·婴宁》相同,这一点笔者已经有专文说明,不再赘述。此外,《金发婴儿》的基本情节与《聊斋志异·罗祖》有较高的相似性。下面逐条分析。
首先,都是丈夫当兵长年在外,且均受到领导器重,独守空房的妻子出轨。《金发婴儿》中丈夫孙天球是某市警备区指导员,“在警备区的十几个指导员中,数着他才貌双全,头头们很器重他”,家里的妻子紫荆非常贤惠,照顾瞎眼的婆婆,但最后还是与黄毛出轨。《罗祖》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罗祖,即墨人也。少贫纵,族中应出一丁戍北边,即以罗往。罗居边数年,生一子。驻防守备雅厚遇之。会守备迁陕西参将,欲携与俱去。罗乃托妻子于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
《罗祖》中罗祖也是当兵长期在外,“驻防守备雅厚遇之”,妻子红杏出墙。
其次,丈夫们对于第三者入侵的处理均冷静理性,第三者都受到官方的惩罚。一般来说,得知妻子出轨,男人总是怒火中烧。比如《水浒传》武大郎都要捉西门大官人的奸,闹得街坊邻居皆知;《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蒋淑真与“奸夫”朱秉中被蒋氏丈夫张二官杀死;《醒世姻缘传》小鸦儿杀死妻子唐氏与晁大舍,后两者都是私通男女被丈夫当场杀死。但《金发婴儿》与《罗祖》中的情况却大不一样,《金发婴儿》中孙天球发现妻子与黄毛的私情后,只是踢了黄毛一脚,并说“滚你的”,他哀求妻子:“紫荆,我原谅你,只要你改正错误,我会好好爱你。”事后孙天球把黄毛告上了法院。孙天球说:“紫荆,逮捕他我也不愿意,可你要知道,王子犯法,一律同罪,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然孙天球把黄毛送上了法庭,但这个情节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通过孙天球的口说出的,因而给人的感觉是孙天球对第三者并没有常理中的愤怒。
《罗祖》中罗祖回家后发现妻子与友人李某睡在一起,不过罗祖并没有对妻子与李某做出过激的行为,只是斥责了友人,并把妻子与儿子、马匹器械等都给了友人,然后飘然而去。“乡人共闻于官。官笞李,李以实告”。虽然罗妻与友人被官府逮捕,但是与罗祖并无直接关系,这只是邻人代罗祖打抱不平而已。
再次,都有一个小孩子。《金发婴儿》中有一个“金发婴儿”;《罗祖》中罗祖有一个儿子,人称小罗祖。
最后,两部小说的主旨也有一定的联系。《罗祖》结尾有“若要立地成佛,须放下刀子去”,而《金发婴儿》孙天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掐死了婴儿,小说最后说“我非常后悔,我看到他的头发像一缕缕黄金拉成的细丝,每一根都闪耀着迷人的光辉”,可见孙天球虽然在事前没有“放下刀子”,没有放下心中的怨恨,但到最后醒悟过来了。《罗祖》中的罗祖为明代无为教(罗教)创教祖师罗梦鸿,此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笔者以为,《罗祖》这个故事多少影响了《金发婴儿》。
此外,孙天球看到婴儿是个黄发孩子,就把婴儿掐死了;与《聊斋志异·黑鬼》中的黑鬼看到儿子皮肤白就杀死儿子同一机杼。《聊斋志异·杜小雷》有忤逆的儿媳妇虐待盲人婆婆,最后这个可恶的女人变成了一头猪;《金发婴儿》写一个善良的儿媳妇无微不至地照顾瞎眼的婆婆,《金发婴儿》虽然没有写到儿媳妇变成猪(当然如此孝顺的儿媳妇也不可能变成猪),但是小说中却用大量的笔墨描写,“这头猪体型矫健,四条腿粗壮有力,身体呈优雅的纺锤形。紫荆对这头猪是敬而远之”。紫荆带着哭腔说:“这不是个猪,这是个妖怪!它两年没长一钱肉,还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受不了啦。黄毛,我受不了啦。”不难看出,这里的猪是人性化了的猪,是有灵性的猪。燕妮就曾亲昵地称马克思为“我的小野猪”。《金发婴儿》的这头猪隐约的指“黄毛”或“紫荆”。这也可以算得上对《杜小雷》的“反模仿”。
《金发婴儿》中写了“人工湖边塑了一尊裸体女人像”,战士们都盯着看。当时发生的一件真事似乎也影响了这篇小说,《〈少女之心〉把我拉向深渊》:
我叫贺X X,一九八○年一月入伍,原是某部五连战士。入伍后,我一度上进心比较强,利用自己会做木工的一技之长,经常为连队修修补补,做好事,多次受到表扬,并入了团……我从地方工厂的废纸堆里看到一张外国报纸上的裸体女人像,一边盯着看,一边想,这东西在中国是没有的。想多看几眼,不愿离开。
这则故事最早在1985年以内刊的形式发行,当时莫言还在部队,完全有可能看到这篇文章。
二、丈夫何为:当妻子怀上了别人的孩子
莫言说,《金发婴儿》“深入到人的隐秘世界里”。一般来说,文学是人学,总是强调直抵人心,叩问灵魂,《金发婴儿》涵摄这些意义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还需要莫言再如此强调吗?作者如此强调“人的隐秘世界”到底指的什么?《金发婴儿》的主旨是什么呢?从钟本康先生《现实世界·感情世界·童话世界——评莫言的四部中篇小说》到藤井省三先生《鲁迅与莫言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下)》等均未注意到私生子对男性尊严的“挑衅与侮辱”;张永辉《从伪女人到真女人——浅析〈春夜雨霏霏〉与〈金发婴儿〉中的女性形象》重点在分析《金发婴儿》中的紫荆,而未对孙天球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江涛《人格面具的认同、拒认与缺席——莫言〈金发婴儿〉的再解读》“更让他怒火难平的是婴儿头上生出的黄毛。‘黄毛’的意象,揭穿了婴儿与孙天球之间父子关系的谎言,孙天球再次遭到背叛”。已经注意到婴儿对孙天球的伤害,但未进一步分析。以上学者各有侧重,对《金发婴儿》的主旨有不同程度的揭示,但总体来说,学界对此研究得不够。
笔者认为,《金发婴儿》中“人的隐秘世界”是指一个正常男人面对“妻子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所产生的痛苦折磨与剧烈反应,这就是此小说的主旨。
古今中外,妻子出轨,不论在小说中还是生活中都是令男人最不堪容忍的事情,因此孩子的命运都极为悲惨,“有些家法族规对奸生子基本就是遗弃或者杀掉”。姜泽峰《中国古代奸生子继承研究》:
由此可见,西方历史上几个主要国家对待非婚生子女都是持歧视态度,甚至父母都不得认领非婚生子女,而非婚生子女中的乱伦子和奸生子的处境更为悲惨。
对男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还留下一个“野孩子”。然而这种事却成了检验人格的试金石,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诸葛亮有七种“知人性”的方法,有一种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小说理论中常说,把一个人物置于危急时刻来观察及表现人物的性格,因此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妻子怀了他人的孩子,并且生出了这个孩子,以此来考验一个男人,这应该是对男人最严酷的考验,也是作家展现人物复杂性格所设置的最佳情境。
我们来看一下,小说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经笔者简单梳理,基本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杀死孩子;第二种是开始时痛苦,但慢慢接受了这种现实,甚至爱上了孩子;第三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不得不忍受着孩子。
(一)第一种:杀死孩子
很多情况下,男人会杀了这个“孽种”。较早的当数《左传》“成公十一年”发生的一件事: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
施孝叔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于是妻子成了郤家的人,妻子在郤家生了两个娃娃。当郤家灭亡,妻子无奈领着两个孩子回来,施孝叔却把两个娃娃沉到河里淹死了,这肯定是施孝叔的妒忌心在作怪。不过,这个妻子生娃娃时已经与施孝叔离婚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对施孝叔的屈辱感。再如蒲松龄《黑鬼》:
胶州李总镇,买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为途,往来其上,毫无所损,总镇配以娼,生子而白,僚仆戏之,谓非其种。黑鬼亦疑,因杀其子,检骨尽黑,始悔焉。公每令两鬼对舞,神情亦可观也。
这篇小说并没有说黑鬼的妻子生的是他人的孩子,黑鬼只是怀疑,只因这可怕的疑心,就杀了自己的孩子。这种强烈的妒忌心让黑鬼酿成了大错。
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中段皇爷(一灯大师)的爱妃刘贵妃(瑛姑)与老顽童周伯通生了一个儿子,段皇爷心如刀割:
我也不让宫女太监知晓,悄悄去她寝宫,想瞧瞧她在干些什么。刚到她寝宫屋顶,便听得里面传出一阵儿啼之声。咳,屋面上霜浓风寒,我竟怔怔地站了半夜,直到黎明方才下来,就此得了一场大病。
最后这个孩子被人(裘千仞)拍成重伤,瑛姑让段皇爷去救时,段皇爷拒绝了,最后孩子被母亲瑛姑杀掉了(因段皇爷不肯相救,母亲怕孩子受无谓的痛苦)。当时段皇爷想:
她又在为一个人而心碎,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情人,是为她的儿子,是她跟情人生的儿子……大丈夫生当世间,受人如此欺辱,枉为一国之君!我想到这里,不禁怒火填膺,一提足,将面前一张象牙圆凳踢得粉碎。
看来贵为皇帝亦有如此儿女私情。虽然这孩子不是段皇爷杀死的,但他的见死不救,也说明他心里充满了怨恨。
民间故事《书生救蛇得奇缘》中,梁生受人挑唆,误以为自己的妻子花衣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野种”,他想“那花衣腹中的孩子,岂非就是野种”,“若是这怪物不是自己骨血,那才愧对祖宗”。于是他拿了堕胎药让妻子喝下去,把孩子打下来了。其实花衣怀的孩子就是梁生自己的孩子,可见男人对这种情况难以容忍。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话》有一个情节写斯琴格勒与相好的同居后怀孕,“斯琴格勒的丈夫出门放牧三个月,回来却发现她怀孕了……斯琴格勒的丈夫生了气,觉得这是相好欺负自己,用皮鞭抽斯琴格勒”,斯琴格勒的丈夫“掂着一把宰牛刀上了路……上去就要拼命”。可见,几乎所有的男人在这种事情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陈彦的《主角》写张光荣认为自己妻子胡彩香生的娃是胡三元的。郝大锤还说:“张光荣多牛啊,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老婆在家里连牛牛娃都给你生下了。白拾个爹当着。”张光荣找到胡三元大吵大闹,两人展开了肉搏。最后胡彩香要摔死孩子,并力证孩子是张光荣的,张光荣才平静下来。
上面的例子证明,男人很难容忍这种情况,通常采取的举动是把孩子杀死。
(二)第二种:善待孩子
男人很难容忍这种情况,不代表没有男人容忍。在小说中也常常有能够容忍的男人。
《补江总白猿传》中欧阳纥的妻子被白猿盗走,当找回来时,妻子已经怀孕,后生一子。当时白猿就对欧阳说“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可见欧阳纥明白自己妻子生育的是白猿之子,但欧阳纥没有杀死这个“孽种”,颇具有宽容的胸怀。
《萧萧》写童养媳萧萧因为丈夫不到同房的年龄,后来发育成熟的萧萧与青年花狗野合怀孕,婆家人计划把萧萧淹死或发卖,但当她生下孩子后,萧萧的婆家却十分善待这个婴儿。“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
《射雕英雄传》完颜洪烈娶了已有身孕的包惜弱,当包氏生了杨康后,完颜洪烈对杨康极为疼爱,也显示了一定的人性美。所以完颜洪烈在小说中虽是反面人物,但却是一个好丈夫与好父亲。当然了,包惜弱是被完颜洪烈“骗”到手的,原本不是完颜洪烈的妻子,而是杨铁心的妻子。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许三观知道自己的儿子一乐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何小勇的孩子时,他说:
九年啊,我高兴了九年,到头来一乐不是我儿子,我白高兴了……
所以我的第一个儿子是别人的儿子,我许三观往后哪还有脸去见人啊……
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吗?他们都说我心善,要是换成别人,两个何小勇都被揍死啦……你别找我商量,这事跟我没关系,这是他们何家的事,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吗?我要是出了这钱,我就是花钱买乌龟做……行啦,行啦,你别在哭啦,你一天接着一天的哭,都把我烦死了。这样吧,你去告诉何小勇,我看在和你十年夫妻的情分上,看在一乐叫了我九年爹的情分上,我不把一乐送还给他了,以后一乐还由我来抚养,但是这一次,这一次的钱他非出不可,要不我就没脸见人啦……便宜了那个何小勇了。
许三观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在说三个儿子里他最喜欢一乐,到头来偏偏是这个一乐,成了别人的儿子。有时候许三观躺在藤榻上,想着想着会伤心起来,会不住地流眼泪。这里许三观是一位颇具人性的男人,许三观说:“他们都说我心善。”确实,心善与否是处理私生孩子问题的关键。
在当代小说中,高满堂的《于无声处》存在一个争议很大且令多数人无法接受的情节:国安人员马东与已经怀孕的冯书雅结婚,而书雅怀的是别人的孩子,孩子生下来后,马东又对这个儿子疼爱有加。网上很多人对此表示难以理解。我们可以从网上引两种评论,网评一:
这部电视剧个人感觉还不错,能追得下去,于是就去搜了下后续剧情。结果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陈其乾消失的时候,冯书雅已经有了陈其乾的孩子,然后马东放弃国安的身份跟冯书雅成亲,然后照顾他们母子,这不就是接盘侠么?这剧情简直让我完全无法接受。
网评二:
萧峰和马东都是胡军扮演的。两人都是硬汉形象,两人对阿朱和书雅都是真爱无悔,两人对兄弟都是义薄云天,萧峰对段誉,对虚竹可谓两肋插刀,义重恩深。但和马东还是有差距,至少萧峰没把阿朱让出去,至少萧峰没去把两位兄弟的孩子养大。总得来说,两位均可用侠骨柔情来形容。但两人结局却如此不同。如果让男人选一个心目中的偶像和自己愿意成为的人,我想大多数男人会选萧峰。结论:金庸真男人,高编剧心理变态。
不论如何,让男人接受“妻子怀了别人的孩子”这一现实是很难的,但不是绝对没有的。评论中“高编剧心理变态”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并非心理变态,而是“心地非常善良”。
贾平凹的《人极》中亦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光子遇到了一个怀孕的女人白水,光子是个光棍,白水想嫁给光子,光子不同意,白水说,“你要可怜一下我的孩子”:
光子这才注意到她的肚子微凸,就叫道:“这是哪来的孩子,谁的孩子?”白水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的。”光子一阵恶心,唾了一口骂道:“不要皮脸,你还有脸寻到我这儿来!”浑身打颤,砰地把门就关了。
但好心的光子最后还是娶了白水,白水生了一个儿子,光子非常喜欢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徐则臣《北上》中马思艺生的孩子胡念之不像丈夫胡问鱼,却非常像在他们家住过的年轻水利专家。丈夫胡问鱼喝酒解忧愁,他痛苦得用碎了的玻璃瓶子扎自己的大腿,马思艺说:“你要信,他就是你儿子;你要不信,离婚,我带他走。”但最终胡问鱼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
在日本小说《源氏物语》中光源氏的夫人三公主与柏木发生了关系,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光源氏心怀隐痛,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从而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由此可见,能够宽容的男人展现了人性美,他们超越了狭隘的思想,受到人们的尊重。
(三)第三种: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忍受
有的男人或因为不能生育,或者有其他目的,只能忍受着这个孩子。清中叶曹去晶《姑妄言》中出现了至少两次这种情况,如第六回:
此后金矿常常来往,不必繁叙。过了数月,阴氏竟得了孕,二人更加亲厚,半年有余,阴氏陆续得过他有百余金,还有许多衣服首饰,街坊上的人渐渐知觉。
按,妻子阴氏有个情人金矿,丈夫嬴阳是个戏子,身体弱不能养家,阴氏与金矿生了一个女儿皎皎,嬴阳默然受之,并不反对。再如第七回:
只交七个月,便生下一个女儿。牛质暗想道:“我自得了他,只在陆路驱驰,从不曾水门来往,何得忽生此女?”虽知这娃娃来路有些不明,因没有多的儿女,也就葫芦提认了。反向人拿话掩饰。
按,妻子计氏结婚七个月就生了孩子,丈夫牛质虽然明知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既然没儿女,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丈夫出于无奈,所以勉强接受的。这种情况在现实中虽然隐秘但却是不少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小山道:“去年我与你此事甚稀,算来十个月之前,正是七月内了,我并不曾与你下种。此是你与他两个生的,我不管。”巧娘说:“呆东西,有了千金家私,只少个儿子,拿了一千金子也不肯钻在你肚里,别人吃辛吃苦,你做现成老子。好不便宜你,还要分清理白。”
这类小说有夸张荒诞的成分,与我们所讨论的写实小说有一定的距离。张爱玲《怨女》中写九老太爷不能生孩子,于是他故意让自己的太太与下人在一起,“是他叫个男底下人进去,故意放他跟他太太在一起”。这种借人生子是属于生理有问题,与我们所讨论的还有所差别。
刘醒龙《蟠虺》中出现了两个情节,一个是在梦中,一个是在现实中。在曾本之的梦里,沙璐与那个前夫鼻屎处长生了一个儿子,却被发现血型对不上,原来孩子的父亲是万乙。曾本之把此梦告诉好友马跃之,“马跃之更加不以为然,他觉得曾本之的心智出了问题:妻子怀孕分娩,孩子的父亲却不是妻子的丈夫”。曾小安婚前怀了男友郝文章的孩子,郝文章入狱,曾小安与郑雄结婚,婚前小安就告诉了郑雄她已经怀孕了。但郑雄看中的其实是小安的父亲曾本之的权势,所以忍辱与小安结婚,而且婚后八年没有碰小安一下。能容忍如此大的“屈辱”,此人用心之狠难以估量。
在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中,“母亲”所生的孩子都是与其他男人所生。这是因为“母亲”的丈夫“不行”。
这种情况可以归为不得不忍,或因男子身体问题,或因男女双方为了达到某种不可说的目的。
三、对此道德困境的思考
莫言的笔下,那个金发婴儿被扼杀了;而在沈从文的笔下,那个孩子活了下来。扩展到整个人类范围应该如何对待这个事情呢?在我看来,我们理解不能容忍的,佩服能容忍的。毕竟这种事对一个平常人来说,甚至对动物来说,都难以做到。阿城文集之四《常识与通识》的《攻击与人性之三》写道,一只雄狒狒咬死了其“嫔妃”与别的狒狒“勾搭”而生下的小狒狒。一男人疑神疑鬼杀死了他认为不是亲生女的亲生女儿。
据说以前有“摔死头孩”的风俗,也就是受屈辱的汉人往往都会把第一胎摔死,因为第一胎不是自己的“种”。(关于这种说法,历史学界未能证实或证伪,但是从中反映出来的情感是真实的。)应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有法律专家指出:“这类奸生子的出生违背了伦理道德。”但是,无论成人如何作孽,孩子是无罪的,尽管她(他)是私生的,这“私”是对人类社会来说的,而对于自然界来说,任何一个孩子的到来,都是美好的,无所谓公或私,有道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贾平凹《人极》中说“可孩子他没有罪呀”。再举一例,《救助日本遗孤》中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了两个失去父母的日本小姑娘。大的五六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又受了伤。聂荣臻将军知道后,立即叫前线部队把孩子送到他那里去。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同胞,但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她们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照料,决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类似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善良的中国人民,妥善收养及安置日本遗孤,“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统计,回日定居的日本遗孤总数近4000人”,“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容、博大的胸襟,而这种抛开民族恩怨、不计前嫌、拯救生命的善举也彰显了中国为世界和平多方兼顾的大国风范”。“日本兵库县一位友好人士说:‘我们对中国抱有尊敬的感情,中国对日本孤儿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充满友爱,这是世界上少见的’”。中国人民对待日本遗孤的态度是值得思考与提倡的。
国人对于“私生子”也有包容之同情。在世俗中,虽然这些孩子们被嫌弃被遗弃,但是却从法律上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古代他们有财产继承权;在当今社会,《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作家笔下却有不同的写法。莫言《金发婴儿》与沈从文《萧萧》有着大体相同的情节,然而却有不同的结尾,这个不同的结尾与其说是作家处理素材的不同,倒不如说是作家的心态及文化折射的不同,与各自所处的时代及文化背景也有密切的关系。沈从文《边城》在谈到妓女时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莫言生长在孔孟之乡,受传统教育影响程度较为深厚。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说:
当沈从文小说时代过去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这种文化追求,在莫言那里得到了并不遥远的历史回应。莫言像沈从文一样,他的“红高粱家族”小说,要弘扬的就是那种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敢歌敢哭的非文化规范状态下的生命原动力,而这种生命的原动力是超越道德标准及其相应的价值判断的。
由此看来,在莫言的笔下终究少了几分宽容,多了几分戾气。最近,笔者在网上浏览到一则新闻《一个令人震惊的强奸犯的故事》,说2002年在意大利发布一则寻人启事:
1992年5月17日,在瓦耶里市商业区第5大道的停车场,一个白人妇女被一个黑人小伙子强奸。不久,女人生下了一个黑皮肤的女孩。她和她的丈夫毅然担当起抚养女孩的责任。
当时这对白人夫妻很想遗弃这个黑皮肤的女婴,丈夫说:
我们绝望了,曾经想过把孩子送给孤儿院,可是一听到她的哭声,我们就舍不得了。毕竟玛尔达孕育了她,她也是条生命啊!我和玛尔达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最后决定抚养她,给她取名莫妮卡。
可是女婴生病了,急需生身父亲的骨髓,即强奸犯的骨髓。最后这强奸犯勇敢地站出来,挽救了孩子。大家认为“也许他曾经是个罪犯,但现在他是个英雄”。不知道这是个真事还是个故事,不过对本文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是真事,那么就可以“生活真实”地反映人性;如果是编造的,那它就是小说,可以“艺术真实”地反映人性。白人夫妻能有如此胸怀,当真了不起。他们容纳了常人不能想象的痛苦。
用痛苦来考验人性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地震、火山、屠杀这种外在的硬伤有时未必触动人心中的最深处,这种不见血的软伤更让人难以忍受,亦更令读者动容。
对于《萧萧》之类“容忍”的小说,更让人感到一种人性的高尚(这里并不涉及作品艺术水准的评价)。平心而论,在这种情况下,“不宽容”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宽容”则显示了更高层次的爱与怜悯。
在徐则臣《北上》中胡问鱼痛苦地用碎玻璃瓶扎自己,而妻子为了此事也用碎玻璃瓶扎自己的大腿,可见此事对当事人情感震动之大。明白这一点,我们在经历人生及阅读作品时才会有更深的感受。比如《天龙八部》中的钟万仇对于妻子甘宝宝的爱,因私生子钟灵的存在而将这种爱超越了庸常之爱,从而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聊斋志异》之《土偶》写王氏青年守寡,后生一子。据王氏说是她丈夫之魂夜夜来与她相会,因此生了一个儿子。里人讪笑。邑令用滴血法断定这个儿子就是王氏与“鬼丈夫”的亲生儿子,于是“群疑始解”。在这篇小说中,王氏的丈夫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了,但王氏的婆家、邻人、仇人等都在监督着她,并在无形中质问着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就今天的科学知识而言,王氏一定是与“活”的男人在一起才能生娃娃。但不管如何,在我们为王氏担忧时,邑令善意的“装神弄鬼”,带来了邻人会心的“恍然大悟”,让大家非常宽容地接纳了这个没有丈夫而生子的王氏,显现了人性美。韩田鹿先生分析《土偶》时说:“在县令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智慧与温暖……在很多时候,法律与人情,礼教与生活之间,确实存在难以两全的情况,县令的这种做法,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难说严谨,但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我以为还是一片菩萨心肠,值得称赞。”法国著名诗人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确实如此。
杨红霞先生呼吁:“公平地对待奸生子、关爱奸生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这一点上,文学上已经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为和谐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