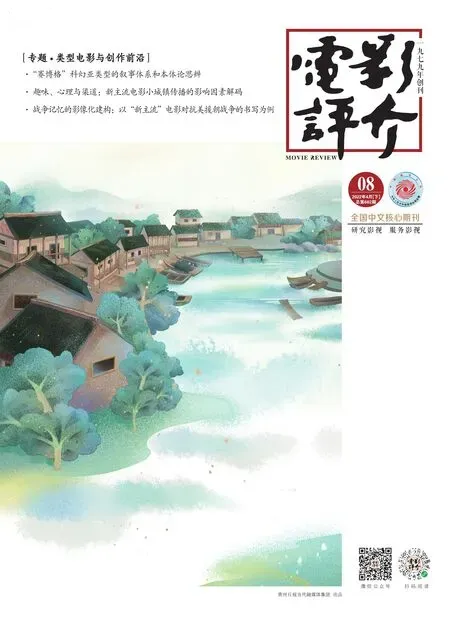多维向度与美学指归
——论电影艺术的疾病书写与隐喻
石迪 刘可文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承担着记录时代、讴歌时代的职责与使命。疫情将全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同的国家以电影艺术来叙述疾病的方式不一致,但是他们都以相同的社会关切和美学意义为指归。电影艺术中的疾病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在电影里已超越了具体的生理病象与医学意义,成为一个隐喻化象征。作为实践生活的身体也随着疾病入侵发生了种种变化,“作为生理学层面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因此探究电影艺术中的疾病表征,进而进一步挖掘其在文化层面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电影艺术的疾病书写
(一)疾病书写的特点
福柯说:“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灾难电影中的疾病通常是来源不明的新型感染病毒,在世界上较为罕见。并且没有相对的治疗措施,所以治愈率低,致死率高,易引发民众的恐慌。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疾病斗争史,当疾病进入电影领域,疾病的书写就被赋予了政治、文化和审美的意义。疾病书写在电影中,成了连接故事人物、隐喻电影主题、推动矛盾发展的推动器,同时也呈现出具有一定规律的表征与特点。首先,电影艺术的疾病书写从精神和身体两个维度进行探求与表达。其次,电影的疾病书写隐喻时代的社会性问题与矛盾。如《传染病》(美国,2011)讲述了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的故事,由于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病毒在不停地蔓延,最后肆虐全球。管理的混乱,人性的贪婪,导致一系列社会危机。第三,电影的疾病书写连接历史的反思与未来的希望。疾病肆虐、战争残酷、权力纷争、科技狂欢等,都让人类承受不可承受之重,而始作俑者往往是人类自己。电影通过对人类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压抑的疾病书写,展现其苦难画卷,叩问其文化根源。
(二)多元的叙事方式
1.个体叙事
病原体叙事即交代疾病产生的原因。在韩国影片《流感》(金成洙,2013)中,疾病来源于偷渡者集体死亡的集装箱,唯一的幸存者成为“超级传播者”,他携带病毒四处逃窜,造成疾病的大范围传播。《卡桑德拉大桥》(意大利,1976)里的鼠疫病毒来自国际卫生组织的意外泄露,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保人员打斗过程中意外感染鼠疫病毒,一人被抓、一人携病毒逃至火车上,由此拉开了故事的序幕。《感染列岛》(日本,2009)中菲律宾暴发禽流感,人们私自离开疫区,为病毒在日本甚至在全球的传播埋下隐患。这类书写疾病的影片对作为病原体的个体,以及初感染者进行了详细的交代,这也是故事的起因。
2.英雄主义叙事
英雄是灾难电影的叙事核心,英雄给电影和观众带来希望。灾难中的人民需要来自集体和权威力量的拯救,当求助无门时,普通人(自愿或环境所迫)便化身为英雄人物出场,这类影片通常以英雄的身份来完成人物的建构,影片结构也围绕其展开叙事。例如《卡桑德拉大桥》中的男医生,当他得知火车上有鼠疫病毒时,他没有设法脱身,而是临危不惧地提供帮助。他带领人民反抗列车上的守卫,炸断车厢挽救了几节车厢中人民的生命。
3.矛盾叙事
矛盾冲突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矛盾双方间的抗衡制约丰富了戏剧效果。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对抗、官僚之间的互相抵触、人性善恶之间的对立通常是这类影片着重刻画的矛盾冲突。如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医生和上校,一位是富有人道主义的医生,一位则是直接受政府指令的军官。当医生发现高浓度氧气可以治疗鼠疫,可以挽救火车上被感染者时,毅然主张上车救人。而上校仍谨遵上层命令“过桥”(意外坠毁),用整列火车上人民的生命去掩盖“美国在日内瓦研究生化武器并导致其泄露的罪行”,这不仅是关于疾病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流感》中,疾病在整个盆塘市蔓延,而对整个国家的人民来说,盆塘市民只是少部分群体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构成了利益的对立。当盆塘的疾病还没有对全国其他地区造成威胁时,韩国民众封锁盆塘的意向为35%,当病毒在盆塘蔓延开来后,盆塘市民四处逃离,韩国民众封锁盆塘的意向上升为96%。除了市民群体的利益冲突,影片中的总统和总理所代表的势力也体现了官僚之间、国际政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影片的走向扑朔迷离,推动事件达到高潮。
二、疾病书写的向度与隐喻
“疾病是整个世界的象征和重大隐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出,任何一种疾病只要是起因不明,治疗无效,就容易成为隐喻的对象。人们在谈论疾病时常常使用隐喻化的思维方式。“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电影中对疾病的书写,超越了它本身的生理病象与医学意义,成为了关于个人、社会、国家以及人类等诸多问题的隐喻。
(一)主体向度:人性道德的试金石
在灾难来临时,个人所追求的是生命的延续,在疾病面前个体生命权是最大的利益追求。疾病不仅会带来身体机能的损伤,也会在人类的精神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痛楚。正如苏珊·桑塔格在谈论癌症的隐喻时说道:“反映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并非无根据的恐惧”。疾病会带来人们关于生存和情感的焦虑,当人类处在灾难的漩涡中的时候,人性的善恶就会暴露无遗。电影《流感》中,政府以地上的黄线将人性的善恶撕裂给银幕前的人们看。疫苗研发人员仁海的女儿不幸感染了流感,为了加快疫苗研发的进程,军队将她的女儿绑架拐走,以此来威胁她尽快研发出疫苗拯救这个城市。反观,小女孩美日和她的妈妈虽然被黄线隔开,但她们都怀揣着真善美的初心,不顾一切地双向奔赴。当仁海被子弹打中肩膀,血流不止时,美日张开了自己小小的身体挡在妈妈面前,哭喊着恳请警察不要开枪打她的妈妈,整个画面静止,暴动的人、武警、总统都被她的行为所感染,这就是人性至善的力量。电影《非典人生》的故事发生在非典爆发时期。林韦皓是一线护士,她顶住巨大的压力奔波在疾病的前线,与疫情暴发就想逃跑的医生陈俊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灾难面前,人性被置于太阳底下暴晒,那些闪闪发光的就是至善至美。
(二)现实向度:社会生活的回响曲
“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身体上的疾病反映着世态生活的凉薄与污浊,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密切相关,蕴含丰富的文本内涵。
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社会网络更高节点的行动者会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反之则将限制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差异,导致在对抗疾病时有不同的方式和结果。在《传染病》中,美国疾控研究中心主任老黑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了解到疫情正在蔓延,重灾区芝加哥即将被封锁,于是他让妻子离开芝加哥,脱离疾病所带来的困境。在疫苗研发生产之初数量不够,全国上下通过摇号领取时,老黑和妻子利用职业之便,跳过摇号这一环节,直接注射了疫苗。相比之下,等待摇号的清洁工家庭便没那么幸运,只能在漫长无边的等待中期待死亡来得不那么快。灾难之前,阶级差异只表现在生活质量上,灾难之后,阶级差异则表现为生与死的鸿沟。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国,2018)的角色说出“世界上最难治的是穷病”,由金钱、权力和地位带来的差异是不同人命运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影片叙事中的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健全的医疗卫生系统和社会体制,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这些看似“健全”的体系显得不堪一击。领导阶层也同样脆弱不堪,错误预估危机,没有及时做出相应的决策,疾病袭来,民众生命岌岌可危。电影《流感》中医疗专家向政府报告疫情情况,建议及时防控,政府以防止恐慌为由忽略了医疗专家的意见,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导致疫情不可遏制地在盆塘传播。当地领导实施错误的防控措施,让民众集中隔离,交叉感染导致数量成倍地增加,疫情蔓延,最后不可控制。
在这类影片中,由于体制和体系的不完善,民众生活在动荡的社会中,部分人精神空白、缺少自我判断能力,舆论被有心之徒操控。恐怖源于未知,人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信息,在网络的作用下,谣言就像传染病一样扩散。《传染病》中的记者艾伦,散布关于疫情的言论,包括阴谋论、神药论(连翘)等,从而建立利己的话语权并从中盈利。一方面虚假传播疫情的发展状况,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另一方面动摇了民心,导致民众极度恐慌,造成精神危机。舆论是一个风向标,是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确的舆论导向会安抚民众,减小疾病防控的难度,反之将会引发民众的恐慌,给救治工作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增加疫情防控的难度。
(三)意识形态向度:政治色彩的反射剂
隐喻使疾病失去了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的本来面目,被附上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道德和社会文化意义。桑塔格剖析了疾病隐喻背后的政治修辞色彩:“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电影《传染病》的结尾揭开了贯穿全片的悬念:东南亚的香蕉林被伐,惊飞了蝙蝠,蝙蝠之粪被猪误食,香港餐厅本地的厨子处理生猪头,没有洗手就和美国某公司女高管握手合影,于是病毒由女高管扩散至全球。这条线索的处理是典型的西方视角,充满着东方主义的隐喻:病毒源自动物,亚洲过度的经济活动侵占了生物的栖居地,以及东方人备受争议的烹饪和饮食习惯。“原罪”叙事,几乎是这类电影的主流框架。从早期希区柯克的《鸟》(1963)到索德伯格的《传染病》,西方电影对病毒的溯源,不断在深化演进,但始终没有脱离人们对瘟疫的认知,当然,更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偏向和影响。在早期商业片的逻辑里,“动物即恶”这是最简单的表达。自从八千年前,人类学会驯服动物开始,瘟疫就和人相生相伴,除麻疹外,疫、猪瘟、禽流感和蝙蝠,致命病毒无不和动物有关。
(四)共同体向度:命运与共的共鸣语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学院发表演讲时说,“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疾病面前不分国家、种族、肤色,全人类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全球人民必须同心协力同呼吸共患难。《流感》中的美国指挥官试图干扰韩国的疫情指挥,企图炸毁盆塘市达到彻底消灭病毒的目的。这种自我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思想违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同住一个星球,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集体,只有互相帮助共同战胜病魔才是最佳方案。《惊心动魄》(中国,2003)被称为“中国最为真实的灾难电影”。影片讲述在2003年的春天一段封闭的列车空间中,此时传染病肆虐全国,而一名疑似病人突然失踪,当列车上出现危机的时候,列车长一声令下,那些普通的乘客便挺身而出,加入救治队伍。灾难和疾病在患难与共、互相救助的人类精神给观众带来了灵魂震撼和洗礼。小到一个家庭,大到全人类,在疾病面前,我们是永远的命运共同体。
三、疾病书写的美学指归
疾病超越了具体的生理病象与医学意义,因此电影中的疾病不仅仅是对真实疾病的客观反映,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美学等方面的意义。学者叶舒宪说:“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
(一)隐喻与修辞
作为修辞方式之一的隐喻通常意义上是用某种事物、特性或行为的词来指代另一种事物、特性或行为。电影中的疾病叙事不仅与身体的脆弱、命运的不确信、生存的艰难相联系来展示现实的焦虑,同时也形象地将人性的善良和质朴刻画出来。疾病从产生到治愈,社会生活从平静、混乱到平静,这不是一个首尾相连的循环怪圈。疾病过境后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初的社会,而是经过灾难洗礼后又得以重生的社会。
面对灾难,政治制度往往和个人的利益和生命息息相关。《流感》中的政府和民众分成两派,政府想隔离,民众欲逃生,如果要“选择更重要的大韩民国”,就要舍弃“20万人”的盆塘市。政府可以隔离病毒,但不能隔离爱,不能剥夺人民生存的权力。灾难和疾病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的存在不是耻辱,而是经验、教训。纵观疾病书写类型的电影,《流感》中集装箱里的集体死亡、《极度恐慌》(美国,1995)里非法捕捉的猴子、《感染列岛》里原始生活的菲律宾小岛……不规范的生活习惯成为滋生病毒的摇篮。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依生”到“竞生”再到“共生”,证明了人类必须要和大自然和谐共生,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不侵犯自然以及其他生灵,才能构建和谐美好的生态系统。
(二)人性与身体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承担着记录时代、讴歌时代的职责与使命。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电影应该如何书写现实?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表示,灾难电影在现实与想象中营造视觉奇观,同时反思现实,询唤人性回归,彰显人性关怀,而且通过主人公面临“救己与救他”“崇情与尊法”等剧情矛盾时的抉择,让主人公在“为他”“为情”“为集体”的行为选择中凸现人性的光芒,阐释爱与责任的价值,表达人类内心深处最单纯、最耀眼的品质。书写灾难,不止于呈现灾难本身,而是透过灾难去向每一位观众反映背后的深意,或是敲响保护生态的警钟,或是展现那些人性的光辉和感情的力量。
人性在灾难面前会面临选择,身体作为肉身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在以疾病为主题的电影的特定场景中显现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身体的肉体性表现为它的欲望”,疾病题材电影着重体现了人的生存欲望,“但欲望由于对所欲的渴求实现便使自身变成了身形成身体的外感觉,如视听和触摸等”,人们用各种方式争取生存,或正义或邪恶。直面死亡状态的人剥离了社会属性,留下了原始的肉体性,为争取肉身的完整会做出有违人类社会法则的斗争,弱肉强食成为生存的唯一法则。当肉体性成为身体的主宰,国家通常就会陷入瘫痪、暴乱之中。因此“身体”作为一切的基点,它的健康完整满足了生存的欲望,才有其他的发展可谈,“我们可以说,身体美是自然美的顶峰,是社会美的载体,是艺术美尤其是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美的中心”,身体的美融合了欲望、社会、艺术、自然,在灾难境遇下它们的制衡散发着人性的复杂之美。
结语
疾病作为电影的主题选题之一,在疾病书写和叙事模式方面呈现出相似的表征。同时以疾病为题材的电影也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身体作为“符号”便超越了疾病的表征现象,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问题关涉起来,以隐喻的姿态反思当下的社会问题,引发全人类社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