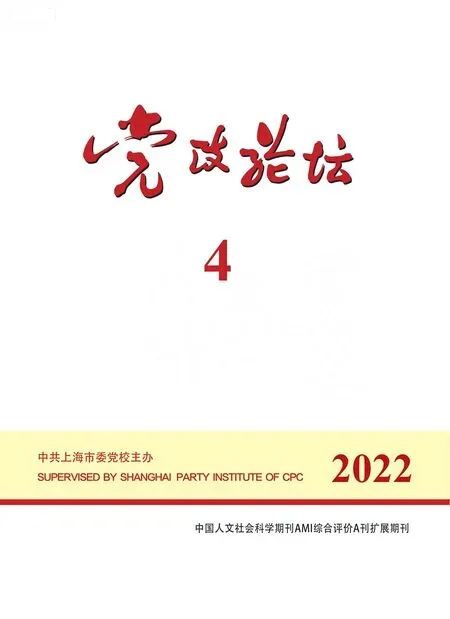陈望道同志革命履痕新考
——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浅析
○周 晔
陈望道(1891-1977)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经担任党的早期组织劳工部长(又称工会部长)、《新青年》杂志和《民国日报·觉悟》等进步刊物编辑,还受党组织的委派担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务。
(一)
1956年时为复旦大学新闻系青年教师的宁树藩和1963年与宁树藩同为新闻系青年教师的丁淦林两次就建党前后革命报刊的宣传情况访问陈望道,并把两次访问记录合成《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以下简称:《谈话纪录》)一稿,在1980年第3期《复旦学报》上发表。对这两次访问,特别是1963年3月18日这次,宁树藩教授后来回顾道:“所谈范围已大大超过我们的提问,很多涉及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艰难经历以及和各种反动派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拼搏的情况”“学界有较好的反响”,许多相关党史研究文献均引用了该《谈话纪录》。
2017年12月5日,复旦大学中文系卢康华同志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撰写了《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一文,全文发表了一份由马曼荪、沈恒春、张廷钰三人访问、沈恒春整理的《陈望道访问记录》(以下简称:《访问记录》)。“该份记录写在20×15绿格稿纸上,共九页。从纸张、笔迹到一些特殊的简体字、异体字再到具体内容,皆可判为一手的旧档案无疑”“(《访问记录》)包括四个部分,计两千三百余字,虽叙事较为简略,仅是谈话要点而已,但时间跨度从1920年至1949年,基本涵盖了陈望道解放前参与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所涉人物与事件颇为丰富”。
关于这份记录的时间,卢康华同志经过几层逻辑考证认为,《访问记录》原稿所记访谈时间“1951年1月16日”应为沈恒春等人“誊抄时笔误所致”,推测该稿可能的年份应是1958年或1959年。笔者查阅了该年代与陈望道相关的文献发现,《党史资料丛刊》收录的《党的建立时期情况》一文第一部分,即“(一)”的内容与《访问记录》前五分之一、即“关于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内容完全一致,其注释①写明:(一)为“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工作人员访问整理摘要”,故而可以判断,原稿中的“1951”系“1959”之误,访问人在记录摘要发表时,予以了更正。据考,《访问记录》的整理人沈恒春同志当时就是上海市委党校的教师且从事党史教育,1979年1月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年8月,调入当时新设立的上海史研究室,后任该室主任,1987年离休。访问人之一的张廷钰时为复旦大学学生,1961年毕业后曾在重庆大学任教,后任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2021年6月去世。这样一来,整理人的身份与其中一位访问人的在校时间又佐证了上述考证。
卢康华同志将其新发现的《访问记录》与《谈话纪录》作了初步比对,“可发现后者是前者第一部分(笔者注:即关于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扩展版,对一些人物、事件的回忆,更为具体”“但新见访问录中回忆此阶段事迹,也并非没有逸出的内容”,但囿于篇幅等原因,未展开论述。一般认为,重要史实亲历者若干年后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回忆,一是事件本身比较重要;二是记忆中的细节对当事人自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其经历该历史事件的重要履痕。因此,本文相关部分亦采用两篇访谈记录相比对的方法,重点考察新发现《访问记录》的一些新细节。为了时间跨度的同步,本文考察的历史事件主要聚焦在1920年春首译《宣言》至1930年5月中华艺术大学被查封这十年,其他时期内容略加引证分析。
(二)
比较两篇访谈记录,都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党的刊物、《宣言》首个中文全本和主持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校务作为回忆的重点,它们构成了望老参加革命的“重头戏”。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访问记录》提到,“不出10个人参加,后来施存统、施复亮等也参加”。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卢康华同志的文章中,专门指出“施复亮与施存统为同一人,此处错误,当是访问人疏忽所致”。笔者认为,此处应无谬误,当是陈望道同志有意为之,且名字间用了“顿号”,也就是说的同一个人,但把此人曾用名和现用名一并讲出,便于日后读者知晓,根据望老与施存统的师生情谊,是绝不会有此类“疏忽”。此一段陈望道有意指出1920年5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一套正规的入会手续”,并解释“因为环境关系”,又补充道:“也还注意了解的。”这显然与《谈话纪录》中关于这一组织的松散性质是吻合的,且在后者中,陈望道补充道:“研究会吸收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后来就严格了。五、六个人比较机密,总共不到十个人。以后把邵力子也吸收进来。邵力子是国民党员,怎么办?当时有争论。经过讨论,大家同意用跨党的办法。”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并不满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样相对“松散的研究性社团”,而是致力于建立组织严密的列宁式政党,于是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值得一提的是,《谈话纪录》中,陈望道表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结构,有书记,陈独秀就是书记。”将研究会与党组织视为一体、只是内外称呼的差异,显然不够准确。但就在那年夏天,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秘密成立。由于研究会与党的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前后差距不大,且确实经历了“起初比较宽”到“后来就严格”的过程,这就不难理解,经过严格规范的“研究会”在望老心中就是“共产党”了。
第二,关于负责《新青年》《觉悟》的编务。《访问记录》中强调,《新青年》是“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宣传阵地”,“游击”阵地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进一步表明了陈望道在主持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办刊思想,即“主战场”与“游击战场”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利用各自优势、特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传播力和引导力。在后来的《谈话纪录》中,陈望道详细回忆了担任《新青年》执行编辑的细节,并对《觉悟》的“游击”阵地地位,作了补充:他通过邵力子把《觉悟》“拉进来”“发表文章转弯抹角地批驳《民国日报》的社论”“《觉悟》还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主要是中学以上学生写来的,提出青年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对于青年学生提出的改革要求和罢课行动,我们是坚决支持的”。《访问记录》中此段有一处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直指当时《觉悟》的“对立面是张东荪的《时事新报》”;《谈话纪录》中,则对斗争策略、方式、举措进行了具体论述。《觉悟》在当时的社会各基层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正张人家不要看,都要看副刊”“《觉悟》起先附在报上,以后印成单张,独立发行,可以零卖,每期印几万份”。对此,宁树藩同志后来补充道:“《觉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着意发表系统性专论,而是注意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探讨与争论中精心阐发,参与者大多为学校师生和知识青年,文字朴实,通俗易懂。《觉悟》又是天天出版的副刊,其对社会影响之大自可想见。《觉悟》副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约50篇(语言文学类除外),这种情况过去未见。”要指出的是,与张东荪、陈布雷等的斗争,如同陈望道与胡适关于《新青年》主导权的论争一样,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的论战、是社会主义同反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觉悟》的“游击战”,陈望道等党的早期组织骨干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谬论,坚决地捍卫了这些刊物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第三,关于首个中文全本《共产党宣言》。首译《宣言》是陈望道为民族解放振兴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在《访问记录》中虽然篇幅不长,但十分重要:“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三、四月间,以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的。(初版本在张静庐处可能有)”。虽然只有短短一句,但将首译《宣言》的时间、时长,特别是参考的底本予以了强调,这也足以廓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模糊之处。陈译《宣言》的底本系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详见鄙人与何若伟拙文,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提出的是,陈望道在《访问记录》中首次披露初版本《宣言》可能的拥有者:张静庐。张静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新中国成立后,在出版总署任处长的张静庐高度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勠力搜集近现代出版史料,并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在辑注该书时,张静庐指出“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一九二〇年四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书中该段落还收录了1920年9月再版的陈译本《宣言》(俗称“蓝本”)的封面,张静庐标注为:“同年九月初版重印本书影”,并由此推测初版(笔者注:也就是错版、俗称“红本”)出版于1920年4月。陈望道同志一方面与张静庐早年就有来往、彼此相识,另一方面也会注意到该史料与《宣言》初版本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其赫然印有“蓝本”的书影,因而同访问者提供上述线索;《访谈记录》第四部分,“关于文物和访问线索”段落,再一次提及“文物还可以向一些收藏家去访问征集,如北京的张静庐”。事实上,直到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向陈望道询问《宣言》的初版本时,望老对其确切下落还一无所知。
第四,关于党领导下的上海大学。《访问记录》中,此段开宗明义指出上海大学“于右任挂的名,实际上是党办的”,对该校的办学性质、定位讲得很清晰直白。该记录指出,(上大)“开始在西摩路一个三层洋房里,五卅运动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时有一个大幅标语从三楼悬挂到楼下”。大革命时期,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前沿,围绕工人运动主导权的问题,一开始共产国际与我党就有分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翼”,而我党领导人张国焘认为,中共现阶段即使将国民革命视为自己主要的奋斗目标,但也不能将党发展成为国民党的左翼势力,因为工人运动应有中共独立领导。我们党接办的上海大学能够成为“五卅运动的指挥部”,是1925年1月中共四大作出在上海等新式产业发展的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将国民党的工会改造成“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工会”等一系列决定的结果,是我党争取工人运动独立领导权的重要证据之一。“指挥部”一词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大学在我党领导五卅运动中的地位,“指挥部”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上海大学师生“对五卅当天的行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部署”。据该校党支部书记高尔柏回忆 :“五卅时的游行、演讲由恽代英、侯绍裘和我们一起布置,分小组指定地点活动,每组8至9人。当时,南京路中心地段,由‘上大’负责,到处可以见到‘上大’的学生在向群众演讲。传单由我与黄正厂(附中国文教师,党员)一道拟写,侯绍裘指导,内容基本有两条:一为揭露顾正红被害真相,二为打倒帝国主义”。5月30日当天,学生们拿着这些传单在南京路上广为散发,力图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广到社会上去,“学校的组织分工有通讯队、救护队、敢死队等,敢死队的任务是到各大马路上宣传演讲”。根据这一指挥部署,全市各校三千多名学生到南京路等上海主要马路演讲,指挥部虽设在望志路(今兴业路)永吉里34号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但由两位上大骨干“恽代英(时任团中央委员、《中国青年》主要编委之一)和侯绍裘(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和教育委员)实际指挥”。上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连他们都这样记录道:“鼓动此次引起扰乱之学生或学童皆来自过激主义之大学——即西摩路之上海大学。”1923年秋,陈望道初到上海大学任教就出任学校最高议事和行政机构的成员、中文系主任,1925年4月和次年3月,共产党员邓中夏和恽代英先后调离上海大学,陈望道则接任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的职务。五卅中,陈望道始终和师生们战斗在一起,发挥自己的重要影响,因而他能清晰地记得“当时有一个大幅标语从三楼悬挂到楼下”。关于陈望道对于上海大学的历史功绩,《访谈记录》关于文物和访问线索段落提到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乐嗣炳同志(亦是著名语言学家,曾在上海大学任教)曾评价说:在望道教授领导下,上大学生已经锻炼成既是最勇敢的革命战士,又是最勤奋的好学生”。
此后,上海大学搬迁至青云路继续办学但又一次被反动当局查封、再到陈望道于江湾购置房产、重新复校,宁树藩同志在后来《谈话纪录》的回顾文章中,进行了详尽地描述:“6月初,英帝国主义施行武装占领,陈巧施妙计,用金钱收买警察,将学校设备全都迁至临时新址,并亲自起草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为免遭帝国主义迫害,他还四出勘察,筹措资金,于1927年春在江湾西镇建立新的校址。这是对上海大学的又一重要功绩。”这里,提及了陈望道为上大江湾重建筹措资金,乐嗣炳曾有类似的记述:“经过党和各方面的努力,一九二六年筹集了三万多元的基金,望道教授在江湾镇西边,设计建筑上海大学自己的校舍。”《访谈记录》进而补上了一处宝贵的细节——“孙中山先生也捐了一部分”。根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同志研究,孙中山一贯热心扶植上大。“1923年2月,他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亲自批示每月拨款资助上大。为筹募经费,同年8月,上大特设校董会,孙中山为名誉校董。”“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谈判途经上海时,上大和全市学生到码头热烈欢迎。上大学生返回时,在嵩山路法国巡捕房附近,巡捕竟将上大校旗夺走,并不准通行。大队学生和无数市民奋不顾身直奔莫利哀路中山寓所,谒见孙中山时,学生高呼反帝口号。经孙中山严厉抗议,百余名武装巡捕不得不让学生自租界返家。以后,也不得不将校旗归回。”由于孙中山担任名誉校董并定期出资捐助,再加上“夺旗事件”,作为当时上海大学行政管理者之一的陈望道记得前述细节,便在情理之中了。
第五,关于担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关于中华艺术大学,已是《谈话纪录》的结尾,望老指出:“中华艺术大学的文学系是党办的,图画系的面貌则不同”,对此宁树藩同志在回顾《谈话纪录》时进一步提到,中华艺术大学的前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上海艺术大学,负责邀请陈望道出任中华艺大校长的则是中共地下党闸北小组成员冯雪峰和夏衍。“陈主持学校的全部校务,是在冯、夏积极关心和推动下开展的”,而他们的一些党务工作和筹备“左联”等活动,也常在艺术大学进行;在《访谈记录》中,则言:“1927年,‘上大’被封后,这个形式也不行了,就利用别的形式。如办了中华艺术大学”。所谓“这个形式”应当指的是直接领导组织和参与革命暴力活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利用别的形式,则是望老自述的“参加文化教育工作”,团结文艺文化界的左翼人士,用手中的笔继续与我们党站在一起,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
(三)
《谈话纪录》发表31年、宁树藩和丁淦林同志访谈陈望道近50年之后,宁树藩同志总结望老的这些革命履痕说,即便是“退党后开始进入的文化教育工作阶段”“其一,在上海大学,他所接受的是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其主要工作都是由党安排的。其二,虽然担负着提高学术文化的重任,他在上海大学还开设了一些课程,但主要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这段论述高度凝练了陈望道同志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从党的“二大”之后退党到 195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三十四年,陈望道身在党外,但坚定恪守“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的诺言。陈望道早年曾表明心志,“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晚年他仍对中国新闻社记者说,“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这一点,在新发现的《访问记录》中也得到了佐证。访问中,陈望道单独讲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建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大学教授联合会”(简称大教联)并担任主席,在大力推动师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中的一件往事,从而多次强调,“凡事必须有党的领导。任何一点点成就,都是党领导的结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学生的反饥饿斗争中,大教联决定不参加,以免束缚学生的行动,同时避免反动派找不到学生而打击大教联。但是学生不明真相,敌人又从中挑拨,以致关系紧张,情况复杂化”。陈望道强调,亏得有党的统一领导,“就迅速消除了误会,解决了问题”。可见,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这一信念在陈望道心目中从未改变过。
此外,两次访谈讲到与敌人展开斗争的策略时,陈望道总表现得饶有兴致,甚至“有时,还略有一点激动的感情”。例如,在《谈话纪录》的《附记》中,宁树藩、丁淦林同志回忆:“在讲到和《时事新报》作斗争的时候,他忽然从坐椅上站起来,做着手势以加深人们的印象。”《访问记录》中望老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的部分也十分精彩。例如,讲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还以嬉皮笑脸的小品文来模糊革命意志……我们(陈望道、胡愈之、鲁迅等)就以小品文对小品文,编辑出版《太白》,作为阵地,和它们作尖锐的斗争。同时也利用报屁股——报纸副刊作为‘游击’阵地。”“国民党对出版检查很严,斗争也很尖锐。《太白》中好几篇文章是骂检查狗的。为了应付检查,不被看出作者笔迹,我们是排好清样送去。被删之处……用删节号代替”。又如,抗战时期、上海苏州河以北沦陷以后,“(我们)在大新公司楼上开语文展览会,陈列自古至今的文字,进门就有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有岳飞的‘还我河山’四字的碑帖,观众一看就心里有数”……这些都体现了陈望道卓越的斗争本领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卢康华同志新发现并公布的这份《访谈记录》,还原了陈望道同志从事革命工作以及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宝贵细节,彰显了望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英勇斗争、对党忠诚的精神,它们也是党的先驱们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缩影。习近平多次讲述陈望道同志追求真理的故事,2020年6月27日,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中,高度评价陈望道同志为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访谈记录》中不少细节,恰恰是对这一重要论述鲜活的注脚。这份新发现的访问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的理解,对于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也有积极意义。
①⑦⑰⑲㉒㉓ 宁树藩:《陈望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一稿的回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 期。
②④卢康华:《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 年12 月5 日。
③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一辑,第29-30 页。
⑤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 页。
⑧周晔、何若伟:《〈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的重要细节》,《浙江日报》,2020 年6 月29 日,第7 版。
⑨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7 页。
⑩张静恬、应悦:《重温陈望道与中共领导人的故事》,《义乌商报》,2018 年7 月8 日,第1 版。
⑪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 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版,第293 页。
⑫ ⑮ 邵雍:《上海大学师生与五卅运动》,《都会遗踪》,2020 年第4 期,第21-22 页。
⑬ 高尔柏:《回忆上海大学及其他》,载《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 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1 页。
⑭ 丁郁:《我在博文女学、上海大学等校的经历以及赴苏前后的活动》,《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 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7 页。
⑯《会审公堂记录摘要》,《东方杂志·五卅临时增刊》,1925 年6 月9 日。
⑱ ⑳ 乐嗣炳、杨景昭:《怀念陈望道教授》,《陈望道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31,30 页。
㉑ 任武雄:《在帝国主义虎穴中奋斗的先锋队——记上海大学的光辉历史》,《上海党史研究》,1997 年第5 期,第33 页、35 页。
㉔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