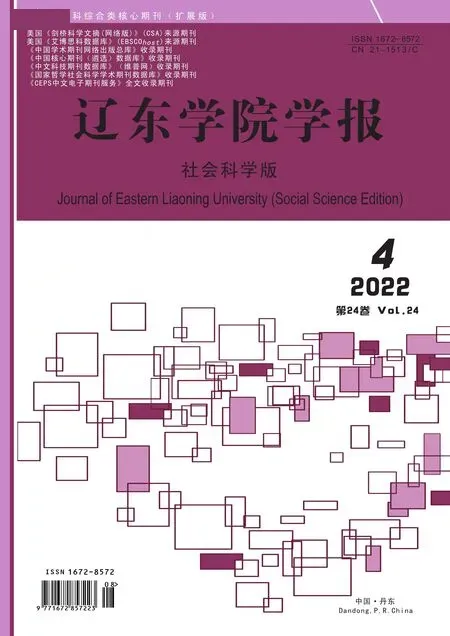元明之际唐赋批评之演进
——以“律赋非赋”与“唐无赋”为中心
姚 奎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有唐一代,辞赋创作极其繁荣,正如清王芑孙所谓:“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1]140。遍检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唐以赋名篇者共1 671篇,作者583人。由此观之,唐赋数量堪与唐前辞赋总量比肩。即便如此,唐赋自其产生便争议不断,至元明甚至出现“律赋非赋”与“唐无赋”说,唐赋自身价值受到严重挑战。历来对李梦阳“唐无赋”论的关注,遮蔽了元代赋学观念对明代的影响。从“律赋非赋”到“唐无赋”的理论演进,批评对象从律赋发展到整个唐赋,其实质是明人承续元代赋学观念的自然结果,亦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流行和祖骚宗汉观念的内在驱动。
一、雕虫微艺:“唐无赋”论的唐宋先声
赋的声律化是赋体文学在形式上的一种演变,《文章辨体》对于律赋的解释是“律赋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题,每篇限以八韵而成,要在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迨元代场屋,更用古赋,繇是学者弃而弗习”[2]55-56。曹明纲认为:“律赋是唐代在齐梁骈赋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统治者对人才选拔与甄别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演进和发展与骈赋的关系最为密切。”[3]115赋的声律化比诗稍晚,完成于初唐,形成律赋。律赋在形式上比骈赋更加严格,除满足骈赋的特点外,还有限韵的要求。因此尹占华认为“律赋就是限韵的赋”[4]前言。律赋的理论基础是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其后徐陵、庾信等人的“隔句作对”进一步强化了律赋的理论支撑,固此,唐宋才能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制定以律赋取士的科举政策。
律赋文体的形成与“律赋”一词的产生并不一致,唐人一开始称律赋为“甲赋”“试赋”抑或“新体”,其中以“试赋”最为常见。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谓:“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5]356-357“试赋”本义为“考试之赋”,乃是士子入朝为官之利禄津梁。因应试之赋皆依韵律所作,所以试赋也称律赋。而“律赋”之名最早可追溯至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其“好知己恶及第”条提到郑隐“少为律赋,辞格固寻常”[6]96。王定保虽是五代人,但他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而唐王朝灭亡于公元906年。可见“律赋”一词至少在晚唐时已经流行。作于中唐时期的《赋谱》一书中提到:“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若《登楼》三段,《天台》四段之类是也。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7]13作者从辞赋作品的段落出发,将“新体”与“古赋”对举,且“新体”赋分头、项、腹、尾四段,每段字数相对固定,颇类近体诗的整饬与严格。故此,清人周中孚在《郑堂札记》中说:“唐人称应试之赋为甲赋,盖因令甲所颁,故有此称,以别于居恒所作古赋”[8]5。
律赋是限韵之赋,然韵之多少并无定数。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试赋用韵》云:“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有三韵者,如《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有四韵者,如《蓂荚赋》以“呈瑞圣朝”为韵;有五韵者,如《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有六韵者,如《君子听音》;有七韵者,如《五声听政》;有八韵者,如《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唐文宗太和以后,主要以八韵为主,分为二平六侧、三平五侧、五平三侧、六平二侧、四平四侧[9]375-376。总体来说,唐代律赋的平仄押韵较为灵活。至宋代律赋限韵更为严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春正月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10]393。即韵若是一平一侧相间,必须按照韵字的顺序押韵。王栐《燕翼诒谋录》亦云:“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11]48因此,四库馆臣评价宋代试赋“拘忌宏多,颇为烦碎”“苟合格式而已”[12]1736。
唐宋律赋与科举的紧密纠葛,招致众多文人批评。中唐时期,权德舆与柳冕就曾讨论过科举试赋存在的问题。柳冕《柳福州书》谓:“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阁下岂不谓然乎?”[13]625故权德舆于《答柳福州书》答:“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13]628权、柳二人批判试赋取士制度的弊端,反对绮靡雕虫和形式主义,倡导务实文风,以治国之道作为考试内容而取贤纳士。此后,舒元舆在《上论贡士书》中再次以“雕虫”论律赋:“今之甲赋律诗,皆是偷折经诰,侮圣人之言者,乃知非圣人之徒也。……试甲赋律诗,是待之以雕虫微艺,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之道也”[14]7487-7488。律赋辞藻绮靡,雕镂过甚,形式以对仗工稳为美,题材以儒家经典为务,成为了经学的空洞注疏,被认为是“雕虫微艺”。
不仅如此,还有士子在行动上表达对试赋制度的抨击。杜牧于《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记载:“进士李飞自江西来,貌古文高。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飞曰:‘如是选贤耶?即求贡,如是自以为贤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径返江东。”[15]743律赋在体制、题材、内容、音律上的种种严格制约,导致当时士子大为不满,质疑此种制度是否能选贤任能,因此,李飞一怒而抛弃功名利禄,是对试赋制度的极大挑战。
北宋姚铉《文粹序》中对唐代律赋也颇为不满:
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尔,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得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类相从,各分首第门目,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16]自序
唐宋以诗赋取士,故《甲赋》《赋选》《桂香》等律赋选集颇受唐宋士子欢迎,一如当今之“高考作文选”和“申论范文选”,然此类“干名求试”之律赋,以雕篆为工,侈言蔓辞,与两汉、三代之文,直不可以道里计,并不能作唐贤诸人文章之典范。故姚铉以“复古”自命,选唐贤诸人符合“古雅”“古道”之文,汇为《文粹》,文粹者,文章之精粹也。因此,姚铉选赋以古体为主,律赋一律不取,且将古赋列为目录之首。
李廌《师友谈记》记载与秦少游讨论律赋创作心得:
少游言:“赋之说,虽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观少游之说,作赋正如填歌曲尔。”少游曰:“诚然。夫作曲,虽文章卓越,而不协于律,其声不和。作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尔。”[17]21
李廌将作律赋与填词作曲类比,表明律赋与文章之分离。律赋创作追求的是“协律”和“偶俪”,而不是“文章卓越”。故宋人与唐人一样,对于律赋取士制度多加质疑。刘敞在《杂律赋自序》中也表达了对试赋制度的不满:“当世贵进士,而进士尚词赋,不为词赋,是不为进士也;不为进士,是不合当世也。君子何亟乎合当世?曰:不得已焉耳,得已,则君子必不赖也。”[18]208但律赋是士子进入仕途的唯一选择,不得不为。因此,强至《送邵秀才序》中说:“予之于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此进取,既得之,方舍而专六经之微,钩圣言之深,发而为文章,行而为事业,所谓赋者,乌复置吾齿牙哉?”[19]509由此可见出唐宋士人对于律赋之态度,不过仅为利禄津梁而已,一旦入仕,则弃如敝屣。
曹丕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然律赋严苛的限韵要求、平仄对仗的属对拘束、经义为题的内容制约,导致其与文章功用产生巨大的割裂。文人对律赋的“雕虫微艺”之讥,恰是对律赋功用缺失的清醒认识和历史反思。文章之功用,不仅在于经国理政,还在于为国选材,然律赋制度限于种种弊端,并未发挥其正常的职能。唐宋文人对试赋制度的反动与挑战,预示着律赋取士制度在后世的退位与消亡,也是元明“律赋非赋”与“唐无赋”观念产生的先兆。
二、律赋非赋:元代科举视阈下的试赋批评
元朝为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算起,国祚160余年。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转变,使元朝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中书省上表言科举事:“‘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20]58。紧接着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20]58史称“延祐复科”,延祐元年(1314年),全国举行乡试,试古赋。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从唐朝开始的科举试律赋传统,到此中断。明代试八股,一直到清代翰林院试律赋,律赋才重新纳入朝廷考试中。元代科举分为“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其考试内容亦不相同。前者不考词赋,“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20]59。因此,古赋作为科举考试科目,直接引领了元代辞赋创作的风向,古赋与律赋之辩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元代科举试古赋,官方诏诰亦用古体,文坛亟需对前朝科举之律赋进行价值重估。故袁桷发其端,首提古赋的宗法问题,倡导复归汉魏;祝尧著《古赋辩体》,正本清源,祖楚骚而宗汉魏,重新确立古赋正统地位;陈绎曾首倡“律赋非赋”论,否定律赋之价值。
袁桷首先在《答高舜元十问》中回答了“古赋当祖何赋?其体制理趣何由高古?”的问题:

袁桷是元初大儒,师从戴表元和王应麟,大德(1297—1307)初,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又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等职,至治元年(1321年),迁侍讲学士。其在朝二十余年,应当参与了“延祐复科”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此文当是写于复科之后,回答士子高舜元关于古赋考试的疑虑。自宋祁提出《离骚》为词赋祖以后,在这篇小文中,袁桷也回答了古赋的祖述和高古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着楚辞和汉赋。袁桷为元初文人,对于晚宋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大为不满,强调诗赋创作要本于性情、不事雕琢。因此,他极力推崇楚辞、汉赋,为赋之正体,而以“柳子厚赋”为代表的唐赋则是东汉以后赋之流变,为赋之变体,袁桷这种“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念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
此后,祝尧在袁桷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古赋的正统地位。祝尧字君泽,元中期文人,延祐五年(1318年)进士,官至无锡同知,著有《四书明辨》《古赋辩体》《策学提纲》等。祝尧在“延祐复科”四年后即中进士,足见其辞赋造诣之深厚。祝尧所著,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元代科举试三场,首场为经义,第二场为古赋诏诰章表,第三场为策论。从其所著书目来看,与这三场考试一一对应,《古赋辩体》即是元代科举试古赋制度下的产物。《古赋辩体》编撰目的相当明确,即严格区分古赋与律赋的体制,向当时的科举士子展示真正的赋体文学样式。祝尧在“祖骚宗汉”观念导向下编定的《古赋辩体》,自然要将律赋排除在古赋之外。可见祝尧与陈绎曾几乎同时形成了这种崇古轻律的赋学审美倾向。祝尧以“古赋”为名,于唐、宋两朝律赋皆不入选,其对律赋态度可谓鲜明。
《古赋辩体》卷七“唐体”云:
尝观唐人文集及《文苑英华》所载,唐赋无虑以千计,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赋之体,其变久矣,而况上之人选进士以律赋,诱之以利禄耶!盖俳体始于两汉,律体始于齐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后山云:“四律之作始自徐、庾,俳体卑矣,而加以律,律体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来进士赋体所由始也。雕虫道丧,颓波横流,光铓气焰,埋铲海蚀,风俗不古,风骚不今。后生务进干名,声律大盛。句中拘对偶以趋时好,字中揣声病以避时忌,孰肯学古哉?”……是以唐之一代,古赋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22]325-326
东汉以后,赋之本义“铺陈”在赋中逐渐隐匿,取而代之的是六朝赋的骈俪和唐赋的声律。祝尧认为,唐代科举以律赋为中心,文人士子为求功名,不得不苦心孤诣律赋创作,声律、对偶、平仄进入辞赋领域,必然导致辞赋的绮靡与浮夸。祝尧引陈师道语,二人都以科举对律赋的影响为中心,强调唐代律赋“雕虫道丧,颓波横流”的历史倒退,是对唐代律赋的价值否定。
比祝尧稍晚的陈绎曾是元代重要的文论家、书法家,元统(1333—1335)间举进士,官国子助教,著有《文筌》《文式》《翰林要诀》等书。据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十六《荐吴炳、陈绎曾》记载:“江南陈绎鲁(曾),博学能文,怀材抱艺,挺身自拔乎流俗,立志尚友乎古人,放志山林,富贵浮云。但人既不自鬻,恐后日或有遗贤,如于文翰之职内,不次征用,不惟摅其素蕴,抑亦可以砥砺流俗。”[23]534陈氏立志以古人为友,在文论思想方面同样推崇复古。其《文筌序》中倡导复归三代之文,“所以六经之文不可及者,其实理致精故耳”[24]4。因此,陈绎曾同样持祖骚宗汉的观念,在《文筌》一书中只作《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
陈绎曾在《文筌·唐赋附说》中表达了自己的唐赋史观:
汉赋至齐梁而大坏,务为轻浮华靡之辞,以剽掠为务,以俳谐为体,以缀缉饾饤小巧为工,而古意扫地矣。唐人欲变其弊,而或未能反本穷源也。乃加之以气骨,尚之以《风》《骚》,间之以班、马,下视齐梁,亦已卓然。楚、汉不分,古今相杂,谓之自成一家则可,谓之追配古人未可也。其法浮其体,漓其制,杂其式,乱其格,则有绝高者,难以谱定也。因为之说,以附楚、汉赋谱之后。
鲍照、陈子昂、宋之问、萧颖士为唐古赋之祖。江淹、庾信、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为排赋之祖。唐古赋见《文粹》,排赋见《翰苑英华》。[24]104-105
陈绎曾认为汉赋至六朝,体制大坏,古意尽失,所以他并未给魏晋六朝作赋谱,反而对唐赋评价较高,认为唐赋虽与汉赋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自成一家。唐赋上承《风》《骚》,以班固、相如为法,故其能附于《楚辞》《汉赋》之后,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因此,陈绎曾在《文说·下字法》中云:“唐宋诸赋,未可轻读。有唐古赋,当读《文粹》诸赋,《文苑英华》中亦有绝佳者。有唐律赋,备见《文苑英华》”[24]211。陈绎曾对于唐赋,有严格的古、律之分,古赋可读,律赋不可读,这是其“律赋非赋”立论的前提。
对于律赋,陈绎曾提出了“律赋非赋”的观点:
右唐赋外有律,始于隋进士科,至唐而盛,及宋而纤巧之变极矣。然赋本古诗之流也,律赋巧,或以经语为题,其实则押韵讲义,其体则押韵四六,名虽曰赋,实非赋也。[24]108
陈绎曾《文筌》作于至顺三年(1332年),此后即进士及第,至正年间官至国子助教,可知其是科举试古赋的受益者。陈绎曾一生都在接受古赋教育,在其入仕前,为了科举成名,不得不习作古赋,入国子监,为国子教学,也要教学古赋习作。因此,在元代科举制度的巨大影响下,陈绎曾“律赋非赋”的赋学选择是合乎时宜的。他认为唐代律赋的创作因为科举制度的干预,以经义为题,追求押韵与对偶,已经与古赋创作迥异,不宜再将律赋作为赋之一体,只能称之为“押韵的四六文”。所以他在论述唐赋的时候,只论述了古赋和俳赋的赋制,律赋被排除。
唐、宋、元三代文人对于唐赋的批评,主要还是针对律赋而言,于唐代古赋批评甚少,甚而高度评价韩、柳诸人古赋创作。因此,陈绎曾在总结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律赋非赋”说,是历史与现实双重考量的结果。元人科举试古赋,其理论之出发点当然是古赋为先,律赋价值必然会被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非常激进和主观的。但是考虑到元代科举试古赋的大背景,以及元代帝王对辞章之学的轻慢,重功用轻辞藻的文学观念由此滋生,“律赋非赋”论自有其产生的土壤。
三、唐无赋:明代文学“复古”维度下的唐赋批评
在元代科举制度影响下,辞赋经历了古赋正统地位的确立以及对唐代律赋价值的否定。明承元绪,明代科举试八股而非古赋,因此,明代的唐赋批评主要受文学复古思潮的影响。明代文学“复古”与“反复古”此消彼长,互相纠葛,但明前中期,复古一脉声势浩大,尤其是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贯穿了整个明代,其影响波及清及近代。李梦阳“唐无赋”论即是此种文学复古思潮下的产物。
弘治时,“七子”之间相互唱和,言文必称先秦诸子之文,言赋则曰屈、宋与汉、魏之赋,言诗则谓汉魏、盛唐之诗。李贽论李梦阳文风:“弘治初,北地李梦阳首为古文辞,变宋元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宗汉魏,近律法李杜。学士大夫翕然从之。”[25]577因何景明、李梦阳二人在弘治朝文坛地位颇高,文学复古流风所及,当时文坛学士大夫欣然宗之。康海认为:“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鄠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榖、济南边廷实,……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26]505当时文坛之流弊,实乃明初台阁体与理学对诗文的影响,造成了空疏、卑弱的文风,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钱谦益因此称杨士奇为“太平宰相之风度”[27]162,即便李东阳倡导重振文风,但也不免受其陶染。
嘉靖、隆庆朝,“后七子”继承“前七子”文学复古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王世贞《艺苑卮言》:“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后,方足覆瓿。”[28]960又曰:“司马相如、邹、枚、雄、褒诸才士,其赋颂卓然,脍炙于西京者。”[29]530王世贞评李攀龙:“李于鳞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28]1063《明史》亦称李攀龙:“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30]7378王世贞、李攀龙二人皆宗西汉之文,实为承何景明、李梦阳文学复古之余绪。自弘治至万历,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潮长达百年,其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风靡一时,主张复归楚汉之文,力图纠正台阁流弊,重振文坛新风。
在文学“复古”思潮影响下,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提出了“唐无赋”的观点:
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31]446
四库馆臣谓:“(李梦阳)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12]1497李梦阳高举“文学复古”大旗,以“毋读唐以后书”的崇古口号,吸纳了明中叶大批文人,确立了自己文坛盟主的地位。在这一则材料中,李梦阳就是在践行其“文必秦汉”的创作主张。参照《明史》对李梦阳评价:“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0]7348。李梦阳极力反对当时大行其道的台阁体和理学风气对文学的影响,于是以复古为号召,强调“文必秦汉”,向古文学习格调、文法。李梦阳从创作的角度来否定唐赋的成就,认为唐赋不足学,可学者为楚辞、汉赋。“唐无赋”论亦不过是为其文学“复古”的创作理论服务。根据《潜虬山人记》中佘育“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的行为和“文必秦汉”的主张,李梦阳无疑是用楚骚、汉赋为标准评价唐赋[31]446。
同时代的何景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32]。显然何景明在李梦阳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其论断更加绝对,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否定了整个唐赋的创作,认为赋之一体,唐代已亡,遑论宋、元。“后七子”中的王世贞旗帜鲜明地继承了李梦阳“唐无赋”的观点:“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28]964所以他对于唐代文章尤其是赋,进行了大力的批判。王世贞《艺苑卮言》:“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律赋尤为可厌。白乐天所载玄珠斩蛇,并韩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学究语。”[28]1015又谓:“唐温飞卿八叉手而成八韵小赋。俱不足言。”[28]1079王世贞认为科举制度下的律赋创作是不可能有佳作的,即便如韩、柳诸人,其律赋创作也不过是“村学究语”。此后不断有人对李梦阳“唐无赋”观念进行阐释,试举几例。韩上桂《蘧庐稿选·曾伯子诗稿序》:“诗自三百篇后,何其递降而递靡也。骚出而风雅绝,《上林》《子虚》出而骚绝,古诗绝于六朝,汉赋绝于初唐,律诗绝于宋元。”[33]吴应箕《楼山堂集》:“予早嗜赋,而未尝为,然不读汉以下赋。昔人云:‘汉无骚而有赋’,骚不可再也,则近骚者犹汉赋耳。”[34]249清程廷祚《骚赋论》:“东汉以后,始有今五言之诗。五言之诗大行于魏、晋而赋亡,此又其与诗相代谢之故也。唐以后无赋,其所谓赋者,非赋也。君子于赋,祖楚而宗汉,尽变于东京,沿流于魏、晋,六朝以下,无讥焉。”[7]512以上诸人论述基本不出何景明、李梦阳二人畛域,都在文学复古视阈下评价唐赋,汉赋成为标准,东汉以后辞赋创作每况愈下,乃至于出现“唐无赋”的评价。
梳理元、明之际唐赋批评理论,深入剖析陈绎曾“律赋非赋”和李梦阳“唐无赋”两种唐赋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唐赋在赋学史上之贡献。从“律赋非赋”到“唐无赋”的理论演进,是元、明两代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内容的真实反映。元代科举试古赋,重新树立楚骚、汉赋传统,律赋创作基本消歇,陈绎曾据此而提出“律赋非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明代提倡文学“复古”,李梦阳扛起复古主义大纛,倡导文学复归楚汉之文,其“唐无赋”论实为学赋于汉的辞赋创作主张,非谓唐真无赋。
在“律赋非赋”和“唐无赋”两种观念的形成中,律赋作为唐赋的代表,对这两种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否定了唐代律赋却未否定其他赋体,而后者虽然是对唐赋的全盘否定,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唐代科举试律赋,律赋创作盛况空前,“天宝后,进士试杂文专取诗赋成为定制,出现了文人以律赋争胜的局面”[3]116。只要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基本上都有律赋的创作。祝尧云:“唐赋无虑以千计,大抵律多而古少”[22]325,律赋常常作为唐赋的代名词,因此,历来对唐律赋的评价往往会扩大为对整个唐赋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