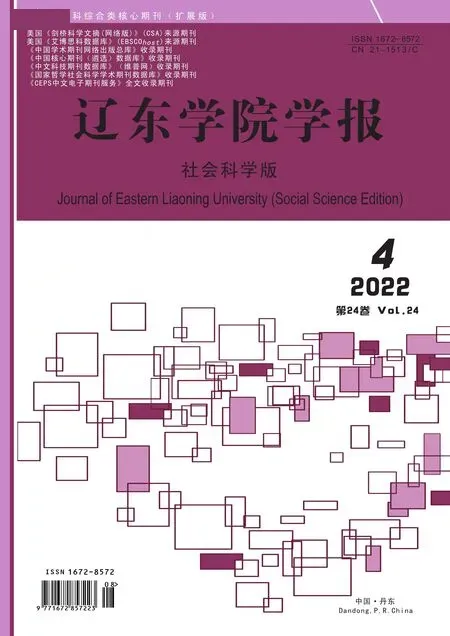孟姜女滴血认取夫骨的伦理问题
张同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引 言
敦煌写本P.5039《孟姜女变文》残卷全文中没有出现“孟姜女”三个字,叙述的对象是姜女或杞梁妻[1]。虽然如此,从敦煌文书这个故事以及孟姜女故事的流传来看,其实也不妨将其视作“孟姜女变文”。变文中的孟姜女故事,在叙事逻辑上存在着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即孟姜女滴血认亲何以可能的问题。
敦煌写本P.5039《孟姜女变文》残卷为韵散结合,其散文写道:“骷髅无数,死人非一,骸骨纵横,凭何取实。咬指取血,沥长城以表单心,选其夫骨”。紧接着在韵文中唱道:“一一捻取自看之,咬指取血从头试。若是儿夫血入骨,不是杞梁血相离。”后又在散文中叙述孟姜女滴血认取夫骨成功:“点血即消,登时渗尽。□(筋)脉骨节,三百余分。不少一支,□□□□□□。”[2]99《孟姜女变文》叙述道,姜女咬指滴血,认取夫骨。孟姜女哭诉黄(皇)天逆人情,夫妻不能共生死。
对以上引文中孟姜女寻夫为什么滴血认取夫骨的质疑早已有之,例如洪颐煊在《论滴血认亲》中问道:“孟姜之与杞良止是恋爱关系,并非血统关系,滴血何得验耶?”[3]291然而,洪文仅仅是质疑而已,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入探究。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亦有过梳理,指出“滴血认骨是六朝时盛行的一种信仰”[3]28,但没有关注孟姜女夫妇之间若没有血缘关系,滴血认亲何以可能的问题。笔者尝试从地域文化、种族身份和婚姻形态等角度回应《孟姜女变文》中孟姜女何以能够滴血认取夫骨的问题。
一、孟姜女与杞梁近亲血缘婚可能性的推测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滴血认亲是一种人人皆相信的医学知识。以血沥骨认亲的说法大致始于魏晋南北朝。《南史·梁豫章王综传》曰:“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其骨,沥血试之。”[4]1316《南史·孙法宗传》云:“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渍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余年。”[4]1808当时,“滴血认亲人骨”的说法,在民间颇为流行。从《同贤记》所记杞良妻认丈夫尸骨的细节,可以推知这个故事形成时间的上限不会早于南北朝。
现代科学认为,最可靠的办法是用HLA蛋白质证明血缘关系。滴血认亲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因为只要血型相同就会有血液融合的现象,但是,既然敦煌变文无意识地以有说有唱的方式讲述了夫妻之间滴血认亲的故事,则表明在事实上敦煌地区委实曾存在近亲血缘婚。否则,中国自西周以来就践行同姓不婚、反对血缘婚,而晚至中晚唐,俗讲变文故事中竟然堂而皇之地讲述族内婚,难道不会也不曾引起当时人们的惊诧或质疑?也就是说,《孟姜女变文》中的夫妻滴血认亲书写既然煞有其事,则表明孟姜女的滴血认夫骨就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孟姜女与杞梁本来就是兄妹婚或姐弟婚甚至是蒸报婚等之近亲血缘婚;如果敦煌变文所述纯属虚构,那么,它就在艺术上反映了敦煌地区在事实上曾存在着血缘婚,而说唱者和听众皆对其司空见惯而不以为意外。
二、在中晚唐的敦煌,近亲血缘婚何以可能?
当代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所呈现的新知识完全可以重构敦煌的历史文化生态。在文化环境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重构敦煌的地域文化,了解敦煌人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若不了解敦煌人的种属、族属和具体的文化类型,就无从探求敦煌文化背后的深层结构。
(一)时间透视
从时间上来看,《孟姜女变文》成于何时?王伟琴在《试论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河陇地域特征》认为是晚唐:“唐代晚期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故事发生地则具有浓郁的河陇地域特征,追根溯源,主要原因在于晚唐民族融合过程中,作者借杞梁妻故事委婉表达河陇地区民众对吐蕃劳役反抗以及对中原思归主题的需要。”[5]王伟琴对《孟姜女变文》故事发生地的考索很有价值,但是笔者对其时间上的判定及论证则不敢苟同。其文中所谓的吐蕃劳役,如果是晚唐,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晚唐敦煌地区已经属于归义军统治时期,反抗吐蕃劳役从何谈起?
848年,张议潮驱逐吐蕃出河西。851年,张议潮派人到长安投诚,被朝廷封为节度使。从此之后,河西地区基本上就是独立半独立的藩镇状态。中唐指的是代宗大历初至文宗太和末(766—835),共69年。历史上的分期,中唐是指从穆宗时期至僖宗在位的875年;从875年唐朝进入了晚唐时期,直至907年灭亡。由此可知,如果说《孟姜女变文》讲述的是对吐蕃劳役的控诉,那只能是在中唐时期。如果像当前大多数学人所以为的是晚唐,那么它就绝对不是对吐蕃统治进行反抗的艺术化表现。
笔者认为,《孟姜女变文》应该成于中唐时期,而不可能是晚唐。为什么呢?孟姜女滴血认亲的故事情节转录自盛唐类书《琱玉集》中的《同贤记》。《琱玉集》第14卷卷末写道:“天平十九年岁在丁亥三月写。”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九年是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这就是说,《琱玉集》所收集到的《同贤记》只能在盛唐之前成书,而不可能在其后。顾颉刚认为“《同贤记》之作必在中唐以前”,而孟姜女滴血认骨故事“最迟是在初唐”[3]281。笔者认为这一估计过于保守,孟姜女哭倒长城、滴血认骨之故事应该生成于北齐、隋代,因为唐朝统治的289年间,从未修建过长城,而北齐、隋代却曾修过长城,从而孟姜女哭长城的现实缘由不可能形成于唐代,而只能在修筑长城时的北齐或隋代。
钟敬文认为,杞梁妻哭倒长城的故事与北齐统治者多次驱民修长城有关[6]。从南北朝到唐代,在北方筑长城徭役最重、民怨最大的要数北齐和隋王朝。北齐在短短的六年里筑长城三千余里。仅天保六年(555年)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筑长城九百里,就发夫“一百八十万人”,占当时男丁的三分之一还多。从故事将杞梁这位春秋时期的齐人改写为燕人来看,哭长城故事发生的时代为北齐的可能性更大。
孟姜女在哭倒长城、点血认夫骨之后,继以背骨还乡而终。《同贤记》是大唐天宝之前的著述,文本中杞梁改写为杞良;齐人改为燕人;杞梁妻改为孟仲姿。孟仲姿看见杞良,主动“请为其妻”,与杞良订婚,这完全不符合汉民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习俗,极有可能是西胡人或鲜卑人的婚俗。
《琱玉集》既收录了出自《春秋》的杞梁妻故事,又收录了《同贤记》记载的孟仲姿故事,后者所载内容显示出杞梁妻故事发生了巨大变化。黄瑞旗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指出:“孟仲姿传奇除了继承西汉以来‘妻子哭夫城崩倒’这个情节单元以外,其他如时代、主角身份、结局全是新出,说法与杞梁妻传说大不相同,已经可以据此建立起故事的‘类型’。”[7]53孟姜女故事至《同贤记》而发生质变,并且是在民间,具体地说就是在敦煌地区成为当今孟姜女故事的定型。
《同贤书》孟超女“仲姿”这一命名也令人深思,其父孟超,女儿以仲排行?何以见得是排行?因为《文选集注》对曹植《通亲亲表》的注解中将孟仲姿写作孟姿。于是,这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系统的叙事。孟仲叔季之排行,表明孟超与孟仲姿在说唱者的意识里或许是已经解构了辈分之关系,而这种可能性只能出现在游牧民族或西胡婚姻形态中。
《文选集注》中的孟姿故事与《同贤记》中的孟仲姿故事相比,可以发现前者汉文化色彩较浓,例如它认为父女孟仲排行是不合乎伦理的,故将孟仲姿改为孟姿;它认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之间滴血认骨是不可能的,故将后者的滴血认亲改为“泪点之变成血”。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73曹植《通亲亲表》“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况徒虚语耳”句下注语有孟姿故事的记载。《列女传》云:
孟姿□□未婚,居近长城,杞□□□□□□□避□此。孟姿后园池□树水间藏。姿在下,游戏于水中。见人影,枝上见之。乃□请为夫妻。梁曰:“见死役为卒,避役于此,不敢望贵人相采也。”姿曰:“妇人不赤见。今君见妾□□□此,更□□子。”……馈食,后闻其死,遂将酒食往收其骸骨。至城下问尸首,乃见城人之筑在城中。遂向所筑之城哭。城遂为之崩。城中骨乱不可识之,乃泪点之,变成血。[8]346-347
笔者以为,此处的“孟姿”当为“孟姜”书写之讹误。
从伦理文化的维度来看,孟姜女故事中的滴血认亲显然不是汉文化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来自异域文化,具体地说就是来自西域粟特人的婚俗文化。或许有人质疑:如果哭长城之叙事最早出现于北齐,那么彼时是否存在着粟特文化呢?其实,从灵太后拜胡天、金鸡放赦等现象来看,北齐胡风劲吹之胡,实乃西胡,即粟特人。
(二)地域考察
从地域来看,唐代孟姜女哭长城之地有官方与民间的区分。朝廷依然依据文字文献认为,杞梁妻乃齐人。《唐会要》载:“(唐玄宗天宝)七载五月十五日诏:‘……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齐杞梁妻(济南郡)……以上烈女一十四人。’”[9]502由是可知,官方对孟姜女故事的认知承续的是自春秋以来杞梁妻的故事。
《孟姜女变文》故事的讲述地是敦煌,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体现了民间立场。敦煌在文书中被称为“善国神乡,福德之地”。王伟琴在《试论敦煌本〈孟姜女变文〉的河陇地域特征》认为:“在晚唐敦煌本《孟姜女变文》残卷中,除了‘长城’‘塞垣’‘塞外’‘塞北’之外,更有‘陇上’‘金河’‘莫贺延碛’‘燕支山’等河陇地名,这充分说明该变文演绎的故事发生地是在西北河陇地区。”[5]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即顾颉刚所判定的唐代孟姜女故事的大转折和基本定型就是在唐代,而这个后世所熟知的基本故事内容不是确定于官方的叙述,而是来自民间,具体地说,源自敦煌地区的俗讲变文。
据现有关于孟姜女民间小唱的敦煌文献可知,这首词的主要内容是孟姜女给丈夫送寒衣。西北地区有寒衣节,便是古代战争期间送寒衣习俗的遗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别说八月即飞雪,笔者曾亲身经历过四月飞雪。西北气候酷寒,故有寒衣节。孟姜女送寒衣,是将这件事典型化了。从而得知,孟姜女故事与敦煌地区具有特别的关联。
(三)人口种族
从种族来看,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和聚落》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生活着大量的胡姓居民,他们有粟特人、回鹘人、鄯善人、焉耆人等[10]。据《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当时敦煌县的胡蕃居民在归义军时期约占整个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如加上“常住敦煌的龙家、达怛、鄯善、于阗及其西域波斯、印度移民,敦煌地区的非汉族居民占整个居民的百分之四十或者更多”[11]。其中的粟特人为东部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属于白种人。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如上所述,生活在这儿的居民一大部分都是粟特人。敦煌学的这一新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因为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敦煌地区的居民都是汉人。不同的人种族群,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姻形态等。正是由于对敦煌地区人口的构成有了科学的认识之后,就能发现孟姜女故事中夫妻滴血认亲的不合情理之处有了合乎种族逻辑的解释。
(四)宗教信仰
人的伦理身份问题,是解决学术困惑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因为主体的宗教信仰、婚姻形态和习俗文化都与主体的伦理身份密切相关。中晚唐时期生活在敦煌地区的一大部分人口是粟特人,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应该予以考察。
从宗教信仰来看,粟特人信奉祆教和佛教。“粟特人既信仰祆教也信仰佛教,是佛、祆二教并重的民族。”[12]祆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中亚化之后的宗教,打上了中亚佛教的烙印。祆教流传到中土后,被汉人混同为佛教。由于祆教的一些教义,尤其是它倡导族内血缘婚,为汉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所排斥,因而在公共空间粟特人经常以信仰佛教的面目出现,而在其聚落内部则露出真面目,信奉祆教。
祆教,又名拜火教、火祆教。这是中原人对祆教的认知。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自称马兹达教,马兹达是“智慧”之意。他们并不认可将其宗教称为拜火教,因为他们认为琐罗亚斯德教不仅崇拜火,还崇奉水。
祆教基本上拘囿于栗特人自己聚落内部,从来不主动向教外人士传教。由于这个缘故,即使是唐代人,也将祆祠里面的战神得悉神混同为佛教中的摩醯首罗。摩醯首罗本来是婆罗门中的三大神之一的湿婆,其三头六臂,被佛教吸纳进其护法神系列。得悉神也是三头六臂,拿着三叉戟。正由于祆教不主动向外传教的这一特点,导致有人误以为祆教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甚小甚至于无。笔者认为这是错的,因为祆教对中国民间文化尤其是民俗节日的影响极为深远。
粟特人既然信奉祆教,那么祆教所倡导的婚姻形态是如何的呢?敦煌地区的粟特人信奉祆教,了解了祆教所倡导和践行的婚姻形态,就可以把握他们的婚姻习俗和传统。
(五)婚姻形态
从婚姻形态来看,粟特人在宗教上信仰祆教,祆教提倡族内血缘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土后,除却经商、做官或参军外,主要生活在小聚落里,依然奉行族内血缘婚。
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阿维斯陀经》训示说:“最为正直而又正直的人,便是奉我马兹达教的信徒,他们一遵我教近亲结婚之规矩行事。”[13]《亚斯那》写道:“我向崇拜马兹达(光明神)的宗教效忠,放下武器,遵行族内婚姻,这是正当的。”[14]林悟殊对祆教的研究很有造诣,他说,“古代琐罗亚斯德教是主张近亲结婚的,即双亲和子女结婚,兄弟姊妹自行通婚”[15]73。这是因为族内血缘婚提倡母子、父女、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琐罗亚斯德教认为这是至善。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尊奉和践行族内婚。粟特人是东部波斯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实行血亲通婚。中国史书对此也有记载,如《隋书·西域传》说安国粟特人“妻其姊妹,及母子递相禽兽”[16]1849。唐代和尚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说粟特人“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17]130。史书认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遵循族内血缘婚的粟特人由于“多以姊妹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18]920。这些记载或书写,表明粟特人委实是践行族内血缘婚的。
要言之,敦煌地区的粟特人,他们的婚姻形态是血缘婚,因此,当他们在俗讲中演说孟姜女滴血认亲的故事时,他们绝对不会感到惊诧、意外或困惑;相反,他们视之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的。事实恐怕是,正是因为粟特人实行血缘婚,曾经有过滴血认亲的现实经验,所以在孟姜女故事的俗讲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叙述了滴血认亲的经验,无意之中在孟姜女故事中留痕。
粟特人在金鸡放赦、血社火、元宵节放灯等节日习俗中对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潜在的、深远的影响。唐武宗灭法时,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皆遭到迫害,教徒被勒令还俗。这些教徒们为了谋生,一部分进入娱乐行业中去,因为尤其是其中的祆教教徒本来就有酣歌醉舞、吃喝玩乐、享受人生的民俗传统。
(六)民风习俗
从民风习俗来看,粟特人所信奉的祆教不提倡苦行,而是倡导享受人生。据《阿维斯陀》载,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应该用于吃喝玩乐。即使是在伊朗西南亚兹德和克尔曼地区琐罗亚斯德教的村落里,那里的人们生活如此艰难,但仍然不肯放弃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娱乐。

安禄山本姓康,是昭武九姓康国人;史思明为史国人:他们都具有粟特人血统。历史上虽然称他们为“杂种胡”,但是实际上从习俗文化而言,皆为粟特人文化。
《安禄山事迹》记载:“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20]83从中可知,胡商拜见安禄山,“诸巫击鼓、歌舞”,但他们聚会并非仅仅关乎歌舞娱乐,而是亦有其宗教信仰成分在,粟特商胡似乎将安禄山视作他们神话中的战神——Roxshan。
如上所述,当唐武宗灭法时,祆教、摩尼教等为了生存,就会混迹于说唱歌舞之地,甚至成为民间戏曲、说唱艺术的中坚骨干力量。
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记载:
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21]191-192
从中可知,杂剧中的“末”乃末泥之简称,而末尼即摩尼。
《张于湖误宿女真观》演书生潘必正与道姑陈妙常在建康通江桥女真观内的风流情事,妙常因身怀六甲哀求住在观内生子,法诚听后十分恼怒。剧中写道:
卜云:“你到说的好也。我这观里与你生儿长女做三朝满月,两糖三果做筵席。”净云:“我与你请和宁院里香儿来弹唱,他也是还俗的尼姑,就叫几个末尼来,做个尼姑还俗的杂剧,也带携我吃些酒,不枉了替你看门子。”[22]25
从“叫几个末尼来,做个尼姑还俗的杂剧”来看,杂剧与摩尼教、末尼似乎有着密切的关系。已有学者做过考证,认为摩尼教被朝廷取缔后,一部分教徒被遣送回国,一部分转入了娱乐行业,这或许就是诸宫调、院本杂剧的缘起?因此,水浒故事、西游故事、三国故事中都有祆教、明教之身影。回观俗讲变文,尤其是敦煌地区的俗讲变文,其间出现粟特人的文化痕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七)骨葬印证了孟姜女、杞梁为粟特人
唐代,招魂葬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23]4279的情况。举国上下,上至皇室,下至草莽民间,都曾出现过招魂葬。唐肃宗曾下诏举行大规模的招魂葬。《安禄山事迹》记载,史思明埋葬安禄山时,“禄山不得其尸,与妻康氏并招魂而葬”。史思明自立为燕王,“以礼招魂葬禄山”[20]110。……这些记载,表明粟特人有“招魂而葬”的习俗,与《孟姜女变文》中的“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此言为记在心怀,见我耶娘方便说”完全一致。“唐时敦煌地方社会,佛寺经常举办向孤魂野鬼普施法食的超度施食仪式。”[24]由此可知,招魂葬在敦煌地区也很流行,那么试问孟姜女为什么不举行招魂葬而哭倒长城、滴血认骨,将夫骨背走后去骨葬呢?
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死后实行天葬,尸体放在寂静塔顶上,肉被兀鹫、老鹰吃掉,骨头放到石瓮里。中亚的祆教教徒死后,尸体上的肉让狗吃掉,骨头放到石瓮里。中土的粟特人受汉文化影响,实行土葬,但是修建石室,里面有石床,死者的骨头放在石床上。
李白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指南死后,李白为其行二次捡骨法葬仪式,或以为这是受到了蛮族的影响,或以为是突厥人的葬俗,其实都不是,而是祆教的葬仪。孟姜女对丈夫杞梁的骨葬与李白为朋友的剔骨迁葬都是祆教教徒的葬仪。
既然唐代普遍实行招魂葬,孟姜女就完全可以在家里为其丈夫举行招魂葬即可,何必跑到长城边,哭倒长城,滴血认亲,将夫骨背回举行骨葬?《孟姜女变文》中的骨葬叙述,表明孟姜女实乃粟特人,从而印证了本文最初的假设,即孟姜女与杞梁夫妻是血缘婚,或者说孟姜女滴血认亲的叙事反映了敦煌地区粟特人践行血缘婚的事实。
三、后世孟姜女故事对滴血认亲的沿用和变异
大多数故事中几乎都有孟姜女哭倒长城后,咬破手指滴血认夫骸骨的情节。湖北宏文堂刻有《送衣哭夫卷》,又题《宣讲适用送寒衣》,其中有“滴血认骨”的叙述。燕地静海《孟姜卷》中也有关于孟姜女滴血认骨的讲说。河南《孟姜女》唱本中亦有滴血认尸的故事情节。有的传说中孟姜女抱着骨骸边走边哭,眼泪滴落到骨头上,长出了新肉而得以复活。……这些都是孟姜女变文故事的流传。
后世孟姜女故事中的诸如“城中骨乱不可识之,乃泪点之,变成血”之类的叙述,此处的论述则是对孟姜女滴血认亲书写的以讹传讹。也就是说,讲述者认为滴血认夫骨是不可能的,从而改写为泪水滴到骸骨上成为血。其实,这样的叙述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在事实上不可能,但在伦理文化禁忌的情境之中,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即虽说泪血之变的叙事不合乎情理,但毕竟比乱伦悖理更容易被接受。
结 语
综上所述,《孟姜女变文》中的孟姜女滴血认夫骨之叙事,反映了敦煌地区粟特人奉行近亲血缘婚的事实。敦煌地区的粟特人信奉祆教,祆教坚信血缘婚为至善,故他们在聚落中践行族内婚。从而孟姜女与杞梁之夫妻伦理,实则展现了粟特人血缘婚的婚姻伦理。从这个维度对《孟姜女变文》中的夫妻而血亲的伦理叙述进行透视,就获得了孟姜女滴血认夫骨其背后合乎因果逻辑关系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