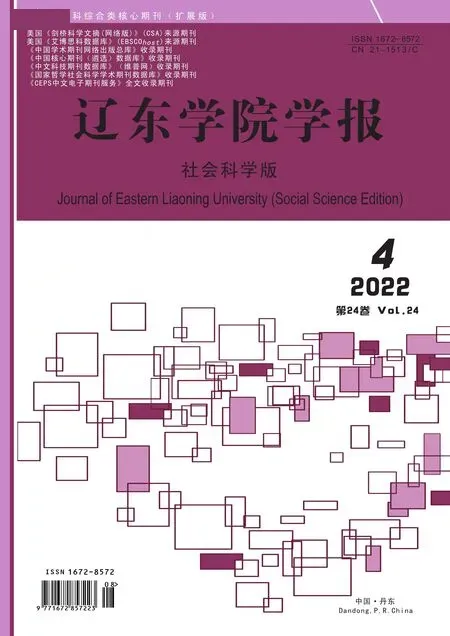浦铣《复小斋赋话》的赋论思想
马悠悠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1],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宋人王铚《四六话·序》:“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2]3首次提出“赋话”之名。赋话产生于汉代,但处境颇尴尬。赋者古诗之流,赋多依附于诗,赋话亦零散地存在于诗话中。清及近代是古典赋学的总结与转型期,此时期赋的编集(编选结集)及评论著作空前增多。以浦铣《历代赋话》和《复小斋赋话》的出现为标志,赋话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批评形式。浦铣的赋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复小斋赋话》中。浦铣《复小斋赋话》书成后,袁枚为其作序,言:“创赋话一书,……为艺苑之津梁无疑也”[3]3,对浦铣《复小斋赋话》一书评价颇高。
浦铣《复小斋赋话》分为上、下两卷,在零碎的论赋条目中,集中体现了浦铣的赋论思想,涉及辞赋创作的各个方面。首先,在赋法论上从破题、用事、琢句炼字、整体布局等方面提出赋的创作观念,从创作要求上提出赋体创作应重视独创性,需自置地步、学古而不泥古;其次,在赋体风格上提出阳刚与阴柔并济的风格,同时主张文以情为贵;最后对于赋作中情感的表达,浦铣追求一种情真语至、自然真切的状态。浦铣的这些赋学观念在赋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赋学理论批评体系。
一、赋法论
赋法与诗法类似,即辞赋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唐代受科举试赋制度的影响,律赋成为文学“正典”。初唐的文学家逐渐开始对赋法进行研究,出现了一些讨论赋格、赋法的著作,如唐抄本《赋谱》、郑起潜《声律关键》等,但这时期的赋论专书并不多。直到清代赋论专书才大量出现,其中大都涉及赋法论,如浦铣的《历代赋话》和《复小斋赋话》、李调元《赋话》等。这些赋论专书对历代赋作品及赋作家进行评论,并针对律赋的创作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指导律赋创作的独到见解。总的来说律赋创作有六个关键:审题与破题,用韵与限韵,用事与用笔,偶对与辞格,炼字与琢句,制局与炼局。
浦铣作为清代赋论大家,编纂了《历代赋话》以及《复小斋赋话》两部赋论专书,其律赋创作思想在《复小斋赋话》中体现明显,如浦铣对律赋破题、琢句炼字、制局炼局、内容情感等方面的理解。
(一)认题与破题
清代赋论家汪庭珍在《作赋例言》中云:“作赋之法,首重认题。”[4]肯定了作赋认题的重要性。律赋创作,认题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影响着整个文章的立意。郑起潜也在《声律关键》中云:“凡见题目,先要识体。”[5]识体即辨别不同的体裁,体裁不同,创作方式则不同,其在《声律关键》中也列举了不同体裁赋作的不同写法。清余丙照在其赋论著作《赋学指南》中也指出:“赋贵审题,拈题后不可轻易下笔。先看题中着眼在某字,然后握定题珠,选词命意,斯能扫尽浮词,独诠真谛。”[6]可以看出清代赋论家大都肯定了辞赋创作中认题的重要性。浦铣《复小斋赋话》云:“作小赋必先认题。”[3]382且在赋话中列举了《凉风至》《小雪》《握金镜》三赋加以说明,认为这三篇赋题的侧重点都在第一个字上,也就是题中的形容词或动词。如果赋题抛开具有修饰性的形容词和动词,题意则会发生变化,文章含义也会不同。浦铣指出律赋创作如果认题不准,则文与题必相去远矣。从此则赋论可知,浦铣认为作赋应重点抓取题中的动词、形容词,文章内容围绕动词、形容词展开,文章立意才妥帖,这是浦铣对赋作认题方面的独特见解。
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云:“唐赋重破题,宋人亦然。”[7]破题在唐代试赋中极为重要。许结也在《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一文中专门讨论过此问题[8]。浦铣也持此观点,认为律赋创作中破题是非常关键的,其在《复小斋赋话》中提出“律赋最重破题”[3]371一说。《复小斋赋话》云:“李表臣程《日五色》,夫人知之矣。宋唯郑毅夫《圆丘象天赋》,一破可与抗行。”[3]371又云:“黄御史滔《秋色赋》:‘白帝承干,乾坤悄然。’能摹题神。”[3]371浦铣对注重破题的赋作十分赞赏,可知其提倡律赋创作重破题的理论,不过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没有提出律赋创作中破题的具体方法,但他提及的破题理论也给清代赋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其后多部赋论著作都继承了浦铣重破题的观念,如李调元《赋话》云:“唐人试赋,极重破题”[9]。
(二)字法与句法
易闻晓在《中国古代诗法纲要》中讲到诗句法的重要性:“夫句法者,诗法之切要者也,篇章积句所成,字词就句而下,而诗家撰作,固有得句为先,乃论者讲求,恒以句法为务。”[10]133诗讲句法,赋亦讲句法。陈骙在《文则》中云:“作文不难,难于炼句。”[11]66余丙照在其赋论著作《赋学指南》中还针对长短句式的不同提出炼短句与炼长句的不同方法。可知,在作文时,句法是十分讲究的。浦铣在《复小斋赋话》的开篇就提出赋贵琢句,强调了赋创作中琢句炼字的重要性。
李调元《赋话》也提到了辞赋琢句的理论:“唐人琢句,雅以流丽为宗。”[9]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评价张仲素《管中窥天赋》云:“‘月既满而犹亏,日将中而如昃。’”[3]370谓其佳句。“又无名氏一联云:‘桂魄未圆,余晖来而尚溢;阳乌当昼,远色照而全亏。’同是一意,而笔用反正,加以锤炼,便觉出色。”[3]370浦铣认为两个句子表达的意思近似,但句子读来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加以锤炼的句子更加出色,更能打动人,使人印象深刻。此乃作赋琢字炼句重要性的体现,也是浦铣提倡作赋需琢句炼字的原因所在。
浦铣认为律赋要精工雕锼。《复小斋赋话》云:“鲁望诸赋,精工雕锼,不遗余力。”[3]392浦铣从句子锤炼的角度对鲁望赋作进行评点,赞扬其赋作精工雕琢,多篇皆佳作。高度评价鲁望的赋作,也正因为鲁望赋作炼字琢句不遗余力,句子雕刻精工。
从句式上看,浦铣认为赋作的句式需灵活多变。其在《复小斋赋话》中论及律赋句法云:“鲁望诸赋,……句法多用四五、五四,四七、七四,八四、六四不多用之,以等剩字。”[3]392指出鲁望赋作句法灵活多变,可四五、亦可五四,可四七、亦可七四,不固定为具体的一种形式。还列举黄滔、陆龟蒙诸家的赋作加以观察评论,同样得出赋作句式灵活多变可使文章思想内容更加丰富这一结论。又《复小斋赋话》云:“律赋对句,宜用流水法。既避重复,且有生动之趣。”[3]391唐赋用隔句作对,句法变化多端,非常灵活。四六句式是律赋创作中较为常用的句式,但须交错使用,使句式流转多变,以此来增加偶对的艺术效果,使文章更具艺术性。余丙照在《赋学指南》中也提出赋贵琢句、句式需灵活多变的观点:“赋贵琢句,律赋句法不一,唐人律赋不必段段尽用四六句,亦有全不用者”[6]。
从《复小斋赋话》中浦铣对赋家作品的评论可知,他非常重视赋作句法的运用:从琢字炼句方面,其认为应该精工雕锼、不遗余力;从属对方面,则认为应使用流水对以及隔句对的形式,使句子灵活多变,以此增加文章的艺术感。
(三)用事
“用事”又名“使事”,或称“用典”。郑起潜在《声律关键》中针对赋作用事提出:“故事虽多,切题为工。”[5]认为作赋用典应在前人众多的典事中,选取切合自己赋作题目的典故。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云:“食古而化,乃为善用故实。若堆垛填砌,毫无生趣,奚取哉?”[3]377浦铣认为运用典故,应该懂得食古而化,将典故经过加工变成新的故事,这样才能体现典故运用技艺之高超,而不是一味地将典故堆砌在一起。另《复小斋赋话》云:“辅文《琉璃窗赋》一联云:‘碧鸡毛羽,微微而雾縠旁笼;玉女容华,隐隐而银河中隔。’上用宋处宗‘鸡窗’事,下用《鲁灵光殿赋》‘玉女窥窗’句,精切而无痕迹。”[3]392浦铣赞扬辅文《琉璃窗赋》中的这两个典故用得好,究其原因,是这两个典故的使用切题且无搬用的痕迹。可知浦铣推崇赋作用事确切、灵活、食古而化的理念。
(四)制局构造
易闻晓在《中国古代诗法纲要》“篇法”一章阐述了篇法的含义以及篇法的重要性。诗讲求篇法,赋亦然,篇法对赋的创作亦是至关重要的。余丙照在《赋学指南》中指出辞赋制局需灵活、曲折的要理:“盖一题到手,认题既真,必先炼局。局贵活不贵板,贵紧不贵宽,贵曲不贵直,总宜相题立格”[6]。
浦铣继承了前人作赋制局的观点,同时对赋作叙次制局的观点又有其独特性,认为赋作的制局需精工、叙次需整齐。《复小斋赋话》:“潘黄门《西征赋》,笔力雄健,虽不及叔皮《北征》,而叙次整齐,……黄门诸赋,当以此为压卷。”[3]401浦铣对潘岳《西征赋》之所以评价高,是因为他认为潘岳此赋叙次整齐、语句圆美,读毕亦觉意犹未尽。可见浦铣对制局整齐的赋作十分喜爱与推崇。
浦铣论律赋,从破题、字法句法、用笔到整体布局,既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又有所创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同时对律赋创作提出了创作要求,即学古而不泥古,贵创新。
文学在继承中发展,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模仿和学习前人的成分。浦铣提倡学习古人,但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要懂得“食古而化”。《复小斋赋话》:“食古而化,乃为善用故实。若堆垛填砌,毫无生趣,奚取哉?”[3]377同时浦铣以王棨《凉风至赋》为例,指出学习古人的精妙之处在于引用典故,但典故的引用需巧而化之,使之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复小斋赋话》云:“用《长门》《秋兴》二赋,令人无从下注脚,真上乘矣。”[3]377又:“谢惠连《雪赋》,辟初四句皆三字,后人祖之者不一,如梁简文《舞赋》,……最佳者,唐杜牧之《阿房宫赋》、陆鲁望之《苔赋》、虽规仿前人,而各成其胜,学古者当阐此秘。”[3]374“明杨守阯《闵贞赋》,仿佛《长门》体制,虽追踵潘黄门《寡妇》一首,可也。每读之不厌,百回击节。”[3]400“潘黄门《寡妇赋》,蓝本丁廙一作,而情文过之。”[3]403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论到的这几则赋论,集中体现了其对模仿前人而产生的佳作的赞赏。模仿前人而成其胜,是学古的要理所在,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申明了这一观点:“作文须自置地步”[3]403。正如陆机《文赋》所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12]7也正如刘勰所说:“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13]133浦铣反对一味学习模仿古人而不懂创新者,其认为学习古人需有变化,似模仿又如己出般自然,赋作才能有奕奕新色。同时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批评那些一味模仿古人的赋作,态度十分明确,如:“雅不喜明人赋,以其模仿而无真味也”[3]379。批评了吴伯允模仿江淹《别赋》作《感秋赋》,袁宏道模仿谢惠连《雪赋》作《玉壶赋》,毫无创新,遭人唾弃。
纵观以上浦铣关于赋题、字法句法、制局构造和创作要求方面的作赋技巧的探讨,是其在个人丰厚学识的基础上对前人在赋体创作中技巧探索的总结,对后人创作与赏析赋作均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辞赋风格论
历代赋作风格千姿百态,对于赋作呈现的不同风格,浦铣并不偏向于某一种,其视野开阔,推崇不同的风格。多样化辞赋风格的推崇,体现了其“博综”的思想。总体来说,对于律赋的艺术风格,浦铣既推崇“阳刚”一类,也不排斥“阴柔”一派。“阳刚阴柔”的审美风格一说是姚鼐提出:“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14]554姚鼐认为大凡雄浑、劲健、豪放、壮丽等风格,可以归入“阳刚”一类;而流丽、淡雅、高远、飘逸等风格,可以归入“阴柔”一类。余据姚鼐文体艺术风格“阳刚阴柔”之说,总结浦铣的律赋艺术风格论,则亦可将其归纳为“阳刚阴柔”之说。
浦铣推崇赋作“阳刚”之说,可从其对汉人赋、杜甫赋、明人古赋的评论中窥见。在《复小斋赋话》中,浦铣提出“汉人赋气骨雄健,自不可及”[3]394。此一则,可看出浦铣对气骨雄健之汉赋的推崇与赞扬。《复小斋赋话》:“少陵诸赋,直欲追踵杨、马,唐人中无其敌手。公自称道:‘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者也。’”[3]383浦铣评价杜甫赋风直追扬雄、司马相如,对其赋作大气、阳刚风格予以肯定。又《复小斋赋话》:“明人古赋,予独取金文靖公一人,以其有大气以包举之也。”[3]404浦铣提出明人古赋中独有金文靖公之赋作有大气包举之势,谓赋作词气充沛,强调了赋作中词、气的重要性。可知浦铣推崇赞扬境界阔大、气象宏阔、气势充沛、骨力劲健的阳刚赋作。
浦铣推崇境界阔大、气骨雄健的阳刚之赋时也对清新、流丽、恬静的“阴柔”赋作多有赞美之语。
在《复小斋赋话》中,浦铣从多则赋论中展现出对“阴柔”风格赋作的推崇态度,如清丽风格的赋作。“清丽”,即清新秀丽,与淫丽相反。李调元在《赋话》中云:“赋贵艳丽芊绵。”[9]与李调元认为“赋贵艳丽”不同,浦铣提倡赋作风格“清丽”,浦铣这一观点新颖且独特。《复小斋赋话》云:“田谏议锡,有宋一代謇谔之人,乃观其《春云》《晓莺》诸赋,芊眠清丽,亦宋广平之赋《梅花》也。”[3]374又:“东坡小赋极流丽,畅所欲言,而韵自从之。所谓‘万斛泉源,不择地涌出’者,亦可见其一斑。”[3]381体现了浦铣对“清丽”赋作的推崇与赞扬。
《复小斋赋话》:“明王忠文公祎《咏归亭赋》,气味恬静,深入理趣,乃宋元人所不及者。”[3]387“恬静”表现的是一种安静、宁静的状态,是一种清新的风格。再有《复小斋赋话》:“袁永之帙《远游赋》,词旨清雅,其得法处尤在序时令两段,便无平铺直序之病。”[3]401可知恬静、清雅的风格也为浦铣所提倡。
还值得一提的是,浦铣对“有画意”的赋作也颇为推崇。

三、情感内蕴
赋作字句的精雕细琢、文章的制局构造,都是为了使文章的“文”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浦铣认为作赋不仅要求“文”的质量,而且“情”也要体现,“情”是“文”的灵魂所在。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明确提出了赋作中“情”的重要性,他强调“文以有情为贵”,这一观点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同时又与时人相异,极大地丰富了清代赋学理论。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15]206提出诗以言志的观点。“志”最初指志向、抱负,后来意义扩大,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人的情感、思想和意愿。“诗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6]381,认为诗用来抒发情志。祝尧在《古赋辨体 》中云:“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穷之而愈妙,……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17]说明了辞赋内在情感表达的重要性。浦铣提倡赋的创作首先要注重真实情感的表达,其提出“以情为本”的观念,这一观念受古赋“以情为贵”观念的影响。浦铣继承并发展了古赋的这一观念,为赋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导向。
浦铣于《复小斋赋话》中表明他最爱明兴献帝言赋之语:
余最爱明兴献帝之言赋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此即卜子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义也。”[3]377
明兴献帝在论赋文字中梳理了辞赋中言、事、情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事必须与情共存,事与情兼具才能称得上是好的文章。浦铣赞同明兴献帝之言,同样认为能流传千年之赋者,乃兼容“事”和“情”也。祝尧《古赋辨体》云:“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17]认为赋是为情而生,发乎情且歌咏性情,指出了辞赋中情与理的关系、情与理的重要性。文章发乎情而歌咏性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离骚》,《离骚》的创作是因为内心有情,发而为文。在自然的叙写中将真挚的情感表达出来,正是这种不求工而自工的自然书写方式,使得情感表达更为真切,故能流传千年,成为典范。但像《甘泉》“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辞”[18]这类赋,虽然言辞与论事功夫都很深,而情感方面的表达却不如《离骚》直接真挚。可见赋作中真情实感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情”是决定赋作境界高下的关键。
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评价王仲宣《登楼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登楼赋》情感真实动人。浦铣还高度评价了范石湖的《惜交赋》,其云:“忠厚悱恻,怦怦动人,有《小雅》、骚人之余风。序所谓‘君子览之,有以增义合之重’者也”[3]400。范石湖《惜交赋》能动人,也是因为其情感真切,有《离骚》之遗风,情感抒发真切自然。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还提及黄文江《送君南浦赋》与王辅文《离人怨长夜赋》两赋情感真切,故能动人。还论到归有光的《冰复草堂赋》,言其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情感真挚且动人,读完感动不已。可谓真情才能动人,真实情感的表达是赋的关键。
浦铣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不仅推崇赋作中“情”的表达要真切,且表达方式要自然。《复小斋赋话》云:“舒元舆《牡丹赋》,秾艳极矣!不尔,便与题不称。”[3]396浦铣评价舒元舆《牡丹赋》,因其描写浓艳,故情感与题不称。真实的情感并不需要过多浓艳华丽的词藻,文章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表达内心情感,更能真切动人。
余 论
清代是我国古典文学全面总结的时期,赋话也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出现了大量的赋论专书。第一部以“赋话”命名的赋论著作即浦铣的《历代赋话》,浦铣的《历代赋话》与《复小斋赋话》在赋论史上具有开创之功。之后,其它赋话著作犹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浦铣《复小斋赋话》以律赋批评为主,对著名赋家赋作进行点评,既继承前人观点,又有所超越,集中体现了浦铣在赋法论、辞赋风格论、辞赋情感表达等方面的赋论观点。浦铣赋论思想是清代赋学理论批评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中国赋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赋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