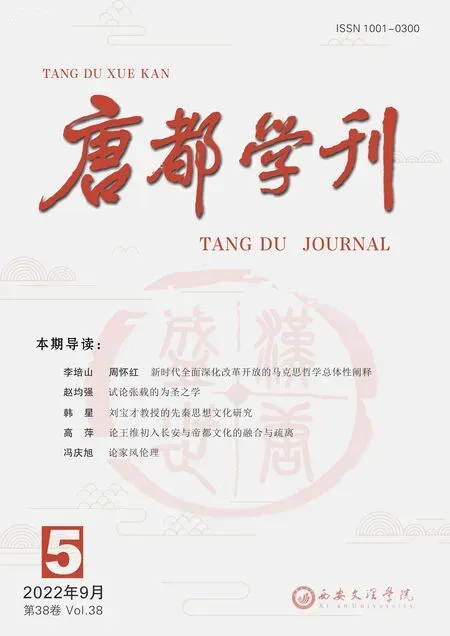伦理思想体系框架下的扬雄德福观探微
桑东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作为汉代思想巨擘,扬雄不仅擅长抽象思辨思维,精心构建起太玄的本体论结构,而且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儒学思想家一样,非常关注现实社会的秩序构建,特别是人们的日用伦常和道德修养,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在扬雄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德福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概括地看,扬雄将德福观建立在太玄本体论基础上,并基于阴阳消长、盈虚变化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福祸互相转化的规律,且通过君子修养论高扬起修德致福、德福一致的大纛。
一、建立在太玄本体架构基础上的思、福、祸三段论
扬雄模仿《周易》作《太玄》,并以太玄图式构建其体大思精的本体哲学大厦。在扬雄的本体论架构中,通过玄、方、州、部、家的层级涵摄模式将整个世界收纳其中,所谓“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载庶部,分正群家”[1]211。同时,扬雄将这个太玄图式在形式上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即“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为八十一卦。以四为数,数从一至四,重累变易,竟八十一而遍,不可损益。”[2]卷五十九《张衡传》这里所谓的八十一卦实际就是扬雄在《太玄》中创造的81首,其中每一首相当于《周易》的卦。每首下又有九赞,赞相当于《周易》的爻。整个太玄就是由81首、729赞组成的。按照《周易》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扬雄在太玄体系架构中,也从天、地、人“三才”的维度对其理论进行了大三段论和小三段论的“三摹九据”式的擘画。所谓“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规,规生三摹,三摹生九据”[1]215。具体而言,“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谓之九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谓之九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谓之九人”[1]215。在天、地、人“三摹”的基础上,每一摹又分别细分为三据,三摹合而为九据,即“天三据而乃成,故谓之始中终。地三据而乃形,故谓之下中上。人三据而乃著,故谓之思福祸”[1]215。也就是说,天、地、人是宇宙图式中的大三段论,其中天道、地道、人道又分别涵摄个小三段论。所谓“参分阳气以为三重,极为九营”[1]212。具体而言,天道的小三段论是始、中、终;地道的小三段论是下、中、上;人道的小三段论是思、福、祸。亦即所谓的“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祸也”[1]194。进而以人为例,在思、福、祸这个小三段论的宇宙图式基础上,又可再进行“三摹九据”的细分,即更小层级的三段论划分,所谓“思福祸各有下中上,以昼夜别其休咎焉”[1]194。这种“三摹九据”格局不仅在人道中存在,天地之道也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架构的。以天而言,天有九天,即中、羡、从;更、眸、廓;减、沈、从。以地而言,地亦有九地,即沙泥、泽地、沚厓;下田、中田、上田;下山、中山、上山。同样,以人类的祸福休咎而言,也是在思、福、祸三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三摹而成九据,即思始、思中、思终;福初、福盛、福隆;祸始、祸中、祸终。在扬雄看来,“下欱上欱,出入九虚;小索大索,周行九度”[1]215。对于扬雄所谓的九据、九营、九虚、九度这些代表层级、位次、次序等含义的概念,笔者下文中统一用九度代替。从语境上讲,这个九度既包含空间层级上的从下到上,又具有时间顺序上的从始到终的意蕴。
思、福、祸三段论集中体现了扬雄德福观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其求福避祸的思想主张。为什么说扬雄的德福观是求福避祸的,这主要体现在其崇福抑祸的思想倾向中。众所周知,《周易》是尚中的。同样,模仿《周易》而作的《太玄》也是尚中的。在扬雄太玄本体论的宇宙图式中,“中”占据重要位置。他将《中》列为《太玄》81首之首。同时,基于对称和谐的美学思维,在扬雄所构建的“三摹九据”的九度本体框架中,“五”处在最中的位置。因此,在扬雄擘画的太玄宇宙本体论中,五是九度的核心和中心。进而,扬雄也像先秦思想家们一样将中与和结合在一起,并将五界定为中和,从而通过中和将美学与伦理学融为一体,生发出了中和的道德美之意境。在扬雄看来,处中对称,故为美;同时,和谐乃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中和是将美与善融为一体的道德美境界[3]。在这个意义上,五因其处中而具有中和的美善之誉,故为最吉,所谓“五为中和”[1]203、“中和莫盛乎五”[1]213。稽考扬雄著述,其对中及中和的称道是始终一贯的,所谓“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刚则甈,柔则坏。龙之潜亢,不获其中矣。是以过中则惕,不及中则跃,其近于中乎!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过则昃”[4]27。参之以扬雄“五为中和”的道德美学思想倾向,不难看出,扬雄在人生哲学方面也具有崇福的思想倾向。譬如,在《太玄·玄数》中,扬雄就明确提出“中,福也”的思想主张,旗帜鲜明地将和谐至美的中与人生追求的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从前面提到的天道“始、中、终”、地道“下、中、上”、人道“思、福、祸”的“三摹九据”宇宙体系中也不难看出,人道的“福”所对应的天道和地道中的相应位置竟然都是“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印证了扬雄的“中,福也”的观念。
除了坚持五为中和最为吉的义理,在扬雄的九度结构中,二、八也因其相对处中而不乏吉兆。我们知道,在81首的太玄体系中,每一首又有九个层级,即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每一个层级则有赞,有测。从初一到上九,又可分为上、中、下三节,二、五、八分别处于三节的中间位置,相对于五这个全首的大中而言。二、八无疑是小中,虽不及五之位正,但亦为小三段论中的中数,故亦可称为位正。如果再与阴阳昼夜搭配适当,则位置处中的赞往往是非吉即福。譬如,永首次五赞曰:“三纲得于中极,天永厥福”[2]111。对此,司马光集注曰:“五为中和而当昼,王者正三纲以建皇极,永保天禄也。”[1]111除了次五,次二、次八也不乏吉赞。如锐首次二赞曰:“锐一无不达”[1]33。务首次八赞曰:“黄中免于祸”[1]56。此二赞之所以分别具有“无不达”和“免于祸”的寓意,主要是因为皆处中(二为思中,八为祸中)。当然,处二、五、八的中位并不是得吉得福的唯一条件,要想得到好的结果必须要满足处中和当昼这两个条件。以上所举的三首中的吉赞均是因为处中且当昼。在这方面,处中而不当昼的反面例子也很多。如戾、干、毅、众、亲等首的次五虽处全首中最中最佳的位置,但因皆当夜而终不吉。限于篇幅,兹不展开详述。
总之,透过太玄本体论的表象,不难发现,扬雄擘画九度结构、设计人道中的思福祸三段论,其根本在于为人类社会道德秩序立法。如果把研究的视野再向上追溯一下不难发现,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周易》还是两汉之际的《太玄》,其所擘画的宇宙图式都是在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框架内。再进一步剥茧抽丝,不难看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立论依据虽然都是宇宙、阴阳等天道规律和自然法则,但其落脚点却都实实在在是人道,是为了构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准则。强调人与天地相参,倡导“知天地之化育”[5],无疑是往圣先哲进行本体思维和人类秩序构建的思维元点。“扬雄以天道论人道,充分肯定了宗法等级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合理性。”[6]所谓“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1]212。因此,无论是天道还是地道,最终都指向人道,指向人类社会的祸福。所谓“天地所贵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1]192。在扬雄看来,福居人道之中,是人类社会乃至每个个体人所应追求和尊奉的理想境界。故而,扬雄建立在太玄本体论基础上的思、福、祸三段论构成了其德福观的价值取向,其基本倾向是崇福的。
二、建立在阴阳消长辩证思维基础上的福祸转化论
扬雄不仅建构了气势恢弘、结构缜密的太玄宇宙本体模式,难能可贵的是,其太玄本体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且有规律可循的。概言之,扬雄的“罔直消长、盈虚消息”的变化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法思想。在扬雄看来,“物靡盛而不亏,故平不肆险,安不忘危”[7]120-121。在《太玄·玄文》中,扬雄揭示了“罔、直、蒙、酋、冥”的万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盛到衰的循环往复、盈虚消长道理,即“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东方也,春也,质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则复于无形,故曰冥。故万物罔乎北,直乎东,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罔蒙相极,直酋相敕,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这种辩证思维还更直观地体现在其所构建的“三摹九据”九度宇宙架构中,体现在其81首中每一首的从最初到极致的发展过程,以及由极致而进入到下一首即下一个递进循环中。所谓“思心乎一,反复乎二,成意乎三,条畅乎四, 著明乎五,极大乎六,败损乎七,剥落乎八,殄绝乎九”[1]213。

为了更清晰地阐析扬雄的祸福转化论,在这里笔者从初一到上九试举几个典型案例进行说明之。如在《太玄》第一首的“中”首中,其初一赞曰:“昆仑旁薄,幽”。其测曰:“昆仑旁薄,思之贞也。”对此,司马光阐释说:“赞者,明圣人顺天之序,修身治国,而示人吉凶者也……君子思虑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贞也’。”[1]4-5从初一的思虑之初到次二的思虑之中,为善恶吉凶的初期萌芽阶段。到了次三,则为思终,往往处于由“思”的阶段跨越到“福”的阶段之前夜。司马光在阐述“度”首次三赞之“小度差差,大攋之阶”时,就曾指出“三为思终而当夜,思不中度则事乖失矣。故曰‘小度差差,大攋之阶’”[1]108。此外,阐述“唫”首次三赞时,司马光也指出“三为思终,又为成意,思虑既成,则言貌可以接人矣”[1]118。相对于祸福而言,思是善恶、祸福的基础和萌兆,所谓“外物之来,入乎思也;言行之动,出乎思也。得其宜则吉,失其宜则凶”[1]8。思的阶段(包括思始、思中、思终)成为招祸还是致福的总开关和大前提,故强调“思之慎也”。而次四则为福之资,是由思迈进福的初始,是培福的重要阶段。如盛首次四赞曰:“小盛臣臣,大人之门。”注释者认为:“四为福始,故曰小盛也。……君子当小盛之初,能自卑贱,承事仁贤,以致大盛。”[1]79而次五虽为盛福,多为吉兆,但如果当夜不当昼,亦主小人而不利。如格、乐、务等首的次五皆因当夜而表示小人难负盛福。所谓“五以小人而享盛福,恣其淫乐,乐极必悲,盛极必衰也”[1]52。按照太玄的九度结构,各首的次六往往为“盛多”,为“上禄”,故处于由福转祸的前夜。到了次七则为祸始,故多现失志、败损、消耗之象。经过次八的祸中,到了上九则为祸穷,即将迎来转折点,所谓“物极则反,故复变而开通,化生万物,萌赤牙白者也”[1]160。在司马光看来,上九虽为“祸之穷也”,但如果君子能“事君尽节,有死无贰,顺义忘生”,也是符合“天之正命”[1]166-167的。综上,不难看出,扬雄的太玄九度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以此构建其祸福转化的思想内涵。
三、建立在强学力行修养观念基础上的德福一致论
作为儒家思想巨擘,扬雄与历史上的其他儒者一样,都将思想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伦教化上。按照“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的儒家信条,扬雄在其《太玄》《法言》等著述中,核心都是在讲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如何,突出的就是扬君子抑小人的君子道德修养论。扬雄的修养论在形式上强调“君子强学而力行”[4]7,在内容上突出扬善抑恶的道德修养,在结果上追求修德致福的德福一致。
首先,以《太玄》为例。在《太玄·玄摛》中,扬雄指出:“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日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玄之道几矣。”扬雄通过擘画玄之81首、729赞的相摩相荡,目的是使“君子小人之道较然见矣”[1]187。一言以蔽之,强调天、地、人“三才”的义理,其根本就在于达致“天地设,故贵贱序。四时行,故父子继。律历陈,故君臣理”[1]187的天人合一境界。通过天道影响人道,通过吉凶祸福来引导人“遵道显义”[7]120,“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7]114,根本点还是教化人民要向圣人、君子看齐,为善去恶,向善成人。有学者总结道:“扬雄开出智、仁、勇、公、通、圣、命、道、德、义等道德范畴,作为玄的功用和原则,并贯通于天、地、人三道和人际伦辈之中。”[9]难能可贵的是,扬雄非常注意将道德善恶与个人的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所谓“吉凶见,故善否著”[1]187。在扬雄看来,“君子在玄则正,在福则冲,在祸则反”,而“小人在玄则邪,在福则骄,在祸则穷”。因此,“君子得位则昌,失位则良”;而小人反是,“得位则横,失位则丧”[1]207。通过对天地、阴阳、昼夜等天地之道的遵循,扬雄最终是要阐扬“君子道全、小人道缺”[1]214的德福一致义理。
无独有偶,在《法言》中,扬雄也致力于积善得福的君子修养论,并以德福一致观来佐证和激励人要强学力行,学为君子。所谓“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4]37,并且将福寿与修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曰:“或问寿可益乎?曰德”[4]40。扬雄赞赏“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的“孟轲之勇”[4]33。在扬雄看来,君子所当学的治国理政之道核心就是“张其纲纪,议其教化”[4]26,具体包括导之以仁、莅之以廉、临之以正、修之以礼义等多种手段。按照扬雄的德福一致思想,尽管修德不一定马上得福,甚至有时还会招致祸患,但长远地看,修德是有大利益的,这些利益有时不是物质上和世俗观念中的荣华富贵,而是精神上和名节道德上的佳名美誉。正是基于这种德福观念,扬雄指出,“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4]22。所谓“众人愈利而后钝,圣人愈钝而后利”[4]22。在扬雄看来,坚守道德操守眼前可能会有所损失,但将来一定有回报。所谓“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类,莫能加也。贵无敌,富无伦,利孰大焉”[4]22。因此,扬雄在面对占星与吉凶的关系时强调“在德不在星”[4]23。他也极其赞赏吴起针对魏武侯以山河之固为国家屏保而提出的“在德不在固”[4]20的德本论。从中不难看出,扬雄的祸福观不在于世俗的利益富贵,而在于道德上的荣辱臧否,所谓“君子德名为几,梁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4]15“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4]3。“先生相与言,则以仁与义;市井相与言,则以财与利”[4]3。扬雄基于“善恶混”[4]7的人性论,主张人要通过“强学力行”成为圣人、君子。所谓“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4]2。人性善恶混的可塑性决定了“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4]7。扬雄赞赏孔颜之乐的道德愉悦感,认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愉悦感才是最大的利益和成功,如“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4]4。在扬雄看来,五常之德本身就是最大的福禄,就是最根本的富贵利益。就像衣食住行等人类根本需求,五常就等同于人类得以在社会中生存的最基本需求。所谓“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知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4]7换句话说,只有具有了道德仁义,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所谓“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 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 ”[4]9-10反之,如果一个人背弃了道德仁义,则必为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弃。 “仁疾乎不仁,谊疾乎不谊。君子宽裕足以长众,和柔足以安物,天地无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谊乎! ”[1]207
基于以上分析,扬雄的君子修养论实则受其德福观的影响,并成为其德福一致思想的核心内容。在扬雄看来,只有修德才能做到避祸致福。当然,修德有时并不是马上就能得到眼前的现实利益,为恶的小人也不一定马上就会招致灾祸,但无论如何,从长远看,最终必然在天道规律的影响下,君子修德而得福,小人为恶终遭祸败。《太玄》“盛”首次五赞云:“何福满肩,提祸掸掸”。测曰:“何福提祸,小人之道也。”对此,宋人陈渐解析道:“五居正位,故云何福也。福至盛,故云满肩。极盛必反,故云提祸。”司马光也认为“以小人而享盛福,祸必随之”[1]79。也即是说,修德才能有福,如果不务修德虽暂时享有盛福,则祸不远矣。概言之,扬雄德福一致思想主要表现为由修德到致福的道德逻辑推演。首先,他认为强学力行的目的是要塑造君子人格,即“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4]2。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努力成为君子,而不要变成小人,所谓“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4]3。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君子务德,小人不务德。务德的君子即使遭到险阻和困难,最终因其崇高的道德坚守,也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不务德的小人即使暂时获得盛福,因其道德缺失,最终也难以负担其荣华富贵(即所谓的“何福”,何者,荷也,负担之意也),而终招祸败(即“提祸掸掸”)。基于此,扬雄倡导人们要强学力行,向圣贤学,学为君子,并以君子最终获得超过荣华富贵的根本“大利”而鼓励人为善去恶,修德成人。
一般说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大多将扬雄归入儒家道统中。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扬雄思想中不乏老子道家的影响。如罗国杰先生就曾指出扬雄的《太玄》受《老子》的影响,但罗先生还是坚持将扬雄划归儒家序列。徐复观在研究扬雄祸福观时则坚持认为扬雄更多地受到老子祸福相倚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扬雄在西汉末年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受老子祸福思想影响,“惕于人生祸福之无常,借撰《太玄》,以远离政治,逃避祸灾”“安处于无福无祸之地”[10]。由此,有学者认为,“扬雄在《太玄》中表现的主要是洁身自好,远祸避害,以及对祸福无常的感叹,调子是悲观而消极的”[11]。抛开扬雄德福观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问题不论,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扬雄的德福观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修德致福、德福一致的思想,同时也吸纳了先秦道家祸福相倚、避祸存身的思想,并创造性地从本体论、辩证法、修养论等角度进行了缜密的论证和生发。在本体论层面,扬雄将思、福、祸的人道机理巧妙地嵌入天、地、人三才体系中,嵌入“三摹九据”的九度宇宙图式中。在辩证法层面,扬雄将九度位置的变化递嬗与阴阳昼夜的盈虚消长结合相参,总结出人道祸福转折变化的规律。在修养论层面,扬雄按照修德致福、德福一致的理论基调,明确了“强学力行”“学正否邪”“仁宅义路”的君子修养原则。扬雄的德福观将本体论、辩证法、修养论熔于一炉,无论是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是论证的严密周延,抑或是实践的可操作性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创新开拓和现实指导价值,成为中国德福观念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个高峰。剔除其中的一些囿于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扬雄的德福观对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