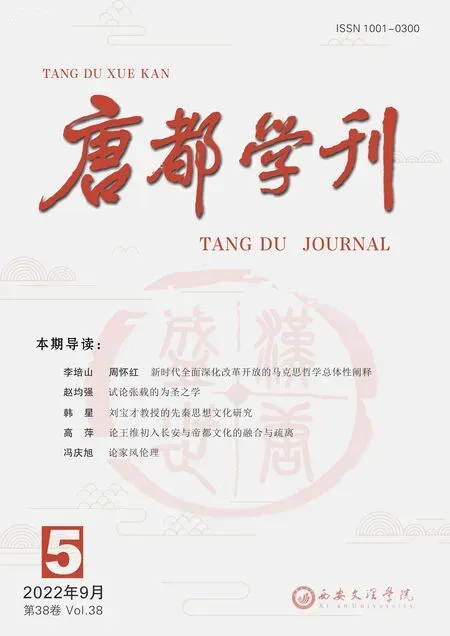汉代饮食禁忌及其社会风俗论析
舒显彩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饮食禁忌是人们在避凶求吉的心理下,因厌恶、恐惧或崇拜某些食物而有意规避的行为。《说文解字》云:“禁,吉凶之忌也;忌,憎恶也。”[1]9汉代饮食禁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饮食习惯、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还集先秦饮食习尚之大成,开后世饮食禁忌之新风,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学界对汉代禁忌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综合性探讨以王光华的《简帛禁忌研究》和《禁忌与战国秦汉社会》、胡迪的《汉代禁忌探讨》最具代表性;专题性研究如马新之《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贾艳红之《汉代的民间禁忌与地方政治》、李秋香之《秦汉民间禁忌及其社会控制作用——以出土文献为中心考察》(1)参见王光华《简帛禁忌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光华《禁忌与战国秦汉社会》,载于《求索》2007年第3期;胡迪《汉代禁忌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载于《民俗研究》1996年第1期;贾艳红《汉代的民间禁忌与地方政治》,收入《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秋香《秦汉民间禁忌及其社会控制作用——以出土文献为中心考察》,载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上述成果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汉代禁忌的类型、特点和成因,对推进两汉社会史研究大有裨益。但是,时贤们在讨论汉代日常生活中的禁忌时多沿袭王充“生人饮食不时”和“饮食不择日”[2]1155的观点,仅聚焦于衣、住、行方面而缺少对饮食禁忌的关注。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为依托,借鉴医药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相关成果,钩沉汉代饮食禁忌的概貌,探赜饮食禁忌与汉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不当之处,敬祈方家赐教。
一
张仲景云:“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3]370在汉代人的认知结构中,“有妨”与否,不仅由食材本身的特性所决定,还与饮食者的身份及进食时间密切相关。
(一)依食材而禁
与其它禁忌相比,饮食禁忌最大的不同点是禁忌对象纷繁复杂,该特征取决于食材类别的多样性。依食材而言,汉代的饮食禁忌可分为单一型禁忌和组合型禁忌。
人们禁忌某一特定食材,往往是因为它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涵。由是,大众便不再从营养和科学的角度,而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审视其价值及意义。两汉时期对动物心脏的禁忌,即属于此。《黄帝内经·素问》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4]62。汉代人将促进血液循环的心脏视为生命之本、能量之源,其神圣性无以复加。出于对“君主之官”的敬畏,禁食动物心脏成为医学家微谏不倦的信条。张仲景云:“凡心皆为神识所舍,勿食之,使人来生复其报对矣”[3]372。因果报应论和灵魂不灭思想对汉代饮食禁忌的影响,于焉可见。
若言汉代人认为心脏是灵魂的依托,那么,肝则是怨气的寓所。张仲景曰:“凡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甚”[3]372。清代学者程林分析道:“凡畜兽临杀之时,忿气聚于肝,食之俱不利于目,故不可轻啖”[5]。在动物肝脏饱含剧毒的传言中,马肝杀人说甚嚣尘上。《金匮要略》言:“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3]384。《论衡·言毒篇》亦云:“走马之肝杀人”[2]953-954。探本索源,禁食马肝的社会心理在西汉初期业已存在。汉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就汤武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互相论难,最后,景帝居中调和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6]3123。景帝能以“食肉不食马肝”说服二人,或可表明这一饮食禁忌已为朝野上下所熟知。武帝即位后醉心黄白之术,方士齐少翁因坑蒙拐骗而被揭发,武帝秘密将其诛杀,对外却宣称“文成食马肝死耳”[6]462。武帝的谎言,也是建立在时人相信马肝有毒的基础上的。自此至明清时期,对马肝的禁忌长期存在,就连名医李时珍也强调“马肝,有大毒”[7]。现代医学表明,动物的肝脏(包括马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它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物质,但如果摄入过量,则可能引起中毒[8]。由是征之,汉代人过分夸大了马肝的毒性,这其实反映了民众既恐惧又依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因对肝脏的机能不解而心怀敬畏,害怕受到忿怨之气的报复;另一方面,随着马匹在负重致远、驮物载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代人对马的依赖愈深,对马的情感也愈笃,故不忍心杀之食之。
汉代人对组合型食材的禁忌,主要受物类生克说的影响。《神农本草经》称:“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煞者。”[9]时俗以为,一旦将“相反”或“相煞”的食物混合食用,便会诱发疾病。仅张仲景便总结了46条不可“合食”或“共食”的食材,涉及瓜果蔬菜、禽兽虫鱼及各色调味品,如“青牛肠不可合犬肉食之”[3]386“鸡不可共葫蒜食之,滞气”[3]398“芥茱不可共兔肉食之,成恶邪病”[3]432。不唯汉代医学家热衷于总结各种饮食搭配禁忌并将其公之于众,经师宿儒们也对此深信不疑。纬书《龙鱼河图》云:“黍米糜粥合糒中,食病杀人,米食不可合穄,食洞下,杀人也。”[10]1157合食伤身说是汉代人在万物感应论基础上主观构建的联系,它夸大了食物搭配不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但这类禁忌开了后世食物相克论的先河,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二)依食用者而禁
有学者认为:“秦汉时期的食忌理论突出表现在疾病时的禁忌与日常生活中的禁忌方面”[11]。揆诸史乘,该观点不甚全面。因为于日常生活之外,遵从饮食禁忌的特殊群体不只病人,还包括孕妇和守孝者。
汉代以前的医学家便主张通过饮食禁忌的方式促进患者身体的康复。里耶秦简8-1290+8-1397云:“以温酒一桮(杯)和,之,到莫(暮)有(又)先食(饮),如前数。恒(服)药廿日,虽久病必已。服药时禁毋食彘肉。”[12]类似的记载,亦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两批简文所云服药的方式、次数、时间完全相同,只是汉代医书增益了一则关于鱼肉的禁忌:
[脉]者:取野兽肉食者五等之毛等,燔冶,合挠□,诲(每)旦[先]食,取三[指大撮]三,以温酒一杯和,饮之。到莫(暮)有(又)先食饮,如前数。恒服药廿日,虽久病必□。服药时毋食彘肉、鲜鱼。[13]85

与患者相比,孕妇的饮食禁忌条目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千金方》曰:“儿在胎,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腑脏骨节皆未成足,故自初讫于将产,饮食居处,皆有禁忌。”[18]自汉代以来,孕妇的饮食便颇有讲究。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道:“一月名曰留(流)刑,食饮必精,酸羹必[熟],毋食辛星(腥),是谓财贞。二月始膏,毋食辛臊……三月始脂,不食(葱)姜,不食兔羹。”[19]张仲景谓:“妇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山羊肉及鳖、鸡、鸭”[3]396。在孕妇众多的饮食禁忌中,兔和姜出现的频率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论衡·命义篇》谓:“妊妇食兔,子生缺唇”[2]53。《金匮要略》则指出:“妊妇食姜,令子余指”[3]431。汉代人基于相似律的原则,将兔子的嘴唇比附为小孩的裂唇,又将多枝节的生姜想象为小孩多出的手指,认为孕妇一旦吃了这两类食物,其体内的胎儿就会患兔唇病和多指病。从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看,这两则禁忌牵强附会、荒诞不经,因为食物的外形与胎儿的健康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在汉代,无论是悬壶济世的医者,还是博闻强识的士人,皆对此深信不疑。刘安等人甚至将孕妇对兔子的禁忌由饮食延伸到观看层面,认为“孕妇见兔而子缺唇”[20]。乃至于后世,孕妇依旧对兔和姜避之不及。张华《博物志》载:“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缺唇;又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21]
除病人和孕妇外,守孝者的饮食亦需遵从诸多禁忌。《礼记·间传》云:“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士与敛焉则壹不食。”[22]1365早期儒家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制定了一套通过节制饮食来表达生者对死者哀悼程度的居丧礼制。迨至“以孝治天下”的汉代,饮食禁忌不只是孝子思亲之情的自然流露,还成为部分人邀功求赏、沽名钓誉的筹码。如和熹邓皇后在其父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2]418。按儒家礼制,练祭期满后便可“始食菜果”[23],邓氏则不然,除将为期一年的菜果之禁延长至三年外,她还开创了居丧忌盐的传统。至南朝时期,由邓后居丧时首倡的食盐之禁被江左士人们争相效仿[24]。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守孝而素食逾期的事迹,亦见于汉代民间。如张表遭父丧而疾病旷年,“每弹琴恻怆不能成声,见酒肉未尝不泣”[25]。甚至连9岁幼童申屠蟠在除服后还坚持“不进酒肉十余年”,每至其父忌日“辄三日不食”[26]1750。禁酒肉十余年本已大大超过了儒家所规定的时限,忌日三天不食更为传统礼制所无。《礼记》言“忌日必哀”[22]1211“忌日不乐”[22]170,并无忌日禁食的记载,而申屠蟠不仅将忌日哀思的时间由一天延长至三天,还于居丧禁忌外新增了父母忌日的饮食禁忌,这是东汉礼制史上的新举措。
(三)依时间而禁
汉代人“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2]1149,于饮食方面,亦是如此。不同月份、节令和日期的饮食禁忌条目繁多而又各具特色。
时俗以为,每月皆有一至两种不宜享用的食物。《金匮要略》称:“正月勿食生葱,令人面生游风;二月勿食蓼,伤人肾;三月勿食小蒜,伤人志性;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神;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气力;五月五日勿食生菜,发百病;六月、七月勿食茱萸,伤神气;八月、九月勿食姜,伤人神;十月勿食椒,损人心,伤心脉;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3]424-425一年十二月中,五月份的饮食禁忌最具约束性,这与时人的“恶五”情节息息相关。《说文解字》释“五”为“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1]738;又谓“午”者,“啎也,五月阴气啎逆阳,冒地而出也”[1]746。《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27]。作为“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22]453的特殊时段,该月的饮食万不可违背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四民月令》劝诫道:“(五月)先后日至各十日,薄滋味,毋多食肥醲。距立秋,毋食煮饼及水溲饼”[28]。否则,将导致消化不良,甚至患伤寒病。“五”既意味着阴阳交错,那么,在双“五”重合的五月五日,阴阳间的分争最为剧烈,若此时食用生菜,则可能导致阴、阳二气失衡,从而患“脉流薄疾,并乃狂”[4]19的疾病。
至于节令中的饮食禁忌,则以寒食最具代表性。自先秦以来,历代皆视寒食为一重要节日,它有两大源头:“其一是周代仲春之末的火禁之说,其二是春秋晋国故地祭奠介子推的传统”[29]。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吃冷食的习俗,于汉代北方地区尤甚。桓谭《新论》云:“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30]随着民俗文化的传播,“火食”之禁更加严苛,以至于“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26]2024。迨至汉末,民众既钦服于介子推焚骸之惨烈,又惮于神灵之威严,吃冷食的时限由一月增至105天,饮食禁忌所笼罩的地域也由太原蔓延至其周边的上党、西河、雁门三郡。
依禁忌的特点,我们可将其分为吉凶之禁和礼仪之禁两类。
特定日期中的吉凶类饮食禁忌主要受择日术的影响。至迟在秦国末期,民间卜筮之书已标明了饮食不利的时间,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之《官》云:
卯(昴),邋(猎)、贾市,吉。不可食六畜。
毕,以邋(猎)置罔(网)及为门……不可食六畜。[31]389
简文以二十八宿的值日情况推演吉凶,进而规定行事忌宜。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星官》亦循此理,惜简文残泐,有关昴日、毕日的禁忌不得其详。但比勘秦简《官》与汉简《星官》中的同一条目,不难发现,二者内容近似(2)如睡虎地秦简《日书·星》云:“尾,百事凶。以祠,必有敫。不可取妻。生子,贫。箕,不可祠。百事凶。取妻,妻多舌。生子,贫富半。”孔家坡汉简《日书·星官》的记载与之相似:“尾,百事凶。以祠祀,必有败。不取(娶)妻。司亡。以生子,必贫。不可杀。箕,不可祠祀,百事凶。取(娶)妻,妻。司弃。以生子,贫富半。”分别参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壹),第388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著:《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当源于同一数术派别。据此推测,昴日和毕日“不可食六畜”的禁忌亦当留存于汉代《日书》之中。
除《官》外,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也规定了禁饮食的时间:
敫,是胃(谓)又(有)小逆,毋(无)大央(殃)……不可临官、(饮)食、乐、祭祀。

刘乐贤先生认为篇题中的“稷”通“稯”,汉武帝时有“丛辰家”,《汉书·艺文志》录有五行家所作《钟律丛辰日苑》,故“稷辰”当作“丛辰”[32]58。战国晚期的丛辰家们所制定的时日法则和吉凶标准,亦为后世所传承。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云:
〔徼日〕……不可以取(娶)妻、嫁女、出入畜生(牲)、为啬夫、临官、酓(饮)食、歌乐、祭祀、见人,若以之,有小丧,毋(无)央(殃)。
将其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进行对比可知,孔家坡汉简中的时日类饮食禁忌多袭秦而来。依简文所言,每月皆有一个地支所在之日为“徼”,有两个地支所在之日为“介”,如“正月二月,卯徼,辰申介”“三月四月,巳徼,午戌介”[33]131。若一年12个月皆有30天,且以甲子日为岁首,则每两个月就有15天逢徼日或介日(4)如正月和二月的徼日为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卯,共5天;介日为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壬申、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共10天。下一组两个月所对应的60甲子中的徼日和介日,亦由此推算,合计为15天。,全年不可饮食的时间多达90天。
汉代的“时日之书,众多非一”[2]1149,且各家说辞扞格。除徼日和介日外,“临日也不可饮食。对此,孔家坡汉简《日书》解释道:
临日:正月上旬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丑,五月戌,六月卯,七月子,八月巳,九月寅,十月未,十一月辰,十二月酉,帝以此日开临下降央(殃),不可远行、酓(饮)食、(歌)乐、畜生(牲),凡百事皆凶。[33]140
按,每月上旬均有一日是天帝下凡的“临日”。从“凡百事皆凶”来看,天帝盛气凌人、不容触犯,其降临之际,包括饮食在内的一切活动皆当禁止,故有学者认为“临日”是《日书》中最厉害的一个忌日[32]155。
汉代《日书》在涉及饮食禁忌的大致有“不可食六畜”的毕日、昴日,“不可饮食”的徼日、介日,以及“百事皆凶”的临日。从概率上讲,它们分别占全年的1/14、1/4和1/30。禁忌的泛滥程度,可见一斑。
至于特定日期中的礼仪类饮食禁忌,则深受儒家思想的渐染。以祭祀、祈祷或参加庆典前所进行的净化仪式——斋戒为例,它要求人们调适身心、约束言行,是斋戒者服膺于礼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两汉时期的斋戒活动十分频繁,史称“一岁之内,大小祭祀,斋将三百日”[34]。在“斋必变食”的原则下,饮食亦当遵从禁忌。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分析道:“斋戒之忌酒肉,其即起于汉时欤”[35]405。钩沉史籍,笔者认为,此论可商榷之处有二:
其一,斋戒忌酒古已有之,并非肇始于汉。《庄子·人间世》载颜回问孔子:“‘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孔子言:‘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36]颜回因斋戒而数月不饮酒、不食具有刺激性气味的荤菜。这表明先秦人行斋戒礼时就已开始忌酒。此后,这一规定亦为汉代官员所遵循。据《汉官仪》,太常周泽曾于斋戒时患疾,其妻前往探病,周泽竟以“干斋”之罪将她收捕入狱。时人颇感不平,乃作谚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37]127。谣谚虽系夸诞之辞,但“一日不斋醉如泥”从侧面说明两汉人只有在不行斋戒礼时方可醉饮,斋期则当忌酒。
其二,汉代斋戒并不禁肉。赵翼云斋戒忌肉源于汉代的依据是“每逢水旱,莽辄素食”[35]405,然考求《汉书·王莽传》,王莽食素的原因并非斋戒,而是因天灾自省、以节俭自饰,这最多属于“忧民”的行为,是生活在阴阳失序、灾害屡臻而又经常处于上天警示威胁之下的两汉帝王们的惯常伎俩。且元后王政君得知此事后,遣使者诏王莽“以时食肉,爱身为国”[38]4050。若王莽确在斋戒,太后断不会公然违反礼制,劝其食肉。其实,汉代官方不仅没有斋期忌肉之习,反而以律令的形式规定了斋期的食肉标准。《汉旧仪》载:“斋则食丈二尺旋案,陈三十六肉,九谷饭”[37]99。同书又云:“斋法:食肉三十六两”[37]99,其量较平日更多。由此可知,汉代斋戒时的饮食禁忌主要是酒而不包括肉。
二
表面看来,饮食禁忌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为减少饮食不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主动避开某些食材。实则,这一看似惯常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大众心理、民间习俗乃至社会整体风貌。两汉时期条目众多的饮食禁忌,亦由当时特殊的文化土壤所孕育。
(一)饮食禁忌渗透着儒家的纲常伦理和礼制法则
《礼记·曲礼上》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22]8礼制“正俗”的功能,就体现在饮食禁忌,特别是居丧期间的饮食禁忌中。纵观两汉历史,守孝者对饮食禁忌的恪守程度,始终与儒学的兴衰起伏成正比。西汉甫建,君臣多笃信黄老之术,崇尚简约务实之风,统治者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丧礼只会导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6]433-434,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产、大父母、大父母之同产十五日之官”[39]60。文帝遗诏,百官只需为自己守孝三十六日,并免除了服丧期间的酒肉之禁,“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6]434。自此至西汉后期,“大臣不行三年丧,遂成定例”[40]70。在孔孟之学沉潜没落、四书五经被束之高阁的时代,儒家所创制的三年之丧未成为国家定制,居丧期间的酒肉之禁自然也不具约束力,朝廷重臣和诸侯王在服孝期间纵酒嗜肉的事迹极其常见。如灌夫就罔顾“疏食水饮”[41]的守孝准则,应武安侯田蚡之邀前往魏其侯窦婴家作客,于宴会上畅饮美酒,起舞助兴;常山宪王太子刘勃在丁忧时“私奸、饮酒、博戏”[38]2434;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38]2940。服孝而不禁酒肉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以至贤良文学们在盐铁会议上讥讽道:“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42]353-354。
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地方豪强的崛起和世家大族的昌盛,儒学的主导性地位被进一步强化,不唯“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40]92,帝王们也自愿浸润于礼教的荣光之中。作为儒学的虔诚信徒,明帝、和帝及献帝都曾为其父或其母服孝三年,安帝则诏令天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43],将居丧时间作为品评士人的标尺。因朝廷的大力倡导,东汉时期不仅“实多三年丧者”[44],还涌现出了许多过度节制饮食甚至常年不食酒肉的孝子。前已述及,邓后开禁忌过礼之端,张表继其后,申屠蟠接其踵。盛行于东汉时期的以素食逾期、禁绝酒肉为特征的守礼、过礼风尚,与西汉士人普遍不服三年之丧或居丧而饮酒食肉的违礼、悖礼行为大异其趣。这一反差,看似是饮食习尚的不同,实则是儒学地位的巨变。可以说,借饮食禁忌之门径,东汉儒学在规范世人言行举止、维护尊卑长幼之序的同时,亦重塑了自身的权威。
虽然汉代儒学的表层镀着礼制的金边,然其骨干却是架构于谶纬神学基础上的灾异论,董仲舒所创制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目的论体系”[45]奠定了汉代儒学的基本范式。在感性思维的迷雾中探索世界的两汉人秉持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46]的灾异思想,他们认为,大到国运兴衰、君主废立,小到生产祭祀、衣食住行,无不承载着上天的意志。灾异思想对饮食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外形奇异、色彩驳杂的动物因被指斥为“羽虫之孽”而位居禁食名册。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云:“玄鸡白头,食之病人。鸡有六指,亦杀人。鸡有四距,亦杀人。鸡有五色,亦杀人。”[10]1157《河图括地象》也有类似的记载:“白马玄头,食之杀人;下病。食马肉,亦杀人。”这些饱含神秘主义色彩的饮食禁忌几被医学家全盘吸收。《金匮要略》言:“鸡有六翮、四距者,不可食之”“乌鸡白首者,不可食之”[3]397“白马黑头者,不可食之”[3]383。其二,汉代人深信,天象异常时不可饮食。所谓“典籍所忌,震食为重”[26]265,日月食往往被视为最严厉的天谴。《风俗通义》云:“临日月薄蚀而饮,令人蚀口。谨案:日,太阳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里语:‘不救蚀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饮食,重惧也。”[47]灾异论以自然现象预测人事吉凶的特性,为汉代民众的饮食禁忌平添了几分神秘主义色彩。
(二)欣欣向荣的医药学为饮食禁忌提供了源头活水
汉代是中国医学的定型阶段[48],也是中医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中药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它由原来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视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49]。屹立于汉代医学高峰之上的,不唯张仲景、华佗、宋玉等妙手回春的名医,还有《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流芳千古的著作,更有望、闻、问、切的诊病步骤和食药同源、以食养病的理念。《黄帝内经》载:“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4]150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汉代医学家逐渐意识到,饮食不当可能诱发某种特定的疾病。或为防微杜渐,或为亡羊补牢,他们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将饮食禁忌系统化、规范化。仅《金匮要略》便列举了数十条以健康为主旨的饮食禁忌,大致包括如下三类:其一,禁食颜色异常的食物,如“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3]374“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羊悬蹄,食之,令人癫”[3]390;其二,禁食腐败变质的食物,如“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3]376“生米停留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3]413;其三,禁食患疫而死的动物之肉,如“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3]412“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3]411。上述禁忌中,后两类集中反映了汉代医学对人体健康的理性主义关照,因为过期食品中的霉曲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对人体危害较大,而患疫动物极可能成为疾病的中间宿主,将病毒或寄生虫传染给食用者。即便从现代卫生的角度考虑,这些禁忌也极具科学性。
(三)原始道教对汉代饮食禁忌的助推作用
建立在黄老无为思想、神仙方术和巫觋文化基础上的原始道教萌芽于西汉中晚期(5)林剑鸣、龙显昭和姜生等学者皆认为,原始道教在西汉中期便已产生。参见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6页;龙显昭《汉代道教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页;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180页。,它具有两大鲜明的特点: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顺时应势、物我合一,主张依阴阳五行的运行规律行事;第二,在个体生命的建构上,原始道教渴望度世延年,希冀以养生的方式实现肉体的不朽。这两大特性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塑造着汉代饮食禁忌的形态。就前者而言,原始道教建立了饮食与四季、五味、五脏间的有机联系,认为疾病皆源于阴阳乖戾、饮食不调。该思想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医学家。《素问·宣明五气》言:“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4]150张仲景也是基于自然节律而规定饮食禁忌的,他强调:“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3]371。在五行系统中,春属木、主肝;夏属火,主心;秋属金,主肺;冬属水,主肾;“四季”(6)据《黄帝内经》,“四季”乃“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的“长夏”即每季的最后十八天,是方士们为了以季节配五行而人为设定的一个时段。参见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释》卷29《太阴阳明论篇》,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86-187页。属土,主脾。又由“木克土”可推演出“肝克脾”,故而,“春不食肝”的原因是在于时人认为春天乃肝气升发的季节,“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3]371。夏、秋、冬和“四季”的饮食禁忌,亦循此理而来。就后者而言,当部分道教徒意识到“度世者,万未有一人”[50]451的现实后,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向此世,致力于寻求强身健体、养寿延年的良方。饮食禁忌就是由此风靡两汉社会的。《太平经》极力鼓吹绝食的益处,宣称“食者命有期,不食者与神谋,食气者神明达,不饮不食,与天地相卒也”[50]718。为尽可能扩展生命的长度,社会各阶层掀起了一股“服食药物、轻身益气”[2]337之风,其中不乏限制饮食、绝禁五谷者。如留侯张良功成名就后“道引不食谷”[6]2044;李少君曾以谷道、却老方见信于汉武帝,所谓的“谷道”就是“辟谷不食之道”[6]453;王充晚年著《养性书》16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26]1630。既要节欲,王充所节制和禁忌的自然也包括肥肉厚酒等“烂肠之食”[51]。由是可见,在原始道教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少食、禁食已由抽象的养生术语变为被各色人士奉行不悖的实践指南。
三
饮食禁忌在汲取汉文化丰厚而多元的营养的同时,又反过来形塑着两汉社会文化。概言之,汉代饮食禁忌的社会功能集中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饮食禁忌架构了官方与民间互动的桥梁
张家山汉简《盖庐》云:“治民之道,食为大葆”[39]11。饮食习尚攸关王朝统治,故当权者或颁发律令,或下达诏书,力图将饮食禁忌作为移风易俗、宣扬教化的支点。官方对民间饮食禁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革除陋俗方面。如前所述,寒食节期间禁热食的习俗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以至多地频现“老小不堪,岁多死者”的惨象。为整风正俗,并州刺史周举晓谕百姓,“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其温食”[26]2024。此举虽有“众惑稍解,风俗颇革”之效,但仅凭新任循吏一己之力,遽难完全废除盛行已久的陋俗。周举离职后,寒食之风愈演愈烈。最后,当权者曹操不得不采取铁腕手段,他一方面颁发律令,禁止百姓继续禁热食,“令到,人不得寒食”;一方面严惩办事不利、因循推诿的官员,“若犯者,家长岁半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52]。在朝廷的管控和干预下,太原等地积久难改的禁热食之陋俗才有所缓和。官、民间的互动,不仅体现在伤风败俗的饮食禁忌被官方所取缔,还体现在官方所规定的饮食禁忌为民间所接受、吸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云:“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39]11作为“现今所见最早的食品安全法的条文”[53],此律表明了政府销毁有毒脯肉的及时性、严厉性和彻底性,凸显了统治者对百姓生命安全的重视。而后,张仲景亦告诫世人:“脯藏朱瓮中有毒,及经夏食之,发肾病。”[3]378有关脯肉的禁忌之所以能深入民间,与官方的宣传、劝导不无干系。只是汉律更关注事后的补救措施,规定一旦有人中毒,则当燔毁所有剩余的脯肉;而民间医书则更侧重防患于未然。通过饮食禁忌层面的种种互动,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向民间渗透,汉王朝政治、文化大一统的格局进一步加强。
(二)饮食禁忌有助于礼与俗、儒与道的融合
饮食禁忌中有不少条目本于儒家礼制。如孔子云:“割不正,不食”[54]。《礼记·曲礼上》谓:“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22]58这是要求人们在宴饮时保持恭谨、谦让、庄重的态势,一举一动不逾矩。但在“礼不下庶人”的闾里巷陌,民众对礼之本质的认识可能存在偏差,对礼的践行力度也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为提高礼仪类饮食禁忌的威信,汉儒们“托之神怪,若设以死亡”[2]979,以民俗为缘饰,力求达到“世人信用畏避”的效果。譬如,《金匮要略》称:“父母及身本命肉,食之,令人神魂不安。”[3]431乍看之,不食父母和自己的生肖肉是为了避免神魂不宁,其实,该禁忌的内核乃儒家的孝悌思想。曾子言:“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22]1225-1226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尽孝不仅要恭敬虔诚地侍奉双亲,还需爱惜保全自己及父母的身体。汉代民众将这一理念投射、比附到象征生命的生肖方面,便推衍出了对本命肉的禁忌。此后,道教徒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解释。六朝道书《太微灵书紫文仙忌真记上经》云:“勿食父母本命兽肉,则元形丧始,根本亡度,胎形号咷……勿食己身本命兽肉,则形神犯真,泥丸减落,三宫闭门,婴儿交错,魂爽飞逐,魄求棺椁。”[55]孙思邈《摄养枕中方》所录“道仙忌十败”也包括“勿食父母本命肉”和“勿食己本命肉”[56]。在化礼为俗的过程中,儒、道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二者的互补趋势也更为明朗。由此看来,儒家的纲常伦理是汉代饮食禁忌的催化剂,而道教又以科条戒律的形式提高饮食禁忌的权威,使其集义理性与神秘性于一身。
(三)饮食禁忌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
汇而观之,汉代饮食禁忌集先秦以来饮食习尚之大成,开后世饮食禁忌之新风,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食材、食用者、时间,构成了饮食禁忌的三要素。就食材而言,汉代民众既有对宗教色彩浓厚的单一食材的禁忌,又有对性能相克的组合型食材的禁忌;就食用者而言,汉代的儒生和医师限定了病人、孕妇及守孝者等特殊群体的饮食;就时间而言,不同月份、节令和日期皆有条目众多的饮食禁忌,仅《日书》中禁饮食的时日便多达全年的1/3。汉代饮食禁忌的文化因子斑驳繁杂,既有儒家礼制的远源,又有谶纬神学的近因,还有中医理念的启发和原始道教的沾溉。一方面,汉代饮食禁忌吸收了早期民众的生活经验,以保障生命健康为旨归,闪耀着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光芒;另一方面,汉代饮食禁忌掺杂着同类相感的原始巫术,附丽着士人们长生不老的迷梦,依旧具有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与时令挂钩、与礼俗联姻、与主流意识形态互相捆绑的过程中,汉代饮食禁忌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凸显。在政治层面,饮食禁忌架起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桥梁,通过取缔民间不合理的饮食禁忌和传播食品安全律令,汉王朝大一统的格局进一步加强;在文化层面,有关父母及自身本命兽之肉的禁忌本乎仁爱孝道,后被道教徒阐发为因果报应说,这是假鬼神信仰之威力,传儒家思想之精髓;在生态层面,汉代统治者秉持“不时不食”的理念,排斥反季节食物,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总之,以汉代饮食禁忌为视窗,我们不仅可体悟官方与民间互动的曲折历程,还可领略礼俗融合、儒道互补的景象,更能看到汉代人为与时令合拍、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