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文化共情
——从《小鹿斑比》看早期好莱坞动画电影的中国风韵
王玉良
动画电影作为世界电影发展史中的一种独特样式,早在20世纪初就进入了公众的视野。1907年,美国的维塔格拉夫公司(Vitagraph)就开始通过“逐格拍摄”的方法进行动画短片的创作,很受当时观众欢迎。随后在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动画电影开始出现不断的繁盛。这位有着德国和爱尔兰血统的动画奇才,从最早创作动画电影开始,就注重吸纳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精粹进行交融。他不断从英国文学故事、德国民间传说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了诸如《爱丽丝漫游仙境记》(Alice's Wonderland,1923)、《骷髅舞》(The Skeleton Dance,1929)等经典作品。早期迪士尼动画电影大量运用了英国浪漫主义、德国表现主义的创作技法,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品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跨文化烙印,较早地呈现了动画电影的“世界主义”特性。
无论在文学书写还是电影创作中,“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时时出现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这里讨论的“世界主义”,既非梁启超笔下的大同世界,亦非偏狭的西方中心论,而是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归属焦虑、对全人类命运普遍关注的自在状态。电影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受多方位因素的影响,其中影人特质、艺术风格和传播样态占据主导地位。电影作为一种流动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最能彰显其世界主义特质。通过弥合文化间的壁垒,讲述一个个世俗故事,产生一种共情效果。二战期间,好莱坞制作的动画长片《小鹿斑比》(Bambi,1942),无论从主题呈现、还是形式彰显方面,都体现了这种明显的“世界主义”特性。抗战结束后,好莱坞电影又重新回归中国主流电影市场。影片《小鹿斑比》于1946年8月29日在上海的大上海大戏院举行放映,这是战后在中国放映的好莱坞动画电影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影片打破了国家、民族与文化间的隔阂,以“大自然和生命关爱”为主题,阐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与道家精神的美学印记,用一种另类的生态叙事彰显了全人类共同的命运处境。
一、黄齐耀与《小鹿斑比》的因缘
提及动画电影《小鹿斑比》的创作,就不能忽视它的一个重要创作成员——黄齐耀(Tyrus Wong)。黄齐耀作为第三代美国华裔代表,9岁就随父离开故土台山远赴美国,自身的世界主义身份,影响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20世纪初,美国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已经对外来移民的限制非常严格。黄齐耀的父亲很清楚,如果想顺利进入美国,要么需有较高的身份地位,要么是有美国亲属。当时,为了满足这些条件,许多移民开始伪造身份,催生出了许多此类的伪造证书行业。这些证书大多价格不菲,各种伪造“纸生仔”(paper sons and daughters, 即美国亲属证明文件)的黑市也应运而生。“从1910年至1940年,有超过17万的中国人在位于旧金山湾天使岛的移民过境站接受审查。其中大约有八九成的都是这种‘纸生仔’,就包括黄齐耀父子。”这些难忘的经历,让黄齐耀认识到了当时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处境,无形中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更加坚定了他后来在西方社会传播中华文化的决心。
中国抗战爆发后,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形象的展现,较之前出现了较大的反转。中美政治上的同盟关系,直接辐射了好莱坞的电影创作。此间,好莱坞制作了一大批中国题材的电影作品。此类作品的创作,无形中带动了华裔影人的参与热情。这一时期,除了黄宗霑、黄柳霜、陆锡麟、杨秀、李霞卿、邝炳雄、黄爱瑞、蒋汉之、陈西兰、罗瑞亭、李清华、郭罗兰之外,还有影片《大地》的技术顾问李时民,雷电华的布景师陆奇等,都活跃在当时的好莱坞大制片厂。1938年,黄齐耀经朋友介绍进入迪士尼公司动画部,开始做中间画画师(in-betweener)的工作。迪士尼公司一向十分重视画师们的绘画技巧,经常出资让他们接受各种艺术培训,甚至还组织专门研究动物的画家为他们举行讲座。但中间画画师繁琐刻板的工作流程限制了黄齐耀的创作活力。他后来转到了《小鹿斑比》的创作团队,因为这部影片需要大量的自然风景。最终他决定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写意风格,融入这部作品的创作中。作为旅美华侨,黄齐耀从小受中华文化浸染,他的绘画风格自由活泼,对故事气氛的营造也比较别致,尤其对形状、色彩、构图的独特运用,重视意境情感而非细节,这种充满中国风韵的创作理念,马上征服了影片的美术指导汤姆·科德里克(Tom Cardick)。随后华特·迪士尼看了他的设计,认为与《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7)华丽的画风不同,黄齐耀的画风比较简约,东方元素的加入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很快就认可了他对影片的美术设计。
华特·迪士尼一贯把独创性看成高于一切,往往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根据共事的艺术家和自己的情绪开展,根本不考虑那些陈腐的概念”。《小鹿斑比》摄制组的很多人也认为,黄齐耀创作的气氛图能启发他们的拍摄灵感,诸如清晨雾气弥漫的森林、质感十足的雪景、熊熊逼人的火焰,很好地把西方的印象派风格与中国的传统诗韵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在黄齐耀看来,对光影柔和笔触的运用能表现角色的天性,突出其个性特征,从而吸引观众注意力。同时他对色彩的运用也非常大胆,通过色彩强化故事情节中的情感要素。《小鹿斑比》以其特有的美感、独特而鲜明的风格超凡脱俗,都得益于黄齐耀的个人奉献,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借鉴,这充分印证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并为民族成员所推崇和膜拜”。作为一部实验性电影,《小鹿斑比》故事性比较淡化,却充满诗情画意,就像一首抒情诗。虽然影片在1942年8月公映后,并没有获得很高的票房而被埋没,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团队都遵从一个华人艺术家的风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好莱坞并不多见。由于黄齐耀在迪士尼片场的出色工作,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迪士尼传奇(Disney Legend)”。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这部电影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风景背景的自然主义风格,像森林和草原的环境,得益于艺术家黄齐耀的印象主义灵感;(2)动画形象设计和动作设计的生理学逼真性。”《小鹿斑比》之所以被公认为动画电影中的经典作品,除了它主题上对生命的礼赞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在画风上对传统形式的突破。英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曾谈到,中国画家认为,“在画中寻求细节,然后再把它们跟现实世界进行比较的作法,在中国人看来是幼稚浅薄的。他们是要在画中找到流露出艺术家激情的痕迹”。西方绘画注重描绘大量细节,中国画家真正要做的是往画中注入自己的激情,这是中西绘画里面的最大不同。早年在奥提斯美术学院(Otis Art Insititute)学习期间,黄齐耀受艺术家斯坦顿·麦克道纳德·赖特(Stanton MacDonald Wright)的启发,就决定将中国传统写意绘画和西方的具象刻画结合在一起,这随即成了他一生追求的艺术目标。他创作中的中国化风韵,很好地弥补西方绘画审美中的缺失,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融合。表现在电影《小鹿斑比》中,即是那种张弛有度的分寸感,在张扬中有内敛,在含蓄中见真实的创作笔触。正如他本人一样,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一直在努力打破东西方艺术创作理念间的壁垒。即使后来加入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美术部门,在他创作的近20部作品的故事气氛图中,也不难发现黄齐耀这一以贯之的创作风格。黄齐耀与《小鹿斑比》结缘,是中国文化在早期好莱坞的一次彰显,这种彰显既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内容意蕴上,也体现在简约质朴的影像风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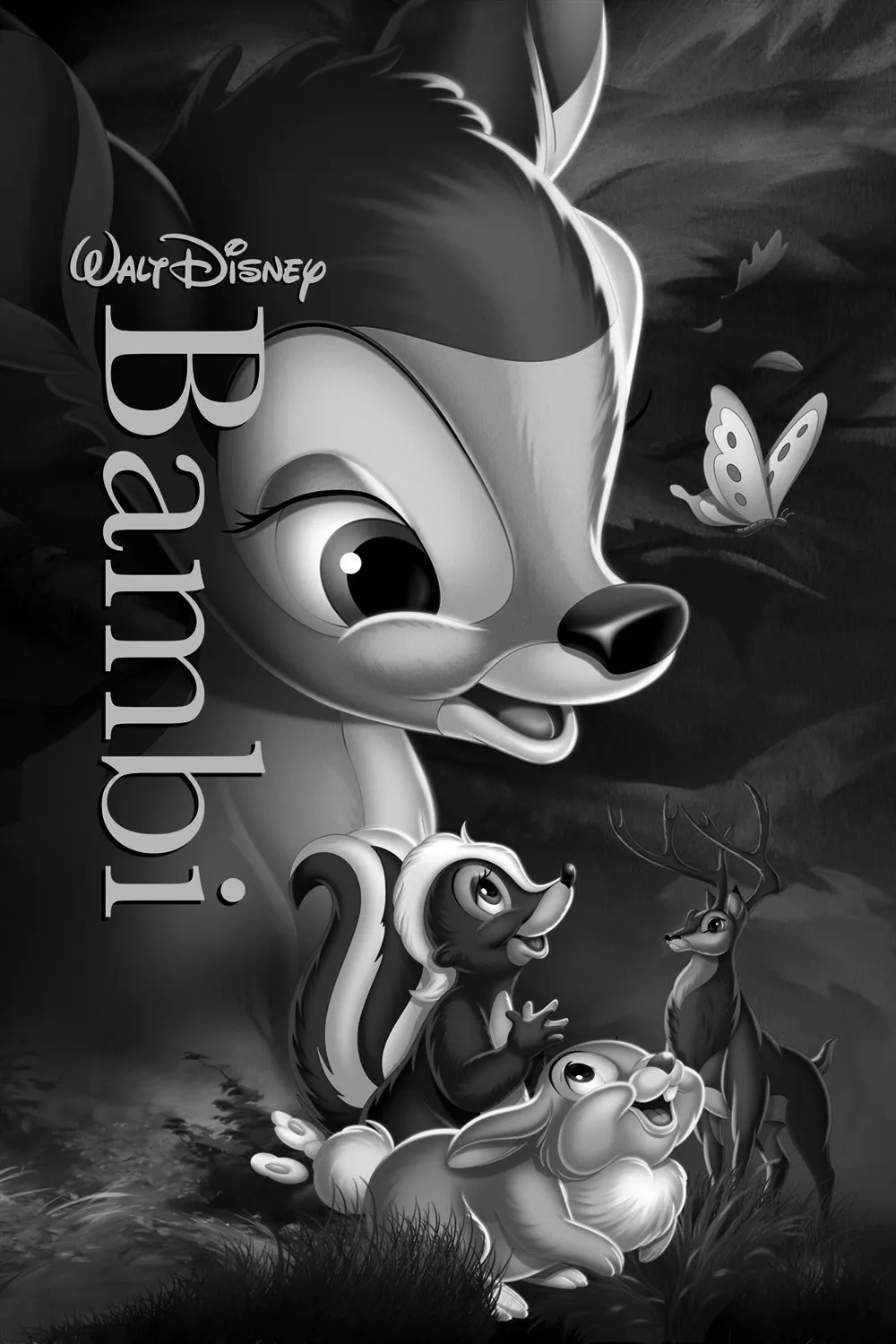
图1.电影《小鹿斑比》海报
二、天人合一的主题意蕴
人对自然的崇敬,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特点。林语堂在《论宏大》一文中曾指出,“人类应被安置于‘适当的尺寸’中,并须永远被安置在用大自然做背景的地位上,这就是中国画家在所画的山水中总将人物画得极渺小的理由。”正是如此,通过“人与景”在画作中尺寸比例的明显差异,凸显大自然和宇宙万物的的宏大与浩渺,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艺术效果,这是中国传统审美艺术观的一种典型理念。“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主要指生命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关系。迪士尼电影公司早期制作的一大批作品中,诸如《花与树》(Flowers and Trees,1932)、《老磨坊》(The Old Mill,1937)、《农田交响曲》(Farmyard Symphony,1938)、《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小鹿斑比》等,都有关涉生命与大自然的主题。华特·迪士尼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位大自然的爱好者,自己很崇敬自然,通过观察大自然中动物的习性,人类可以学到很多。因此,他对自然的这种崇敬感,在影片《小鹿斑比》中得到了极大的宣泄。这是一首对大自然美好生命的抒情诗,也是对生命轮回自然规律的深入思考,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有很深的关联性。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出了宇宙万物的本质属性,那就是遵循“自然而然的规律”。“自然”在这里指一种“自在之状态”。“道法自然”的内涵丰富,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存在关系,尤其是对“生命与大自然”的关系阐释,更是精妙绝伦。影片《小鹿斑比》在主题探讨上,始终是围绕生命与大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关系展开的,对生命轮回深入思考,在敬畏大自然的同时,也注入了对大自然更多的关爱。
首先是对生命的礼赞和轮回的思考。影片以小鹿斑比的出生开始,以斑比孩子的出生结尾,新生命的诞生始终是作品关注的重点内容。这反映出创作者对生命的一种致敬和关爱,一切都处于一种“自在之状态”。尤其是森林中的那个生态群落,更加增添了生命的昂昂生机。在影片开头部分,各种动物们在早晨第一缕阳光的照耀下苏醒过来,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展现了一幅和谐安详的美好景象。一个个温馨可人的家庭,一群群活泼可爱的小动物,勾勒出了生命的美好样态。任何生命的成长都不是平坦无忧的,在欢声笑语中也时刻潜藏危机。斑比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从一头幼崽慢慢成熟,交友、求偶、冒险成了它的必修课程,生理与心理的成长,这一切都是生命演进的自然过程。在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和痛失母亲之后,斑比慢慢认识到了外在的很多威胁,不仅学会了自我保护,而且学会了保护朋友。它所经历的许多坎坷与挫折,正是它的父亲“森林王子”曾经历过的。它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成长的经验。而作为生命符号的“人类”在这里被边缘化了,甚至作为一种危险象征被强调。恰如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人类在大自然中显得十分渺小,甚至被忽视。他们只是作为小动物们的潜在恐惧而存在,枪声和篝火成了动物们的梦魇。人类作为一种批判对象被描摹,这是早期迪士尼电影生态美学的一种策略。影片通过展现斑比的成长经历,阐释了一种生命存在的自然状态,既是对生命轮回的无尽思考,也是对大自然和环境问题的殷殷关切。
其次是对“道”与“自然”的关系阐释。老子所说的“道”指的是自然之规律,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道法自然”即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里的“自然”则是指事物本有之状态。影片《小鹿斑比》就很好地阐释了“道”与“自然”的微妙关系。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生老病死的生命更替,都可以视为“道”的外在表现,而这些外在表现又都是一切事物本有之状态。在影片中,季节的转换十分明显,尤其是斑比出生的季节,正是冬去春来的交替时节,在经过了严冬之后,万物苏醒、草木葳蕤,小动物们迎来了成长的最佳季节,生命在这里勃发。在多雨的夏季,母亲带着斑比在森林里练习生存的本领;在瑟瑟的秋风中,斑比与所有小动物一样,都在寻找各自温暖的家园;在皑皑白雪的冬季,失去了妈妈的斑比开始面对严酷的命运现实;在鲜花盛开的春季,斑比为自己孩子的出生感到骄傲。影片中春雷、夏雨、秋风、冬雪这些影像符号,不仅很好地诠释了季节的更替,而且也与斑比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生命的更替在这里也成了自然之规律,斑比的成长、母亲的死亡、孩子出生,一切都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此外,影片也一直在展示一种心理规律,即个体生存的“恐惧与死亡”。影片对这两种心理进行了真实而又自然的描摹,通过具体的影像空间展示了斑比的这种精神状态。当斑比第一次步入大草原时,母亲谨慎的声音加剧了它对草原危机四伏的恐惧心理,“千万不要跑到草原上,那里到处都是危险,没有树林和灌木让你藏身”。草原的场景暗示了大自然不仅仅是动物幼崽的游乐场,同时也是危险的存在。这是生命最本真的心理状态,同样阐释了“道”与“自然”最质朴的关系。影片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化繁为简,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不谋而合。森林、草原、河流、冰川这些自然景观,在影片中与生命融合在一起,无形中上升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之中,倾诉了《小鹿斑比》这部作品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无限关爱之情。
影片《小鹿斑比》实践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意蕴,同时又超脱了这种意念。在这里“人”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它已经泛化为一切生命。影片是对生命的礼赞,甚至通过对“人类”的反证,来诉说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破坏大自然规律,给森林生物带来灾难的,正是人类。因此,影片自始至终甚至没有出现一个人类的全幅画面,从侧面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揶揄和批评。在这里,人类成了灾难、恐惧和死亡的代名词,他们肆无忌惮地屠猎森林中的动物,粗心的露营导致了森林大火,给小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无形中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产生一定的隐喻关系。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讲,难免不会联想到纳粹集团在全球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难民们在战火纷飞中四处流散的悲惨场面。表面上看,影片在于倡导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命价值的可敬可贵。虽然没有明确的反战暗示和所指,但作品诞生的时代,又让我们不能不产生一些联想。正如布雷恩·汉德森在讨论神话的作用时所强调的那样,这“始终联系着讲述神话的时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时代”。
三、至简至情的影像表达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大道至简”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种质朴简约的美学追求。郑板桥就曾以“删繁就简三秋树”来要求自己,主张以简练的笔墨来表现饱满丰富的内容。简约并不等于简单,它可以有效平衡形似与神似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中国绘画艺术常常遵循的一些规则。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它从绘画中继承了很多东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维克多·弗里伯格(Victor Oscar Freeburg)在其著作《银幕上的绘画美》(Pictorial Beauty on the Screen,1923)一书中曾说,“我把电影当作绘画来欣赏。除了作为绘画以外,不可能作为其他东西来欣赏。”影片《小鹿斑比》的背景画创作者黄齐耀在采访中曾坦言,他从宋朝绘画中吸取了很多营养,诸如简单的线条,淡淡的水墨,都是它创作本片的灵感来源。因此,影片《小鹿斑比》在影像表达上,基本呈现了一种“至简至情”的美学风格,不仅画风简约质朴,而且景语与情语互为依托,很好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今天看来,《小鹿斑比》每个画面中的景物背景都是相当简洁,展示出一种简单的形式美。当时有中国杂志评价迪士尼动画时这样描述“迪士尼的作品,在结构的设计上,看来是这样的简单,但它们却是上流的美术作品。”尤其是黄齐耀把中国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很好地融汇到了影片中,他创作的背景图既华丽又简约,而且还有十分强烈的氛围感。诸如影片开头的段落中,先用横移镜头和推镜头介绍森林中的主要环境,随着各种小动物的出场慢慢把焦点落到斑比母子身上。作为背景的景物都相当简单,森林中的树木、草地只起到一种陪衬作用,并没有被刻画得十分真切,仅仅是一种气氛渲染。当母亲第一次带斑比进入草原时,画面前景只是一些寥寥的草叶,背景是整块的青蓝色色调,主体位居中景,整个画面在简洁中透出一种紧张与不安,叙事中的情绪自然而然地被带动出来。全片的背景处理很明显避开了写实技法,通过写意的方式,让画面的意蕴很好地传达了出来。当然,这些场景都是从现实中生发而来。据说,迪士尼为了营造影片特殊的艺术氛围,特意派两位摄影师前去缅因州的卡塔丁州立森林,为动画师拍摄鹿和树叶的模型镜头。通过定格处理,在场面调度方面给场景赋予了非凡的深度感。从部分段落中不难看出,创作者通过这些简单的构图,仅寥寥几笔。便将这些情节中的情感、意境和神韵都展现了出来,同时也为森林附着上了几分神秘的质感。
早在电影诞生之处,色彩已经作为叙事的重要元素,在影片创作中广为流传。据统计,“早在1920年代,大约80%到90%的默片的胶片都已着色,制作者宁愿牺牲自然主义风格,也要用颜色来表达情感。”因此,早期电影都青睐于通过色彩来营造视觉奇观和激发观众情感。《小鹿斑比》作为迪士尼的高预算大制作影片,延续了此前动画作品的形式风格,在色彩方面也下足了工夫。本片在色彩使用上十分考究,充分发挥了色彩的表意功能。罗素·坎贝尔在其《电影摄影实践》一书中曾提到,“对美国人来讲,颜色与情绪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冷色调(像蓝色)有种离间效果,而相反的暖色调(黄色或红色)则让观众走近。”《小鹿斑比》在色彩处理上,通过一种简约的风格,形成了全片整体的色彩基调,这些主基调主要由深绿、灰白和火红组成。在呈现森林和草原的景貌时,大部分用的深绿冷色调,凸显森林的神秘和草原中的危机四伏;在冬天下雪的段落,几乎都是灰白的冷色调,暗示了环境的恶劣和即将到来的不幸;森林大火的段落主要以深红色调为主,营造了一种炼狱般的境况,把当时情况的危急和小动物们的命运很好地关联在了一起。这些单纯的色调简约而不简单,却带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在这里,色彩除了产生戏剧化的效果之外,更起到了强化叙事的内在情感作用。
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国学大儒王国维也曾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都说明了在艺术创作中,景语与情语相互交融的重要性。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这些叙事艺术都十分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都典型人物,达到情景交融的美学效果。景属于客观范畴,情属于主观范畴,情与景的关系属于心与物的关系。因此,在电影创作中,好的场景选择往往能够产生“景有尽而意无穷”的作用,最终达到情与景的完美交融。影片《小鹿斑比》之所以能成为影史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片在景物呈现上,能很好地与主题意涵相契合。通过对大自然的描摹,无论是森林中的晨雾、雪景,还是火焰,都能展现得充满诗意又意蕴十足。例如,斑比和妈妈在雪地觅食那个情节,满眼的雪花飞舞,寒风凛冽,妈妈带着斑比在撕咬树皮充饥,食物短缺母子在丛林里忍饥挨饿时不禁让我们产生一种怜悯之心;当母亲发现一片嫩草,赶快叫出孩子充饥时,又有一种温暖如春的感觉;而母亲为了救斑比被猎人开枪打死的那刻,森林中的幽暗又给人一种不详之感。结合情节发展,环境的变化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情和景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交融。以景抒情,以情衬景,二者互为表里,是影片《小鹿斑比》最为突出的特征,这种情景交融的叙事影像,流露出了创作者悲悯的生态观感和人文情怀。
结语
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全球肆虐,其咄咄逼人之势使好莱坞的电影创作开始不断关注战争、民族主义、民主和平这类主题。虽然《小鹿斑比》诞生于二战期间,但影片却采用了另类的叙事策略,它没有明显的政治宣传和战争色彩,而是倡导了天人合一、生命轮回的美学观感。影片在主题阐释上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线,用一种另类的生态叙事向世人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生命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过程。2011年,该片被列为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名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名录,永久珍藏。由于当时战争的原因,迪士尼丢失了包括欧洲在内的大片发行市场,致使《小鹿斑比》没有取得很好的票房收入和观众口碑。但迪士尼早期动画电影中的这种审美倾向,却形成了一种美学气质被传承,即通过讲述人类的共同命运,引发全球观众的文化共情和情感共鸣。例如,近些年的《寻龙传说》(Raya and The Last Dragon,2021)就是典型案例,影片以史诗剧的气魄,纵论天下“分久必合”的大趋势,在民族、国家、地域之间探讨团结和信任的重要性,用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的终极命运投入了极大的关切。今天看来,《小鹿斑比》是迪士尼发展历史中一部至关重要的作品,尤其是通过世界主义视角和文化共情机制,对典型角色的拟人化塑造、对自然景观的抒情性描写、对动物群体的纪实性观察、对田园生活的操纵性处理等,都成了后来动画电影创作上很好的参考范本。
【注释】
1影片《小鹿斑比》广告.申报[N].1946.08.29.
2 Julie Leung,Chris Sasaki.Paper Son:The Inspiring Story of Tyrus Wong,Immigrant and Artist[M].New York:Schwartz & Wade Books,2019.
3[美]陶乐赛·琼斯.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M].邢祖文,刘宗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15-138.
4[美]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M].刘宗锟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540.
5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257.
6 Jenny Cho and the CHSSC.Images in America:Chinese in Hollywood[M].Charlesston, South Carolina:Arcadia Publishing, 2013:52.
7 Kirsten Moana Thompson.Classical Cel Animation,World War II,and Bambi[J].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1:12.
8[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3.
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越裔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264.
10同5,12.
11[美]布里恩·汉德森.《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J].戴锦华译.当代电影,1987(04):68.
12[日]岩崎昶.电影的理论[M].陈笃忱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91.
13纪录片《美国大师:华裔动画师黄齐耀》,导演帕梅拉·汤(Pamela Tom),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出品,2017。
14世界权威卡通画家华尔特·迪士尼之研究[J].冯天佑译.中国电影,1941,1(02).
15Roderick T. Ryan.A History of Motion Picture Color Technology[M].London:Focal Press,1977:77.
16Russel Campbell.Practical Motion Picture Photography[M].London:Zwemmer,1970:89.
17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278.
18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