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身体的影像建构与意义生产
——再读电影《大路》
乔洁琼 孙 磊
《大路》是孙瑜20世纪3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集合了全联华的男星和当今中国银坛最负盛名的小鸟陈燕燕,甜姐儿黎莉莉”,有“二十明星主演/四支特制新曲/全部配音歌唱”,因此,《大路》的公映被誉为“民国廿四年第一大事件”,放映一时到处客满。甚至有人说没有看过《大路》就是“没有看过电影”。《大路》“启发了观众的一种民族意识……从这里,显然地国产片转上了一个新动向。这就是从现实主义的阶段更进一层的大步走入了反帝的阵线了”。《大路》不仅表现了抗日的热情,更重要的在于“进一步把抗日的斗争与中国工人阶级联系起来,将工人阶级描写为抗日斗争的中心力量”,“是一部歌颂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诗篇”。《大路》作为一部左翼电影的典型代表,塑造了“工人”这一具有政治意味的“现代身体”。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身体?约翰·奥尼尔认为身体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通过社会来思考身体,通过身体来思考社会、影响社会”。中国现代身体产生于革命、启蒙、救国等现代性议题下。所谓中国的现代性,可以理解为,“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紧密相关,这种意识本身来自中国人对达尔文进化概念的接受,……在这个新的时间表里,‘今’和‘古’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新的重点落在了‘今’上,‘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时刻,它将和过去断裂,并连续上一个辉煌的未来”。现代身体是在新旧交替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政治性身体,本身代表了“今”的诸多特征,并融入了政治性、阶级性、社会性等范畴。
《大路》中的“筑路工人”就是新旧历史时期产生的“新民”,其健康美是在晚清以来提倡的军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对身体进行改造的历史背景下建构起来的银幕形象。《大路》中的筑路工人也体现了当时最时尚最先锋的意识。影片将现代身体以时尚的面容进入电影产业,通过“凝视”这一观看机制,工人“主体”形象得以建构和传播。同时,这个身体的呈现又指向了未来,与社会主义工农兵电影的身体美学一脉相承。
一、政治与现代身体的影像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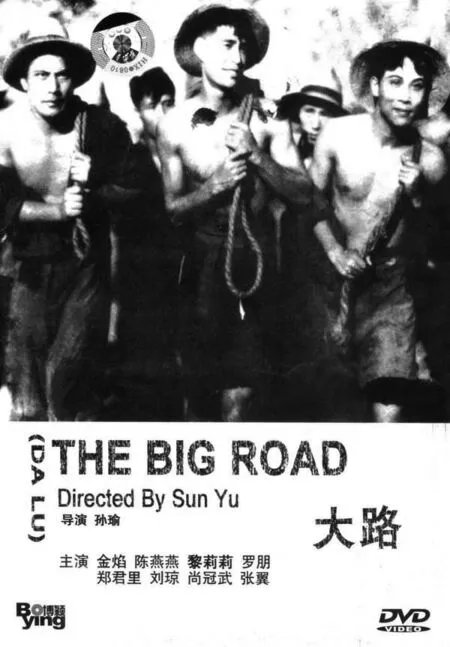
图1.电影《大路》封套
中国现代身体建构的过程是中国由传统儒家伦理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蜕变一种政治表征,是新旧交替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角力的结果。直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从来不认为是问题的身体上。梁启超在《新民论》中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孙中山呼吁中国应将身体视为国富种存的根本基础。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认为西方列强的强大首先在于国民身体强健,中国人要摆脱东亚病夫的面貌,必须从强身健体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现代身体”作为一种“行动纲领”上升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领导阶级的观念被召唤和建构。“工人”由一个职业称谓逐渐变成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词汇,而“工人身体”从形象到叙事都需要建构起一整套话语来取代由传统伦理纲常规定下的“封建身体”,进而适合新的政治观念和文化逻辑。如果说中国“传统身体”是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受家庭的“托管”,服务于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现代政治观念中的身体则走出家庭,交付于“国家”,“倾向于以国家主义来统整人民的心智与身体”。约翰·奥尼尔认为,“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以某种符号性的方式表达其有关信念。”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中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呈现的“工人身体”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阶级属性的劳动者的身体,而是与国家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询唤功能的政治符号。
从20世纪20到30年代,中国电影的银幕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反映出的是潜在的国家政治走向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国产电影的男性“身体”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家庭、婚姻、爱情为主题的身体叙事。这类影片常常描写跨越阶级的爱情,迎合当时小市民的观赏心理,银幕上的男性形象整体呈现出阴柔羸弱的气质,充满了忧伤哀怨的情调。以金焰主演电影为例,《野玫瑰》中的画家江波,《桃花泣血记》中为情所困的少爷,《银汉双星》中的明星等。另一类则是被主流社会放逐的男性身体,如土匪、侠客等。风靡一时的武侠神怪片,其角色虽阳刚豪放,却缺乏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银幕形象依然寄宿在传统的伦理纲常体系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救亡图存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国影坛集体“左转”,在此氛围下,“身体”被推到一个关涉民族存亡的重要位置,中国电影中呈现出明显的“身体转向”。此时,中国电影开始践行民初以来知识分子的身体主张,“体育救国”多次出现在电影创作领域。孙瑜的一系列电影所呈现出的身体叙事,就是当时社会政治在身体上的反映。他曾说:“强身不见得就可以救国,但是救国家的国民,身体必须是强健的”,“我们研究提倡体育,在强身的条件以外,还必须养成一种新的精神:纯洁、诚恳、坚忍、奋斗、勇敢、求进、切实、公正,还有那最要紧而我们最缺乏的团结精神!”《野玫瑰》《小玩意》等片中的孩子军形象就是清末民初“军国民运动”的缩影,《体育皇后》中的林樱是当时提倡现代健康美的反映,《大路》更是将身体政治推向极致。
“民族危机有助于化减旧有道德和伦常体系对身体的垄断和支配,但也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身体许多新的政治使命。”《大路》彻底摆脱和抛弃了传统的伦理纲常体系下的“中国身体”,代之以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身体形象。影片强化了筑路工人身体的国家属性和民族属性,他们不属于某一个家庭,而是属于国家和民族。他们筑路是为了国家,而国家也是他们最后的保护,这样影片就将“身体”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大路》作为金焰塑造的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劳动者形象,一扫之前银幕小生的淫邪气质,为影坛吹来一股清新健康之风。金焰从扮演大少爷、明星、大学生到筑路工人,不仅影片中角色的身体进行着政治的蜕变,作为演员的金焰也同样交付了自己的“私人”身体,从传统的家庭伦理“身体”转向了共有的“身体”。为了拍摄《大路》,金焰无暇照顾即将临盆的妻子。在影片公映前夕,金焰领唱影片的主题曲《大路歌》《开路先锋》,而他与王人美的孩子生下八天,不幸夭折。金焰与片中角色同时将身体交付与国家和民族。
影片通过新旧身体的二元对比建构了新的工人阶级身体。在《大路》中,正、反两派的身体对立通过空间进行了呈现。工人劳动的场景是开阔的外景空间,采用自然光,男演员较少化妆痕迹,这使得影片呈现出粗犷、奔放、大气的视觉效果和纪录片一般的真实感。他们修筑的是一条军事公路,这条路是为了抵抗敌国炮火蹂躏而建,工人的动作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这一空间变成了富有政治意味的场域。“道路”也因为工人身体的“展演”而产生了普遍性意义。“筑路工人”代表着新的权力话语载体,这在之前的电影中从未出现过。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份表征,他们身体的属性具有公共性,属于国家和民族,而非家庭,这正是“现代身体”的重要政治表征。同时,工人是以“群像”形式出现,这赋予工人以社会意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伦理关系,而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同志”关系,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奸。他们是乡绅地主,家庭的构成有老爷、管家、夫人、小妾、丫鬟、护院,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结构中的家庭。作为反派,电影赋予其落后性和反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庭院后面的地窖,是封建社会乡绅家庭的标配,是为了惩罚那些挑战传统礼教、伦常和夫权的叛逆者,通过对身体残酷的刑罚,来迫使这些叛逆者践行礼教、遵守权威。工人们被汉奸、劣绅关押在地窖之中,地窖变成了一个爱国者与汉奸的斗争空间。封建乡绅代表的不仅仅是旧秩序、旧权力,还代表一种卖国势力站在了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现代身体”与“传统身体”在影片中通过空间这一载体得以建构,空间作为“权力的眼睛”建构着身体,身体也决定着空间的建构,并“通过空间的建构来凸显自身的价值”。
因此,《大路》中建构的身体高度符号化并具有超越性。影片放映后,有评论就指出“作品前半部分看到的劳动者的生活,使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一种诱人的憧憬和热情,而绝不是现阶段的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作品所表现的劳动者的生活,是编剧者的理想化的社会的幻觉。”影片中强调的“工人身体”并非现实中受剥削与压迫的真实的“工人身体”,而是被赋予了阶级、救亡等政治色彩,是具有革命、启蒙意义上的现代身体。《大路》中劳动者不再是《春蚕》中的受压迫的弱者形象,而是与力量,健康、生命、精力联系起来的先进阶级形象,这个形象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影片通过景别、造型、运动等表现手法,强化了符号的象征意义,如影片以工人们赤膊干活开场,伴随着激昂的歌声,“联华”男星集体上阵,呈现在银幕上的是荷尔蒙爆棚的健壮的男性身体。在烈日的照射下,他们裸露着的肌肤闪烁着健康的光芒,散发着雄性阳刚的魅力。这一场景奠定了影片的总基调:阳刚、乐观、质朴、正气。开篇中工人们身体的光泽、姿势、动作都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而是具有德勒兹所谓的“超验形式的呈现瞬间”,这一瞬间不只是单纯的运动,而是指向了永恒。在《大路》中,导演孙瑜通过多次的重复强化了工人身体的“特殊瞬间影像”。除影片开头部分赤膊干活之外,他们身体前倾,吃力地拉动着沉重的石磙,大路在他们脚下延伸……最后工人们壮烈牺牲的场景,也被高度抽象化,这完全超越了影片中的其他运动瞬间,仿佛定格在那里,具有永恒的意义。马克思说,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并在对象化的本质活动中升华了自身。《大路》因此完成了现代身体的影像构建。
二、凝视与现代身体的意义生产
《大路》中的现代身体既然是一种政治表征,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那么这种工人形象如何实现意义生产并进入历史场域?换言之,作为现代身体的“工人”的观念是如何与公共空间相连接进而进入历史的维度并指向未来?在未经历过工业革命,整体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现实来讲,“工人阶级”不仅是一个新生的劳动阶级,也是一个具有革命和启蒙意义的新兴词汇。“工人阶级”这一主体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领导者的形象还未被建构起来,其政治符号意指仍未形成。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镜像阶段是个体生命史、主体形成的阶段,……而主体不等于自我,是自我形成过程中建构性产物。”彼时,民众对工人阶级这一主体及其认知仍处于拉康所谓的“婴儿阶段”,不仅工人阶级无法确认自身的形象,民众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政治意义的对应物。观众作为一个“先验的主体”还未形成,因而不能与银幕形象实现“认同”。因此,当孙瑜运用“高尔基式革命浪漫主义”将筑路工人以一种全新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工人形象”呈现在银幕上时,这一现代身体却超出了当时观众的“期待视野”。这一现代身体却超出了当时观众的“期待视野”。当时观众认识并理解的工人形象是苦难、悲惨、深受蹂躏的。影片被认为没有“忠实描写筑路工人的生活”,是“非现实的”,认为《大路》用一种热情把黑暗的现实诗意化了,因此“形式与内容不调和”。观众通过“凝视”影片形象,建构起一种对理想身体的想象。他们的凝视对象是“非现实”和“不可见”的。工人的“现代身体”在现实中处于缺席状态,也就是麦茨所谓的“想象的能指”,“观众通过自己在场去指认这种缺席”。因此,具有政治符号意味的工人身体需要经历一个自我对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确认的过程,这也是现代身体意义生产的过程。《大路》中全新的工人身体通过“凝视”这一观影机制进入形象的建构与认同中。与好莱坞电影通过剧中人物视角来体验故事,刻意切断观众与银幕空间的做法不同,《大路》打破封闭空间,让观众直接进入故事,观众不仅能够达到“缺席”,还能够获得一种反身性自我建构。
《大路》将“工人身体”纳入消费主义语境中,通过摩登女性的凝视突出了“现代性”。《大路》中“凝视”包含着复杂的层次,除上述的直接凝视外,还具有鲜明的性别视角。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电影叙事》中指出,人们的观看实际上是被男权主宰,女性作为客体被展示与被观看,承受着男性的凝视,迎合着男性的欲望。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情节框架内被动的客体,因为在好莱坞电影中情节大多由男性推进,女性形象承担着片中男性与观众“凝视”的功能,辅助男性完成叙事。纵观中国早期电影莫不如此。《申报》中的电影宣传基本上站在男性消费的角度上,“肉感”“刺激”等描述女性肉体来获得宣传效果。“肉感之能达到精神上的兴奋,精神上的刺激是毋庸讳言的,所以,浪漫肉感、诱惑刺激、丰满的臀、乳峰肉感的号召性标语在营业不振时尤其要作为生意的依傍,以‘肉感’为生意经来标榜,是舶来片的妙招,也是早期民族电影的法宝。”除了电影的女性身体被男性作为欲望对象进行了消费之外,早期中国电影的女性在叙事框架中,也常常作为附庸被动跟随叙事进程。即便一些为女性量身打造的影片,如《桃花泣血记》《恋爱与义务》《一剪梅》《野草闲花》等,依然是将女性塑造成被凝视的“客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男权视角。
作为一部男性主创的电影,《大路》却反转了以上的论述,“混杂”了女性与男性的观看视角,将“身体”功能复杂化。影片既有“女性展示,男性凝视”,又有“女性凝视,男性展示”。女性凝视具有崇拜性,如丁香和茉莉对男性的“点评”:“我爱金哥的勇敢!他总在微笑,他永远向前,从没说过这事难办!我爱老张的铁臂!他不大说话……”勇敢、铁臂、聪明、粗笨等男性特质成为青年女性的新宠,与之前太太小姐的审美趣味迥异。她们在评价这些男性的时候,眼睛看向画外上方,这一视线也高于观众,她们的凝视具有崇拜性和公共性,指向了一个并非现实的对象,使筑路工人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承载了人们憧憬和向往。影片通过丁香和茉莉这两个摩登女性,使本身并不具有消费特征的工人身体具有消费性,从一个现实职业变成了富有政治含义的艺术符号,从而成功进入公众视野。当时评论认为,本片的不足在于,丁香和茉莉是“擦粉烫发”阶级的女性,是一种“编剧者理想之女性,而不是现实的劳动阶级的女性”。然而,换一个视角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这两个“摩登女性”架起工人形象进入大众的桥梁,《大路》很可能会成为像《春蚕》一样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因此本片成为年度“不得不看”的电影之一,就在于其对电影时尚本性的充分利用和挖掘,进一步促进了影像的意义生产。“民国时期时尚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总体上的进步感,时尚是一种媒介,通过它,人们能跟上自己所选择的民众团体”,联华公司正是将新型的意识形态通过时尚引领的方式确立了“新派”电影公司的身份。而《大路》成功将一种个人的审美与公共空间相连接,将新型的工人身体通过时尚、大众媒介转化为一种新的共同意识,赋予工人身体以“生产性”。在都市消费环境语境与明星效应下,通过多重“凝视”,使个人选择和社会趋向紧密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下,丁香、茉莉和工人们的觉醒以及她们的民族主义意识通过大众媒介变成了时尚的一部分,通过跟随这些新的偶像,大众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现代身体并逐步构建起自己的身体形象。
《大路》的“凝视”也赋予女性身体现代意味。传统伦理观告诫人们:“非礼勿视”,而影院的放映环境却将男性身体放大,这一方面赋予女性观看男性身体的合法性,赋予她们性别平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也构建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通过电影的放映、观看、评价等一系列机制将妇女解放这一现代观念隐藏其中。再如观看男人洗澡段落突出了女性的主导性和控制性。茉莉和丁香“俯视”着男人们,空间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让她们得到一种超越封建伦理的居高临下的精神快感。众所周知,当时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是被动的弱者,在大部分影片中面临着被抛弃、堕落、死亡的命运,而《大路》满足了她们主宰世界的幻想。本片的叙事框架并非仅仅由男性构建与推进,女性既是男性的欣赏者、观看者。随着故事的推进,她们成了男性的“拯救者”。影片后半部分,丁香和茉莉主导了叙事的进程。当她们勇闯虎穴,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拯救了男人,她们不再是柔弱的代名词,而是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现代身体的主体召唤
《大路》所创造的“现代身体”以一种“新人”的形象出现在早期中国电影中,其所召唤的工人“主体”的建立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对中国电影的人物谱系开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应该说《大路》中所塑造的工人身体进入了历史的维度,体现了工人阶级这一具有先进意识的领导阶级是如何成长为历史主体的。阿尔都塞指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存在的,但不具有“主体性”。银幕上的工人形象与真正的工人之间是一种“想象性关系”,而这种想象关系由于缺乏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构架,其位置与合法性受到质疑。观众会根据现实中的工人形象的标准去评价电影中的人物,觉得电影人物脱离了现实。具有进步思想的孙瑜在电影中的工人阶级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时候,就在《大路》中将工人这一具有未来指向的形象进行表达,突出描写了工人的反抗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片头曲《开路先锋》唱到:“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同/是谁阻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我们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对准了它/轰轰轰/看岭塌山崩/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歌曲中的道路、障碍、炸药、山峰等意象都具有十分明显的隐喻色彩,障碍就是指汉奸、乡绅、日本侵略者。面对这些阻碍我们进路的障碍,工人应主动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工人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阶级,这就是“我们”。从“我”到“我们”,从被欺压到团结起来反抗的叙事意味着工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构架下,工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合法位置,因此,影片只能提供一种想象性解决,即以工人以身殉国作为结局,正是这种身份不定、前途不明的“主体”的必然命运。
新中国建立后,以工农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份整体性想象图景”,工人作为“主体”成功被赋予了合法的位置,也接受了现存位置的合法叙事。因此,如果说《大路》生产了一个“现代身体”,那么“工农兵”电影则将“工人”身体的生产转向主体认同,将工人成功从“个体”传唤为电影的“主体”,同时也是国家的“主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大路》所创造的工人形象指向了未来,与工农兵电影的身体美学一脉相承。
1949年后的中国电影是以“工农兵”文艺思想为指导进行创作的。工人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新中国的银幕上。如《桥》讲述了东北某铁路工人为了支持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工人们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将大桥修复。《桥》中的工人同《大路》中的一样,他们的身体属性都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性,都是以一种“新人”面貌出现,同时他们的身体都具有“生产性”。不同的是,《大路》的工人在斗争中死亡,结局弥漫着一股悲壮之美,而《桥》的工人取得了胜利,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豪情。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大路》上映于1934年,此时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前途生死未卜,工人阶级力量薄弱,而工人主体尚未建立,人们是在消费主义语境中理解工人及其身份意义。而《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故事片,站在回溯历史的视角去讲述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已经从边缘人成为国家主人,“主体性”已经建构。或者说观众是在一种建设新中国的语境中理解工人及其身份。此时的身体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制化话语,“生产和建构着想象界与现实界的身体和身体话语”。因此,《大路》中的身体由于缺乏主体的认同主要以“消费性”为主,而《桥》则是一种已经建构起主体的“生产性”身体。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主体性的建构。
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与启蒙”的左翼话语之下,《大路》的产生具有重要的谱系意义。“电影只不过是一个主体的映像”,从《大路》到新中国电影,这个映像呈现了主体的生成过程,让我们在镜像中,看到了工人主体形象的流变。《大路》中工人们修筑的公路遍布祖国大陆,并不断向远处延伸,这些影像象征着工人的地位与位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大路》召唤出了作为现代身体的工人主体,并将这一主体纳入历史的网络,预示着未来工农兵电影的方向。
结语
《大路》是20世纪30年代一部独特的左翼电影,编导孙瑜所创造的工人群像在中国电影史上首次赋予工人身体以现代属性。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影片通过新旧对比建构了工人的现代身体,通过电影的观看机制实现了现代身体的建构与意义生产。在时尚风潮的引领下,影片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阶级意识、女性意识等现代性议题逐渐得以传播。应该说,《大路》有意识地将具有政治意味的工人身体的“展演”带入公众视野,将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者塑造为救亡主体进入历史的维度,与建国后中国电影中的工人形象具有一脉相承的谱系性。
【注释】
1孙瑜全力修筑“大路”[J].联华画报,1934(5):1.
2广告[N].申报,1934.12.25(27).
3广告[N].申报,1935.01.05(33).
4转引自袁庆丰.左翼电影的模式及其时代性—二读《大路》[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9(4):15.
5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343.
6[加]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态[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7[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4.
8黄金鳞.政治·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6.
9[加]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态[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10黄金鳞.政治·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2.
11同10,191.
那既然这些活动都交给学生来自主管理、自主参与了,那中队辅导员们是不是就无事可做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队辅导员除了要在活动中适时地给予队员必要的帮助外,还应该在每次活动前设立合理的评价机制。当然这个评价机制应该是多渠道的,并非仅仅包含辅导员对队员的评价,还包含个人自评、队员互评、学校和家长评价等。如此多渠道的评价模式,必能激励和促进队员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活动,提高队员的评价能力和自我改进能力。
12光洲.大路·评一[A].陈播.三十年代左翼评论文选[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168.
13[法]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M].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8.
14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3.
15孙瑜.银海泛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12.
16同12,165.
17流冰.大路·评二[A].陈播.三十年代左翼评论文选[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168.
18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8.
20同12,165.
21[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6
22陈越选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361
23史静.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内外的身体话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
24[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