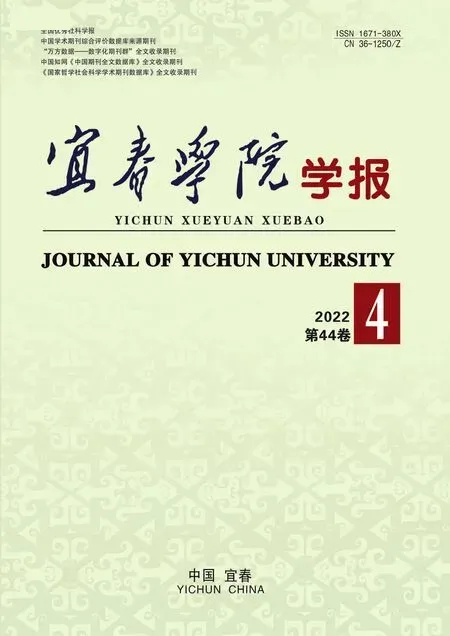巴赫金语言教学法的现象学之维
罗益民
(宜春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并非专门的教育理论家,但随着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他的观念已经对教育领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1](P1)就其影响的主要方面而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复调学说被教育学界关注与吸收,甚至在国际上已出现“巴赫金式的教学法”(Bakhtinian pedagogy)[1](P1)的提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著作中也有对教学法思想的直接阐发,这体现在他写的《中学俄语课上的修辞问题》一文中。“就风格而言,此文属教学法研究著作。”[2](P483)这篇关于语言教学法研究的文章对于探讨巴赫金特有的教学法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是其教学理念与语言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通过把语法现象还原到情境感知来培育出学生的表述能力,以此生成学生的语言个性。在此意义上,这种教学法可以说是一种表述式的教学法,它既承续了古希腊已出现但未得到彰显的重声调的语法传统,也体现了巴赫金语言理论的现象学立场。而学生的语言个性最终指向学生主体及其个性的培养,教师的责任则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言语主体,即巴赫金后期语言现象学中语言化的主体——在一种对话关系中的对话者。这也构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一种补充,对话的建构不仅需要对话态度,也需要愿对话、能对话与会对话的人,也就是对话者,而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在实践层面便是培养这种对话者的。这种教学法对中学语文教学、大学的文学教学甚至作家的文学创作均富有启发意义。
一、语言教学中的现象学立场
巴赫金的这篇教学法文章可分为教学法与思想两个层面,[2](P484)两者均力图还原到直观的维度,而就直观在胡塞尔现象学那里的基础地位而言,这两个层次共同指向了一种现象学的立场。
巴赫金教学法的这两个层面也与当时教学法界的两个主要派别有关。一派是侧重对活的语言的学习,重视修辞尤其是语法修辞,批判语言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和繁琐哲学的倾向;而另一派则遵循理论语言学或索绪尔—形式主义语言学立场。巴赫金接近第一种立场,在教学法层面侧重语法修辞的教学,而在理论层面批判理论语言学或索绪尔—形式主义语言学。俄文巴赫金全集的编者为此文写的“题注”中对这两个层面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从表层看,这篇文章是对具体句法现象(无连接词复合句)所作的局部性修辞与教学法的分析,其目的就如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培养学生言语的个人独特风格;而从第二层面,即理论层面看,文章的主旨同时又在于更精确地阐释作者一个总的语言学见解。”[2](P486)这个总结所概述的两个层面都可以还原到直观的维度。

而就第二个层次即语言理论层面来说,俄文巴赫金全集编者所写的“题注”一方面承认这个层次体现了巴赫金“总的语言学见解”,但在解释中却突出了巴赫金后期的超语言学或表述理论对其语言教学法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从巴赫金总体的语言学见解来说,不仅包括后期语言学思想,也包含前期语言学思想。在巴赫金前期思想中,“语言是在服务于参与性思维和行为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4](P33)具体说来是参与存在事件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在其后期的超语言学或表述理论中,表述及其对话性构成了人之在场或存在的基础,是早期思想中的存在事件之在场性与共在形式的语言化呈现,这也在根本上指向了存在事件。就此而言,巴赫金总的语言学见解均指向人的存在事件。虽然早期思想中以“我-他”形式出场的伦理事件在后期语言理论中演化为以“我-你”形式呈现的对话事件,两个时期有着差异,但都在与事件的关联中,而在巴赫金那里,事件乃是“某种生动的、具体的、直观的统一整体”,[4](P34)由此,总的语言学见解也与直观相关联。“‘直观’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具有中心意义。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直观’作为认识的源泉是现象学反思和研究所依据的最终基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直观’作为意识行为本身也是现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5](P41)巴赫金对存在事件的直观性之揭示,也是一种现象学的把握,巴赫金直言:“存在事件是现象学的概念。”[4](P285)巴赫金总的语言学见解以此也具有现象学特征。
巴赫金早期思想经历了一个现象学阶段,受到过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尽管巴赫金对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胡塞尔有重要区别,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有相近之处。无论是就上述教学法层面重声调的传统中声调之可感知的特征而言,还是就语言理论层面所指向的存在事件之直观性而言,巴赫金这篇教学法文章的两个层面均具有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意味,在此意义上也显示出其语言教学法的现象学立场:两个层面集中体现在语法教学的修辞现象中,通过把修辞还原为语言形式所呈现的可感情境,从而将学生带向语言形式的情境感知之中。
二、语言教学中的情境感知
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体现了胡塞尔对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所做的区分。胡塞尔认为,符号行为奠基于直观行为,并且要还原到直观行为的基础上。[5](P42)巴赫金在语法形式的教学中所呈现的情境感知便是这种还原的具体实行。
巴赫金比较了语法上的无连接词复合句与带连接词主从复合句的区别,通过互换句法形式的训练,能揭示出语法教学中修辞分析的必要性。巴赫金以普希金与果戈里作品中的句子为例,通过朗读时的语调、面部表情、手势等措施来“增强句中蕴含的戏剧性因素”,让学生“感受到这类句子中语调的主导作用,要让他们感到并看到,朗读普希金的这一诗句时,语调与手势的结合是一种内在的必需。学生听到了这个句子,对句子的情味有了真切的艺术感受,在这之后就可以着手分析那些造成艺术效果并产生出表现力的具体手段了”。[2](P113)在语法与修辞上都是正确的情况下,无连接词复合句能让学生“感到并看到”,是突出学生对语句形式中的情境感知的维度;而带连接词主从复合句则“失去了情感的韵味,变得比原来冷漠、枯燥,只剩理性的内容了”。[2](P114)巴赫金认为,这种语法形式的改变导致情境感知的变化,在于连接词的非直观特征。“我们向学生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像主从连接词这类表示句子间纯逻辑关系的虚词,不包含任何直观形象的成分,它们的意义绝不可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在我们的言语中获得隐喻意义,它们不能用来表示讥讽意味,不能负载包含情感的语调”。[2](P115)主从连接词排斥直观性与情感的语调,这未明言地对应于前述教学法的两方面,即语言层面所指向的直观性与语法领域中重声调的传统。直观性与语调之可感性作为其语言教学法中分析评判上述两种句法形式的尺度,是其现象学立场在教学中的具体实行。
在胡塞尔看来,对语言符号所传达之物的感知,只能是一种拟-感知,不能如对某物的当下在场之感知那般充实,例如,对语言中描述的一棵树的感知与对眼前的一棵树的感知是不同的,前者具有“好像”或“仿佛”的样式。在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中可以见出胡塞尔所做的这种区别,尽管巴赫金力图还原到可直观的情境,但这种通过语言符号而展示的直观,也是以“好像”或“仿佛”的样式出现的。巴赫金有时直接谈语言形式中的情景感知,有时也在严格意义上描述出学生的这种感知的“好像”或“仿佛”样式。巴赫金在分析“普希金原句的直观、生动的动态戏剧性”[2](P118)时,便点明了这种直观的仿佛样式。“我们仿佛亲眼看见事情在舞台上展现;第二个简单句(‘众人放声大笑’)与第一个简单句(‘他一笑’)此呼彼应,有声有色。这里不是在讲述事情,而是事情本身在我们眼前发生。这种动态型戏剧性来自前后两句结构上严整的对仗:‘他’对‘众人’,‘笑’对‘放声大笑’;第二句就像是第一句在境中的影像,宾客的大笑声就像是对奥涅金的笑声作出的实实在在的反响。由此可见,话语的结构如同演戏一般复现了它所讲述的事情。”[2](P117-118)普希金的句子所描述的内容如同在舞台上动态展现出来的戏剧,使学生如亲眼看见一般,但这与在剧院现场观看舞台戏剧表演时的亲眼所见的直观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巴赫金用了“仿佛”亲眼看见。这与胡塞尔对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的区分有着一致性。
尽管如此,巴赫金在这里也提出了自己的语言理论观点,普希金的句子之动态戏剧性及其直观的仿佛样式,也表明了话语结构具有直观地讲述事情的功能。话语结构也具有形式意义,可视为话语的形式。巴赫金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普希金的无连接词复合句不是在讲述某件事,而是借助其结构形式,像演戏一样把事情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2](P118)话语结构形式的这种能直观地述事的特征,指明了语句的“涵义和它的语言表达形式是无法分割开的”,[2](P117)这实际上也是其超语言学或语言表述理论在语法教学中的运用。在表述中,语法现象与修辞现象能够统一起来。“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语言现象中,语法和修辞都是既合又分的:如果把这个现象放在语言体系中研究,那么这是语法现象,而如果放到个人表述或言语体裁的整体中去研究,那么它就是修辞现象。因为说者选择特定的语法形式,这本身就是修辞行为。但对同一具体语言现象的两种观察角度,相互间不应壁垒森严,也不应简单地机械替代,而是应该以语言现象的实际统一为基础而有机地结合起来。”[2](P146)语法现象与修辞现象应统一为语言现象,而表述作为语言现象的实际统一,即是语法与具体言语的统一形式。在此意义上,巴赫金把语法与修辞相结合起来的教学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表述式的教学法。“我们只有在表述的形式中,才能学习语言的形式。”[6](P279)其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表述,在表述中响起个人独特的语调,发出个人的声音。
三、个人声音的培育与语言现象学
让学生在书面语的表述中发出个人的声音,从语法层面来说,这是重声调的语法传统在教学中的运用,是让学生学会发出自己的个人声调;从语言理论层面来说,这是对学生的书面表述能力的培育,让学生学会把自己的存在带入到语言表述之中,写出个性化的表述。
巴赫金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学生之个人声音的培育,是因为个人声音在巴赫金那里有其特有的内涵。其一,个人声音代表着学生的语言个性;其二,个人声音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其三,个人声音表示对话式的主体及其存在。对作为个人声音的言语主体的揭示,具有独特的现象学意义,是巴赫金对胡塞尔那里出现的他人意识与心灵之难题的一种解答,巴赫金的语言教学对学生个人声音的培育也在此基础上展开。
个人声音的第一个方面,其作为语言个性在同千人一面的书面语做斗争中得到凸显。“无连接词复合句是同千人一面的书面语作斗争时可以使用的有力武器: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这类句子中,说话人的独特面貌能得到最清晰的反映。……学生的个人独特语调将到处破土而出。”[2](P124)这种对立的模式同巴赫金的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离心力与向心力等组对现象有相似之处。应注意的是,巴赫金提到的与千人一面的书面语做斗争,并不是排斥书面语,而是要让学生学会写出具有个人声调的书面语,把自己的独特声调表述于书写之中,从而摆脱泯灭个性的千人一面,而是要做到千人千面。
作为语言个性的个人声音,其来源之一便是自由的自我意识,后者即是个人声音的第二个方面的涵义,也被巴赫金名之为“人身上的人”。[7](P111)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身上看到这一点。陀氏小说的主人公是“人身上的人”,“人身上的人”依靠主人公的自我议论和对世界的评价展示出来,“一个人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只有他本人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和议论中才能揭示出来,却无法对之背对背地下一个外在的结论。”[7](P76-77)人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并不能由他人的外在立场来完成,这样会使自由的自我意识物化,会把外在他人的想法观念强行塞到自由的自我意识之中,从而使后者丧失自由,自我意识也被固化,故而只能通过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言说与议论才能得以揭示。这一方面表明个人声音只能通过自我发声来显现,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巴赫金对个人表述能力之培养的必要性,因为个人表述正是让学生发出个人声音的恰适形式。
自我意识的自行发声,在对话的情境中才能得以维持与存留,是一种对话式的言语主体,这是个人声音的第三个方面的涵义。个人的声音作为人的个性与自我意识,无法外在地完成,那只能让其自我言说与自行揭示,由此,需要对话的态度。“对个性之人的唯一能维护他的自由和未完成性的关系,就是对话关系。”[7](P385)这种对话中的个人声音也是对话者的声音。在此意义上,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所培养的是对话者,也是对话式的主体。
与叔本华所言的“意志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所强调的东西不同,①巴赫金的对话式主体突出的是其语言维度。个人声音的三种涵义,无论是作为个人的声调、个人的自我意识还是对话式的言语主体,都是在语言维度展开的,这显示出巴赫金后期语言学的现象学特征。个人声音作为对话式的主体,表明在主体问题上,巴赫金与胡塞尔的绝对主体有着区别。一方面,主体是言语式的,以言语方式存在,“主体在它被巴赫金称为言谈(Rede)的言语行为中得到展现。”[6](P281)另一方面,主体是在以对话样式出场的主体间性中,“存在就意味着对话的交际……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7](P340)在巴赫金那里,“语言构成意识,是‘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6](P281)就语言与世界或主体间性的关系来说,巴赫金与胡塞尔也有相近之处。“生活世界——‘我们大家的世界’——与能够共同谈论的世界是同一的。每一种新的统觉通过统觉的转移本质上都导致周围世界的新的类型化,并且在交往中导致一种命名,这种命名立即汇入到公共的语言中。因此世界始终已经是可在经验上公共地(主观间共同地)解释的,并因此同时是可用语言解释的世界。”[8](P262)这句话中的intersubjektiv(主观间共同地),也可译为“主体间性地”,[9](P213)指世界的公共性是对不同主体之间而言的。胡塞尔指出了生活世界的同一性与语言化,或可言说化,这种语言化也是对不同主体共同显现出来的,是在主体间得到共同解释的。从世界之同一性与公共语言的共同性来说,人也生活在语言之中。但胡塞尔强调世界语言化的共同性,巴赫金突出世界语言化中的主体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不同言语主体发出各自独特的声调,形成个人的声音,把个人的存在带入表述中,从而使主体的自我意识、个人声音及其存在都在个人表述中得到揭示。这也显示出巴赫金语言现象学的独特之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他人意识与心灵之显现的难题,巴赫金通过对话中的自我言说与个性化表述,让他人的自我意识与心灵在个人声音中如其所是地呈现,以此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个人声音成为言语主体或对话主体的显现方式,这既显明了巴赫金语言现象学的立场,也是其语言教学法展开的一个基点,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教师的责任。对于学生独特声调与个人声音的培育,“教师所要做的,将只是通过灵活、谨慎的指导来促进学生语言独特个性的诞生。”[2](P124)众所周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多层面多领域都提倡对话性,而要让对话发生,需要对话者。就教育而言,要求在教学中培养出对话者,让学生学会发出富有自己个性的声音。严格来说,让学生学会写出自己的声音,让其鲜活的口语与书面语相融合,也使其写出来的表述及其声音与实际生活相关联。“教师要做的工作,是努力促使学生的笔语发生新的转折,使之重新向生动活泼的口语靠拢,向实际生活靠拢。”[2](P123)在巴赫金看来,“话语成为实际生活构造自身的手段”。[10](P254)学生之表述中的个人话语,也是其实际生活的构造,将实际生活带入表述之中。由此,教师也在对学生个人声音的培育中完成其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并非空洞的理论推演,也并非脱离实际的方法创新,而是与实际教学相结合的。为了具体落实上述教学目标,巴赫金在语言教学法中还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式,可以分为三步:1.让学生做专门的练习;2.批改作业,改动语法形式;3.课上讲评并有意引发争论与对话。巴赫金所提的教学上的三个步骤,在通常的教学行为中比较常见,但却是围绕学生的表述能力之培养来展开的:布置的作业及其批改围绕语法形式的修辞来进行,这是书面写作中的表述练习;而在课堂上促成的争论则让学生既发出自己的个人声音,也获得了一种对话中的表述训练。
此外,这种教学的效果如何,巴赫金也依照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标准,去检验其语言教学法的实际成效。巴赫金通过教学与学生作业等情况了解不同年级的学生表述能力的特征与差异。学生在低年级时笔语与口语大致一致,写作的句法接近口语语法,写出的句子具有活泼、形象等特征;但从七年级到九年级阶段,由于受刻板的课本语言与语法的影响,学生的笔语缺乏个性;巴赫金因此提出应在七、八、九年级时尤其是在第七年级要扭转学生笔语中千人一面的刻板化倾向,按其语言教学法进行教学,改变他们的句法结构,从而在十年级时能在学生的表述中“听得到他的生动的个人语调”。[2](P122)至此,可以看到,学生能通过表述发出自己的个人声音,也意味着能发声的言语主体已初步被培养出来。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实现了其教学目的。
结语 巴赫金语言教学法的意义
巴赫金的语言教学法承续并拓展了在古希腊未得到发扬的重声调的语法传统,也以其原创性的表述理论为基础,无论是语言的声调还是语言情境之感知,均体现了向现象学的直观进行还原的倾向;而其表述理论中的语言主体或对话者,是对他人心灵的一种现象学揭示的方式。这构成了重在培养学生“个人声音”的巴赫金语言教学法的现象学之维。巴赫金的教学法也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并经受了教学效果的检验。它虽然是针对中学俄语教学而来提出来的,但因其扎根于传统并富有理论创见而能超出自身语种及学段的限制,对中学语文教学、大学文学语言的教学甚至对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具有更深广的意义。
这里不妨把其意义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三个阶段: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初级阶段,针对大学文学语言教学的中级阶段,以及针对作家之文学创作的高级阶段。
在汉语言的语文教育中,学生在中学熟悉汉语语法之后,汉语写作在语法上能中规中矩不出错,但表达上的刻板与千人一面的情况也较为明显,算得上是通病。巴赫金针对中学语言教学的这种通病而提出的语言教学法及其教学步骤,在此初级阶段具有借鉴意义。
而就大学文学语言教学来说,以中文系的文学语言的教学为例,也存在重义理而轻修辞的倾向,通过四年文学专业的学习学会个性化表达并在书面表述中能发出个人声音的学生并不多。哪怕有少数者能做到这一点,似乎主要也是通过自己不断尝试写作而练出来的。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中文系的文学写作班、语言理论课程,以及文学史等相关课程中,凡涉及到对文学语言进行分析的,均可参考巴赫金的表述式教学,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述能力,让学生学会发出自己的“个人声音”。巴赫金语言教学法对此中级阶段具有参考意义。
而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一高级阶段,巴赫金的语言教学理论也并未丧失其意义,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能突出其价值。作家虽然并不需要像学生那样由老师在课堂上教,但作家的写作也是不断学习使用语言并磨砺语言的过程,作家的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作家的成熟与创作个性也突出地表现在其独具个性的表述中,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恰恰能更好地表现个人风格与个性。“艺术作品的体裁最为适宜:这里表现个人风格直接属于表述的任务,是表述的主要目标之一。”[2](P142)由此,在作家追求个性化表述的语言写作与学习中,巴赫金语言教学法也有其意义。有些作家能自觉认识到,文学创作即是个性化表述的学习与追寻,如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便把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过程概述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11](P59)作家的创作即是学会并写出个性化表述的过程,陈忠实所言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不仅仅是指内容上的独特性,更是指语言形式上“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作家面临不同质地的写作对象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才可能把自己体验到的生活内容,完成一次最充分也最富有个性化的独特表述。”[11](P71)作家体验到的生活内容与语言形式相结合而形成作家的个性化表述,陈忠实所追寻的“属于自己的句子”便可以视为对巴赫金表述范畴的作家感悟式表达。这也见证了巴赫金语言教学法中的表述形式对作家之文学创作的意义,同时也表明,巴赫金的语言教学论具有超出校园教学范围之外的价值。
注释:
①对叔本华的“意志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之理解与批判,可参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