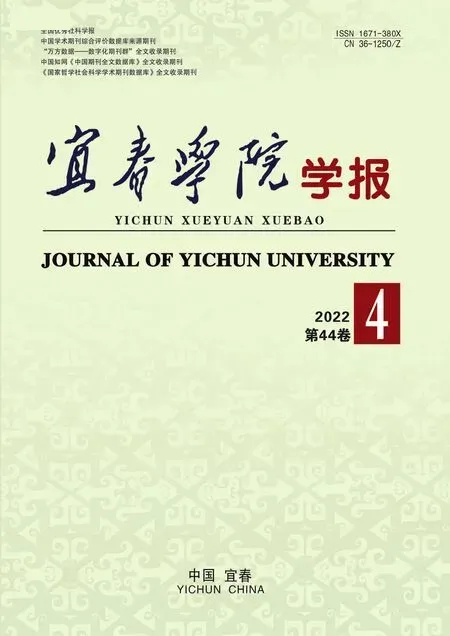徽州板凳龙舞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人类学阐释
陈文苑,汤洪丽
(1.安徽医科大学 人文医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2.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徽州板凳龙舞是指流行于古徽州地区(绩溪、歙县、祁门、婺源、休宁、黟县),以长形板凳组合及龙灯等为道具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在徽州,板凳龙又被称之为“游烛龙”“嬉龙灯”“嬉排灯”等。
舞板凳龙是徽州民间的传统习俗,此习俗可以追溯至清中前期,据清康熙二十九年《歙县志》记载:“元夕,家悬灯于门,游烛龙于衢巷。”[1](P1033)清时期,祁门县“上元夜,庙宇张灯,或扮龙灯,钲鼓游于里巷,以庆‘元宵’”,[1](P1036)婺源县“农历十三日,灯节开始,县城和大的村庄晚间迎灯,十五日元宵节,晚间迎龙灯、闹花灯”。[2](P533)《休宁县志》明确说明休宁的舞龙情况:“海阳、万安、五城、潜阜、溪口以及各乡较大村族,(元宵节)均有闹龙灯活动。”[3](P591)《绩溪县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板凳龙舞的细节:“清代始有板龙、纸龙、布龙、手龙、滚龙,龙身长者20余米。北村板龙长百板,元宵节可东南西北中隅各演一夜。各隅龙身分青、红、白、黑、黄色,农业合作化后,改为春节演出,龙身内燃烛。今或安装电池电珠,每节一人执撑。翻滚盘蟠悉由掌龙首者指撑,亦有领舞者执彩球或明珠引导。”[4](P790)徽州诸多村落历史上都有舞板凳龙的习惯,甚至一个村落同时出现过几条板凳龙的情况:“歙南王村,有九社,一社一龙(板凳龙),要游上村郊观音山和游下河滩,行‘九龙会’。”[5](P785)
一、徽州板凳龙舞仪式概述
徽州板凳龙起舞的时间点分为两种:元宵节和中秋节。绝大多数徽州板凳龙均在元宵之日起舞,现如鹤城乡右龙村、潜口镇潜口村、许村镇许村等,徽州童谣中曾唱到“金打铁银打铁,一年四季打不歇!打铁打到正月正,家家门前嬉龙灯”。中秋节起舞的板凳龙并不多见,目前只见于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除起舞时间有别外,田里村板凳龙与其他板凳龙相比,形式上亦存有一定的差异性。田里村板凳龙虽亦使用长条凳,但“龙灯”却是插上香火的破开南瓜瓣,而其他板凳龙“龙灯”均为内设蜡烛的灯笼。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整个徽州地区,仅右龙村与田里村的板凳龙多年来基本未中断,可谓活态传承至今。
徽州板凳龙的形状分为“龙首”“龙身”和“龙尾”三部分,“龙首”“龙尾”均是由竹篾制成骨架并将绵纸粘附其上,形似传说中龙头部和尾部的一种造型。“龙首”“龙尾”上,常绘有各种图案和文字;“龙身”则由多条长条形板凳组成,每户出一板,俗称“一丁一板”。每条板凳长度约五尺,宽约八寸,板凳面用铁丝固定3—5盏灯笼或3片南瓜瓣。板凳龙仪式即将开始前1小时左右,每户家庭选派一位代表将板凳送至特定的地点(田里村在本村“老井”前,右龙村在“土地庙”前),并按照到达的时间顺序将板凳依次衔接好。
板凳龙舞仪式进程可分成“起龙”“舞龙”和“收龙”三个环节。“起龙”为仪式的开始环节,仪式组织者择吉时宣布开始游龙仪式,此时田里村村民进行祈祷叩拜,右龙村则为焚香叩首;“舞龙”为仪式的核心环节,即将拼接好的板凳龙抬扛着在村中各条巷道、各家门口游走、舞动,之后又会集中于村中空旷地方进行“打转”“走同心圆”等动作表演。不论是田里板凳龙,还是右龙板凳龙,游龙时都必须经过村中的每家每户门口。当板凳龙即将到达口前时,各家各户便开始燃放烟花或爆竹以示欢迎,这一行为也被称为“接龙”;“收龙”为仪式的结束环节,即“舞龙”环节结束后,板凳龙游舞进指定地点(田里村、右龙村均为本村祠堂)后,参与者拆下各自板凳并将其抬入家中,而“龙头”则被放置于祠堂中。至此,板凳龙仪式基本宣告结束。
象征人类学大师特纳认为,仪式是象征符号的布局,象征是仪式最基本的建筑砖石,或称之为仪式的分子,徽州板凳龙舞仪式从器物到行为再到指涉内容无不象征性地表达着当地人们对于生育的渴望和崇拜。
二、徽州板凳龙舞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符号
象征人类学“把文化视为一种能够传递信息和表达观念的象征体系”。[6](P1)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体系主要由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两部分构成,而象征符号又可具体分为三种类型符号。
人类学家基姆伯拉将象征符号视为仪式活动的中心、向导和源泉。作为仪式中保留着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象征符号“如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事件和空间单位等”。[7](P23)在徽州板凳龙舞仪式语境中,生育崇拜的象征符号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以及虚拟象征符号。
(一)物化象征符号
仪式中,物化象征符号指的是具有隐喻内容的各种物质形态,物化象征符号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多采取的是类比联想法。徽州板凳龙舞仪式中,生育崇拜的物化象征符号包括南瓜瓣、灯烛、“龙须”“龙珠”等,人们首先通过这些象征符号的陈设意图实现求育和生子。
南瓜是一种常见的可食用果实,因其多籽的属性和强大的繁殖能力而常被隐喻多子多福。以南瓜作为象征物求子的场景非常多见,《徽州竹枝词》曾记录过歙县“偷南瓜送子”习俗:“送子中秋纪美谈,瓜丁芋子总宜男。”另在芜湖,“适逢阴历三月初三日……乏子嗣者,备一南瓜,全瓜入锅烂煮,于午时取出,夫妻并肩坐,同时举箸,尽量食之,必然得子。”每逢中秋节人们会通过摸南瓜的方式来求子;又南京“(中秋)有夜分私取圆瓜,谓之摸秋,以兆生子”。[8](P150)摸秋即摸(偷)南瓜,《繁昌县志》载:“(妇女)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可见,中秋摸南瓜、送南瓜即蕴含求子之意。
徽州田里村的板凳龙以破开的南瓜瓣为灯烛,不仅是为方便插上香火,破开的南瓜造型更象征着已婚女性的生育器官。在中国民间,破裂的物体常被比拟为女性生育器官,如石洞、陶缸、山谷等,人们“视女阴为瓜,处女膜破坏为‘破瓜’”。[9](P58)生育之事离不开女性,“在古代宗教,阴门被用来象征整个女人”,[10](P54)也象征着生育之源,因为“女性生育器官是妇女的根本特征,它既是两性交媾的媒介,又是生育子女的产门。”[9](P60)田里板凳龙以破裂南瓜瓣为象征物表达着生育的期望。
灯烛为板凳龙舞中内设蜡烛的灯笼。在徽州方言中,灯与丁的读音十分相近,而丁又是钉的古体字,钉常作为男性生育器官的象征物,丁也有男人之义。《帝京岁时纪胜》载:“元夕妇女群游……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也”,当地人们认为摸钉可以得子。另外,蜡烛自身也与男性生育器官形状相似,徽州人借此希望男性在生育过程中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心愿,徽州板凳龙也常被称为“人丁龙”“人丁烛”等等。在徽州歙县,板凳龙行舞至“久婚未孕之家时,男人常以新烛换下‘龙体”内的残烛,意为‘烛营’,取义盼子。”[11](P80)
板凳龙的“龙须”呈长条形状,“龙珠”则是板凳龙“龙头”口腔里所含的圆珠,两者均为绵纸制作而成。在板凳龙仪式语境下,“龙须”亦是男性生育器官的象征符号,而“龙珠”既是女性生育器官(卵巢)的象征符号,又是受孕后形体的一种模拟象征。《史记·夏本纪》曾引《帝王本纪》中关于禹母吞神珠的神话传说,可见,先民们认为接触珠状物体可有助于女性受孕。
物化象征符号是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象征仪式中最基本的单元。在板凳龙舞场域情境下,人们首先通过设置南瓜瓣、灯烛、“龙须”“龙珠”等物体传递出生育诉求,并憧憬借此实现该目的,恰如霭理士所述,“为了表示生殖崇拜的心理,早期的人们便设有种种象征,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生殖器官本身。”[12](P67)
(二)行为象征符号
行为象征符号指的是一些规范化或非规范化的行为举动,体现了行为主体与物化对象一种关系性的形态联系。与物化象征符号的静态性、常态性特点相比,行为象征符号呈现的是一种动态性和瞬间性。徽州板凳龙舞蹈本身就是生育崇拜仪式的行为象征符号。除此之外,触摸“龙珠”、接收“龙须”、置换“蜡烛”、抢抬板凳回家等动作则是具体化的行为象征符号。
对于那些期望生育的家庭,歙县的一些村落会在仪式进程中置换蜡烛,《歙县记俗诗》曾说到“元宵灯火闹长堤,舞出神龙振鼓声,争向龙头请龙烛,烛龙双引入香闺”。[11](P79)徽州区潜口村则会在仪式结束时让未孕妇女触摸“龙珠”,并赠送“龙须”。休宁田里村在板凳龙仪式行将结束时,大家会争抢着抬扛自己的板凳回家,他们认为,最早到家的人,来年一定会添丁增喜。在田里村村民看来,板凳是“龙身”的一部分,也“人丁”的象征符号,而休宁右龙村则会在仪式后,将龙中所含的“龙珠”赠予求子的家庭,并让希望尽早生育的女性到客厅承接“龙珠”。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右龙村一户张姓家庭,结婚多年却未生子。1968年元宵节,村民约定将当年的板凳龙“龙珠”赠予其家。巧的是,在舞龙仪式结束后,当村民捧着“龙珠”到达其家时,想要生子的女子因急事临时串门,“龙珠”只好由其婆婆代接。第二年,婆婆竟意外怀孕,而该女子则终身未孕。这位女性现仍居住于右龙村,笔者在对其进行访谈时,现已年近八旬的这位女子谈及此事,嘘唏不已。这位张姓女子的亲身经历也为右龙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增添了神秘色彩。
不论是触摸“龙珠”,还是接收“龙须”,人们将生育的知识图景投射到这些符号中,并希望通过零距离与象征符号的接触(交通媒介)获得生育神灵庇佑及心理慰藉,进而能在生育上得偿所愿。如果说,“龙珠”等为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的物化象征符号,那么与这些符号的互动和身体接触则构建成为了行为象征符号。这些行为象征符号明显带有着早期先民们“交感巫术”的印记,也是人类学家弗雷泽所说的“接触率”或“触感率”。
(三)虚拟象征符号
虚拟象征符号为人们想象出来的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现象、情景,虚拟象征符号具有非现实性、虚幻性的特征。徽州板凳龙舞生育崇拜仪式元级虚拟象征符号便是龙本身。
龙是中华民族先民们根据现实事物建构出的一种虚拟神物,后逐渐演变成了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关于图腾生子的传说,古典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帝王世纪》曾载炎帝是由其母娇氏女感神龙而生,《竹书纪年》载尧是由母庆都与赤龙婚配后而生,《路史·后记》亦载帝女,感蛇而孕后生下庖牺等等。由于先民们对于生育知识的匮乏,他们单纯地以为“图腾在人的生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图腾崇拜可能就是最早的生殖崇拜方式”。[13](P222)在中华民族先民们的意识里,龙作为图腾掌管着人的生死和命运,掌握着一种人命的力量。龙不仅被认为是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也是民族的徽号和标志,更是民族的生育之神。因此,徽州的板凳龙舞蹈仪式既是生育崇拜仪式,也是图腾崇拜仪式。在中国民间,不仅仅是板凳龙舞,其他的“舞龙习俗,均是以祈繁育丁,旺如虾群,室昌家盛”[14]为目的和旨归。
徽州人以板凳龙舞形式把意念之中龙的形态表现了出来,并希望通过活态群舞的方式激发出龙的作用和功能,参与仪式的每个人都自我认为受到了龙的感应和庇佑。在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符号体系中,“龙身”、灯烛等这些物化象征符号亦可谓亚级虚拟象征符号,“象征场域里,某象征物的含义可以投射到其他象征物上”[15](P19)在大家看来,板凳就是“龙身”,灯烛就是“龙烛”,“龙须”“龙珠”是龙身的组成部分,这些物体对他们来说都充满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因此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
特纳认为象征符号具有浓缩性、多义性和两级性的特征,灯烛、南瓜瓣以及龙等具有着多种指涉意义,只有在生育习俗的文化语境下,它们才成为生育祈求的象征符号。将仪式置于语境下进行考察,也正是特纳所注重和强调的。仪式的语境不仅指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族群传统的知识体系,也包涵着仪式的叙事表达。如果以仪式过程及时间序列角度来看,元级虚拟象征符号龙可称为整个板凳龙舞仪式的支配性象征符号或母题性象征符号,它不仅支配着参与者的行为,也是整个象征体系构建的基本。另外,龙作为支配性象征符号是人们情感的寄托,也是维系仪式进程和仪式参与者关系的纽带,在仪式实践中因此处于中心点的位置。
三、徽州板凳龙舞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意义
象征仪式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的陈设及与其互动进而激发象征物被认定的神秘力量。在整个板凳龙舞象征符号体系中,虚拟象征符号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物化象征符号是虚拟象征符号的具体化、物态化或情境化呈现,而行为象征符号则是行为主体与虚拟、物化象征符号之间建立的一种交感式关联,设立象征符号的目的在于彰显传说中神话世界的力量,人们也把象征符号作为神秘力量降临现实世界的通道。
“生育崇拜是基于人的‘求子’需要而产生的。”[13](P231)在中国民间,农历正月、三月以及八月都是求子的好时期。《礼记·月令》载:“是月(仲春之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古人认为,农历正月,阳气上涨,地气上升,万物即将步入生机勃勃的时段,正月又是一年的开端,在此期间求子即希望能在当年后继的时间里实现这个愿望。元宵节期间,大江南北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生子的愿景,如江苏泰兴、福建闽南一带的“拍喜”习俗,广东东莞“灯头生日”,湖南长沙“送麒麟灯”等等。农历八月,已近中秋,此时寒(阴)气渐盛,古人认为男主阳而女主阴,在此时令求子也非常符合时宜。在先民们的意识里,月属阴,也主管生育,如《琐碎录》里曾记载有“兔蚌望月而孕胎”之事。中秋之夜月亮形状圆满,自然是求子的好时段,全国各地因此有“摸秋”、舞龙等各种与乞子相关的民俗活动。
特纳在《庆典》中强调,对于仪式物品即象征符号的阐释,离不开位置意义视角,位置意义视角指的是时空角度。徽州板凳龙在元宵节与中秋节起舞,遵循着传统求子的时节习性。在仪式中,设置的各种象征符号是大家所熟悉和认同的,人类学家利奇曾说“象征符号只有在人们熟知的时候,才能被理解。”[16](P13)徽州百姓通过板凳龙仪式及多种已被认同的象征符号表达着对生育的向往和崇拜,象征物的指涉对象被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人们用仪式的方式展现了对于这种超自然、超理性力量的尊重和信任,并将命运寄托其上。
在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体系中,象征符号处于表层结构,而象征意义则处于深层结构。象征符号是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而象征意义又是象征符号的内容,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最明显的象征意义当然是表达求子的心愿。生殖之事,造化生生不已的大德。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繁衍才是根本之要,也是最关键的大事。在农业社会里,人口是生产力的代表,人们对于生育更加重视,农业的丰收与畜牧业的兴旺最终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生产和发展,缺乏生育,失去人口,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古徽州民鲜田畴,山限壤隔,人口自身的生产对于徽州人而言更显得意义非凡。
四、徽州板凳龙舞生育崇拜仪式的象征作用
人类学对于仪式的关注,并不在意追求发生的溯源及美学意义,而是把仪式看作一种特殊的“文本”,进而解释其细节性、操作性等具体内容以及总结实践中的叙事逻辑,象征因此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象征人类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分析社会中的各种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并借此认识象征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价值和作用”[6](P7)仪式恰恰“能够最深层次地揭示出价值所在。”[17](P6)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象征仪式的作用主要有:
(一)促进宗族兴旺和稳定
古徽州地狭人薄,各村落又是聚族而居,“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18](P258)在现实中,“宁甘斗讼,好义故争”[19](P19)的徽州人,各族姓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与矛盾,“始则一人争之,一族争之,继而通国争之。”[18](P605)在这样的情境下,“歙人求嗣者尤切”。[8](P272)毕竟,旺盛的人口是宗族之间竞争的根本砝码,徽州各村落因此对人口的兴旺格外重视。生育不仅能为宗族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血缘社会里,还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20](P115)
板凳龙仪式让个人空间社会化,家庭的生育之事宗族化。“仪式将人们应尽的规范和责任周期性地转换成想要做的规范和责任。”[7](P37)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让宗族的每个人意识到了自身生产对于宗族的价值,“通过仪式体验,人们能够理解自我及社会本质意义。”[15](P20)可以看出,村中每户人家的生育之事也是宗族之事,现实中整个宗族对板凳龙舞一直都格外重视,这也是徽州板凳龙舞能够传承至今的关键因素。因此,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不单单只是为了人口的繁衍,更牵涉到宗族的兴旺和稳定。可以说,该仪式既是不断维系“香火”的物化与实践,也是延续宗族存在与整合的有效手段。
(二)有助于家庭和睦
在日常生活中,徽州各村落存在着男女二元结构性对立,但在仪式过程中,男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得到了缓解。尽管传统时期舞板凳龙只允许男子参加,但在生育乞子上,女性依旧受到大家的重视。如果说舞板龙是男子的任务,仪式赋予其生育责任的话,那么接“龙烛”、触摸“龙珠”则彰显了女性在生育方面的重要性,仪式同样也赋予了其神圣的生育使命。可以说,板凳龙舞仪式在操作环节上一方面使得男性与女性关系割裂,而另一方面又促使两者的合力协作。
在整个仪式环节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净化,出现了特纳所认为的“交融”状态(communitsa),日常生活中的结构化、等级化被冲刷和隐藏。可以说,板凳龙就代表着“交融”,这种“交融”无疑有利于家庭和睦以及夫妻关系顺畅。
道格拉斯强调“仪式具有记忆和控制经历的方法,仪式中被标记的时间和地点激活了一种特殊的期望”。[21](P82)徽州板凳龙生育崇拜仪式将过程记忆灌输进群众的脑海中,仪式时间虽然短暂,但起到了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不断发挥控制经历的作用。为了达到或完成生育期望,男性与女性必须要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仪式因此潜在地帮助调和着夫妻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舍克纳认为仪式是神话的证实,仪式中表演目的是使想象中形象成为现实。其实,不仅仅是让想象的形象成为现实,重要的是让仪式中的象征作用成为现实。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人们对于生育之事充满了疑惑、好奇甚至恐慌,此时只能求助于非理性力量的帮助。于是,在实践中人们用一种前科学思维或感性思维方式构建出一套仪式象征体系,用以表达对于这种力量的尊重和依赖。恰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人类既属于大自然,又属于文化,人类的诞生、生育、死亡等不仅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事件,而徽州板凳龙仪式恰恰黏合了自然、生物事实与文化、社会事件,并围绕着主题编织出了一幅象征之网。
美国人类学家巴巴拉·梅厄霍夫认为仪式由某个文化主题为开端,然后对这个问题进行各种处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徽州板凳龙舞仪式具有多种名称,如季节过渡仪式、图腾崇拜仪式、祈雨仪式,但生育崇拜是该仪式基础性的叙事表达,或者说生育崇拜的目的贯穿于求雨仪式、祈愿仪式、过渡仪式及图腾崇拜仪式之中,文章在此以图形形式(图1)进行表述:范·杰内普曾把仪式分为“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三个阶段,即指的是仪式前期、仪式过程以及仪式之后,特纳在此基础上认为仪式过程(“阈限”)会出现“交融”的状态。“仪式的符号性存在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和权威”,[22](P137)在徽州板凳龙舞生育仪式过程中,参与者们通过感受和接触象征符号,不仅能够“联想到有关神话及这些象征物所象征的对象,使它们蕴涵的‘原能’(创造力量)在此时体现出来”,[15](P12)并且让权威所激发出的动力情节嵌入到群体心理中。板凳龙舞仪式展示了参与者内心的期许,更彰显了对于未来生育的决心。“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王尔德语)带着“阈限”中的“原能”激励、心理暗示和精神动力,人们步入到后阈限期,并积极投入到自身生产之中。徽州板凳龙舞生育崇拜象征仪式体现了徽州人的生存哲学、思维模式和群体心态,它承载着徽州人的文化记忆,也将成为流传后世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

图1 徽州板凳龙舞仪式名称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