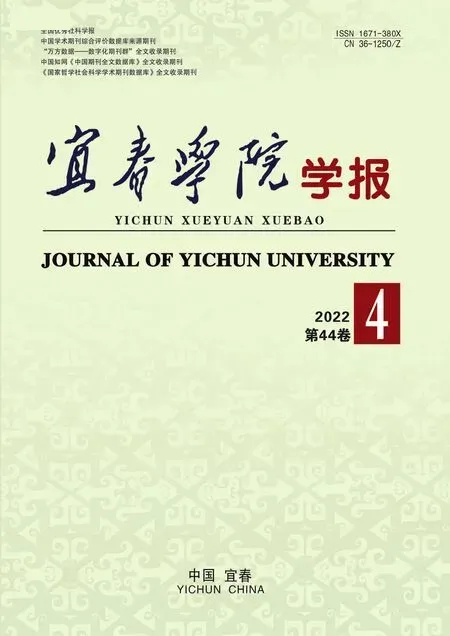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花间集》里的边塞情结
沈传河,刘 睿
(1.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2.衡水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中充斥着对女性姿色的描写,从面容发肤到身体情态,婉媚秾艳得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以致“花间”一词,在中国词学史上后来竟成了一种柔媚浮艳甚至是低俗浅陋词风的代称。就《花间集》的文本实际而言,这种香艳而浅俗的词风确实是存在的,甚至可谓是该词集的“主调”。花间词人在其词作中,刻意营造了种种莺歌燕舞、刻红剪翠的生活场景,着力塑造了诸多艳丽而妖娆的女性形象,将“花间世界”描绘得十分艳丽而浓烈。
然而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花间集》在“主调”之外,尚有不少“别调”,即后人所谓的“花间别调”。刘尊明先生在其《唐五代词史论稿》中指出,“花间别调”“主要表现在欧阳炯、李珣、孙光宪、鹿虔扆等人的创作中”,主要有三类作品:“第一类是表现隐逸生活情趣的冷色调的作品,……第二类是描绘南粤风物人情乃至乡村生活的色彩较清新明丽而又富于乡土气息的作品,……第三类是咏史怀古、抒发兴亡之感的带有感伤情调的作品。”[1](P164-165)其实,“花间别调”还有重要的另外一类,即表现边塞征战生活、抒发相关情感的一类作品。这类作品无疑当属于边塞词。《花间集》500首词作中,大约有20首属于边塞词,其中大多是小令,少数是中调,无长调作品。相关词家主要有:温庭筠、毛文锡、孙光宪、韦庄、牛峤、顾夐等。在这些“花间”边塞词中,出现了风格迥异的边塞地名和意象,反映了边塞征战的生活和情志,抒发了边塞闺中的两地情愁,为我们展示了“花间”词中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可谓是“花间别调”之一种。本文侧重于从情感方面对“花间”边塞词作初步探究,以解读揭示其中的边塞情结。
一、名称中的边塞意蕴
《花间集》中有不少与边塞征战有关的名称,这些名称无不蕴含着一定的边塞意蕴,值得注意。这些名称有的又可以代表着一定的意象,其蕴含的边塞意蕴也就更为浓郁。《花间集》中这些名称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词调名,一类是边塞地名。
(一)词调名中的边塞意蕴
在《花间集》所用词调名中,与边塞征战有关的主要有:《酒泉子》《甘州子》《甘州遍》《定西番》《番女怨》《遐方怨》等。当然,有的词作其内容与其词调本意已呈分离状态,如温庭筠四首《酒泉子》、顾夐七首《酒泉子》等均已如此。上列词调名中,包含着三个重要地名:“酒泉”“甘州”“西番”,尤其值得注意。
“酒泉”,即今甘肃酒泉;“甘州”,即今甘肃张掖;“西番”,亦称“西蕃”,泛指西域诸番族,有时包括或特指吐蕃。《旧唐书·吐蕃传》有载:“昔秦以陇山已西为陇西郡,汉怀匈奴于河右,置姑臧、张掖、酒泉、伊吾等郡,又于碛外置西域都护,控引胡国。”[2](P5236)由此可见,今甘肃、青海、新疆一带,自古就是重要的边防地区。到了唐代,由于吐蕃的强大与扩张,与唐王朝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边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3](P129)“河湟”,即黄河、湟水合流一带地区,亦即河西、陇右一带,即今甘肃、青海一带。这一带地区,在唐与吐蕃的这场冲突中,成了唐王朝最直接的国防前线,酒泉、甘州等地均是其中的边防要塞。如岑参有《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①[4](P2061)一诗,王维《陇西行》中亦写道:“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两诗作均提及“酒泉”。这种绵延不断的边疆战争,对于当时及其后的文人创作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花间”词人的创作。
《花间集》所用词调,均是盛行于当时歌坊酒肆,为广大文人、百姓所熟悉和喜爱的词调。“酒泉”“甘州”“西番”等名称出现在“花间”词调中,证明了在当时的流行词曲中,有不少内容是与边塞征战、征人思妇、塞外风物等(亦即边塞题材)联系在一起的。远溯于词调创制者,近及于倚调填词者,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边塞题材已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将之寓于自己的创作之中,表现为一种明显的边塞情结。这种边塞情结,向外表现为一种隽永的边塞意蕴,显然这是当时广大民众所喜闻乐感的,随着词曲的传唱,广布天下。这在一些歌咏调名本意的“花间”边塞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孙光宪的《酒泉子》其一、毛文锡的《甘州遍》其二等词作均是如此。兹引前者来看:
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
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②[5](P149)
作者依词调名《酒泉子》本意而歌咏,寄心边塞,描述征战,展现相思,加之“空碛”“阳关”“陇云”“戎衣”“胡霜”等意象的运用,使全词洋溢着浓郁的边塞情愁,情韵悠长。
(二)边塞地名中的边塞意蕴
在“花间”词中,有不少边塞地名值得注意。这些边塞地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具体地名,一类是泛指地名。这些边塞地名,对于《花间集》中边塞空间的展现、边塞意境的营造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透过这些边塞地名及其相应的意象生成,我们仍能够体会到明显的乃至浓郁的边塞意蕴、边塞情愫。
1.具体的边塞地名。在“花间”词中,具体的边塞地名主要有“玉关”“轮台”“雁门”“辽阳”等。
玉关即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疏勒河南岸,汉时即置为边塞关口,六朝时移至今甘肃安西双塔堡附近。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玉门关就是内地富庶文明与域外不毛之地的分界线,是边关要塞,玉门关外即是无限的荒漠与凄凉。如骆宾王在其《从军中行路难》中写道:“玉关尘色暗边庭,铜鞮杂虏寇长城”,王之涣《凉州词》中更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玉关”在《花间集》中出现了3次,其中1次指称较实,2次较虚。指称较虚时,“玉关”已不像在唐边塞诗中那样往往实指玉门关,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代指边关,或代指征人所在的地方。三次之中,“玉关”指称较实的一次是温庭筠的《定西番》其一:
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
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
该词发挥词调本意,歌咏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该词当属边塞词,词中“玉关”倾向于实指,边土风物亦有所表现,全词边塞的意蕴、情韵比较浓郁。
轮台,故址在今新疆轮台东南,原为轮台国,后为汉所灭,汉曾驻兵屯田于此,后并入龟兹国。在盛唐时期,轮台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地区。岑参两次出塞,曾写下了大量跟轮台有关的诗歌,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即事》等。“轮台”在《花间集》中仅出现了1次:“星渐稀,漏频转。何处轮台声怨。”(牛峤《更漏子》其一)词中“轮台”的指称已经虚化,仅是代指夫君所在的边塞地区而已。就全词来看,该《更漏子》当是一首闺情词,而非边塞词。虽然如此,其中的“轮台”及其意象,还是为该词增添了不少的边塞情韵。
雁门,即雁门关,又称西陉关,唐置,故址在今山西雁门关西雁门山上。这也是古代一处边地要塞。崔颢有《雁门胡人歌》,卢照邻在其《战城南》中亦写道:“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这些都说明雁门关在唐人心目中是与边塞划等号的。“雁门”在《花间集》中亦仅出现了1次:“雁门消息不归来。又飞回。”(温庭筠《番女怨》其一)这里的“雁门”,其所处情状及功用,与上文所述“轮台”十分类似,兹不再赘述。
辽阳,又称辽东。战国燕置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十六国后燕末为高句丽所有。唐贞观十九年(645)取辽东城,置辽州,后废。这里曾是东北边塞,是唐王朝和契丹争夺的边疆地带。唐太宗李世民曾有“驱马出辽阳,万里转旂常”的诗句,张籍也有诗句“忆昔君初纳彩时,不言身属辽阳戍”。可见,辽阳在唐代同样是一个边塞重镇。“辽阳”在《花间集》中共出现了3次,这三次出现,其所处情状及功用,与上文所述“轮台”同样十分类似,兹略举一例(牛峤《菩萨蛮》其一)以见其情形:
舞裙香暖金泥凤。画梁语燕惊残梦。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
愁匀红粉泪。眉剪春山翠。何处是辽阳。锦屏春昼长。
显然,词中“辽阳”指称上的虚化已十分明显,与其说它实指辽阳,不如说它仅是代指女子夫君所在的地方而已。该《菩萨蛮》一首,与其说是边塞词,不如说是闺情词。虽然如此,“辽阳”一词及其意象,在这首词中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一片浓郁的闺情中,为词作点缀了些许边塞的情致与韵味。
2.泛指的边塞地名。在“花间”词中,泛指的边塞地名主要有“关山”“边城”“塞外”“塞门”“边庭”“辽塞”等。
上文提及,在“花间”词中,一些具体的边塞地名在指称上已不再实指,而是出现了明显虚化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泛指的边塞地名,在《花间集》中往往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被使用的。它们逐渐失去原有地理实体或地理界域的含义,指称上被模糊虚化,只是被用来代指边塞地区而已,甚至只是用来代指征人所在的地方而已。它们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提供背景、引出人事、点缀情调等。它们所属的词作,往往是闺情词而不是边塞词。虽然如此,它们在词中的作用意义还是有的,并不能完全否认。其主要作用意义有:引入新的题材因素,即边塞题材;扩大文学空间,将文学空间由闺阁扩展至边塞;于浓郁的闺情之上,点缀出新的边塞情韵。兹略举一例(温庭筠《菩萨蛮》其九):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总体上看,该词显然是一首闺情词。但因为“关山”或曰“故人万里关山隔”的加入,使这首词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异质的新的边塞题材得以加入,虽然只是少许的;文学空间瞬间得以延展,由目下的闺阁延展至万里之外的边塞;绮艳香软的闺情之上,被点缀上几许异质的新的边塞情韵。
二、边塞闺阁两情愁
在古典诗词中,边塞与闺阁这两种题材其实是经常会合或交织在一起的,原因就在于思妇与征人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诗经·卫风·伯兮》如此,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大致如此,到了唐代,边塞题材兴盛,这类诗词多有创作,十分兴盛。沈佺期、王昌龄、白居易、陈陶、陆龟蒙等人,无不创作有这一类的作品。《云谣集》中亦有此类作品,如《凤归云》(征夫数载)一首即十分典型,不妨引介于此: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起,寒雁南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6](P12)
上阕,前四句写征夫,后五句写思妇。下阕主要写思妇,但其情、其怨、其血泪、其燃香、其祷告,又无不指向那个远征边关的夫君。因而,从题材上讲,这首词可谓是边塞与闺阁两种题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花间集》中,同样不乏这一类作品。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而把相关词作分为两类:一类是“闺人怀远”,一类是“征人思亲”。
(一)“闺人怀远向边塞”
“花间”词人擅为闺阁之音,塑造了大量的闺中思妇形象。这些思妇形象,虽然她们所思对象有所不同,但都是亲人在空间上离开了自己,使自己陷入了孤独的情状,从而饱受相思之苦,无奈只能与怨恨情愁作伴。在这些思妇中,有一种思妇她们的思念指向了边塞,指向了远征边塞的恋人或丈夫。与那些负心而离去的浪子不同,远赴边塞的征人是值得人们认同、钦佩和赞美的,因此,指向边塞的闺阁之音在感情上更显得真切、深沉而绵远。《花间集》中,写“闺人怀远向边塞”较多的词人是温庭筠和毛文锡。
温庭筠的词,向以艳丽软媚为特色,缺少骨力与气度。在闺情词中,适当加入一点边塞题材,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温词的这种状况。温氏《菩萨蛮》其四:
翠翘金缕双鸂鶒。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
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
以景物描写起笔,整个上阕全是景物描写。“绣衫”句点出了美丽的女主人公,最后两句集中抒写女主人公内心的慨叹与感伤,心系玉关,情归边塞。全词总体上倾向于艳丽婉媚,末尾处少许边塞题材的介入颇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动与平衡的作用,使词作稍有阳刚之气,但遗憾的是力度偏弱,效果有限。再来看温氏《杨柳枝》其八:
织锦机边莺语频。停梭垂泪忆征人。塞门三月犹萧索,纵有垂杨未觉春。
同样以景物描写起笔,但第二句即点出“停梭垂泪”的思妇形象,并指明她的心思、情愁是指向“征人”的,后两句通过边塞景物描写进一步申明此意。显然,这首温词边塞题材的介入较多,阳刚之气多有,在骨力与气度方面要好过上一首所举温词。
毛文锡的词“多写男女之情,质直匀净,善以景写情”,[7](P139)从下面两首例词中亦可见出毛词的这一特点。毛氏《醉花间》其一: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
前三句以述情起笔,奠定全词的情感基调。“春水”以下四句全是写景,然景中有情,状景以托情。前七句全是闺情之语,词末二句突然加入一点边塞之辞,点明女主人公情感所系、情感所归,艺术效果很好。又有毛氏的《河满子》一首:
红粉楼前月照,碧纱窗外莺啼。梦断辽阳音信。那堪独守空闺。恨对百花时节,王孙绿草萋萋。
全词的表达构成很明确:写景——抒情——写景。写景者,均是闺情之语,中间抒情,引入一点边塞题材,点明闺情所向,境界顿觉阔大,艺术效果同样很好。
(二)“征人思亲归故园”
情感往往是相互的,互动的,“边塞闺阁”的情愁往往亦是如此。《花间集》中,既有闺中之人对远方征人的相思情愁,亦有边塞征人对故园亲人的牵挂与向往,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边塞情结、征战情愁。《花间集》中,温庭筠、牛峤、孙光宪等人均有此类词作。
温庭筠有《番女怨》一首(其二),写的就是征人厌战思家的故事与情愫。该词如下: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从边塞景物写起,起笔雄健,清人陈廷焯评曰:“起二句,有力如虎。”[8](P573)该词前五句确实具有盛唐边塞诗雄奇刚健的状貌,然第五句有转,厌战情绪有所流露。最后两句突然引入新的闺情题材,致使抒情急转直下,心向故园,集中抒发了征人对妻室的思念之情。
又有牛峤《定西番》一首,同样是抒写戍边丈夫对妻室故园的思念之情。该词如下: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该词的题材构成是:边塞——思乡——边塞。首尾处皆边塞景物的描写、戍守生活的展现,重在突出边塞的苦寒,征战的艰辛。中间“梦长安”三句,重在抒写男主人公的故园之思,闺阁之恋。一句“梦长安”确系点睛之笔,指明了征人深沉情感的寄托方向。
除了戍边将士与闺中思妇,与边塞结有一定情结的还有古代出塞远嫁异域的公主。这在古典诗词中有不少反映,《花间集》中即有此类作品。远嫁异域的公主,也可谓是一类“征人”,只是她们远征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和亲。《花间集》中,孙光宪有《定西番》其二一首: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
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
据说这首词是歌咏乌孙公主(即西汉江都公主刘细君)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9](P3172)此事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刘细君被远嫁乌孙国以和亲,生活悲愁,思汉心切,然终未得归汉。词中的“帝子”即指乌孙公主。该词上阕类似闺情题材,风格柔婉,下阕言及关塞、戍楼、寒笛等,并点明思亲思乡的主旨取向,感情真挚深沉,风格悲切悠长。
三、边塞征战中的情愫
边塞是一种地理空间,是一种文学空间,亦是一种各种情愫交织的精神空间。就远赴边塞征战的将士们来说,这里除了有他们对于妻室的思念,对于故园的向往,这里还有他们对于立功受赏的渴求,对于连年征战的厌恶,还有他们对于边塞风光的诸多感受。前二者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对后三者再略加论述。
(一)对立功受赏的渴求
对于远离故乡、征战边塞的将士们而言,他们往往是有现实诉求的,那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军功,获得封赏,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到了唐代,甚至不少诗人也想投身边塞,获立军功。在他们的诗歌里,那种对功名的渴望有时表现得十分直接而明白。如岑参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高适说“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逤取封侯”(《九曲词》其三),而李贺的一首七绝更是广为传诵:“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
《花间集》中的边塞词,有的同样表达了将士们对建立军功、得封受赏的向往乃至渴求。其中毛文锡的《甘州遍》其二即十分具有代表性: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番奚。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
这是一首典型的边塞词,简直可以和盛唐边塞诗中的代表作品相媲美。沙漠之地,秋风劲吹,飞沙茫茫,迷人路途,环境是如此恶劣;阵云、边声、戍角声、征鼙声,一起涌现,战斗的气氛是如此紧张;飞沙不定,铁衣冰冷,马蹄沾血,战斗的过程是如此艰苦;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愿望,英勇战斗拼搏的意志,为的只是最后能够“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他们认为,为了这份凯旋的荣耀和无比光明的仕途,现在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罪,无疑都是值得的。陈廷焯评该词曰:“结以功名,鼓战士之气。”[10](P150)是为的评。
(二)对连年征战的厌恶
战争是把双刃剑,利用它伤害对方的同时,其实也在伤害着自己。战争不仅意味着团结、勇敢、英雄、荣耀等,它同时还意味着耗费、分离、伤亡、痛苦等。尤其是那些缺乏正义性的战争,诸如为了统治集团的某种利益而穷兵黩武,为了吞并或占有他国的领土而发动战争,或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功邀宠的欲望而刻意制造战争等,都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痛苦甚至是灾难,因而这些战争往往受到人们的质疑、反对和厌恶。这种反战、厌战的思想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是很常见的,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盛唐的边塞诗派,都可找到相关的例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同样不乏这一类的作品,如《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
《花间集》中,也有少数词作同样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情绪,值得注意。上文第二部分所述“闺人怀远”“征人思亲”“边塞闺阁两情愁”,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含蓄地揭示了战争给人们的婚恋、家庭带来的伤害与痛苦。征战、戍边、伤亡,使多少人夫妻分离,有家难聚,痛苦相思,甚至是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也就是说,上文第二部分所举例词,除孙光宪《定西番》其二外,均应蕴含着反战、厌战的思想情绪。仔细读验,发现确实如此。其中较为突出者有两首词,一首是温庭筠的《番女怨》其二,一首是牛峤的《定西番》。前一首词中,“年年征战”一句最为紧要;后一首词中,“梦长安”一句最为紧要。这两句都可谓是词作的点睛之笔,于此,男主人公反战、厌战的思想情绪流露得更多更集中。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加激起了男主人公对于亲人的思念,对于故园的神往。
(三)对边塞风光的不同感受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边塞地区的风光图景与内地相比总是有明显的不同,往往以阔远、雄浑、奇丽、矫健等为主要特色。这在唐边塞诗中多有表现,在《花间集》中亦有一定程度的表现。面对这些非同一般的风光图景,观者总会有着诸多不同的心理感受。
首先是边塞的苦寒图景。这方面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数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了,其中有诸多典型的苦寒描绘,如“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黪淡万里凝”等句。《花间集》中也有类似的描绘,只是相比之下没有那么出色罢了。如温庭筠《番女怨》其二中的“飞雪千里”,牛峤《定西番》中写道“雪漫漫”,孙光宪《酒泉子》其一里的“胡霜千里白”等,都写出了边地苦寒的特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间接描写,即通过戍卒的切身感受来表现边地苦寒,如“铁衣冷”“金甲冷,戍楼寒”等。可以体察到,经历或描绘这些苦寒图景者,或惊奇,或慨叹,或感伤,或苦痛等。
其次是风沙漫天的情景。毛文锡《甘州遍》其二有这样的描绘:“秋风紧,平碛雁行低。……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这里对边塞风沙的描写即很好,随之亦可以看出蕴含其中的情愫,诸如慨叹、伤悲、迷茫等。看了毛文锡的描绘,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人的一些类似描绘,如岑参的“银山碛口风似箭,……飒飒胡沙迸人面”(《银山碛西馆》)、“湖沙莽茫茫。……沙石乱飘扬”(《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王昌龄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军行七首》其五)等。当然,相比之下,岑参、王昌龄的描绘无疑更为出色。
其三是大漠荒凉之景。这在古代边塞诗、边塞词中都比较常见。如王维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的诗句,范仲淹有“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渔家傲》)的词句。在《花间集》中,类似的描写也能找到一些。如温庭筠《番女怨》其二的“碛南沙上惊雁起”和毛文锡《甘州遍》其二的“秋风紧,平碛雁行低”,皆是描写边塞空旷的荒漠之上大雁在惊飞或低飞。孙光宪《酒泉子》其一中的“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描写更为出色:无边无际的荒漠里,道路绵延,马嘶人去,愁云相伴。面对这些边塞荒漠之景,无不让人倍感孤独、凄凉、郁闷乃至痛苦,这也正是人在边塞所常有的一些情愫。
其四是描写边塞游骑高超的骑射技艺。边塞地区的胡人,往往男子擅骑射,女子善歌舞,这在古代边塞诗词中亦有不少反映。《花间集》对此亦有所反映,其中少数词作即反映了边塞男子擅于骑射,技艺高超的生活情状。最典型者当数孙光宪的《定西番》其一:
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
该词陈廷焯评为“笔力廉悍”。[11](P411)词作以边塞地区深秋季节早晨的大草原为背景,以“马蹄轻”为词眼,刻画了一位骑术娴熟、正纵横驰骋的骑手形象。骑手取弓搭箭,拉弓成月形,一支响箭射出,正中高空飞翔的鸿雁,一个射技精湛的神射手形象跃然纸上。整首词作,可谓是一幅边塞游骑骑射图。全词洋溢着浓郁的边塞生活气息,风格昂扬而雄健。透过该词,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轻快、爽朗、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这种词在《花间集》中是不多见的。
诸多生动鲜活的描绘,诸多边塞风光图景的展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奇丽而又多彩的边塞空间。诸种光景,诸种形象,诸种情愫,有机地交织在这一广阔的边塞空间之中。这一边塞空间,迥异于《花间集》主流的香艳软媚的闺情空间,因而在《花间集》中它显得弥足珍贵。
总的来说,虽然《花间集》里的主流作品是那些依红偎翠、风流恻艳的词作,但同时也应看到,《花间集》中的词作是多种多样的,“主调”之外还有不少“别调”,而其中的边塞词就是重要的“花间别调”之一。在《花间集》里的边塞空间中,交织着诸多意蕴、情感、欲求等,它们一起构成一种边塞情结。其中主要构成有:词调名、边塞地名中的边塞意蕴、边塞闺阁两相思念的情愁、对立功受赏的渴求、对连年征战的厌恶、对边塞风光的不同感受等。
注释:
①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下文所引不再一一注明。
②本文所引《花间集》词,均出自后蜀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文所引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