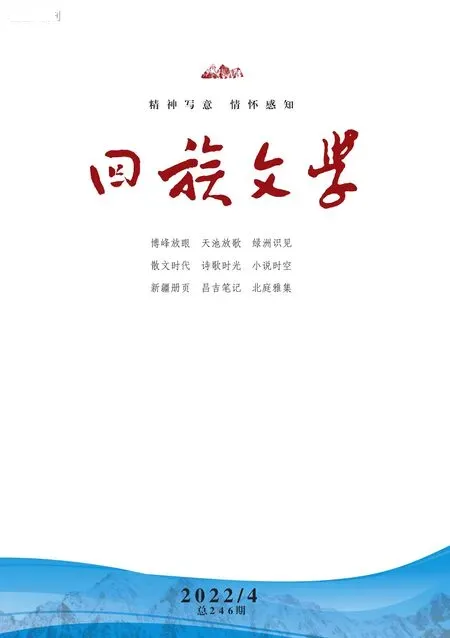在逃逸与摩擦之间
刘群华
横竖的扁担
挑起扁担,就挑起了艰难的生计和不屈的生命。
一条扁担,横竖人间,行马天下。要么一挑锦衣玉食,要么一挑贫贱低下,其间变数,顺应天命。扁担横是一,竖也是一,肩上的扁担,挑有形的担子,挑无形的担子,都是向时光挑人生的活路。
扁担多是木扁担,亦有竹扁担。木扁担多是杂木,檀木、梨木、柏木、樱桃木、枫木、桎木,肉质细,韧性好,能挑重活儿。竹扁担也有韧性,楠竹一剖两开,选竹节密的,更有绵劲儿,上坡下地,可轻摆担子。
扁担有的在一端号字,姓甚名谁,像刻上的粗茶淡饭,清汤寡水。有的扁担龟裂,包了铁皮,就像穷人家的单衣打上了补丁,将就着用。有的扁担抹了桐油,油光可鉴,像个左右玲珑的讲究人。有的扁担一直弓着身,像椎骨难直,立不起腰、说不起硬话的人。有的扁担厚,可挑大任,繁华奢侈,像黄帘轿顶,旌旗猎猎。有的扁担薄,仅能挑南北杂货,像寒酸贫困之人,没见过世面,壶里有三两荤油,整日记在嘴上吆喝。
一条扁担是一个家的支柱。它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也彰显一个家的沧桑、向上。在使用一条扁担时,一个家的喜乐悲哀都在扁担上挑着,扁担不说话,说话也罢,一个家的目光全聚集,一个家的手脚都迁徙,一个家的嘴巴在翕动。从一条扁担,我可以看到一个家的未来是渺茫还是兴旺,可以看见一个家的稻穗是壮实还是空瘪,可以看见背负的生命是牢靠还是懈怠,可以看见每天的故事是重复还是更新。
其实,一条扁担两端的四个木扣,像扁担的护卫、随从。担子挑在肩上,扣子扣住了挑绳,轻易不会滑落。如果不小心,扣子断裂了,甭管担子的轻重,都会被倏地坠落的担子闪腰。人生这样的闪腰会有许多,总是突然。挑扁担的人,铆足了劲儿,就是不敢分心,双手紧握了挑绳。挑好自己的担子,管好自己的扁担,握定挑绳,是挑担人的规矩,也是做人的规矩。
别人的扁担我们可以不管、不看、不问,那是别人的生活。我们只管把紧自己的扁担,让自己的扁担上有香甜,有时是对的,有时又不对。对于善良之人的疏忽,人家的扁担我们要提醒,对于贼人的扁担,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我们要管,还要一扁担挥下去,把他的扁担砸断,担子砸烂。
在乡下,一个人长大了,十岁的样子,父亲会递给他一条扁担。就是我不识字的爹,也把扁担削好,郑重地递到了我的手中。那一晚,我想着日子里的艰难,一次次地辗转难眠。但是,我又知道,以后,我家的牛栏边、粪堆旁、菜园里、稻田上,都会有我扁担的光芒。我肩上的扁担,又分担了一个家的重量,或许可以让爹撂下扁担片刻,仰望门里的那棵苍树,看看闲散的小鸟在鸣叫。
上坡,让扁担下的脚步脚脚紧,下坡,让扁担下的脚步多轻快。上坡的扁担像阳光吐出的唾沫,勒进了肩头。气喘吁吁的土地上,必定挑出金疙瘩银块块。上坡的扁担考验人,其中的猫儿腻常被老人奉若神明,但是让细伢子娇嫩的肩头,满怀惆怅。下坡的扁担尽管比上坡的扁担轻快,但脚下的路坎坷不平,弯弯曲曲,稍不留神,又瘸了脚踝。一条扁担没有绝对的辛苦,也没有绝对的轻松。我的远方,竖起扁担一指,挑的是苍穹白云,横起一指,挑的是高山平地。
一条扁担也要知天命。小扁担挑起的注定是小担子,不可强行挑重担。重担一挑,拦腰一截。大扁担注定挑重货,耐得住重压,稳稳地伫立在肩头。另外,人的肩头也有大小,狭窄的肩膀放不下一条宽厚的扁担,只有雄壮的肩头,才可容纳一条厚而大的扁担。当然,扁担诠释的故事也有长有短,长的与人相伴一生,短的在一朝一夕,莫管前程。故事也有贫贱富贵,粗糙之人挑的扁担,故事像一袋老辣的旱烟,呛人不已,简单平实。聪慧之人的扁担,故事像九曲河湾,暗流涌动,曲折而悬念万千。
倘若一个人丢了扁担,是劳动人的笑话。担子挑不回不说,还得马上削新扁担。如果不削新扁担,自己的生计就空空落落,像风在山岗上扬,像月光在夜里流泻,都是没有影子的臭事。没有一条扁担的日子,是悲惨的,是屈辱的,无所事事的人,整天在路上行走,到头来无法果腹,并且寒酸。只有握一条扁担的人,支起生活的帷帐,挑破了人生的豁口,不挑剔,不放弃,佝偻着身子,畏缩着眼神,卑微地把担子挑在肩上,则家里温暖和睦。
一条扁担就是一口吃食。人的吃,已经远远高过了一切,甚至健康。吃是人最低的追求。高过了吃的东西,我看在扁担下窘迫得连一束阳光都不是。扁担外的青翠、橙黄、紫红、淡白、黢黑,所有的繁华、伟岸、高尚、雅致、精细,像半瓣青山绿水,虽然好看,好听,却无法囊括一条扁担心底的煎熬和宽阔,甚至斑斓。
一条扁担是春耕秋收的一帧记忆。在春天的旅程,扁担恐惧一粒种子的生长,扁担哀怨地看着一片绿叶的绽放。在扁担复杂的内心,这粒种子是否发芽,成苗,结籽,这片叶子是否拔节,开花,结实,左右徘徊。懂扁担的种子,抚摸着扁担,对它的恐惧予以安慰。懂扁担的叶子,亲昵着扁担,对它的哀怨予以阳光。
一条扁担不可能没有困顿,在春天。春天的灵性,让一条扁担光泽鲜润,像一垄麦苗,一纸桃花,铆接在秋天。
秋天的扁担是一碗酒。袒露着胸膛,或许还要与山雀歃血为盟,让兄弟情义束缚山雀去稻田偷谷粒。浓烈的青稞酒,像高原上的雄鹰,展开了强劲的翅膀,执着地充盈着梦想和激情。这时,一条扁担上的担子金灿灿,黄澄澄,沉甸甸,像一幅陈列在旷野上的神圣画面。神圣是美好的,是扁担在春天的祈愿,是扁担在秋天的感恩。如果我用扁担呈献,则大地的灯红酒绿里,多了一层纯净的光彩,在杯盏碟盘中,多了一次粮食的丰足。

《秋 色》(油画) 马小宝 作
扁担挑在肩上,汇集了人的精血,像聚集了天地之间的火焰。它的身躯由才削时的新白,变成了红彤彤的陈红。而在时光中淬火的扁担,家的使命,赋予它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生命。生命是何其豪迈,生命是何其坚定,像长安街上飞驰的骏马,像城垛上瞭望的箭镞,宽广,空旷,锋利。扁担的盘花纹理,在阳光中慢慢消失,磨灭,棱角在月色中逐渐模糊,圆滑,它看它的主人,满眼苍老和佝偻,心中未免落寞,唏嘘。
这是一生挑扁担的人。却有小部分的人,挑出了新的前程新的路途。那是扁担的荣耀,那是它不离不弃的主人!可是,人一旦骑上快马,攀上了高枝,有时候,扁担被卑鄙地遗弃,无奈地换了主人,继续奉养一个家庭;有时候,被卑鄙地遗弃于角落,落满了厚厚尘埃,蒙住了双眼,然后腐蚀虫蛀了。一条扁担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归宿,活了,叮叮当当地开出了花朵,死了,捻成长歌,磕磕绊绊地流泪。
一条扁担挑出了基本的生存。一天三顿米饭、烙饼、咸菜、烤鸡、肥肠,塞满了一个家的肚腹。一条扁担也挑出了无辜的饥饿,非是懒惰,全是造化弄人,挑出了酸甜苦辣咸几味,在人的每一个毛孔里每一条血管里放肆流窜。如果有条扁担断成两截,各奔东西的心疼,难免难料。就是有人用铁箍重新箍起,分道扬镳时的破损,依然未来凶险,不测。
一条扁担到了最后,还是躲不过破碎,沦为尘土的命运。这时,人不一定老了,但扁担老了,枯了,黄了,在风霜中伤了筋骨、精神。一挑担子从扁担上骤然应声而下,挑绳在手里不停摇曳、叹息。担子中的什物乱撒了一地,易碎的碎了,不容易碎的,残躯断腿,或沾了一地的尘土碎石,像覆水难收。
扁担离开了肩膀,就没有了支点,就很难有当初那一棵树的初心。扁担的灵魂在人的生计中叫嚣,在命运的火焰中燃烧。
不说也罢,我那条扁担。
蒙眼的碾盘
碾盘在碾坊沿着碾槽缓缓滚动,像穿越时空的一束阳光,不变地汹涌而至。
碾盘是碾坊里的核心。稻谷、玉米的璀璨光芒,在心性刚烈的碾盘下反复蹂躏,被破皮,碎粒,磨粉。碾盘的职责是不停、不紧、不慢地滚动,牛的职责是围着碾盘不停、不紧、不慢地旋转。拉碾盘的牛是蒙上了眼睛的,它看不到眼前馥郁的稻谷、玉米,只听到碾盘碾谷时清澈的咔嚓咔嚓和碾盘在石槽里滚动的轰鸣。
碾盘有大有小,碾坊也有大有小。大的碾盘像一轮圆月,照亮了远山近水,流泻了一地嫩白。小的碾盘像一面油盆,潺潺清流,滋润了千家万户。碾盘的大小,决定了牛用力的大小,力使大了,把小的碾盘扛出了石槽,力使小了,碾盘在石槽里屹立不动。人是不敢蹚这趟浑水的,小的碾盘拉不动,大的碾盘更是枉然。碾盘在人的面前,目光炯炯有神,十分坚定;人审视碾盘的目光,像天穹俯瞰的大地,凹凸有致。
在碾坊,我不知碾盘是牛心爱的工具,还是牛是碾盘心爱的工具。牛和碾盘同步协作,高度和谐,让稻谷玉米被碾得惨不忍睹、浑身碎骨。一些麻雀会偷窃石槽里的稻谷玉米,稻谷哪粒结实,哪粒干瘪,麻雀洞察秋毫,明白知晓。在它的眼睛里,碾盘来了,它避一脚,碾盘走了,它的尖喙悠闲地啄食颗粒,或者倏地凌空而起,钻进了瓦楞之中。
外面碾坊的一棵枣树,根系庞大,四围杂草清除,坚硬而凌乱的石头,沿枣树根茎砌了一圈。这棵枣树可遮盖西落的阳光,也是麻雀欲偷窃石槽内稻谷的前哨。麻雀飞在枣树的枝头上,透过镂空的窗叶,眼睛瘦小黢黑,不时警惕地张望。它有时不完全是偷窃,它看蒙眼的牛麻木地拉着碾盘,心无杂念地走,甚为奇怪。平日张狂的牛,奔腾的牛,威武不屈的牛,怎么这般温驯、可怜。
碾盘亦有水轴带动的。在碾坊之下,有一条暗渠,水从碾坊下走,带动了渠里的水轴叶片。于是,水不停地流,水轴不停地转,碾盘也不停地滚动。这类碾盘较牛拉的碾盘轻巧,碾稻谷的速度也比牛拉碾稻谷的速度要慢。不过,水不吃青草,无须照顾,只需打理水渠源头的水坝即可。水碾坊的碾盘,像定格了的夕照,柿子一样红得生涩。纯洁的云,在夕照旁拂动,像是碾盘下溅出的玉米稻谷。
水碾坊闲置时,多是秋高水瘦的时候。河里的水灌不进渠道,这时渠道里的浅坑里,总有些银白的鱼和灰不溜秋的螃蟹。这些美味,通过油盐酱醋的霸气浸润,让猫看了,馋出了炊烟中的不安。碾盘会在灰尘与蜘蛛网的覆盖下蛰伏一阵子,等待一个风狂月黑的日子,一场雨水严丝合缝地下来,河里的水位上涨,碾盘挺拔地在岁月的长歌中婆婆娑娑地摇曳。
碾坊外的水坝,像一大片的芦苇,通过一条水渠,与碾盘耳鬓厮磨。一条明晃晃的水渠,流水时雾气氤氲,时旖旎荡漾,时窈窕婀娜,时风韵绰约。正是秋水柔弱纤纤的时候,碾盘像一把镰刀,收割了梯田的稻谷和旷野上的玉米。稻谷在碾盘下蹭糠皮,一粒粒光滑洁白的大米,像稻谷羽化的仙子,在粗糙苍遒的手掌里,翩然飞舞。玉米则褪下了暗红的云裳,大方地露出奶酪一样的乳白。玉米和稻谷的宿命各异,但归途一样,在石碾的滋润或燎烤下,一次次的磨砺之后,成长成一帧时光里的图画。
碾坊是乡下人不可少的,顺应二十四个节气。在芒种,碾盘碾得比较单一,除了稻谷,还有玉米荞麦。但到了清明,种类多了,万物都繁盛起来,碾盘下碾的则是米粉。这时,坟上青草萋萋,要做叶子粑祭奠蛰伏于地下的亲人。有时碾剩余的种子,这些已挑选一遍,被碾的不是空瘪,就是虫蚀,躺在碾盘下像变节和失身的人,眼睛被粉尘吞噬,被风扬起,被阳光照亮。
没有哪一粒粮食可以避开碾盘。碾盘像人的舌头,像一把扫帚,不断地沉浮于时光的斑斓。在立秋之后的中秋,碾盘上的月光何其地圆,何其地亮。碾盘在月光下给故交的粮食破壳,碾粉。一粒大米潜伏在米糠里,轻易不愿见天,不愿与米糠分离。有一些大米,被月下的松鼠暗度了陈仓,囤积在温暖的小窝,在铺垫的干燥的狗尾草、松针上接受松鼠崇高的礼遇。大米在松鼠的窝里不言不语,但心里明明白白,像敞亮的明镜。
大寒后的碾盘最忙碌。一年之尾,丁是丁,卯是卯,该准备过年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会少。在碾坊磨糯米粉蒸米粑,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谁插队都不行,否则乱了秩序。平日少食的高粱和小米,也就进了碾坊,都碾磨成粉,都印些牡丹叶大的粑粑。这时,高粱粑像气息红润的桃花,在起伏的心田荡漾。高粱粑用它细腻的肢体暗合人的舌头,在美妙的味蕾上旋转、颠簸。小米粑一片黄,在慢火中煨一个,外焦内软,掰开两半,拉开长丝,呈示芳香,达到了人生的高潮,将产生无限的华彩。
碾坊是乡村的一面旗帜。白边红底的小旗,吊在碾坊的瓦檐之下,上面几个墨字:某某碾坊。曾经我们这儿有十里九碾一说,即十里路程,九个碾坊,可见当时的繁华。自然,出门与人介绍,多了一份自豪。碾坊调动了山沟土壑的人家,那些麦啊,那些谷啊,那些玉米啊,顺着崎岖小道挑进了古拙的碾坊。此时的碾盘,在碾坊里疯狂咆哮,在喧嚣里不断飞翔。一个碾盘像旗帜下的骏马,蹄声清亮,尘土腾空,谷物在碾盘下穿插,被娴熟地碾粉。石槽里的米粉像洁白的玫瑰花,朵朵鲜艳,开了一片。
碾盘用久了也会烂。身上或龟裂,或缺口,或已破碎。碾盘饱经了稻谷的打磨、米糠的挑衅,甚至碎石泥土小铁块的进攻,它们的粗糙和坚韧,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次次挥向了碾盘。碾盘辗转反侧,先被它们撬动了牙齿,蹒跚了双腿,然后薄了,像脸上的皱褶。在碾盘的眼里,碾盘下的一切都是它的至亲好友,它对稻谷的态度,像一颗温煦的太阳,对伤害它的物事,除了温煦,多了宽容。风拂过苍老的碾盘,像抚摩一次时光的隽永雅致。它静谧地躺在大地之上,野草穿过它的裂隙,探出的青翠,像一束不灭的生机。
碾盘没了,碾坊也将倒塌。倒塌的碾坊,像凌乱的冬天,白云和雪光,惨淡而无趣。躺在碎冰积雪中的碎瓦和烂茅,像鹰蹂躏下的兔子,不知所措。一条暗渠的流水,丰盈而清澈,像雪山上神圣而短暂的霞光。
一个碾盘,是一个乡村的风铃,如果没风去摇响它,它就没有来过。
飞翔的萝卜
被雪藏匿的萝卜,一转瞬被阳光发现。风冷冽寒碜,断壁残垣的村庄,在透明素洁的冰中,灰白空蒙。
人窝在土墙下猫风、晒太阳,一截萝卜嚼得咔嚓咔嚓。靠近手的一端,一小段留存了萝卜皮,方便相握,余下的萝卜裸白,水汪汪,如玉一样无瑕。这截萝卜,像半条村巷,阳光剥了它的覆雪,剩雪中挣扎的吊脚楼、飞翔的瓦檐重见了天日。萝卜的眼睛澄澈、纯净,像一簇青苔,在大地上的繁华,呈毛茸茸,呈湿漉漉。
村里栽的萝卜不多。够自家用菜,种三五十蔸的,几十家。能用担子挑,一丘一大片的,三五家。但土塬梯田上,临近深冬了,还有剩的,只两三丘田地了。这两三丘萝卜,从萝卜蒂上生出的一丛长叶,像风中的长幡,叶面皱褶不平,波浪样四展。根下毛须丰富,一簇一簇,丝一样细,但掘劲大,扎入土壤,封存了牛粪肥、羊粪肥、人粪肥的养料和琐碎。
萝卜在田地除了一众同亲,还有邻居彼岸花草、车前草、野烟叶、荷叶草、野菊、虾米草……晚上,还会有野猪、野兔、野山羊、麂子、竹根猪、老鼠来串门。这些动物,在风雪月光的缝隙里嗅到了萝卜的清鲜气息,迫不及待地偷食、糟蹋。在糟蹋这方面,没有比野猪更放肆、胆大的了。它们不来则已,一来就是一群,三五只是小群,十几只才常见,入了萝卜地,你一脚,我一脚,你一嘴,我一嘴,撒着欢,嗷嗷叫,差不多几个时辰,就把一亩萝卜田踩蹂,踢烂,拱翻了个遍。我感慨它们灵敏的鼻子,总在冰雪覆盖的村庄老远找到自己的喜爱。
冬天的旷野一片枯萎,绿色较少,枯黄色较多。常青树的流韵,像留恋春夏时节流逝的时光,还艰难地浅蓝,炫耀它的风采。细细碎碎的野草、藤蔓,不知忘了更替,还是什么原因,总有一小撮零碎的绿叶支撑,有的还长得很好,很嫩。但光秃秃的藤蔓和枯黄的野草,用一根光秆来嫉妒,来抱怨,来诅咒,来愁得头更光亮。只有青菜、白菜以外的萝卜,大片大片地集中地绽放青春。
萝卜在雪中展露的姿颜,土壤中的底蕴和热气,让它的那份端庄与气质,有别于其他绿色。绿色在冬天,不是主色,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如此。风反反复复地冰凉,冰凌反反复复地凝结,云反反复复地集结,雪反反复复地下。一只小鸟穿行,在村庄的天地中扒雪啄食并沐浴浅浅尘埃。
咀嚼一个萝卜的声音,十分欣喜、悦耳、动听。这是村人卑微的水果。馥郁的萝卜,用清悠的清脆声,奔波在上下两排牙尖,舌头席卷,像个碾盘,打破了干枯有些充血的喉咙。口腔外的山林深谷,不是一般的白皑皑,迷朦胧。冻鸟已经宁静,宁静得如一片羽毛的飞翔,所携带的风,都听到窜进门来。
我也加入了咀嚼萝卜的行列。这个队列的人有小孩、老人、妇女、男人。我从田垄拔出一个萝卜,拖泥带雪。揪断一簇冻硬的长叶,在枯草中反复抽擦泥土,然后拔出弯刀,挨萝卜皮削去,留下白晶晶的萝卜肉。萝卜有些羞涩,甚至有些强悍。它裸露的身子,在雪中依旧颤抖、不安、惊悚。
我也猫下身子,蹲在田埂上咔嚓咔嚓地嚼。这声音蛮古老的,像浑浊与清脆接替的翻书声,当然,更多的咀嚼声,如足履踏雪,像老鼠爬梁,像板屋松筋,像恬静的竹林被风撩了。这些风情万种、变化莫测的声音,完全被一个萝卜唯美、透彻地演绎,还十分逼真。
有的萝卜生得有些辛辣,像辣蓼草青紫的汁。有的萝卜有些寡淡,比山泉水还淡,淡得坑坑洼洼的味蕾都已经茫然、怀疑。这种机缘,在偌大的萝卜田里皆会相遇。不过,懂萝卜的人,会看萝卜生存的土壤,如果是黑沙土,这萝卜多数淡。如果是砂石土,韧性十足,辛辣之味必定不少。只有黄粘土上的萝卜,肉脆而松,轻轻一碰,水分溢流,甜意绵绵。但倘若种于坟山的萝卜,可能汲取了人的灵魂,则有一股骸骨中的咸味。萝卜爱家肥,用家肥种的萝卜,比用化肥种的萝卜,多了爽的层次。
咀嚼萝卜,冬天的清晨太凉,冰霜浸入,容易伤胃。只有中午太阳下或在炭火边,浑身火热,嚼一个萝卜,那滋味儿,像吮吸了一个6月冰棒,别提多高兴了。我咀嚼的萝卜是黄粘土所生,自然味道贴心。我差不多嚼了两个,就看见雪意茂盛的村庄出来了人,这人隔太远,只有灰白的轮廓。但一挑土箕还是十分明显。他挑着土箕,吱呀摇响了破窗上的风铃,飞快地朝我这边来了。
他肯定是拔萝卜喂猪的,否则大冬天,也没必要挑土箕。况且冬天用土箕的也只有挑萝卜。我不敢怠慢,起身远离了萝卜地。
这丘萝卜非我家所种。我家的萝卜在山腰,还要走百十米远。
我家的萝卜也长破了冰雪的清亮,一大片一大片地茂盛,青翠得像洒了绿油漆。土壤也是黄粘土,味道不差一分。我嚼一个萝卜还要上去,更要爬坡,难免会生懒惰。我朝夕光望去,村庄躺于长长的峡谷,隆起的屋檐雪白无瑕,像一个飞翔的萝卜。
萝卜真的会飞,一阵风,就把萝卜籽种下去了。它像蒲公英的种子,吹到哪儿,长在哪儿,沙滩,石砾缝,瓦楞,荒地,小道旁,只要有土,它都不会刻意选择,似乎生来那么贫贱,没有所谓娇嫩之气。种子被村人信马由缰地播,它也信马由缰地长,好像苦得让你难以忍受,莫名喊痛。
生活中的萝卜是一味好菜。
削皮切丝,或切薄片,不削皮亦可。有人不兴削皮,认为有皮更脆,不管如何,大火炒萝卜丝或片是没错的。吊脚楼的女人,在泉水下洗净了萝卜,白色的萝卜条条壮硕,像一只只白老鼠。但有根须的眼睛,眼睛凹陷,细土钻在其间,抠都抠不出来。这时,挥刀削去根须眼,在砧板上切丝,然后在大柴火上狂炒,放蒜苗味精盐即可。
放久了的萝卜蔫了,用手指一捏,水分去了三成。切丝,伴五花肉炒,油盐浸润其中,嚼一口,鲜而艳,舌头都吞了。
炖萝卜非我村首创。萝卜切坨,伴排骨或童子骨慢火细炖,一时半时,萝卜便在陶罐中沸腾,软塌,不时挤出袅袅清香。这时萝卜下筷就烂,骨头已脱肉,喝汤,美滋滋的。
萝卜还可切丝,晒干,伴米粉或玉米粉及猪肉,在锅中炒出油,成粉蒸肉。然后进土坛封存,时浇坛叶水。一月半月后,蒸之,味儿更胜了一层。
或者切丁,或者切条,晒六七成干,下辣椒面拌,加糖或盐水入瓶,一星期后食之,酸甜适中,多下几碗饭,多提几许胃口。
或刻雕入盘,点缀菜品。这时的萝卜被厨师细细雕琢,刻刀轻盈,意境优美。它洁白如玉的身躯,焕发了不少的灵感,成活了不少的灵魂。一道菜谱上,或是白雪满山,或是白龙入江,或是玉树临风,或是白花竞放,或是……
萝卜入厨,非雕刻点缀进不了宴席,着实让萝卜失落、恼火。但卑微的咀嚼声,唤起了我陈旧的记忆。我所亲的萝卜,在冬天,在旷野,不屈地伫立,是一个真汉子。风从脖子上灌,冰雪从脚下冻起,磨砺萝卜的桀骜不驯。阳光温暖、心慈,万缕金线拴住它,像一团红梅的火焰,燃烧着萝卜日渐寒冷的心。在季节的河流里,雪中的萝卜像大地上的险滩和暗礁,跌宕起伏。风的臂膀挥得更猛,更有力,萝卜的长叶艰难地伏地起伏,腰都差点断了。但它通过萝卜根的传递,叶子衔接了土地的匍匐和力量。
萝卜俨然是逆风中的木舟。10月、11月、12月的风雪,像纤绳深深勒入了肩膀,稍不小心,就被大雪压迫,被狂风拔出,甚至吞噬。阳光有时也有心无力,躲不过厚云重雾的笼罩,站在了茫茫天地之外。
村庄也是萝卜的力量源泉。天气不可预知地变化,我也挑出了土箕,在自家的梯田里拔萝卜。我抬头看天,阴沉沉的,心想这天气冻下来,又不知下几天雪。我得赶紧准备猪的青饲料。萝卜见我是平静的、顺从的、无奈的。阴暗的天空碾轧过来,流云如滚盘,把河流和山巅吓住了,遮盖了,把弯弯曲曲的道路迷蒙了,缩小了。萝卜爬出的脚印,深深地陷入了被人和土箕收拾的日子。
母亲对冬天的凛冽喋喋不休,她是害怕寒冷,也禁不住寒冷。她有哮喘病,对冬天的冷空气,由衷厌恶,排斥。雪在屋外,屋里的炭火通红,整个吊脚楼有阳光的温度。一个萝卜煎煮在瓦罐,祛除母亲的喘息。大多的萝卜躺在厢房的一角堆叠,它舒了一口气,它再不怕冬天的欺凌了。冬天在萝卜的心里,没有好印象,阴暗和寒意,似乎是奔它而来。它不解的是,从10月播种开始,天气就没给过它几天好脸色。
萝卜心里一片悲哀、苦涩。
倔强的萝卜一旦还在田里,就会继续被雪粒细细碎碎、窸窸窣窣地蹂躏。这大概是萝卜的宿命。它的命硬,但苦。因为冬天,它将自己全部的透明的光芒付出,并痴呆地仰望雀鸟盘旋的归途。雀鸟的归途比萝卜好不到哪里,它们都是金字塔的底层之物。雀鸟在空中凄惶、喑哑地鸣叫,翅膀都扇不起来,酸楚的感觉便可诠释、预知它未来的一切。
萝卜在来春的二三月开花,花瓣细,粒儿小,蕊儿黄。馥郁的清香,让蜜蜂在春阳中来来返返,走走停停。此时的萝卜已老,从头到脚布满青筋,像人纵横的僵硬脉络。萝卜秆结实,籽壳修长,密匝匝,稍呈扁形。
萝卜的青翠面貌被残酷的冰雪消融,被岁月磨砺得已经颓废,像夜色临了的浑浑噩噩。偶尔有几个不屈地从萝卜蒂处生出几片嫩叶,也是枉然、幻想。终究它不属于这个季节。不属于它的,再牵强,也没用。
不过,《药性赋》说,萝卜去膨下气,亦利胃和。意思是说能祛除腹胀,能够调和胃气。这时候的萝卜正派上了用场,是入药的最好阶段。如果用冰片与捣碎的萝卜贮藏,放阴暗处发酵成水,不久则是良药。
北宋时期,王安石患偏头痛,疼痛难忍,时常发作。一次上朝议事,王安石偏头痛又复发了,宋神宗让太监用一个小金杯装了秘制药液给王安石,并告诉他这是御用的滴鼻液,需要仰头滴进鼻腔。如果是左边偏头痛,药液滴右鼻孔;如果是右边偏头痛,则滴左鼻孔;若两侧都痛,就两侧鼻孔都滴。王安石听罢,滴后觉得舒服多了,再滴一次,疼痛竟全消。后来宋神宗告诉王安石,滴鼻液由鲜萝卜汁加入少许冰片制备而成。
残暮似的萝卜,孤独而苍遒,在春光中耷拉着头。它叶黄秆枯,像个落牙蹒跚的老人,像天穹上那些坠落的流星,内心无比迷茫、困顿。萝卜回天乏术,但还是遵从了时光的安排。在浩荡的时间之中,萝卜以及万物,像大地狭窄的裂缝,瞬间被风雪洗刷、填满,连寂寞的阴影也显得多余。
母亲把萝卜籽收回,然后晾干,搓壳存籽。萝卜籽一身黝黑透亮,但不太成熟的呈紫红色。这些萝卜种子,每一粒去碰撞,还可听见侵蚀了的风雪、汲取了的春阳。梆梆梆——像村庄滋生的更声,在母亲的陶坛里心无旁骛地贮藏。
我看着这些种子,它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一样,竟如此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