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励 轩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建设的范式,伴随着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广泛流行。理想的民族国家建设要求实现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相一致。这其中,民族往往被理解为是种族和文化上高度同质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国家建设的方向则是在国家范围内构建一个种族和文化上均质的人们共同体。近现代以来,这种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理念对中国影响深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末民国时期曾有一大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张将中国建设成为种族和文化上均质的民族国家,一度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政策。(1)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有学者还提出,清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结束,民国时期则进入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2)周 平:《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51页。不过将中国近现代史解读为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范式存在着很多学理上的争议,如李大龙认为民族国家概念既难以准确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也无法取得广泛认同,提出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来阐释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张会龙、朱碧波则认为民族国家理论难以阐释中华现代国家的精魄气象,提出应用文明国家概念来形容古今中国的国家范式。(3)参见李大龙《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会龙,朱碧波《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本文无意于从理论上对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范式进行商榷,而是将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放在大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考察,剖析不同国家建设理念的博弈以及影响这些理念形成的因素。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不同建国方案的检视和比较,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理念不是民族国家式的,它并不追求建成种族和文化上单一的国民政治共同体,而是试图在一个国民政治共同体内容纳文化多元的各个民族。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这种包容性的国家建设理念成为了主导,现代中国也最终超越了民族国家。本文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方案是对主权在民的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还应被定义为人民国家。本文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一套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民族话语体系,以及在具体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尊重和保护各族人民的民族地位及其政治权利,大大增进了各族人民对人民国家的认同,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也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五族共和——清末民初的国家建设方案
民族主义是肇始于18世纪晚期并在19世纪广泛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运动,根据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要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一致。(4)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83,p.1.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最高限度是建立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在清末传入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中国,并被很多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形成当时广为流行的民族国家话语。梁启超在1901年就著文介绍民族主义:“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5)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4~325页。从介绍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虽未明确提出一国一族,但已使用我族、他族、本国、外国等概念,基本上把民族主义是要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在次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对这种民族主义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欧洲诸国凡是按照民族主义原则建立“民族的国家”的,都能强盛,凡违背该原则,强行合并不同民族而形成帝国的,则会败亡。(6)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92页。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介绍与推崇,其目的是希望国人养成民族主义思想,从而更好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自身的独立,并最终实现国家富强。(7)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3页。
在梁启超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也向国人介绍与推崇民族主义思想。1902年,一位笔名为“雨尘子”的作者在《新民丛报》刊文:“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已往之政治界。”(8)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205页。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族建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雨尘子”次年又撰文详细介绍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将之视为欧洲最重要的三大主义之一。在他看来,属于同一民族的,本身就有凝聚力,早晚会统一为一个国家,而存在数个民族的国家,则缺乏凝聚力,终将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9)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347页。再如笔名为“余一”的作者,在《浙江潮》撰文详论民族主义,指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10)余 一:《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486页。除了自己写文章介绍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还有留日学生编译日人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在国内传播,如《游学译编》曾刊出一篇根据日本人高材世雄文章编译而成的文章,宣扬建立民族国家的主张,认为其合理性在于只有属于同一民族的才能实现团结,而不同民族则做不到真正的团结。(11)《民族主义之教育》,《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405页。
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时,恰好也是革命派宣扬排满主张之时。在革命派看来,满汉不同源、不同种,满人窃据了汉人之中国。《国民报》曾刊出一篇匿名文章,倡言汉人之国已亡于满人之手。(12)《亡国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91页。革命家章太炎更是公然为排满、仇满正言,认为汉人在清廷治下已成异种满洲政府之奴隶,(13)章炳麟:《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526~527页。提出应将满人逐出关内十九省,让他们回东北三省自治,并说:“其地未割于俄罗斯欤,则彼犹得保其主权,尚不失其帝位也。”(14)章炳麟:《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97页。一族一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恰好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提供了理论武器,“雨尘子”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国积贫积弱是因为汉族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我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15)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205页。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到败亡的地步,完全是由于没有同族感情的异种之人占据了汉人的国家,没有遵循一族建一国的民族主义原则。(16)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348页。在排满的氛围之下,革命派的民族主义诉求很自然就成为了建立汉人的民族国家。
革命派建立汉人民族国家的主张,遭到立宪派人士的强烈反对。杨度认为,不能以一族建一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规划中国的未来,若汉人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人均可循例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最终中国将分崩离析。(17)杨 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0~281页。杨度提出一个“同国异种人”的概念,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满、蒙、汉、回、藏之人均已成为中国之人民或国民,满、蒙、汉、回、藏之土地也已成了中国的领土。为了中国不致于分崩离析,杨度主张国家建设要超越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念,保全五族之土地和人民:“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18)杨 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4页。如果说革命派提倡的是建设民族国家的理念,那么杨度倡导的显然是一种建设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在杨度之前,较早介绍民族主义思想的梁启超受到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国家学说的影响,在1903年即修正了自己的主张。伯伦知理区分了民族(英语:People;德语:Nation)和国民(英语:Nation;德语:Volk)的概念,指出前者具有种族含义,后者更具有政治含义。按照伯伦知理的看法,不同民族的人可以共建一个国家(state),而这个国家内的全体人民便是国民,形成国民国家(National State)。(19)Johann Kaspar Bluntschli,The Theory of the State,Kitchener:Batoche Books,2000,pp.79~97.梁启超指出,伯伦知理所说的国民国家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符合中国国家建设的需要,他将建设汉人民族国家的理念称之为“小民族主义”,认为相比于“小民族主义”,更应提倡“大民族主义”,并解释说,所谓的“大民族主义”即“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未来的中国要“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使这一“大民族成一国民”。(20)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梁启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4~215页。在陈建樾看来,梁启超在多民族环境下处理现代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以个体权利的平等来彻底弭平社会成员在民族身份上的差异”。(21)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虽然梁启超在使用“大民族”一词,但跟其先前推崇的一族建一国民族主义理念已有一定区别,某种程度上具有多民族共建中国的内涵。
针对立宪派提出的多民族国家话语,很多革命派人士起先并不以为然。汪精卫1905年在《民报》刊文批驳梁启超的国民论,他认为国民主义要求人人平等,而事实上满汉并不平等,满人处于征服者地位,汉人处于被征服者地位,这种不平等使得共建一个国民国家不大现实。汪精卫提出:“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复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22)精 卫:《民族的国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97页。在汪精卫看来,即使国民主义要实现,也要先排满。孙中山1906年12月在解释三民主义时,仍旧坚持传统的民族国家理念。他提出,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诉求是从满人手中夺回政权,建立汉人自己的国家:“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那里?政权在那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23)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4页。章太炎在1907年作《中华民国解》,批评杨度之前所写的《金铁主义说》,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民族国家并不一定遭致列强干预瓜分中国领土。他认为如果列强真要瓜分中国,早就可以做了:“庚子联军之役,四方和会,师出有名,而虏酋亦已播迁关右,不以此时瓜分中国,乃待日本胜俄之后乎?”(24)章炳麟:《中华民国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743页。
但部分革命派人士则认为立宪派的很多担忧不无道理,他们逐渐放弃了建立单一汉人民族国家的主张,转而开始接纳立宪派提出的多民族国家话语。身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刘揆一在辛亥革命前就承认:“蒙、回、藏者与满洲同为吾国之藩屏也,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刘进而提出,革命党人应团结汉、满、蒙、回、藏五族先进分子推翻满清政府,共同建设共和国家。(25)刘揆一:《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载章开沅,罗福惠等《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7~239页。黄兴涛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同盟会中的领导人物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五族共和指导思想,并在革命后成为南北双方普遍认可的政治信条。(26)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95~97页。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也部分印证了立宪派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担忧,沙俄和英国一直在跟一些外蒙古与西藏地方势力勾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边疆地区特别是外蒙古和西藏发生动荡,受沙俄支持的部分外蒙古地方王公悍然宣布独立,西藏地方也发生驱除满汉官员的事件。至此,革命派清晰地看到,如果再坚持建立汉人民族国家的主张,蒙、藏等边疆地区将很快独立。孙中山在革命后也不再坚持建汉人民族国家,转而提倡五族共和,强调民族统一、领土统一。(27)郑大华认为,除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压力,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也有出于团结革命派同侪的需要,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参见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问题》,《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他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28)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同年2月13日,孙中山在给蒙古王公的电文中再次明确,中华民国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建:“帝制已除,合五大民族为中华民国,幸福无涯,中外同庆。”(29)孙中山:《复蒙古联合会蒙古王公电》,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页。
对立宪派而言,他们本是提倡“五族君宪”,但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使得君主制难以维系,那么过渡到“五族共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也不愿看到满汉之间的种族相残,(30)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最后不得不接受“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写明了“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又明确了五大民族一律平等。(31)《宣统政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93页。就这样,南北双方就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达成了共识,从而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延续性”。(32)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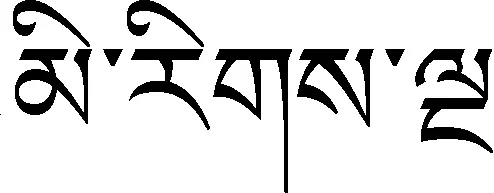
虽然多民族国家理念在辛亥革命前后同时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支持,并在民国初年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但这套话语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稳固。倡导多民族国家理念的梁启超、杨度等人在肯定中国多民族结构现实的同时,还提出一个同化主张。梁启超希望建成的“大民族”是要以汉人为中心,将其他四族“同化于我”,并认为满人实际上已被同化。(3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梁启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4~215页。杨度也是持相同观点,他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说:
夫国民统一云者,欲使全国之民语言文字一切皆同也。然使中国国中各民族,而如俄及匈、奥之数十民族并立,而无一人数多、文化高,可以统一其他诸族之资格者,则虽欲统一而不能统一。而幸也,中国有汉族在,其人数之多,数倍于其他各族之和数;其文化之高,各族中无可与抗而不相下者,则仍以汉化统一之,亦甚一易事耳。又幸也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已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则五族之中,其重要之二民族,既已将合为一矣。由此进而使蒙、回、藏等亦同于满汉之文化,则国民统一之策于以告成。(37)杨 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些晚清民国初年的立宪派人士并不是多民族国家理念的纯粹拥护者,他们只是将多民族国家话语视为维系国家疆土统一的工具。当然,人们也可以将这些言论解释成受到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影响,即通过同化建构一个大民族是为了最终形成国民国家。但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国民(Nation)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种族或文化概念,具有多个民族的国家如瑞士也可以建成国民国家,而不需要通过同化统一境内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本质上,一些立宪派人士在对待多民族国家理念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多民族国家理念有助于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并不满足止步于多民族国家,他们希望以同化的方式将多民族改造成一个“大民族”。在民国初年,五族共和论虽然是官方主流话语,但民族同化的声音不容忽视,不仅立宪派,先前就主张建立汉人民族国家的革命派更是倡导“种族同化”,成为主流话语之外的另一股潜流,有学者就指出,“1912年至1914年间,各政治、社会团体的族群政策主张,不约而同地指向‘民族同化’”。(38)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上),《共识》2014年春刊。
二、民族国家——国民党的现代国家建设方案
“五族共和”承认境内存在五大民族并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固然是有利于汉族政治精英团结满、蒙、回、藏共建一个新国家,但这套方案没有解决的是,如何在中华民国塑造一个共同的认同。在一些汉族政治精英看来,“五族共和”重多元轻一体,是会导致民国“四分五裂”的。孙中山就对“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国家话语进行了批评,认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与革命党人之间以及北洋军阀内部纷争引起的社会撕裂,都源于“五族共和”甚至只是因为北洋政府使用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39)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页。孙中山的批评固然有一些牵强,但从中不难看出,他担忧“五族共和”不利于共同认同的塑造。(40)龙晓燕,薛 昊:《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孙中山民族思想研究》,《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也因此,孙中山1919年对民族主义的阐释又回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理念。他在当年的《三民主义》一文中,将民族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消极的民族主义,即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恢复了汉人政权;第二阶段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即把国内各个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建成民族国家。他认为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要完成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在孙中山看来,建立民族国家是天经地义之事,世界各国都循此例,同属于一个民族的必然会争取摆脱其他民族的束缚而独立建国,如日耳曼摆脱拿破仑、希腊摆脱土耳其、意大利摆脱奥地利、芬兰脱离俄国、波兰重建等等。但孙中山认为,以上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其民族定义主要局限在血统、宗教、历史习尚、语言文字等。他提出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主义,其民族要靠“意志”来定义。他以瑞士和美国为例,瑞士由日耳曼、意大利、法兰西三国人民组成,三者的血统、历史、语言各不相同,但都“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最终形成了一个瑞士民族,美国则是融合了欧洲各个种族以及同化了数百万黑人而形成了一个美利坚民族。孙中山认为,所谓“民族之意志”就是倡导民权或者说是民主,瑞士、美国民族国家的建成有别于日耳曼、意大利、法国,不以血统、宗教、历史、语言而以共同倡导民权的意志来定义新构建的民族。(41)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6~187页。
孙中山关于瑞士、美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观点看起来颇受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影响,与其说瑞士所建立的是文化一致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倒不如说是包容文化多样性的国民国家(national state/nation-state)。但是孙中山要建立的民族国家是瑞士那样的国民国家吗?这里是有疑问的。王柯就认为,孙中山所强调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型的民族主义,“更为重视血统等自然因素,而忽视了建立政治共同体意识对形成Nation的作用”。王柯还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到最后都没有摆脱种族思想的桎梏。”(42)王 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6页。从孙中山后来对民族国家建设的言论来看,他确实更看重种族因素以及文化一致性。在1921年3月6日的一场演讲中,孙中山还耿耿于怀革命之后没能建立汉人的民族国家,认为这就是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的一个标志:“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他认为未来国民党实现民族主义的方式就是要同化满、蒙、回、藏:“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相比于包容文化多样性的瑞士模式,孙中山更推崇文化一致性的美国模式,指出中国应该学习美国建设美利坚民族的经验,把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然后把这个新汉族改称中华民族,这样就建成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才算成功。在那场演讲中,他虽然也推崇瑞士,认为它是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且是采取直接民主的制度,其民主程度要比法国这样采取间接民主制度的国家更高,但全然未提及瑞士在民族政策上并不采取同化政策,反而一直在强调国民党未来应采取民族同化政策:“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本党所持底民族主义,乃积极底民族主义。诸君不要忘记。”(43)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3~475页。在同年12月10日的另一场演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所希望建立的是种族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此种革命主义,即三民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第一之主义,为种族革命,谓排除他种民族,发扬自己民族,组织一完全独立之民族国家也。”(44)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国家建设理念并不是国民国家式的,他对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存在一定程度的误用。为了佐证自己理念的合理性,他呈现了美利坚民族的例子,但他所说的美国将各国人、各种人同化成一个美利坚民族只是一种“民族想象”,并非是当时的客观事实。(45)励 轩:《超越灯塔主义:美国种族与族群政策再认识》,《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的晚期与苏俄接触,受共产党人影响,其民族主义思想又有所变化。从1924年1月23日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来看,他当时放弃了建立文化一致性或种族型民族国家的主张。孙中山将其民族主义的意义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对外而言寻求中国民族的解放,二是对内要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宣言中,他没有提要同化国内诸民族成一个新民族,而是声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6)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119页。如果光看这段表述,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从建设民族国家转型到了多民族国家。但孙中山1月27日起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又呈现了不一样的民族主义思想图景。他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实际上又回到了民族国家理念中去:“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何以在中国是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呢?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47)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5页。孙中山觉得中国的民族结构是一元的,主体就是汉族,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数太少,可以忽略:“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48)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8页。在演讲中,孙中山高度推崇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念,认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49)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0页。积极呼吁国人恢复及养成这种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孙中山在那场系列演讲中,对民族国家的再次推崇,给国民党造成了思想混乱,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他在一大宣言中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设多民族国家等主张的积极作用。(50)郑大华分析过孙中山系列演讲与此前一大宣言民族主义理念不同的原因,认为一大宣言中的“民族建国”思想更多体现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非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因此孙中山很有可能是需要通过系列演讲来重申三民主义本义,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参见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问题》,《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继孙中山之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的蒋介石则继续宣扬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理念。在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构想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如果民族国家只存在一个民族,那么汉、满、蒙、藏、回等应该怎么称呼呢?孙中山在其文章和演讲中,还经常将满、蒙、藏、回都称为民族,这难免会与他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理念形成矛盾。既然满、蒙、藏、回都可以称为民族,岂不是他们也都有资格建立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针对这一逻辑上的漏洞,蒋介石试图通过取消汉、满、蒙、藏、回的民族地位来予以改正。他在1929年关于三民主义的一场演讲中,把汉、满、蒙、藏、回称为种族,把民族留给了“中华民族”,这样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就仅指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五个种族构成。(51)蒋中正:《三民主义纲要》,《中央周报》1929年第63期。抗战期间,他又从孙中山1924年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获得启示,将汉、满、蒙、藏、回等国内各民族的地位从种族降为宗族,认为宗族之间有紧密的血缘关系,有如兄弟组成一个家庭:“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52)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户、千户讲》,载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16页。在蒋介石抛出中华民族宗族论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他在捏造中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53)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摘录)》,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46~947页。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的民族国家话语并非始终坚固如一,孙中山去世后,其内部也存在着对这套话语该如何理解的争议。20世纪30年代初,在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时,就有立法专家卫挺生指出,不提民族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民族问题了,民国成立20年来,既没有解决蒙古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西藏的问题,西北则还有回族的问题。他认为虽然“满洲民族”一些人已经跟内地同化,但还有一些并没有,回民也是这样。他认为不应回避中国存在多民族的事实,建议在宪法上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保障。卫挺生还以瑞士为例,认为“瑞士由三个民族合成,能够相安无事,就是对于各个民族有相当承认的缘故”。(59)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203~204页。在1936年最后成形的《五五宪草》中,并没有把各民族矮化为蒋介石之前所主张的种族,而是使用了“民族”一词,《五五宪草》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份子,一律平等。”(60)王一岑:《“五五”宪草全文述评(附以试拟修正条文及说明)》,《民宪旬刊》1941年第十二期。从这条规定来看,国民党内部对于构建nation-state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但对于这个nation是应该叫中华民族还是中华国族以及是否应该承认国内各民族的民族地位是存在不同声音的。
黄兴涛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高层内部有不少人,如孙科、冯玉祥等坚持认为应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甚至戴季陶、于右任和张继也曾支持这一看法。他还认为,蒋介石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那套中华民族宗族论影响时间是有限的,“它在政治思想界的公然传播和绝对主导地位,也就只有不过三四年而已”。(61)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1~327页。黄兴涛的论断是正确的,蒋介石1945年8月24日在解释民族主义的一场演讲中,就没有用他那套中华民族宗族论。他说实施民族主义有三大原则:“1.必须怀抱崇高的精诚,共同尊重民族独立的原则,保障其地位。2.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扶助他们独立自由。3.在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于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62)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讲》,载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70页。蒋介石的这段话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方面,他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且无论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他允许部分边疆民族的独立。蒋介石此番对民族主义的阐释,与先前要将国内各民族同化为一个大民族的主张完全不同,意味着国民党传统的民族国家话语发生了较大的松动。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变,有可能是蒋介石受到其外国顾问的影响,比如拉铁摩尔就曾为他撰写抗战胜利后处理东北、新疆和蒙古问题的报告,并建议扩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自治权。(63)励 轩:《学者的角色:美国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者与对华政策制订》,《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再则,国民党内部精英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士并不认可中华民族宗族论,而是要回归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上来。(64)格桑泽仁:《向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全文》,《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1946年,第35~36页。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建设方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有关于国家建设的论述,如1922年中共二大决议案中所主张的:“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65)《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摘录)》,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页。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要建设的中国决非是国民党所期望的民族国家。其反对理由在党的早期文献中说得很清楚,认为这种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在捍卫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符合最广大无产阶级和境内弱小民族的利益。(66)《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摘录)》,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页。中国共产党担心主体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借着建设民族国家的名义迫害较弱小民族,如当时土耳其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压迫境内少数民族。进一步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方案跟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推行的五族共和式的多民族国家理念也有差异。五族共和是在单一制中华民国内建设多民族国家的方案,而中国共产党早期想要建立的是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是主张境内部分民族先成立各自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再由这些民族国家组成一个联邦国家或者多个民族国家的联盟(Union of Nation-states)。(67)民族国家联盟可以算是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的一种形式,只是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国家(state)是由多个国家(states)联合而成的联盟(union)。
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国家联盟的国家建设理念当然是来自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还是1922年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均是按照民族国家联盟的理念来建设的。不过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联邦制的,列宁曾经高度肯定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建设形式,在1914年发表的《论民族自决权》中,列宁说:“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68)《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正如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列宁十月革命前夕还在反对联邦制,(69)张祥云:《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规模建制理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3期。他在1917年8至9月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中说:“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70)《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页。列宁乐观地预计只要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俄罗斯各族人民都会热烈拥护这个新的单一制国家。但十月革命形势并没有向列宁先前以为的那样发展,很多少数民族反而纷纷宣布独立,俄罗斯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为了防止国家的彻底解体,同时也为了赢得少数民族对新政权的支持,列宁在承认各民族根据自决原则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主张采用联邦制国家形式,使各民族国家通过联邦制重新统一为国家联盟。列宁1918年1月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71)《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联邦制或者说民族国家联盟的建设方案在当时比较好地解决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承认民族自决权与维护国家统一之间的矛盾。当然,布尔什维克的联邦制或民族国家联盟绝非是松散的,而是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列宁早在1903年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72)《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8页。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好像是黏合剂,把加入联盟的各民族国家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从而保障在特别情况下才出现的联邦制国家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积极主张民族自决,即境内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前提下,自由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民族国家联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至1937年),其宪法大纲就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7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摘录)》,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提倡建设联邦制国家或说是民族国家联盟,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单一制国家,其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内存在多个民族,且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视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之所以成立初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推行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在倡导的联邦制,原因可能在于它实际控制范围内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长征时期,红军经过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的涉藏地区,中国共产党就帮助藏族在当地成立了两个民族国家,即1935年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和1936年建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并以自愿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的形式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联盟。但联邦制的尝试非常短暂,随着红军陆续北上,这个民族国家联盟就结束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方面开始提有别于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并在陕甘宁一带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建立回民自治区、乡等。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发言中还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74)毛泽东:《论新阶段(摘录)》,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这一主张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联盟方案有很大区别,它不强调先分后合,而是认为应该在自治原则下直接建立统一国家,我们完全可以将毛泽东的这段讲话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话语的开始。当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也一再运用中华民族话语来团结国内民众进行抗日,毛泽东甚至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7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但中国共产党所认识的中华民族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前者承认中华民族是由各个民族构成的,某种程度上应作为包容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国民政治共同体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民族国家”则应是国民国家而非国民党宣扬的种族与文化同一性的民族国家。由于民族国家话语在国民党的宣扬和实践中已经刻上了民族同化等负面烙印,为了防止在学理上引起误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此之后几乎不再提中国是民族国家这类说法。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最为有名的当属1947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不过,这不意味着联邦制的选项当时就退出。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黄铸回忆,中国共产党真正决定彻底放弃联邦制是在1949年。李维汉1983年曾经给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写过一封题为《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的信,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联邦制的过程。信中说道:“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作了点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76)黄 铸:《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具体的理由则给了两条:第一是中苏之间人口结构不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47%,而中国则只占6%,且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是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第二是苏联实行联邦制有迫不得已的成分,十月革命前列宁是主张在单一制国家内推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而非搞联邦制的,但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用联邦制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而中国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进行革命,直接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共和国,没有经历过民族分离。(77)李维汉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解释过中国为什么不搞联邦制,较为详细的论述是在一篇写于1962年的文章中,参见李维汉《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5~5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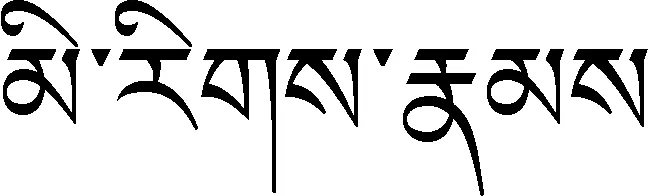
四、建设人民国家——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实践
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理想与真实世界的现实存在着极大的差距,真实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人口均质化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为了消减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实现国民团结与凝聚,早期的西方国家往往会通过改变文化群体多样化的人口结构,建构一个所谓的国族,从而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理想。(80)张会龙,朱碧波:《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但这种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往往意味着对国内少数民族地位的否定,对其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同化,甚至是肉体上的消灭。同时,这种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也极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甚至战争,纳粹德国正是打着统一整个德意志民族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泛德意志主义旗号,吞并了说德语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成为“二战”爆发的前奏。与这些欧洲经典民族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塑造共同认同的方式并不是靠建构人口均质化的国族。列宁1922年根据苏俄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指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要尽可能关心和满足各民族的利益,才能消除各民族冲突的根源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才能建立起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列宁认为,没有这种信任,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是无法建立的。(81)《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9页。由此可见,列宁是不支持把苏俄国内各个民族都同化成一个苏俄民族或苏联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建设有别于早期欧洲经典民族国家执着于建构出一个均质化的国族,而是强调国家的人民性,主张各族人民自愿联合为一个人民共同体,从而在国家层面构建出一个超越民族的共同体。李林将这种基于人民性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人民国家”,认为通过确立和强调国家的人民性,国家得以通过“人民”来摆脱被“国族”所绑架的“民族国家”。他还指出人民国家相对于民族国家的优越性:“由于国家将自己的属性确定在超越‘族裔’的人民性上,而不再以某个民族的族性作为自己的‘标准’,从而使超越‘国族’的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分大小的所有民族,相应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平等对待各个不同的民族。”(82)李 林:《超越“国族”的主权国家建构走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二战”结束后,西方各国也意识到了传统民族国家建设的局限性,基本停止了通过民族同化、种族灭绝、对外扩张等构建国族的方式,转而拥抱公民民族主义、宪法爱国主义等包容性政治理念,将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与种族和文化上的民族脱钩,从而实现最高层次人们共同体的国民化或去民族化。这种去民族化事实是对主权在民的回归,强调的是建构可以容纳各民族、各种族、各族群或各文化群体的人民共同体,(83)励 轩:《对一些多民族国家“人民”话语的分析》,《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也就说是,当下西方那些所谓的民族国家启示更强调民族(nation)作为国民政治共同体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不仅形成了一套包容且自洽的民族话语体系,同时也在具体政策层面表现出对各族人民民族地位和政治权利的尊重及保护,从而大大增进了各族人民对人民国家的认同。自1953年至1979年,政府先后组织了数次民族识别工作,一共识别出了56个民族。不同于早期西方经典民族国家中的种族或其他文化群体,中国的56个民族是具有相应政治权利的。党和政府在除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并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中保障各少数民族有相应代表,同时还通过各种法律保护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信仰权利。由于中国的民族结构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在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为了防止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曾发声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8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7页。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这些实践总体来看是非常成功的,大大增进了各族人民对人民国家的向心力,保障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的总体和谐。从纵向来比较,中国历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人民国家各族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权益是最多的,各族人民对人民国家的认同度是最高的,同时人民国家对分离主义势力的控制也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从横向来比较,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西方国家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还远远无法达到中国的水平,如美国对少数族裔还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歧视,澳大利亚还以文明化的名义对原住民群体实施同化政策。在此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处理民族问题的理念和实践,实际上逐渐被很多西方国家所肯定和借鉴,部分国家也陆陆续续推出一些类似政策,包括肯定原住民的自治权利和民族地位、保护和发展原住民文化、消除种族和族群不公、推行平权行动等。(90)励 轩:《超越灯塔主义:美国种族与族群政策再认识》,《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
五、余 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经过百余年的探索,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国名就在告诉世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人民国家,各族人民都属于一个人民共同体——中国人民。人民国家的建设理念深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骨髓,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9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1日。再次代表中国共产党表达了继续建设人民国家的伟大决心。中国共产党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理念与实践具有世界性意义。随着“二战”后人权及少数群体权利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世界各国已不太可能采用以往民族同化、种族屠杀等方式进行国家建设,甚至西方国家也转而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和调整。比如,有鉴于运用民族国家概念在理解现代国家时往往会忽视后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现实,有西方学者开始积极倡导使用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 multinational state)概念来形容那些人口结构多样化的现代国家,(92)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11.从而在话语上消减现代国家建设必须通过构建民族国家来完成的困境。此外,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还出现了一个最高层次人们共同体去民族化的过程,即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不再与同质化的人口结构进行绑定,而只保留其国民政治共同体的内涵。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理念与实践无疑走在了前列,为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更为包容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应对边疆民族地区一些分裂势力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以及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中央在十九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命题。就增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来说,我们不能聚焦于建构种族和文化上单一的民族国家,这种路径早已被中国共产党所否定,同时也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本身早就超脱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束缚,强调的是在国家层面建设一个可以包容各个民族的国民政治共同体,各族人民则均属于这一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凝聚各个民族的并不是要将各个民族取代的族裔因素。在早期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其实是通过强调各族人民的阶级性使各族人民产生出超越民族的阶级感情,从而达到凝聚各族人民认同的目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阶级观念逐渐淡化,我们很难而且也不应再依靠强调阶级性来增进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人民国家建设就需要新的凝聚因素,且它们需要超越民族并又能被各个民族所认同。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凝聚因素中,宪法与共同价值观是其中最应该值得我们重视的。在中国,宪法不仅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也是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契约,是超越各个民族之上的存在。作为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凝聚各族人民人心、定义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认同的中国信念(Chinese Creed)。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质是要加强和巩固各族人民对中国及其国民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大方向之一无疑应是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国宪法和中国信念的认同、信仰和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