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李素伯
素伯是我的弟弟。他原名李文达,进了南通师范学校后,遂以素伯字行,笔名所北。当时他的笔名很多,有的笔名我现在已记不清了。
我的老家,原在长江下游的北岸,现在太安港向西南十多华里处。这地方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坍入长江之中。那时从南阳村向南一直到长江边,称为崇明外沙,属崇明县管理;从南阳村向北,到蒿枝港,东到黄海,属海门县管理。踏在家乡的土地上,东望长江出口处,但见海燕纷飞,水天一色;隔江南望崇明岛,但见树影时隐时现,犹如浮沉于长江之中;西望长江上游,但见白浪滚滚东流,似无尽期。当时身临其境,素伯曾对我说:看到此情此景,真觉得气象万千,心胸为之畅快。他在1935年写的一篇《家》的小品文中也作了描述: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个住所的环境的优美。那时的家滨临一泻千里的大江,在一条小港旁边,跨着港口有一架不很阔大的桥,桥两边有成排的瓦房,成了个小小的市集。最有趣的是江上的风光:在月光下一片浩渺如练的江波上,风帆缥缈,沙鸟翱翔,远远隐现着淡灰色的一片,那是峙立江心的崇明岛。明朗的日子,会辨得出那‘如荠的一团团绿树;偶然风雨横来,怒涛汹涌,也着实惊心骇目。……十岁离开那里,几年后据传闻所得,那个小市集子整个迁移,小桥曲港遗迹难觅,我的家当然也唯有永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家除父母外,唯兄弟二人。父亲帮人家酒店做伙计,母亲常帮人家做做针线活串串纸锭,收入低微,生计维艰。即便如此,父母亲仍克心尽力送我们兄弟俩上学。在素伯7岁时,父亲去世了。素伯在《府君述》中回忆道:
府君讳选青,字飘庵,性廉洁,喜饮酒,不屑屑治家人生计。宅前有隙地数弓,暇辄携铲芟草,植芜菁之属,青翠肥泽,间植樱桃月季数本,甚茂盛。优游数十年,以嗜酒得疾,卒年仅五十有一。时达七岁,犹记府君貌甚奇伟,鬑鬑有须,居恒默默不与人接,视其意,若有不可与人言者,岂其中有不自得者欤。自府君之卒,家益落,乃迁于通之垦牧乡。
通之垦牧乡,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海复镇一带。父亲去世后,我姨母看到我们母子三人在这坍海滩边难以生活,就叫我们迁到她那边的海复镇居住。到海复镇后约一年有余,我的母亲又去世了。于是,我家一切事情,都由我的姨母作主安排。她把我送入人家商店里去当学徒,把素伯陪送到南通师范学习。从此,我们兄弟两人相见的机会就少了,十多年中,除假期相会外只能通信相问。
童年时代,我与素伯一起上学,同出同归。我们开始入学时,适在辛亥革命之后,这时,大一些的市镇都有所谓“洋学堂”,而农村中的私塾,仍然有很多,他们所教的书,是《百家姓》《三字经》《古文观止》等。而我们在“洋学堂”里所学课目有: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手工等。素伯读书很是用功,每逢下课时,大多数学生在操场上打球,跳绳,踢毽子做各种游戏,而素伯往往独坐在课堂里看书写字。
我们那所学校,名“三镇公学”,共有五六名教师,其中龚步高、薛丕仁两位老师对我们最亲热。素伯学习用功,每次期末考试总是名列前三名之内,他们曾因此而赠送给素伯簿子等物。
我们这里,开化风气较先,谈新思想,新潮流的人很多。素伯听在肚里,思想就发生了变化。记得在初上学那一天,他向我说,我们这个尾巴(指头上的辫子)一定要剪掉它。他嘴里说,就拿起剪刀把头上的辫子剪去,同时替我也剪去。我现在想想,他这种胆识自幼就在他脑海里孕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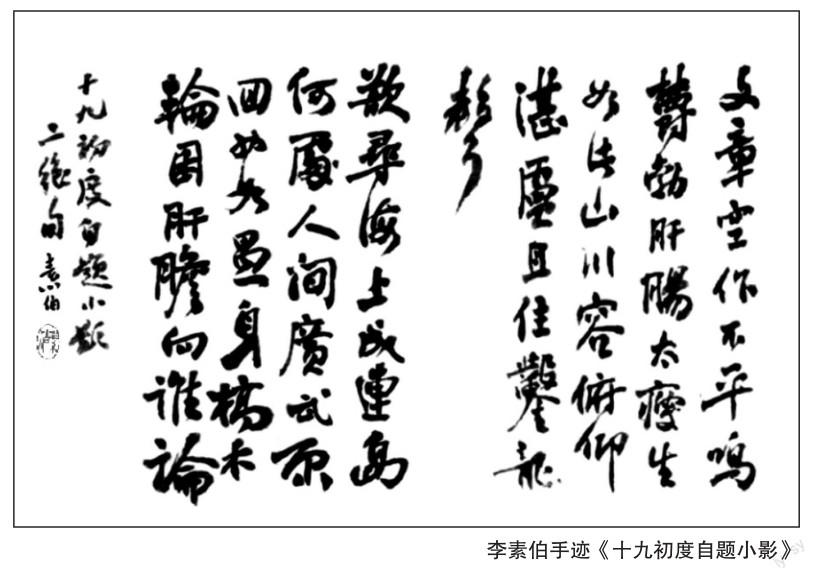
每逢清明、中秋等佳节,老师领导我们全体同学正队游行,一名踏青,又名远足。我们的队伍,在柳荫麦浪中前进时,大家唱着平时所教的歌曲,如:《燕子歌》《下雪歌》《辛亥革命歌》,歌声悠扬而悦耳,步伐整齐而严肃。队伍行到大江边,大家散队,自由取乐。面对浩瀚的大江,素伯常喟叹不已。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此大好河山,眼看要被列强瓜分侵占,我们都要做亡国奴了。我们全国人民宜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切不可含糊了事的。” 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在他后来的作品(如《春的旅人》《血写的历史》等)和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我们兄弟二人,弟弟崇尚笔墨逞风流,而我则信奉“铁与血”的武器批判,彼此心意相通。1927年间,我参加了海复地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江允昇、周智民等对垦牧公司及地主阶级作出了种种斗争。后在1929年,我奉命打入海复公安局内部,对士兵做宣传工作,并伺机搞他们的枪械。那时党内缺乏武器,搞到枪械后,准备组织武装暴动。谁知到了1930年,大批国民党省保安队开到苏北来,把共产党的海门县委书记洛克捕杀,并把各个区的组织摧毁,又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海复地区的党组织也未能幸免,江、周两烈士牺牲,于是我和上级的联系完全断绝。苏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走向低潮。发生此事后,我曾去信告诉素伯,素伯对革命非常同情,当即写下了《寒食得兄书悲愤交集怃然有作三首》发表在当时南通报纸上。其中第二首写道:
贫贱有兄弟,艰难复乖离。
诗书得穷饿,少壮乃羁栖。
重以狷狂骨,宁为世俗知。
中原成画晦,何处啜残糜。
家境的清贫,羁栖的身世,社会的黑暗,前程的迷茫,使我们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素伯在他的作品中以各种不同的笔调表现着这种仇恨,发挥了时代浪潮中一滴水的作用。

素伯当教师的后期,生了痔疮,曾入南通基督医院割治,没有得到根治。后有友人介绍,说西亭有个专治痔病的医生,他就到西亭去医治。那个医生是用挂线烂的法子医治的,谁知烂破了血管,一直放血。而这个医生不懂扎血管的办法,任其放血。这时来信叫我去,我到那里时,他的面色洁白,精神不振。我就叫一只木船,送他到南通医治。当时替他输血,并吃各种营养食物。我在那里看护他约三四个月,渐见好转,面色也起了红润。他对我说,现在你可回家了,我这里有护士照顾,你可放心。于是我就回家了。后来到了将过年时,他写信来,要我接他回海复过春节,我就叫了一辆汽车去接他。哪知第二天回来时,天阴下雨,汽车在路上颠簸不稳,到家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适。后来身上各处起块粒。因此,过了春节,我只得再叫了一只木船送他回南通医治。据医生说,那是不治之症,因血液中有毒,所以起这种块粒。果然,于1937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素伯不幸与世长辞了,享年仅30岁。
当时,素伯的好友丁守谦、李也止、余谷澄等,协助我们(当时去南通办理丧事的有4个人,我和我的姨母陈佩兰,我的姨姐夫许忠孝,还有我的姨母的大孙子沈鉴渊)办理丧事。把他的遗体寄放在师范校河东文峰塔下的五福寺中。顾怡生等老师以及素伯的学生,都来哭祭守灵。后来,我们把素伯的棺木云回海复,在海复镇买了二亩地做了坟场。在“大跃进”时期,素伯墓被拆迁。我们把他的骨殖移入一瓮坛中,放在海复镇的公墓上。于1986年,由他的学生出私资,在启东县政协的支持下,并派老主席陈邦才等与海复乡政府研究拨给了一块坟地,替他重建了坟墓,四周种了各种树木,并立了石碑。
素伯在通师时,曾做了二张书橱,放在师范校后楼上。这间楼房里,大部分是他的东西,除二张书橱外,还有近十只书篮,里面装满了书籍和他的创作手稿等。素伯逝世后,我们曾想凑船的便,把它们运回海复。后来,他的同事和极知己的朋友,如丁守谦、俞谷澄等对我说,你们带回去也没有什么用,不如放在这里,等我们有了空闲时间,把他的著作整理出来,结集出版,将来也好作个纪念。我想那是一件美事,就答应了。哪里知道,后来日寇侵占南通时,素伯的东西也就毁尽了。这是使我极感痛惜的事。
素伯回海复时,曾带回近十幅他自己作的画,内有一幅长卷,长约三公尺,中间是他自己的画,两头是他的好友题的诗或词。并又带回《小品文研究》一书。这几样东西,也在日伪侵占海复时遗失了。因我家曾被敌伪抢劫过三次,家中东西,几乎被抢光。仅存的素伯早年著述一本,以及一本影集,已于1982年捐赠给南通博物苑了。
另外,关于素伯的婚姻。我的母亲,自幼替他定了婚姻,后来因为他不满意,就解除了。在他20岁后,一方面因为患病,更主要的是立志教学和写作,所以直到去世时,尚未成家。
素伯去世虽有44个年头了,至今每一念及,仍不免悲戚。今天大家纪念他,素伯在天之灵,也应得到告慰。
(作者简介:李文奎,字逸农,号海滨野叟,江苏省启东市海复镇人。李素伯的哥哥。幼孤,家貧。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江允升单线领导,抱定个人牺牲,积极为党工作。1930年8月江允升壮烈牺牲后,李文奎未暴露身份,但从此失去与党的联系,后从事商业工作。此文为李文奎先生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