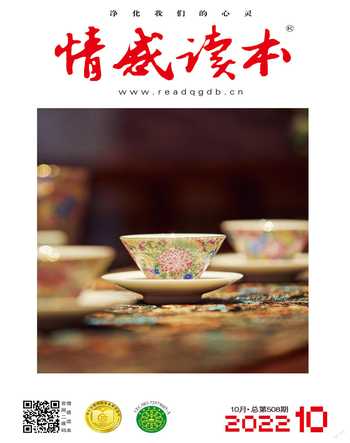拥抱父亲
罗生
去医院的路上,父亲只顾埋头蹬车,骑得飞快,不多说话,只是偶尔回头问一句:还痛不痛?忍着。抱紧。
记忆中,唯一与父亲怀紧贴背的拥抱,就是初二那年我踢足球左手骨折的那次。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也不用参加什么补习班,每天放学以后都有大把的时间任由挥霍,彼时我已经彻底掉进了足球的坑,每天下午放学就跟着一班同学往足球场跑,在球场上尽情宣泄自己的青春荷尔蒙。踢球的时光是快乐的,但受伤也是不期而至。
夕阳映照下的高州大球场,霞光漫天,尘土飞扬(彼时球场还没有草皮),一个个小伙伴的面孔影影绰绰,看不真切,但“传球”“大脚”“射门”等叫喊声却是此起彼伏,清晰可辨。那时流行“两翼齐飞,边路传中”的战术,沿边线带球一路狂推的我,风驰电掣之际,突然前头人影一晃,横刺里杀出的小伙伴一记飞铲把我放倒在地,刹那天旋地转,眼前一黑……
隐约中,耳边传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音,小伙伴纷纷围上来,关切地问是否要紧,彼时,我是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感到阵阵钻心的疼痛。浑身使力爬起来,才发现左手手腕已严重变形,小伙伴们看着都吓坏了,有人搀扶我到旁边跑道坐下,有人赶紧跑去我家叫家长。
惊魂稍定,疼痛钻心倒不觉得什么,心里害怕的是父亲的责备。彼时沉迷足球,经常晚自习迟到,影响学习成绩,父母一直都有抱怨。
等到父亲赶到现场,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嘴角抽搐了一下,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慢慢地,父亲的目光转为温柔,他小心翼翼地扶我坐上单车后座,要帶我去农校旁的骨科医院打石膏。待我坐稳,父亲蹬上单车,回过头,用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抱着我,不要动。
大球场在环城路,农校在东门,两者说远也不算远,但却要翻越一个城里最陡最长的斜坡。街上行人不多,去医院的路上,父亲只顾埋头蹬车,骑得飞快,不多说话,只是偶尔回头问一句:还痛不痛?忍着。抱紧。我乖乖地伏在父亲后背,骨折的左手放在胸前,完好的右手缠绕着父亲的腰,紧紧地抱着。父亲在蹬车上斜坡的时候,隐约传来父亲滋滋的喘气声,伴随着单车链条咯噔噔的响声。车身有点晃,我抱得更紧了,一动也不敢动,生怕从后面掉下来。记得那晚月光如水,父亲在前面用力蹬车,儿子在后座紧抱着父亲,一辆单车载着两个人穿城而过,驶过宁静的街道,留下一段长长的轨迹,多年以后仍不曾磨灭。
時间之河静静地流淌。一转眼,我考上了大学,目的地是偏远的重庆,这是我自己坚持填的志愿。无他,就是想离父母远远的,越远越好,不用再忍受父母的唠唠叨叨。父亲送我去重庆报到。彼时,家里穷坐不起飞机,高铁没有开通,高州也还没有火车站。我们先是辗转到了湛江,踏上最便宜的绿皮火车,中间经停贵阳,一路哐当哐当,摇晃了36个小时,才抵达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父亲送我到了学校,帮我找到宿舍安置下来。当天,同学们已经全部报到了,寝室没有空的床位。晚上,父亲就睡在了寝室中间的长条大桌子上(四张书桌拼在了一起)。在同学的眼里,我的父亲有点怪,我也感觉有点怪怪的, 纳闷父亲为什么不去学校招待所住一宿。
重庆的暑天,出了名的酷热,即使到了深夜,温度也不会稍降。床上的我辗转反侧,偷偷看了眼睡在桌子上的父亲,父亲却睡得很沉,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完成了某种使命后的放松。窗外淡淡月色,映在父亲蜷曲的身躯上。黑暗中,我的眼角渐渐湿润了。
第二天,我送父亲走出校门,临别一刻,父亲看着我,只说了句,每个月,家里会定期汇钱给你,不用担心。凝视父亲的背影,我想着要跟父亲抱一下,但双手却不听使唤,只是呆呆站在沙坪坝街头,目送父亲消失在异乡的人海。
一晃这么多年,父亲给予了我足够的包容。从大学报志愿一定要去最远的地方,到寒暑假也不回家的四处游荡,再到成年后旁人看来不可容忍的错误,父亲都没有苛责,而是站在男人的角度,以沉默表达他的意见。
如今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年了,我怀念单车给我们父子之间唯一有过的拥抱。
郝兵摘自《人生与伴侣·综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