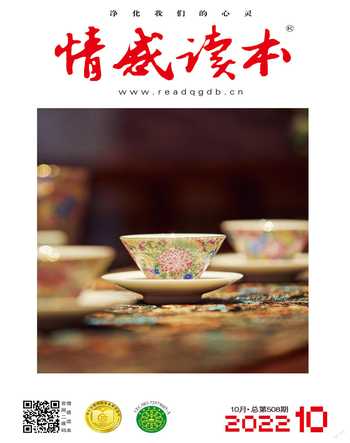我和母亲的感情, 就像一封从未拆开的信
不响
和母亲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个夜晚,我想起了那封未送出的信,我握着她的手,她用力地捏了一下作为回应,这封信也许还没有过期。
母亲今年53岁,过了九月的生日,踏入54岁,她这半生,没有什么被爱直接触动的时刻。
我今年20岁半,过了六月的生日,迎来21岁,我从来没有对母亲说过爱。
我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单亲家庭,父亲失责,强势固执。母亲全责,隐忍坚强。当谈起对家人爱的表达,我只能是对母亲,但许多年来,我一直逃避著任何有关谈论家庭温情的场合,中国人含蓄内敛,讲究留白的谈话艺术,母亲与我都做到了极致。我们很少讨论彼此内心的波澜,只在各自的房间吞声噎泪,我以亲眼所见的伤痕去衡量她所受的痛苦,却从来没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我愿意倾听。母亲时而用推测的语气试探着我:
“不会对你造成心理阴影吧?”她小心翼翼,暗含听到肯定回答的希望。
于是我也故作轻松:
“怎么会,我挺好的。”
一次本应开启的对话,在心照不宣的试探和领会中,成了冬天张嘴时的一团雾气,字句还未成形,便顷刻消散。
记得高三成人礼,学校要求家长与孩子给对方各写一封信,在典礼上互换信件。准备的那几天,母亲总是拿着纸笔,眉头紧锁,似乎使了竭尽脑汁的力气,最后只是敲开了我的房门,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我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话说就算了。但实际上,我并不愿意就这么算了,当时我的面前铺着信纸,也在想要对你说什么,我想对你说什么,我能对你说什么。
“成人”的命题,互换的仪式感,都让我对这份或许会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情感表达寄予了期待,我在意母亲的无话可谈,“期待”的每一条笔画,都以裂痕的模样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我在期待中破裂,但破裂依然是“期待”的模样。
成人礼那天,到了交换信件的环节,但我却为了下一项活动被安排到后台提前等待准备,母亲与我就这样,暂短地分离了。主持人声情并茂,配乐催人泪下,镜头扫过一个个拥抱的身影和哭泣的面孔,而我和母亲都在人群中,不知所措,我们是被“感动”排除在外的情感因子,是温情时刻永远的缺席者。我写了信,就放在母亲身边的椅子上的包里,在后台,我期盼着她能对我有所期待,忍不住打开包,看看有没有这样一封信,或许在逐字阅读的过程中,心中响起了我的声音,浮现了我的样子。
但没有。
仪式结束后,我们在散乱的人群中找到了对方的身影,母亲拿着我的包,说刚才大家都在哭,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要干嘛。我说,我也是。
我找到一个角落,打开包查看,里面只有我的信,封口的贴纸服帖平整,封线平直对齐,像是我们保持缄默的嘴。我抽出信纸,搓开每一张,确定了都是我的字迹我的内容,又倒了倒信封,再三检查我那一览无余的小包。
我的期待的确破裂了。
信的落款时间停留在了2019年12月8日22:52分,它的生命本应从这一刻开始,但因为一次无法避免的短暂分离,这个时间,成为了它保质期的最后期限。
疫情暴发两年以后的一个寻常的夜晚,母亲一如既往,洗漱,按摩,准备入睡。我因为疫情,不得不居家学习,面对难解的文章,正烦躁不已,喝了一杯又一杯水。我突然听见母亲叫我的名字,我略过声音的细弱和闪烁,心里只想着任务还没有做完,急不可耐地进入母亲的卧室,看到她平躺在床上,脸色发红,手止不住地颤抖,母亲说,给哥哥打电话,去医院。
在我去外地上学的日子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晚上,母亲在厕所突然晕了过去,她一个人在家,失去意识了很久,才醒了过来。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距离发生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在母亲口中,它已然成为了一件过去了的小事,她用“没什么”的口吻讲述,似乎这不再构成威胁,但听者有意,母亲突然的晕倒又恢复,以后怕和庆幸的形式存留于我的情绪中。我试图说一些温情的话语做一些迟到的安抚,但张口,只是喂进了一团米饭,最后这一话题以不痛不痒的一句:“还是得做个全面的检查”,告终。
十一点的夜晚,车辆虽少,但我们一路遇到的都是红灯,母亲靠在座椅上不断深呼吸,我握着她的手,冰凉嵌进她手上每一条粗糙的褶皱。在倒数第二个红灯处,母亲对我说,靠近一点,她的声音微弱,断续,感觉如果再大声一点就会震碎她自己。她告知了我每一份保险,银行卡密码,手机密码和保险代理人的名字,说,如果记不住这些流程,记住这个名字就好。我说,别说了,医院马上就到了。红灯依旧红,只是在我眼中,红色溶解,滴落在了眼镜上,最后泛滥成灾,我不忍出声。
想起来,我不仅几乎跟母亲没怎么说过动人含情的话语,我也不会在她面前流露出浓烈的情感,比如哭。被家人发现我在哭,对我而言,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会问你,怎么了,而我却不能说没事,即使沉默,这也会以悬而未决的心事留在母亲的心里,在家人面前哭,意味着我正在彻底地袒露着我自己,意味着我的确拥有着一些,我逃避着表现出来的情感,比如爱和在乎。
夜晚的急诊,白天的全面检查,换了三个医院,从心脏、大脑到神经,结果都是一切正常,但这让我们更加不安,因为未知,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母亲只是按照症状,吃药,吃得清淡,她小心翼翼,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复发,她总是想起院中一些差不多年龄的人,都没能过去五十几岁的坎,前一天正常,早早睡下,却再也没能醒来。
在五十岁的语境下,“正常”似乎自带悖论的性质,正因为此,母亲忧心忡忡。
还是一个夜晚,母亲一个人坐在客厅,安安静静,没了往常综艺的嬉笑,短视频的吵闹,她只是一个人坐着,若有所思。母亲突然叫我来一下,她再一次,更为正式具体地交代给我了一些事情,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点开一个个软件,让我重复她所演示的步骤,带我去看她藏在床垫下的东西,我说,你别吓自己,也不要吓我,肯定好好的。母亲说,就是以防万一,你也大了,得知道这些。她开始自顾自地在手机上操作着,我借口上厕所,在厕所里面失声痛哭,借着冲厕所和洗手的水流声,擤了鼻涕,换了气。
厕所冲了两次,水一直在流,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带着收拾好的平静,坐在了母亲身边。
那个晚上我一直在听,但什么也没记住,深夜我陪着她入睡,我握着母亲的手,她也用力捏了一下作为回应,她手背上的褶皱,似乎也因为一点一点上升的热度而舒展开来。听着她的呼吸,平稳,连续,我闭上了眼睛。但黑暗之中,我的思绪蔓延成一个个问号,勾连起我的不安和回忆入睡前我忍不住地想,如果明天早上醒来,发现母亲已经离开,将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办,心中吹过一阵风,几页信纸翻动,窸窣作响,我想起两年半前那封未寄出的信。它依旧静静地放在当时背的包中,成人礼结束以后,这个棕色的小包就被我掛了起来,它在衣架的最后面,被春夏秋冬的衣服所覆盖,我再也没有背过。蹑手蹑脚下床,离开了母亲的房间,找到了这封信:
“展信佳。
首先我要给你道个歉,因为在写信这一天,我又和你吵嘴了。”
我忘记了那天是因为什么吵架,但我们确实总是产生不愉快。母亲是个急性子的人,我总是慢吞吞,上学期间,我们总是在早上的时候因为我偶尔的臭美,夹了十几分钟的头发,或者穿了十分钟的鞋子,忘了东西又返回而浪费的几分钟拌嘴。因为答不出母亲问我的关于未来的规划,原本和谐的饭桌,吃进去的是饭菜,咽下去的却成了想要逃离的急切心情。母亲说她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我却不愿跟她分享有关我的学校生活、偶尔也获得的好成绩以及我到底想做什么。
尽管我感觉步入成年后,我们现在正慢慢地接近无数次我所幻想的温情时刻,但是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力量拉扯着我偏离这一轨道,或者说是回到那条既疏离又温存的正轨。当我拿出这份靠近却偏离的心情反复咀嚼时,我总在想,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大胆表达家人之间的爱,从我记事起就习惯于这种敞开直白的亲情关系中,能够将自己的心事、爱好分享给母亲,拥有面对彼此情绪的勇气,不再偷偷哭泣,这些温情在她的五十岁与我的二十岁,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别扭。但当我将这份关系勾勒得愈发理想而美好,我和母亲的面目就愈发空洞,最后只剩下两个轮廓。我们似乎没有想象另一种可能的余地。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且只能是这样,沉默的,偷偷的,总是无话可说,却也渴望再多聊一句,我们的感情形态就是如此,像一封从不曾拆开的信。情绪的河流在我们之间浩浩荡荡穿行而过,我和母亲都未曾见过这条河,但我们早已被浸湿。
和母亲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个夜晚,我想起了那封未送出的信,我握着她的手,她用力地捏了一下作为回应,这封信也许还没有过期。
田宇轩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