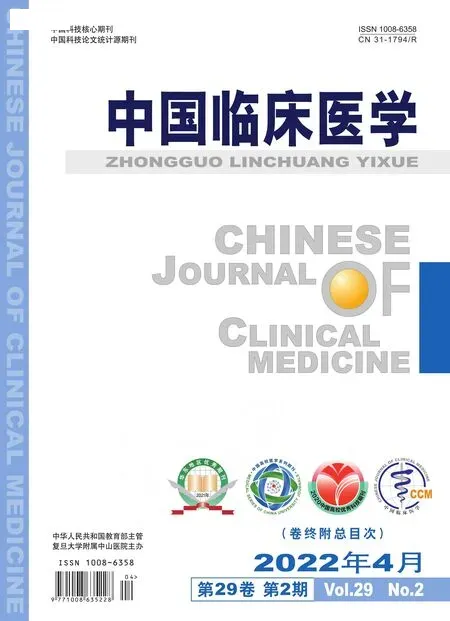药物涂层装置治疗椎动脉起始处狭窄病变的临床疗效分析
王永刚,史振宇,郭大乔,唐 骁,司 逸,郭宝磊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上海 200032
自从Sundt等[1]于1980年报道了第1例椎动脉经皮血管成形术以来,越来越多研究[2]报道了使用球囊血管成形术和(或)支架治疗椎动脉病变。目前研究[3]表明,对于椎动脉起始处狭窄(ostial vertebral artery stenosis,OVAS)伴有椎基底动脉系统症状、无症状双侧椎动脉狭窄大于70%,以及单侧椎动脉狭窄伴有对侧血管发育不良或闭塞的高危患者,可考虑腔内治疗。然而腔内治疗中普通球囊血管成形术(plain old balloon angioplasty,POBA)和(或)裸支架(bare metal stent,BMS)植入术后易发生再狭窄,再狭窄率可高达25%~ 30%[4]。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或药物涂层支架(drug-eluting stent,DES)可释放抗增生及免疫调节药物来防止内膜增生,有效预防再狭窄[5-6],目前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疾病的腔内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7],但是国内缺乏药物涂层装置用于OVAS腔内治疗的报道。基于此,本研究对药物涂层装置治疗的18例OVAS患者进行随访观察,评估药物涂层装置在OVAS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连续收治的18例药物涂层装置治疗OVAS患者。纳入标准: (1)症状性患者,包括眩晕或晕厥、反复发作的后循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或表现为后循环的脑卒中;(2)OVAS的 高危患者[8],如单侧椎动脉狭窄伴对侧血管发育不良或对侧椎动脉闭塞;(3)椎动脉中度及重度狭窄。排除标准:(1)无症状及椎动脉轻度狭窄患者;(2)未进行规律随访及失访患者。本研究得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B2021-063)。
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和(或)颈部血管超声(carotid ultrasound,CUS),必要时通过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确认。根据北美症状性动脉内膜切除协作研究组(the North American Symptomatic Carotid Endarterectomy Trial, NASCET)标准计算椎动脉狭窄程度。轻度狭窄:血管狭窄率<50%;中度狭窄:50%≤血管狭窄 率<70%;重度狭窄:血管狭窄率≥70%[3]。
1.2 手术方法 在复合手术室内,所有患者在局部麻醉下,医师依据股动脉血管条件行股动脉切开或经皮股动脉穿刺,放置5F导管鞘后,常规静脉肝素化(60~100 IU/kg),将7F长鞘通过0.035 inch 导丝推进到锁骨下动脉。在路图(Roadmap)引导下,将0.014 inch的微导丝通过椎动脉狭窄病变进入远端椎动脉。依据病变侧血管条件和解剖学形态,决定是否使用远端栓塞保护装置(embolic protection device,EPD)。在球囊血管成形术和(或)支架植入前,术中DSA结合术前影像学检查选择球囊或支架尺寸(oversize 10%~15%)。新 发 病 变 手 术 方 式:DCB、DCB+BMS、DES。对于椎动脉起始处明显扭曲的OVAS患者在POBA序贯扩张的基础上,单纯使用DCB;对于椎动脉形态好、直径≤4 mm且短病变的患者可使用冠状动脉DES;而对于直径大于4 mm的患者,因目前市场上所能提供的冠状动脉支架直径最大为3.5 mm,因此选择使用DCB+BMS。再狭窄病变手术方式:DCB、DES。术后再次造影测量残余狭窄、明确后循环血流变化以及排除血管破裂、远端栓塞或血管穿孔、穿刺点血肿等不良事件。
1.3 随访方法及终点事件 围手术期技术成功定义为残余狭窄≤30%,无院内卒中或死亡。临床成功定义为技术成功,加上椎基底动脉系统症状消 失[9]。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定义为院内卒中或死亡,血管穿孔、出血、远端栓塞、穿刺点并发症等[9]。患者分别于术后3、6、12个月以及每年进行门诊随访,行CTA、MRA和(或)CUS等无创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行DSA检查。随访过程中血管通畅定义为再狭窄≤50%。随访终点事件:主要终点事件包括死亡和脑卒中;次要终点事件包括支架移位或断裂、再狭窄、再发TIA、眩晕或晕厥等[2,9]。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3.0 处理相关数据。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用%表示,Kaplan-Meier法分析随访期间血管通畅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18例患者(表1),其中新发病变16例、再狭窄病变2例;男性12例(66.7%),女性6例(33.3%);年龄54~84岁,平均(67.5±7.8)岁。其中左侧OVAS患者12例(66.7%)、右 侧OVAS患 者6例(33.3%)。吸烟患者2例(11.1%)、饮酒患者3例(16.7%);冠心病1例(5.6%)、高血压4例(22.2%)、糖尿病2例(11.1%)、高脂血症3例(16.7%)。伴发的主要症状:眩晕或晕厥患者15例(83.3%)、后循环TIA或脑卒中患者3例(16.7%)。一侧椎动脉闭塞患者2例(11.1%),其中1例合并锁骨下动脉病变(5.6%)。合并同侧颈动脉病变2例(11.1%)。中度狭窄病变血管10例(55.6%)、重度狭窄病变血管8例(44.4%)。

表1 OVAS患者基本信息
2.2 围手术期结果 16例新发OVAS患者中,手术方式为DCB的患者6例,5例采用Orchid DCB (Acotec Scientific公司)、1例采用Reewarm DCB(中国 Endovastec公司);手术方式为DES的患者8例,4例患者采用Xience Xpedition DES(美国 Abbott Vascular公司)、3例患者为FireBird2 DES(中国 MicroPort公司)、1例Buma DES(中国 Sinomed公 司);DCB+BMS患 者2例,1例 为Orchid DCB、1例为Reewarm DCB,裸支架均为Herculink Elite支架(美国 Abbott Vascular公司)。
2例OVAS再 狭 窄 患 者,1例 为PALMAZ BLUE支架(美国 Cordis公司)再狭窄,处理方式 为Buma DES;1例为Express SD支 架(美国 Boston Scientific公司)再狭窄,处理方式为Orchid DCB。2例患者使用EPD,其中1例为Emboshield NAV6(美 国 Abbott Vascular公 司)、1例 为Filterwire EZ(美国 Boston Scientific公司)。2例合并同侧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均一期处理,处理方式为颈动脉支架植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1例合并对侧锁骨下动脉狭窄的患者一期处理,处理方式是POBA+BMS。
手术进展顺利,DCB扩张和(或)DES/BMS植入后残余狭窄≤30%,未发生血管破裂、穿孔、远端栓塞和穿刺点血肿等不良事件。围手术期1例患者眩晕症状未得到缓解,1例患者发生小脑卒中。技术成功率为94.4%(17/18),临床成功率88.9%(16/18),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发生率5.6%(1/18,表2)。

表2 药物涂层装置治疗OVAS患者的围手术期结果N=18
2.3 随访及统计学结果 18例患者随访时间3~38个月,平均(15.4±10.9)个月。随访过程中1例眩晕症状患者好转,未作任何处理。1例脑卒中患者予对症支持治疗后好转,未作任何处理。1例新发病变在Orchid DCB扩张后,于术后第3个月发生再狭窄,狭窄程度约50%,因患者无症状,未作处理。随访过程中未发生脑卒中、TIA、出血、死亡等并发症。随访过程中血管通畅率94.4%(17/18,图1A)、不良事件发生率5.6%(1/18,图1B)、二次干预率0。

图1 患者随访结果A:所有患者随访期血管通畅情况;B:所有患者随访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3 讨论
临床上约80%的脑卒中是缺血性的,20%~ 25%的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在后循环中。10%~20%的椎动脉狭窄(vertebral artery stenosis,VAS)患者会发生脑卒中。因VAS(狭窄程度大于50%)引起的TIA 5年内脑卒中复发的风险为30%。VAS患者发生卒中或死亡的风险是非VAS患者的6 倍[10]。其中,OVAS是VAS最常见的病变部位[8]。
目前对OVAS治疗方式尚存在争议,但对于OVAS高危患者可以考虑腔内治疗,然而POBA和(或)BMS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为再狭窄。再狭窄主要是因血腔内治疗会导致血管壁损伤,平滑肌细胞增生,导致新血管增生进而导致血管狭窄。而使用DCB/DES可释放抗增生及免疫调节药物来防止新内膜增生,预防再狭窄[11-13]。目前,国内尚未见OVAS使用药涂装置治疗的报道,在国外一项关于椎动脉DCB的研究[14]中,12例患者中位随访期6.1个月,均未发生再狭窄。相较于BMS,DES有更低的再狭窄率,再狭窄率分别为4.5%(DES)和19.1%(BMS)[15]、4.7%(DES) 和11.6%(BMS)[16]。本研究也表明,采用药物涂层装置治疗OVAS患者(无论对于新发病变还是再狭窄病变)安全有效。
本研究入组18例患者均为OVAS的高危患者,技术成功率为94.4%(17/18)、临床成功率88.9%(16/18)、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发生率5.6%(1/18)。围手术期仅1例患者发生小脑卒中,随访过程中症状消失。与既往椎动脉支架研究[13]报道的0~5%相似,也从一方面说明,腔内治疗对OVAS是安全有效的。随访过程中血管通畅率94.4%(17/18)、不良事件发生率5.6%(1/18)、二次干预率为0。再狭窄率和再干预率明显好于同时期使用普通BMS治疗的患者,说明药物涂层装置的使用确实有助于防治OVAS腔内治疗后的再狭窄。
本研究中16例新发OVAS病变中,6例患者使用DCB,8例患者使用DES,2例患者使用DCB+BMS。对于不同药物涂层装置的选择,研究[17]表明,DCB在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diseases,ICAD)疗效确切,甚至鼓励在颅外血管中也使用DCB。
笔者依据有限使用经验认为,相较于DES,对于OVAS病 变,DES和DCB各 有 利 弊。DCB柔 顺性更好,特别是对于明显扭曲OVAS病变,操作更加灵活。使用DCB治疗后的血管内没有残留的异物,减少由于锁骨下动脉与椎动脉解剖关系,造成的支架断裂等。此外,DCB患者不需要延长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DAPT)的持续时间,而DES患者的DAPT持续时间建议为3~6个月。在使用较短DAPT持续时间(1~3个月)的DCB研究[18]中,与观察到的较长DAPT持续时间相比,主要心脏不良事件无显著增加。但是,DCB使用的主要缺点在于对于OVAS病变缺少支撑,即刻的残余狭窄和迟发性的弹性回缩更明显。而本组单纯使用DCB患者中,存在1例在随访过程中出现弹性回缩,反映了DCB在这一方面的不足。释放时后定位更准确的自膨式DES可能是今后的一种选择。
本研究入组2例支架内再狭窄患者,其中1例 为BMS术 后 植 入DES,1例 为BMS术 后 应用DCB。随访均未发生不良事件,但对于已发生的OVAS再狭窄患者药物涂层装置是一种选择。本研究中2例患者使用EPD来防止栓塞事件,对于EPD的使用目前尚存在争议,有研究[13]表明额外的操作可能导致更高的并发症发生率。但是对于治疗侧椎动脉接近闭塞(斑块负荷量大)或完全闭塞、对侧椎动脉闭塞、病变侧椎动脉直径在 3 mm以上的患者可使用EPD来防止栓塞,同时要注意治疗侧椎动脉起始处扭曲不明显,保护伞易于释放及回收。
综上所述,药物涂层装置在OVAS患者中应用再狭窄率低、安全有效。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