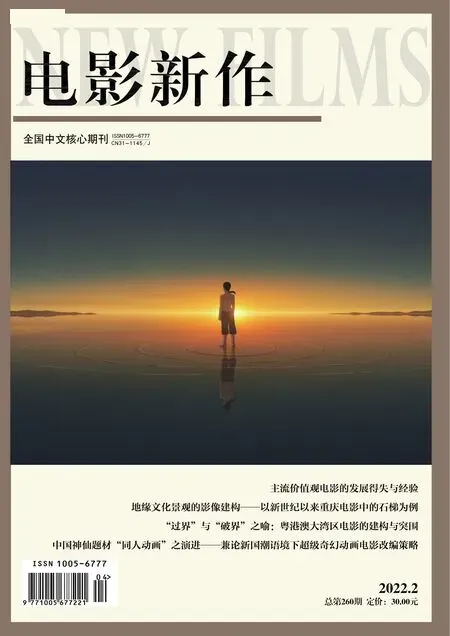《爱情神话》:主流文化内部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再生产
王华杰 赵新彤
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真实事件或流行现象中提炼出来的人物,《爱情神话》中所塑造的诸多角色,具有我国中产阶层的高度概括性,皆在其所处的生活环境、阶层环境、种族环境、家庭环境、性别环境等极具真实感、即视感的语境中,通过一些典型事迹获得了典型人物意义的表征。这些表征既是本片诸多啼笑皆非的事件能引发观众共鸣的原因,又是影像所呈现的主流文化内部暂时未能和解的阶级、身份和性别话语的再生产。该片以实现财富自由的离异中年男女为主要言说对象,通过他们日常生活里的嬉笑怒骂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诸多生存困境。
一、主流话语的边缘与阶层环境
当下大部分的小成本喜剧常选取小人物作为主要的叙事主体,围绕家庭、爱情、伦理、梦想等主题,通过讲述个性鲜明的小人物被无奈所裹挟的命运、角色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或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碰撞等营造戏剧冲突,在角色揭露和反叛一切假、恶、丑或权、贵、腕之后,最终在想象式的和解中化解了冲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喜剧采取了让小人物于命运的反复受挫中逐渐成长的叙事模式,在《煎饼侠》《羞羞的铁拳》等影片中也多有呈现。可惜的是,这些电影虽然笑料十足,但其喜剧效果很大程度上往往并不直接来源于这些戏剧冲突,而是源于其夸张的表演、游戏化的视听语言、小品式的段子等调侃意味十足的桥段的拼凑,从而给观众带来闹剧式的狂欢体验。这样的喜剧段落虽然迎合了绝大部分观众的消费品位,但其跳脱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语境,不仅弱化了情节,也忽视了角色的功能和任务,甚至还梦幻式地消解了影像序列所建构的文化冲突,使影片陷入了消解一切意义与价值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而以上提及的一些窘境皆在《爱情神话》影像文本内外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一方面,作为一部笑料十足的喜剧,该片的喜剧效果直接来源于剧作的戏剧冲突,结构在影像的叙事、视听和文本之内;另一方面,该片在角色定位方面反而以一些小资市民为中心,通过他们的日常点滴,讲述了有一定物质基础但非偶像化的人设基于“面包”之上的困境。

图1.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不论是角色的语言、职业身份、生活细节,还是角色生活的都市空间,都透露出了小资色彩和精英趣味。当然这并非一部美化和宣传中产阶层无忧生活或是旨在刻画消费景观和享乐主义的电影,相反《爱情神话》中角色的都市生活多少带着普通人的苦涩。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和他们所代表的强势文化在这部电影中实际上处处遭到了消解和祛魅。电影中,老乌是一位典型的“海归”。中文、英语、法语的运用上,他切换自如。他对李小姐的自我介绍是:“法国公司中国总代理,中欧贸易代表”。他的身上始终有某种优越感。尤其是,他反复提及的与索菲亚·罗兰的扑朔迷离的异国情缘等,生动地刻画了一位生活在“上只角”的老上海人价值取向。但就是这么一位精英人士却因为停自行车的问题与城管起了争执。老乌和城管分别操着上海话和外地方言产生了争论。耐不住城管的严苛,老乌只能另寻他处停车。最后,老乌只得无奈地说道:“这个地方越来越不好玩了,越来越没人情味了,为啥找这种吹毛求疵的人来管理这里,我们变成客人他们变成主人了。”虽然看似是一段调侃,但却也是一部分老上海人的真实写照。随着都市现代化的深入,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观念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冲击,应对城市生活的精神力量已然开始衰退。“事实上,大城市的普通市民,其生活仍旧是艰辛的,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并不亚于乡村、小城居民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同时,一个家庭的进城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创业者到后来的继承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个家庭才能在城市中真正获得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基础和从容应对城市生活的精神力量。”因此,相对于外来者,老乌作为老一辈上海人的代表,作为一个活在过去和回忆里的人,这种被边缘化的过程无疑使他更加深刻地体认到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对中产阶级的困境描摹实际上于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物质条件充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对大批的观众来说是陌生且空虚的。即使没有外在物质力量的威胁,人类仍然可能受困于来自其他方面的痛苦,导演恰以此为出发点,削弱了某一群体的“崇高性”和“优越感”。从老乌的角色塑造上,我们看到主流话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被时代、制度、文明等不断边缘、更迭、取代的话语。现在的边缘是曾经的主流,而现在的主流未必不会是将来的边缘。恰如老乌那辆再无法通过“人情”“关系”停靠的自行车。老乌因谣传的索菲亚·罗兰的死讯而伤心过度,醉酒后去世。他带着那段与索菲亚·罗兰感人肺腑的美好爱情离开了。导演最后并没有向观众解答老乌这段感情纠葛是否真实发生过。无论影片结尾出现的房产公司代理背后的人是索菲亚·罗兰,还是某位欧洲富豪女人,都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们都未能再见一面。命运的荒诞之处正在于它不随人的意志所转移。老乌代表了那些孤独的现代人、拥有优渥的物质生活,追求浪漫的爱情但又反困于其中。影片通过对老乌的刻画,向观众传达和展现了老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浪漫但又悬浮的爱情观念,与李小姐母亲满口“房子”和“钞票”的台词传达出的市侩又现实的爱情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

图2.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二、混杂的多重身份与家庭环境
无论是混血的玛雅、外裔亚历山大还是会多种语言的老乌、李小姐,《爱情神话》所刻画的人物的语言、身份和文化都极具混杂性。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第一次将“混杂性”引入了文化研究当中,而这里的混杂性指的是指,“不同的文化在接触时,并不是完全的分离,而是一种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这种碰撞和影响造就了文化上的混杂化”。巴巴阐释了文化混杂化的过程,并指出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会出现一个间隙性空间,不同的文化在这个空间中不断交流与互动,文化在这里被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意义,因此也被称作“混杂空间”和“第三空间”。这一空间产生于矛盾和含混的中间地带,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情况,表现出更为广泛的包容性,跨文化交流在这一空间中得以实现。无疑,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国际交流最频繁的大都市之一,成为这种“第三空间”想象和写作的最佳场所。现代性的、跨国性的身份认同成为《爱情神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为“第三空间”的夹缝生存者,电影中玛雅的身份认同困境尤为非常典型,而这个困境既来源于她的国籍,又来源于她的家庭。就国籍来看,她既作为本民族内的他者,也作为民族内的他者,具有双重的身份,被双方双向视为“异类”。而这种双重的身份不仅使她被本民族和本地人所指认,更被她自身更深刻地体认,并使得她具有某种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又不得不接受游离性和无根性。比如白老师在咖啡厅问玛雅说:“你什么时候回英国?”,玛雅较真地回道:“不是送,是回,因为我是英国人。”白老师顺着玛雅的话又问道:“那你妈妈跟你一起回英国吗?”玛雅认真地纠正了白老师:“她不是回,她是去,因为她是中国人。”在玛雅与白老师你来我往之间,一个机灵、有主见、又有些话痨的小姑娘跃然银幕。更重要的是,导演表现出了一个混血的小孩子对自己双重身份的体认。尤其是,在父母离婚的情况之下,这种体认似乎被玛雅洞察得更为透彻,而这恰是作为局外者的本地人所不能深入理解和感受的。再就家庭来看,一旦父母组成新的家庭,她又将成为父母两个家庭内部的“他者”。如果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双重身份,那么她将具有三重乃至四重的身份。几种身份便意味着要遭遇几种与原初环境中主体性力量的冲突和碰撞,而这几种身份都集中或即将集中在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身上。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些身份的杂糅,这对玛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比如,电影中的玛雅英语不好这一问题,既遭到了李小姐的训斥,又被白老师当作话柄揭短。如果玛雅去了英国,那么她的主体性又将遭遇困境。可以说,这是玛雅又一次新的危机写照。在家与国之间,身份的混杂性及异国父母离婚所导致的角色外在的流动性和迁移性问题,实际上是要求角色对几种混杂的文化实现内在的转换和整合。于是,玛雅便出现了“我是谁”“她/他是谁”“你是谁”等身份割裂的症候。事实上,语言的问题只是一个表象,而身份认同的困境才是玛雅所真正要考虑的。故而,“她生活在中国,国籍却是英国。”“她的国籍是英国,但是她英语又不好”等“问题”才会成为一个问题。紧接着,当白老师问玛雅喜不喜欢英国的时候,玛雅一改之前的倔犟,灰心丧气地说道她并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她爸爸。可见,拧巴、矛盾而又含混的心态流露在玛雅的言辞之间,而这正源于她身份的混杂性。
不仅如此,经由玛雅的折射,我们看到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个显著问题,即国家离婚率的上升。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会,离异问题尤为突出。正如社会学学者李银河曾在一档节目中所提到的“婚姻制度终将消亡”的预言,这一预言或并非悬停在电影中的某种人物设定,而似乎正在成为当下的一种流行现象的真实写照。因此,《爱情神话》所讨论的既是现代爱情的神话,实际上也是现代人稳固家庭再建的神话,而父母离异导致的家庭割裂及对后代所造成的难言之隐,亦借此被导演搬上了银幕。
三、女性话语的崛起与性别环境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男性学者,对社会领域进行区分的时候将其分为公领域和私领域,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机制也正建立在公领域,而这个公领域就是市场。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在市场之外还有两个领域:家庭和自然。工业革命以前,脑力劳动一般无法取代体力劳动的情况下,男性由于体能优势可以进入公共领域为市场提供劳动力,而女性只能作为劳动力和人的再生产工具待在私人领域,比如在家里生儿育女、照顾老人、伺候丈夫。因此,在过去的生产领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更是对女性物质基础和生产资料的统治,故而当时的社会权力亦由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中产男性、中年男性所掌握。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家庭经济被大工业机器所瓦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愿意向女性开放,工人开始以个体身份不分性别地进入劳动市场,社会劳动力被大量女性所填充。女性从家庭妇女向职业女性进行转换也意味着现代女性将会拥有更多的经济独立的机会。经济的独立必然会促使女性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于是一些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也应运而生。而《爱情神话》恰以这些经济独立的都市新女性为原型进行了呈现,并质询了一些女性问题。
作为新兴崛起的年轻男性代表,走中性风的白鸽与电影中女性和父亲的关系便十分典型。儿子这一身份曾经作为家庭生产力、家族父权遗传和迭代的重要媒介和符号,且由于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思想曾是儒家父权主义对后代进行精神统治和人格规训的重要意识形态和文化烙印,男孩子从小就被要求要有阳刚之气。但是,《爱情神话》中“妈宝”且中性化倾向明显的白鸽显然颠覆了这种现象。譬如,电影中白老师在奶茶店前面问儿子:“你是不是拔眉毛了?”儿子说:“拔了点野眉毛。”白老师说:“眉毛还分家养的野生的,人家小姑娘都没有拔眉毛。”实际上,这一段落不仅制造了一段笑料,也表现了现代青年男性和传统中年男性之间对两性思想、气质和性别表达的割裂。并且,这一矛盾也在电影末尾白鸽向几个阿姨传授保养秘诀时进一步深化。由于迫于几个女人对白鸽的袒护,老白只能选择骂骂咧咧地走开。这一场景不仅表现了父子两代人对男性气概认知的偏差,更集体性地、仪式性地展现了这三位中年女性对老白燃起的男性权威和家长气概的围攻、讨伐和不屑。
如果就电影中人物的职业和分工来进一步透视影像系统中的男女性别话语权力的话,那么它的背后就是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爱情神话》中,李小姐在广告公司担任制片,格洛瑞亚开场说自己有钱有闲。与之相反,白老师却在家当房东、开画室,磨练厨艺,闲暇之余还帮李小姐带孩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白这个中年男性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即她们都想找老白这样一个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能提供支持的伴侣。或者说,随着女性进入并深入公共生产领域,她们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随后,她们所渴望的、欢迎的男性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反而把白老师这样愿意居家的男性当做一种稀缺的再生产工具,进行了同性之间的互相竞争和资源掠夺。不容忽视的是,在《爱情神话》中,除了老去和年纪尚轻而没有劳动力的女性,其余的青年和中年女性都在为社会提供劳动力。藉此,随着女性对生产资料的逐渐占有和改造,家庭经济已不再被男性所垄断,继而影片中白老师对白鸽合法地进行规训和惩戒的地位已非不可取代,而这也导致我们曾经被前人暴力地、强加地、先验地决定的社会角色范式,或曰我们曾经被社会的性别结构所切割成的男性与女性的边界愈发模糊,这是影片鲜明展现的一幅男主内、女主外的社会图景。因此,男性曾经所幻想的、凝视的恋爱对象在这部电影中只能是一出“神话”,而女性则正在为自己的爱情创造“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不论是格罗瑞亚给白老师花钱,还是蓓蓓理直气壮地“出轨”,笔者在男性去中心化的过程中,发现男性权力的让渡并没有改变影像社会中由资本所掌控的运行规律和逻辑。只不过,曾经是男性消费女性,而现在是女性消费男性,且依然是集体消费之下对流行的性别气质的再定义。在格罗瑞亚和蓓蓓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有关性别和解的可能性,而唯有拒绝消费与被消费的李小姐(给鞋子不要,给房子不住)和白老师(拒绝出轨,拒绝收画钱)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以上种种作为现实的“互文”,或许不失为导演对当下男女去性别化的、去消费观的、非物化的、以人为中心的、相互尊重的目光审视。
结语
“喜剧电影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笑料以引起观众的喜悦和笑为根本目的地影片。”但有深度的喜剧往往悲喜交织且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在笑声之外能让我们体会到复杂的社会内涵和丰富的审美意蕴。正如郑正秋当年提出的“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爱情神话》虽然是一部喜剧,但并不是作为观众片刻的心理逃避空间,完全沦陷在功利的消费逻辑之中;实际上,该片藉由中产阶层的现实困境,展现了我国另一处谐趣的社会风情。此外,在诸多笑料之外,影片还存在着丰富的所指。“也就是说,文本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可能是这种社会情境的一种建构性的介入力量,至少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事实上,“楚门的世界” 早已不是预言,不论是电影中的角色被边缘的议题、多重的身份或是被女性重新定义的性别话语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味。因此,经过喜剧化的处理,电影中呈现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往往会被我们一笑而过。或许正是这种一笑而过的“小波澜”,更值得我们去细细揣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2.
2王建光.社会转型中失意者的精神症候——对贾樟柯电影的一种社会心理分析[J].文艺争鸣,2015(03):153-156.
3David Huddart.HomiK.Bhabha[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7.
4[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邹韵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5.
5聂欣如.类型电影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44.
6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0.
—— 玛雅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