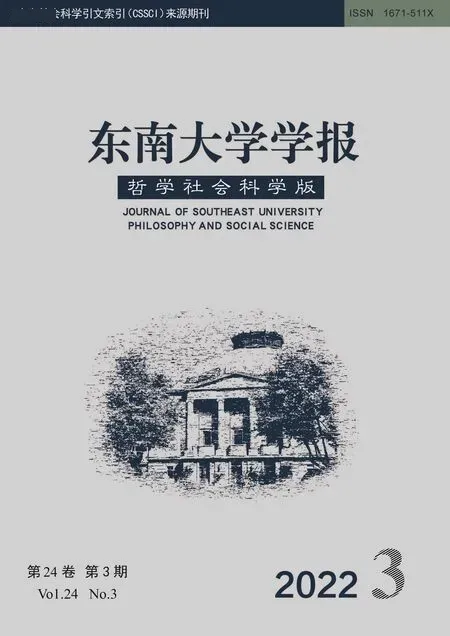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之维
马 勤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司法改革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哪项制度像认罪认罚从宽一样引发如此之多的变动。有些改变相当直观,比如认罪具结、程序简化;另外有些改变则相对隐蔽,并非一眼就能发现,比如律师辩护、公正审判等权利保障机制逐渐被架空。从2016年试点启动,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到2019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六年间基本建成。据最高检工作报告统计,2021年全国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率已超过85%(1)参见《张军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检察日报》2022年3月9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办案“重器”。学界对该制度的讨论内容颇丰,对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亦有探讨,但是,较缺乏从权利视角对该制度的体系考察。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传统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理念带来了重大冲击,为促进制度完善以期行稳致远,有必要从权利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系统性审视。
二、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新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然成为我国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及功能因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刑事程序的重心转移到侦查起诉阶段,刑事被追诉人的抗辩权、对质权、律师辩护权、公正审判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法院庭审程序中的证据调查、事实认定等核心功能趋于弱化。因此,在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下,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面临重新定位。
第一,人权保障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张力,权力主导型制度容易遮蔽权利保障的重要性。该制度确立之初,学者对其基础理论进行了激烈探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制度本质,有学者认为这项制度是“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2)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实质及其实现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另有学者则主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回归权利(3)闵春雷:《回归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法学杂志》2019年第12期。。二是关于制度目标,有观点认为追求效率是制度实质,有学者主张公正基础上的效率观(4)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另有学者则认为效率优先是一种误区(5)参见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以程序公正为基本要求(6)参见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三是认罪认罚从宽与速裁程序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程序简化是“认罚”的内容(7)参见孙长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另有观点主张程序简化是“从宽”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速裁程序是程序性的认罪答辩(8)参见施鹏鹏《认罪认罚从宽的类型化与制度体系的再梳理》,《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随着制度全面推行,权力主导、效率提升、程序从宽的现实使部分理论争议尘埃落定,但有些争议仍悬而未决。上述理论分歧的背后,权力视角与权利视角的差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主导的制度现实可能面临权力失序风险(9)参见闫召华《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正因如此,重新定位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权利放弃激励说”这一权利视角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础,有助于重新定位人权保障机制。有关该制度理论基础的争议主要形成了“权力说”“权利说”“人身危险性降低说”“司法资源节约说”“权利需求模式”等多种观点。“权力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基础是司法公权力,主要目标是提升诉讼效率。目前而言,制度运行确实形成了权力主导的局面。不过,“权力说”容易导向效率优先,难以充分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可能使制度潜藏弊端。相反,“权利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本质上是为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应当在正当程序基础上提升效率。“权利说”中有一种激进观点是“权利放弃对价说”,主张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被追诉人承诺放弃部分权利,国家因此节约了诉讼资源,故予以从宽(10)参见赵恒《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对价说”基于辩诉交易理论,忽略了我国职权主义制度背景,难以形成有效的“讨价还价”机制,与我国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不相容(11)参见亢晶晶《认罪认罚从宽模式的转型——以从宽的正当性根据为切入点》,《人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
关于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探讨还存在“权力治理模式”与“权利需求模式”之争,有学者指出后者更加契合司法改革的本质目标(12)参见卞建林、谢澍《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以中德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为线索》,《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所谓“权利需求模式”,指的是这一制度是以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需求为起点而建构的,强调权利保障的面向,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可以得到明确与尊重,有助于增强制度的认同感,激发制度的内生动力。该观点具有一定理论说服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推行并未将“从宽”视为被追诉人的权利,而是将其视为公权机关裁量判断的“权力”。因此,为凸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放弃权利行为的法律意涵,本文提出权利放弃激励说。
所谓“权利放弃激励说”或“权利放弃补偿说”,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权利保障,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具有补偿性质的一种制度激励,为了“邀请”刑事被追诉人放弃对抗、积极悔罪、退赃退赔等。被追诉人是出于悔过或出于利益衡量,无论何种原因而自愿认罪认罚,即放弃对质权、抗辩权等诉讼权利,就可以获得从宽处理,从宽是对弃权行为的一种激励性补偿,而非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对价。因为讨价还价的前提是双方力量大致均衡,控辩平等的理念和制度相对完善,这两点都不甚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换言之,权利放弃激励说是对“权力对价说”和“社会危险性降低说”的一种融合:一方面,在功能意义上,认可被告人权利放弃应当获得相应补偿;另一方面,在规范意义上,刑罚的施行不能被用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弃权激励的从宽显示的是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改造难度等恢复性司法理念。正是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兑现法律预先允诺的弃权之激励,方能强化司法公权力的责任意识,注重办案质量,以避免在权力主导模式下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的轻视甚至是无视。
第三,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之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心应当定位在侦查起诉阶段。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重心前移到侦查与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相对虚置,人权保障的重心亦应当前移。2022年3月,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专访中提出,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三年以来,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已稳定保持在85%以上;2021年全国已办结刑事案件中,有89.4%的人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比达32.8%,诉讼效率提升显著,但适用过程中地方出现一些片面追求高适用率导致部分案件质量不高的问题(13)沙雪良:《认罪认罚成办案“重器”,精准高效适用待“打磨”》,《新京报》2022年3月10日第A08版。。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制主要体现为赋予被告人一系列基本权利:不受任意逮捕、拘禁,不受任意搜查、扣押,公正、公开审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对质权等(14)参见易延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然而,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放弃了绝大部分诉讼权利,尤其是缺乏有效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无法运用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诉讼权利。因此,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研究重点,应当转向完善侦查起诉阶段尤其是认罪认罚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
三、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要素
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要素,有助于推动制度的规范运行。刑事被追诉人对自身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具有基本处分自由,既包括主张权利的自由,也包括放弃权利的自由,认罪认罚本质就是一种弃权自由的行为表现。简言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被追诉人对部分或全部抗辩权等实体性诉讼权利的放弃;而“速裁程序”的本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
(一)“弃权自由”的权利基础、制度动因与底线
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追诉人一系列基本诉讼权利,包括沉默权、辩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公正审判权、迅速审判权、公开审判权、对质权、质证权、特免权、上诉权等等。这些权利中的绝大多数内容,被追诉人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这一理念被称为“推定弃权自由原则”(Presumption of Waivability)(15)See to United States v. Mezzanatto, 513U.S. 196, 202 (1995).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贯认可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可以自由放弃的,这一理念被称为“推定弃权自由原则(Presumption of Waivability)”。。从理论基础来看,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这些权利是为了对抗和制约政府公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侵害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无疑,这一系列对抗性权利增加了案件侦查、审判和定罪难度,影响了刑事司法效率。因此,各国法律或司法机关往往出于种种目的来鼓励、激励被追诉人放弃一些对抗性权利。2017年“公正审判”国际组织的一项研究考察了世界范围内“放弃审判制度”等激励性合作式诉讼程序,明确了被追诉人为获得从轻处罚而认罪并放弃审判权是其制度核心(16)See to Fair Trials, The Disappearing Trial: Towards a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Trial Waiver Systems (2017-04-27)[2022-03-01],https://www.fairtrials.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Report-The-Disappearing-Trial.pdf.。
为了提高定罪率和诉讼效率,辩诉交易制度应运而生,它是催生刑事被追诉人弃权的典型代表(17)See Michael E. Tigar, “Foreword: Waiver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Disquiet in the Citadel”, Harvard Law Review, 1970, 84(1), p.1-28.。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被追诉人通过放弃一些诉讼权利可以换取减少起诉罪数、改变罪名、降低量刑等从轻处理,但控方要求被告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很广泛,除了常见的沉默权、抗辩权、陪审团审判权之外,还包括上诉权等重要救济性权利(18)比如,美国绝大多数法院包括所有联邦上诉法院都允许被告人放弃上诉权,只要其弃权行为是明知且自愿的。。这些几乎不受限制的弃权协商,可能造成被告人基本权益保障不足,加之控辩力量悬殊而导致被告人的认罪并非明知且自愿,容易引发虚假认罪,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引发诸多批评(19)See to Daniel P. Blank, “Plea Bargain Waivers Reconsidered: A Legal Pragmatist’s Guide to Loss, Abandonment, and Alienation”,Fordham Law Review, 2000, 68(6), p. 2011; Jane Campbell Moriarty, Marisa Main, “Waiving Goodbye to Right:Plea Bargaining and the Defense Dilemma of Competent Representation”,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2011,38(4), p. 1029.。
鉴此,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并规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和上诉权,这些法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为被告人的基本权益提供了底线保障(2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但是,究其实质,无论是在辩诉交易之下,还是在认罪认罚制度之下,刑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行为的法律实质都是对其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的放弃。
(二)“认罪认罚”本质上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等部分或全部抗辩权
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章基本原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2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十五条。。这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表达,刑事被追诉人通过认罪认罚而放弃依法享有的以抗辩权为核心的部分或者全部实体性诉讼权利,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正如“坦白”的实质是放弃沉默权,“认罪认罚”的本质则是放弃包括沉默权在内的一项或多项实体性诉讼权利。这条规定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在被追诉人的权利基础之上。认罪认罚从宽不仅延续了坦白从宽的法理基础,而且扩展了这一理念,使其内容趋于完整。
1.沉默权奠定了坦白从宽的理论基础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最重要的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基本原则,正式开启司法理念从偏重犯罪控制到正当程序的转向(2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一条。。其中,第五十条新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标志着法律明文确立了沉默权(2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五十条。。有学者主张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或者说是只确立了部分沉默权(24)参见陈瑞华《天下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424页。。这种否认沉默权的解释方法会造成法律条文内部的自相矛盾,其实源于对法律条文的误读。
沉默权的确立为“坦白从宽”的法律规定奠定了理论基础。沉默权与辩护权本质上是同一个权利即刑事被追诉人所享有的抗辩权的一体两面,因为权利行使方式不同而表现为消极抵抗与积极对抗,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仅允许积极抗辩而不保护消极抗辩,法律强迫被告人自己做证反对自己,实际上是架空了抗辩权。如果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自身就负有必须回答且如实供述的义务,那么坦白只不过是履行法律义务的应有之义,不值得获取激励或奖励。相反,不坦白就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甚至应该予以惩罚。如此一来,坦白“从宽”的法律基础就丧失了。唯有当法律保护沉默权的时候,被告人坦白自己罪行是放弃了自身享有的沉默权,法律才应当给予其从宽作为激励或补偿。否则,被告人就有可能沉默到底,缺乏动力去坦白。究其根源,“坦白从宽”在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中才能找到法理依据,这也是此次修法在引入坦白从宽的同时确立沉默权的法理逻辑。
2.“如实供述”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认罪”的法律表达,实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即“自首”或“坦白”。据1997年《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2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第六十七条。。此后,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这里如实供述的是自己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2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第六十七条。。2012年刑诉法通过修改第一百一十八条以便与刑法的坦白从宽进行衔接(2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五十条。。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时保留了如实供述的相关规定(2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之后,如实供述的罪行是尚未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即是自首;如果是已经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即是坦白。换言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自首和坦白的本质并无不同,都是对沉默权的放弃,不过二者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异。自首所供述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尚未开展刑事追究,针对该罪行的沉默权尚未被激活,主动供述相当于提前放弃了沉默权。因此,自首在主观上悔罪态度更好,在客观上更有助于侦查犯罪。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认罪认罚与旧有自首、坦白既存在交叉又存在区别,但都尚未明确具体如何区分(29)参见赵恒《“认罪认罚从宽”内涵再辨析》,《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事实上,从放弃沉默权的思路出发,结合法律条文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既可能构成自首,也可能构成坦白。
3.“承认指控”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事实层面上的抗辩权
“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意味着被追诉人放弃事实层面上的抗辩权,即“认罪”。从法律条文的表述来源看,最为接近的表达出现在2003年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后首次进入法律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中关于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第二项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3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二百零八条。这里,适用条件并不要求被告人必须以“如实供述”的自首或坦白情形为前提,只要被告人在事实问题上不表达异议,不进行抗辩,就构成“认罪”,从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被告人认罪的实质是放弃了关于指控事实的抗辩权,在法律层面的效果是案件事实争议不大了,因此适用简易程序也不致损害审判公正。由此可见,认罪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并非必须依附前一个要件的自首或坦白。同样,自首和坦白也不必然包含认罪。2018年刑诉法延续这一表述并进行了精简压缩。有论者提出,认罪必须包含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作为实质要件,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两个要件的本质差异,忽略了认罪具有独立评价的空间(31)参见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从放弃权利的视角来看,自首或坦白是对沉默权的放弃,认罪是对事实问题抗辩权的放弃;前两者放弃消极对抗的权利,后者放弃的则是积极对抗的权利。
若要放弃消极沉默的权利,必须有所作为,因此如实供述在证据意义上形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若放弃积极抗辩的权利,可以消极无为,只要不发表异议就够了,不必详细供述,简单地一句“我认罪”就已足够。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量刑意见》)将当庭自愿认罪作为独立的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只不过单独当庭认罪的法律评价低于自首或坦白,从轻的幅度也更低(3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2013)。。此外,该意见还存在一个误区,法律规定已经依法认定自首或坦白的就不再适用当庭认罪从轻,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重复评价,但其实是没有认识到认罪行为所具有的独立法律意义,模糊了认罪具体内容和表现方式的多元化特点。
4.“接受处罚”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
“愿意接受处罚”的实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在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即“认罚”。如果说第一个要件“如实供述”关注的是被追诉人所带来的证据效果,第二个要件“认罪”关注的是定罪效果,第三个要件“认罚”关注的则是罪名和量刑的效果。认罚的表述在2018年首次进入刑诉法,为控辩之间的量刑协商开辟了法律空间(33)参见胡铭《认罪协商程序:模式、问题与底线》,《法学》2017年第1期。。此前,量刑通常由控方提出建议,辩方可以提出异议,最终由法院依法判决。法律之前并不考虑被告人是否愿意接受量刑建议,通常辩方都不愿意接受,会想方设法进行辩解。为了让被告人愿意接受,控辩之间就需要沟通,这事实上将庭审中的量刑争议转变成了庭外的控辩协商。但也不排除一些情况下,被告人因为无可奈可、无从辩驳或真心悔罪而愿意接受处罚。总之,认罚实质上放弃了对量刑问题的法庭抗辩,亦即被告人放弃了在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
综上,“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三个条件性要件各自具有独立法律意义,满足其中任何一个、两个、三个要件都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只不过从宽的幅度存在差异。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是捆绑在一起的,还有学者认为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二者捆绑在一起,但是在实践中有所分离,这些观点都存在一定误解(34)参见樊崇义、李思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前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有学者认识到了认罪与认罚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意义(35)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但都尚未明确三个条件式要件之间的关系。三者并非缺一不可,或存在包含或捆绑关系,三者之间并非“串联”而是“并联”关系。如果说“如实供述”是放弃沉默权而愿意做证反对自己,作出自白或有罪供述(confession),那么“认罪”只是一种对指控在定罪或法律问题的承认,没有异议,放弃辩驳,不包含自白或积极证实自己有罪,本质上更接近于辩诉交易中的“单纯放弃抗辩协议(nolo contendere plea)”,“认罚”行为本身更接近于辩诉交易的“单纯接受处罚协议(Alford plea)”(36)应当指出二者在弃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层面具有相似性,其在各自制度中的法律效果等方面仍有很大差异。美国辩诉交易之下,控辩除了可以签订“认罪协议”(guilty plea),被告人还存在其他两种选择,比如选择“单纯放弃抗辩协议”(nolo contendere plea),被告人可以对自己是否有罪保持缄默,只是对检方指控不予抗辩,刑事案件可以根据该协议定罪,但本案不得用于在民事案件中反对被告人;再如可以选择“单纯接受处罚协议”(Alford plea),被告人可以主张自己无罪,但是愿意接受法律处罚。See to Curtis J. Shipley, “The Alford Plea: A Necessary But Unpredictable Tool for the Criminal Defendant”, Iowa Law Review, 1987, 72(4), p. 1063; Jenny Elayne Ronis, “The Pragmatic Plea: Expanding Use of the Alford Plea to Promote Traditionally Conflicting Interest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emple Law Review, 2020, 82(5), p. 1389.。有学者主张,虽然传统上经常将辩诉交易中的认罪协议与自白等同视之,甚至认为认罪包含供述,但事实上大部分辩诉交易中的认罪并不包含被告人对事实的详细供述或承认,也不必包含被告人供述(37)Brandon L.Garrett, “Why Plea Bargains Are Not Confessions”,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2016, 57(4), p. 1415.。
从法律规则的内容结构来看,之所以存在“如实供述”“认罪”“认罚”这三种要件的区分,是因为刑事被追诉人的抗辩权的内涵具有多样性:在实现形式上可以分为积极或消极,在内容上可以针对事实或法律、定罪或量刑问题等。因此,被告人放弃沉默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抗辩权;即使放弃在事实或定罪问题上的抗辩,也不意味着放弃了在法律或量刑问题上的抗辩权。这解释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多样现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如实供述但不认罪,比如主张是正当防卫;可能认罪但不认罚,比如认为量刑畸重;甚至可能不认罪但认罚,比如认为自己无罪,但表示愿意接受处罚等等。
(三)“速裁程序”的本质是被追诉人放弃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
速裁程序是从2012年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进一步简化而成,属于程序从简内容。从法律规定来看,速裁程序的本质是被追诉人自愿选择放弃了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包括公正审判权、对质权等普通程序中的诉讼权利。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有关规定虽然同时进入《刑事诉讼法》,但是二者并非一体两面,而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功能,后者在适用条件上部分依赖于前者,但前者并不依赖于后者。
1.“被告人认罪”是速裁程序得以“从速”的现实要件
《刑事诉讼法》规定速裁程序适用条件包括:一是案件类型,即“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二是证据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即被告人放弃了包含沉默权在内的抗辩权,不仅对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承认罪行,是对关键实体性诉讼权利的放弃;四是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即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这一程序性权利(3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二百二十二条。。
被告人认罪,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是程序在实践层面得以简化的必要基础。若根据1996年简易程序的适用规定,很可能导致简易程序既不简单也不容易的局面。因为被告人虽然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发言权,或者被告人即使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若不承认犯罪,必然会积极抗辩,可能会在庭审中不停发表异议,那么法庭调查很难真正简化。应当注意的是,程序简化和实体从宽都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要件,但是,认罪并不必然导向程序的简化,因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39)参见顾永忠《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此外,认罪也不一定导致从宽处理,因为坦白从宽是酌定量刑情节,法官仍享有最终裁量权。
2.“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实质是放弃普通程序中的程序性诉权
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是程序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简化的必要基础。刑事被追诉人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中最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就是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而普通程序等庭审通常被认为能够更好地发现事实,是维护公正审判权的基本性条件(40)See to JagoRussell,Nancy Hollander, “The Disappearing Trial-The Global Spread of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Suspects to Waive Their Right to a Trial and Plead Guilty”, New Journal of European Criminal Law, 2017, 8(3), p. 309.。世界各国普遍将公正审判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刑事诉讼权利(41)《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第十四条。。这一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而1996年刑诉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规则就侵害了这项权利。不过,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如果法律提供了程序选择的空间,被告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自愿选择。正如一些国家的陪审团审判权就是可以放弃的,我国的普通程序审判权也是可以放弃的(42)比如在英国、美国等被告人享有陪审团审判权的国家,被告人可以自愿选择放弃陪审团审判(jury trial),从而选择由法官审理(bench trial)。。因此,唯有当基于刑事被追诉人明知且自愿的放弃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或对程序简化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程序从简才符合法律规定。
概言之,“被告人认罪”与“被告人同意”共同组成了“程序从简”的法理基础。在实质上,被告人认罪放弃的是抗辩权等实体性诉讼权利,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放弃的则是依法享有的程序性诉讼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基本上把程序简化规定重新拉回了法治轨道。2018年刑诉法的程序简化模式就是这一思路的发展(4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二百二十二条。。
3.“速裁程序”并不等于迅速审判权
应当厘清一点,速裁程序并不等于迅速审判权,适用速裁程序既有可能符合也可能侵害被告人的权益。通常而言,刑事被追诉人等待审判的不确定状态是一种煎熬,早日获得审判结果能够减轻这种身心折磨,故各国法律普遍规定迅速审判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44)See to Richard S. Frase, “The Speedy Trial Act of 197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76, 43(4), p. 667.。但迅速审判不意味着简化审判,而只是要求庭审不得造成不必要的迟延,防止司法机关通过程序拖延的方式来变相惩罚刑事被追诉人(45)See to Anthony G. Amsterdam, “Speedy Criminal Trial: Rights and Remedies”,Stanford Law Review, 1975, 27(3), p. 525. Seth. Osnowitz, “Demanding a Speedy Trial: Re-Evaluating the Assertion Factor in the Barker v. Wingo Test”, Case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 2016, 67(1), p. 273.。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与控方达成一致量刑意见,对诉讼结果成竹在胸,庭审实无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告人可以选择速裁程序,这是被告人权衡之后自愿选择的结果,有可能符合自身利益。
但应当注意的是,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一般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4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二百二十二条。。可见,速裁程序强调速度更强调简化,是通过省略证据调查、法庭辩论等压缩庭审实质的方式来追求效率目标,是极不充分的庭审,不等于迅速审判权。若被告人认罪认罚但仍希望得到完整公正的庭审,那么盲目适用速裁程序可能损害其公正审判权。
四、透过权利视角审视“从宽”的制度意涵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明确了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性规定。有关基本概念的讨论至今仍然存在不少争议。事实上,从权利视角来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刑事被追诉人对抗辩权予以放弃的行为,“从宽”本质上是法律对放弃部分或全部抗辩权行为的一种激励性补偿。为保障法律有效施行,维持激励功能的可持续性,作为从宽体现的量刑建议应当具有约束力。为规范制度运行,避免其被滥用,应当明确从宽的内容不包含程序从宽或程序从简。
(一)“从宽”制度的法律起源、规范表述及辨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从宽”最初是一个单纯的量刑问题或实体法问题,规定在《刑法》中。1979年《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自首和立功作为“可以型”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从宽范围包括“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4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第六十三条。。1997年《刑法》修改后细化并扩大了自首的认定,增加了重大立功的情形,并扩大了从宽的范围和幅度。第六十七条增加了在案的刑事被追诉人或犯罪嫌疑人可以认定自首的情形,“……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4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第六十七条。这条规定延续了“从宽”的制度初衷并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仅用于激励侦查阶段的被追诉人,而且也适用于已经进入服刑阶段的罪犯。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引入了“坦白从宽”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4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第六十七条。这是坦白从宽的法律表达,这一规定延续了“从宽”的初衷,亦即激励犯罪嫌疑人放弃抵抗、配合调查。
也许是因为“坦白从宽”的响亮口号已是老生常谈,所以从宽二字听着也有悠久年代感。但事实上“从宽”这一表述第一次进入法律要等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5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五十条。这一规定是为了与2011年《刑法》增加的坦白从宽规定相衔接,只不过《刑法》未使用“从宽”这个词,而是使用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第六十七条。。可见,从宽最初的法律内容是作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
2018年刑诉法的修改保留了如实供述从宽规定并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内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是作为一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律规定,正如《刑法》中的实体从宽量刑情节包括自首、立功、坦白等,都是通过在法律之中开辟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给予刑事被追诉人一种希望或动力,从而以此激励被追诉人自愿作出主动投案、放弃对抗或者不再逃避调查、将功补过或者积极赔偿等行为。“从宽”在起源上的本质就是一种激励性的法律规定,其激励的是作出某种行为。具体到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是为了激励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也就是作出对抗辩权予以放弃的行为。
(二)“从宽”制度本质是对被追诉人放弃抗辩权的激励性补偿
“从宽”在刑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前具有一种激励性质,在其认罪认罚之后则具有一种补偿性质。简言之,从宽本质上是对刑事被追诉人放弃抗辩权的一种合法激励性补偿。如果刑事被追诉人符合“认罪认罚”要求的行为条件,满足了可以“从宽”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法律的激励效果已经达到,因此予以从宽是符合法律的一种补偿。唯有当这种激励性补偿在大多数时候真实可兑现的情况下,才能赋予这条法律规定以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是为了落实这种从宽处理的法律允诺”(52)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如果大部分被告人发现自己认罪认罚之后并未获得任何从宽处理,或者控辩协商一致的合法量刑建议被法院频频推翻而被判处更重的刑罚,那么法律就违背了其激励的允诺,从而使法律激励变成了一种诱惑式陷阱,从宽的法律激励效果就会逐渐丧失以致沦为一纸空文。
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规定包含了自首从宽、坦白从宽、认罪从宽、认罚从宽及其组合情形,前三种激励规定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经验可循,其所具有的从宽幅度也较明确,具有突破性的是“认罚”激励,可能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司法实践中的控辩协商。两高三部《指导意见》指出,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53)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第33条。。合意须经过交涉、沟通、协商才能形成一致(54)参见唐力《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为激励被告人“认罚”即接受量刑建议,实践中必然存在你来我往的协商空间。控辩协商不意味着双方势均力敌,也不意味着双方力量判若云泥,而是说明案件存在共赢的空间。我国学者普遍认可控辩协商的存在,并强调应当增强控辩平等原则的贯彻(55)朱孝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但也有观点认为,控辩地位有别、力量悬殊,刑事协商只能形成屈服而不是合意(56)参见[德]许乃曼《公正程序(公正审判)与刑事诉讼中的协商(辩诉交易)》,《中德刑事诉讼法学高端论坛“公正审判与认罪协商”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3页。。诚然,控方代表的国家力量整体处于优势地位,但侦查与诉讼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具体分配到个案的资源有限,因此控辩双方的力量在个案中呈现动态差异的相对均衡。刑事司法资源稀缺且易耗,因此司法机关力图以最少的诉讼资源来解决最大的案件数量(57)参见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2005年第 4期。。控方为提高定罪率或其他政策激励目的,辩方为换取从宽处理作为补偿,使得双方都有协商的动力。协商达成的合意不能包含强迫或欺骗,但也不意味着心满意足,无论对抗式还是纠问式诉讼制度之下,现实的合意往往都是在沟通与博弈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妥协(58)参见马明亮《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中外法学》2004年第1期。。
从宽处理的激励目标实现的法律表现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二是控方提出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二者共同组成事实上的弃权激励补偿协议。问题是,法律应当在何种程度上认可并保护这一激励补偿协议?若法院毫不尊重控方所提量刑建议,实际判处更重的刑罚,那么激励就变成了圈套(59)参见《余金平交通肇事二审刑事判决书(2019)京01刑终628号》。余金平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在辩护人见证下签署具结书,同意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一审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余金平上诉,同时检方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该案引起舆论探讨,批评者认为法院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也不利于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见,法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原则上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更加符合公众的司法感知。。若法院盲目认可量刑建议,又可能出现被告人遭到欺骗强迫认罪,或控辩“勾兑”“花钱买刑”等腐败问题。鉴于此,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6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这里采用“一般应当”的表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于“可以”与“应当”之间,表明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在原则上“应当”采纳控方提出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可以”不采纳。法院将“应当采纳”作为原则,使量刑建议一般具有法律约束力,保障了补偿的兑现力。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列举了五种例外情形作为“可以不采纳”的依据:一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法院应当作出更轻的处理,不违背补偿效力;二是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即违反了自愿性原则,相当于未达成激励;三是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即被告反悔或主张抗辩权,相当于未达成激励;四是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即适用法律错误;五是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是为法院保留裁量权的一项兜底条款。正如大部分学者所主张,除了例外情形,“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对于法院具有拘束力”(61)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6期。。除非法院审查发现有违反认罪认罚的规定,或罪名认定错误,一般都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或兑现从宽作为激励补偿。
(三)“从宽”的内容既不包含“程序从简”也不应包含“程序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中的“从宽”源于刑法坦白从宽的量刑情节,属于实体从宽,这不存在疑问。争议在于,“从宽”是否包含或应当包含程序从宽?程序从简是否就意味着从宽?有学者认为程序从简是“认罚”的内容,另有学者认为程序从简是“从宽”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优先适用非羁押刑是“程序从简”的内容。《指导意见》第八条指出“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这些争议观点都存在理解偏差,事实上,程序从简或程序从宽都不属于“从宽”的内容,应当予以澄清。
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等“程序从简”的制度设置从起源之初的目标就仅涉及诉讼效率和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非认罪认罚从宽中“从宽”的内容,也绝非“认罚”的内容。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各有独立的法律意涵,并非一项制度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程序从简总是符合司法机关的效率追求,但并不一定符合被告人的利益,甚至可能侵害基本的公正审判权,更谈不上是对被告人的一种从宽。速裁程序并非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目标或必然产物,而只是带有随机性的取决于被追诉人如何行使程序选择权的附带产物(62)参见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此外,有学者主张,“认罚”既要求被追诉人同意量刑建议,又要求其同意简化程序,这一观点存在着误读(63)参见孙长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64)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换言之,只要如实供述、承认犯罪、接受处罚,就可依法从宽,控方不得以拒绝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为由来限制从宽。
容易引起误解的是,2018《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这说明判断是否进行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时,应当将“认罪认罚”列为评价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看似并无不妥。这一规定源于2015年两高两部关于印发《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二)》的通知,“优先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且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取保候审”(65)两高两部《关于印发〈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二)〉的通知纪要》(2015)。。《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要求公检法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由于认罪认罚被视为是降低了社会危险性,容易优先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从而获得了看似“程序从宽”的效果。但是,这一规定存在被误用的危险,可能引发程序性制裁。
首先,刑事强制措施本身只是一种前置性社会安保及辅助诉讼正常进行的措施,不应具有任何法律制裁层面上的意义,不属于实体从宽。但事实上,强制措施客观上具有惩罚性效果,应当慎重使用。其次,“社会危险性评价”成为连接强制措施与“认罪认罚”的桥梁,容易给司法机关较多的裁量权。目前有实证研究表明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存在被倒逼的高羁押率和虚假认罪风险,应当谨慎防范(66)参见周新《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实证审思——以G市、S市为考察样本》,《现代法学》2019年第5期。。再次,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被滥用的现象,若认可强制措施从宽等任何意义上的“程序从宽”都会导致被追诉人的程序性诉讼权利变成司法机关手中的程序性制裁工具。强制措施不能作为侦查手段,只能以防止发生新的犯罪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为目的。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过采取强制措施作为重要的侦查手段,利用羁押措施的严厉程度来讯问犯罪嫌疑人从而击破其心理防线,获取口供等。最后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实,“程序从宽”或强制措施从宽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诸多弊端,从法治精神角度出发,绝不应当将其纳入“从宽”的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宽处理不具有任何“程序从宽”的含义,所谓“强制措施从宽”其实是惩罚性地适用逮捕措施,违背立法精神和相关国际准则,应当停止使用(67)参见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66-170页;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5版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27-729页。。
五、权利维度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方向
从权利视角出发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予以系统审视,可以发现:第十五条是原则性的权利规定,第一百二十条是侦查讯问环节对认罪认罚从宽相关的权利告知条款,第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六、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审查起诉期间控辩沟通从宽激励和补偿的实现方式,第一百九十、二百零一条则是法院审判阶段通过审查自愿性与合法性的权利救济条款。现有法律规定已相对完善,需要警惕的是误读与误用。因此,本文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索改进思路。
(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原则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是宽严相济中的“宽缓”一面,该制度理念是正当程序和恢复性司法。应当注重平衡诉讼效率与保障权利之间的冲突,坚持正当程序优先,守住人权保障的制度底线。根据一项针对某市的实证研究表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比例高达89%,可见其对诉讼效率的追求非常明显(68)参见刘亚军、黄琰《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审查》,《人民司法》2020年第1期。。这是值得警惕的,应注意防范实践中效率压倒程序正义的现象,避免重蹈辩诉交易的覆辙。
根据刑诉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主要包含实体从宽,程序从简只是附带效果,应当依法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绝不能为追求诉讼效率而克减权利。只不过,因为控方手握从宽幅度的裁量权,被告人对诉讼效率尤其是程序简化的贡献可能事实上影响从宽幅度的大小,甚至不少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认罪认罚从宽之制度底色的误读(69)参见苗生明、周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本问题——〈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理解和适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6期。。虽然《指导意见》指出:“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70)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但这一规定的理解思路应当是越早、越主动、越稳定认罪说明主观恶性越小、越有助于查明事实、悔罪态度越好的恢复性司法因素,绝非单纯考虑其对程序从速从简的效率贡献。唯有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中坚持人权保障理念的原则性,才有可能防止为追求效率而牺牲程序正义的现象。
(二)落实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的有效律师帮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下,刑事案件的重心集中于庭审之外,尤其是侦查讯问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探索相应机制以保障审前阶段律师帮助权的有效实现。从法律文化层面来看,纠问式传统对我国诉讼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合作基础是权力主导,相对轻视了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加上被告人和控方之间的力量差距悬殊,可能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但并未从宽”的现象出现,不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为了缩小这种悬殊的差距,应当注重强化有效律师帮助权的保障机制入手。
现有法律规定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需要有值班律师在场,从形式层面来看,法定的值班律师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律师帮助权提供了看似全面的保护(71)参见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但在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几乎不会见、不阅卷、不沟通、不协商,很大程度上沦为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的橡皮图章(72)参见韩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21年第3期。。实质意义上的有效律师帮助权的保障机制仍存在较大完善空间。建议适度强化律师在审前阶段的作用,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来增强被告人的力量(73)参见闵春雷《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这种以激励律师发挥作用来促进控辩协商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方式,往往比依靠法官监督更为有效。
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开展制度建设:一是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交流免受监听、监视。律师与委托人交流秘密权的保障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而信任是律师得以发挥辩护功能的基础。通常情况下,保障沟通交流的秘密性,才能让刑事被追诉人敢于坦诚地向律师进行咨询,从而切实享有律师帮助权。二是可以探索建立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对办案机关的侦查讯问规范性进行有效监督,杜绝变相或隐藏式刑讯逼供的现象。三是考虑到值班律师面临经费不足、案多人少的问题,可以探索联合律所和高校法学院参与值班律师相关法律服务工作的辅助模式。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批判地借鉴对抗式主导诉讼国家关于律师辩护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法律层面上的对质权,是赋予被告人针对不利于己的证言予以质疑和交叉询问的机会,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加强法院裁判中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实体真实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赋予被告人全面的对质权,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在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对于被告人针对必要出庭证人的对质权进行了保护(74)参见易延友《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这里,针对证人证言是否提出异议、是否影响定罪量刑的判断前提是证据获得开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了解针对自己的指控都有哪些证据,便没有机会提出异议,更不可能行使对质权。在没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被告人可以在庭审的过程中对证据进行审查和质疑,法院也会严格审查证据,保障办案质量。
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同时放弃了抗辩权,也几乎放弃了用于实施抗辩的庭审对质权。放弃对质权意味着案件的证据状况缺乏辩方的有效监督。而从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主要停留于书面过程,也意味着难以像普通庭审中一样详细充分地审查案件证据,可能导致证据不充分的潜在问题。根据基层检察院工作人员反映,实践中确实存在个别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存在较大缺陷的情况。
目前而言,我国侦查阶段的证据开示制度仍是空白,亟待完善。《指导意见》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75)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第29条。。但整体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都缺乏进行证据开示的动力,唯恐披露证据不利于案件侦查,会导致刑事被追诉人投机取巧。证据开示的制度建设存在现实必要性的同时,也存在客观困难。
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保持高质量的推行,应注意考察其他国家的有关经验以批判性地借鉴较为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简单而言,第一是明确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为辩护权的行使提供基础,体现程序正当性的价值;另一方面,是为了规范办案机关的证据收集程序,避免案件在证据质量方面出现重大缺陷。第二是明确证据开示的范围。从域外实践来看,美国在宪法层面规定了有关被告人无罪的相关证据属于强制开示的内容,具体的细化规则值得借鉴。第三是明确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则,比如证据开示的时间、方式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其具体施行。证据开示时间过早可能影响侦查工作,或者导致证据内容变动;过晚则可能导致相对方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就认罪认罚案件而言,证据开示不应晚于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前。证据交换的方式应当坚持便利于被告人,同时节约资源的原则。第四是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惩戒与救济规则。证据开示制度的有效运行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惩戒性措施作为保障,从而在证据开示权被侵害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
(四)厘清律师和被告人之间的角色差异
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决策权争议问题在各国普遍存在,我国相关规则仍较为欠缺,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极端表现为,被告人认罪认罚而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情况。根据刑诉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是否从宽主要依赖于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律师做无罪辩护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从法律层面来看,我国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虽然律师享有的辩护权本质上来源于被告人的辩护权,但律师有权根据其专业知识发表独立的法律意见。从律师的职业伦理来看,无罪辩护显然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伤害被告人,积极辩护是值得鼓励的职业操守。从实践来看,既然被告人都已经认罪认罚,律师原本没有必要再做无罪辩护,既然做无罪辩护则必有理由和依据,检察院和法院依法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这些意见,但绝不能因为律师发表相反意见而去限制或剥夺对被告人从宽的适用(76)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司法实践亦有案例支持这一立场,应予明确。
律师的首要任务是在法律范围内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但律师和被告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律师在诉讼中有自身利益考虑,甚至可能选择牺牲委托人的利益。即使是在律师为被告人的利益而竭尽全力的职业文化占据主流的美国,早在1975年的一项实证研究也表明无论是自行聘请的律师还是法律援助律师,都会因包括时间成本、经济利益等因素的考量而在辩诉交易中缺乏去为被告人的最佳利益而战的动力(77)See to Albert W. Alschuler, “The Defense Attorney’s Role in Plea Bargaining”,The Yale Law Journal, 1975, 84(6), p. 1179.。因此,实践中在认罪认罚案件里,律师为了节约时间和调查成本,或维持和司法官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等因素考虑,有时甚至可能选择牺牲部分被告人的利益。因此,应当尽早建立关于有效辩护问题的法律规则和保障机制。同时,应当认识到,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审查功能仍然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
(五)平衡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权责分配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的“量刑权之争”一度尤为突出,核心争点在于“量刑建议”的约束力问题,亦即法院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的审查和处置权限如何。虽然有的学者主张量刑建议的约束力已经明确,早期实践中不同案件的判决却体现出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澄清(78)参见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属于控方主导协商、法官积极审查模式。为了改进规则,第一,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精准量刑权;第二,应当落实法官的积极审查监督职责;第三,建议探索明确法官不得作出对被告人更为不利的判决。《指导意见》明确了公检法等机关的权责,要求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并说明理由和依据(79)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第33条。。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同时应当依法审查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80)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第40条。。这是对刑诉法第二百零一条内容的细化表达,明确了应当采纳量刑建议的条件是达到证明标准、罪名准确、量刑适当,在内容上并无突破,但在表述结构上从“一般应当”到“应当”的变化,应当理解为明确法院应坚持原则上“一般应当”采纳并确认量刑建议约束力的立场。换言之,针对认罪认罚案件,法院在事实上将量刑裁量权让渡给了检察院,为自身保留的是监督权和修改权。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某地区法院对于量刑建议直接采纳率高达96.5%”,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量刑建议以幅度刑为主而非确定刑,另一方面是法院审查流于形式(81)刘亚军、黄琰:《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审查》,《人民司法》2020年第1期。。这一情况不利于认罪认罚制度健康发展。检察院的精准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的动力所在,如果检察院不提出确定刑建议,就要由法院来决定,可能导致控辩协商变成控辩审三方协商,这种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既不利于诉讼效率,也可能导致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之后丧失公正审判的机会。因此,应当明确检察院的量刑权责,强化并探索机制落实法官的积极审查与监督义务,避免法官的实质审查沦为走走过场的形式。
关于法官的量刑建议修改权,可以考虑借鉴广为称赞的意大利经验。意大利规定法官只能在从轻方向上修改量刑建议,亦即不得作出对被告人更为不利的修改,既坚持对控辩协商的尊重,又可以纠正控方滥用强势地位侵蚀被告人权益的不公现象(82)Albert W. Alschuler, “The Trial Judge’s Role in Plea Bargaining, Part I”,Columbia Law Review, 1976, 76(7), p. 1059.。唯有明确权责分配,才能保障控辩协商的有效运行,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高质高效推行。
六、结语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及功能带来了体系性冲击,人权保障理念与机制面临重新定位。从权利视角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这项制度的权利底色:认罪认罚是刑事被追诉人对沉默权、抗辩权等实体诉讼权利的放弃,从宽则是一种对被追诉人弃权行为的激励性补偿。通过重新梳理认罪认罚制度中的权利要素可以发现:沉默权的确立奠定了实体从宽的理论基础;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并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体两面,应当重视前者,但不应过分追求从速从简;速裁程序仅仅是认罪认罚从宽的附带产物,而非制度目的。面对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主导下效率优先的现实,有必要在权利维度之下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思路。一是明确人权保障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原则性地位;二是落实有效律师帮助权,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和基本诉讼权利,以提升实质公平;三是探索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质量;四是厘清律师和被告人之间的角色差异,明确决策权争议和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处理机制;五是平衡检察机关与法院的权责分配,原则上应当尊重量刑建议的效力。总之,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心应当前移至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以避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念的落空。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