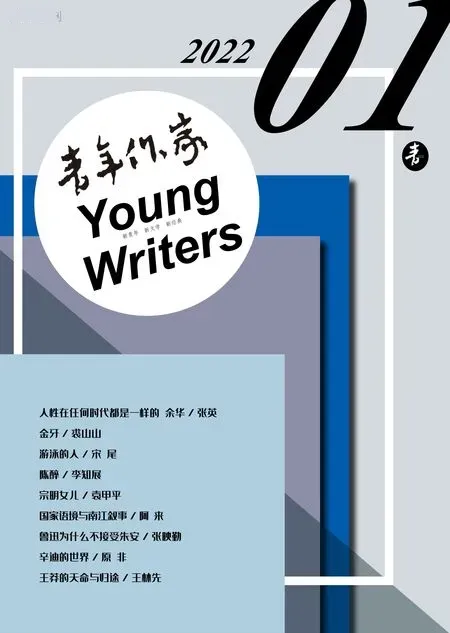陈 醉
李知展
一
老陈好酒。
老陈没什么出息。他自己说的。
老陈好酒到什么程度呢?花生米也买不起的时候,拿筷子头蘸点酱油,就能喝几盅。至于出息,老陈应该和所有乡村出来谨小慎微勤苦做事的父亲差不多。
老陈算是他的朋友,至少他们喝醉时,朦胧间,彼此曾这么以为。可等到老陈死后,李牧仔细想了想,发现除了他愿意透露的一点枝叶,他对老陈的了解,并不比别人更多一些。
但这也不碍事,谁没有一方来历和去处呢,谁也不可能对朋友那么坦白。他们能偶尔聚在一起,只为喝点酒,想聊就聊几句,不说也可以,完事各自分散,奔往这个城市的罅隙。
本来他们的交集就很偶然。有段时间,李牧常在平乐坊巷子尽头一家夫妻档川菜馆解决晚饭。这家店主要是干净,因为位置稍微偏僻,生意不温不火,大多是老顾客。老板老曾有几道拿手菜,回锅肉堪称一绝,剁椒鱼头香辣醇厚,有时心情好了,他会卤点肥肠,这个算额外恩典,因为主要是老曾自家吃的,难得他赏脸,会赠送几个相熟的顾客一盘。卤好的肥肠以青椒爆炒,如果幸运,适逢从老家寄来腊兔,再来一份干锅腊味,就可以召唤老板娘打酒。酒是店里泡的,高度散白,浸泡人参、陈皮、枸杞几味。李牧问过老曾:“从开业到现在,你那人参没换过吧?”老曾也不介意,探出眼神,狡黠一笑。老曾性格好,软绵绵的,顾客少的时候,你邀请他喝两杯,他必坐下。问他:“何不换个地理位置好的地方,将生意做大呢?”老曾摆摆手,笑笑:“房租水电消防工商,不好搞,再说,我这生意也不差嘛。”他身上有份恬然散淡的知足感。独老板娘泼辣,身形粗大,和顾客嬉笑怒骂,迎来送往,指挥男人如调兵遣将,她骂起老公来,热热烈烈,半嗔半怒的,是一团喜气的火热,不让人觉得难堪。老曾挠挠头,笑笑,不当回事,丢下和客人寒暄的酒杯,进后厨继续煎炒烹炸。
李牧常在靠后厨的位置临街而坐,因为无聊消磨,坐在那里,不影响他们生意,还有一点,离厨房近,烈火烹油,诸菜下锅时激起的“嗞啦”,让人心旷神怡,觉得生活尚有热气腾腾的意趣。李牧就这样慢慢吃、慢慢喝,虚掷一个晚上,吃完和老曾打几圈小牌,或是杀一盘象棋,如果还早,就沿街去平乐坊老街转转,看看别人家的世俗烟火、喜怒哀乐。直到转累了,回去冲凉,睡觉。
他一个人其实很快活。
如果没有家庭、婚姻、孩子、房贷这些城市标配的担子压在肩头,那基本上就可以自私地放飞自我了。但这份快活是隐秘的,白天他还要扮演痛心疾首的失败状,特别是面对单位那几个老妇女的眼光。“小李,给你介绍个姑娘,本地的,和你一样,离异,可有车有房,做茶叶生意,要不要去见见?”“我这啥条件,不敢奢望,琳姐。”李牧还得感谢人家关心的好意,心里虽然想骂一句,管你屁事。可在这些大姐眼里,一个有正当工作貌似正常的男性,没有家庭,就是失败的。似乎不和她们在同样的婚姻阵营,就罪不可赦。所以李牧只好极力贬低自己,或者说是如实交代:没房,跑了五万公里的破车,工资不高,聘员,升职没戏,性格闷骚,父母年事已高,抽烟喝酒,轻微不举……陈述到最后,简直不配做人,但求她们放他一马,他心说,大姐,求您了,你和大腹便便的老公四处抛头露面的生殖器斗智斗勇孩子叛逆您老每天买菜做饭搞家务腰酸背痛性生活三个月没两次还千篇一律还争分夺秒……你沉浸于如此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就让我这种低阶社畜自生自灭吧。
他在单位是个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枯木。
只有在老曾这里,枯木才抽出枝条,经了酒的滋润,有些活意。
其实李牧酒量有限,三四两就上头,主要是酒的气氛,是轻微的毒,无伤大雅的麻痹,有种致幻的效果。
这天,喝得有点多,正和歇下来的老曾闲聊,进来一人,是老陈。老曾招呼道:“老陈,又来买彩票,中奖没?”餐馆对面有个彩票站。
陈有德“嗨”地干笑一声:“上期差一个数字就是二等奖,二等奖哦,一百多万呢!开奖时老子激动得不行,结果瞎激动,最后他妈的,就八百块。”
“那得接着买,下次把差的补上。”
“这都是命,咱命不好,买着玩的。”老陈自顾去接了一杯酒,一转头,看见李牧,点点头,笑笑:“领导也在呢。”
“得了,老陈,领个鸡毛的导,都是打杂的。来,喝酒。”
确实,他们都是打杂的,不过老陈在物业,李牧在单位而已。
李牧怀疑是因为上次敲错门,新任的局长对他冷淡之极。房丽娜在局长办公室常做长时间的汇报,李牧知道,却不关心。那天,因为有个急件,报到市里,市里审核说漏个章,还有两个小时就要下班,他心想,今天搞完算了,要不,这么热的天,明天还是他来弄,所以急着找局长签字补章,就敲了门。敲门也没事,局长没开。下午还在的呢,他心说,不知哪根筋搭错,一屁股坐在旁边拐角楼梯上抽烟。过不了一会儿,房丽娜探出脑袋,四处看了看,整整衣角,出来了。遇到拐角守候的李牧,她低头,下楼。第二个月,李牧就被告知,管理单位后勤,对接物业部门。他简直想蹦起来扇狗日的一巴掌。这是单位最细碎而不讨好的工作,后勤鸡毛一地,物业千头万绪,都不是好惹的,谁让他没一点后台呢,只好硬着头皮,做一天是一天。幸好也无大差错,不过是耐得日常繁琐。
李牧对老陈还不错。或者说,他从老陈身上看到了部分自己未来的投射。老陈老了,物业经理几次有意要将他辞了,可工资那么低廉,一时也找不到这么勤快的人选。老陈主要负责打理单位的花木绿植,以及一个小小的空中花园,可门岗有事他顶上,搬运物品他一马当先,出去办什么事跑腿的也是他……老陈能做的无非卖力一点、小心沉默一些,总汗涔涔的。问他:“累吗?”他笑笑。人都说老陈脾气真好。这其实是最廉价而恶心的评价,说一个人脾气好,无非是好使唤罢了,并且使唤起来,都不手软。
李牧权力有限,单位有几家下属行业报刊,仓库很小,他定期清理,大多数都让老陈以送出去的名义分批次运走,一月总有个几百斤。还有一项,要派送一份街道新闻周报,名单上千份,他勾画出重点人员,不需交代,老陈便已领悟:必须派送的名单要按期送到,其他的隔三岔五送一次就好,一个街道小报,也没多少关注,真有反映收不到的,下次单送他就是了。老陈下了班,骑个电车,送送派派,剩下的积攒起来,加上派送费,一月有千把块钱。这都是顶着个太阳,变通出来的辛苦钱。为了替老陈打掩护,定期的物业会上,李牧也偶尔提点一下老陈,哪家哪户怎么反映没收到,一定要注意,记住喽,一家也不能遗漏。老陈唯唯点头,半站起身子,惶恐忐忑的样子,可心里自然明白什么意思。
所以老陈对他挺感激。几次要送东西塞钱,都被李牧一句话顶回去:“怎么,老陈,难道你报纸没送,变成垃圾卖了?要不送我东西干什么,心虚?”老陈黑着脸,嘿嘿笑,知道什么意思,再不敢送礼。
为什么要对老陈好呢?他也说不上来,虽然是举手之劳,可物业还有老石呢。想来还是因为老陈儿子争气。据老陈透露的消息,他儿子在北京某名牌大学读书,老陈辛辛苦苦,都是为了儿子挣前程,所有的钱,零的攒整,按时汇入儿子卡里,让他安心学业。
熟悉的,都挺替老陈高兴。老陈很谦虚,搓搓脸,低头竟然轻微叹口气,说一句:“不容易啊。”不知道是说他儿子学业上取得如此佳绩不容易,还是老陈以一己之力供他不容易。老石就捶他,说老陈:“别装了,你就偷着乐吧,明年你儿子毕业了,怎么也得弄个县里的小官干干,对吧。老陈你有福啊。”
中秋节前,老陈邀请同事去他那里聚聚,也试探性地邀请李牧:“去吧,李老师,赏个光哈。”知道李牧确实称不上领导,老陈就改口叫他李老师。老师这个称呼挺好,可大可小。李牧也就随他去了。
李牧想着在他租屋里,应该破费不了多少。到了,才发现,老陈是花了血本了:一整只订做的荔枝烧鹅,鹅是如此香艳巨大,老陈没有合适的盘子盛它,只好垫着塑料袋摆在中间;此外,还有江中岛上抓的走地鸡,白切一只,吊汤一只;大虾五斤,白灼;清蒸鲳鱼一盘;还有猪耳、牛肉、菜心等等。大家一见,都说:“老陈你发财了,搞这么豪华!”特别是与他局促的陋室相比,有份过了头的隆重。老陈从保温桶里还摆出两样菜,回锅肉和卤肥肠,专门从老曾那儿打包来的。老陈看看李牧,不好意思似的,笑笑,让李牧挺感动。
那晚喝了不少。记得大家闹哄哄地走了,老陈收拾一屋狼藉,李牧侧躺在老陈不知从哪儿寻来的旧躺椅上,揉着太阳穴说:“老陈,没必要这么破费嘛。”老陈咧咧嘴:“难得请大家一回。”顿了顿,他又说,“我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嘿。”
哦,怪不得,老陈高兴。
老陈还让看儿子和那女孩的合照,照片上女孩高挑浅笑,唯睫毛拉得细长,看起来有点媚相。儿子倒是跟他挺像,国字脸,浓眉,皮肤有点黑,气质是青春的,可微蹙的眉头,带着似有似无的忧愁,总不太像是名牌大学的学子。老陈解释:“小时候他懂事,帮干农活干多了,晒的。”
李牧照例祝福:“老陈,你真是好样的,儿子培养得这么棒,这下好了,儿媳也帮你找好了,你省心了。”
老陈就笑。
二
以后李牧就和老陈往来得密集了些。大多是周末,在老曾那里,各执一杯酒,面对几碟小菜,分担一桌沉默。稍微的区别就是,如老陈提前执意声明要买单,肉菜就少点,换上拍黄瓜和油炸花生米。
他们常常从头到尾也没几句可说的。但气氛是对的,不觉得尴尬,就像什么呢,大约是两块冰,在一起放松地解冻。茫茫人海,气场相合,又都愿意喝点儿,其实已经非常难得。沉默的人,心上关门落锁,几杯入喉,门即便不开,也会留有缝隙,说些体己的言语。
李牧在单位戴着面具夹着尾巴,太憋屈,所以,在酒的怂恿下,轻易地将自己那点破事,不知不觉向老陈兜了底,工作上多么受排挤,生活多么操蛋,妻子如何背叛,如何离的婚:
“她很漂亮,至少配我,绰绰有余,但有一点,心气高,总要好了还想好,本来,我们奋斗了几年,有了房有了车,虽然房子是二手的、车子是国产的,但在这城市,又没有依靠,全凭自己挣来,我觉得就不错了。她不行,列出计划,要换房,要买第二套,要换车,要存款……她想要很多,这没有错,可我却奋斗不动了,有一段加班太多,得了病,住院两个月,我都在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奋斗是为了早点猝死吗?我觉得她有点过了。病愈后,我从大厂辞了职,考进了这个单位。她仍像加满油的马达,开足马力,冲锋陷阵。她做起了生意,很快,她生意就有了起色,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对我也越来越看不上了……这都正常,我都理解。可到最后……”
李牧说,他们是大学情侣,毕业后,在同学的撺掇下,来到这个城市。同学帮忙找了房,付完房租,请同学吃了饭,身上就没什么钱了。第二天,他们就分头去找工作,从租房的地方出发,在汽车站转车,对照着一张临时从报刊亭买的地图,一个站牌一个站牌地查看。南国的艳阳高照,她那么娇小,他们手拉着手,带着初来的兴奋和尚未找到工作的焦灼,一次次以汽车站作为中转站,搭车去城市不同的方位面试。通过那家著名的电子企业复试的那天,他们仍相约在汽车站公交牌下会合,她刚从公交车上下来,李牧就奔过去抱住她,他们肆无忌惮地抱着……因为他觉得,终于可以养她了,他记得当时说:“好了,我有工资了,你不要着急,慢慢找,找到自己适合的。”等过了试用期,李牧更兴奋,在他看来,工资已经很高,除了房租和两人生活花销,还有富余。正是由于他承担了养家的前提,并在李牧乐观的劝说下,女友才有裕如的心境和经济支撑,为了兴趣而非一份工作急于兜售出去。女友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商会找到了喜欢的工作。
工作了几年,他们攒下了一笔钱,当时房价刚开始上涨,报纸上专家兴旺,大部分意见是一个平方五六千元,这疯了,会跌的,最迟半年。可半年过去,又涨了不少,专家的意见还是老一套,李牧觉得不对劲,但也觉得六七千买一平方米,确实有点夸张。他还在彷徨,妻子说一句:“你就再观望吧,马上吃屎也赶不上热的。”妻子当机立断,将攒的所有钱都聚到一块,朝亲戚朋友借了几万,勉强凑了首付,看了一天,就决定了小区楼盘户型。李牧后来非常佩服妻子的英明。
交完首付,做了简装,为了省钱,墙上四面刷白,存款再一次清零。李牧每月发了工资,就交给妻子,由她来买早已相中的家具,是一件一件地买,将近一年才凑齐沙发、饭桌、茶几、组合柜、衣柜、化妆台、双人床,然后电器再这样一件件搬回来,像是燕子筑巢一样,他们一点点衔来物件,组成一个叫家的地方。从东到西十七步,南北十二步,通风好,采光强,三个房间,这里每一寸,都是他们的。空间带来的笃定和实在,妻子笑逐颜开,让李牧觉得每月的房贷,是值得的。
李牧记得,最后双人床运来,他和妻子将旧的木板床清理走,组装新床。妻子铺上被褥,李牧躺在床上,手摸到的都是柔软,他感到强烈的幸福。他感谢妻子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李牧抱着妻子,在夕阳的余晖里,两个人缱绻旖旎。
每想到这个场景,李牧都要心碎一次。
不过,这些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李牧并没有讲夫妻间的冷暴力、他的不举、他的恶言相向,甚至最后安装摄像头,也只是为了占据道德高地,让妻子放弃房子。
他只管以酒遮脸,卖弄他的深情和受伤。
“我对她这么好,到最后,她和商会会长暧昧那么长时间,我在家偷偷装了摄像头,他们,就在我们一起布置的双人床上……”那晚,李牧哽咽欲泪,他倒没发觉,还沉浸在委屈一方的角色里,“老陈,这太欺负人了……”
李牧饮尽杯中酒,犹自滔滔:
“其实,现在也挺好的,一个人,多自由啊,不用天天赶回去给她做饭、看她的脸色,在屋里抽支烟都被数落,何必呢,是吧?自己多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想和他们争了,平平淡淡,不也挺好。”
沉默的老陈,放下杯子,悄悄说了一句:“哪里是与世无争,只是争不过罢了。我也一样。”
李牧一愣。
老陈垂下眼睛,重新摆回低微的姿态,给他斟酒说:“再喝一杯吧。”他悄声说,“我老了,可以不争,混吃等死;你不同,还年轻。”
看来老陈并不一味唯唯诺诺,其实世事洞明。李牧默然无语,抬起头,嘿嘿一笑。
他们继续喝酒。
李牧那晚喝得有点多,最后是被老陈搀着出来的。给他打车,他拒绝,还在那呜呜哇哇地说些醉话,大都是他对前妻好什么的。老陈不放心,只好架他回出租屋里,让李牧躺倒在床上,他去大排档买海鲜粥,给李牧醒酒。
李牧其实并没有多醉,他是暂时不想回到空荡的屋子里,那种百无聊赖且没有生机的灰败,让他在今晚难以承受。李牧歪着脑袋,在想自己怎么一步步混到这样,却想到脑仁疼也想不明白。他随手翻老陈床头柜上的书,竟然错落摆着几册《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之类的泛黄小说,旁边还放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本子,李牧翻了下,里面夹着花花绿绿的新旧彩票,本子上记录的大多是老陈每天的花费账单,小到今天吃了什么快餐、多少钱,都记录在案。另外,还摘抄了一些从书上看来的句子,没想到老陈这么喜欢读书,摘抄了一大卷。李牧对老陈多出了一份敬重。最新的摘录是《罗状元醒世歌》里的:
时来易得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
堪叹眼前亲族友,谁人肯济急时无。
老陈写字一板一眼,笔画粗重,这摘录的句子似是贯穿所有的心事,李牧对着起卷的本子,琢磨着这几句歌词,也感慨不已。在将本子放回原处时,忽然从折页间掉落一张纸,他拾起来,无意间瞥了一眼,是老陈的体检单。他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物业公司组织过工作人员去人民医院做了一次体检。单子上其他都寻常,唯肝功能那里,谷丙转氨酶(ALT)(170)IU/L,这个指标下老陈划了线,备注似的,在边上写:比正常偏高四倍,疑似肝癌。翻过来,在单子的背面,写了两行字: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半世无能,只欠一死。
字写得工整大方,像是对命运最后的呈堂供词,颇有些不忧不惧的坦荡样子。
李牧一呆。
老陈打包两份热粥回来。他赶忙将本子合上。
“醒啦,喝点粥吧。”老陈说,“今天怎么喝这么多,有什么烦心事?”
李牧想笑笑带过,却想着刚才老陈本子上的体检结果,不知说些什么。喝了两口粥,李牧说:“老陈,再去买点啤酒吧,陪我再喝一会儿。”
他想安慰老陈,也想从老陈这里得到安慰。因为,今天是他前妻的婚礼。
三
李牧有时想,酒是什么呢?对强者,是助兴剂,却是贫贱者暂避的港湾,是鸵鸟把头扎进去的沙堆。多数的人,见面聚集,彼此客套,酒就是那个催化剂,掀开人和人之间隔着的门帘。高度的白酒,猛喝一口,像一滴油溅在热锅上,腾地起一股烟,伴随执杯人一声长叹,人间的酸辛苦乐都在其间了。
他的没出息就在这里,没几杯酒,他睡不着,失眠越来越厉害。他能和老陈掏心掏肺,毫无防备,诉诉苦,倒倒情绪垃圾,是因为觉得他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不像在单位,周遭都是利益相关者,他得人模狗样,一丝不苟,见人面带微笑,面对上司卑躬屈膝,遇到窝囊事苟且腹诽,只有在老曾饭馆里,面对老陈,才有一些放松。冗长的日子里,有几个空隙,喘口气,觉得还可以再去继续忍受这世界的蝇营狗苟。
可李牧最近却不敢再叫老陈对饮。那张被老陈用力标记的体检单,总浮现在眼前,有几次,他想开口问,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能说什么呢?可老陈似乎一点也不受影响,照旧上班下班,偶尔买一注彩票,顺道来老曾这里吃个快餐。
月底,老陈和他又在老曾店里遇到,一起吃了晚餐,老陈没喝酒,主动把单买了,还不走,一直搓着手。李牧看出来了,问他:“老陈,有事?”
老陈望着他,眼巴巴地说:“李老师,能借我点钱吗?”他还是那么客气,那么低微。“我儿子要和那女孩订亲,我没本事,东借西借,还差一点。”
“好事啊,老陈。”李牧说,“要多少?”
“两万……行吗?”因为渴望和惶恐,老陈的眼睛像揭开的蒸笼,溢满水汽,他抬了下头,又迅速低下去,也许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实在冒昧,老陈嗫嚅着说,“没事的,李老师,你要是不方便,就算啦,我再想其他办法……”
正是他这份小心翼翼的神情,触动了李牧,他拍了下老陈的肩头说:“行,把你银行账号给我下。”
老陈忽然眼圈红了,深深给李牧作了一揖,不停地说道:“谢谢,谢谢你……”
李牧再拍下他:“没事,老陈,不算啥。”实际上,李牧离婚后将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换掉当初一件件置办的家具,竭力清除前妻留下的痕迹,再借助酒力,才能囫囵睡上一觉。现在他身上全部加起来,仅余下不到三万。
李牧立时将两万块钱转给老陈。
老陈的慌乱表明他实在没想到李牧会这么爽快。他要给李牧补写个欠条,还要拉上老曾做个见证,保证最迟到来年上班如期归还。看着他慌张说着感恩的嘴唇,不知如何是好的眼神,李牧摆摆手,笑了,表示不需要,他想,毕竟都这么熟了,钱也不多,而且是成全他儿子的好事。李牧心里涌起一阵施恩于人的感动和欣慰。他甚至都没有细问老陈怎么儿子还没毕业就急着订亲。老陈给同事的解释倒也合理,儿子和女友早晚是要结婚的,双方家长先见下,老陈拿点钱,就当把亲订了。
借了钱后,老陈请了一段时间假,回家为儿子操持。在他粗陋的践行宴上,李牧还另外封了一个红包,算作老陈的路费。那天众人都劝酒,李牧晕晕的。也只有在这些身份比他更低微的人跟前,他才觉得自己像个人。他是对他们好吗,他后来想,其实是享受这份被虚假围绕的恭维气氛。
老陈要赶火车,先离开饭桌,老石接替过老陈的位子,接着花式劝李牧喝酒。到后来,老石大着舌头,说一句:“老陈这次回去,来年可能就不回来了,街道送报纸的活儿是不是可以……”
“没有啊,他说给儿子办完事就回的。”李牧故意岔开说,“老陈也算圆满了,虽然得了癌症,但儿子学有所成,又订好了儿媳,真不错。”
老石瞪着眼睛:“他得了什么病?”
“肝癌嘛,你不知道?”
老石竟然摇摇头,诡异地笑了笑:“老陈这家伙真是……”
在李牧的逼问下,老石才支支吾吾地还原出老陈的真实故事:
老陈是有个儿子,却是个混子,根本不是什么北京某名校高才生。“他家祖坟根本就冒不出这股子青烟。”老石说。老石也有儿子,学习一塌糊涂,中考在全校排名倒数,根本没有上高中的必要,老石给他找了个电子厂,没干一月,他就嚷着辛苦,天天和老石吵,嫌弃其父没本事,顶起嘴来口舌灿烂,常常一句话噎得老石半死。自己的孽子如此,以己度人,老石不信木讷的老陈会有优秀到变异的种子。老石偷偷查过老陈入职时的个人信息,这年代打听一个人太容易了,网上搜索到他村里大队的电话,老石打过去一问,全不是老陈吹嘘的那么回事。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家养猪、养鸡,老二倒是上了学,考了两年,才上了省内一个建筑专科学校,毕了业,在工地上混生活,却完全不是老陈这样的本分角色,好吃好喝,还赌博,输急眼常跟人打架,“合着还不如我家那个小祸害呢。”老石嘻嘻笑了,他搞不懂老陈为何要虚构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李牧却懂,不过是为了在人前找那么一点可怜的尊重。
“那他的癌症?”
“嗨,根本就没那回事。”老石笃定地说,“体检我们一起做的,医生只说他有点脂肪肝,劝他最好戒酒,其他都是他自己杜撰的。”老石呵呵笑,“老陈这家伙挺会虚构的。他图什么呢?”
李牧一愣,如果说就为博得他的同情,借那两万块钱,老陈这套演技也太多此一举了。他想,或者老陈觉得不出此下策,就没可能从他那儿借到钱。想来,他们终究不过是陌生人,无非在一起常喝点小酒罢了,老陈将关系分得很清,没想过平白无故李牧会帮助。在这点上,老陈活得透彻,深知炎凉。可到最后,他这么势单力薄,却是老陈以为处在绝境时唯一能施出援手的人。老陈可怜。他也可怜。他旋转着酒杯,一口压进去,辛辣从嗓子眼往心窝里钻,李牧怆然一叹。
四
临近年关,工地上提前放假,儿子没挣下钱,还欠了不少外债,不好意思回家。喝了酒,儿子和隔壁工头赌得大发,也是想博一把,炸金花到半夜,一算,输了几万,没钱赔,争执起来,酒意上涌,寡不敌众,被打了一顿,伤着腿了。老陈那几天感应似的,眼皮跳个不停。
老陈两个儿子,老大去年刚成家,和他一样踏实,在家搞养殖,虽然长子结婚,彩礼、建房子就花光了老陈的积蓄,老陈还是挺欣慰。老陈头疼的是小儿子。
小儿自小聪明伶俐,老陈寄予厚望,着力培养,小儿学习也确实可喜,整个小学阶段,在班里垄断第一。老陈常摩挲着小儿的头发,笑呵呵的,想自己当时家里穷,没条件继续读书,现在终于有儿子可以成全他的梦了。
老陈真是开心。小儿所有的要求,他都极力满足,哪怕是不合理的,他也没说过一句重话。正是老陈这种笑眯眯的态度,怂恿得小儿的脾气水涨船高。
到了初中,小儿就坏了,老陈没反思自己的溺爱,只是想,或许就坏在让他上了市里的初中。拔高一截似的,他输送着打工挣下的那点钱,硬撑着小儿的花销,期望博个前程,却不知什么时候小儿沾染了那些来自街面上学生混混的习气,讲究衣服牌子,同学之间互相过生日,经常在外面聚会……学习自然一落千丈,可他自恃聪明惯了,以为凭借自己的小聪明,突击一下,成绩还可以过得去,凭着这过得去的成绩单,就可以继续兑换老陈的血汗钱。却不知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糊弄到初三,中考就露了馅,市里三个公费高中,他一个也没考上。聪明误人之处,就在这里。老陈咬咬牙,缴了巨额赞助费,让小儿上了高中,小儿的成绩却再也没能翻身。他没受过挫折,努力了一下,没达到心里预期,便急遽地自暴自弃,熟谙地和小混混们勾搭在一起……到最后,只能上一个学费高昂的专科。
但在老陈心里,小儿还是那个伶俐的男孩,聪明可爱,透着灵气,会攀着他的耳朵,悄悄对他说:“爸爸,我又考了个第一哎……”这些年,老陈喝醉了,在心里将期望养着,像是海里的帆船,在他那里,儿子原定的前程,一步一步,越发驶入辽阔之境……
可事实上,老陈和小儿半年没联系了,他打电话,儿子不接,就算接了,他除了嘱咐那几句老套,也说不出什么。何况,儿子对他的嘱咐,深恶痛绝,常常没等他说出一句:“乖儿,好好干,别和人置气,多学学本领……”儿子就嘟囔着“行了行了知道了”,给他挂了。即便是问他要钱的时候,口气也天经地义似的。
老陈想起,就要叹一口气,锁着眉头,喝杯酒,溜达着,去买张彩票。每次都选儿子的生日。他在为儿子赌运气。
这天半夜,儿子大醉,打来电话,没提要钱,却沉默许久,传来断续的呜咽。在天津大邱庄工地上,儿子蜷缩着伤腿,流了泪,含混地说:“爹……我错了……这些年你供我,辛苦了……我混到现在才明白,晚了……我想你了……我朝着南方给你磕个头吧。”
有这句话,老陈说,狗日的,值了。
浪子回头啊。
老陈爬起来,捉住酒瓶,猛灌了一口,酒却从眼睛里跑出来了。
五
日子就这么重复地滑过。李牧每每独酌,心说,也该戒酒了。他嘿嘿苦笑,再喝这一次,下回就戒。如此过了半月,李牧正在店里和老曾吹水,一转身,老陈黧黑的脸杵在门前,却迟迟不进来。
“什么时候回来的,老陈?还没吃吧,来,我再加个菜。”老曾招呼道。
老陈眼睛低垂,悄悄走过来,坐下。他的眼窝深陷,带着浓重的疲倦,掏出一条家乡产的烟,递给李牧:“尝尝这个。”他说,“你都知道了?”老陈反而吁一口气,“不该骗你,我儿子不争气,他在工地上伤着腿了。”老陈眯着眼睛,笼罩在烟雾里,李牧看不清他的表情。老陈连喝几杯酒,攥着的手心展开,递过来一张纸,是写给李牧的欠条。“对不起,”老陈说,“放心,就是死,钱我也会想法还你的。”
李牧没说话,拍拍他的手。
老陈似乎来时就喝了不少,这会儿又要了两杯。老曾还劝:“少喝点吧,老陈,我那泡的酒就一点了,不打算再泡了。过完这月,年后我就不干了,这里房租也涨得厉害,干不下去啦。”老曾说,“算了,不干拉倒,我也该和老伴回老家歇歇了,这些年她跟着也受不少罪。”老曾看向妻子,讨好地笑,“来吧,一起喝点,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能聚到一起喽。”
老曾一席话弄得大家挺伤感,小店不再,李牧想,以后还去哪里消磨呢。老曾妻子罕见地温柔,还将早上点好的私家豆花端上来,让他们爽口醒酒。
老曾一语成谶,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场醉。
到最后,老陈一直在嘀咕:“对不住了,小李。”
李牧也喝晕了,心说,有啥对不住的,那点钱不还,你还能跑了不成,不就喝多了,待会儿要我扶你回去嘛,多大个事儿。
可他错了,他妈的,老陈是真对不住他了。
转天,单位做年终前大扫除,物业清扫房顶花圃和凸出栏杆处围绕的花丛,老陈自告奋勇,承包了最危险的工作。李牧在挨近顶楼的五层平台处,关切地望着老陈,嘱咐他注意脚下,别逞能。老陈一直埋头干活,眼看着要干完了,就剩下栏杆那里,有些落叶和积灰。老陈直起身,忽而对李牧笑了笑,似乎是说一句:“欠你的从我抚恤金里扣掉,谢谢了。”然后,弯腰,踏出一步。
儿子还在医院里,腿被钢管砸得有点狠,醉酒打他的早都跑路了,医治却耽误不得,儿子哭着,不想成个瘸子,他还跟老陈说,等腿好了,都听老爹的,在老家市里租个门面房,他想做点小生意。老陈得用身体给他兑出一张彩票。
李牧刚要叫出一句:“我操!”转身就往楼顶跑,在他拔脚的刹那,在众人惊讶的注目下,老陈从七楼寂静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