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心灵”如何可能
朱生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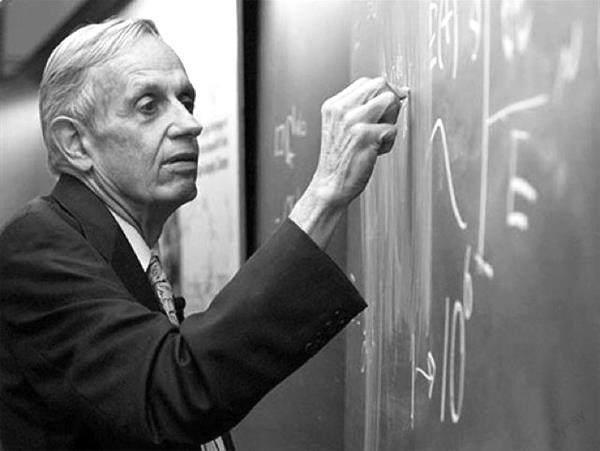
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2015)
朗·霍华德(Ron Howard)导演的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约翰·纳什(纳什I),看到一个数学家的心灵历程。在此之前,一九九八年,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出版的同名传记《美丽心灵:纳什传》,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纳什(纳什II)。传记纪实,电影有虚构的情节,但这两个纳什的形象基本相符。还有第三个纳什,就是电影观众和传记读者心目中的纳什(纳什III,准确地说是无数个纳什III,构成一个集合)。
那么,这三个纳什与那个曾经在数学上取得巨大成就、陷入精神分裂症三十多年而又奇迹般地康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的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2015)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精神分裂症
纳什I的精神分裂症是电影的看点。即便聪明如你,多半也会始料未及,看到一半多了才发现,前面的很多情节,已然是你从一开始就等着看的纳什I的幻觉。纳什II的症状出现在一九五八年,他与艾莉西亚(Alicia)结婚后的第二年。电影將时间提前到了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一天。这是合理的虚构。
毫无疑问,纳什是一个不世出的数学天才。纳什II完全生活在数学里:“他的难以控制的理性使他愿意把生活中的决策……统统转化为利弊的计算以及与情感、习俗和传统分离的算法或数学规律。”(西尔维娅·娜萨《美丽心灵:纳什传》,王尔山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P11-12;下文仅标注页码)如此说来,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恰恰在于精神过于专注。或者说,他对于理性的狂热达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这也不是纳什II一个人独有的状态。他曾经为兰德公司工作。“这里对于理性生活的崇拜已经到了一种近乎荒谬的程度,兰德的男男女女都相信系统思想和量化方式是解决复杂问题的钥匙。事实,最好是从感情、习俗和偏好中隔绝出来的事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P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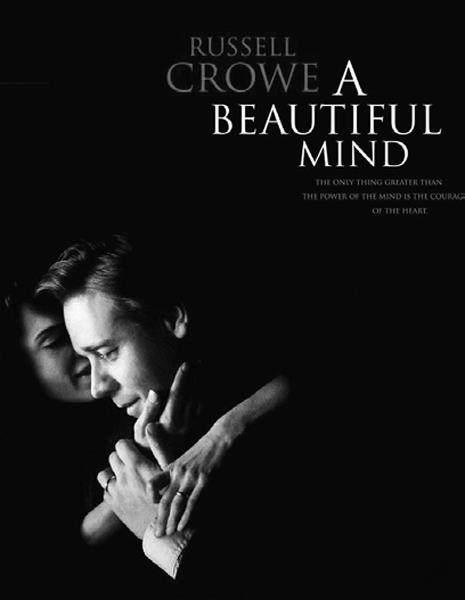
电影《美丽心灵》海报,2001年
高度的专注力是天才的特征之一。有些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还可以像常人一样,把一些不正常的幻想压制下去。纳什的幻想突破了自己可以控制的阈限。那一年他三十岁。而他发表他的博弈论是在二十一岁,比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年龄小五岁。“数学家们将他们的职业看作一种年轻人的博弈,因此三十岁具有更加令人沮丧的意味……一个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数学家面对日历的时候,内心体会到的恐惧和警告如果不是同模特儿、演员或者运动员一样,就是更加强烈。”(P275)不幸的是,家庭和婚姻生活,所谓心灵的港湾,似乎也未能缓解他在事业上的恐惧和焦虑—对这样一个人来说,需要用心去维系、平衡的婚姻和家庭是一道不可解方程,只会增加他的困扰。这不得不说是他个人的不幸,与他自己的家庭、父子关系和在此之前的生活经历都有关。
不仅如此,纳什的精神分裂症也与世界风云有关。他的幻想是从普通的报纸上解读出他所说的来自宇宙的信息或者军事阴谋。而纳什I所幻想的三个人,对他的困扰最大的是那个神秘的黑衣人,国防部官员威廉·帕彻。他代表国家意志,把纳什I卷入了一场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巨大旋涡—正是在电影所提示的笼罩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让我们起初无从分辨纳什I所经历的究竟是真实还是他的幻想。
这是纳什I的幻想,是电影的虚构,但是,他简直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不过电影把这种幻想人格化了。在二战中,美国海军曾经将博弈论用于反潜艇战术;战后,美国海军通过资助组建兰德公司,继续支持此项研究,试图将研究成果用于外交和军事策略。一九五○年夏,纳什为兰德公司工作(他最重要的两篇博弈论论文发表于1950年和1951年)。当时,“整个国家越来越关注保守机密的问题,甚至到了一种多疑的地步……从一九五○年夏天开始,兰德就日益受到苏联人有办法弄到美国军事机密的恐慌情绪的影响”(P119)。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兰德公司对它所聘请的研究者相当宽松,没有严格的“业绩考核”,甚至也没有什么必须完成的项目,但是它的恐慌情绪免不了也会影响到纳什。一九五○年,正好是二十世纪的中点。这个疯狂的世纪,前半期的两场世界大战,后半期的一场冷战,轮番演示人类“理性的毁灭”(卢卡奇一本书的标题);而后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冷战中热核战争的危险,更是一度激化到了毁灭人类的边缘。在整个人类分裂为两大阵营的疯狂博弈中,纳什的精神分裂症只是沧海一粟。

至于后来的奇迹般的康复,通常都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突出强调他的内在因素:他那强大的理性。当然,这的确是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外部因素同样不可或缺:一九六三年离婚之后,艾莉西亚并未对他弃之不顾,而是一直收留他、照顾他;普林斯顿大学竟然也一直给他容身之地,继续聘用这样一位似乎已经失去正常研究和教学能力的病人。
博弈论
纳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他在博弈论上的贡献(他在数学上的成果实则远远不止于此)。博弈,就是赌博和对弈,人类从很早就开始玩的游戏。一九四八年,纳什进入普林斯顿读研究生。在一些同学的记忆中,“纳什把自己在普林斯顿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休息室里下棋了”(P72)。纳什I下过围棋,可惜无从确认他的段位/级别;而纳什II下各种棋,还自己发明了一种棋,用黑白两色的围棋子下。这些棋类游戏说到底都是计算,但是棋手(甚至包括棋类游戏发明者)所需要的数学知识可以非常有限:学龄前儿童就能学会围棋,而围棋大师用到的数学知识也并不比初学者多—这是题外话,却也可以说明,数学在现实中的运用,尤其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场合,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要说真正的数学上的较量,主要还是在数学领域。

一九二八年,匈牙利裔犹太人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博弈论正式诞生(约翰·纳什同年出生)。一九四四年,诺伊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car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发表,被称为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巨著,它把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纳什正是从这部巨著的瑕疵入手,撰写了后来成为现代经济学经典文献的《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和《非合作博弈》(1951)。简单说来,所谓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就是多人参与的非合作博弈中存在一个均衡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达成一种均衡,任何人改变自己的策略,就会降低自己的收益,这是对所有参与者具有约束性的最优策略组合。这是一个自然的静止点,它倾向于持续下去。在某些数学家看来,纳什均衡最让人入迷的还不是它可能有什么用处,而在于它的优美和普遍性。“其中的数学非常优美,在数学上简直是太正确了。”(P98)数学的真,同样呈现出一种数学所特有的美。本来,纳什早就有望获得各种奖项,包括诺贝尔奖和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但都由于他的健康原因而花落别家。直到四十多年之后,康復后的纳什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一起,分享了一九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从一九九四年到二○一四年,共有七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与博弈论有关。除了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之外,博弈论也广泛运用于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众多领域。
博和弈,本来就是竞争。多方博弈中的均衡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环境中,博弈者总是想要占据优势,最好是自己一家独大,赢者通吃;事实上,政治、经济、军事中的博弈所激发的欲望和恐惧通常也使得参与者别无选择,只能争取胜利或优势,而不是谋求均衡。由此,命中注定,“纳什均衡”常常陷于困境之中。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和影响力。它是一种数学模型。“所有数学模型的正当性在于,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是过分简化的、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还是能迫使分析者们面对那些在数学模型以外也许不会想起的可能性。”(P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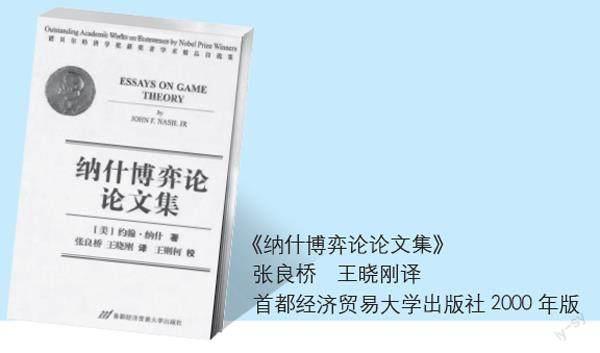
还有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博弈论也好,纳什均衡也好,其基本假设都是所谓“理性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尽管这个假设可以说是经济学不得不认同的奠基石,但是对它的质疑一直层出不穷,有人提出“有限理性人”的概念,有人认为过分相信理性不仅是经济学的缺陷,也是现代思维之大弊。人不能没有理性,但人又不仅仅是理性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包括友爱、信任、合作、包容、奉献、牺牲等,它们与公平、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都会对权力、利益斗争构成调和、平衡。
有意思的是,纳什证明了多人非合作博弈中存在着均衡点,而他本人的性格非常争强好胜,总要出人一头。纳什I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甚至还值得欣赏的范围之内;而纳什II确然有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个性,比如毫不遮掩地轻视不如自己的人,不会回答他觉得愚蠢的问题,会随时中断跟别人的谈话,一秒钟都不浪费。在他年轻时代的个人生活中,在他与他所交往的人之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均衡”这个词。后来,当纳什从精神分裂症走出来之后,他的性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自我贬低的幽默感表明了他有一种更加明确的自我意识;跟朋友们推心置腹地谈论伤心、快乐和依恋,显示了他的一系列更加广泛的情感体验;每天努力给予别人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且对他们向他提要求的权利表示认可,说明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冷漠而傲慢了。”(P494)一个人的才华与性情,得与失,乃至整个命运,似乎有一种无法以任何人的名字命名的均衡。
创造力
“在纳什看来,人生的基本乐趣来自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与别人的亲密关系。”(P484)尤其是在他的年轻时代,“他的压倒一切的兴趣在于数学形式,而不是人。他最大的需求就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强有力、无所畏惧、富于创造力的思维资源,在内部和外部的混沌状态中理出一些头绪。他明显缺乏普通人的需求,这在他看来就是令人自豪与满足的东西,这能进一步确定他是独一无二的”(P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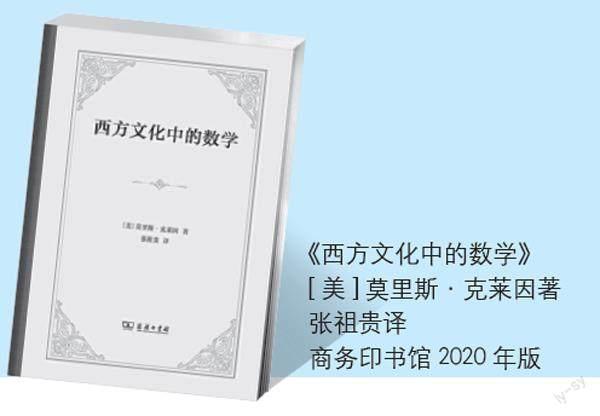
纳什II的创造力主要表现为数学研究中的直觉,简言之,就是在进行推导和证明之前,早就已经看到了结论。有不少大数学家就是这样工作的。一位数学家如此描述纳什:“他属于那种数学家,他们的才华当中最突出的部分在于几何方面的视觉洞察力。他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将一个数学问题看作一幅图画。数学家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有一个严谨的证明加以支持,然而这不是答案出现在他面前的方式。反过来,只是一堆直觉的细碎线索,有待缝合一处。有些早期的想法就是直观可见的。”(P145)这种“视觉洞察力”,或可称之为通常所说的造型能力,结合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人类早期并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些纷繁复杂的范畴、法则、逻辑等思维工具,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真是怎么赞颂也不过分的思想成果。不过,古希腊人还是认为,所有数学结论只有通过演绎推理才能确定,他们抛弃了过去数千年里的数学通过经验、归纳或其他任何非演绎法得到的所有规则、公式。“这样,我们将看到,与其说希腊人是在创建文明,倒不如说是在摧毁旧文明。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莫里斯·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如此说来,纳什直觉式的创造力就像是回归到了古希腊之前的人类思维的本源:那种“目击道存”式的思维运作,与纳什II的“视觉洞察力”有相通之处。或者说,纳什III很像那些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就能工作的哲学家。跟维特根斯坦一样,他也属于那种“给自己制造空气”的人;而纳什II“看书少得惊人”(P63),这一点也跟维特根斯坦一样。
另外,与这种直觉或洞察力相关,纳什II“喜欢具有高度普遍性的问题”(P31),而且他“随时随地准备发现问题”(P64)。也就是善于通过他所接触到的任何特殊性的问题,直接到达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具有穿透性的创造力,类似于艺术创作中塑造“典型”的方式。而纳什III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范例,说明真正的革命性的创新更多出现在基础理论研究,而不是应用性研究。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如此。也正因为纳什II关注高度普遍性,也就是高度抽象的问题,他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建立在大量材料和前人成果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不关注现实,恰恰相反,他强烈要求通过实践进行学习,而对单纯吸收知识深恶痛绝。
说到这里,或许可以回过头来调整对纳什III的一种偏见。确实,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对身边的人所在的这个世界毫不关心。只不过他以一种极不合常规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世界,以至于在别人看来,他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幸运的是,创造力反过来又会提高专注力,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修炼,也对纳什起到了保护作用。“具有科学天才的人,无论多么古怪反常,很少真的发疯,而这一点就是创造力可能具备保护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P16)

电影《美丽心灵》剧照,2001年
美丽心灵
如果不是(有意的)误译的话,“美丽心灵”是对传记和电影原题(A Beautiful Mind)的意译。“心灵”和“mind”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无须赘言。问题在于,这里的“美丽”(beautiful)一词,真的没问题吗?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的界定,于人所认识和欣赏的对象而言,“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有限性,也就是边界清晰的,确定的,让人可以理解和掌握的。古希腊人害怕那些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的东西。这种观念在西方影响深远。同时,包括古希腊人在内,人类又一直在试图采用各种手段,来提高自己的理解和掌握能力,寻求突破界限。数学就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与很多人一样,纳什II“一直认为宇宙是合理的……他认定万物都有意义,万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没有任何事物是随机或巧合的”(P21)。他想要用数学来解释一切,这无疑是一种谵妄。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人类还不足以认识、理解,更不要说掌握、控制,只能去欣赏、观照,努力有所体会、领悟。人类的内心世界,亦复如是。况且,作为认识手段的数学本身,其目的在于达到清晰、正确、完美的论证,却也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性的消失”(莫里斯·克莱因《数学简史》的副标题)。一切都会发展出对自己的否定。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理性会以自己的方式转身进入非理性。如此,所谓“美丽心灵”,不能只是一种静态的描述,它也必须意味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约翰·纳什与他的妻子艾莉西亚(Alicia Nash,1933-2015)
納什以他的康复证明,他做到了在这样的意义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本来,纳什I的精神分裂症也有它的“合理性”,可以视为“孤独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抑郁、迷惑以及毫无意义,而是超常知觉、过度敏锐以及一种不可思议的警觉”(P405)。根本用不着什么理论,纳什I幻想中的那个室友,有点像个浪荡子的查尔斯,可以理解为纳什I的另一个隐秘的、向往“放飞”的自我。同样的,那个小女孩玛西,则来自纳什I心中的某个柔软的地方,也许象征着一种依恋和被依恋的需要。无论男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最终,纳什I凭借极其顽强的理性,与他们达到和解,保持共存。这个结果意味深长。要是非得把他们完全清除干净,是不是也会对纳什I造成另一种伤害?也许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也许不会,因为他有妻子艾莉西亚—《美丽心灵:纳什传》一书是纳什的传记,作者却把它题献给艾莉西亚,无论如何,这是她应该得到的,正如纳什I在颁奖典礼演讲中对她的感谢和赞美一样。
就像柏拉图《会饮篇》里的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古老的说法: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不完整的,总是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纳什就是艾莉西亚找到的另一半。但是她未曾料想,她的另一半将会对她带来什么样的艰难。他们一九五七年结婚,一九六三年离婚。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艾莉西亚一直照顾着纳什。她的守护是不是可以媲美于珀涅罗珀的等待?他们于二○○一年复合,于二○一五年一起丧生于车祸—不管这是不是命中注定,反正,要说这是或不是不幸,都是可以的吧?那么,这是爱吗?大概只能说:是,而又不仅仅是。

电影《美丽心灵》剧照,2001年
电影或许美化了他们的关系,传记作者的评价则更为切实:“婚姻毫无疑问是人类关系中最神秘莫测的一种。表面看来肤浅的情感,可以变得惊人地深挚绵长,纳什和艾莉西亚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回顾往事,人们就会觉得这两人的结合并非偶然,他们确实都需要对方。”(P490)
准确地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互相错位的需要。事实上,人世间的爱情、婚姻,甚至在童话和神话故事里被祝福的两个人之间,大体都是如此。在电影中,爱情到来的那个夜晚,纳什I与艾莉西亚来到聚会的屋外,他握着她的手,指向夜空中的星星,描画星座的形状。这大概是电影中最美丽的时刻。一切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俩的情感体验是一样的吗?在多大程度?
也许,这样的追问会让人觉得大煞风景。但是,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从这个美丽的时刻得到更多的启示。在浩瀚的星空中找出一个星座,这暗喻着纳什的工作,从混沌中发现规律,揭示宇宙的奥秘,又或者是一些人想要对另一些人隐藏起来的秘密。只不过,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纳什I并没有特定的目的。他们只是沉浸在那个荷尔蒙荡漾的时刻,就像艺术家沉浸在创作之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努力想要从星空中看到命运,在那个时刻,纳什和艾莉西亚也许看不到他们的未来,但是他们在内心确认彼此。他们的心灵投射在星空,让那个时刻如此美丽,超越一切推理和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