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蒂姆·高特罗
程应铸

蒂姆·高特罗(Tim Gautreaux)
一
在我的翻译生涯中,邂逅蒂姆·高特罗是一个重要的坐标。那还是二十三年前我刚定居纽约不久。这年,因为翻译一本艾伯特·卢宾撰写的梵高心理传记,我常到各处书店翻阅有关梵高的资料,当时纽约的实体书店可不像现在这样凤毛麟角、难觅踪影,徜徉于不同的街区,随时可以撞见供你消磨时间的新旧书店。
一天我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去家附近的一家书店闲逛。我的关注点是美术类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儿子基于对美国生活的好奇,便在摆放美国小说类的书架前浏览翻阅。离开书店前,我见他手中还依依不舍地拿着一本书,他说这书挺有趣,想要买下,为了鼓励他的求知欲和学习英语的兴趣,我立刻慷慨解囊。于是这本书便成了儿子课余的捧读之物。
那时我的所有心思都放在自己心仪的梵高身上,对儿子挑中的这本书一点都没关注,只是觉得那书名有点怪怪的—Same Place, Same Things。心中唯一的疑团是这个书名到底是什么意涵,但无暇也没有心绪去解读它,至于它的作者蒂姆·高特罗(Tim Gautreaux)究竟何许人也,更是没有探究的兴趣。光阴荏苒,几年的时光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儿子也已离家进入大学深造,那本书就成了一个弃儿,静静地躺在家里地下室一个简陋的书架里,再也无人问津。
转眼到了二○○八年,在我回国探亲前夕,由于思乡情绪的纠缠,想用阅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于是目光落到了书架上那本儿子留下的Same Place, Same Things上。至此,我才知道这是一位美国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共有十二个故事,书名就是其中第一个故事的篇名。
开卷之后,我散乱的心立刻就被攫住了。它的第一个故事Same Place, Same Things在我眼底展现了巨大的张力: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中年农家妇女,长年以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却并不甘于死守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和死水般的日子,她的内心膨胀着出外看世界并改变自身命运的野心。她偶遇一个外乡来的修泵工后,认为这是一个离乡闯荡天下的大好机会,但是她的勾引不仅受到挫败,反倒让修泵工窥探到她丈夫系死于她的谋杀。然而,最后他仍未逃脱这个村妇狠毒而致命的一击。
接着是一个引起化学品爆炸并毁掉一个小镇的火车司机的故事(《晚间新闻令人胆寒》),他行车时因醉酒导致满载化学品的火车出轨,危急之中他选择逃离事故现场,躲进一家旅馆。从每天的晚间电视新闻中,他看到大火连绵不绝的可怕后果,在良心的敲打下,他决定投案自首,并让电视台实况转播了一场抓捕他的即时新闻。
看到第三个故事《赌桌上的调味酒》时,我再也无法自持,禁不住笑出声来。汽轮停泊后,七个无所事事的船员聚在船舱打扑克牌赌博,牌局上每人争相讲述了一个个听来的,或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故事。它们无不生动有趣,让人发噱而又深思。赌局结束时,作者借用一个赌徒幻念中的画面,向读者警示赌博带来的可怕恶果。这篇水手们一边赌牌一边讲故事的小说,立刻让我想起李青崖所译莫泊桑笔下浪荡水手的浪漫故事,那是我年轻时代最为钟爱的短篇作品。在这种情愫的冲击下,我的心飘飘欲醉,并且立刻有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要把这本小说集译成中文,以飨国内的文学爱好者。当时,根据第一篇故事的内容和意涵,几经斟酌,我决定把“Same Place, Same Things”译成“死水恶波”。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本书的作者蒂姆·高特罗是难得的故事天才,他的小说主角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态和现状,而且无不展现了作者的审美原则和道德高度,潜移默化地予人向善的教益。他对故事的编排常常如平地惊雷,给人一种始料不及的心动。他的语言朴素、简练、诚恳,既有浓厚的乡土味,又有一种高雅的书斋气息。他的作品犹如一枚枚产于旷野而又经过精心打磨的玉石,既难掩它自然天成的质地,又随时可见作者雕琢磨制的功力。
带着这样的印象,我对作者蒂姆·高特罗作了深入的了解。让我倍感亲切的是,他竟是我的同龄人,我们在地球的两个不同的角落同步经历着时光的冲刷。他成長于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摩根城,长期在故乡的大学教授文学创作,同时坚持写作。这时他已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死水恶波》《融入孩子》)和三部长篇小说(《下一个舞步》《林中空地》《失踪》)。他的短篇作品连续多年被刊入《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和大学文学教科书。他的长篇小说也在美国获得过许多奖项。
就这样,我以极大的热忱,摆脱了思乡病的干扰,投入到《死水恶波》的译事中。到二○○八年十月我启程返沪之前,我已译毕该书的前四个故事。本打算回美国后继续工作,然而命运弄人,在我满载着友人的情谊返回纽约的第二天深夜,一个越洋电话把我惊醒,电话线那端的朋友悲痛地告诉我,前几日还相聚畅聊的朱家玮兄在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弃世。我犹如遭到致命一击,陷入失友的巨痛中,万念俱灰,扔笔弃纸,此前翻译《死水恶波》时的满腔热情荡然无存,译事处于停顿。我认为生命也罢,文字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而无意义的。但在这种颓靡不振之中,上海相聚时,朱家玮兄聆听蒂姆·高特罗的故事时殷切的眼神每每在我脑海闪烁,那是一种对朋友的真诚期待和鼓励,是我振作起来的唯一动力。于是沉寂数月后,我终于重返《死水恶波》的翻译工作。后来我很喜欢的那篇《赌桌上的调味酒》刊登在了二○一一年九月号的《重庆文学》上,这是蒂姆·高特罗的作品首次面对中文读者,也无疑是命运对我的极大馈赠。
二○一三年三月,《死水恶波》顺利付梓,蒂姆·高特罗的故事构建能力、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受到读者的青睐和文学界的关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子夜书社”读书节目曾作过两次专题广播,朗读和讨论其中的篇目。从此,在中文读者的视野中,又多了一个闪亮的名字—蒂姆·高特罗。
二○一八年初,蒂姆·高特罗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信号》在纽约问世,中文版翻译的工作又一次落到我身上,我再次沉入到蒂姆·高特罗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的小说框架之中,再一次细细品味他既朴实、淡雅,又幽默、机锋并且饱含泥土气息的文风和语境,再一次和他笔下的一个个芸芸众生共享喜怒哀乐。
《信号》共收入蒂姆·高特罗的二十一个短篇故事,其中十二个是新作,其余九个精选于他的第一个短篇集《死水恶波》(三篇)和第二个短篇集《融入孩子》(六篇),因此,该书堪称是他短篇小说的一个概括,反映了他短篇写作成就的全貌。
我想,作为《死水恶波》和《信号》两书的译者,是时候就作者的写作风格与读者分享一些自己的体会了。
二
蒂姆·高特罗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这源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他一九四七年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摩根城,在当地读了十二年天主教教会学校后进入该州的尼科尔斯州立大学,四年后毕业,又入南卡罗来纳大学深造,取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然后返回路易斯安那州,在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文学创作长达三十年之久,二○○三年退休后担任该校的名誉教授和驻校作家。
纵观高特罗的经历,除了短暂的三年研究生生涯外,几乎一直在美国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生活和工作,他熟悉那里的生活和文化,也挚爱他的乡土、乡人和故乡的风物,所以他虽然身居学院却能写出具有浓郁南方乡土风味的作品。他的小说大多以该州为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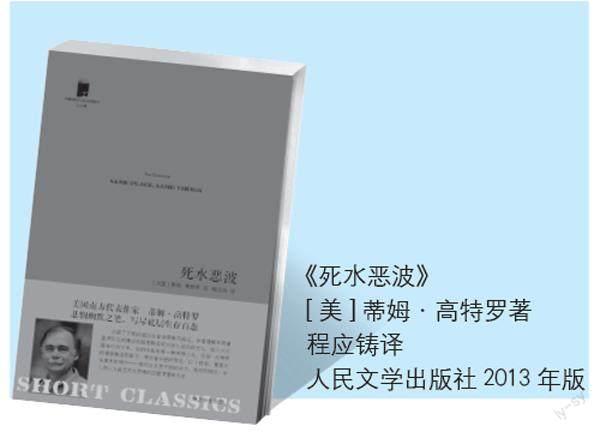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颇为落后,以农业为主,民风比较朴实淳厚。其中百分之四十的面积为法裔区,早年这些地区盛行法语,如今法语虽然逐渐式微,但当地的法裔依然坚守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坚守他们的语言、音乐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传统。故而,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一个非常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地方。比如高特罗经常写到的新奥尔良市就是一座具有特別文化气息和民俗风情的城市,除了具有浓郁的法裔文化气息外,还具有多元化的国际特色,它距高特罗的居住地哈蒙德城仅一小时的路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盛事,其时,全城三四十个乐队会在城里大大小小的酒吧和俱乐部狂欢演奏。高特罗对这样的文化氛围非常倾心,他说:“那就是新奥尔良的象征。”他特别喜欢去一个由四十年代保龄球馆改建而成的俱乐部,那里演奏的音乐是一种多元的混合,融合了白人音乐、美国黑人音乐、法国黑人音乐、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的音乐。这里还时时可以看见非裔美国人,他们头戴牛仔帽,说法语,演奏手风琴,这些都是只有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才可以见到的人文和风情。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这种地域文化对高特罗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把那些故事场景表现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一位评论家说:“看完高特罗的小说,就像看完一部日场电影后进入到阳光之下,这时你会觉得你进入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而剧院里的那个世界才是真的。”
在高特罗的小说里,也时常出现一些流行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特定用语,这更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地域特色。他说:“如果你要准确地为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写真,你就必须关注那个时代的语言模式,熟知当地的方言、习语和谚语。你必须诚恳真实,这是一个作家务必考虑的事情。”
《柯克斯书评》针对他的短篇小说集《死水恶波》说:“这部甫一面世就震惊当今文坛的小说集出自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作家笔端,由于他对劳动阶层抱有极富同情心的理解以及他深受当地法语土著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在同时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作家和评论家苏珊·拉森在《皮克云时报》撰文说:“绝妙的故事—这些以不同时间和地点为背景的故事……无不带有浓重的家庭、地区、种族和宗教特色,那是所有南方小说赖以成功的根本。”
由于高特罗笔下所表现的地方特色,有些书评家将他称为“南方作家”。对此,高特罗幽默地说:“‘南方作家 这个标签令我望而生畏……我宁可将它稍作改动—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作家,我生活在南方。如果我出生在北达科他,我还会是一个作家,我可能会有相类似的生活,但是我笔下的人物、环境、氛围、气候以及水路航道会来自北达科他州或南加拿大,我仍然会写出东西。”又说:“无论你诞生和成长在何地,它都会对你笔下的小说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他说得对,他首先是个作家,所以虽然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但是他的读者却没有地域之分,他的作品广受各地的读者青睐。
除了地域的影响,高特罗的家庭背景也是左右他写作的一种力量和灵感来源。高特罗是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他的先人在一七八五年自法国移民而来。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穿梭于水路航道上的拖轮船长,家里希望高特罗能够子承父业,延续这个他们引以为荣光的职业,而高特罗却走上了自己的文学之路。父辈生活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里有着明显的痕迹。他得心应手地描写水手生活。《赌桌上的调味酒》就是一篇以水手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小说中的环境氛围和那些鲜活奇趣、出自船员之口的故事显然和高特罗童年受到父辈职业生涯的熏染有关。高特罗回忆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我周围生活着许多长辈和亲戚,他们反反复复向我讲述有关他们的职业、地区谋杀案、警察、癌症、私刑杀人,以及建造锯木厂、修理蒸汽机、烤猪肉中毒、杀鸽子、祈祷、坐雪橇滑冰、乘汽轮航行、焊接等方面的趣事。”后来,这些长辈们口传的故事都渗入到他的作品之中。《死水恶波》中《思想的领航员》一篇也是一个以水手为主角的故事,只是这些水手原先是大学里的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把父辈的船员生活经历和他本人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体验糅合到一起。高特罗说,他小说里的很多情节“都是来源于我幼时所听到的无以数计的故事和传说”,“促使一个孩子成为作家的先决因素就是懂得记住每一件事的重要性”,“小说的精髓来自屏住气息地倾听”。
高特罗作为教文学创作的教授,出于职业习惯和责任感,对自己的写作十分严谨。他从不让自己的作品仓促、草率地问世,往往数易其稿,修改、增删、润色,仿佛永不满意。他有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当完成第一稿的时候,觉得自己只是刚刚进入一个漫长、黑暗、烟雾弥漫的隧道,于是自然就有了第二稿。然后让妻子过目,根据她的意见便有了第三稿,然后将稿子送到经纪人手中,其结果便导致了第四稿。然后出版社买下版权,于是就有了第五稿以及做最后两次润色的第六、第七稿。终于摆脱它的纠缠,回转身来捧读第一个精装版封面的印刷样稿,当看到第六页的某处时,又会脱口而叹:‘唉,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怎么会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两个词…… 所以,它永远不会结束,你也永远不会产生‘这是伟大杰作之类的感觉。”
高特罗有两三部长篇小说成稿后,因为觉得不够完善,至今搁置在家中阁楼无意发表。他说他认识几位身负盛名的作家,他们每个人都有几部手稿被自己扔到壁炉里化为灰烬。他很推崇这种严格苛求自己的写作态度。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下一个舞步》的初稿中,高特罗花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篇幅来描写洛杉矶的生活场景。原因在于高特罗经常和妹妹去加利福尼亚度假,自认较为熟悉那里的生活形态。但后来,一位来自洛杉矶的编辑告诉他,他的描写和当地的习俗不甚相符。这引起高特罗的警觉,于是一改再改,并忍痛割爱,删了又删,最后有关加利福尼亚的内容被浓缩到仅占全书的百分之七。他在写作上的一丝不苟,由此可见一斑。

勤勉不懈是高特罗追求的境界,他说:“我经常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天分的歌手和舞蹈者,你不去唱歌和舞蹈的话是极大的错误。我认为文学家和艺术家同样如此……”
高特罗的写作道路漫长而艰辛。他先是作为一个诗人而崭露头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写短篇小说,他表示:“短篇小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表现形式。”然后再写长篇小说。他说:“长久以来,我必须写大量的文字来证明我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教授的存在……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使自己对作家和教师的工作应付裕如。需要不断地争夺时间,但即便你手不辍笔地写作,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假以漫长的时日。” 他曾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成为一个作家的不易—他退休前,在学校邮筒里收到的最后一封邮件是一本美国作家的诗文选集,它的最后一部分是美国新生代作家的作品。高特罗仔细阅读每位作家的小传,发现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出生于一九四九年。他感叹地说:“这就说明,要成为一个娴熟驾驭文字的作家,其道路是何等漫长!”
追求真实是高特罗的另一个写作原则。为了追求文字表达上的真实感,他常常身临其境,深入地体验生活。他的长篇小说《林中空地》中有一个演奏手风琴的片断,为写好这个章节,他花了五十元从网上买了一架二手手风琴。他将这个硕大的手风琴挂在胸前,专注地学习演奏一首名为《西班牙女郎》的乐曲,最后,他说手风琴“擦破了我的背,扭伤了我的肩膀,我的手指被它左边的一百二十个黑色琴键搞得忙乱不堪”。
高特罗的小说里有诸多关于机械装置的描写:火车制动器,汽轮的动力装置,修泵的焊接工具,锯木厂的鋸木设备,等等。这些描写无不来自他的生活体验。他自己说,他对机械装置有一种说不出原因的痴迷,他常常会亲手将割草机、拖拉机、蒸汽机拆卸解体,了解它们的构造、工作原理,然后进行检修,以期让它们获得更好的运转效果。这种生活体验使他可以在小说中对此类情景做出神入化的描写。
高特罗在文学创作课程的教学中,一再强调深入生活和熟悉生活的重要性,他经常要求学生去沃尔玛超市观察那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商品,他说那是故事的绝妙源泉。
难怪美国著名作家詹姆士·李·伯克评论高特罗说:“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我可以坦诚地说我爱读他的小说,他从不夸大其词地故作惊人语,他从不对读者煽情,操弄他们的情感于笔端。尽管如此,他总是能牢牢捕获读者的心。”
作品的价值观是高特罗甚为看重的,他说:“没有涉及价值观问题的小说是不会引人关注的。”对于高特罗的短篇小说集《死水恶波》,《出版者周刊》如是评论:“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些充满戏剧性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高特罗对他的人物所倾注的感情始终浸染着闪亮的希望和救赎的热望。”《南方生活》则说:“(这些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提醒我们,是怜悯和仁慈使得平凡的生活得以安然度过。”
在这两本小说集里,高特罗的故事主角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物,他们是水手、机车手、灭虫人、水泵匠、修炉人、驾驶员、农夫、农妇、锯木工、钢琴调音师、废品经营者、流浪汉、鳏夫……所发生的故事也极其平凡,但是它们被作者提升到一定的道德高度,从而被赋予不平凡的意义。
这些看似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故事,通过高特罗朴实而又生花的妙笔,被转换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俗图,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南方腹地的民俗风情和道德风貌。其中,人物彼此之间以及同一个人物的内心深处,无不纠结着是与非、正与邪、良知与恶习、高尚和卑微、担当和逃避、坚持和放弃、真诚和虚伪的对抗,乃至道德观和价值观层面上细微而不显形迹的矛盾冲突。令人读罢免不了掩卷深思,余味不尽。
当然,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不等于布道和说教,它还意味着以某一种语境来关注世界,并告诉我们有关它的故事。高特罗将他摹写生活的创作与他的责任做了最好的平衡。
对于自己的写作活动,高特罗把它们既当作是一种享受,又当作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一旦我进入写作状态,我将其视为享受,然而由于我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兴趣,要我重复地专注于某一件事很是困难,所以我必须依赖责任感。”“是否你认为我有了足够的钱,我有了摘取到的美丽桂冠,所以我可以放下写作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可以那样想,那也很自然,但这样做会使我产生一种罪恶感,因为我没有付出我应该付出的。”他还说:“你必须利用你的天资,不管它是什么。这就是你坐在电脑前面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做,你的感觉会很糟。”
本文引用的蒂姆·高特罗话语译自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及帕姆·金斯伯里(Pam Kingsbury)对他的访谈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