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上的卡夫卡
褚孝泉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托马斯·曼善于捕捉人的神情,他看了卡夫卡最后的那张相片,觉得已经四十多岁的卡夫卡看来像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大孩子:“一张稚气、羞涩而肃然的脸庞。”而同为犹太裔的卡内蒂是这样描写卡夫卡的:“他身材矮小,步伐迟疑,好像脚下的地面很不可靠。和他在一起时,你不会因他而激动。他摒弃了诗人常有的那些幻想和声势,诗人们的那种光彩,在他的语句里踪迹全无。”卡夫卡的同代人给他画的这幅肖像是意味深长的,不仅写出了这位作家个人体魄的特征,也很能传递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精神。正是这个瘦小个子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留下了巨大的身影。在弱小和伟大之间我们不仅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更值得留意的是,卡夫卡的这个瘦小的身躯富含着象征意义,从中我们能看到西方现代文学不同于以往文学传统的深刻变迁。
卡夫卡在短短的一生中创作的作品并不多,其中大多还是未完成之作,然而,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作家中他特别引人注目。卡夫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创作的文学意象和情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显示了现代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和命运,他的表达方式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事实上他的文学创作标示着一种新的文学的诞生。他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和内涵,是与卡夫卡对文学本质的看法以及他对艺术的看法密切相关。
卡夫卡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他白天是一位勤勉的保险公司职员,晚间和业余时间投身于写作。公司的事务只是为了谋生,文学才是他真正的事业。他在给未婚妻费里斯的信中说:“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文学就是我的一切,除了文学我什么也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别的什么。”(本文中的引语均为笔者自译)他在日记中也写道:“我在福楼拜的书信中读到,‘我的小说是座悬崖,我就悬挂在悬崖上,世上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这很像我在五月九日为我自己写的内容。”福楼拜的话引起了他的共鸣,因为和福楼拜一样,卡夫卡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成为一个艺术家,文学是他选择的艺术形式,文学的艺术是他回应人生挑战的唯一方法和途径。然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呢?他是怎样看待艺术的呢?这是理解卡夫卡的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卡夫卡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不同寻常的看法,这直接导致了他文学创作的独特品质。
卡夫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生平和创作到处都显示着悖论。尽管卡夫卡如此热爱文学,把一生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但他同时看到在他的时代艺术不是或不再是一种神圣崇高的事业。卡夫卡写过三篇描写艺术家的短篇小说,这三篇小说都在他生前就发表了,显然他认为这三篇小说足以体现他的思想。第一篇题为《第一场痛苦》,描写的是一位高空走绳索的杂技演员。这位演员专心于他的艺术,全副精力都用于完善他的技艺,他整天生活在杂技团大棚的最高处,只有在杂技团巡演时他才不得不落地,非常不情愿地和剧团经理一起乘火车去下一个演出地点。在一次旅途中,他忽然提出要经理给他在高空布置两根绳索,经理马上答应了。但这并没能使得这个高空艺术家安静下来,他越来越焦虑,甚至哭了起来,说:“我没法这样活下去了。” 第二篇題为《饥饿艺术家》,讲述的是一位表演忍饥能力的演员,他能够在众目监视下,保持几十天不进食的纪录。然而,观众对这种耐饥艺术的兴趣没有保持很久,他在几乎被人忘却的情况下,饥饿至死。第三篇是卡夫卡的绝笔之作,是他逝世前的最后作品,题为《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讲述的是一位歌唱艺术家,尽管她的演唱会很受欢迎,但是她就她的艺术的价值和大众发生了争执,在没能让大众信服之后,她不知不觉地就在大家的眼前消失了。


卡夫卡描写的这三位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艺术尽管能一时赢来掌声,却并不能永远为观众所赞赏。高空绳索上的艺术家尽管表演的是“人所能及的难度最大的艺术之一”,但是因为常常使观众在看别的节目时分心而成为剧团经理烦心的原因。饥饿艺术家具有远远超出常人的不可思议的耐饥能力,但是这种耐饥表演的风尚一过,这位杰出的饥饿艺术家只能加入一个马戏团成为那里的一个无人关注的余兴节目。女歌手约瑟芬的歌声很受欢迎,但大众拒绝让她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他们认为来听她歌唱已经是厚待她了。
卡夫卡笔下的这些艺术家,与西方传统中受崇拜的艺术家形象截然不同。在传统中,艺术家一直被视为天之骄子,是些超群绝伦、禀赋非凡的巨人。这个传统来自古典时代,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苏格拉底让他的对话者相信,艺术家的出色表演能力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什么艺术法则,而是来自神赋的灵感,就像磁石让铁悬浮空中,文艺女神缪斯让艺术家超出常人。当抒情诗人吟唱时,他们不再用自己的理智,而是被神附了身。伟大的诗句不是诗人们创作的,而是神通过他们之口传给世人的。艺术家是人和神之间的媒介。
古典时代以后,艺术家的地位仍然崇高,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同时为教会、国王贵族和大众所仰慕。如果说苏格拉底认为艺术家是在替缪斯代言,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则认为艺术家具备了和上帝一样的创造力,因此常常能听到“神圣的米开朗琪罗”这样的称呼。
一直到十九世纪,欧陆的艺术家们仍然是社会上不同凡俗的一个群体。雨果就凭着手中的一支笔,可以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对决,最后还是雨果赢了。巴尔扎克声言,他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用剑没能达到的伟业。歌德为人谦逊,这并不妨碍他被整个德国民族敬仰。勃罗德在他的《卡夫卡传》中说到,卡夫卡对歌德有着非常特别的热爱,认为歌德生活在一个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
但是,卡夫卡及早地看到,这样的艺术家时代过去了。到了卡夫卡的时代,到了现代,艺术家不再可能这样卓然特立地现身于世间了,卡夫卡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个变化。我们知道,卡夫卡的作品几乎都和他自己的身世感触密不可分。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从自己日记里的片段演绎而成的,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有自己的身影。这三篇艺术家的故事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在这三个寓言式的故事中,不仅大众不再崇拜艺术家,艺术本身也不再是什么瑰丽的珍宝。高空杂技的艺术难度惊人,但是艺术家太投身于这项艺术后,他在乘火车旅行时居然必须躺在悬空的行李架上才安定,艺术使他失去了在平地生活的能力。饥饿艺术家在被人忽视而死于饥饿时,对围观的人说他之所以从事饥饿表演,是因为没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这个解释完全否定了他从事的艺术的内在价值。约瑟芬的故事更是将艺术置于可疑的地位,因为贯穿故事的一个主要疑问,就是约瑟芬表演的到底是真正的歌唱,还是人人都会的吹口哨?也就是说这个明星艺术家的艺术实际上可能就是个日常小技藝。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遗嘱执行人勃罗德把他的手稿付之一炬,这并不是出自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偏执。他根本就认为文学艺术不是什么值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伟业。艺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柏拉图以来的魅力,只是现代社会荒原上的一片石壁悬崖。
卡夫卡文学人生的矛盾性就来自他面临的这个现代困境。他从事的艺术已经不可能像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的艺术那样出入历史风云;他内心太真诚严肃,不愿也不会像王尔德那样把艺术当作炫露才华的手段;他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更不愿追随着时尚改变自己,他故事里的三位艺术家都不肯因为时尚的变迁而放弃或改变自己的艺术。在这三个故事中,艺术只对艺术家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是个可以生死相托的事业,但对社会、对世界,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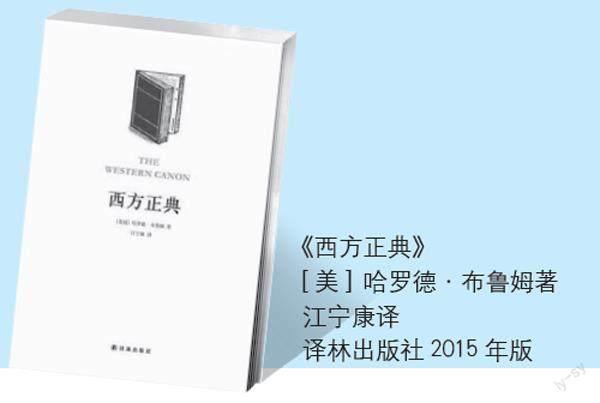
当代世界的艺术家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绝望的境遇,但是,当你读卡夫卡的作品时,你感到的不是绝望,不是黑暗,而是一种冷静的勇气。艺术不再重要,但是艺术仍然可以是个人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卡夫卡对艺术的这个看法以及他据此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因此触动了同时代人心灵的最深处。奥登有个著名的评判,他说:“如果要举出一个艺术家,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堪比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关系,首屈一指的当是卡夫卡。”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里说,从纯粹的文学角度看,卡夫卡是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预测,如果到了二十二世纪还有文学读者,他们或许会把卡夫卡比作我们时代的但丁。卡夫卡研究权威罗伯逊指出,卡夫卡之于二十世纪,就如同拜伦之于十九世纪,最能描述一个时代的形容词,在十九世纪是“拜伦式的”(Byronic),在二十世纪就是“卡夫卡式的”(Kafkaesque)。拜伦是位桀骜不驯蔑视俗规的贵族,要以一己之力来为希腊争得独立,卡夫卡则是一位连对婚姻都充满疑惑和恐惧的业余作家。从“拜伦式的”十九世纪到“卡夫卡式的”二十世纪,这两个时代之间发生了断崖式的巨变,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是这个巨变的最具表现力的见证。
卡夫卡将艺术和艺术家请下了神坛,然后又把毕生全部精力献给了艺术,这似乎充满了矛盾;把作品有限的卡夫卡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而不把这个殊荣归于创作了鸿篇巨制的普鲁斯特或乔伊斯,这似乎也是个悖论。常常有评论家说,卡夫卡艺术的特色就是矛盾、悖论、荒诞和不可理喻,这样说只是描述了表象而没有说明为什么卡夫卡是卡夫卡。什么是他的艺术的内在逻辑?为什么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对当代人有如此的吸引力?阅读卡夫卡总是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而释读卡夫卡常常会让人陷入困境,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卡夫卡,我们就能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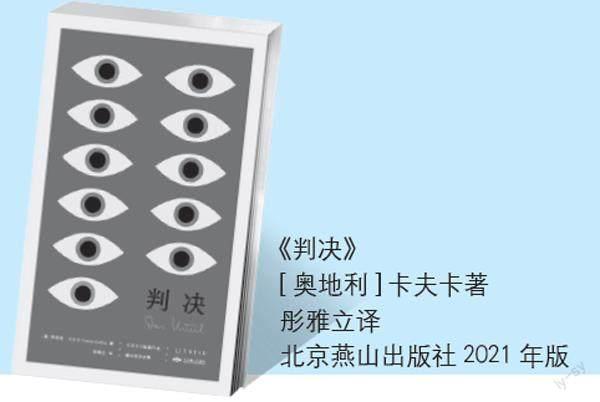
卡夫卡的一生无甚大事,白天他勤勤恳恳地做他保险公司的工作。但是卡夫卡绝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庸人,他毕生的挚友勃罗德说,卡夫卡永远在寻找着真实,从每一个细节来认识来自真实世界的真理,由此他具有直面现实的执着的真诚。这使得卡夫卡从不沉溺于幻想,或许世界上最不认为卡夫卡是天才的就是卡夫卡自己了;看出现代社会里艺术和艺术家真正地位是什么的,正是卡夫卡锐利的洞察力。他厌恶自欺欺人,总是在现成的假象下揭示出生活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卡夫卡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出生于布拉格;而我们知道的作家卡夫卡则可以说是诞生于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这天晚上十点,他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准备写点什么,突然,长期酝酿在他心中的一股力量爆发了出来,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挥笔直书,一口气写了八个小时,到次日清晨六点,一部完整的作品像十月足胎的孩子来到了世上。卡夫卡小说艺术的一切特点都在里面了。这就是他的那篇一直在使人惊异的小说《判决》。
就像卡夫卡其他的小说一样,《判决》的故事并不复杂。格奥尔格是一位年轻的商人,他继承自父亲的生意很兴旺,又刚订了婚。于是打算写信把婚事告诉远在俄罗斯的一个朋友。信写好以后,他走进父亲的房间,准备让父亲读读这封信,因为他父亲也认识他的朋友。不料父亲突然开始指责他的种种不是,最后以父亲的权威判处他溺死,他果然冲出家门跳进河里自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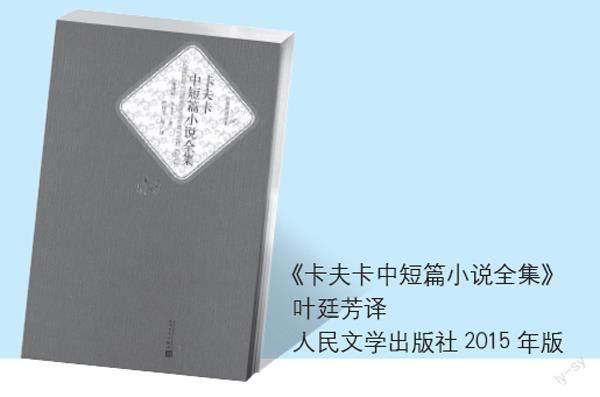
这篇小说篇幅不大,但是小说中出场的和不出场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包含了现代人生的所有关键因素。他和他父亲,他和他朋友,以及他和他的未婚妻,构成了无法协同的三角关系,原来相安无事的父子和友朋关系,因为未婚妻的到来而彻底破裂。按卡夫卡说法,是未婚妻导致了格奥尔格的毁灭。冲突的最后是走到了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生和死,格奥尔格溺死的同时瞥见桥上的车流交通,按卡夫卡自己的解释,那是出生的开始。
在这整个故事冲突中,格奥尔格总是弱小的一方,在父亲高大的身影和严厉的训斥下,他完全不知所措,毫无抗拒地执行父亲的判决;在和他远方朋友的交往中,他一直在犹疑,什么能告诉朋友,什么不能告诉,老是担忧会得罪朋友;在和未婚妻的关系中,他也是受指责的一方。弱小,是卡夫卡自我意象最恒常的特征。《第一场痛苦》中的高空飞人稚嫩得就像个孩子,经理担忧地看到“最初的皱纹爬上了他孩子般平滑的额头”。饥饿艺术家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的,就是他的虚弱,他能保持四十天的极度虚弱。歌唱家约瑟芬为了获得观众的支持,做出受伤而必须让助手搀扶着上场的姿态。卡夫卡其他更著名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弱小无助。当卡夫卡以动物来寓言人类时,他选择的也是比人更低下的弱小生物,《变形记》里格列高尔变成了一只爬虫,约瑟芬属于耗子民族。十九世纪文学热情描写的巨人和英雄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不见踪迹,成长小说里通过磨难达到救赎的历程也无从起步。弱小无力成了现代个人无可逃逸的命运。比起他同時代的作家,卡夫卡最早地感知到了在作家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这种嬗变。他在最后的日记里写道:“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打破了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一切障碍打破了我。这个‘一切是我们共有的。”
面对这样的无可逃逸的生存境况,该怎么回应呢?卡夫卡以为,“有两个可能性:变得无限地小,或者本来就小。第二种可能性很完美,但无所行动。第一种可能性是开始,是行动”。如何行动呢?他在日记里自问自答:“你建设什么呢?我要挖个地下通道,必得有这个进展,我在地上的位置太高了。”文学的可能性不再来自高瞻远瞩俯视众生,而是来自挖掘出最微小最低下的生存意志,因为这样才能达到他所希冀的“不可被摧毁”。
卡夫卡认同弱小,这自然与他个人的心灵历程有关。他自述一生处于强势父亲的阴影下,在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他以非虚构的方式把这一点表达得很直白;在虚构的《判决》中,故事的驱动力的源头也是父亲。这来自卡夫卡自身的经验,然而卡夫卡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样的无法抗拒难以理喻的威权并不止于父亲。在《审判》《城堡》等其他作品中,无名的威权笼罩着人生,置人于绝境的是某种无处不在却隐身不见的主宰力量,这恰好与人在现代的处境若合符节。现代社会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在操纵着你的命运,个体的人都原子化了,没有了互相间的牢固纽带,不可抗拒的利维坦高居社会之上,不管它的名字是什么:官僚制度、无意识、国家机器、大资本、组织、结构……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之所以能打动当代读者的心灵,就是因为在他创造的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无法规避的某种本质性的现代存在。
卡夫卡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是他并不提供任何解说。自卡夫卡的作品问世以来,对他小说的含义的解读层出不穷,几乎所有当代流行的文学社会理论都曾被用来解释卡夫卡,当代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也几乎都对卡夫卡的作品提出过他们的诠释。但是,所有这些理论性解释似乎都不乏可商榷之处。
将卡夫卡列为荒诞派作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初涉卡夫卡的作品,会觉得这个评判很恰当。卡夫卡会运用非常突兀而奇特的叙事手法,在《判决》这个故事中,前大半的情节发展完全按照日常逻辑和现实理性,在临近结尾的时候骤然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衰老的父亲翻身起立,不合常规的非理性的变化出现了,儿子被父亲的一句话而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熟悉的庸常生活突然滑脱出了轨道,读者惊愕地看到格奥尔格跳入河中,一个大大的问号跳入脑中:“真的?”《判决》的这个叙事结构其实和卡夫卡更著名的小说《变形记》的结构是对称而相似的。只是在《判决》中,现实的叙事发生在前半部分而结尾时转入非现实的事故;而在《变形记》中,超现实的事故发生在故事的开始,格列高尔一夜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后续的故事则遵循着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假若你家藏着这么一只大甲虫,你的应对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荒诞指的是常规的思维和行为逻辑的消失,你无法对发生的事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卡夫卡的故事并不是荒诞的,基本上都合乎寻常的生活轨迹。卡夫卡思考他写作的目的时说:“只有当我能将世界升华到了纯粹、真实和永恒的境界,我才会觉得幸福。”这个文学目的与荒诞派或超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只要比较卡夫卡的叙事和《等待戈多》《秃头歌女》这样的作品,就能看出他虚构的世界和荒诞派的世界图像是非常不一样的。卡夫卡作品中的所谓“荒诞”色彩,其实是他在使用寓言手法,他的独特之处是打破了文学类型的规范,在同一个故事中穿插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这给读者带来了冲击性的阅读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早期的作品中还经常想象出噩梦般的情节,就像在《判决》和《变形记》里那样;到了他后期的作品,这样的超现实的情节越来越少了,他越来越着眼于从日常理性的经验中揭示生活的深层含义。即便像《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这样一个故事,除了题目和叙事过程中的极少的几处暗示,他写得完全像是寻常人的故事,而不像是个离奇的耗子歌唱家和她的啮齿类听众的故事。同为捷克人的昆德拉曾指出,西方评论家不了解捷克文学的传统,以为荒诞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特色,事实上使捷克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卡夫卡作品中的写实因素。
为何卡夫卡能在对寻常经验的书写中演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来?作家的创作都来自生活的经验,对经验的不同的剖析理解和采取的表述方法构成了不同的文学特性和流派。文学评论家们一直试图将卡夫卡归入某个我们容易理解的文学流派中,但是卡夫卡最终越出了任何类别或流派的畛域。卡夫卡处于十九世纪文学进入尾声而二十世纪文学即将谱出序曲的转折关头,以文学为业的艺术家在这个正在到来的未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卡夫卡的天才在于他对未来有一种迥异寻常的把握方式,卡夫卡是位属于未来的作家,属于那个酝酿着噬人巨流的二十世纪的未来,但是他不是直接经验这个未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或许,我是首先通过理智和愿望来认识未来的冷酷轮廓的,然后在理智和愿望的牵引和推动下再走进这个未来的真实之中去。”这个感悟了以后再经验的未来是个什么样的未来呢?这个未来不是过去的延伸,不是构筑在记忆上的,他感知到的未来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前景。女歌手约瑟芬只是吹吹口哨但是她坚持要人们给她不劳动的特权,听众们似乎离不开她的演唱会,但是坚持不答应她的要求,艺术家和大众纠缠在承认还是不承认艺术的重要性的争执中,最后艺术家退让了,约瑟芬消失了。卡夫卡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最后一节里写道:“或许我们并不会有太多的缺憾,约瑟芬从尘世的劫难中被解救了,她以为这个劫难是为天选子民所预定的,她将幸运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无数的英雄之列中;因为我们不创造历史,很快地,她将和她的兄弟们一样在更高的解救中被遗忘。”艺术家被救赎了,但也被遗忘了。卡夫卡清醒地理解并准备好去经受这个艺术家的未来。
这个并不辉煌的未来没有使卡夫卡失去对文学的热忱。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来获得救赎,他不担忧被遗忘,遗忘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救赎他的觉悟只是他个人的觉悟,是他弱小的个人的认识,世人期待的宏大的真理是无法在他或任何其他艺术家的创作中陈说出来的。对此的思索导致了他对文学本质的独特见解。卡夫卡写道:“作为谴责而表述出来的文学是如此强力的一种言语的减缩(Sprachverkürzung),它渐渐地导致了思想的减缩(Denkverkürzung)—从一开始大概就是有这个意图的。这种思想的缩减妨碍了正确的视角,让谴责远离目标而失落在一边了。” 卡夫卡对文学的这个清醒而毫不乐观的看法与他的文学前辈和后来者对文学的信念迥然不同。普鲁斯特以为可以用文字在回忆中织出一幅生命的全息图像,乔伊斯认为他通过文字的秘径揭示了意识的深层底蕴。他们都相信文学的魔力,相信文学能够拓展思想,不会认可文学的这个“减缩”(Verkürzung)的宿命。
二十世纪很少有作品具备卡夫卡艺术的这样一种独特魅力,促使你不断地回到他的作品中去感受世界。一个来自世纪末的奥匈帝国的边陲小城的作家,一个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不再抱任何幻想的艺术家,却创造了这样一个意象的世界,能让现代人在其中看到自己,看到当代个人的命运,看到生存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卡夫卡为现代世界的艺术家创作了毫无夸饰的画像,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艺术家,然后他在他挖出的地下通道里创造的艺术成了最具现代性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