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如茶”蠹测
周朝晖
一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达到的两座高峰,这是文学史的常识。但唐诗和宋诗相比如何呢?元明清以来,似乎“崇唐贬宋”,认为宋诗的美学价值远远无法和唐诗相提并论的议论占了主流。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都已经被唐诗写完了。”言下之意,诗歌留给宋人挥洒的余地已经很有限了。倒是钱锺书持论较为中肯,他推崇唐诗,也肯定宋诗的独特价值,如《谈艺录》中就有这样的见解:“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在《宋诗选注》中,钱先生更为宋诗说了不少好话,大约这也是至今只要论及宋诗,就或多或少要提起钱锺书的一大因素吧。

研究中國文学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评论唐诗与宋诗的不同特点时,写道:
唐诗如酒,宋诗如茶。正如唯有酒客才知道酒中天地,唐诗要讴歌的是特殊诗人才能锤炼出来的特殊情感,还要有使那种情感能够兴奋的题材。唐诗至少以此为理想。宋诗则不然,是把任何人都能够拥有情感、能够经历的题材创作成为诗。宋诗没有唐诗的兴奋,或者有意避开了那种兴奋。可是沉静、熟视、内在的美存在于宋诗之中。(吉川幸次郎《宋诗随笔》,转引自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唐酒宋茶”这个比喻很有趣,形象而又直观地道出了某种本质的差异,令人耳目一新。吉川对宋诗美学的总体概括,所持论的依据是:“唐代气势恢宏,盛世伟业,故唐人有着一种自信与豪气。而宋朝哲学发展极大,又面临着来自西北和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威胁,忧患挥之不去,故宋人重思索,宋文化又带精致内敛之特点,这也就造成了唐宋诗的风味的不同。唐诗如同醇厚、浓烈之美酒,宋诗则如清新悠远之香茗。”因此,宋诗有着不逊色于唐诗的独特美。
茗边漫兴,以茶说诗,从宋人茶盏中管窥蠹测宋诗风味,或许可以找到另一种进入宋诗的方式吧。
二
吉川幸次郎认为叙事性是宋诗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具体来说就是“以文为诗”与叙事性有机结合,将日常生活作为诗歌的主要内容,强化诗歌的叙事性。
叙事诗并非始于宋代,六朝乐府、唐诗都有非常出色的叙事诗,如《木兰辞》,如《琵琶行》《长恨歌》等。只是宋代的叙事诗数量更多,也更为普遍,这是诗歌发展到宋代的一大变化。以茶为例,茶事“兴于唐,而盛于宋”,由于以饮茶为中心的茶事活动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茶成为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以茶事为素材的叙事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个高度,比如范仲淹的这首《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冥。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这首诗是范仲淹读了章岷抒写建安斗茶盛况的诗作后,所作的和诗,章岷的原诗没有流传下来,但从范仲淹的和诗也可一窥其貌。这首和诗通篇读来,与其说是诗,更像一篇记叙性散文,“宋诗散文化”的特点在这首诗里体现得很充分。全诗由两个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描绘“采茶”“制茶”和“斗茶”的情景,进而又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概述建茶拥有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历史悠久,名冠天下;第二层描写初春时节茶农抢时间采摘嫩芽后精心焙制,以备纳贡;第三层主要描绘贡茶产地的“斗茶”风气—从精选茶具、用水,直到烹煮之后比茶味,比茶香,品评之后胜败者的精神状态,整个过程用语华丽,形象凸显,色彩鲜亮。后一部分由实入虚,由建安“斗茶”习俗引发无尽感慨,思接千古地与屈原、刘伶、卢全、陆羽、伯夷、叔齐等历代名士的人生际遇建立关联,感叹饮茶的赏心乐事,淋漓尽致渲染闽茶的神奇功效。
这首咏茶诗历来脍炙人口。当然将这首诗称为叙事诗,多少与人们对叙事这一题材的既定印象有差异,最主要的是从全诗来看,并没有可以称得上故事情节的部分。不过,在吉川幸次郎看来,宋诗的叙事性不一定以讲述故事情节为主,更多的叙事常常用以概述描摹某一事物。另外,宋诗的叙事性离不开理性的概括,理性与叙事性的关系在宋诗中更为重要。对此,吉川幸次郎说:“宋诗题材的积极动机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接触到的日常事物作为诗歌题材。贴近生活的宋诗趣味就产生于此,还产生了以往所没有的诗趣。”(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转引自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
三
贴近日常生活也是宋诗的一大特征。
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中说,宋人写诗热衷于表现日常生活,常常捕捉生活的细部,捕捉身边的生活,这些过去从没进入诗歌的素材进入了宋代诗人的视线中,并且成为书写对象,这是宋诗贴近生活的特征,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型。这个特征可以从宋人如何看待和赏玩日常饮茶看出一些端倪。
宋诗人乐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乐趣与情趣,使得诗歌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但这并不是说,宋代以前的诗歌就没有写日常生活的。以茶诗为例,茶作为开门七件事的日常之一,入诗并非始于宋代,远的不提,中唐的诗人白居易、皮日休等就极为细致地写过日常饮茶的种种。只是,最为普遍集中地表现茶事这一题材、对日常茶事最细微的描写,还要等到宋诗才开始出现。
从宋初开始,茶事大量进入文学书写领域,尤其成为诗歌的一大题材。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概括起来,不外两点:其一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其二是茶在宋代全方位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茶文化与文学所呈现的新气象,按照吉川幸次郎的文学史观来看,根源在于“宋代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生活环境形成了划时代的界限,走進了我们的现代”(《宋诗概说》)。如果以今天的常识来回望宋人的社会生活,当然与所谓的“现代”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但相比宋之前的时代,宋人的生活无疑向近代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商品经济发达,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发展,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和未来前景抱有期待,等等,这些社会现象的巨大变迁,使得原本属于上层社会的生活享受一下子走进了平民阶层,特别是平民文人。这种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必然在文人的诗文歌咏里表现出来,这也就是吉川所说的“宋诗日常生活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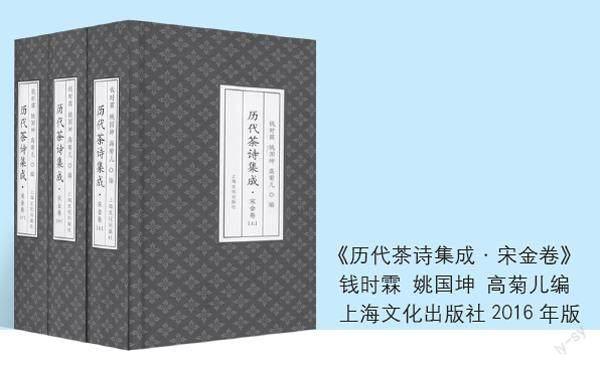
这种诗歌创作上的趣味偏好,又恰好契合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茶事盛况。两宋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登峰造极的时代。宋代的茶叶生产,是在唐代兴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起点本来就很高,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州郡产茶,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大批制作精良的名优茶种接连涌现,出现了如“龙凤团茶”“小龙团”“瑞雪翔龙”“万寿龙芽”“新龙团胜雪”等名品;饮茶的方式,在日趋精进讲究的同时也呈现多元化,除了延续唐代的煎茶、末茶之外,民间还出现了较为随意便捷的散茶法;两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准的茶学专著,如《茶录》(蔡襄)、《品茶要录》(黄儒)、《东溪试茶录》(宋子安)、《宣和北苑贡茶录》(熊蕃)等,甚至连宋徽宗赵佶也是一个茶迷,撰有《大观茶论》,将宋代的茶艺推到一个与书画艺术等量齐观的审美高度。与茶业发展生机勃勃景象相映成趣,宋代茶诗也同样迎来一个鼎盛时期。
宋初诗坛出现了不少擅长茶诗的名家,如与南唐时期的韩熙载齐名的徐铉以及著名古文家王禹偁,不仅本人好茶,也极善于写茶诗。徐铉的《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洋洋洒洒,纵说横论,从新茶萌发、采摘、碾叶、烹茶、品饮以及茶客、茶空间、茶的功效等全方位进行评述,堪称宋初茶诗代表作,不过这类作品基本延续了唐五代茶诗的写作范式。茶诗题材的写作发生重大变化,似乎是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才出现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梅尧臣。宋初茶诗到梅尧臣手中,不但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且着眼于在极为琐屑的日常中描写茶事,在写法上开始具备不同以往的特质。
梅尧臣是与欧阳修齐名的北宋前期倡导诗文革新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以大量创作开拓了宋诗的领域,为宋诗跳脱出唐诗的笼罩找到一条途径,在二○○七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对他在拓宽宋诗创作领域的功绩做了这样的评价:“他的诗歌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有意识地向各种自然现象,生活场景和人生阅历开拓,有意识地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者在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开启了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新风。”梅尧臣嗜好饮茶,他的茶诗不但数量多,而且对茶事的书写几乎就是他创作理论的实践—他写了摘茶的器具和蒸茶腾起的烟雾,“采从青竹笼,蒸自白云家”(《建溪新茗》);写斗茶中茶沫持久咬盏的心得,“烹新斗硬要咬盏,不同饮酒争画蛇。从揉至碾用尽力,只取胜负相笑呀”(《次韵和再拜》);写茶喝多了睡不着觉,数羊似的数月光下树上乌鸦的啼叫声,“夜枕不得寐,月树闻啼鸦”(《李仲求寄建溪洪井茶七品,云愈少愈佳未知尝何如耳因条而答之》);写空腹喝茶肚子里“咕噜噜”的响声,“诗肠久饥不禁力,一啜入腹鸣咿哇”(《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等等。用这样的笔触写茶是前人少见或不曾有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称道梅尧臣开创一代诗风,就列举了他诗中写的“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等看起来不像诗的“琐碎”之事,其实这是梅尧臣在诗歌的日常性方面所作的尝试。

叙事性与日常性既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增加了宋诗的生活气息。上引的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同样体现了这一特质。这首状物叙述诗的高潮部分是斗茶的场面:“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这一场面的描写用的是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细致入微—碾茶的时候,铜制的茶研四周绿色的茶末飞扬;烹煮后点茶,茶汤在紫玉杯盏里浮泛着翠绿色的微波。茶香比得上美酒,茶味比得上幽谷的芝兰。还附带一笔写观众和参赛者的情状:“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其中“十目视而十手指”一句,典出《礼记·大学》中“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语,众目睽睽之下的比赛,令竞技者紧张到极点。胜者飘飘欲仙,败者形同败军之将,无地自容的窘态同样一览无余。这首诗,散发着茶香和竞技的烟火气,那也是扑面而来的浓浓生活气息。更不必说,斗茶的题材在这首诗之前,还是没人涉足的领域,就是在白居易的诗歌里,如此细腻刻画一种日常生活的,也很罕见。
四
在诗中表现哲理性与政治性,是宋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宋诗多说理,这是宋诗历来受到诟病的一大原因。文学艺术的表达应以形象思维见长,抽象的说教和说理不是文学的基本表现形式,以议论为诗,以理为诗,会冲淡诗歌韵味的和谐,破坏诗歌形象性。然而,宋代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极为发达,宋人对于宇宙人生有自己一套哲学观念和理论,这就导致他们自然而然会借助诗歌来表达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大多数宋诗,因为贴近了现实生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抽象性,也减少了破坏诗歌形象性的程度。同时由于有了成熟的哲学新思想的支撑,宋诗有了深刻机智的、更富于学问思辨的色彩,折返归来成就了宋诗的深刻性,是唐诗中所没有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吉川幸次郎例举了陆游的《啜茶示儿辈》一诗:
围坐团栾且勿哗,饭余共举此瓯茶。
粗知道义死无憾,已迫耄期生有涯。
小圃花光还满眼,高城漏鼓不停挝。
闲人一笑真当勉,小榼何妨问酒家。
这首诗颇有趣味。垂暮之年的陆放翁以饭后家族茶会的形式,以自身的道德修养为经验教训对儿女进行家教,家国情怀的微言大义出现在茶余饭后的家族谈话中,其间散逸着浓厚的儒家气息。首联叙写茶会时间、地点、气氛,用语“团栾”“勿哗”“共举”表明场面庄重而和谐。颔联重在讲述自己今生遵照孔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圣训,努力践行儒家的道义准则,如今年届耄耋,死而无憾。颈联训示后辈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奋发进取,莫让年华付水流。尾联训示后辈对待生活学习要永远保持谦逊的姿态,此处说理,运用比喻修辞,形象生动,让晚辈易于接受。由此可见,宋诗的理性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另一种形象性,一种诗艺审美情趣。
另外,对政治的批判也形成了宋诗的理趣。以诗歌表现社会政治生活是儒家的诗歌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远的不说,唐诗中就不乏具有强烈批判现实意义的诗篇,如《石壕吏》《兵车行》《卖炭翁》等。这一传统在理学盛行的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是因为,在宋初奠定的重文抑武的框架下,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人成为国家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员,士大夫的主体性意识和参政议政意愿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参与国事、议论政治,这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也是理学在宋代繁荣的时代背景。从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他们不但热衷于在诗文中讲道论学,也有很多卫道的议论。可以说,比起前代,宋代诗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更强烈的使命感,也更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这种时代思想文化影响所及,自然也会在表现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中投下浓重的影子,也会在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观察中留下痕迹。宋代茶诗中也有不少将茶事与为政之道、与官风民风联系的讽喻和批判,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意味。在这个话题中,我想举苏轼的《荔枝叹》为例。

这首诗作于绍圣二年(1095),当时他贬谪广东惠州。惠州盛产荔枝,苏轼写的这首荔枝诗,结合朝政身世,抒发自己对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感慨。这首诗很长,在诗中,苏轼写了惠州荔枝的美味,转而想起祸国殃民的“红尘妃子笑”典故,于是狠狠鞭笞了古代进贡荔枝的做法,然后剑指当朝的贡茶制度,把丁谓、蔡襄这两个宋初督造贡茶取悦皇上的官僚前辈都拎出来笔伐一顿: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豈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苏轼指出,为邀君王宠幸,不计手段,一味争宠,这是宫中粉黛的“爱君”;但作为一个贤明忠实的臣下“爱君”,应该是以忠君恤民为念,正直磊落,刚正无私。将蔡襄不惜民力精制贡茶取悦皇帝之举与宫女邀宠相提并论,政治批判意义够浓的。惠州荔枝与建安团茶,都是地方名物,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政者失德,不仅败坏官风,也将祸及国家。这些可以写成杂文、散文的内容,苏轼同时也将它写进了诗歌。只是,诗歌讲究含蓄,因此在诗中,苏轼没有直接去抨击某种体制弊端,而是通过描写具体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比如,在日常茶事中也隐含着执政者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富于讽喻性和哲理性,而不会给人说教之感,也说明了宋诗在题材上的开拓和创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文学无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对宋诗政治化现象的成因,吉川幸次郎将其归结为宋代开始蔚为繁荣的理学在文学上的反映,是颇有见地的。
二○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修订于厦门海沧马銮湾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