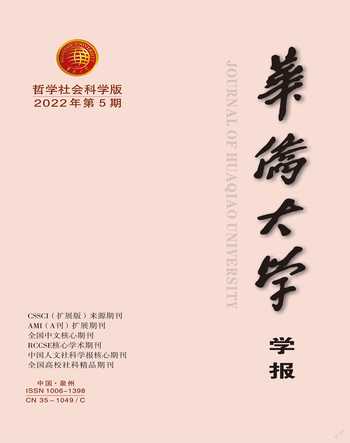新时期执法认同的转型与构建
摘要:执法认同是法律认同的重要领域,是社会对执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是一种以“集体观念”为基础对执法(制度与实践)的象征性认可。过往学界对法律认同的研究缺少对执法认同的关注,而法律认同所关注的个体与国家间的互动,在执法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执法认同在法律认同体系中更加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变动性。过去执法认同机制存在机制要素单一、认同标准偏重客观性、认同主体范围小等问题。新时期,在社会关系更加具有复杂性、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等新的社会条件下,执法认同发生转型,在机制要素上由单一要素变为复合要素,标准上由客观变为主客观相统一,主体上由直接主体变为大众主体。构建执法认同的根本是形塑认同执法的观念基础。通过观念基础的生产机制和整合吸纳机制,完成执法认同观念基础的形望。关键词:法律认同;执法认同;观念基础;嬗变
作者简介:胡敬阳,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社会学、执法制度(E—mail:1004607073@qq.com;重庆40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社会治理”(17VHJ006)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5—0094—10
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只有被普遍认同,法治秩序才能充分实现,法治权威才能真正建立,公民也才能普遍守法。法律认同是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实践经验和理性逻辑,对社会生活中所运作的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社会生活事实进行判断后产生的一种集体观念,①是个体(观念)与国家(制度)之间双向的信息交流和建构过程,关涉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背后精神的、无形的心理机制,是政府与民众持续信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制度稳固的源泉之一,表现出主客观结合的连续统一体的特征。人类社会的客观与主观是辩证统一的,客观化的外部世界与主观化的人类心理共同作用,调和着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促进人类的实践和进步。
从学界对法律认同的既有研究来看,有学者侧重于法律认同中法律制度的主体性地位,将法律认同理解为“一国法律制度体系基于利我动机而主动与关联主体进行互动交往的活动”②,更多学者则站在法律受众(民众)的立场上,认为法律认同就是法律满足民众的期待和需要后,民众信任并主动服从法律,③包含着一个从认知到认同(守法)的过程,④还有学者将其生成过程细分为良法品格、法律实施、认知获取、内在评价、情感迎合、认同形成等阶段,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过程。①法律认同本质上是法律制度运作于社会、与民众发生互动的实践过程,可以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定义,如个体与群体、国内与国际、内部与外部、形式与实质、规范与情感等。②在法律认同的具体领域层面,学者们大多将注意力放在司法认同上,讨论司法认同的形成机制与条件。③由上可知,我国目前的法律认同研究缺少对执法认同这一具体领域的关注,对执法认同一般理论及机制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少。由于民众最经常在执法中触摸法律符号、感受法律权威并形成法律评价,而法律认同所关注的个体与国家间的互动,恰恰在执法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执法认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上,“执法认同”是一个随着社会条件变化而不断演化的、具有很强时效性的概念。那么,执法认同在法律认同体系中具有何种特殊性?过去执法认同机制存在哪些问题?新时期在社会关系更加具有复杂性、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等新的社会条件下,执法认同机制发生了何种转型?构建执法认同的关键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期对我国法律认同的系统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执法认同的一般理论
法律认同问题一直以来都得到学术界直接或间接地广泛关注。韦伯将统治权威的理想类型,分为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权威,三者都包含“合法性”的内涵,只有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即被认为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缘故”,政治统治才具有合法性。④韦伯的概念体系秉持一种权力或制度的单方视角,以形式合理性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忽视了建构认同中民众的主体性作用。休谟定理问题提出,法律规范的“应当性”来自于规范秩序的参与者对规范相互期待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决定了法律能否正常运转并实现其制度功能,这也意味着一个获得民众认同的制度才具有实际效力。麦考密克在论述其“对规范的认同”理论时,认为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一种建立在默示(implicit)的认同观念之上的慣例,而这种惯例的核心就是一种实践者之间相互期待的共同观念,⑤它是不同于规范的、来源于人们内心自主确信的观念共同体。⑥这说明构建法律认同的根本是培养基于价值认同的观念共同体,在这种观念共同体的影响下,个体服从制度规范的动力就是内心的信念和理性的选择。
较高的法律认同会转化为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而执法认同是法律认同的重要领域,法律认同所关注的个体与国家间的互动,在执法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履行法定职责、执行法律的活动”⑦,执法的领域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城市管理、交通出行、环境保护、市场监督等等,可以说执法不但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还是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深入互动的重要场域。民众是否对于执法普遍地认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法治秩序的实现和法治权威的建立,执法的成效高度依赖于执法认同的构建。执法认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某一个个体的情感认同或者价值判断,而是社会对执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是一种尊重和信任法律的集体意识,一种普遍自觉遵守法律的群体影响力,一种接受法律规则的价值共识,一种以“集体观念”为基础对执法(制度与实践)的象征性认可,是执法实效形成的价值观念支撑。
当国家与社会在执法中交锋和互动,“认同”或者“不认同”就被不断生产,并反过来对执法的运行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执法认同不但蕴含着个体与国家的互动,更意味着执法不是法律机关简单的实施法律的过程,也不是单向的国家塑造社会的过程。任何治理行为和法律目标的达成都需要行动者各方的信任和配合,①如果当事人不能主动参与到法律游戏中去,法律机器的运转就会停滞下来。②在执法这一实践过程中,民众也会反过来对执法本身产生影响和塑造。在执法者和执法对象的互动中,执法认同起着联结个体与国家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行动者之间的认同程度影响着双方的行动模式或行动倾向。当认同程度高,民众就更可能在内心信任执法者的公正性,行动上积极配合,与执法者形成良好的合作。而如果认同程度低,民众可能一开始就对执法采取内心不信任乃至抵制的态度,在行动上不配合、无理取闹,甚至直接对抗。在另一个层面,执法者对执法对象的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执法方式。当信任程度高,执法者更愿意与执法对象沟通协商,而不会采取更激烈的制裁手段;另一方面,行动模式会反向塑造主体间的信任和认同程度。执法行动者之间的认同程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恰恰是在执法实践中被生产和改变的。执法双方在实践中的行动模式往往释放出有关双方关系的指引信号,从而影响彼此间信任的维系和变化。
由上可知,执法认同作为一种动态的“集体观念”和心理归属感,不但决定了执法制度实施的成效,是执法行动者形成良好合作的价值观念基础,同时还塑造了执法的实践形态,影响着执法各方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国家通过执法进入、塑造和影响社会,抽象的制度、规则借此得以具体化,广泛发生的执法活动是比法律宣传和司法裁判更具一般性和普遍影响力的法律传播方式,执法这种法律传播方式也可以促进执法认同的生成,塑造出认同执法的社会文化心理。③执法认同在法律认同体系中具有独特性。
执法认同是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构建的。由于执法更贴近社会和日常生活,执法的制度及实践更容易被民众感知,国家的制度规范通过执法更为深入地作用于社会及具体的个人,执法认同主体具有广泛性,执法认同对执法实践形态的塑造具有复杂性,故而执法认同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执法认同在法律认同体系中更加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变动性,执法认同机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更易发生嬗变。在社会快速变迁、价值多元化的新时期,执法活动正日益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夺权利的表达方式,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于执法认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影响。为此构建执法认同的根本是形塑认同执法的观念基础,通过培育认同执法的观念基础,凝聚价值共识,可以使得执法更好地衔接国家意志与社会力量,弥合制度与实践的落差,有效整合多元的社会意识,促进执法的良好合作。
二新时期执法认同机制的嬗变
作为法律认同重要领域的执法认同,不但是社会对执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而且是由客观机制所影响和作用的。这种“机制”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执法(制度和实践)”和“执法认同”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随着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因果关系。“在社会中,不同规则体系和规则执行相互竞争与合作,存在许多正式法律制度的替代物。法律命令的实际效果或影响从来都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①过去执法认同机制存在机制要素单一、认同标准偏重客观性、认同主体范围小等问题。由于执法更贴近社会和日常生活,执法认同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执法认同机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更易发生嬗变。新时期,在社会关系更加具有复杂性、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等新的社会条件下,执法认同发生了转型。执法认同机制的生成,在机制要素、标准和主体三个层面上嬗变。
(一)从机制要素上来看:从单一要素到复合要素
过去执法认同机制生成的机制要素是单一要素,即公正执法。一方面,执法中的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国家所垄断的、具有强制性的公共力量,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公平公正最有效的工具,也可能成为侵害公民私权利最厉害的工具。②为此,必须要公正执法,防止权力被滥用;另一方面,执法所要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内容的复杂性决定自由裁量权成为执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自由裁量权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存在被滥用可能。执法机构在执法中要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审慎地做出行政执法行为,以符合社会大多数群体的公正观念和价值标准。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只要具备公正执法这一单一要素,就能形成执法认同机制。
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性的陈述,但也存在着为一般性的陈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③法律的理想状态距离现实世界总是存在着距离,执法认同也是如此。埃里希将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在制度层面制定和实施的“国家法”;二是“活法”,也即“人类联合的社会秩序”本身。他指出,“不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④。随着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执法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执法的场域更趋流动性和变幻无常,执法认同机制生成的机制要素也从单一要素变为复合要素。执法的公正性,是社会大众普遍认同执法的基础。但公正标准的客观性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时空中,公正的客观标准是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執法的实践、成效和认同也受制于体制背景和行动者所处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由于执法体制植根于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中,执法机构事实上很难完全按照理想化的“公正执法”模式来行动。法律在社会关系更趋复杂化的新时期中的具体实践是复杂多元的。故而,执法认同机制在新时期由复合要素生成。
(二)从标准上来看:从客观到主客观相统一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不管是执法、司法还是守法,要使法律规范从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就要让法律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信仰。正如卢梭所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⑤主观和客观是一体而非割裂的,往往主观的内容和对象同时也是客观的内容和对象,比如当我们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看起来是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要通过提高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司法责任制改革、提高法院执行效率等客观制度机制来实现这一主观目标。过去执法认同标准偏重客观性,主要采用客观标准来评价执法,如执法体制是否合理、多部门联动机制是否完善、执法事权与人力资源是否匹配、执法的合法性依据是否充分等,但这只是执法认同客观性的层面,并且只采用客观标准容易陷入社会控制理论下的工具主义,事实上,“除了社会控制外,还存在其他能够促使人们遵守法律的社会基础性因素”①。在新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制度评价更加凸显民众主观感受的主体性位置。在执法的整个运行过程中,都会受到社会个体及群体认知和评价的影响。当执法认同机制采用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也就是在执法的制度和实践中加入一种精神的、无形的心理机制,表现出主客观结合的连续统一体的特征。美国学者泰勒认为,民众内心认同和接受法律规则的重要前提是人们对法律制度充满信心,是民众赋予了法律制度和执法机构的合法性,从而将守法当成责任。②事实上,法律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建立恰恰在于民众的广泛认同,将法律“强加”于社会公众身上并不能彰显法律的权威。这也是执法认同机制从客观标准发展为主客观相统一的内在机理。
(三)从主体上来看:从直接主体到大众主体
过去执法认同机制的生成主体是直接主体,即执法者和执法相对人,执法活动的运行和评价主要通过直接主体来完成。但是新时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把现代社会改造成了“网络社会”“数字社会”和“虚拟社会”,包括执法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和行为既基于物理时空又超越于物理时空,③从而把无处不在的现实存在或网络存在的大众主体都加入到执法认同机制的生成主体中来。在数字社会中,执法的信息和数据随时都可能打破时空界限流入任何一个地方,国家不再垄断执法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社会也成为执法数据生产的场域。在数字社会中每个接入网络的个体,都可能是评价执法的主体,也就是成为了影响执法认同的因素。即使个体不亲身参与或直接接触执法活动,但在数字社会下通过各种传媒的传播,当执法活动涉及到一些个体的价值准则或者对社会的具体期待时,“局外人”就可能将自己代入执法活动中,关注和评价执法的成效,甚至希望改变不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执法结果。“虚拟空间对现实社会的塑造,使得现实空间反而更加虚拟化,我们的偏好、意识和自主,很可能只是系统操控的结果。”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执法的认知和评价,可能未必来源于执法的真实样貌,而是数字社会中系统操控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记忆”。当执法认同机制的生成主体由直接主体变为大众主体,执法认同机制的生成路径就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三执法认同观念基础的形塑
执法认同的形成绝非易事,因为“所有认同都是构建起来的”⑤。执法认同不是预先给定的,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复杂的社會情境中构建的。新时期,执法认同发生了转型,执法制度及实践与执法认同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具有不确定性。青木昌彦将制度看作是“通过协调人们的信念控制着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⑥,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输送并培育价值观的过程。价值观念对于制度和组织结构来说既是一个自变量,也是一个因变量,因为它既能产生影响又能被影响。社会共同观念层面的价值观不仅深刻影响制度的执行能力和执行效果,而且对制度建构和制度评价都有重要作用。⑦执法认同始终归类于人类主观上的情感,受到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深刻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于执法认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由此构建执法认同的根本是形塑认同执法的观念基础。
(一)观念基础的生产机制
1.观念基础的制度化生产
第一,制度化生产的主体:党。如果把执法看成我们党治国理政中的一项治理活动,那么形塑执法认同的观念基础也要放在党治国理政全局性的高度来看。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当着推动国家和社会政治运行与变革的引擎使命,统摄、规划、引领着社会的观念和行为。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直接以党的命令来指挥国家机构,更不是用党的组织替代这些机构,而是通过一系列政治的、思想的和组织的建制与运作机制来实现的。”②在此背景下,党自然成为了执法认同观念基础制度化生产的主体。
党作为价值目标生产的主体,需要吸纳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源、中华文化传统资源、地方性优秀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及其社会化创新资源,生产足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资源,③为包括执法在内的治理行为提供观念基础。党生产价值目标与执法实践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制度化目标吸纳机制。一方面,要健全价值目标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机制。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只有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才能获得无穷的力量。我们党的工作一直强调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利益。群众路线的政治伦理嵌入到执法中,就是执法为民,以人民为中心,④这也是执法所应贯彻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要健全区域差异下社会价值的补强机制。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的国家,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法治化程度不尽相同,价值目标的生产既具有全国层面的一般性和共性,也具有显著的区域特色和地方性。在执法的价值目标上应充分考虑地方实际,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社会生活中新价值目标的形成保持足够的转化应用能力。
第二,价值治理: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新时期,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流动性的特质,人们往往难以形成道德观念之共识,“新旧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相互冲击,社会成员内心道德律令及社会状态左右摇摆以致杂乱无章”⑤,从而产生价值观念冲突和认同危机。隐藏在认同活动背后的是一套文化和观念体系,其是界定行为发生环境的经验信息、政治态度、情感、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⑥这就要求在执法中融入价值治理的维度。所谓“价值治理”,是指“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通过价值观生产和价值动员整合机制,对包括政府自身在内的组织、市场、社会实施的一种公共治理行为”⑦,强调价值观念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与相对刚性的“硬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相比,价值治理强调从强制性向共识性理念的转变,在供给产品、治理主体、行为方式上倾向于一种精神的、无形的、柔性的“软治理”⑧。作为“软治理”的价值治理与作为“硬治理”的制度体系的相互配合会形成一种正向合力,⑨对制度运行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在执法中进行价值治理的关键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由于执法认同是社会对执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是一种以“集体观念”为基础对执法(制度与实践)的象征性认可,强调从个体到形成治理共同体的进化过程,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深刻机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在于凝聚社会广泛共识,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关键在于实现执法的价值认同,缓解甚至消解执法机构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并将两者型构成利益统一体和治理共同体。完成此项任务,应当着眼于执法机构之道德价值层面,结合执法活动对社会道德的塑造功能,在执法体系内部嵌入核心价值观。具而言之,即在个体层面培养内在德性、在制度层面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规范层面推进道德立法。
首先,以核心价值观涵养执法者,将伦理道德嵌入执法者的行为模式中。执法者自主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或接受党性教育均是提升其内在德性的方法与途径;其次,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必须持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当前,人类正在迈入“智慧社会”①时代,治理方式与治理场域已开始发生深刻变革,在此时代背景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并构建起公共行政官员应当遵循的价值规范,确保治理的有效性。”②“智慧社会”不仅是一个存在着多元利益与复杂风险的社会,亦是一个服务型社会,这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角色定位,由“守夜人”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将实现民主、文明、和谐、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理想追求;最后,应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规范之中,以制度刚性提高执法者的价值治理能力。③例如,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将“富强”“文明”“爱国”作为原则性遵循;将“民主”“平等”“公正”“法治”作为规范行政行为过程的具体要求;将“和谐”作为衡量行政行为效果的价值标准;将“诚信”“敬业”“友善”作为对执法者的品质要求。一个社会的成员对共同价值观念的信仰,对制度规则的敬畏,都是要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模仿、学习、培育形成的。④执法认同的构建正是行动者通过执法实践证成的过程。⑤
2.观念基础的社会化生成
执法认同是制度与社会、记忆与当下的动态平衡过程,并且总是处于变化中。⑥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在社会中被建构、整合与延续的,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这种有关过去的知识就是记忆,它连接了个体与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⑦执法认同的主体是民众,民众对执法的记忆及认识是在社会中被建构、整合与延续的,从而执法认同观念基础也要在社会中社会化地生成。
由上文分析可知,信任影响着执法实践的形态及其认同程度,观念基础社会化生成的关键是充分信任的社会化培育。“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①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个体的角色行为与角色规范保持一致的表现状况就是信任,信任也是成员对互动对象可信赖特征的一种积极性的心理反应。②任何社会系统的运作,都需要一个成员互相依赖的环境。在执法中,看起来是单方面的强制,但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执法对象的配合,执法目标的达成依赖于行动者各方的充分信任。在现实中,“某些或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和他们从法律中得到的东西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使正当性与信任对任何法律制度来说都极其重要。”③事实上,在每一次执法过程中,执法者都必须充分估量不同当事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具有的不同能量及关系网,寻求最简便有效、又能最息事宁人的执法方式,进而在网络中规避执法阻力,完成执法任务;执法对象在行动策略上往往也会偏向选择和运用各种非正式规则与私人关系,积极建立有别于执法场域的私人关系来促成事情的非正式化解决。执法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复杂面向,充分说明执法认同依赖于充分信任的观念要素,正是这一观念要素的缺乏,才会让执法各方当事人寻求规则之外的行动策略。
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的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如果他人或系统表达了诚实,证明了抽象原则的正确性,就给出了可信赖性,即信任存在。作为社会现象的信任,其关键不在于心理学上所谓的“我相信你会做这件事”,而是在于信任对象言行一致的角色表现状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只要个体坚持已为人所知的一切,他就是值得信任的。这样的视角转换就把信任从一种个体心理特征转移到了他人或群体所具有或存在的一种可信任状态,从而信任也就成了一种独立于个人的、具有独特内涵的、客观呈现出来的社会事实。这一社会事实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建构、整合与延续,成为一种共同记忆和知识。由于它是人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性呈现,所以它的强弱或状态就能够被参与其中的人们感受、体验到,从而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维系,影响着特定社会生活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构成了支撑制度运行的观念基础。当执法各方行动者始终如一地进行自我呈现,给他人一种确定性的行为预期,且满足了社会的角色期望,则其行为就具有一致性或可信性特征,他就给出了信任。④
(二)观念基础的整合吸纳机制
在新时期,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化急剧发展中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虚拟化”并重,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权威型认同模式日渐式微,对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性联系造成巨大冲击,社会治理往往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冲突,传统的执法体制暴露出与外部社会互动的失灵。整合是社会运行不可避免的重要过程,整合缺乏或者整合过度都可能破坏社会的有序运行,实现价值观的有效整合是价值治理的主要目标。⑤执法认同观念基础的形成需要有效整合和吸纳外部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和利益需求,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⑥要让价值体系能“说服人”,就必须确保价值体系自身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促使其在时代变迁的动态结构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1.标准化的行政空间与个性化的生活空间的合理平衡
现代社会被国家打造成了标准化的“行政空间”。这一标准化的行政空间,意涵着标准化的景观建造、权力支配和认同模式,意味着国家期望把每一个人都绘制成同样的画作。标准化的景观建造,构成了画作的底板。人们都生活在相似的、模块化的时空背景中,每天面对着差不多的景观,日积月累地塑造了模块化的思维方式。在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国家文化①的推动下,现代国家建造了标准化的政治景观,如政府办公大楼、标准格式的政府公文和布告、统一涂装的行政执法车辆与统一制服的执法人员,他们往往转换成一束束政治符号,将国家秩序弥散在整个人口中。现代国家还制造了标准化的日常生产生活景观,如现代化的都市和乡村、文化体育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机构等,它们虽然没有政治景观具有明显的权力支配感和浓厚的仪式性,但它们具有隐蔽的政治性。它们嵌入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作为日常活动的基础设施或规范性背景,禁闭着景观所辐射空间内的社会,守卫著秩序的边界,再生产着国家偏好的可见性”②;标准化的权力支配,是国家事实上取代个人,由国家和集体握住画笔进行绘制。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标准化的认同模式构成了选定好的涂料,人们不但无法自己握住画笔,而且涂料也是相似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世界都无法自我定义和赋予,而是笼罩在国家统一的教育和文化系统中。现代国家标准化的行政空间,披上了非人格化和理性化的外衣,契合了现代社会高效、精准运转的要求,但却压抑了人性深处对个性和自由的追寻。
在这样标准化的行政空间的支配下,有些执法机构会做出像“坚决取缔无证经营的街头摊贩”“以环保之名取缔所有的临河店铺”这样没有经过充分调研论证的、“一刀切”式的行政执法行为,虽然创造了标准化的景观,但是却压抑了民众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背离了现代人多样化的审美需求,也侵蚀了执法认同的观念基础。构建执法认同的观念基础,应该在执法的价值目标上,整合吸纳民众多样化的价值和生活需求,合理平衡标准化的行政空间与个性化的生活空间。2.行政执法理念对伦理道德思想的适度吸纳
在相当长的一段時期内,我国行政执法的理念都是秩序和管制,通常以强制力为保障,以给行政相对人实施管制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在这种执法理念之下,执法者多倾向于采取给被执法者增加义务和负担的方式来完成工作任务,缺少与民众的沟通与合作。站在公民的角度来看,缺乏尊重与沟通的秩序行政,是一种行政关系双方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不但容易产生不认同的社会土壤,还可能滋生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从古至今,我国法律思维都具有一定的道德主义倾向,包含着崇高、抽象的道德理念。传统的中华法系吸收了“仁”“和”“家”等道德价值,在“和谐”理念主导下遍布社会的民间调解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的调解制度、家庭主义的赡养、继承和产权法则仍然延续着道德主义倾向的古代法律传统。③在执法实践中,执法的目的不是增加冲突和对立,而是如传统法律那样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那么,执法理念也应该适度吸纳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将“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贯彻到执法过程中;用“推己及人”“和为贵”的道德观念调和行政的强制性;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态去对待弱势群体。这样使得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契合,有利于形成认同执法的观念基础。
任何制度的运行过程都有“结构”和“道德”两个范畴,法律认同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是对制度研究的有益补充,凸显的是文化研究的视角。而目前学界对法律认同重要领域的执法认同研究相对欠缺。执法认同既有法律认同的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执法认同在法律认同体系中的特殊性即表现在其更加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变动性,执法认同在新时期发生了转型。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于执法认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影响,构建执法认同的根本是形塑认同执法的观念基础。研究执法认同,就是在执法场域中,探究人心、观念对于法律运行隐蔽但却深刻的价值。然而,执法认同研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果选择定性的研究路径,难免受制于研究者本身认识及立场的局限性;如果选择定量的研究路径,也不可能穷尽所有样本而导致研究过程的片面性。笔者认为,执法认同始终归类于人类主观上的情感,讨论个体乃至集体的心理机制对于制度运行的影响,在定性研究上需要深入发掘社会心理对制度运行作用机制的各种客观性影响因素,在定量研究上也要通过丰富的经验呈现来不断验证价值观念与制度运行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执法认同在法律认同体系中的独特性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厘清,执法认同的机制研究也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这些都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中继续延展和丰富。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of 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 in the New Era
HU Jing-yang
Abstract: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legal identity,a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formed by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a symbolie recognition of law enforcement(system andpractice)based on the "collective concept”.The previous studies on legal recognition in the academie circle lacked atten-tion to 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whi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tate that legal recognition focused onwas most typical in law enforcement.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 is more social,practical and changeable in the system oflegal recognition.In the past,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echanism of 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such as a singlemechanism,more objective in recognition standard,and a smallscope of recognition. In the new era,under new socialconditions such as mor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law enforcementrecognition has transformed from single to composite in terms of mechanism elements,from objective to a combination of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 terms of standards, and from a direct subject to a publie subject in terms of subject.The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 isto shape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based recognition of law enforcement can be completed through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absorp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cept basis.
Keywords:legalrecognition;law enforcement recognition;transmutation;conceptual basis
【责任编辑:陈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