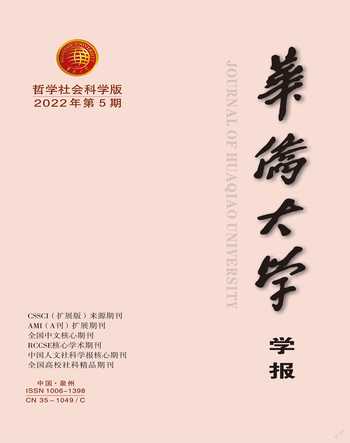我国育儿假的法理分析与制度构建
摘要:我国育儿假面临中央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和地方立法规范性不足的问题,亟需在厘清基本法理的基础上构建专门性的育儿假立法。在法理层面,育儿假以工作一家庭平衡、性别平等及社会连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其具有权利属性,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参照劳动合同中止理论予以构造。出于落实积极人口生育政策、推动生育假期制度完善的需要以及地方立法难以保障育儿假有效实施的现状,我国有必要对育儿假进行统一的专门立法。宪法提供立法基础、地方立法实践的探索以及域外的有益经验也进一步证成了立法的可行性。在立法层面,我国育儿假的立法模式应实现从短期的单独立法向长期的体系化立法的转变;在具体规则上,应同步构建育儿假的请假和销假等程序规则和育儿假的覆盖范围、休假条件、休假期限、休假方式、经济补偿等实体规则。
关键词:育儿假;生育假期;性别平等;生育保险
作者简介:李富成,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法学(E—mail:lifuchengldf@163.com;重庆401120)。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风险防控法律问题研究”(CLS(2021)D49);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项目“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下生育假期的完善研究”(22SKGH041);重庆市科研创新项目“性别平等视角下的育婴假法律制度的构建”(CYS20154);西南政法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平台用工的性别平等法律保障机制研究”(2021XZXS—037)。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5—0104—15
2019年5月9日,为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幼有所育”的民生政策,满足人民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育儿假,由此,全国性的育儿假政策应运而生,后苏州、咸宁等地相继出台育儿假政策。①2021年3月13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中再次提出要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自2021年5月起,中央相继宣布全面实施三孩政策以及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与此同时,作为生育支持配套政策的育儿假也逐步得到落实,经由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到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从“政策之治”走向“法律之治”。然而,我国当前对育儿假的理论研究尚付阙如。育儿假的基本法理未能理清,导致其无法与现有的产假、陪产假②等生育假期3进行区分并在功能上予以衔接。此外,我国当前的育儿假立法也呈现“粗线条状”,中央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地方立法各行其是,有损法治权威。有鉴于此,对育儿假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在阐释其法理基础并构建具体规则的前提下,出台全国性的育儿假专门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在对育儿假的概念、规范现状和问题进行检视的基础上,从法理的角度阐释育儿假的理论基础、法律关系和法律属性,并对育儿假立法作出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证成,最后从立法论的维度,提出构建我国育儿假制度的具体建议,在国家、单位、家庭、劳动者之间重新分配生育责任,以期对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有所助益。
一育儿假的概念、规范现状与问题检视
(一)育儿假的概念范畴
广义的生育假期是指劳动者因生育而有权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保留劳动关系的一段时间,
①通常包括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其中,育儿假(也称育婴假、父母假、亲职假)是指以照顾和看护孩子为目的,由父母一方或双方享有的一段较长时间的假期。②育儿假与产假、陪产假区别:第一,目的不同。设立育儿假的目的是照顾和教育孩子,而设立产假的主要目的是使生育女职工本人的身心健康得到恢复,陪产假是产假的衍生假,其创设目的是满足男职工照顾分娩配偶和新生儿的需要。第二,性别指向不同。育儿假男性和女性均能使用,而产假和陪产假分别只能由女性和男性使用。第三,内容不同。在休假时间方面,育儿假通常在产假或陪产假期满后才休,且时间相对较长;在报酬方面,育儿假期间的报酬通常低于产假或陪产假期间的报酬,或者完全无薪;在具体的标准和负担主体上,产假或陪产假的报酬主要由雇主或社会保障系统参照原工资福利标准支付;③而育儿假期间的待遇(如有)通常按照固定费率或部分收入替代的标准由社会保障系统承担。此外,育儿假在休假条件、灵活性及可转让性方面也与产假和陪产假有所差异。然而,在现实中,育儿假与产假、陪产假间仍然存在模糊地带。如在英国,育儿假是产假的一个部分,只是主体增加了分娩者的配偶;④在某些国家,陪产假和育儿假并无严格的区分,当父亲享受时,陪产假将成为育儿假的组成部分。⑤
(二)我国育儿假的规范现状
从2006年开始,我国妇女组织就致力于倡导父亲育儿假。⑥2010年至2012年深圳市在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时也曾提出父亲育婴假和双亲育婴假的条款,但最终未获通过。2019年,育儿假作为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再度被提出。2021年8月20日,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育儿假制度由政策转化成法律。⑦随后,各省级地区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设育儿假制度。截至2022年7月30日,共有30个省级行政区出台育儿假规定(见表1),这些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育儿假具有双重制度定位。绝大部分省将育儿假作为积极生育政策的一部分规定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但也有少数省同时将育儿假规定于妇女或女职工权益保障条例,将其定位为女性的特别保护措施。第二,休育儿假并非劳动者的法定权利。绝大多数省将育儿假规定于“奖励与社会保障”一章,可见其作为倡导性规定(仅甘肃、安徽和河南规定单位有给假义务)而非一项法定权利。②第三,育儿假的覆盖人群主要是“職工夫妻”和“职工父母”,即拥有完满婚姻状态和家庭形式的两性劳动者,仅少数省赋予离异夫妻中抚育孩子一方、养父母等以育儿假;江苏则较为特殊,将父母和男方同时规定为育儿假的覆盖人群。第四,育儿假的适用条件趋同。绝大多数省仅规定应满足合法合规生育且孩子在三周岁内,仅少数省增加了合法收养、应在产假和护理假后使用等条件。第五,育儿假的天数为每年10日到40日,多数不以孩子数量而累加。第六,育儿假期间的待遇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除少数省未有规定外,无论是规定工资待遇照发还是享受在岗职工同等待遇,本质上都是由单位来支付假期待遇。第七,育儿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劳动者可以一次或分次休完,也可以在夫妻之间转让(仅北京)。(三)问题检视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育儿假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现行育儿假国家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我国育儿假的法律依据,但其充斥浓厚的政策色彩,基本不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第二,现行育儿假地方立法的规范性不足。一方面,在程序规则上几乎处于空白,大多数地方立法对劳动者如何请假和销假,用人单位如何回应等未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实体规则上,育儿假制度也存在较多不足,具体而言:其一,覆盖人群范围较窄。大多数省对于不具有传统劳动关系的职业劳动者(如新业态从业人员)、单亲父母及养父母等是否可以享有育儿假未作规定,导致这些群体难以享受育儿假。其二,给假条件过于宽松。我国当前的育儿假给假条件门槛较低,对于若干重要条件如是否需要劳动者达到一定任职期限、是否要亲自照顾孩子等均未有规定,容易导致育儿假在偏离制度目的轨道上被滥用。其三,假期期限过短。与奖励性生育假相比,育儿假在性质上更接近带薪的事假,对于婴幼儿的照护只能起到聊胜于无的作用。其四,休假方式单一。虽然地方立法规定劳动者休育儿假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总体而言形式仍显单一,缺乏与强制性休假的配合,且制度效能也由于假期过短而难以实现。其五,假期待遇不足。一方面,我国当前采取雇主责任制的待遇给付模式不合理地增加了用人单位的负担;另一方面,国家责任的缺位又使得育儿假期间收入中断的风险无法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分散,最终其不利后果将由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承担。上述制度层面的困境呼吁专门立法的出台,而出台立法首要的任务就是对育儿假的基本法理予以厘清,并以此指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二育儿假制度的法理分析
(一)育儿假的理论基础
1.工作一家庭平衡理论。工作一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作为工作一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基础和核心内容,①是指个体对工作和家庭满意、工作和家庭职能良好、角色冲突最小化的心理状态。②对该理论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面向来理解:前者是指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相互不冲突或干扰;后者则是指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相互促进和提高(也称积极的工作一家庭溢出效应)。③劳动法中的工作一家庭平衡则是指劳动者行使就业权利和履行家庭照顾义务间的平衡,主要包括“时间平衡”和“角色平衡”,即在工作时间的规则设计上充分考虑劳动者家庭责任承担的时间要求,使其同时满足作为工作者和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需要。④在现代社会,双职工模式已经逐步取代了男性养家模式。劳动者既是“工作人”也是“家庭人”,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放弃工作而回归家庭,反之亦然。而育儿假政策则被认为是连接工作和家庭领域必要的桥梁,可以减少两者因相互竞争的需求而产生的冲突。⑤育儿假平衡工作与家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工作保障。劳动者在休假期间,其劳动关系得以存续。第二,家庭义务履行保障。请假的劳动者不仅有时间照顾小孩,而且有权获得足够的经济待遇,以弥补其因不工作或工作量减少而导致的收入下降。第三,由于工作一家庭平衡制度的最终目标是鼓励有家庭责任劳动者参与就业,①因此,劳动者有权在假期内与劳动力市场保持一定的粘性,避免因履行照顾责任而导致劳动能力衰退,并在假期结束后恢复原来的工作。
2.性别平等理论。性别平等是指所有人,無论其性别,都有发展个人能力、从事其专业的自由,并不受任何陈规定见、僵化的性别角色和偏见的限制而做出选择。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性别平等旨在消除性别对人发展的限制。育儿假所追求的性别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结合。形式平等的核心是给予相同的人以相同待遇,不同的人以不同待遇。然而,育儿假与产假不同,产假是基于女性怀孕和分娩的生理特征,出于保障其身心健康的特殊需要而规定的休息时间;但养育子女是男女双方共同担负的任务,这一点与生理差异无关,不存在女性在养育子女问题上的特殊需要。③因此,育儿假应采取性别中立的立法表达,原则上由父母双方平分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分配,避免将育儿假作为女性产假的延续或将男性休假的权利规定为事实上的附属性权利。④然而,形式上的性别平等也有局限性,其并没有考虑两性的社会差异,忽略了只有当女性像男性一样行为和生活时,她们才有权获得平等待遇。⑤现实中,承担抚育子女义务的女性雇员压根无法适应“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下形成的工作模式。⑥同时,男性也被定位为公共领域的经济角色,难以进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因此,在形式平等外,有必要建立实质意义的性别平等观,消除或减少因性别分工导致的社会工作和育儿责任不平等,保障人的发展不因性别而受到限制。育儿假允许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休假,参与抚养和照顾事务,其设想是,给予父母任一方育儿假的立法最终将实现家庭内部更平等的育儿责任分担,从而更好地实现在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⑦对此,国家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消除育儿假运行中可能产生的性别差异,鼓励两性共同或接续请育儿假,尤其是提高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和意愿,有效方法是为其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和灵活的休假方式。
3.社会连带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一部分和一阶级的痛苦与不安,往往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安宁,解决这些不安也因此是整个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⑧在传统上,生儿育女被认为是每个家庭的私事,生育责任也主要由家庭及其成员承担,国家和企业起的辅助作用相当有限。⑨然而,在社会连带理论的指导下,生育跳脱了狭隘的家庭和个人责任本位,被视作整个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因为生育不仅能够为家庭带来幸福感,同时也能够产生促进优质劳动力再生产、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以及实现国家人口均衡发展等正外部性影响。社会连带的实现方式包括通过育儿假制度限制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使得其不得在劳动者请育儿假照顾孩子期间解除劳动合同,以及通过普惠性的育儿津贴或社会保险等将育儿假期间产生的收入下降风险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予以分散。但是,强调社会连带也并不意味将个人埋没于社会全体的利益之中从而牺牲个人的自由,①在育儿假中,劳资双方仍有基于自身利益作出自由选择的空间,如劳动者可以在假期满前提出复职申请,同时用人单位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推迟给予劳动者育儿假或者在复职时变动其工作岗位。
(二)育儿假的法律属性考辩
育儿假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劳动者的权利。尽管我国绝大多数地方立法未将劳动者休育儿假定位为一项权利。但在比较法上,将育儿假作为权利已成为多个国家的制度事实。②欧盟在其《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③和《关于父母和照顾者工作与生活平衡指令》④(以下简称《工作与生活平衡指令》)中也采用了育儿假权利(right to parental leave)的表述。我国亦有学者认为男女享有对子女照顾的“育儿假”的休假权。⑤笔者赞同该观点,并认为育儿假是劳动者基于亲自照顾孩子的需要而请假并获得劳动保护和经济补偿的权利。该权利具有下列特征:
1.在权利性质上,育儿假权利属于形成权。尽管劳动者的请假行为在形式上看似在行使某种“请求权”,但是,与请求权旨在要求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目的不同,请育儿假的目的在于将劳动者不能提供劳动给付的事实及其障碍存续的长度通知用人单位并由其确认。⑥将其解释为以劳动者单方意思表示并依据法律规定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权利义务的结果,即行使形成权更符合法理。在德国,立法和学理通说也认为劳动者请育儿假的权利是形成权,只要具备法定资格、文件齐备且于法定期限内提出,一经提出即产生免除勞务给付义务之法定效果。⑦
2.以是否可在父母间转让为标准,育儿假权利可分为家庭权利(family right)和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前者意味着假期可以在父母间任意转让;后者则相反,假期只能由父母一方使用,相互间不可转让。⑧20世纪70年代,随着各国在政策上朝向更高程度的性别平等迈进,大多数国家都将育儿假规定为家庭权利。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即使两性都有权利请育儿假,但实践中通常是由女性使用。⑨因此,各国政策的关注点逐渐聚焦育儿假中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利上。因为研究表明,在将假期规定为个人权利的国家,父亲休育儿假的比例往往更高。⑩1993年,挪威创造性地在家庭育儿假中增添了父亲配额(father's quota),即在育儿假中指定一个月是专给父亲提供的假期,父亲不休则视为放弃权利,不能转移给母亲。挪威的做法提高了父亲的育儿假使用率,其他北欧国家纷纷效仿其做法。目前,在多数国家,育儿假通常是家庭权利,但有一定的期限是留给母亲或父亲使用的。
(三)育儿假的法律关系内容
育儿假的法律关系内容是指育儿假所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实中,存在劳动合同当事人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导致合同没有得到履行的客观状态。①其他国家将其纳入“劳动合同履行障碍”“劳动合同中止”制度中予以规制。我国在地方立法和学理上也存在“劳动合同中止”概念,②尽管这一概念及其内容仍有较大争议,但也存在共识,如中止期间劳动关系存续及劳动者有权获得部分劳动保护。笔者认为,育儿假属于劳动者因亲自照顾孩子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客观状态,可以适用劳动合同中止的法理,并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调整假期间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具言之:育儿假期间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性质可以分为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前者又可以根据主体的不同进一步区分为个别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集体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个别劳动关系上,第一,劳资双方保留劳动关系,但主给付义务暂停或间歇性履行,劳动者免除劳动给付义务或减少劳动给付的时间;根据对价原理,用人单位也无需或仅需支付部分工资。第二,劳资双方仍应当履行相应的附随义务。例如,用人单位应履行照顾义务,并将职位空缺和技能培训等信息告知劳动者,使其可以及时申请或参与;劳动者应履行忠诚义务,且不得参与和育儿相冲突的工作。在集体劳动关系上,休育儿假期间,作为工会会员的劳动者仍然享有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如参与集体协商。针对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在劳动者休育儿假期间应有权获得社会保险支付的育儿补偿并继续参加社会保险。具体来说,生育保险应当支付育儿假期间的待遇(下文述)。对于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在劳动者完全不工作时,用人单位所承担的缴费由政府补贴,劳动者承担的缴费可延迟至恢复工作后分次补缴;在劳动者缩短工时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仍需按照新的工资标准缴纳保险费。对于工伤保险,在劳动者完全不工作时无需缴纳,在劳动者缩短工时时由用人单位按照新的工资标准缴纳保险费。
三我国育儿假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育儿假立法的现实必要性
1.落实我国积极人口生育政策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二孩、三孩政策的相继制定以及法律的修改,是关乎中国千家万户的大事,是一项重大的法律变革,必须于法有据。③在我国,育儿假制度的首要功能是落实积极人口生育政策,以应对人口结构不均衡的危机。当前,少子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趋势。如表2所示,我国人口出生率近5年来逐年下降,2020年的出生率首次跌破10‰。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仅在2016年回升,随后逐年降低;2020年出生人口与2019年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程度在10年内却不断加深,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接近中度老龄化阶段,预计2035年前后将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在劳动力市场中,生育将使得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用人单位则需要对其提供劳动保护且安排其他劳动者顶替工作,如果贯彻劳动自由原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人单位将减少对女性的雇用,而女性出于职业发展的考量很可能会选择延缓甚至不生育,最终导致新生劳动力的削减和人口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因此,国家有必要通过育儿假立法,适度干预劳动自由,明确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受保护的时间内照顾孩子并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从而服务于优质劳动力再生产,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积极生育政策目的。
2.推动我国生育假期制度完善的契机。长期以来,我国生育假期制度发展较为缓慢和滞后。主要体现为:第一,生育假期的理论研究不足。生育假期包括其他劳动法上的假期制度更多被置于劳动者休息权的研究范畴①,或者聚焦其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等价值,②对于休假制度的内部构造尤其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研究较少。第二,生育假期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劳动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虽提及产假等生育假期,但整体上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于产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其他生育假期则语焉不详。第三,生育假期的功能定位不清。生育假期在我国以98天的产假为基础,以奖励性生育假期(包括奖励性产假、男性护理假、哺乳假及育儿假)为补充,后者随着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行而逐步增长。但是,除基础产假以外的生育假期均承担了育儿的功能,甚至有地方通过扩大基础产假赋予其育儿功能,③导致了不同生育假期间的功能发生混淆。第四,生育假期和社会保险的衔接不畅。对于基础产假,立法规定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支付,但存在社会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即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的生育职工,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对于其余生育假期,多数地方的生育保险并不支付生育津贴,而是规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在岗职工的标准支付待遇。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对育儿假进行统一立法,将休假法理融入育儿假的制度设计、细化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厘清育儿假与其他生育假期的功能边界,以及引入社会保险对育儿假期间劳动者所得丧失予以补偿,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生育假期制度的完善进程。
3.地方立法难以保障育儿假的有效实施。由于我国育儿假在全国层面的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育儿假在事实上通过各地立法予以落实;但从现实来看,地方立法难以保障育儿假的有效实施。第一,地方性立法由于效力位阶不高且多为鼓励性立法,企业缺乏执行动力。据报道,许多地方的用人单位在请假申请中未列入育儿假,以总部未出具育儿假相关细则拒绝员工的育儿假申请,④以生孩子后领结婚证不批育儿假⑤,以及以未见红头文件为由拒绝劳动者休育儿假①等问题逐步出现。尽管其中有部分企业及时准假,但个案的事后补救无助于问题的普遍解决。第二,省级行政区及其下属的地方性立法之间也出现了相互抵触的情况,如《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其育儿假分配给男方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育儿假分配给男女双方明显存在冲突;又比如在甘肃,省级的育儿假与地级市的育儿假在外延和内涵上并不相同。②第三,不同省之间的地方性立法也存在差异性,导致了公平性不足的问题。例如,重庆、陕西等将收养孩子也作为给予父母育儿假的情形,而大多数省并没有作出类似规定,导致在这些省的被收养孩子及其养父母难以享受照顾权益和履行照顾义务。例如,大多数省规定劳动者休育儿假可以连续或者分散休,但仍有部分省如吉林、河北等并未作出规定,导致这些省的育儿假在执行过程中,可能由于灵活性不足而出现单位不准假,或者假后影响复职的问题。对此,制定国家层面的育儿假立法,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可以有效克服地方性立法各行其是所产生的弊端,推动育儿假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育儿假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1.宪法提供了立法基础。宪法是国家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③由此,我国《宪法》也为育儿假奠定了立法基础和制度依据,具体体现为:第一,《宪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妇女和男子应当在经济和家庭生活中等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通过育儿假立法,可以有效贯彻本条规定的性别平等原则,保障男女劳动者平等享有工作权利和共同履行育儿责任,消除或逐步松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第二,《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同时第3款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表明国家在儿童照顾上同等重视父职和母职,并努力实现婚姻和家庭福利的最大化。对育儿假进行立法既是为了需要关爱的孩子,也是为了需要时间与孩子建立关系的父母。④对儿童而言,其作为人具有原生的天赋权利……获得父母的细心抚养,直到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为止。⑤育儿假为父母共同履行抚养义务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对母亲而言,父亲休育儿假可以减轻其因独自照顾孩子而带来的身心负担,使其更容易从妊娠和分娩中恢复并重返职场。对父亲而言,通过休育儿假参与早期的幼儿照顾工作使其更能体谅女性育儿的艰辛,并在后续的育儿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家庭的幸福感和对婚姻的满意度,实现《宪法》所保障的价值取向。
2.地方立法实践已有探索。尽管我国地方立法和试点实践存在若干弊端,但整体而言仍不失为试验性规制制度在劳动法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⑥其中的经验性收益和反思性收益有助于为未来的育儿假立法提供经验。具体来说,地方性立法作出了若干务实的规定,如将育儿假适用的儿童年龄定位为0—3岁与我国幼儿园最低入园年龄相符;此外,各地还明确了一些制度细节,如育儿假是工作日,其中的“每年”按照子女满周岁计算。有的地方甚至作出了较有新意的探索,如北京市规定育儿假可以在父母中进行分配,重庆市规定育儿假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请一年等。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对育儿假的立法和实践累积了较大陆更为丰富的经验,亦值得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施行细则”以及“育婴留职停薪实施办法”构成了育婴假的规范基础,具有可操作性,其中,“留职停薪”的表述更是从法理上明确了育婴假的性质为因照护幼儿而中止劳动契约。①此外,台湾地区“就业保险法”还规定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给付项目,以社会化的方式分散了劳动者因休育婴假而导致的收入损失风险。上述地方立法实践的有益探索可以为全国性立法提供必要的参考。
3.域外立法经验可供借鉴。在育儿假立法方面,域外国家和地区相比于我国积累了更多的有益经验,可在结合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予以借鉴。例如,作为世界首个制定育儿假政策的国家,瑞典的《育儿假法》经多次修订后,明确赋予父母劳动者可转让的共同育儿假(300天)和不可转让的专属育儿假(各90日),且通過收入替代(正常工资净收入的80%)和固定费率(60瑞典克朗)两种模式给予劳动者育儿津贴,并对父母平等休假予以奖励,旨在强调共同照顾的价值。②德国于2006年颁布《联邦父母津贴和父母假期法》,该法共28条,前14条规定了父母津贴的领取规则,第15条以下则是劳动者申请父母假期的规则。父母津贴由税收承担,不仅考虑到了父母收入的计量,而且设计了“附加津贴”等激励父母休假的机制。③日本于1995年颁布《育儿和家庭照顾休假法》,该法规定了劳动者和雇主基于育儿假产生的权利义务(包含劳动者申请、变更和撤回育儿假的权利和雇主不得拒绝及禁止不利待遇的义务等),④并于2021年的最新修改中增加了若干促进男性休假的措施。⑤此外,对于休育儿假的被保险劳动者,日本通过雇用保险向其提供休业给付。欧盟则先后于1996年、2010年和2019年颁布《育儿假指令》及《工作与生活平衡指令》,逐步将育儿假从平等的家庭权利向不可转让的个人权利与家庭权利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并强调育儿假的有偿性和灵活性。⑥对于域外经验,可以在吸收其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社会发展状况予以调试。
四我国育儿假立法模式选择与具体规则设计
(一)立法模式选择
在立法模式上,我国育儿假应当实现从单独立法向综合性立法的转变。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方立法将育儿假制度规定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少数规定于《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和《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表明立法者倾向于认为,育儿假在宏观上属于积极生育政策的法律化,在微观上则属于为女性(劳动者)提供的特殊保护制度,后者在机理上与产假并无二致。然而,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着眼于人口结构的宏观调控,涵盖了人口规划、生育调节以及生育服务等庞杂的内容,难以对育儿假这一具体制度作出细致的规定;而由前文可得,育儿假制度的目的并非基于生理差异而给予女性特殊保护,而旨在贯彻育儿作为父母共同责任这一理念。因此,笔者认为,将育儿假制度规定于女性或女职工权益保障类立法中并不适当,容易传达女性作为弱势性别群体的信号,与育儿假所追求的性别平等理念相悖。个别国家将育儿假规定于劳动法体系,如加拿大联邦将育儿假纳入《劳动法》,各省则纳入其《劳动基准法》。①对此,笔者认为,育儿假不仅是一种劳动基准,同时还具有人口政策和公共福利的属性,其所涉成本的分配需要更多社会化的制度设计,故不宜简单纳入劳动基准法或劳动法。综上,本文认为,在短期内,我国在立法模式上宜参照瑞典或德国,以单独立法的形式出台《育儿假法》或《育儿假实施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待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成熟后,再参照日本或我国台湾地区,制定统一的《家庭休假法》②或者《性别平等工作法》,通过设立专章对育儿假进行规定。
(二)具体规则设计
1.程序规则设计。第一,劳动者请假的规则设计。劳动者休育儿假意味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提供劳动,对此应提前告知用人单位,为其安排接替者留出时间。同时,由于休育儿假涉及一系列私法和公法上权利义务的变动,应当将相关情形通过书面形式予以固定。申言之,劳动者计划在产假或护理假结束后休育儿假的,应当提前以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此处涉及三个待决问题:首先,应提前多久?对此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如日本为1个月,德国为7周,瑞典为2个月)。基于提前通知的目的是让用人单位有时间寻找接替的劳动者,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劳动合同法》中关于预告辞职的规定,将劳动者提前通知的期限确定为1个月。其次,书面形式包括哪些?学理上对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历来存在争论,但如果基于劳动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点,③则书面形式不仅包含纸质文件、也包含其他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④笔者赞同该观点,并进一步主张,劳动者以口头形式请假的,秉持法律行为有效性原则,⑤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书面补正,仍应自补正之日认可其请假的效力。再次,告知的内容包括哪些?结合域外立法和实践状况,笔者认为在申请书应载明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子女出生的具体时间、对子女享有监护权且共同居住的事实及证明、请假的具体时间段等。最后,用人单位如何进行回应?基于育兒假的形成权属性,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劳动者的申请,至于是否可以基于某些理由推迟给假,各国态度不一。欧盟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指令》规定成员国可以决定是否允许雇主在某些情况下推迟给予育儿假。笔者认为,劳动者请育儿假的权利原则上不应附加特殊限制,因为从法理上看,既然形成权相对人必须接受他人行使形成权的事实,那么不应该再让他面临不确定的状态了。⑥然而,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如果劳动者在指定期间内休假会使用人单位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则后者可以推迟给假,此时应当提供书面证明并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核,且必须在困难消失后给假,否则劳动者有权要求给假并请求赔偿,还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二,劳动者销假的规则设计,基于与请假相同的理由,劳动者的销假即复职申请也应采用书面形式;但与请假不同的是,劳动者复职时可能无法胜任原工作,或工作岗位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动,导致能否恢复先前的履行状态不无疑问。劳雇之间因受雇者留职停薪育婴发生争议,有相当高的比例与复职有关。因此,雇主对复职申请的回应需立法重点关注。笔者认为,对此应分两种情况讨论:首先,劳动者在休假期间申请提前复职。如果用人单位此时已经通过劳务派遣等方式使用替代劳动者,为顾及该劳动者的期待利益,应赋予用人单位选择权,既可以选择拒绝复职请求,也可以和劳动者协商以其他灵活方式工作至育儿假结束。如果用人单位仅安排本单位其他岗位劳动者暂时顶替,则原则上用人单位不得拒绝,但可以基于留出一定时间办理任务交接等原因安排推迟,同时应设置时间上限。其次,当劳动者育儿假休满后复职,原则上应当恢复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和地点,用人单位不得拒绝,但如果有正当理由,如用人单位依法变更组织、解散或转让,或者企业业务性质变更等原因,导致原工作岗位已经不存在,基于利益平衡原则,用人单位可以对其指派新工作,但新指派之新工作仍应与受雇者之原有工作相当,尤其是劳动条件不可降低。①
1.实体规则设计。第一,育儿假的覆盖范围。首先,笔者认为,将育儿假的覆盖范围仅限于拥有完满婚姻状态和家庭形式的劳动者不具有正当性。从理论上说,任何劳工,不论性别、社会阶级、婚姻状态或家庭形式,若有育婴需要,都应享有这样的权利。②因此,应逐步将育儿假拓展至有育儿需要的单身父母、养父母和继父母等。其次,当前育儿假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职工即具有传统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对不具有传统劳动关系的职业劳动者如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则无规定。该群体绝对数量较大且逐年增加,对于新业态企业具有一定的从属性。更重要的是,该群体与普通劳动者一样需要面对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难题。在德国,男女劳动者、学徒、家庭工作者以及类似的人都可以请求给予父母假期。③欧盟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指令》也确认了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将育儿假适用于所有工人,包括非典型工人(如非全日制工人、定期合同工人等)。④基于此,笔者认为,育儿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可以考虑以职工为主体确立一般性规则,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非职工群体设计特别规则,以体现数字时代背景下育儿假立法的包容性。
第二,育儿假的休假条件。对此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可供借鉴。在德国,根据《联邦父母津贴和父母假期法》第15、16条的规定,请假者原则上应当满足以下条件:是劳动者,与孩子共同居住以及亲自照顾和抚养孩子。⑤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育婴留职停薪的条件包括:受雇者任职满6个月,有不满3岁的子女以及其配偶已就业。⑥笔者认为,首先,立法宜规定劳动者应连续工作满1年。从劳资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对劳动者请育儿假设置1年的等待期可以避免劳动者在短暂就业后即请假离开岗位给用人单位带来的不安定状态,同时也与继续性合同对信赖利益保护的要求相契合。⑦其次,立法应当设置“和孩子共同生活并亲自照顾和抚养孩子”的条件。不同于怀孕和分娩,育儿工作并非要本人亲自完成。然而,考虑育儿假的目的在于满足父母亲自照顾孩子的需求,对于那些事实上无法参与育儿(如因工作原因长期不在孩子身边)的情形,不宜给假。再次,立法不宜采纳“劳动者配偶已就业”的要件,因为该规定意在表明如果劳动者的配偶未就业,应当由其照顾小孩,劳动者请育儿假不具有正当性。然而,对于父母双方均有意同时停薪留职共同经历抚育子女之受雇者,此制度无适用空间。①因此,为鼓励职工父母同时参与育儿,应不采该要件。最后,育儿假对应的儿童年龄区间因国而异,从1岁(加拿大等)、1岁半(瑞典等)、3岁(德国等)、6岁(韩国等)到8岁(欧盟等)均有。笔者认为该问题并无标准答案,且儿童年龄区间与具体的育儿假期限在实践中通常也并不重合,我国多数省规定孩子在3周岁以内可休假,主要是考虑3岁是幼儿园的最小入园年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不予变更。
第三,育儿假的休假期限。育儿假的休假期限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标准(见表3),从3个月到100个月不等,但表3的中位数和众数均为12个月。鉴于我国目前各省規定父母每年各享受的育儿假为5至20天,3年间共有育儿假1个月至4个月,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较短的假期,难以在实质意义上发挥育儿作用。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借鉴表3中多数国家的立法期限,规定育儿假的期限为12个月,自产假或护理假结束后可以使用。一方面,育儿照护需求最迫切的年龄段是孩子出生至1周岁,该段时间内孩子尚未形成说话、行走等技能,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照顾。另一方面,在域外,规定12个月的育儿假与实践情况基本相符,如在加拿大,尽管可以请育儿假的最早和最晚的时间点在各省并不一致,但算起来使用育儿假,各省的规定,多为应在小孩出生1年左右使用完其假期。②在日本,育儿休业期间是在该子女达到1岁前的连续期间。③
第四,育儿假的休假方式。由于育儿假的期限较长,有必要采取灵活的休假方式,一方面有助于平衡劳资利益。劳动者可以在获得育儿时间的同时维持和职场的联系,用人单位也可能不需要支付寻找和雇佣替代劳动者的费用。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双亲,特别是父亲请休的可能性。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其一,立法应明确育儿假采取家庭权利和个人权利的混合模式。允许父母根据工作和育儿的实际需要在彼此间进行转让,同时,为了避免工作父亲将假期转移至工作母亲身上,应规定前者休满不低于一定时长且不得转让的配额育儿假,不休满将失去所有的经济补偿。其二,在休育儿假的全过程中贯彻灵活性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灵活的育儿假主要有七种形式,包括以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方式休假;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或几个较短的时间段休假;选择休较长时间的低福利假或较短时间的高福利假;将休假权利转移给非父母照护人;父母可以选择休全部或部分假期,直至子女达到某个年龄;生多胞胎或少数其他情况下的额外假期;父母双方同时休全部或部分假期。①笔者认为以上几种方式均可为我国所借鉴,立法可以初步规定在产假或护理假使用完后至孩子1岁内,父母可以完全脱离工作岗位,每次以周或月为单位,连续或交替请育儿假;在孩子1至3岁时,父母可以通过缩短工时的方式在部分时间离开工作进行育儿,包括可以采用休半天、四分之一天甚至八分之一天的方式累计计算。在数字时代,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实施远程办公尤其是在家办公,使雇员将部分时间用于承担家庭责任或者在工作间隙承担家庭责任。②对于单身父母,可以将部分育儿假权利转移给同为劳动者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等。
第五,育儿假期间的经济补偿。在世界范围内,育儿假期间的经济补偿有以下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其一,雇员责任模式。该模式以美国为典型,指雇员休育儿假没有经济补偿。然而,研究表明,在实行无薪育儿假的情况下,两性休假的比例都很低,③故该模式不可取。其二,雇主责任模式。该模式为我国多数省采用,指劳动者休育儿假期间的待遇完全由雇主支付。该模式无限拓宽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会自发减少对女性的雇用以将内部责任外部化,从而加剧对职场母亲的“惩罚”,故该模式也不可取。其三,社会保障模式。该模式在国际社会较为普遍,又包括社会福利模式和社会保险模式。前者以德国为代表,其通过社会促进(相当于我国法律语境下的社会福利)之给付,以国家税收而非保险的方式提供育儿津贴。我国个别城市也采取了社会福利的育儿补偿模式。④后者可进一步区分为失业保险(或称就业保险)负担模式和生育保险负担模式。前者以加拿大和日本为代表;后者暂未在比较法上找到先例,我国大陆实行生育保险制度,但对于产假以外生育假期的经济补偿未作规定。我国有学者指出应通过失业保险支付育婴留职停薪津贴。⑤本文认为该观点有合理之处,但主张当前仍宜通过生育保险负担育儿假的经济补偿,理由有三:一是育儿假负有平衡工作与家庭的任务,只能以工作群体(包括职工和非职工劳动者)作为保障对象,应采取团体性的社会保险模式而非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模式。二是通过失业保险支付须对“失业”概念进行扩大解释,涵盖因育儿而暂时中断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情形,由于此涉及立法理念的转变,短时间难以完成;而通过生育保险支付的制度阻力则较小。三是我国规范性文件更加强调生育保险制度对于优化生育的作用。⑥
关于育儿假期间的待遇项目及其标准。笔者认为待遇项目至少应包括基本育儿金和育儿奖励金两大部分。其中,基本育儿金应当与劳动者收入相挂钩,以避免本就持有较高收入的男性劳动者因收入骤降而拒绝休假。具体的标准可以设定为孩子出生前12个月本人平均工资的67%左右。如果父母仍然从事部分工作,获得部分收入,那么基本育儿金的额度可按照现在收入和原来收入差额的67%标准计算。此外,还应设定最低标准以保障低收入劳动者。为鼓励男性休育儿假,可以为休假的男性加发基本育儿金,具体比例可以根据受照顾孩子的年龄确定,如孩子在出生头两个月照顾可增加25%的基本育儿金,出生3至4月照顾可增加20%,以此类推。育儿奖励金则是对父母共同使用育儿假的家庭提供奖励,以激励父母更加公平地分担育儿责任从而促进性别平等。我国可参照德国的合作育儿奖金(Partnerschaftsbonusmonaten)和瑞典的性别平等奖金(Gender Equality Bonus)进行制度设计,前者规定如果在儿童出生后父母双方的工作时间均连续4个月在每周25—30小时,则父母双方可以分别获得额外4个月的合作育儿奖金。①后者规定父母在各自的共享育儿假期间,每共同休1天育儿假将获得免税的奖金;当父母各休了一半的育儿假时,奖金数额最大。②最后,对于特殊群体如单身父母或养育残疾孩子的父母,可以单独设计特别规定,确保其享有的待遇标准不低于双亲共同抚养者所享有的待遇。
五余论
育儿假的出台使我国生育假期体系初步形成,但强烈的政策宣示性并没有体现该制度本身的机理和机制。本文以育儿假的概念、规范现状与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从法理层面探讨了育儿假的理论基础、法律属性及法律关系内容,并在证成育儿假立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基础上对我国育儿假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具体规则的构建提出建议。本文旨在主张通过立法将育儿假塑造为工作者养育子女的专属制度,该目标的实现不是短期的,尤其在松动传统性别分工上任重道远;更不是孤立的,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将涉及整个生育假期体系的调整,特别是当下应当遏制产假、护理假的延长趋势并适时减少休假天数,使其回归女性保护的目的;同时逐步取消哺乳假,避免与育儿假发生功能上的冲突。其次是实现育儿的社会化。在育儿假之外,应对非劳动者群体但有育儿需求的公民提供福利式的育儿津贴,完善儿童照顾公共服务体系,方能有效缓解家庭的育儿责任、平衡家庭和工作乃至提高生育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Legal Analysi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arental Leave in China
LI Fu-cheng
Abstract:China's parental leave is faced with lack of operability in central legislation and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in local legislation,so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specialized parental leave legisl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basie legal princi- ples.At the legal level,parental leav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ork-family balance,gender equality and social solidarity, which has the attribute of rights,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various subjects ar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abor contract. Due to need to implement the population fertility policy an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er- tility leave system,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local legislation is difficul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aren- talleave,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make special legislation on parental leave. The constitution has provided the legisla- tivebasis,the local legislative practice and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abroad also proved the feasibility of legislation.At the legislative level,the legislative mode of parental leave in China should change from short-term separate legislation to long- term systematie legislation; in terms of specific rules,the procedural rules for asking for leave and retuming from leave,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rules for coverage,leaveconditions,leaveduration,leavemode,economiccompensation,ete.of parental leave should be constructed simultaneously.
Keywords:parentalleave;matemityleave;gender equality; matemity insurance
【責任编辑:陈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