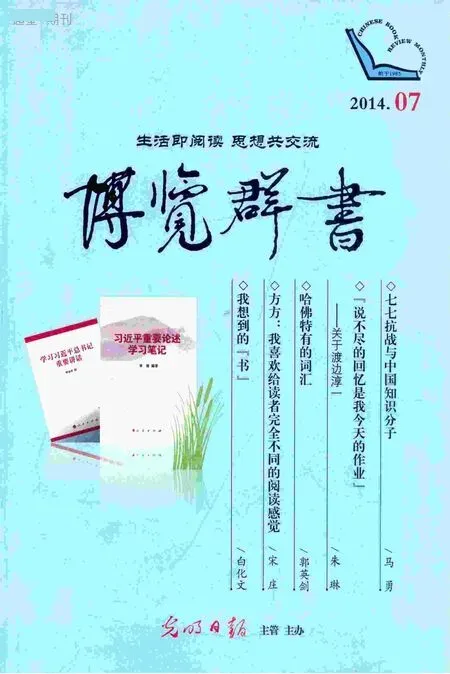这两部电影对鲁迅原作的误读与反哺
张嘉欢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是文艺创作界约定俗成的现象,文学作品为影视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与精神源泉,影视作品对文学原著的搬演与创造为原作创造讨论与读解的话语空间,实现意义层面上的反哺,比如鲁迅经典作品《祝福》《阿Q正传》影像改编过程。
十七年到新时期:影像改编的时代烙印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毛泽东曾评价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先生的一生铸就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块不朽地标,“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也在鲁迅手中成熟”,可以说,鲁迅早已不再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其本人及作品纠缠了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多个方面。迄今位置,鲁迅的多部小说都被搬上大银幕,如《祝福》《阿Q正传》《伤逝》《药》《铸剑》,在鲁迅作品改編的电影作品中,《祝福》《阿Q正传》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两部影片在剧作上基本符合了原著的主题精神,又在细节处做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祝福》《阿Q正传》两部影片分别上映于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分别是“十七年”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电影创作者在基本还原原著的基础上对原著的多重主题进行了筛选处理。
新中国建立初期,旧时代的苦难记忆与新时代的朝气蓬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民众的普遍心态,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承载着抚慰旧时代创伤与高歌新时代风貌的作用。回看1956年桑弧导演、夏衍编剧的《祝福》,影片开始与结束的画外音颇有意味,影片伊始,一段画外音拉开故事序幕:
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多年以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山村里……
结尾处,影片又以一段画外音结束:
祥林嫂,这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两段画外音首尾呼应,其中,《祝福》本身的复杂性被暂且搁置,影片把矛头首先指向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立上,通过祥林嫂的悲惨境遇构建旧时代社会的创伤记忆,借此使民众由衷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内涵,从而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细节上,电影版《祝福》不同于原著的地方有多处,比如在人物的设置上,影片完善丰满了祥林嫂的第二任丈夫贺老六这个人物形象,增添了几处原著没有的情节。譬如在影片开始增添了卫老二与祥林嫂的婆婆商量将祥林嫂卖给别人的情节,在祥林嫂与贺老六成亲后增加了地主七老爷、王师爷上门讨债的情节。影片中人物的增删和情节的组织强调了旧时代底层人民的悲剧性以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性,在对旧时代的鞭挞中巧妙地将国家认同、阶级情感与革命意识编织在一起。
1981年,恰逢鲁迅100周年诞辰之际,由陈白尘编剧、岑范导演的《阿Q正传》登上荧幕,电影版《阿Q正传》以“我”为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在叙事逻辑上基本与原著吻合。与原著相比,岑范改编的版本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其一是对原著中悲剧色彩的冲淡与喜剧化的凸显。其二是电影的改编着重侧重于对“哀其不幸”的渲染,淡化了“怒其不争”的表现,岑范在谈及《阿Q正传》的构思时,坦言对阿Q这个人物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对“怒其不争”的处理不够深入。电影另一处对原著的改写也颇有意味,即把原著中见风使舵的土谷祠老头做了美化处理,影片中,以土谷祠老头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善”与以赵太爷为代表的旧社会势力的“恶”形成鲜明对比。其三是影片对“个人”的强调顺应了80年代初以人本主义思潮为核心的人文语境,脱离了80年代之前电影集体主义元叙事的固有范式,将目光聚焦到“个人”,这也体现出编剧和导演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误读”与“重构”:改编错位中的价值再生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缝合”的概念,用来指代主体生成语言意义的机制。在拉康看来,能指具有先于所指的优越性,“缝合点”的建立作为一种基础意识形态的运作将处于漂浮滑动状态的能指串联起来,缺失感得到想象性的满足。继拉康之后,法国理论家让 - 皮埃尔·欧达尔首次将“缝合”理论应用于电影分析中,他认为,电影观众所看到的电影的“所指”只是创作者想让观众看到的部分,而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则被隐藏在叙事结构与情节之中。
如果说电影版《祝福》《阿Q正传》的创造性元素是特定时代电影创作者的一种不可回避的叙事缝合手段的话,那么这种对原著的“编码”究竟是不是一种误读?
夏衍版本的《祝福》有几处改编是历来学者们广泛讨论是否构成“误读”的焦点,其中较为典型的即是祥林嫂砍门槛这一情节。原著中,祥林嫂对“捐门槛”的热衷以及重复提及的“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是最能表现底层民众受封建迷信荼毒的情节,毫无疑问,在祥林嫂的认知中,人死了以后是有魂灵的,并且祥林嫂对此是极为忌惮的。而电影对祥林嫂砍门槛这一情节的改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物性格的错位。诚然,在影片创作的年代,砍门槛这一情节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时代精神的融注使影片呈现出极具辨识性的政治刻痕,在这个层面上,“误读”与否也难以客观评判了。另一处对影片“误读”的讨论是叙事结构与叙事视角的转变,原著小说采用倒叙形式以及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在这个视角模式下,读者完全跟随“我”的视角去了解故事原貌。而夏衍版本中则删去了“我”这一人物,叙事视角从内聚焦转变为外聚焦叙事,按照顺序的方式组织故事,这样做虽然简化了叙事结构,但无疑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鲁迅原著里的“我”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而存在,“我”的设定映射着鲁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的批判,而电影的删减弱化了原著的批判力度,只是将批判重点着重放在阶级压迫上,呈现出极大的时代局限性。岑范版《阿Q正传》倒是保留了“我”这一说书人的角色,叙述视角几乎未做改动,但依然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照搬割裂了叙事的完整性,由此可见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之间的某种不可调和的“壁垒”。
电影对原著人物的调整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夏衍版《祝福》争议较大的一处是对贺老六这一形象的改动,在原著中鲁迅对贺老六这一人物着墨不多,而电影中有关贺老六的情节则较为丰富。夏衍版本中,贺老六忠厚老实,且电影还呈现了一段祥林嫂与贺老六婚后相濡以沫的温馨日子。然而,鲁迅在原著中意在揭露封建社会妇女身上的三座大山——夫权、父权、族权的层层压迫,电影的改编则将“夫权”剥离出去,将贺老六这一人物置换成地主阶级的压榨对象,把贺老六、阿毛的死归因于地主七老爷、王师爷的催债,在情节编码中巧妙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再一次完成了话语的置换与意义的重构。与之相比,岑范版《阿Q正传》秉承着“宁可笨拙,不可油滑”的改编态度,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做了较为成功的演绎,但影片对原著中几个次要人物的改编也呈现出“误读”倾向,一是前文提到的土谷祠老头的美化处理,二是对吴妈形象的处理模糊不清,原著中阿Q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完全是出于长久以来的性压抑,是完全不带有任何情愫的,而电影中则对二人之间的情愫进行了刻画,削弱了原著的讽刺意味,增添了喜剧色彩。再就是小D这个人物,影片结尾众人在酒馆议论阿Q被枪毙的事情,小D义愤填膺地说“我看呐,阿贵哥还是一条好汉!”,说完愤然离席,在鲁迅原著中,小D作为未庄里与阿Q一样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不该有如此高的思想觉悟的,影片结尾对小D这一人物的改写略显生硬。
实际上,“误读”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在20世纪前的传统阐释学中,误读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取的阅读或阐释行为,然而当代阐释学和现代语言学将误读现象放到阅读论的体系之中,重估了“误读”的意义再生机制。1987年法国学者罗贝特·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将“误读”解释为一种“创造性的背叛”,由于时空距离造成的文化背景的变化是改编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而某种意义上“误读”不可避免。在对鲁迅的改编与演绎中,意义的重构与置换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正如葛林伯雷所说:权利和政治不仅活跃在历史再现中,而且还活跃在那些话语的阐释中。如果说前文提到的种种改编细节是囿于创造者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等因素合力下的一种不得不采取的“误读”策略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原作的“改写”与“过滤”也体现出电影创作者“贵在有我”的主体意识的彰显,这种“筛选”与“过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内涵。
跨媒介到跨文化:文学经典影像化的传播策略
鲁迅的作品是人类文化的宝库的一部分,自1909年日本报刊介绍鲁迅兄弟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的消息至今,鲁迅的海外研究迄今为止已经有了110年的历史。在中外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鲁迅的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文学领域乃至社会领域都有着廣泛的影响。相较鲁迅文学作品的光芒,由鲁迅经典改编而成的电影则黯淡得多。在为数不多的几部由鲁迅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中,1956年版的《祝福》与1981年版的《阿Q正传》算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两部。尽管学界对于两部影片的艺术成就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两部影片的改编实践为文学经典影像化的演绎与传播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文学经典的跨媒介改编最为核心的原则即是对原著即原作者的尊重,正所谓“忠于原著,慎于翻新”,较于一般文学作品而言,经典具有典范性、权威性,是被历史“选择”过的精髓,因而对经典名著的改编需要慎之又慎,情节的增删应考虑到作者的本意与思想内涵,抓住原著的整体气质与精神内核。但是,既然是“改”与“编”,那就意味着不能完全照搬原著,夏衍认为:“改编不单是技巧问题,而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改编者的世界观问题。每个改编者必然有他自己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总是反映到改编作品中去的。”反观夏衍版《祝福》与时代政治的对话以及《阿Q正传》对整个“80年代”的呼应,可以体认的是,改编并非是简单地从文学到电影的跨媒介转换,它既应是与已经成为“历史”的原作品的对话,又应是与正在发展着的“现实”的对话,基于此,文学、电影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某种微妙的“不可融合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调和。其次,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在构成要素、修辞风格以及接受方式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电影改编本质上是一项跨媒介叙事活动,改编者应从电影的媒介特性出发确立改编的原则。但凡成功的电影改编,一定是文学“电影化”了的产物。因而在对原著作品进行选择与加工时,应遵循媒介本身的基本属性与艺术规律,把握好故事在不同媒介中的存在状态。时至今日,在媒介市场运作的艺术生产环境下,文学经典的影视化改编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创作活动,亦成了一项市场规约下的生产活动,在市场化运作体系之下,经典改编更应把握尺度、避免媚俗,在商业化策略与艺术审美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以实现新时代影视文本对经典原著的价值“反哺”。
近几十年里,鲁迅遗产一方面在学院派的话语表述中被不断演绎着,一方面又在导演、剧作家的改编实践中成为时断时续的母题。某种意义上来说,原著的跨媒介改编与传播过程亦是鲁迅经典得以延续的重要途径,而改编后的文本也将作为鲁迅“生命力”的一部分,在时间长河中等待进一步的读解与检验。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祥林嫂的悲剧原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