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与西南联大校舍委员会
陈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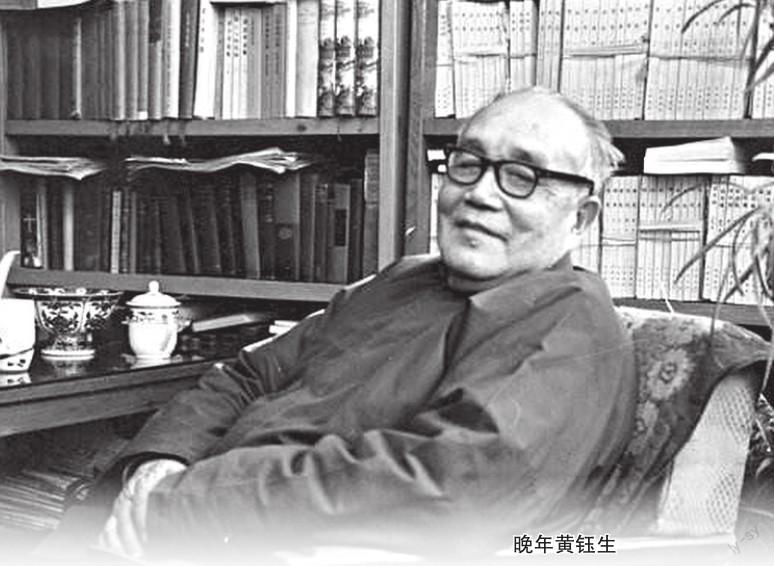
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形成于抗战中的艰苦环境。对办学来说,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校舍,而恰恰此事让流亡而来的师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正如陈岱孙所说,来到昆明,联大才真正意识到“成为一所被剥夺了办学物质条件的大学”。以往有过不少关于当时校舍困难的记述,但是要了解联大是通过怎样的工作应对难题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联大校舍委员会和其召集人黄钰生。
从建设长到校舍委员会主席
联大为解决校舍问题,曾设立建设处和校舍委员会。建设处运行时间较短,仅存在于1938年1月至8月。校舍委员会则自1938年8月成立,基本持续至联大结束。虽说先后两个机构、两种机制,但其负责人——建设长和校舍委员会主席均由黄钰生担任。
黄钰生(1898—1990)曾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留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回国后任教南开大学。联大时期,南开校长张伯苓一般不在昆明,黄钰生成为南开方面主要代表之一,参与联大常委会、校务会,还一度在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有事时,代为主持工作。
在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三校曾有北大负责教务、清华负责总务、南开负责建筑设备的最初分工。黄钰生遽然受命建设长,要安排众多师生上课与住宿。当时学生宿舍借用了清末旧军营,可是没有床。为了在地板上把稻草垫铺得厚一点,黄钰生“心急如焚地忙得不可开交”。
临大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久,按照国民政府要求筹设师范学院,黄钰生被推任为院长。师院不同于其他学院,自成体系,后又设有附属中学、小学,办有在职教师晋修班等,是一所“校中校”。黄钰生为专心治院,请辞建设长一职。学校同意并撤销了建设处。然而实际上,黄钰生并未因职务变动,卸去重任。
联大治校的一大特色是,每遇专项事务往往成立一个由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应对。这样不增设行政岗位和人员,充分发掘教授共同体的治校能力,择人任事,用人所长。这些委员会由常委会决定设立,向常委会报告工作,有的为常设,有的为临时。黄钰生参与过近30个委员会,并在其中十余个担任召集人。比如,他曾任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主席。1938年4月,联大成立建筑设计委员会。正带领学生步行赴滇的黄钰生受任为委员长,到达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舍建设。可是此时的校舍事务不仅仅是建筑设计,工作几乎从零开始。特别是1938年下半年,联大新生即将入学,曾驻蒙自的文学院、法商学院也将迁至昆明,解决校舍问题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30日校舍委员会成立,刚刚卸任建设长的黄钰生又担任起校舍委员会主席,再一次临危受命。
校舍委员会主要工作和机制
校舍委员会成立时共聘请来自三校的8名教授任委员,即黄钰生、樊际昌、沈履、冯友兰、吴有训、陈序经、施嘉炀、毕正宣。对照此时行政分工,樊为教务长、沈为总务长;冯、吴、施、陈、黄分别为文、理、工、法商、师范五院长;毕为总务处事务组主任。也就是说,该委员会包含了各行政、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随着人员流动,委员会也经历过改组。比如1939年增入训导长查良钊(训导长为本年新设);1940年沈履去职,继任总务长郑天挺加入。这些调整具有席位制特点。此外,工程处长王裕光、总务处会计组主任刘镇时及训导处诸人也曾参会讨论校舍事务,不过是作为委员,还是临时参与,有待再考。
由于校舍委员会并无专档,黄钰生也无相关记录、回忆存世,所以无法直接获知工作详请。但从近年逐渐披露的其他档案、他人日记、回忆资料中,仍可大致勾勒校舍委员会主要工作如下。
寻觅勘察。因为办学空间短缺,联大几乎始终在寻找用地用房。还在校舍委员会成立前夕,黄钰生任主席的建筑设计委员会觅定三分寺附近,进行测量清丈、征地建设,此后建起联大最主要的新校舍。然而一处校舍不足以安置全部师生,此后常委会记录中仍不时有黄钰生报告勘察校址、房舍情形。日军空袭下,联大几度计划疏散,比如1938年10月计划将师、理两院迁往晋宁县盘龙寺,1941年又觅地城郊梨烟村。虽然计划终未实施,不过档案、日记中可见黄钰生等反复勘察择地。1940年樊际昌、黄钰生等还曾赴四川泸县、叙永勘察,此后联大一度设立叙永分校。
建筑事宜。联大撤销建设处后,由工程处负责具体建筑事宜,但校舍委员会也深度参与前期谋划与后期验收。比如1941年9月,黄钰生向常委会报告筹建梨烟村校舍事,说偕同吴有训、郑天挺与工程师接洽,“据估计约需建筑费国币一百五十万元”。1943年3月,郑天挺约王裕光至黄家共商建筑学生宿舍事,“约需大小五十间,费在五百万左右”。1944年10月,黄钰生、郑天挺等验收昆中北院新建楼房后,表示“有不合式、不坚实者均令改造,然后验收”。
租赁房屋。联大还通过租房应对校舍不足。比如,1941年9月黄钰生曾向常委会报告向各方进行租赁情形。为避空袭,昆明本地学校曾疏散到晋宁、呈贡等县,腾出的校舍成了联大租用的重要房源。此外,联大还租赁多个会馆房舍。郑天挺日记记有一次签约现场:“至太华饭店与两广同乡会签两粤会馆租约,凡四条,租金年二万。”校方签字者为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但黄、郑等校舍委员是主要参与者。
校舍分配。校舍委员会成立之初即召开多次会议,拟出“本校校舍分配办法十四条”,经常委会审议修正后施行。不久,又通過了“校舍分配详表”“各建筑之用途详表”,对每处建筑每个房间进行盘点,对各单位办公、教学、住宿、后勤等用房进行分配。由于联大校舍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学生也有毕业入学等新情况,因此校舍分配不断调整,如档案中有1939年《新校舍分配决议》《二十九年秋季校舍分配计划》、1941年《租用之昆华中学校舍支配办法》、1942年《关于全部校舍分配的决议》、1944年《校舍调整办法》等。
除上述工作外,由于联大曾遭日军轰炸,校舍委员会还参与了修缮事务。如黄钰生、郑天挺曾“令工匠估价修缮前炸之小楼”。校舍委员会还曾开会“审查修缮账目”。
从史料中,不仅可钩沉校舍委员会工作情形,也可略探其运行机制。校舍委员会委员由常委会聘请担任,其中投入工作最多的是主席黄钰生和总务长郑天挺;各院院长作为委员,会在涉及本院用房时有针对性地参与工作。对一些问题,委员会开会商讨,经研究后提出方案,报常委会决策,最终根据常委会意见修正后公告施行。
校舍工作面临的难题
校舍委员会工作的背景是战火纷飞、客居他乡、物价飞涨、三校合作,因此必然面对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连性格温和坚韧的梅贻琦,也在一次和郑天挺、查良钊、黄钰生谈校舍难题时“颇觉恼丧”。
困难首先源于日军侵扰。校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战争造成的。联大为避战火来到昆明,又因敌军尾随而至,不得不随时准备疏散、迁校。联大校舍被日军当作轰炸目标,建好的校舍被炸,租用的校舍也被炸,在轰炸中还有联大人罹难。
其次是房源紧张。联大多处校舍租自本地学校,空袭稍稀时,各校纷纷希望回城,这本无可厚非,却令联大难以应对。1940年4月,昆华工校催腾校舍,联大校舍委员们约请其校长,希望续租一年,未获同意;7月,昆华中学教导主任上门索还校舍,“其势汹汹”;8月,昆华师范校长来索校舍,“坚执五日必须移让”。只是因战事危机再起,各校暂罢回城。至1942年,昆工再索校舍,借此上课的联大附中无处安身,欲借地太华寺,却遭云南省主席龙云函拒。据郑天挺日记:“外间有种种流言,谓龙因子女未得入校,对联大深为不满,以致各地有房舍者亦不敢租与联大。”流言并非空穴来风,黄钰生晚年回忆:“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虽然租房困难是否为此,很难确认,但附中确实被迫延迟两月开学,又露天上课三周,黄钰生专门写家长信道歉。
再次是经费支绌。黄钰生至少两作“说帖”向国民政府争取建筑经费,但未获满意结果。其一写给教育部长陈立夫。1941年5月,梅贻琦在重庆面见陈。陈问:“昆明校舍如何,是否拟在乡间筑建?”梅贻琦告以准备在梨烟村造房,并拿出黄钰生的说帖。结果陈答:“学校既然打算出四十万元,当无需再添许多。”梨烟村造房计划徘徊至1943年最终作罢,经费不足是一项主要原因。黄钰生的第二份说帖写给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1944年3月,孔祥熙视察昆明,梅贻琦提交说帖。这次得到建筑费300万元。然而此时物价高涨,300万元照市价仅够30间宿舍建筑之用。而教授们原本希望建宿舍400间。当梅贻琦在临时校务会上报告这一消息时“众大哗”,有人甚至主张拒绝接受。作为说帖起草者,黄钰生也遭到埋怨,成为众矢之的,结果他推说有课,先行离开会场。
最后是校内误解。用房短缺下,校舍分配复杂敏感,很难人人满意。1942年9月校务会上报告“教职员宿舍调整办法提请公决案”时,黄钰生正奉命出外寻觅校舍,与会者对方案多所指责。事后,黄钰生书面陈词:分配办法虽由校舍委员会拟具,但在常委会核准后才施行,自己“设计审有未周,而施行则不能负责”。黄钰生招致怨嫉的另一原因,是他兼任附校主任。他将附校视为“得意之作”,力图用南开中学的经验按高标准办好。然而有些人则认为附校主要职能是服务教职员子弟、服务大学。理念不同,难说对错。但黄钰生却常为此“于不知不觉间得罪人”。这也影响到校舍事务。附校一度欲租南菁中学校舍,该处原租给中法大学,租约将满,南菁已答应转租联大,但中法不愿离去。当时联大一些教授在中法兼课,黄钰生希望他们能向该校晋言,于是与郑天挺、查良钊一起请客,然而席间众人都不愿出头。郑天挺在日记中分析,某教授夫人未能到附校任教、某教授之子未能入附校就读,导致他们对黄钰生不满,因此不愿出力。
困难面前,黄钰生也曾申请辞职。他于1939、1944年先后辞任校舍委员会召集人、师院院长兼附校主任,但均被常委会慰留。在留任师院院长时,常委会指出黄钰生“一切筹划,煞费精神,任劳任怨,至于今日”。这一评价其实也适用于他在校舍委员会主席任上的表现。任劳不易,任怨更难。如果说克服战争、客居、经费造成的困难,是“任劳”;那么面对校内误解继续坚持,就是更难的“任怨”了。
戆直坚毅、安贫乐道的工作精神
之所以任劳任怨,是因为对抗战、对办学有着超越个人荣辱得失的大担当。黄钰生鉴于时弊写下过一篇《偶语》。他见时人对公事相互推诿,办公成了“办理文件”“办来办去,只剩下一堆纸”,一切都推卸责任给“生活困难”,不禁感叹:“全国的人,个个聪明,其结果——一塌糊涂。”由于抱有“这样抗战能胜利吗”的义愤,黄钰生在工作中不愿做聪明人。就像南开校长张伯苓常用天津乡音说的“苦干硬干拼命干”“傻不济济的干”。
联大史专家、美国学者易社强称黄钰生是一位“戆直而公正”的教授。戆直,就有傻、笨的意思。确实作为一位知识分子,黄钰生在行政中并非圆融老练、左右逢源。他晚年也反复讲自己“不懂工程”“建设非我所长”“本无才干,而从事行政”。但他又是联大少数几位始终承担行政责任的教授,学校不断交付一项又一項重任,体现了对其能力的肯定。所谓戆直,其实就是不做聪明人,不避劳怨、质拙勤恳,这是对时弊的反省,也是对联大校训“刚毅坚卓”的践行。巧合的是,黄钰生字子坚,郑天挺字毅生,他们从事的校舍工作恰好诠释了校训中的坚与毅。
1945年,联大终于在昆明城内建起了教师宿舍。不过仍是“粥少僧多”,只得抓阄分配。黄钰生没去抓阄,青年教师邢公畹的妻子陈珍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都是无房、缺房才参加抓阄,我有这么高大的一间房,不是很好吗?”可当陈珍看到他的住处时“大吃一惊”。黄钰生一家住的是一间内有多层台阶的储藏室,他将床安置在台阶之上,笑称自己“高枕无忧”。陈珍不由得想起他常说的:“君子固穷,安贫乐道。”
安贫乐道是为人境界,也是事业担当。当时外间传言,联大行政要人每月“均另有补助”。郑天挺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联大“各长”均为教授,但因为要付出大量办公时间,不能像其他教授那样从事兼职,补贴生计。他们还谢绝了“政府规定之特别办公费”。郑天挺说,黄钰生、查良钊和自己因此“皆负债累累”。如此安贫尚有“谰言”,可以想象在高度敏感的宿舍分配中,主事者如参与抓阄,更难保没有私弊之论。看淡个人得失,有助于减少校舍工作纠纷。
大学重在大师不在大楼,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空间条件都没有,大学精神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联大校舍委员会所做的正是在抗战烽火中,克服各方面困难,奋力保障办学空间。其完成的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工作,为形成联大精神提供了必要条件,为成就教育史奇迹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作者系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