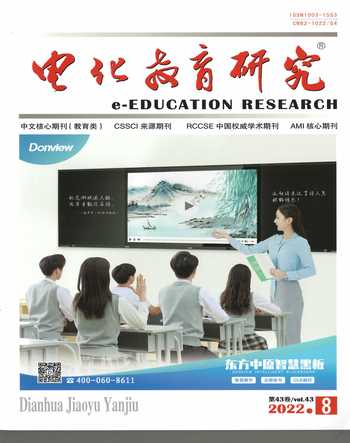积极技术:信息技术支持积极心理干预的创新形态
周榕 郭佳瑞

[摘 要] 积极技术是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积极心理干预的新型技术。它借助视频、脑机交互、可穿戴生物传感等技术以及严肃游戏、大数据虚拟社交系统等产品,实现积极情绪激发、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和积极社交环境构建。经验表明,积极技术能够通过治疗性对话、浸入式交互、生活化环境、意外的成功以及弥合人—技术缺口等方式,完成唤起情绪觉知、支持行为操作、诱发情境认知、引导目标达成和消解技术压力等目标。目前,积极技术的应用存在技术—心理融合失效、个体适应性不足、目标群体错位、缺少辩证思考等问题。未来,理论研究将着重探索积极心理干预与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聚焦方法体系构建、跨学科研究和伦理研究;技术应用层面则将加强大数据、浸入式交互和脑电交互等技术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 积极技术; 积极心理干预; 信息技术; 积极情绪; 积极心理品质; 积极社交环境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周榕(1976—),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STEM教育以及智慧教育与创新能力研究。E-mail:rzhou@snnu.edu.cn。
一、引 言
积极心理干预(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PPI)是通过改变积极心理变量促进个体获取幸福,进而达到精神世界“蓬勃”(Flourishing)的干预活动,是积极心理理论向具体操作方法转化的中介。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来激发积极情绪和培养积极人格,并逐渐形成具有成熟框架和操作路径的技术系统,积极技术(Positive Technology,PT)因而成为在生理—心理—社会层面实现积极心理干预的创新技术形态。
二、积极技术的概念与原理
积极心理干预将消极心理状态转变为“零心理状态”,继而通过激发积极情绪,将其提升为积极心理状态。Parks等将积极心理干预的特征归纳为 :(1)专注于积极主题的干预;(2)关注积极心理机制(机制导向)和积极心理变量(内容导向);(3)促进心理健康而非单纯克服心理弱点[1]。2012年,Botella 等首次提出积极技术的概念,认为其目标是“用科学的、实用性的方法来研究和使用信息技术,创設积极心理环境,激发积极情绪体验,培养积极特质,实现全民福祉”[2]。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完成。其一,构建。建立包含积极心理线索的环境,引导个体主动体验和完成情绪调节。其二,扩展。提供浸入式交互和多模态刺激,拓展个体获得积极情绪的感官通道和体验方式。其三,替代。模拟物理环境、客体甚至肢体和器官,提供真实的身体体验和情绪感受。Calvo和Peters进一步将积极技术划分为预防性技术、干预性技术和专用性技术三类[3]。预防性技术通过技术来动态感知和调整阻碍积极情绪产生的因素,干预性技术通过增加技术的新特性来激发幸福感,专用性技术则专门为促进幸福因素而开发技术产品或提供咨询服务。
积极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信息技术“全人教育”价值观与心理健康领域“积极取向”研究范式的相互呼应,亦是积极心理干预在信息时代对技术的必要倚仗。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积极”,不是对技术本身的属性描述,而是对其应用目标的界定。
三、积极技术的应用框架与实例
积极心理学之父Seligman构建了PERMA (Positive Emotion, Engagement, Relationship, Meaning and Accomplishment) 模型,指明积极情绪、参与性、社会关系、意义与成就感等五项促进个体幸福的要素[4]。Riva等将信息技术与上述要素整合,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积极技术应用框架(如图1所示)[5]。该框架将积极技术应用划分为愉悦体验层、个人成长层和社会交往层等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幸福生活的“三大支柱”:愉悦的生活、充实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
(一)愉悦体验层
核心情感是具有愉悦和唤醒等情绪特征的神经生理状态。愉悦体验层的积极技术以面向情感设计和客体表征的技术为主,通过创设积极体验的发生情境,强化客体(场景、事件、经验、案例等)的心理效价来提升核心情感的唤醒水平,进而激发积极情绪。
1. 视频技术
Chen和 Wang的研究表明,视频媒体具有内容可控性以及环境的情感感知性,相较于文本和交互式动画,其激发积极情绪效果更佳[6]。Schatz等利用视频自我建模(Video Self-Modeling)技术帮助自闭症儿童完成特定的行为任务,提取其中的良好行为(如举手求助老师、坚持完成任务等),添加积极的自我评价语句作为字幕,并且作为新任务的引导材料呈现给儿童[7]。结果显示,视频建模技术能够提升自闭症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行为投入度和积极情绪唤醒水平[7]。
2. 脑机交互技术
脑机交互(Brain-Computer Interaction,BCI)技术通过收集脑电信号测量注意水平和焦虑水平,完成对个体情绪状态的解读。Verkijika 等开发了名为“Math-Mind”的BCI数学教育游戏,通过Emotive EPOC BCI耳机和头盔来实时捕捉用户大脑活动,并在焦虑水平上升时提供视觉反馈,通过调节游戏场景、减慢背景乐节奏以及降低游戏难度来帮助用户控制焦虑情绪[8]。研究显示,该款游戏能够成功降低9~16岁儿童的数学学习焦虑水平[8]。
3. 可穿戴生物传感技术
可穿戴设备不仅可以评估个体的皮肤电导率、心脏活动、肢体运动情况,还可以扫描和测量个体情绪状态,提供即时反馈。Positive Technology Platform(PTP)是由Gaggioli团队开发的基于移动技术的压力管理平台。PTP平台创设了基于放松疗法的3D交互环境,支持用户在海滩、森林等四种虚拟环境中完成积极情绪训练[9]。其间,生物反馈组件利用穿戴式心率监测器,将用户的心率变化以动画3D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动态改变3D环境的特征(如篝火、瀑布的大小),从而在用户和环境之间建立反馈循环。结果显示,伴随心率的降低,用户的压力感知水平显著下降,正向心理效价明显上升[9]。
4.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创设出包含特定心理刺激的环境,从而完成积极情绪的训练。Butler系统对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诊断、治疗和娱乐等三个层次的心理干预[10]。诊断层次使用决策算法,一旦检测到抑郁情绪,立即启动情绪治疗程序。该程序构建放松和愉悦两种虚拟环境,要求用户自述以往的愉快体验,并对周围景观的光线、颜色、形状、位置等细节进行描述。系统还设置了自传记忆程序——“生命治疗书”(Therapeutic Book of Life,TBL),在系统监测到用户的负面情绪时主动呈现,从而唤起特定的愉悦记忆,并通过交互工具与同伴分享。研究表明,Bulter系统用户的放松感和愉悦感显著增加,悲伤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10]。
(二)个人成长层
个人成长层以心流理论为基础。心流是个体面对高难度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而复杂的意识状态,在人机交互中激发心流体验的条件是可感知的环境、适度的任务和游戏性。因此,个人成长层的积极技术侧重于提供独特的场景刺激、设置与用户相匹配的任务以及呈现挑战性的内容,通过自我实现培养积极心理品质。
1. 沉浸式虚拟环境
沉浸式虚拟环境能够灵活设置情境和任务,并且提供多通道反馈,利用这一特性设计人机交互活动,有利于促进心流的产生,提升个体(特别是特殊群体)的情绪感知和社会互动能力[11]。Ip等搭建了Half-CAVE(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硬件环境,并开发了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情绪—社交训练系统[12]。儿童在训练员指导下完成校车、教室、图书馆、餐厅等虚拟场景中的情感识别练习和社交任务(如借阅图书、分享座位等),经历关系冲突 (如被插队、喜欢的图书被借走等)。之后,儿童独自应对在操场上体育课时遇到的复杂场景,并反思自己的表现。结果表明,儿童的情感表达、情绪控制能力和社会适应力均得到明显提升[12]。Ahn等利用虚拟环境,支持正常用户体验色盲人群的视觉感受,完成颜色匹配任务[13]。结果发现,用户对色盲人群的心理困境感同身受,对自身状态表现出满足和感恩,并体现出愿意付出双倍努力的行为意向[13]。
2. 智能机器人
机器人技术能够有效应用于知识学习、认知训练和动作训练。TWCs(Transitional Wearable Companions)机器人帮助自闭症儿童完成交谈的任务[14]。TWCs拥有多个互动传感器,当儿童触摸机器人时,它会发出灯光、声音或通过振动来做出响应,增强儿童持续交互的信心。它还将生理传感器和互动传感器相连,通过皮肤电导获得儿童生理信息(如体温、心率和应力水平等),并以此来调整机器人的对话内容、语速及语调。治疗人员或父母也可以控制TWCs机器人与儿童进行互动,发展自闭症儿童的社交技能。
3. 严肃游戏
严肃游戏是具有挑战性目标、趣味性体验,并能够帮助个体连接游戏体验与生活体验的交互式程序。Plan-It Commander是帮助多动障碍患儿改善日常行为策略的在线冒险游戏[15]。它通过10个不同的主线任务和多个支线任务,引导儿童完成故事情节规定的行为,并利用特定技能解决问题,减弱因注意缺陷而带来的消极情绪,培养基于理解与表达的同理心。JEMImE则是训练自闭症儿童表情认知和再现能力的3D游戏[16]。儿童首先观察虚拟人物的面部表情,理解表情的含义,并模仿指定的表情。之后,在积极和消极两种虚拟情境中与系统角色对话,作出表情反应,并开启新的场景和任务。研究表明,游戏中儿童的视觉感和游戏体验良好,情感理解和表达能力明显提高[16]。
(三)社会交往层
社会存在感是衡量个体通过媒介与他人互动程度的重要指标,与个体最佳体验正相关,是促进个体幸福的重要成分。社会交往层的积极技术聚焦建立关系网络、优化互通觉知(参与者产生的与人相伴相助的感觉)和改善社交习惯,进而构建积极的社会交互环境。
1. 基于大数据的虚拟社交系统
大数据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能够 “投其所好”,为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环境和个性化内容。Kandalaft等在Second Life虚拟系统中设置了三个层次的交互任务,首先,用户在虚拟校园中观察同伴的表情和手势,寻找朋友;之后,参与同伴发起的群体讨论,讨论主题根据以往交互数据的分析结果产生;最后,在虚拟生日派对上交替扮演来宾和主持人两种角色[17]。系统对各类交互内容进行数据挖掘,并向用户说明其社交行为对他人情绪的影响。研究表明,該系统在帮助用户获得愉悦感、满足感和群体归属感方面效果显著[17]。
2. 网络协作游戏
网络协作游戏要求基于合作完成挑战性任务,且不允许玩家单独取得成功。Come with Me 是一款双人协作游戏[18]。用户分别扮演Com和 Mi两个角色,合作完成解谜任务。两个角色各有所长,必须相互帮助才有可能成功,儿童也因此获得协作的快乐、成功的喜悦、分离的悲伤等情感体验。Lorenzo团队设计的IVRS(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System)系统创设了10种社交情境,要求自闭症儿童协作完成社交任务,并作出情感反应[19]。系统通过人脸识别监测个体的情绪水平,更新虚拟场景、显示视角以及背景音乐,并在儿童情绪指标过低时发送语音指令,引导其重建社会关系。结果表明,IVRS系统改善了儿童的情感及行为水平,提升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技能[19]。
3. eHealth移动医疗系统
eHealth系统通过移动互联网或蓝牙技术,在医护人员与患者间建立专属虚拟社区,实现远程监控、日常护理和医疗信息共享。eHealth系统支持基于3D眼镜的虚拟医疗,用户可以真实地“经历”信息内容,获得虚拟环境中的存在感。eHealth系统还常常采用积极自我表达的策略,引导用户以“Today, I like”为前缀发表帖子,并智能推送给其他用户,实现积极情绪的传递。实践证明,eHealth系统能够减轻个体在团体交往中的焦虑、沮丧情绪,增强对幸福的感知能力[20]。
四、积极技术的应用策略
积极技术引发情绪积极改变的前提是承认生活中“苦―乐”的矛盾统一性。Diefenbach用“连续统”来形容苦与乐的并存关系,认为“苦―乐”的转换过程存在两个关键点[21]:其一,个体必须具有对当前消极情绪的足够认知,并具有“使其改变”的信念,否则将会滞留在情绪舒适区,忽视、否定或逃避改变的意义;其二,在苦与乐的对抗中,个体必须在干预之初获得迅速增长的积极情绪,否则将会强化焦虑和自我愧疚,拒绝改变的持续发生。因此,应用积极技术的核心是引导个体正确认知消极情绪,并激活各种动力因素(自我實现的信念、自我效能感、成长潜能等)和刺激通道(情境认知、运动体验、生理控制等),实现积极情绪的尽早形成和持续增长。
(一)唤起情绪觉知:治疗性对话
积极技术采用的治疗性对话通常包含差距认知、需求、自觉和激励式反馈四类要素。“差距认知”是利用技术将理想与现状的差距进行可视化呈现。例如:向个体展示其情绪指标的变化轨迹,并引导完成对不良态度和行为的分析。“需求”是唤起个体对改变情绪状态的明确信念。例如:在其情绪数据痕迹上设置“触发器”,通过对话框、选择列表等交互元素来提醒个体实施特定的调节行为。“自觉”和“激励式反馈”是利用技术向个体提供改变情绪的积极因子,前者强调在干预中引导个体进行自主决策,如在技术产品中增加个人定制的提示、预警功能;后者强调对个体的改变行为(特别是改变初期的代表性行为)作出积极反馈,如向个体呈现目标达成的进度条,并表达对其成就的赞赏。
(二)支持行为操作:浸入式交互
实现浸入式交互的策略有五种。第一,简约的自然场景设计。在虚拟场景中引入自然元素,将情境感知体验与日常经验关联起来,产生空间认同。第二,生理指标测量与反馈。动态采集个体情绪状态的生理指标,并利用类似冥想(降低血压、调整呼吸等)的方法来控制注意焦点,降低情绪压力。第三,可调节的环境表征。基于个体生理反馈的结果,对虚拟环境中的场景要素进行调整,帮助个体获得对环境的控制感。第四,身体运动与虚拟操作相结合。个体通过自然方式或者交互控制器来完成特定动作,从而产生较强的动觉反馈、心流体验和具身认知。第五,面向情感表达的社交网络。个体与教练、伙伴等虚拟角色进行自然对话,并配合手势、表情和语调的变化,获得群体生活的情绪感受。
(三)诱发情境认知:生活化环境
心理干预应当发生在面向生活的、信息丰盈的环境中。方法之一是在浸入式环境中纳入生活的因素,如呈现真实场景、角色、情节和结果;方法之二是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叠加,如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来完成场景展示,模拟实物操作和个体运动;方法之三是提供多模态刺激,采用真实、半虚拟和全虚拟方式,模仿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方法之四是支持个体对环境作出特定的解读,将情境体验与社会、文化倾向加以融合,获得思维启发和价值认同。
(四)引导目标达成:意外的成功
意外的成功是将个体自然地引入情绪调节的过程,使其摆脱对失败的担忧,并在成功的惊喜中获得信心和成就。首要条件是设置隐藏的情绪调节目标。例如:将不同类型的用户任务埋藏在主线任务中,并在任务完成后告知所取得的“额外”成就。其次是利用技术准确判断个体发生改变的潜能,并激活相应的积极心理资源(系统对话、虚拟教练、网络伙伴等)。最后,引导个体就成功经历进行回顾和反思,如发表自我报告或者完成心理评估等。
(五) 消解技术压力:弥合人—技术缺口
技术压力包含技术焦虑与技术成瘾。消解技术压力的关键是在个体发展需求与技术应用方式之间建立平衡。技术必须具有改善行为结果的有用性(如提升记忆效果、丰富认知体验等),以便使个体对技术产生信任和期待。技术应该具有易用性,避免复杂操作带来的技术过载效应。例如:实现基于行为偏好的自适应用户界面,使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完成交互。技术应当具有支持个体发展的可靠性。例如:对个体心理特征或状态进行精准的数据分析,帮助完善自我认知。技术应当具有社会性。例如:基于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交场景,实现社会角色认同。技术还应当具有隐匿性。例如:采用智能方法减少技术操作,使个体关注数字世界带来的真实体验而非技术本身。
五、积极技术应用的不足
近年来,学界在构建积极技术概念框架、分析方法、设计策略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积极技术的应用仍存在诸多问题,期待研究范式的变革。
(一)技术与心理难以有效融合
目前,积极技术仍存在技术与心理干预的“貌合神离”现象。一方面,许多技术产品的设计并没有建立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之上,也无法采用科学方法来开展心理评估。一些用于行为改善的软件不能对行为、现象与数字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心理层面的解析,并在动态细节上作出呈现和调整。另一方面,技术系统的交互性和动态元素所具有的潜力常常被忽视,这使得能够真正被作为“新经验场域”来使用的技术十分有限,将积极技术作为替代手段从而将常规干预内容进行简单迁移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对技术自身的负面心理效应及其与积极干预效果的对抗过程缺乏必要的关注,甚至在《积极技术手册》或《技术与心理健康》这类权威书籍中,都没有专门的论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积极技术应用的表面化与单一化。
(二)技术系统缺乏个体适应性
现有的积极技术理论模型并不足以在技术系统与用户之间建立动态的、适应性的交互。例如:系统预设的“焦虑”情绪的判断标准应当对“理性担忧”和“过度忧虑”作出区分。否则,用户可能会认为系统过于“刻板”或“霸道”而放弃积极的行为改变。技术应用水平也部分限制了对情绪状态的诊断和预测的准确度。例如:情绪调节需要对个体的生活状态进行动态、自然数据的抓取,从而分析情感的动力因素和情境因素。这不仅需要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的支持,还需要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然而,许多产品并不具有整合上述技术的能力,因而选择经验取样(Experience Sampling)等侵入式数据抓取的方法,但这可能会对用户的状态造成持续的干扰。
(三)目標群体存在缺失与错位
许多技术产品将目标群体定位为“自我驱动者”(Self-Driven),即具有较高动机水平、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技能的个体。这些产品往往采用严格的规则,要求个体通过高度自律完成持久的自我改善行为,这显然是困难的。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庞大的“自我迟疑”(Self-Hesitant)群体。他们试图对自身行为作出改变,又往往因为不够自律而中途放弃。对他们而言,积极技术本能够对其自我完善过程产生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的技术手段却忽视这些“欠主动者”的需求,对出现的自我怀疑、动机不足、行为失调等现象无法作出策略回应。当系统仅仅在用户达到要求时给出鼓励性反馈,却不能在他们刚刚萌生退意时提供补救性交互,将会流失大量的潜在受益者,而他们恰好是最关键的积极技术应用对象。
(四)缺少对“有限效果”的辩证思考
技术自身的负面效应会对个体的情绪造成损害,如孤独感、社会焦虑以及虚拟暴力等。然而,无论是用户还是设计者,都将积极技术看作是“超级武器”。一旦期待的效果没有达到,许多用户又会转而迁怒于技术,却不能对自身在动机、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此同时,伦理尺度的失衡可能会彻底颠覆应用积极技术的初衷。有关安全、公平、尊重的伦理冲突极易引发对技术的敌视和质疑。特别是当某种积极品质放置在特定的伦理情境中,将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宽恕通常是社会交往中被提倡的积极品质,然而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宽恕反而会提高暴力行为发生的频率[22]。遗憾的是,一些设计者并没有对技术的“伦理阈值”进行充分的考量,积极技术因而丧失理性的立场,陷入技术与人的对立之中。
六、 积极技术的未来发展
(一)理论研究的未来方向
理论研究应首先聚焦对积极技术的理性自省。借助“苦―乐”连续统的辩证关系,对技术自身“令人痛苦”的成分予以剖析,对技术要素能够提供的“积极经验域”进行界定。深入探索积极心理干预与信息技术的整合路径。进一步阐明积极情绪干预的心理机制,引入情境性因素,讨论文化情境、社会情境、问题情境对情绪的作用过程[23]。通过情绪评价标准向数据分析算法的转化、情境因素向交互要素的转化以及心理干预机制向技术功能的转化,实现心理研究与技术手段的深度融合。
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焦点是基础性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一方面,研究文化融合和情感教育视域下的积极心理干预模式、策略和技术工具,以及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特别是“自我迟疑者”的情绪干预方法;另一方面,在神经科学、交互技术、设计学、艺术学等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从而在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法之间建立连接。
理论研究的第三个焦点是对积极技术伦理的探究。积极技术能够控制个体的精神状态、心理轨迹和体验,因此,必须对心理干预中预设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和生活主张进行规范,并深入分析其对个体身份认同、自我感知和情绪调节的可能影响。此外,在数据处理、人机交互、实验操作等过程中存在的技术伦理风险和科学伦理风险,也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厘清。
(二)技术应用的未来方向
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个体出现情绪障碍的可能性,并与基因组技术或神经网络技术关联,给出特定情境中诱发积极情绪的方案,提升干预的精准度。它还将帮助研究者在更大范围和多元群体中开展心理干预的效果检验,为循证心理治疗提供技术支撑。
浸入式交互将继续成为积极心理干预的核心途径。虚拟现实技术将会提供更加丰富的临场体验,并与眼动追踪、面部表情识别等设备整合,准确地记录和分析个体的情绪控制行为及其诱因。基于虚拟社交系统开展的大规模群体积极心理干预也将成为实践和研究的重要领域。
以脑电交互为代表的非侵入式脑刺激技术将与无线记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近红外成像技术以及可穿戴设备紧密结合,快速识别和精准分析个体的情绪状态。基于神经反馈的各类认知模型也将不断出现,使脑电控制信号更加可靠地与外部设备、程序匹配,为积极情绪训练提供更为丰富的手段。
[参考文献]
[1] PARKS A C, BISWAS-DIENER R. Positive interven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KASHDAN T B, CIARROCHI J V. Mindfulness, acceptance,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even foundations of well-being. California: 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2013:140-165.
[2] BOTELLA C, RIVA G, GAGGIOLI A, et al.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positive technologies[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2, 15(2):78-84.
[3] CALVO R A, PETERS D. Positive computing: technology for wellbeing and human potential[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4.
[4] SELIGMAN M E P.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M]. New York: Free Press, 2011:134-186.
[5] RIVA G, BA?譙OS R M, BOTELLA C, et al. Positive technology: using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positive functioning[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2,15(2):69-77.
[6] CHEN C M, WANG H P. Using emo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ultimedia materials on learning emotion and performance[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1,33(3):244-255.
[7] SCHATZ R B, PETERSON R K, BELLINI S. The use of video self-modeling to increase on-task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high-functioning autism[J]. Journal of applied school psychology, 2016,32(3): 234-253.
[8] VERKIJIKA S F, DE WET L. Using a 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 in reducing math anxiety[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5, 81(2):113-122.
[9] GAGGIOLI A, CIPRESSO P, SERINO S, et al. Positive technology: a free mobile platform for the self-managemen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J]. Annual review of cybertherapy and telemedicine, 2014, 199: 25-29.
[10] BOTELLA C, ETCHEMENDY E, CASTILLA D, et al. An e-health system for the elderly (Butler Project): a pilot study on acceptance and satisfaction[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9, 12(3):255-262.
[11] 陳靓影,王广帅,张坤.为提高孤独症儿童社会互动能力的人机交互学习活动设计与实现[J].电化教育研究,2017,38(5):106-111,117.
[12] IP H H, WONG S W, CHAN D F Y, et al. Virtual reality enabled training for social adaptation in inclusive education settings for school-aged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C]//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lended Learning.Beijing: Springer, 2016: 94-102.
[13] AHN S J, LE A M T, BAILENSON J. The effect of embodied experiences on self-other merging, attitude, and helping behavior[J]. Media psychology, 2013,16(1):7-38.
[14] ?魻ZCAN B, CALIGIORE D, SPERATI V, et al. Transitional wearable companions: a novel concept of soft interactive social robots to improve social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2016, 8(4):471-481.
[15] BUL K C, KATO P M, VAN DER OORD S, et al. Behavioral outcome effects of serious gaming as an adjunct to treatment for children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6, 18(2):2-36.
[16] GROSSARD C, HUN S, DAPOGNY A, et al. Teaching facial expression production in autism: the serious game JEMImE [J]. Creative education, 2019(10):2347-2366.
[17] KANDALAFT M, DIDEHBANI N, KRAWCZYK D, et al. Virtual reality social cognition training for young adults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13,43(1):34-44.
[18] YE X. Come with me: a cooperative game focusing on player emotio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21.
[19] LORENZO G, LLED A, POMARES J, et 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n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system to enhance emotional skills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6, 98:192-205.
[20] BURGER F, NEERINCX M A, BRINKMAN W P. EHealth4MDD: a database of e-health system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s[J].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18,21(9):18-24.
[21] DIEFENBACH S.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well-being interventions: posi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sign in light of the bitter-sweet ambivalence of chang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3):331.
[22] MCNULTY J K. The dark side of forgiveness: the tendency to forgive predicts continue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marriag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1, 37(6):770-783.
[23] 翟賢亮,葛鲁嘉.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冲突与视域转换[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2):290-297.
Positive Technology: An Innovative Patter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uppor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ZHOU Rong, GUO Jiarui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Positive technology is an innovative pattern of technology that us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It inspires positive emotions, cultivate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constructs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s with technologies including video, brain-computer interaction, wearable bio-sensing technology, etc. and products such as serious games, big data virtual social systems. Experiences shows that through therapeutic dialogues, immersive interactions, life-like environments, unexpected success, and bridging the human-technology gap, positive technology can achieve the goals of arousing emotional awareness, supporting behavioral operation, inducing situational cognition, guiding goal achievement and eliminating technical pressure.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technology, such as invalid techo-psyco integration, insufficient individual adaptability, misplacement of target groups, and deficient dialectical thinking. Fu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will focu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hodology system,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ethical research. On 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level, the supporting role of big data, immersive interaction and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interaction technology will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Positive Technolog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sitive Emot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基金项目:2021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职业发展的陕西省中小学STEM教师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P023);2021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研究课题“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资格制度的比较研究”(课题编号:JSZG202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