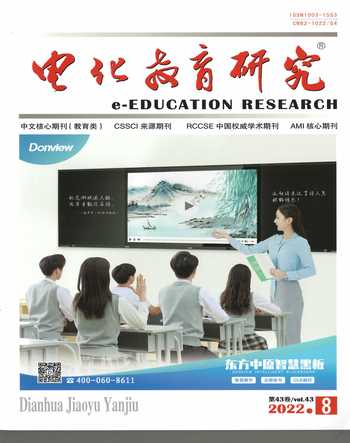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在线深度学习的影响机制研究
刘哲雨 刘畅 许博宇



[摘 要] 在线学习支架可用于改善学习者的计划调节,规划学习任务,引导学习行为,促进在线深度学习。已有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设计更多依赖经验,缺少基于脑加工机制的设计规则研究。文章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动态追踪深度学习过程的脑区激活情况,探究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在线深度学习过程的影响机制;采用测量问卷评估支架对深度学习结果的影响。研究结论指出:深度学习基础阶段、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两种类型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均有利于激活深度学习过程的脑区,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深度学习结果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启示研究者优先采用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在线深度学习;深度学习三个阶段的脑区激活情况与深度学习结果均具有正相关关系,启示研究者可以根据脑区激活情况判断在线深度学习是否真实发生以及发生的程度。最后,基于实验结论提出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设计规则及应用建议。
[关键词] 计划调节学习支架; 在线深度学习;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 设计规则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刘哲雨(1980—),女,天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与深度学习的理论及多模态实验研究。E-mail:zheyuliu@126.com。
一、引 言
互联网时代,知识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在线学习已成为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1],在线学习的质量同时被学习者与教育研究者所关注[2]。合理的学习计划可以帮助学习者规划学习的步调、时间和策略等,助力学习者实现在线学习的高阶目标,提升在线学习质量。但也有许多研究表明,在线学习中存在学习者计划力较低的现象,这些学习者不能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和实际进度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逐步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自发推进深层次学习存在一定的困难[3]。
学习中的计划或规划影响深度学习的基础机制在于,计划调节行为是自我调节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自我调节学习是促进深度学习的主要变量[4]。在线学习支架能够作为外部干预方式支持学习者的计划调节,是促进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有效途径。
学习支架对在线深度学习的促进机制以及促进程度,是在线深度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5]。目前,学习支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支架的应用效果研究[6],且支架的设计或更多依赖经验,或更多关注技术,较少关注不同类型学习支架对深度学习过程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支架对深度学习结果的影响差异。
因此,本研究关注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影响在线深度学习的脑加工机制,探究不同类型的支架激活脑区的方式与影响结果的程度,并基于底层机制的实验结论提出支持在线深度学习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设计规则。
二、文献综述
(一)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研究现状与表征方式研究
学习支架是根据辅助学习机制以及最近发展区理论提出的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干预措施和认知协助[7],具体表征为根据学习者的需要提供一种临时性的支持框架,使学习者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他们之前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中,正向影响学习者的计划调节,促进高阶思维。
目前,相关研究倾向于将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界定为能够增强计划调节学习的交互功能。计划调节是学习者选择感兴趣的学习主题、进行明确的目标定向、安排合理的学习顺序、规划最恰当的学习路径的过程[8]。其中,知识地图正是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知识主题的各个节点以及节点间的逻辑关系,指导和引领学习者明确学习目标、规划学习路径,帮助学习者建立知识网络,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支持学习计划的认知干预[9]。
学习者控制与系统控制是多媒体交互的主要方式,由学习者控制基于完整知识地图的学习进程,由系統控制基于分段知识地图的学习进程,是基于知识地图的学习支架的两种重要交互控制方式,不同的交互控制方式可能会引导出不同的计划调节学习过程[10]。
因此,本研究将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分为学习者控制的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和系统控制的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其中,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提供完整知识地图及其内容链接,完全由学习者自主计划学习顺序进行学习;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为系统分阶段地提供计划调节支持,学习者的学习计划在当前阶段内完成。
(二)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深度学习的机制研究
自我调节是一个递归过程,学习者通过计划调节促进学术任务的执行,依据目标不断地调整或完善计划、定义任务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不断地选择并调整策略,引发不同的认知加工行为,产生不同的认知加工结果[11-12]。
研究表明,与没有使用计划调节的学习者相比,使用计划调节的学习者更加主动地设定专业目标并努力实现,更加积极地调节认知,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效果[13]。在这个过程中,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引导学习者使用他们不能自发执行的深度学习策略,启发学习者采取系统或全局的方法,这种计划调节通常对深度学习是有效的。此外,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有助于管理学习动机,有助于形成持久的学习动力,促进学习者达到深度学习。
(三)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多模态评价研究
有意义学习以及深度学习是大脑皮层神经元联结的结果。探究深度学习的脑机制对于厘清深度学习发生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14]。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作为一种无创检测技术,能够对大脑皮层的脑活动进行实时检测,它结合了fMRI高空间分辨率和ERPs高时间分辨率的优势[15],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认知活动时额叶到颞叶的大脑皮层的活跃程度[16]。因此,本研究应用fNIRS技术,探究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脑加工机制。氧合血红蛋白(HbO)浓度的相对变化量是脑功能激活的测量指标,可以描述在不同水平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支持下被试在深度学习的不同阶段中的脑区激活水平。
在线深度学习不仅重视学习过程,也关注学习结果。在线深度学习的评价还可以结合认知测量来评估深度学习结果的水平。新知理解属于深度学习的基础阶段;拓展迁移体现了学习者联结和迁移知识的能力,属于深度学习的早期阶段[17];创新应用体现了学习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属于深度学习的晚期阶段[18]。因此,本研究对深度学习认知行为结果的评价包含深度学习基础阶段评价、深度学习早期阶段评价和深度学习晚期阶段评价。
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评价不仅需要从认知神经层面解释深度学习过程的发生机制[19],还需要从认知行为层面评价深度学习的结果,多模态数据使实证研究的结论更可靠、更稳定。
三、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影响在线深度学习的
实证研究
(一)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三个不同水平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即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以及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因变量为脑区激活水平及深度学习结果。实验流程包括准备环节、前测环节、在线学习环节和后测环节(如图1所示)。
(二)实验假设
面向深度学习不同阶段的脑区激活水平和认知水平,本实验提出如下假设:
H1:深度学习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下脑区激活水平差异显著。证明在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调节作用显著,且相比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H2:深度学习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下认知水平差异显著。证明在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认知水平上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调节作用显著,且相比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H3: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脑区激活水平与认知水平的相关系数显著。证明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下认知水平与对应脑区的激活水平显著相关。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均为T城市本科生,共有50人参与本次实验,为了控制无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剔除先验知识水平高、自我调节能力过低或过高、脑成像采样率过低的被试,最终保留有效被试38名,其中,男生18人,女生20人,平均年龄21岁,所有被试无脑损伤、精神病史。被试随机分为三组,其中,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13人,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14人,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11人。三组被试之间的先验知识水平(F=0.001,p=0.999>0.05)和自我调节能力(F=1.119,p=0.336>0.05)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实验材料
本实验采用在线学习方式,学习材料选自认知神经科学经典教材之一《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Gazzaniga等著,周晓林等译)中《人类的记忆》章节的部分内容,由三名专家参与确定本实验材料。该材料综合了典型的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符合常态化深度学习中复杂知识的综合形态特征。实验前进行了预实验,旨在确认学习材料难度适中,并且不属于被试的先验知识,从而保障实验干预能够对被试形成学习效应。
计划调节学习阶段的学习材料主要内容和形式是通过多媒体交互设计实现对学习顺序和学习路径的选择与规划。实验材料中的知识地图用于呈现七个与“人类的记忆”有关的知识节点。其中,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设计为整体呈现全部知识节点,完全由学习者自主规划学习;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设计为分块呈现知识节点,即学习规划需要在当前知识模块的范围内完成。
(五)测试工具
本实验选用主观评估工具(先验知识评估问卷与自我调节能力自评问卷)进行前测,采用fNIRS技术监测脑区激活情况,结合深度学习结果问卷评估认知行为结果。多维度、多层次、多模态的测量数据,立体化地揭示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深度学习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
测试工具包括先验知识评估问卷、自我调节能力自评问卷和深度学习结果问卷。先验知识的测试题目主要考查被试对学习主题的先验知识基础,每道题目均采用五等级Likert主观评价,其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22,KMO值为0.63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0.000。若被试自评得分大于或等于12分,则被界定为具有高知识基础的被试,即不符合实验标准。自我调节能力自评采用Pintrich等人编制的自我调节量表[20],包含16道题目,每道题目采用Likert7级评价,其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675,KMO值为0.684,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0.000,符合实验标准。深度学习结果评价包括新知理解水平评价深度学习的基础、拓展迁移水平评价深度学习的早期阶段以及创新应用水平评价深度学习的晚期阶段。所有测试题目由三名专业教师设计,测试结果由另外三名专业教师进行背对背评分,并以三个分数的均值作为最终评价结果。深度学习结果测试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03,KMO值为0.703,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0.000,符合实验标准。
(六)实验设备及实验测量通道布局设置
实验使用日本岛津公司的近红外脑成像记录分析系统(LABNIRS)记录实验过程中被试大脑皮层的氧合血红蛋白(HbO)的浓度变化。实验采用国际10-20系统放置光极位置,共计24个光极,左右两边均采用2×3+3×2的排列方式,分布在前额叶皮层和左右颞叶皮层,其中12个为发射光极,12个为接收光极,相邻两光极构成一个信号记录通道,共形成28个通道(如图2所示)。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包括额上回和额中回),对应通道1、2、8、9;眶额皮层(包括额上回和额中回),对应通道3、6、9、12;左侧颞叶(包括颞上回和颞中回),对应通道16、18、19、20、21;额叶(包括额中回),对应通道2;左侧额叶(包括额中回),对应通道4、5、7;右侧额叶(包括额中回),对应通道8、10、11、13、14;右侧颞叶(包括颞上回和颞中回),对应通道24、25、26、27、28;三角部额叶(包括额下回),对应通道15、22;左侧岛盖部额下回,对应通道17;右侧眶部,对应通道14;右侧中央前回,对应通道23;右侧緣上回,对应通道26。
四、研究数据分析
研究主张深度学习基础是实现深度学习的前提,只有深度学习基础阶段水平符合实验条件,才能进一步分析深度学习的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的机制与结果。三组被试的各项测试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所有进入深度学习过程及结果分析的样本在新知理解阶段均达到合格标准。
(一)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脑区激活水平分析
1. 新知理解过程脑区激活水平分析
新知理解过程中,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氧合血红蛋白(HbO)浓度变化的beta值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通道8、通道9的激活水平三组之间的差异边缘性显著。进一步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9(p=0.025<0.05)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8(p=0.018<0.05)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各通道的激活水平差异未达到显著程度。
2. 拓展迁移过程脑区激活水平分析
拓展迁移过程中,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氧合血红蛋白(HbO)浓度变化的beta值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支架之间通道3、通道4、通道6、通道7、通道8、通道9、通道11、通道13、通道14、通道24的激活水平差异显著,三组支架之间通道1、通道2、通道5、通道12的激活水平的差异边缘性显著。进一步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1(p=0.031<0.05)、通道2(p=0.030<0.05)、通道3(p=0.031<0.05)、通道6(p=0.017<0.05)、通道7(p=0.008<0.01)、通道8(p=0.012<0.05)、通道9(p=0.005<0.01)、通道11(p=0.013<0.05)、通道12(p=0.029<0.05)、通道13(p=0.008<0.01)、通道14(p=0.002<0.01)的激活水平存在顯著差异;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8(p=0.028<0.05)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2(p=0.037<0.05)、通道3(p=0.016<0.05)、通道5(p=0.032<0.05)、通道6(p=0.018<0.05)、通道7(p=0.008<0.01)、通道14(p=0.012<0.05)、通道24(p=0.007<0.01)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3. 创新应用过程脑区激活水平分析
创新应用过程中,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氧合血红蛋白(HbO)浓度变化的beta值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支架之间通道1、通道8、通道9、通道12的激活水平差异显著,三组支架之间通道10、通道13的激活水平的差异边缘性显著。进一步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8(p=0.009<0.01)、通道9(p=0.022<0.05)、通道10(p=0.023<0.05)、通道12(p=0.008<0.01)、通道13(p=0.024<0.05)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通道1(p=0.015<0.05)、通道8(p=0.019<0.05)、通道9(p=0.029<0.05)、通道12(p=0.015<0.05)的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和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各通道激活水平未达到显著差异。
(二)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认知水平分析
1. 新知理解水平分析
新知理解水平的实验数据分析显示,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新知理解水平数据具有方差齐性,但不符合正态分布,正态化转换后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的新知理解水平具有显著差异[F(2,38)=12.296,p=0.000<0.001]。进一步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新知理解水平存在边缘性显著差异(p=0.054);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新知理解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01,p=0.003<0.01)。
2. 拓展迁移水平分析
拓展迁移水平的实验数据分析显示,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拓展迁移水平数据具有方差齐性,但不符合正态分布,正态化转换后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的拓展迁移水平具有显著差异[F(2,38)=27.760,p=0.000<0.001]。进一步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之间拓展迁移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01,p=0.000<0.001,p=0.027<0.05)。
3. 创新应用水平分析
创新应用水平的实验数据分析显示,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创新应用水平数据具有方差齐性,但不符合正态分布,正态化转换后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的创新应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F(2,38)=36.161,p=0.000<0.001]。进一步LSD事后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组的创新应用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01,p=0.000<0.001,p=0.008<0.01)。
(三)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脑区激活水平与认知水平的关系分析
1. 新知理解过程中脑区激活水平与认知水平的关系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新知理解过程中激活的通道8、通道9与新知理解水平的关系。鉴于新知理解水平数据的K-S正态性检验结果不满足正态分布标准,因此,需要对新知理解水平数据进行正态化转换并展开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激活的通道8与新知理解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p=0.040<0.05),见表2。
2. 拓展迁移过程中脑区激活水平与认知水平的关系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拓展迁移过程中激活的通道1、通道2、通道3、通道4、通道5、通道6、通道7、通道8、通道9、通道10、通道11、通道12、通道13、通道14、通道24与拓展迁移水平的关系。鉴于拓展迁移水平数据的K-S正态性检验结果不满足正态分布标准,因此,需要对拓展迁移水平数据进行正态化转换并展开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激活的通道5与拓展迁移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p=0.005<0.01),见表2。
3. 创新应用过程中脑区激活水平与认知水平的关系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创新应用过程中激活的通道1、通道2、通道8、通道9、通道10、通道12、通道13与创新应用水平的关系。鉴于创新应用水平数据的K-S正态性检验结果不满足正态分布标准,因此,需要对创新应用水平数据进行正态化转换并展开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激活的通道10与创新应用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p=0.008<0.01),见表2。
五、研究结论及支架设计规则
(一)实验研究结论
1. 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脑区激活水平的影响
无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与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之间脑区激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下脑区激活水平更为显著;且在拓展迁移的过程中,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脑区激活水平存在顯著差异,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下脑区激活水平更加显著,部分验证了假设1。这一结果说明,两种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脑区的激活作用都可以体现在计划调节学习和问题解决的交互过程中,而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更符合在线深度学习的脑加工机制的需求。计划调节是自我调节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设定目标与实现目标的策略计划,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后续的学习过程的引领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能够调动学习者计划调节的意识与积极性,持续提升学习者对于知识内容的学习动机,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在学习过程中选择深度学习策略[21],使学习者能够合理进行学习计划并在随后的学习过程中更成功地转化为自觉行为[22]。
2. 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认知水平的影响
不同类型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之间被试新知理解、拓展迁移、创新应用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有利于促进个体的在线深度学习,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作用效果优于有系统控制的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验证了假设2。计划调节要给予学习者更多的自主性,这一结论与Dignath等人的观点基本一致[23],他们认为当系统支持计划调节时,针对计划调节的干预对学习效果的作用不强。很多研究结论也支持自我设定的学习阶段(包括情感性的个人目标和自然环境中的学习)比教师或系统设定的学习阶段更能与个体条件相匹配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24]。Manlove等人也对这一结果作出了解释,认为学习者在使用系统提供的支架进行学习时,可能需要分配更多的精力来适应和控制系统支架提供的支持方向[25],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并降低了相关认知负荷,影响了学习效果。
3. 深度学习不同阶段脑区激活水平与认知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激活的脑通道8与深度学习结果的新知理解水平显著正相关,激活的脑通道5与深度学习结果的迁移应用水平显著正相关,激活的脑通道10与深度学习结果的创新应用水平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3。本研究的结论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额叶与新知理解的心理加工过程有很强的相关性,左侧额叶与拓展迁移的心理加工过程有很强的相关性,右侧额叶与创新应用的心理加工过程有很强的相关性[26-28]。这从另一个方面启示研究者,未来可以通过脑区激活水平判断支架是否发挥作用:可以通过右侧背外侧额上回和右侧额中回是否激活来判断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是否对在线深度学习的新知理解水平产生有效的作用,可以通过左侧额中回是否激活来判断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是否对在线深度学习的迁移应用水平产生有效的作用,可以通过右侧额中回是否激活来判断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是否对在线深度学习的创新应用水平产生有效的作用。
(二)实验结论指导下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设计规则研究
综合实验结果,本研究提炼出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设计规则,为在线学习中设计并使用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提供参考与借鉴。
1. 面向自主操作性支架的设计规则研究
实验结论显示,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深度学习的影响效果高于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因此,建议在在线深度学习的目标与需求下优先使用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在设计基于自主操作型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时,教育者应创造相对自由的计划调节学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要,将满足计划调节学习需求的交互与控制的权限还给学习者,学习者通过个性化导航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路径以及学习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有效促进深度学习。
在实践中应用设计规则设计自主性调节学习支架,旨在帮助学习者根据自身的认知习惯、方式和兴趣等对学习内容进行深度加工。例如:整合网络学习空间和学习支架的面向深度学习的翻转课堂模型[29],课前提供学习活动安排与学习支架,有助于学习者明确学习方向,支持学习者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更有利于建立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构建完整且连贯的知识体系,这是实现深度学习的重要保障。
2. 指向深度学习目标的支架设计规则研究
实验研究中,深度学习三个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学习目标,深度学习基础阶段对应的学习目标是深度理解,深度学习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对应的高阶学习目标是迁移、问题解决和创新。指向不同的深度学习目标,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尤其是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中的任务型支架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任务型支架中的学习任务可以为学习者提供计划提示,帮助学习者明确要想实现下一步学习目标自己需要做什么,以及按照怎样的先后顺序去做。学习任务是实现学习目标的载体,是学习新知、提高迁移创新能力的良好驱动。将任务融入各个知识节点中,在由学习者自主选择或系统协助选择学习路径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帮助学习者实现深度学习目标。
在对学习内容分析与加工的基础上,指向深度学习高阶学习目标的任务型学习支架帮助学习者分解学习目标,明确需要做哪些事情。不同层次的具体学习任务作为“抓手”帮助学习者不断向高阶学习目标趋近[30]。实验研究中,虽然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对在线深度学习显示出最优的促进效果,但引导性监控調节学习支架相较于无支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在线深度学习。因此,在某种特殊条件限制下,采用引导性监控调节学习支架也可以起到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作用。例如:基于OERs的自主学习环境,通过设置学习支架,帮助学习者设置阶段性目标,降低任务难度,提升任务可操作性[31];系统为学习者自主学习提供目标并辅助学习者分解任务,当学习者明确学习内容及其要达到的程度,将会激励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学习的效果[32]。
3. 基于实验材料的支架设计规则研究
实验材料中知识地图展现知识节点的支架能够帮助学习者进行计划调节,实现深度学习。知识地图是计划调节学习支架最主要的表征方式之一,为学习者提供知识地图、概念地图与流程图等概念型支架,帮助学习者分析问题、厘清脉络,引导学习者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33]。可视化工具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关系进行外显化映射,尤其为信息迷航的学习者提供有效的导航支持和指引,因此,可视化工具多被用于呈现知识主题节点及节点间的逻辑关系,帮助学习者厘清知识脉络,激活深度学习脑区,提升深度学习效果。知识地图方式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本质在于依托知识图谱生成学习路径[34],学习者根据自身学习需求及兴趣确定学习目标,是自由规划最优化的学习路径的前提。在这类支架的设计中,需要根据知识点属性特征、学习对象属性特征与学习者知识掌握情况等对知识点与学习对象进行序列化。
实验材料中自主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设计采用“部分向导”型设计,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知识节点,但由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路径;引导性计划调节学习支架设计为“完全向导”型,即由在线学习系统决策学习者的学习路径规划范围,通过“向导”指引的方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学习规划。“向导”也可称为指南,将问题、建议等片段性支架根据学习主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组合、排列,形成流程图或学习向导,此时向导支架作引导和解释,按步骤给予学习者系统性的指导,帮助学习者制定具体的计划。向导支架将一个较复杂的、周期较长的学习目标进行细化,使学习者能分组块、分阶段、分层次地完成任务。相比于逻辑性更强的知识地图,“向导”更关注整体性较强的绩效。在设计基于“向导”的计划调节支架时强调“动态性”,即根据学习者完成学习目标情况,适时、动态修改向导内容。例如:基于物联网手机App模式的智能化虚拟课堂平台[35],通过诊断学习情况,调整向导内容,支持学习者规划学习方案,提升学习效果。
本研究从理论层面论证了计划调节学习支架促进深度学习的作用机制,从实证角度挖掘了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影响深度学习的内在机制,提炼了在线学习中面向深度学习的计划调节学习支架的设计规则,为教育者运用计划调节学习支架开展在线深度学习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 翟雪松,楚肖燕,李艳.融合视觉健康的在线学习环境设计原则与技术路径[J].现代教育技术,2021,31(12):12-19.
[2] 杨晓宏,周海军,郑新.疫情期间高校在线教学实施特征与启示——基于在线教学质量报告和在线教学案例的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10):48-53,62.
[3] 张家军,韦敏.自主学习视域下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力的现实样态及提升策略研究[J].教学研究,2021,44(6):23-33.
[4] 吴亚婕.影响学习者在线深度学习的因素及其测量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7,38(9):57-63.
[5] DELEN E, LIEW J, WILLSON V. Effects of interactivity and 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 on learning: self-regulation in online video-based environment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4, 78: 312-320.
[6] ZHENG L.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omputer-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a meta-analysis[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16, 17(2): 187-202.
[7] 乔爱玲,龚鑫,韩涵.形式差异的外部概念支架对学生游戏化学习心流和效果的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12):86-92,99.
[8] 李士平,赵蔚,刘红霞,谭荣姣,赵艳.基于知识地图的自我导向学习设计与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5):74-81.
[9] 陈敏,余胜泉.泛在学习环境下感知学习过程情境的推荐系统设计[J].电化教育研究,2015,36(4): 76-82,89.
[10] 郝晓鑫.基于媒体交互的自我调节对深度学习的影响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9.
[11] 刘哲雨,侯岸泽,王志军.多媒体画面语言表征目标促进深度学习[J].电化教育研究,2017,38(3):18-23.
[12] 刘哲雨,景爽,胡梦琪.基于深度学习核心要素的评课研究[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8,30(2):45-50.
[13] 邓国民,徐新斐,朱永海.混合学习环境下学习者的在线自我调节学习潜在剖面分析及行为过程挖掘[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1):80-86.
[14] 崔亚萌.认知神经科学视域下学习机制的初步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7.
[15] 田媛,亓栀,黄湘琳,向虹钰,汪颖.社会线索促进在线学习的认知神经机制[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2):63-69.
[16] HALL M, CHAUDHARY U, REY G, et al. Fronto-temporal mapping and connectivity using NIRS for language-related paradigms[J].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2013, 26(1): 178-194.
[17] 刘哲雨,郝晓鑫.深度学习的评价模式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7,27(4):12-18.
[18] 刘哲雨,郝晓鑫,王红,吴立宝.学习科学视角下深度学习的多模态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8,28(3):12-18.
[19] 马云飞,郑旭东,赵冉,刘慧.深度学习的发生机制与多模态数据测评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22,40(1):50-60.
[20] PINTRICH P R, SMITH D A F, TERESA D, et al. A manual for the use of the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MSLQ)[M]. USA: 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1991: 13-14.
[21] 李士平.网络学习环境下基于反馈的元认知干预设计与实证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8.
[22] 肖武云.元认知与外语学习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13-92.
[23] DIGNATH C, BUETTNER G, LANGFELDT H P. How c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most effectively?: a meta-analysis on self-regulation training programmes[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08, 3(2): 101-129.
[24] BOEKAERTS M, NIEMIVIRTA M.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learning goals and ego-protective goals[M]//BOEKAERTS M, PINTRICH P R, ZEIDNER M. 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0: 417-450.
[25] MANLOVE S, LAZONDER A W, DE JONG T. Software scaffolds to promote regulation during scientific inquiry learning[J]. Metacognition and learning, 2007, 2(2): 141-155.
[26] 王穗蘋,黄健.句子理解中的语义加工回路——研究热点与未来的展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47-55,158.
[27] KROGER J K, SABB F W, FALES C L, et al. Recruitment of anterior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 human reasoning: a parametric study of relational complexity[J]. Cerebral cortex, 2002, 12(5): 477-485.
[28] FLAHERTY A W. Frontotemporal and dopaminergic control of idea generation and creative driv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2010, 493(1):147-153.
[29] 姚巧红,修誉晏,李玉斌,陈小格.整合网络学习空间和学习支架的翻转课堂研究——面向深度学习的设计与实践[J].中国远程教育,2018(11):25-33.
[30] 张丽霞,商蕾杰.虚拟课堂学习支架的类型及功能[J].中国电化教育,2011(4):27-31.
[31] 邓国民,韩锡斌,杨娟.基于OERs的自我调节学习行为对学习成效的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3):42-49,58.
[32] 王民艺,吴毅坚,赵文耘.自主学习任务的导航和自动创建方法研究[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4,31(12):33-38,88.
[33] 潘星竹,姜强,黄丽,赵蔚,王利思.“支架+”STEM教学模式设计及实践研究——面向高阶思维能力培养[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9(3):56-64.
[34] 高嘉骐,刘千慧,黄文彬.基于知识图谱的学习路径自动生成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1,31(7):88-96.
[35] 汪萍,余成发,张鹏.基于物联网手机APP模式的智能化虚拟课堂平台设计[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7,33(4):58-60,78.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on Online Deep Learning
LIU Zheyu1, LIU Chang1, XU Boyu2
(1.Faculty of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2.The School Affiliated to Luhe High School, Beijing 101100)
[Abstract] Online learning scaffold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learners' plan regulation, plan learning tasks, guide learning behaviors, and facilitate online deep learning. However, the existing design of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has relied more on experienc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design rules based on brain processing mechanisms. This study uses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to dynamically track the activation of brain regions in deep learning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on online deep learning. A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scaffolding on deep learning.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both types of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facilitate the activation of brain regions in deep learning processes in the basic, early, and late stages of deep learning, and both autonomous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deep learning outcomes, suggesting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preferentially use autonomous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for online deep learning. Additionally, the activation of brain regions in all three stages of deep learning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ep learning outcomes, which reveals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could judg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online deep learning occurs based on the activation of brain reg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the design rules and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of the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are proposed.
[Keywords] Plan-regulated Learning Scaffolds; Online Deep Learning; fNIRS; Design Rules
基金項目: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自我调节支架促进在线深度学习:基于多模态技术的脑机制研究与支架设计模型研究”(项目编号:61907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