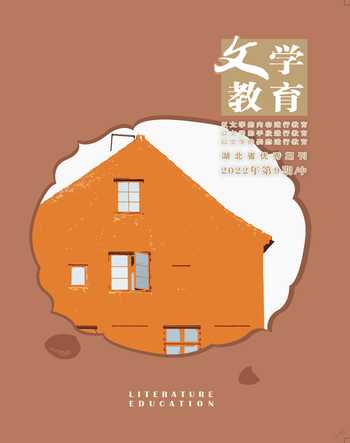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喜福会》中的母亲形象
廖珊珊
内容摘要:美华裔作家谭恩美小说《喜福会》是美籍华裔文学的经典作之一,它描述了吴素云,龚琳达,许安梅,顾映映四位女性美裔华人的故事,体现了不同华裔母亲的形象。本文以四位母亲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受男权压迫的母亲,觉醒与反抗的母亲,拥有自我意识的母亲三个角度的母亲形象。理清母亲们在不同时代遭受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并且为改变自身命运从沉默走向觉醒和反抗并重获自我意识的过程,展示了母亲们独立,坚强,智慧的优秀品质和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精神,并由此呼吁人们尊重女性和尊重女性追求自由的权利,有利于在全社会弘扬女性角色重要性的精神。
关键词:《喜福会》 女性主义角度 母亲形象 分析
女性主义被称为妇女解放、性别平等。女性主义的概念基础是现实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制。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提到,女性并非生而弱小,而是天生的,女性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吴珊珊,2016:167)。美华裔作家谭恩美《喜福会》仿佛是一部女性宣言,讲述了四位华裔母亲和女儿们的故事,展现了母亲们对父权压迫的觉醒和反抗。在喜福会中,细腻又坚强的母亲形象被刻画的淋漓尽致。因此,通过对四位母亲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的分析,以揭示这些深陷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禁锢的中国传统女性是如何追求自己的主体地位。此外,通过对母亲形象的分析,可以理解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尤其是女性主义内涵和女性的根本精神。同时,可以唤起人们尊重女性和追求幸福权利的意识。
《喜福会》通过讲述四位母亲的故事来体现女性主义精神。而母亲们不同的经历也描绘出不同的母亲形象。在中国的旧社会,父权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处于男性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意志、思想,甚至自己的生命。因为几千年来受封建制度的影响,女性几乎将自己视为男性的财产。他们缺乏反抗的意识,连反抗男性的命令都不敢,更别说反抗的念头了。于是,当母亲们留在中国时,她们就沦为沉默的奴隶,逐渐迷失了自我。谭恩美赋予了她们反抗的精神,也就是说,这些妈妈们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她们的女性精神。
因此,本文运用女性主义视角,从受父权压迫的母亲、觉醒与反抗的母亲、拥有自我意识的母亲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详细分析。
一.受父权压迫的母亲
传统中国是男权社会,掌握绝对权利的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使女性在经济和心理上无法独立(邢兰娟,2015:21)。吴素云、龚琳达、许安梅和顾映映四位妈妈在去美国之前都有过各自的悲惨经历。她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父权压迫,包括家庭不幸,婚姻不幸福,饱受战争的磨难等。
在中國,吴素云拥有一个和谐富裕的家庭。她的丈夫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尊严的男人。然而,正是因为丈夫的强势地位,使得吴素云缺乏自我意识,对他无限服从。她在桂林的时候,总是无所事事。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几个女人一起打麻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她在丈夫有力的怀抱中的无力和无助。战争打破了她平静舒适的生活,使她成为无家可归的女人。从桂林到重庆的路上,她经历了危险而艰难的处境。更糟糕的是,她身患重病,怕养不起双胞胎女儿,只好把她们放在路边,希望好心人收养这对双胞胎。后来虽然她获救了,但是却与女儿们分开了,丈夫也死于战争。那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变得一无所有。
龚琳达两岁的时候,就被父母许配给了还是襁褓中的黄天余。后来,她的家被洪水淹没了,家人们不得不搬到南方。她就被送到了黄家,在那里她不得不忍受婆婆的责骂、年轻丈夫的戏弄和繁琐的家务。她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为黄家生儿育女,恪守三从四德。在父权的压迫下,她意识到自己在黄家的地位。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会做一个贤惠孝顺的妻子,比如做美味的菜肴,做精致的针线活,把丈夫奉为上帝。她不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生活,不是真的。她想,没有什么会比看到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掉她准备的蘑菇和竹笋更幸福了。有什么比给黄太太梳完一百下头,还拍拍她的头还更满足的呢?看到天余吃完一整碗面条,从来不抱怨它的味道,她非常满足于现状。琳达是家庭中男性至上的父权制度的践行者,她视其为最高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将自己置于从属地位。至此,她完全满足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同时也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李升炜,2011:99)。
许安梅的人生经历与她母亲的经历息息相关。安梅和弟弟是在外祖母家长大的。父亲在她非常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被富商吴清强暴,成为了四姨太。从此,安梅的母亲被赶出家门,与许家断绝了关系。外祖母告诉安梅不要提起她母亲的名字,因为说她的名字等同于向她父亲的坟墓吐口水。即便是在外祖母临终的时,安梅的妈妈把自己的肉割下来做药引来为其治病,她还是没能得到宽恕。舅舅和舅妈仍然对她说强硬的话。“别看那个女人”,舅妈警告安梅。“她把脸扔到溪流里。她的祖灵永远消失了。你看到的人,只是腐烂的肉体,邪恶的,腐烂的骨头(谭恩美,1989:216)。”虽然小说中对吴清的描写不多,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和安梅的母亲并不是恩爱夫妻,而是主从关系。身为吴家四姨太,饱受歧视和屈辱。对吴清来说,女人只是附属物,身边的女人都听他的,千方百计讨好他。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男主是主子,靠男人生存的女人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从安梅母亲的悲惨故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深受父权制的压迫,没有任何合理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
顾映映出生在中国无锡的一个富裕家庭。她本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然而,保守的家庭教育压制了她天性中的自由和活泼,试图让她成为一个能够满足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要求的女性。她的母亲告诉她“男孩可以跑来跑去和追蜻蜓,因为这是他的本性”,“但女孩应该文静点(谭恩美,1989:72)。”映映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她从小姑那里得知,丈夫已经离开她和一个歌剧演员一起生活。小姑还告诉她丈夫还出轨过其他人,比如美国女人,舞者,妓女,甚至比她年轻的表妹。然而,在“三从四德”的影响下,面对不幸的婚姻,她选择了沉默。她的丈夫如此残酷地折磨她,以至于她逐渐崩溃了。她变成像湖中的女人,湖底的女鬼,失去了力量。
二.觉醒和反抗的母亲
逃避和沉默是无用的。女性要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喜福会》中,在父权压迫下被动麻木的母亲开始转变为坚强的女性,通过自己的觉醒和反抗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凸显了强烈的女性主义精神。在中国,吴素云失去了一切,父母、双胞胎女儿、丈夫。也就是说,她不再是一个窝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娇生惯养的富太太了。她失去了她强壮的手臂,她的丈夫。然而,无家可归但并非没有希望的素云去了美国,她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任何人想成为的人。在美国,她认为一个人人都可以开一家餐馆,一个人可以为政府工作并获得良好的退休生活;可以不用付首付买房子;一个人可以变得富有,并立即成名。在美国,她遇到了同样经历的女性,并把她们召集在一起,举办了一场名为“喜福会”的聚会,对于这些经历过悲惨经历的女性来说,这不仅是她们心灵的港湾,也帮助她们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与黄天余结婚后,龚琳达在婆婆的指导下,学会了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但琳达没能讨好婆婆,因为她生不出孙子。婆婆责骂她。琳达逐渐受不了,开始思考如何不违背对家人的承诺,逃出这段婚姻(谭恩美,1989:63)。她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三月初三,清明节那天,大家都去祠堂祭祀。她用三个征兆让婆婆相信她儿子的婚姻是错误的。第一个征兆,天余的祖父在他的背上画了一个黑点,会长大,吃掉他的肉,直到他死去;第二个征兆,爷爷说琳达牙齿会一颗一颗地掉下来,直到她无法再抗议他们的婚姻;第三个征兆,爷爷在丫鬟的肚子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可以长成天余的孩子。迷信的婆婆相信了她的“谎言”。最终琳达摆脱了与天余的婚姻,成功逃离了黄家。龚琳达敢于摆脱不幸婚姻的桎梏,展现了她固执、聪明的个性。女性意识的觉醒,让她反抗封建社会,找回自我。“我对自己做了一个承诺:我会永远记住父母的愿望,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谭恩美,1989:58)。”龚琳达勇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观,这表明了新思想的觉醒。
安梅的外祖母去世后,她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吴清家。直到那个时候,她才知道,母亲过得并不好。吴清正妻将安梅母亲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她可怜的母亲用自己的死亡换取了吴清的承诺。她选择了农历新年前三天,吃了包鸦片的汤圆自杀。于是,那一天,也就是母亲去世的第三天,吴清答应了,他会把她和弟弟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来抚养。他承诺将她正妻的名分写入族谱。安梅母亲的自杀也是为了反抗父权社会,逃避命运的压迫。虽然她对女权意识的表现与小说中其他母亲不同,但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为地位而死,也算是一种女性觉醒和反抗的大胆行为。
顾映映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伪君子。面对出轨的丈夫,她选择了忍气吞声和沉默。而丈夫却还在继续折磨她,这让她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她知道自己怀孕了,她选择了堕胎。在那个年代,没有后代是一种巨大的愧疚。因此,这种行为似乎是对她丈夫的一种惩罚。然后她离开婆家,回到了自己的家。至此,她以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不幸的婚姻。堕胎行为是对父权社会男性的强烈攻击,也是对父权的不满宣言。她告诉世人,女人不是男人可以随意玩弄或抛弃的玩物,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我价值。
三.拥有自我意识的母亲
自我意识又称“自我”,在人格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在旧中国,不得不遵守迂腐社会规范的华裔美国母亲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母亲们是第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虽然她们在美国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仍然无法融入新的世界。她们说着蹩脚的英语,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按照中国的观念教育孩子。所以,文化和语言的异化往往使他们处于失落的状态。他们渴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但在强烈的文化冲击下逐渐失去了“自我”(张柯玮、张弛,2020:4)。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過去的苦难。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寻找文化认同感。他们的苦难反映了他们的生存本能,帮助他们重建了自我意识。
吴素云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女儿和丈夫,也就是说,她失去了女儿、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于是,她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份危机。痛苦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的身份正在崩溃,于是她踏入了新的土地,以美丽的眼光重新创造了新的自我身份的美国。在美国,她的小女儿吴精美出生了。从此,素云把希望寄托给了女儿,甚至试图将自己的身份强加给她。素云一个朋友告诉她,她和母亲很像,都有同样纤细的手和手势,同样少女的笑声和表情。素云从小就将美国文化的特点灌输给女儿,使她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因为素云知道,自我认同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创造的。
摆脱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后,龚琳达来到美国旧金山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她在糖果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并且认识了另一位中国妈妈安梅。琳达在她的帮助下结识了龚丁。这是琳达第一次有权做出决定。因为,在美国,女人可以选择她想嫁的丈夫。受女权运动的影响,琳达最终决定向龚丁敞开心扉并与他约会。龚丁是一个风趣又痴情的男人,经常在中国戏剧中假装演员取悦琳达,同时表现出对琳达的深爱。琳达感受到了她第一次婚姻从未有过的甜蜜爱情。最终,她抓住了婚姻的主动权,如愿得到了幸福的婚姻。正如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暗示的那样,女性有足够的思想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尊重父母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服从(徐莎莎,2017:41)。琳达明白自己是一个女人,有任何权利做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不能被随意扔掉,这体现了她追求自由权利的女性意识。
安梅的母亲利用丈夫吴清的迷信自杀,以挽救和交换女儿未来的美好生活,同时她的死也让安梅知道了反抗的力量。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大年初一,她当着二姨太的面把假珍珠项链踩碎;那天,她学会了为自己呐喊。然而安梅的懦弱无形中影响了女儿罗斯。所以,当罗斯的婚姻陷入困境时,她既没有试图解决,也没有为自己挺身而出。她甚至相信那是她的宿命。于是,看到女儿的婚姻每况愈下,安梅反省自己,决定把自己和母亲的故事告诉女儿。她告诉罗斯,温顺地接受屈辱是过去女性的唯一选择,但现在女性不需要那样生活了。她还告诉罗斯,冲突是她的沉默造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丈夫说不。最终,罗斯勇敢地对丈夫说“不”,为自己的权利争取走出婚姻危机。安梅在母亲去世后学会了为自己呐喊,这让我们看到了安梅的觉醒。并且她还告诉女儿不要沉默,要勇于反抗。
顾映映摆脱了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后,去上海做售货员。在上海她遇到了克莱尔,克莱尔很快喜欢上了映映,然后开始长达四年的追求,至此,映映开始有了对爱情的向往,内心深处的冰冷被暖化了。最后,映映接受了他的求婚,与他结婚。从此,他们去了美国,映映成为了美国人的妻子,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显然,映映是这段感情的主导者,她可以在第二次婚姻中做出决定。第一次婚姻给她带来了刻骨铭心的伤痛,让她似乎久久没有精神。克莱尔不断的耐心和陪伴最终使她摆脱了抑郁症。她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永远告别了过去,这表明她开始为自己而活。
总之,《喜福会》关注母亲们及其复杂的命运。通过对母亲的坎坷经历和命运的描写,不甘沉默、勇于战斗的母亲形象在本书中栩栩如生。四位母亲展现了中国女性的新形象,睿智、独立、坚韧、乐观、善良、能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母亲的智慧,是中国母亲的缩影。此外,女性主义思想是《喜福会》的突出特点。谭恩美以美国华裔女性的独特视角,通过塑造几千年来受封建文化压迫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和生活在美国的现代女性形象,揭示了隐秘而长期的父权制。经历了惨痛的苦难,四位母亲开始觉醒,然后踏上了反抗的道路,逐渐有了自我意识。失去一切后,吴素云仍怀着美好的人生愿景,远赴美国重新塑造自己的新身份,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执着的母亲;龚琳达巧妙地挣脱了婚姻的枷锁;母亲去世后,安梅开始为自己呐喊,并教导女儿罗斯为应有的权利而战;顾映映从不幸的婚姻中逃脱,自己选择了第二段婚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喜福会》中的妈妈形象是乐观的、聪明的、坚强的、能干的、善良的等等。对被压迫母亲开始觉醒、反抗和持有自我意识的描述,是呼吁人们尊重女性,尊重她們追求幸福的权利,有利于在全社会弘扬重视女性作用的精神。
参考文献
[1]Amy Tan. 1989. The Joy Luck Club.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李升炜.2011.从《喜福会》中的母亲形象解读女性主义[J].西安社会科学(04):99-100+120.
[3]吴珊珊.2016.女性的觉醒和独立——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喜福会》解读[J].海外英语(21):167-168+171.
[4]徐莎莎.2017.《喜福会》中华裔母亲文化身份的重构[D].宁波大学.
[5]邢兰娟.2015.论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D].山东师范大学.
[6]张柯玮,张弛.2020.《喜福会》中身份建构的生态女性主义意义[J].英语广场(下旬刊)(4):3-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